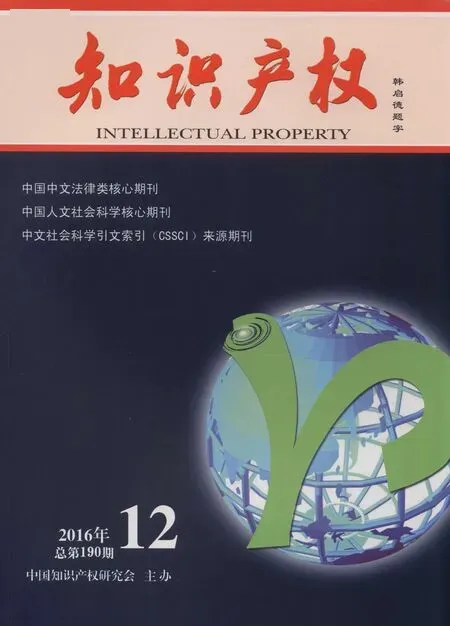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的变革与重构
2016-02-13刘晓军
刘晓军
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的变革与重构
刘晓军
我国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在确立之初曾掀起了适用高潮,但其适用现状不容乐观,总体来看其预期作用并未能得到充分展示。制度设立具有的或多或少的被动性及指导思想的理想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诉前禁令适用的混乱状况。当前知识产权制度仍处于持续变革中,层出不穷的技术创新对既有知识产权制度形成了较大冲击,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仍有可能扩充,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的变革与重构已经迫在眉睫。知识产权诉前禁令要树立“效率优先”的理念,减轻申请人的证明义务和法院的审查责任,重构担保与反担保制度,将是否作出诉前禁令与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密切联系起来,让当事人的意志与利益在诉前禁令制度中发挥一定的作用,积极扩展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适用的新空间,适当兼顾对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利益的平衡保护。
知识产权诉前禁令 担保与反担保 效率优先
一、知识产权诉前禁令的起源与发展
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在我国又称为诉前停止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主要可分为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诉前停止侵犯商标权行为和诉前停止侵犯著作权行为。知识产权诉前禁令是指“为及时制止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的侵害权利人知识产权或有侵害之虞的行为,而在当事人起诉前根据其申请发布的一种禁止行为人从事某种行为的强制性命令。”a韩天岚:《知识产权诉讼中诉前禁令的适用》,载《电子知识产权》2004年第4期。知识产权诉前禁令最显著的特征是诉前性,即禁令申请、审查、裁定及执行都发生在权利人提起侵权诉讼之前。
从诉前禁令的起源上看,当改革开放行进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积极寻求加入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时,就为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的引进埋下了伏笔。我国于1984年加入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10条规定,对于“非法带有商标或厂商名称”、“假冒原产地和生产者标记”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侵权行为,各成员有保证权利人采取适当的法律补救措施以有效制止侵权行为的义务。我国于1992年正式加入的《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第36条规定,各成员有义务采取必要措施来制止侵权行为以保护作者对其作品所享有的权利。一般认为,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属于上述两个国际公约规定的“适当的法律补救措施”和“必要措施”。随后,在历经20世纪末期多轮谈判等诸多波折后,我国在21世纪初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最重要的法律文件之一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下简称《TRIPS协定》)第50条规定,权利人为保护其权利而采取的临时措施包括临时禁令、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其中临时禁令包括诉前禁令和诉中禁令。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几部主要的知识产权法律都作了较大的适应性修改,其中一个重大修改就是规定诉前停止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制度,也就是《TRIPS协定》第50条规定的“诉前禁令”。诉前禁令的引进和确立首先是从专利法的修正开始的。2000年8月第二次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61条第1款规定:“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其专利权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的措施。”显然,上述规定在确立诉前禁令的同时,赋予了申请人较重的举证义务,如其至少需要“有证据证明”存在或可能存在“侵犯其专利权的行为”,且该行为会致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
专利法中确立的诉前禁令制度迅速扩展到随后修正的商标法、著作权法领域。2001年10月同时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57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49条均规定了诉前禁令制度,2001年12月修改后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26条也增加规定了诉前禁令制度,并被统称为诉前停止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其中有关诉前禁令适用要件及申请人证明义务的规定基本上是一致的,其共同点是均赋予申请人较重的证明责任且适用要件较为严苛。随后,2008年再次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及2013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虽然在法律条文序号上作了变动,但有关诉前禁令的条文内容基本没有变动。同时,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制定了《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关于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和保全证据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司法解释,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规定的诉前禁令制度作了进一步的细化,明确了诉前禁令的管辖、案件编号、申请主体、申请人条件、证据、担保、审查、裁定、复议、执行及收费等内容,大大增强了诉前禁令制度的可操作性。
需要指出的是,2012年8月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简称2012年《民事诉讼法》)在总结知识产权法中诉前禁令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诉前禁令扩展到了与侵权法相关的民事诉讼领域,其中第101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前向被保全财产所在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申请人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三十日内不依法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保全。”从实践来看,虽然诉前禁令制度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在家暴纠纷中已经发挥作用了,但总体来说如何在传统侵权法领域充分发挥诉前禁令的威力还有待观察,而且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并未完全克服知识产权领域诉前禁令制度适用的某些弊端。
二、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适用的现状与反思
诉前禁令制度在我国知识产权法中确立之初,某些地方法院曾在一段时期内掀起了适用诉前禁令制度的小高潮。在2006年9月重庆召开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研讨会上,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曹建明指出,自三部主要知识产权法律修订以来,全国地方法院共受理诉前禁令案件300多件,在申请人坚持申请的案件中,实际裁定诉前禁令的支持率达到88%。一些地方法院在适用诉前禁令过程中不断总结审判经验,先后制定了在知识产权领域适用诉前禁令制度的具体实施办法。但随着新一轮知识产权法的修改和实施,诉前禁令制度的司法适用开始降温并转为不温不火的状态。当前,在对知识产权实行最严格保护的政策环境下,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似乎又有可能迎来新的适用高潮,但如果不对一段时期以来的诉前禁令度适用状况进行反思,对其适用前景仍不宜盲目乐观。可以说,我国的诉前禁令制度具有较多的先天不足,导致了当前的制度适用困境。
首先,我国的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迎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而制定的,具有或多或少的被动性,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诉前禁令制度的适用热情。《TRIPS协定》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框架的三大支柱之一,我们只有接受它才能走进WTO的魅力世界,才能享受贸易自由化的盛果。在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经历的诸多艰苦卓绝的谈判中,知识产权领域的谈判是最为重要和艰苦的环节之一。虽然当时已经有了二十年左右的改革开放历程,但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夕的20世纪末期,无论是对知识产权的本质还是对知识产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当时的认识都是不够充分的,与《TRIPS协定》的规定具有一定差距。例如,《TRIPS协定》开宗明义就规定了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但时至今日在我国仍未对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形成普遍共识,知识产权立法及实践中无视知识产权私权属性的现象仍十分普遍。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仍有不少人认为知识产权主要是保护发达国家的利益,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此,我们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作了一些保留,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至今仍未得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承认。这些保留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一个体现就是,《TRIPS协定》所规定的内容是WTO成员必须采取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最低标准,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原则上只要达到《TRIPS协定》规定的最低保护标准即可。相应地,既然《TRIPS协定》第50条规定了诉前禁令,国内的知识产权法当然要做相应的适应性修改,但同时诉前禁令制度又存在诸多不足。“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故知识产权诉前禁令近年来进入适用困境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对公正与效率的精致追求严重窒息了诉前禁令的适用空间。公正与效率是司法的生命线,司法审判当然可以追求兼顾公正与效率的理想状态,但公正与效率概念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调和性,并同每个人的个体感受息息相关。知识产权诉前禁令虽然也要追求公正与效率的兼顾,但诉前禁令制度自身的性质决定了这种兼顾要求的高难度。例如,从法律规定来看,适用诉前禁令的前提是客观的侵权情况或者可能的侵权状况已经相当严重和紧急了,如果不发出诉前禁令就无法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这就要求诉前禁令必须尽快作出,体现了对司法效率的追求。但是,同样的法律还规定发出诉前禁令必须以申请人合法权益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害为适用要件,并强调了申请人指控的侵权行为必须具有成为侵权行为的可能性,这体现了制度设计对公正的要求。侵权可能性也称为胜诉可能性,是指诉前禁令的申请人在随后提起的侵权诉讼中有多大可能性获得胜诉,其主要取决于诉前禁令针对的行为在多大可能上构成侵权。难以弥补的损害往往是以侵权必然性而不是侵权可能性为前提,且无论是难以弥补的损害还是侵权可能性或侵权必然性的审查,几乎都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做出准确的审查结论。如果不允许法官发出事后证明是错误的诉前禁令,则对侵权可能性及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审查必然牺牲诉前禁令制度的效率优势;但如果允许法官发出事后证明是错误的诉前禁令,则又难以避免诉前禁令可能遭受的滥用。虽然在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中适当平衡对公正与效率的追求完全是正当的和必要的,但这种平衡不应当以牺牲诉前禁令制度本身为代价。诉前禁令最大的优势是对效率而不是公正的追求,其更多体现的是效率最大化前提下的公正追求,应当寻求的是更为恰当和精致的制度平衡,而不是仅仅在公正与效率之间做无谓的空洞摇摆。
再次,指导思想的理想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前诉前禁令适用的混乱现状。诉前禁令制度确立以来,一些学者就呼吁“积极慎重”“应当成为办理诉前停止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案件特有的基本原则”,b王伯文:《知识产权法中诉前临时措施的原则及其理解与适用》,载《知识产权》2002年第4期。事实上“积极慎重”随后也确实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的指导思想或基本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在2003年答复常州华生制药有限公司与(美国)伊莱利利公司专利侵权指定管辖请示案中指出:“采取诉前责令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涉及双方当事人重大经济利益,既要积极又要慎重,要重点判断被申请人构成侵权的可能性。”在2008年2月19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上,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曹建明要求各级法院“积极慎重地适用诉前证据保全、诉前财产保全、诉前禁令等临时性司法措施,及时有效保障权利人权益”。一般认为,积极是指受理案件要积极,审查要迅速,采取措施要及时;慎重是指对申请的审查要仔细,程序要合法,采取的措施要适当,避免适用措施不当而损害被申请人的利益。虽然积极慎重的指导思想体现了最高司法机关的良苦用心,既要促进诉前禁令的依法积极适用,又要防止其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可能滥用,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对“公正和效率”的兼顾追求。“积极慎重”体现了矛盾的对立统一定律,在面对新制度适用中的首例诱惑及其比较严苛的适用要件和证明责任时,看似矛盾的“积极”和“慎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诉前禁令适用实践中的“冰火两重天”:一方面,一些法院积极有余,大量适用诉前禁令,虽然有效制止了一部分侵权现象,但诉前禁令制度被滥用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另一方面,一些法院着力于慎重,极少适用诉前禁令,虽有效地避免了诉前禁令制度被滥用的可能性,但也可能被误解为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积极慎重”的指导思想固然高大上,但要求在极短时间内作出的诉前禁令能够兼顾“积极”与“慎重”体现的是对裁判者“神一般”的期望和要求,而制度设计的先天缺陷及对法官可能错误的严苛追责又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其适用空间。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在2009年4月发布的《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条规定:“特别是在专利侵权案件中,如果被申请人的行为不构成字面侵权,其行为还需要经进一步审理进行比较复杂的技术对比才能作出判定时,不宜裁定责令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在被申请人依法已经另案提出确认不侵权诉讼或者已就涉案专利提出无效宣告请求的情况下,要对被申请人主张的事实和理由进行审查,慎重裁定采取有关措施。根据案件进展情况,注意依法适时解除诉前停止侵权裁定。”由此可见,至少在专利案件中诉前禁令的适用似乎已经是慎重优先了。
最后,不够完善的法治环境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诉前禁令的适用。曾几何时,“案结事了”、“调解优先”成为司法工作的重要目标,有时甚至忽视了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感受。例如著名的“彭宇”案虽然实现了对当事人的案结事了,却掀起了社会舆论的滔滔浪潮,引发了全社会对司法工作的极大误解。在过度追求“案结事了”的司法环境下,要在极为有限的时间内正确认定“侵权可能性”、“不可弥补的损害”并发出诉前禁令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一旦因对侵权可能性等实用要件的认定失误发出了诉前禁令,法官就可能被拖入无穷无尽的上访信访程序中。与其冒着巨大风险发出诉前禁令,倒不如系用几乎是零风险的拒绝适用诉前禁令。由此,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的适用必然逐步萎缩,而法官在适用诉前禁令上畏手畏脚,又必然严重打击权利人申请诉前禁令的热情,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导致了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适用高潮后迅速落入低谷。当然,应当看到当前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的改革理念也渐入人心,“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正在成为共同的价值追求。法治环境的逐渐改善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适用的逐步回归。例如,北京法院也在2016年年中的时候,针对“中国好声音”、“The Voice of China”字样的节目名称及相关注册商标发出了诉前禁令,并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
三、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适用的困境与成因
我国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在确立初期,确实在部分法院掀起了适用高潮,不仅出现了大量的诉前禁令申请,而且其实际获得的支持率也极为乐观。但“欢乐总是短暂的”,知识产权诉前禁令的司法实践很快就停滞不前了,甚至沦为不温不火的“鸡肋”困境,同制度设计者当初设想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尽管造成其适用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自身的缺陷可能更为致命,也更值得探讨和反思。
首先,诉前禁令制度的适用要件设置不当。目前诉前禁令的适用要件大致可以分为程序要件、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程序要件如管辖要件,形式要件如申请人资格证明等,实质要件如情况紧急、侵权可能性、难以弥补的损害、担保等。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对诉前禁令的诸多适用要件进行审查,而且这种审查几乎要达到实质审查的程度,明显是不恰当的。要进一步实施诉前禁令,就必须重新合理构建禁令制度,简化诉前禁令的适用要件,删除一些不必要甚至阻碍诉前禁令适用的要件,减轻法官的审查责任,将一些重大事项尽量交由当事人决定,并将是否作出诉前禁令与当事人的利益关联。
其次,对侵权可能性的审查并不具有实质意义。目前对知识产权诉前禁令的申请都需要判断侵权可能性。可能性是指事件发生的概率,而概率是指某个事件发生可能性大小的数值。如果“不可能”可以用“0”来表示,“肯定能”可以用“1”来表示,则“可能”可以用分数或百分数来表示它的大小。必然事件的可能性为100%,不可能事件的可能性为0%,但可能性为100%的事件并不一定是必然事件,可能性为0%的事件并不一定是不可能事件。当然,可能性如果超过50%,一般说可能性较大,可能性低于50%,一般说可能性较小。因此,侵权可能性的判断只是对申请人指控的疑似侵权行为是否确定构成侵权或不侵权的概率判断。一般说来,绝大多数申请诉前禁令指控的侵权行为,都有被最终确定为侵权行为的可能性,但即便这种可能性为100%,也不意味着被申请行为必然构成侵权,同样,即便这种可能性为0,也并不意味着被申请行为必然不构成侵权。从这个意义上讲,侵权可能性的审查更应该是一种形式审查,而且申请诉前禁令行为自身就可以证明这种侵权可能性。但这似乎不是有关诉前禁令法律规定的本意,因为侵权可能性更多地被作为诉前禁令制度的核心审查要件,并且司法实践中又衍生出侵权较大可能性的判断。如果不从可能性的本质含义上去理解诉前禁令制度中有关侵权可能性的规定,而试图量化侵权可能性的数值范围,基本上不具有实际操作性,且即便侵权可能性可以数值量化,存在侵权较大可能性,甚至100%侵权可能性的被申请行为,也不可能完全排除其不构成侵权的可能性。事实上,在终审判决确定是否侵权之前,诉前禁令所指控的疑似侵权行为都存在侵权或不侵权的可能性。从司法实践来看,“胜诉可能性是较大的可能性,如果作出侵权是否成立的判断比较困难,则不宜轻易裁定签发禁令。”c胡永庆:《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中的若干问题和对策》,载http://www.a-court.gov.cn/infoplat/platformData/infoplat/pub/no1court_2802/ docs/200512/d_420502.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12月14日。因此,侵权可能性的审查只是听起来似乎有些动听,但其对于是否应当作出诉前禁令的审查并不具有多少实质意义。
再次,“难以弥补的损害”概念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什么是“难以弥补的损害”?“难以弥补的损害”在侵犯知识产权诉讼中是否存在?“难以弥补的损害”是否具有客观性?它是不是相对于特定的受害人或侵权人而言的?“难以弥补的损害”是一时的难以弥补还是永久的难以弥补?这些都是诉前禁令制度实施以来一直存在且至今仍未有效解决的问题。事实上,知识产权是私权,是民事权利,而且主要是财产权,特别是专利权和商标权往往被直接定义为财产权,著作权虽然被认为含有人身权的内容,但其人身权属性也受到了挑战,也有学者认为著作权应当是财产权。在侵权法领域,民事权利受到的损害都是可以弥补的,同样,侵犯知识产权造成的损害客观上也是可以弥补的。同时还应当看到,虽然不发出诉前禁令可能会给申请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但如果错误发出诉前禁令也可能给被申请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法院是否对申请人的申请发布诉前禁令,不仅会对申请人的利益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将对被申请人的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发布禁令是为了保护权利人免受难以弥补的损失,发布错误的禁令同样也会给被控侵权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d纪晓昕:《诉前禁令之实体要件》,载于http://www.f 5.cn/lilun/minshang/200603/10993.htm,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12月12日。可以说,凡是能够通过诉讼解决的纠纷,基本上都不存在所谓的难以弥补的损害。在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中,判断被申请行为是否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基本上不具有操作性,而且过于强调被申请行为可能造成的难以弥补的损害,不仅容易误导随后的侵权诉讼或者因错误禁令导致的损害赔偿诉讼,而且容易将对诉前禁令申请的审查重点误导到对“难以弥补”的认定,造成有限的司法审查资源无意义地耗费,从而丧失了诉前禁令制度效率优先的本来优势。
最后,在实质审查要求下对作出诉前禁令的紧迫性要件设置不够科学。紧迫性是指只有在案件情况紧急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诉前禁令,一般包括两种情形:一是侵权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权行为(即发侵权),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二是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e郃中林:《知识产权诉前临时措施制度若干问题研究》,来源:法学家网,载http://www.chinalawsociety.org/user/Article/ ShowArticle.asp?id=415,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12月12日。我国知识产权法中的诉前禁令制度,一方面特别强调情况紧急性,而所谓的情况紧急主要体现在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因此必须尽快制止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有这种紧迫性,民事诉讼法及有关知识产权的司法解释特意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接受申请之时起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情况的紧迫性要求人民法院尽快作出诉前禁令的裁定原本无可厚非,但情况紧急性要求与侵权可能性、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成为诉前禁令的实质性审查要件,则可能造成“欲速则不达”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诉前禁令的适用困境:要成全诉前禁令的效率而牺牲对实质要件的审查,要么加强对实质要件的审查而牺牲诉前禁令的效率,甚至牺牲诉前禁令制度本身,如将诉前禁令转化为诉中禁令。从一定程度上讲,诉前禁令制度的紧迫性要求与侵权可能性、难以弥补的损害等实质要件实不可兼得,似乎更应当选择紧迫性要件而放松对侵权可能性、难以弥补的损害等实质要件的审查。
四、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的重构与展望
当前,随着国内企业创新意识的普遍增强及创新成果的大量涌现,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已经从过去半推半就式的“要我保护”模式,逐渐转化到积极主动型的“我要保护”的最严格保护模式。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自身应当有所变革以适应客观形势的变化,其近二十年的适用状况需要进行研究总结,从某种意义上讲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的变革与重构已经迫在眉睫。
首先,知识产权诉前禁令要树立“效率优先”的理念。效率优先是相对于公正优先而言的。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公正优先兼顾效率”是司法审判追求的目标,也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的最大区别。例如,为维护行政管理的高效性,行政权可以为了大多数或者绝大多数的公正而牺牲少数或极少数的公正,但这并不是说被牺牲的公正就不重要,恰恰相反,这些被牺牲的公正就是司法审查的救助对象。司法审查追求的是公正优先而不是效率优先,只有在保证公正司法的前提下,才谈得上追求司法的效率。从某种意义上讲,公正从来不会缺席也不会迟到,且即便迟来的正义依然是正义。对于知识产权诉前禁令来说,由于客观上存在情况紧急性和侵权可能性,而且一旦侵权行为得到实施或者继续实施,可能会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害甚至是难以弥补的损害,故诉前禁令本质上更近似于行政权而不是司法权,其应当树立“效率优先兼顾公正”而不是“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理念。否则,“当权利人历经数月甚至是数年的诉讼最终取得胜利判决时,知识产权的期限可能已经届满。即使该权利仍在法律保护期限内,但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历经漫长的诉讼后,原告有的专利技术或其它知识产权技术可能已经被更先进的技术所取代。”f田路平:《浅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的诉前禁令制度》,载找法网http://china.findlaw.cn/lawyers/article/d464240.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12月9日。更何况诉前禁令仅仅是诉讼前的临时措施,通常还会有紧随其后的诉讼程序来维护司法的公正。从知识产权诉前禁令的适用要件来看,效率优先本身就是对公正的兼顾。如果失去对效率优先的追求,诉前禁令制度将与司法公正南辕北辙。诉前禁令的最大特点就应当是高效,应当在高效的基础上适当保证裁定的正确性,同时如果因为高效导致了诉前禁令的裁定被事后证明是不恰当的,这可以由担保制度、损害赔偿制度等配套制度及随后的诉讼来解决。
其次,减轻申请人的证明义务和法院的审查责任。当前的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中,要求申请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这为申请人设置了较高的证明义务,即申请人必须证明被申请的行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的行为是或者很可能是“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以及被申请的行为如果不能得到及时制止将会导致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简单地说,申请人需要证明情况紧急、侵权可能性和难以弥补的损害,这也是当前审查诉前禁令申请的重点和难点,但其本不应当成为加重申请人举证责任和司法审查责任的要件,更不应当成为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适用的阻碍。相比之下,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101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申请采取保全措施。似乎,2012年《民事诉讼法》不再强调申请人的证明责任,在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法院的审查责任。事实上,在一个较短的时限如48小时内,要求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情况紧急、侵权可能性和难以弥补的损害,要求法院审查诉前禁令申请是否符合情况紧急、侵权可能性和难以弥补的损害的适用要件,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即便对其进行实质审查,也因为这种审查不具有终局性而显得意义不大,却反倒严重阻碍了诉前禁令的适用。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权、商标权主要是财产权,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也主要是财产损害,而财产损害在客观上都是可以弥补的。至于特定侵权人个人赔偿能力的大小,即特定的侵权人财产是否足以赔偿其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这是所有侵权诉讼而不仅仅是知识产权侵权诉讼都需要面临的风险。因此,针对情况紧急、侵权可能性和难以弥补的损害的举证要求不宜过于严苛,一般情况下也不宜进行实质审查,更需要做的是合理构建和完善诉前禁令制度,设置和利用担保制度、调解制度等配套制度来平衡保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利益。
再次,重构诉前禁令的担保制度。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应当充分发挥担保与反担保的作用,平衡保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利益,防止诉前禁令被滥用。现有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中的担保制度设计不够科学,未能有效利用担保制度来防止对诉前禁令可能的滥用。第一,申请诉前禁令必须提供担保,并应当允许被申请人提供反担保来制衡申请人的诉前禁令申请,即被申请人提供足够反担保的,可以不发出诉前禁令或者解除已经发出的诉前禁令。第二,申请诉前禁令原则上应在作出裁定前举行听证,听取申请人陈述意见并允许其提供反担保。“我国有关诉前禁令制度的现行规定意味着做出临时禁令裁定前,听证程序不是必经的法定程序。从公平原则来考虑,这种情形剥夺了被申请人的申辩机会,有失公允。”g齐爱民、盘佳:《完善知识产权临时禁令制度的构想》,载《中国版权》2005年第3期。听证后发现诉前禁令申请明显不成立的,应当驳回其申请。否则,应当要求被申请人提供反担保。被申请人不提供反担保的,则应当作出诉前禁令。被申请人及时提供反担保后,如果申请人同意该反担保或者虽不同意该反担保但未追加担保的,则不作出诉前禁令;申请人不同意该反担保并追加担保的,应当再次允许被申请人提供反担保。如此反复至可以决定以申请人的担保为基础作出诉前保全裁定或者以被申请人的反担保为基础不作出诉前保全裁定。第三,如果确因情况紧急等因素无法举行听证即作出诉前保全裁定的,则该裁定不宜立即执行,或者说应当在其执行前的适当时间内给予被申请人陈述意见及提供反担保的机会。如果被申请人未在指定期限内及时陈述意见并提供反担保的,已经作出的诉前保全裁定在上述指定期限届满即可立即执行。如果被申请人及时陈述意见并提供反担保的,可以暂时停止该裁定的执行并通知申请人,由申请人决定是否追加担保。申请人未在指定期限内追加担保的,则已经作出的诉前保全裁定失效,并告知双方当事人可以另行诉讼。申请人追加担保的,则再次通知被申请人,由被申请人决定是否追加反担保,如不追加反担保,则执行裁定;如追加反担保,则继续通知申请人。如此反复至可以决定执行或不执行裁定为止。同时,在听证程序中可以开展调解工作。这种重视担保作用的制度设计主要是因为诉前禁令对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影响甚巨,在减轻申请人的证明责任和法院审查义务的同时,通过担保与反担保制度平衡保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利益,有效防止对诉前禁令制度的滥用。可能存在的一种担忧是,如果加重担保制度在诉前禁令制度上的作用,是否会造成经济上的强势者欺负弱势者的现象?这种担忧表面上似乎有道理,但其实是杞人忧天。在担保和反担保数额基本上均由当事人决定的情况下,一般不存在所谓经济上的强势者欺负弱势者的问题,也不存在申请人提供的担保数额或者被申请人提供的反担保数额不足以弥补相应损失的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在申请人提供了足够担保的情况后作出了诉前禁令,如果相关行为最终被认定为侵权行为,则实现了对知识产权的强力保护;如果相关行为最终未被判定为侵权行为,则申请人提供的担保是可以弥补被申请人的损失的。另一方面,在被申请人提供了足够的反担保的情况下,虽然未能发出诉前禁令,但申请人可以另行起诉被申请人,如果相关行为最终被认定为侵权行为,则被申请人已经提供的反担保足以实现对申请人利益的保护;如果相关行为最终未被判定为侵权行为,则避免了申请人因其不当诉前禁令申请给被申请人造成的损失而承担赔偿责任,实现了对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利益的兼顾保护。
最后,积极扩展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适用的新空间。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引进中国已经将近二十年了,其间虽有诉前禁令制度适用的小高潮,但总体来看其预期作用并未能得到充分展示,权利人在申请诉前禁令时承受了较重的举证责任,司法机关在适用诉前禁令制度时有些畏手畏脚,同时诉前禁令也存在被滥用的现象,被申请人可能因他人滥用诉前禁令遭受巨大损失,而且申请人往往难以弥补其错误申请给被申请人造成的较大损失。当前,知识产权制度仍处于持续变革中,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仍有可能扩充,层出不穷的技术创新对既有知识产权制度形成了较大冲击,商业方法及软件专利的发展刷新着人们对既有专利制度的认识,标准必要专利的保护已经在探索不同于传统专利保护的实践和理论,诉前禁令制度能否适用于标准必要专利诉讼已经形成了巨大分歧。从欧洲法院有关中兴公司诉华为公司案件的裁决来看,虽然作出了如何认定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没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指示,但其并未禁止在标准必要专利诉讼中适用禁令或者诉前禁令。专利权的私权属性与标准的公共属性必然存在冲突,诉前禁令在知识产权纠纷解决中具有如同原子弹般的威力。为应对创新技术的发展和知识产权制度的变革,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更需要一场变革和重构,将是否作出诉前禁令与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密切联系起来,申请人或被申请人必须为是否作出诉前禁令提供必要和足额的担保,让当事人的意志与利益在诉前禁令制度中发挥一定的作用,既有利于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充分发挥诉前禁令制度的威力,又可以适当防止对诉前禁令制度可能的滥用和错误作出诉前禁令带来的尴尬,适当兼顾了对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利益的平衡保护。
The rule of preliminary injunction in IP cases had been widely applied when it was initially adopted in China. However, its recent application is not that satisf ed as it once was. In general, the anticipatory effect of this rule has not been suff ciently presented. The at least slight passiveness in system establishment as well as idealization of guidelines led, to some degree, to the chaotic situ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preliminary injunction. For now, the IP rules and regulations have been constantly changing, and numerous newly-emerg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are bringing huge challenges to the current IP law system.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the number of subject matters protected by IP law may still increase in near future, which necessitates the urgency of changing and restructuring the rule of preliminary injunction in IP cases. The new rule needs to be based on the notion of “eff ciency goes f rst”, meaning to reduce applicants’ proof burden and courts’ duty of review, and to reorganize the rule of guarantee and counter guarantee. The decision of preliminary injunction should be mad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arties’ interests, which, together with the parties’ will, must play a relative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urt’s decision process.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new occasions where preliminary injunction can apply, and do pay attention to balance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both applicants and those on the other side.
pre-trial injunction in IP litigation; guarantee and counter guarantee; eff ciency goes f rst
刘晓军,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审判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