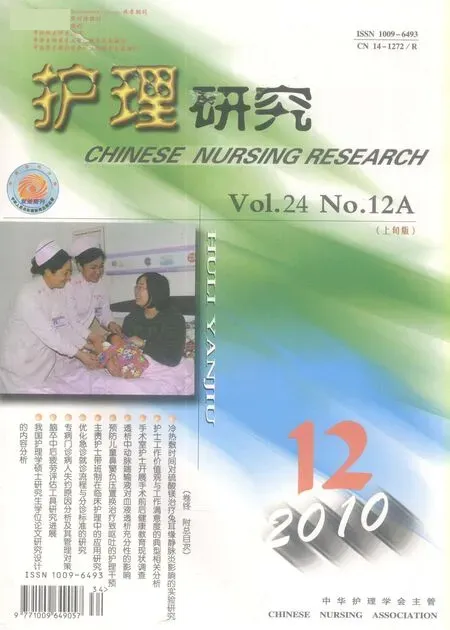有益健康模型的研究进展1)
2010-04-08陈小芳薛小玲
陈小芳,薛小玲
#科研综述#
有益健康模型的研究进展1)
陈小芳,薛小玲
回顾了有益健康模型的发展史,分析了有益健康模型与健康促进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介绍了有益健康模型的核心理论以及研究工具,展望了有益健康模型在护理领域中的运用。关键词:有益健康模型;心理一致感;健康促进
1986年在加拿大渥太华召开的第一届健康促进国际大会上通过了著名的《渥太华宣言》。宣言指出:“健康促进是指促进人们提高(控制)和改善他们自身健康的过程。”而这个宪章的核心把健康看作是人们使用资源和机会来获得良好的生活质量的过程[1]。随着医学的发展,许多健康研究聚焦于人们获得健康的能力,并提倡积极正向的健康(positive health)理念。在这些健康理念中较为著名的是美籍以色列心理学家Antonovsky[2]
提出的有益健康模型理论。该理论认为,关注人们获得健康的资源和健康促进的过程比关注风险、亚健康和疾病更重要。在20世纪80年代,Antonovsky的有益健康模型理论影响着健康促进的发展[3]。
1 有益健康模型的发展简史
1.1 有益健康模型的发展背景 对有益健康模型的研究可追溯到1961年的一项针对大屠杀幸存者的研究。这项研究发现,在绝经期大屠杀幸存女性的健康比未经历大屠杀的女性差。而Antonovsky后来却发现,有30%的大屠杀幸存女性也能够安然地度过绝经期。Antonovsky[2]认为,人的经历和体验以及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健康。他于20世纪70年代,在5健康、压力和应对6一文中提出了有益健康理论和它的主要概念心理一致感(sense of coherence,SOC)。An tonovsky[2]认为,那些面对威胁仍能保持健康的人用一种特定的方式看待世界。SOC便是个体对生活的总体感受和认知。对待健康从传统发病学原理向强调激活健康潜能的有益健康角度开始转变。
1.2 有益健康模型的历史进程 20世纪80年代初,Antonovsky[4]在5揭开健康的神秘6一文中修订和发展了这个理论。然而这时有益健康模型的研究仍然有地域局限。只有很少的几篇科学论文发表,而且主要由Antonovsky自己撰写。90年代,An tonovsky编辑发表了10期5心理一致感简报6。随后,对有益健康模型这个理论感兴趣的研究者越来越多。到1992年,有42项关于有益健康模型研究成果报道,其调查问卷在全世界有 20多个国家 15种不同语言在使用[5]。同年,Antonovsky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研讨会,提出了有益健康模型可以作为健康促进的指导理论。该观点获得了大会参加成员的一致认同。1994年,Antonovsky突然去世,但对有益健康理论的研究并没有因此停止。北欧公共卫生学院开设了第1个有益健康模型的国际研究课程以及欧洲培训集团也开展了培训课程[6]。对有益健康模型理论的研究一直在不断地继续和扩大。研究对象从小孩到老人,有不同群体的病人也有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研究范围从个人、家庭发展到群体和整个社会。到2007年,出现了44种不同语言版本的调查问卷。国际健康促进和教育联盟的有益健康模型主题工作小组在加拿大成立,2008年5月,国际研究研讨会在芬兰的赫尔辛基召开。同年,国际有益健康课程博士学位被授予[7]。
2 有益健康模型与健康促进的关系
2.1 健康概念的异同 有益健康模型与健康促进始于同一个历史时代。健康促进是一个文化的、社会的、环境的、经济的、政治的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迫切需要联合国为维护和引导全球健康创造条件,中心任务为保护人类获得健康的权利。在公共卫生领域,WHO承担这个任务。虽然那个时候已经把健康的概念拓展成3个维度(躯体、心理、社会),但健康仍然被看成是有病和没病非此即彼的两分类变量。同一时期,以色列的大屠杀幸存妇女成为Antonovsky研究有益健康模型的第一个研究群体。但是,有益健康模型诠释的健康是在完全的不健康和完全的健康这条轴线上的一种连续移动,健康成为一个持续变量,并认为可以成为人们获得卓有成效和愉快生活的工具。虽然两者对健康的诠释不同,但是都强调了人类对于健康的主动参与性。
2.2 有益健康模型诠释下的健康促进 Antonovsky认为,人的生命就是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人类出生时便来到这条河流,只通过回避压力或者建筑桥梁来防止人们跌下河是不够的。他针对不同健康发展阶段做了不同的比喻:他认为疾病治疗意味着利用昂贵尖端的技术和专业人士挽救溺水的人;健康保护的
角度是限制疾病的风险,针对的是人群并强调主动,相当于通过筑上栅栏防止人们跌下河;疾病预防是通过加强人们主动参与的意识来进行主动干预,相当于送给人们一条救生衣;健康教育为帮助人们自身做出关于自身健康的决定,这相当于教会人们游泳的技巧。Antonovsky认为,生命这条河流充满了风险,但也有丰富的资源。结果大部分基于人们认识和利用资源来改善健康及生活的能力[8]。有益健康模型诠释下的健康促进为,健康被看作是人的权利,并强调社会和个人的资源以及生理功能,人在这条河流中能识别主流方向,使用资源,使自己在河流中能自在游泳。认识和使用资源能力强的人更容易去寻求和获得支持,采取有益身心的生活方式,从而提高和改善自身健康。
3 有益健康模型的理论核心
3.1 有益健康模型与传统病原学的区别 有益健康模型与传统的病原学理论相比,传统病原学理论注重风险、疾病、诊断和治疗,而An tonovsky更注重人们获得健康的资源和能力,即认知因素。人作为一个整体以及一个开放系统与环境不断进行着互动;紧张和压力可作为潜在的健康促进因素和挑战而不仅仅可以引起疾病;环境是压力的来源也能成为抗拒压力的资源;这个理论强调使用潜在和现有的资源而不仅仅注重减少风险因素,并把主动适应作为治疗的理念。这与以往的传统病原学相比,这个理论视角更宽广,更强调主动。它不仅仅可用于个人、群体,还可以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使用。Antonovsky也特别强调有益健康模型不局限于单学科某一个专业而是一个多学科的方法。
3.2 SOC 有益健康模型的主要概念为SOC。SOC是Antonovsky的有益健康模型得以操作化的关键,综合体现了当个体面对生活中的应激源时,所具有对内外资源的利用能力以及对生活意义的感知能力,也体现了个体应对压力时拥有一种普遍、持久、动态的信心感。它促进个体或者群体在健康这条轴线上向着健康那一端前移。
3.2.1 SOC的组分 个体的SOC是由3个因素构成:第1个因素是个体对内外环境应激源的理解能力,即认知因素。一个人如果理解能力维度的得分越高,那么他就越会认为他将来所遇到的刺激物是可预测的、有序的和可解释的。第2个因素为管理能力(manageability),它是指当个体遇到有害刺激物时,资源能为他所使用,而且足以使他们能应对这些刺激物,即能力因素。第3个因素为意义感(meaningfu lness),是指个体认为生命是有意义的,面对的问题和需求是一种挑战而不是负担,值得为之投入精力和承担义务,即动力因素,也是SOC里最重要的因素。SOC被认为可以作为生存和产生健康促进能力的第六感[9]。
3.2.2 一般应对资源 一般应对资源是有益健康模型里的核心概念。一般应对资源是个人、群体、社会中可被用来有效应对压力的资源,它是SOC发展的关键。它包括生理、心理、社会和物质因素(金钱、知识、体验、自我认同、自尊、信仰、社会支持、健康行为、看待生活的角度等)。这其中的关键因素是自我认同和社会支持。一般应对资源以形成个人与社会环境的平衡和主动参与获得健康为特征,为人们提供有意义和一致性的生活体验,由此创造较强的SOC,它和SOC水平形成正反馈。
4 生命取向问卷
4.1 有益健康模型的研究工具 有益健康模型是由于Antonovsky编制了人生取向问卷才为大家所熟知并运用的。该问卷用来衡量SOC水平,所以也称为SOC量表,该量表分为3个部分,分别衡量理解能力、管理能力和意义感。Antonovsky一再强调这个量表的整体性,反对将量表拆开,将分量表单独使用。量表为7级计分,得分越高,SOC越强,提示被试者应对能力和使用应对资源的能力越强。
4.1.1 量表的版本 该量表目前使用较广泛的主要有两种版本,一种是由29个项目构成的长版本,简称为SOC-29;另一种短版本由An tonovsky抽取SOC-29中的13个项目构成,简称为SOC-13。这两个版本的比较性研究显示,SOC-29的Cronbanch.s A效度为0.70~0.95,SOC-13的Cronbanch.s A效度为0.70~0.92;SOC-29重测信度为0.77~0.93,SOC-13重测信度为0.69~0.72。可见,全版SOC-29量表和精简短版SOC-13量表具有同样良好的信度和效度[10]。但因SCO-13的条目较少,而信度、效度与SOC-29相仿,所以现在更趋向于使用SOC-13。除外这两个版本,目前为止至少有15个不同版本量表出现,有专门针对家庭、学校、孩子的SOC量表。所有版本里条目最少的SOC-3量表,有研究声称SOC-3量表也能有效测量SOC[11]。但同时在395名学生中测量SOC-29和SOC-13和SOC-3量表的信度、效度时,结果显示,3个量表中SOC-3的效度最低,为0. 39[12]。
4.1.2 SOC量表的本土化 周厚余等[13]的研究显示,SOC量表适用于中国的文化背景。包蕾萍等[14]的研究将国外已普及的SOC量表加以汉化,并进行信度、效度的检验,以进一步明确此理论在中国本土文化中的适用性。该研究在上海市选取1 827名居民和44名大学生进行测试的结果表明,SOC-13各项目的项目鉴别力良好,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61,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6;效标关联指数理想。由此可见修订的SOC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14]。汉化后的SOC量表在我国已被用于失业者、短跑运动员、青少年、2型糖尿病病人等研究[15-18]。
4.2 SOC与身心健康相关的研究 SOC对生活质量有预测作用[19]。在一项100例心肌梗死的病人的前瞻性研究中,从病人出院前和出院后2周收集的资料显示,SOC得分较高的病人发生心绞痛的几率较小,他们参与较多的身体锻炼,对治疗满意度较高[20]。Kalimo等[21]在一项10年的随访中也发现,SOC是职业倦怠最佳预测因子。虽然SOC不是一种疾病状态、诊断、症状的检测方法,但却可反映病人从疾病中身心恢复的能力。SOC量表也许可作为一个有效的筛查量表,筛选出哪些病人需要加强干预。但是到目前为止,至今不清楚SOC是从哪个数值开始失去对健康的保护作用的,没有找到合适的临界点,也没有建立正常值范围。SOC的分层依据每个作者自身的观点进行高、中、低的分层的。而如今较多研究证明,SOC量表适合于各类人群和各国文化,所以开发或者研制新量表测量SOC已无太大的必要,重点该建立一个公认的SOC常模。
5 展望
现有很多研究显示,有益健康模型理论和它的工具SOC量表对于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性。但是一个好的理论是需要不断地到实践中使用和检验的。在国外,有益健康模型不但已经作为一个方法来对病人实施个人或者小组干预、还用于职场管理,并且已经用于学习过程和教育评价[9],而最近正尝试用于制定公共卫生策略[22]。而在护理工作中,可在评估病人时把病人的SOC考虑进去,筛选出高危人群,如年轻、病程短的病人可能因为没有适应病人角色,并且对疾病的知晓率也不够亦被视为高危人群[20]。以SOC为焦点的评估能有助于制订有效的护理计划。如果在疾病早期能及时给予疾病知识的介绍,病情变化征兆的告知,这也许能增加病人对疾病的认知能力,遇见病情变化时认为这些是可理解的和可预测的,减轻恐惧心理,及时就医求助,增加病人的应对能力。而在治疗和康复时期,可减少病人住院期间影响治疗信心和心理康复的危险因素,并且通过给予认知、情感和社会支持,促使他们认识到内外环境的应对资源,使其应对资源得以丰富。强调个体在整个疾病过程中是参与的主体,专业人士只提供支持和帮助的作用。未来的研究需要制定能有效提高SOC的干预措施和指南,从而激发病人的应对潜能,提升满意度和生活质量,提升健康促进能力。
[1] A discussion document on the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of health promotion[J].H ealth Prom otion International,1986,1:73-76.
[2] Antonovsky A.H ealth,stress and coping[M].San Francisco: Jossey-Bass,1979:1.
[3] Antonovsky A.The salu togenic m odel as a theory to guide health prom otion[J].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1996,11:11-18.
[4] Antonovsky A.Unraveling the mystery of health:How people m anage stress and stay well[M].San Francisco:Jossey-Bass, 1987:1.
[5] Antonovsky A.The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the sense of coherence scale[J].Soc Sci Med,1993,36:725-733.
[6] Davies J,Hall C,Linw ood E.European masters in health promotion(EUMAH P)(phase 2):Programme delivery final report to the European Comm ission(DG SANCO)[D].Brighton:U niversity of Brighton,2005:1.
[7] E riksson M,Lindstrom B.A salutogen 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ottaw a charter[J].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2008,23(2):190-199.
[8] Lindstrom B,Eriksson M.Salutogenesis[J].JEpidemiolComm un-i ty H ealth,2005,59:440-442.
[9] Lindstrom B,Eriksson M.Antonovsky.s sense of coherence scale and its relation w ith quality of life:A systematic review[J].JEp-i dem iol Community H ealth,2007,61(11):938-944.
[10] Lin dstrom B,E riksson M.Validity of Antonovsky.s sense of coherence scale:A system atic review[J].JEpidem iol Comm unity H ealth,2005,59:460-466.
[11] Lundberg O,Nystrom PM.A simplified w ay of measuring sense of coherence,Experience from a population survey in Sweden[J]. Eur JPub H ealth,1994,4:252-257.
[12] Olsson M,Gassne J,H ansson K.Do difference scalesm easure the same construct?three sense of coheren ce scales[J].J Epidem iol Community H ealth,2009,63:166-167.
[13] 周厚余,郑全全.中国文化背景下心理一致感的潜结构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6,22(2):104-107.
[14] 包蕾萍,刘俊升.心理一致感量表(SOC-13)中文版的修订[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5,13(4):399-401.
[15] 包蕾萍.心理一致感对失业者压力体验的中介作用[J].社会心理科学,2005,20(1):18-22.
[16] 许昭.短跑运动员心理一致感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J].军事体育进修学报,2008,27(2):111-113.
[17] 刘俊升,周颖,包蕾萍,等.青少年心理一致感水平及其与应付方式的关系[J].心理科学,2006,29(5):1107-1110.
[18] 林田,林细吟,万丽红.2型糖尿病病人自我护理行为与心理一致感、抑郁的相关性研究[J].护理研究,2009,23(1A):22-24.
[19] Langeland E,W ahl AK,K ristoffersen K,etal.Sense of coherence predicts change in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home-living residen ts in the community w ith mental health problems:A1-year follow-up study [J].Quality of Life Research,2007,16(6):939-946.
[20] Bergman E,M alm D,Karlsson J.Longitudinal study of patients after myocardial infarction:Sense of coherence,quality of life,and sym ptom s[J].Heart& Lung,2009,38(2):129-140.
[21] Kalimo R,Pahkin K,Mutanen P,etal.Stayingwellor burning out atwork:Work characteristicsand personal resourcesas long-term predictors[J].Work Stress,2003,17(2):109-122.
[22] Lindstrom B,Eriksson M.The salutogenic approach to the making ofH iAP/healthy public policy:Illustrated by a casestudy[J]. Global Health Promotion,2009,16(1):17-28.
Research p rogress on help ful hea lth model
Chen Xiaofang,Xue Xiaoling(Nursing College of Suzhou University,Jiangsu 215006China)
It looked back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helpful health model. It analyzed the comp lem 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helpful health model and health promotion.It introduced the core theory and research tool of healthm odel.And it look forward to theapplication ofhelpfu lhealthmodel in the field o f nursing.
helpfu l health model;sense of coherence;health promotion
R47
A
10.3969/j.issn.1009-6493.2010.34.001
1009-6493(2010)12A-3103-03
1)为苏州大学医学部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
陈小芳(1976)),女,江苏省无锡人,主管护师,硕士在读,从事护理管理研究,学习单位:215006苏州大学护理学院;薛小玲(通讯作者)工作单位:215006,苏州大学护理学院。
2010-05-22;
2010-11-17)
(本文编辑 孙玉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