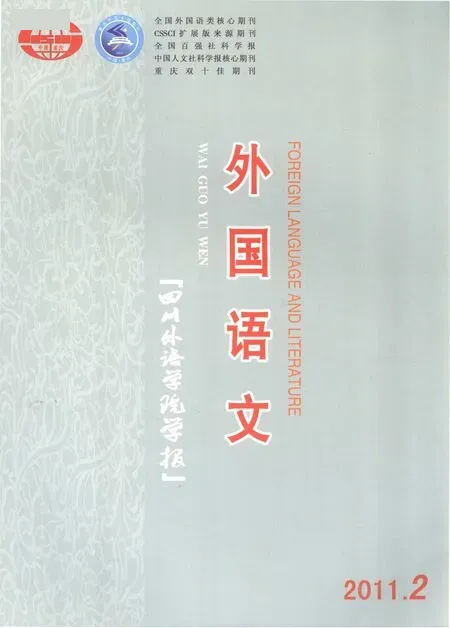口译的跨学科理论概述
2011-03-20蒋凤霞
蒋凤霞 吴 湛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89)
口译理论研究仍属于一门新的学科,在国内外仍然缺少具有实证意义的、科学的系统化口译理论。由于口译活动自身的思维规律、心理机制以及各种因素对口译活动的制约,口译理论研究一直局限于实践经验、教学经验的浅层次探讨,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因此,口译研究完全可以借助相关学科的成熟理论和有效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拓展其研究范国,开拓翻译研究的视野。
笔者根据口译的目的以及口译的交际特点,对于口译的理解阶段与表达阶段中所涉及到的各种跨学科理论,进行了初步梳理,逐一介绍了口译的目的论、口译的交际理论、口译的认知学理论、口译的信息处理理论以及口译的释意理论,以期为口译实践和教学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以期从一定程度上揭示并解释口译实践活动的内在规律性与特殊性。
1.口译目的论
20世纪 70年代,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家提出了翻译行为论 (theory of translational action)与翻译目的论 (skopos theory)两个概念,并将此确立为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内容。目的论认为,所有的翻译都应当遵循三个法则:(1)目的性法则:整个翻译过程,包括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的选择都是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的;(2)连贯性法则:译文必须是连贯的,使接受者能够根据自己的背景知识和情景环境达成理解;(3)忠实性法则:译文与原文间应存在语际的连贯一致。为了达到交际目的和文本间的语际连贯,译者可以根据原文模仿或创造,即,忠实于原文,但忠实的程度和形式则由译文的目的以及译者对于原文的理解决定。
根据目的论三原则,我们可以将口译的目的论概述如下:
首先,口译活动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采取多种策略,殊途同归。口译是一种具有明确目的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可以根据不同的文本、不同的读者对象、客户的不同要求、目的进行调整翻译标准,采取为达到目的的所有可能手段”(陶友兰,2010)。正如威密尔所言,能达到目的的手段就是正当的手段(Ver meer,1978)。上述现实中真正需要的翻译形式与策略主要有“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改译、阐译、译写、参译等”(黄忠廉, 2002)。在口译中,目的只有一个:达到跨文化交际的成功。由于口译的“现时”、“现场”、“限时”的特点决定了口译的标准比笔译的标准要宽松,因此只要保持“准确”和“流利”即可。
其次,口译人员可以凸显很强的主体性。目的论认为,口译员以翻译要求 (translation brief)为指导,从特殊的翻译任务中总结出译语的交际目的,交际目的则使口译员决定如何完成翻译任务。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口译员是个起着积极作用的专家,掌握使用何种翻译手段达到译语的目的。源语只是任由口译员使用的“原材料”,其“王位”已被取消,决定译语 (面貌)的是翻译目的 (Ver meer, 1996:12-15)。因此,口译员不必拘泥于源语的字词结构,而应重在“沟通”、“传意”。当然口译员也要负责任,在许可的范国内尽量明确自己的权限,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口译员的主体性要受到“忠诚”原则的制约,口译员不能胡译、乱译、随意篡改原语、歪曲说话人的意图。
最后,口译的首要法则是“准”,不能脱离说话人的宗旨。目的论坚持语内连贯和语际连贯。也就是说,口译出来的内容本身是有逻辑性的,言之成理,能表达完整的意思,不是支离破碎的语句;同时,口译的内容与源语紧密相关,不可以随意发挥,很大程度上是原说话人的“影子”。
2.口译交际理论
跨文化交际学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是一门涉及众多学科的应用学科。它诞生于 20世纪50年代末 60年代初的美国,其理论来源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以传播学理论为基础;二是综合利用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三是主张以经验为基础,通过大量调查,从而建立一个独特的跨文化交际的理论体系。
跨文化交际学应用于翻译研究,从威密尔(Ver meer,1978,1996)的文章和著作中可以得到印证。他的理论观点可以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1)翻译(包括笔译与口译)是语言行为的一种特殊种类,首先它是一种交际行为,是为了完成特定环境和条件下的特定交际目的。翻译活动中的一切都是围绕这一目的而进行的。(2)翻译活动是跨文化交际的一种手段,在翻译过程中会发生两种转变:首先是交际伙伴的转变;其次是交际环境的随之转变,比如时间、地点、文化与语言背景等。这两种转变决定了一次翻译活动只能是在已改变了的交际条件下,根据新的特定的交际目的对源文从语言到内容上不同程度的再创造。(3)威密尔认为“忠实于原文”实际上只是忠实原文的表层含义,而蕴涵在原文深层结构的非语言性的内涵就很难谈得上“忠实”。因此他认为,“一个译员为了实现他的既定目标,不应害怕将撰写得质量很差的译出语文章重新加 t”(Vemmer,1996)。
口译的一个基本特点表现为它是口头上的双语交际。由此,语言的交际理论成为其中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在口译中还有口译员的介入,形成三位一体的对话链。要做到全面、准确地理解说话人的意思,口译员除了必须听懂源语之外,还应对所译内容进行分析,分析的过程中口译员的思维活动紧随说话人的思维活动,是口译员忘掉源语形式,加深领会说话人的意思并为传递信息打下基础的过程。通过分析可以避免误译、错译以及粗制滥造的符号转换和文字搬家现象。语言形式上的等同不能被看作是意义上的完全等同。这就要求口译员要大胆冲破源语形式的束缚,排除源语语法、用词以及句子结构的影响,在忠实源语内容的基础上,把说话人所要表达的意思用简明易懂的话语解释出来。基于此,跨文化交际学中的口译理论,大致可以体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
首先,口译具有典型的交际特点,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交际。“恰恰是口译的双语交际特点可以解释真正意义上的翻译交际行为”(刘和平,2005: 13)。口译交际特点表现在口译交际双方在场、交际环境和背景相对理想、交际效果立竿见影等方面。
其次,口译活动要运用一定的交际策略。口译活动中最重要的不是语言形式,而是语言之外的交际信息内容。因此,口译员如果仅仅掌握语言知识,那么就很难应付口译实践活动。口译员除了需要精通双语之外,还需要懂得交际中的基本文化常识、演讲技巧和交际策略,因为在口译工作中会经常碰到“双语的文化冲突”,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构成了表达的障碍,这给口译工作带来了种种困难。这种“文化冲突”一方面来自于不同民族所独有的约定俗成的语言习惯,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双方各自不同的理念和思维方式。所以,必须扩大口译员的文化视野,提高口译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加强各民族文化的交融,达到互相理解交流的目的。此外,口译员必须掌握一些演讲技巧。例如,如何吐字清晰、声音洪亮、眼神与听众接触、语调高低、节奏快慢等都可以提高口译效果,甚至为整个口译活动锦上添花。尤其是会议口译和谈判口译,更需要译员掌握高明的谈判技巧和交际策略,增强交际意识,以便有效地促使交际活动取得成功。
再次,口译活动多方位地加强了交际能力。交际能力是一个人对潜在语言知识和能力的运用,包括语法性、适合性、得体性及实际操作性四个参数(Hymes,1972)。Canale和 Swain(1980)将交际能力进一步诠释为四个方面:(1)语法能力 (grammatical competence),指正确理解和表达话语 (utterance)和句子意义所需的语音、词汇、词法、句法等语言知识;(2)社会语言能力 (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指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懂得或使用不同的语体和使用不同的言语达到不同目的的能力;(3)语篇能力 (discourse competence),指在超句子水平面上理解和组织各种句子构成语篇的能力;(4)策略能力,指交际中懂得怎样开始谈话、进行谈话、承接、转换话题和结束谈话的能力以及出现交际障碍时,运用技巧使交际得以进行下去的能力。
简而言之,交际能力是一个人运用各种可能的语言和非语言手段实现某种交际目的的能力,涉及一个人的语言知识、认知能力、文化知识、文体知识、情感因素等多种因素(吉哲民,2001:15)。在口译实践中,口译员要在瞬间及时、独立地进行一次性翻译,没有足够的时间反复推敲,也不大可能在现场求助于他人、查阅词典或其他资料,这就要求口译员要有敏捷聪颖的头脑、扎实的语言功底、较好的汉语和英语表达能力、良好的记忆存储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辨析解意能力,能够根据需要使用适当的文体和语体,还要有较广的知识面和抓重点、记笔记的能力 (梅德明,1996:13)。同时,还要把握好介入交际现场的时机,以最大限度地保持信息表达和接受的连贯性,这需要掌握一些可预见的场合常用的套话和一定数量的习语、谚语、委婉语、缩略语,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应变反应能力,以保证随时解决口译中可能出现的障碍。因此,口译活动能够多方位地训练交际能力。
3.口译认知学理论
口译是一种即席性很强的语言符号转码活动,也是大脑理智地认识事物和获取知识的思维活动。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来看,影响口译这种心智活动最明显的因素就是图式理论在口译理解中的应用。图式概念出现在 20世纪 30年代,20世纪 60年代起又重新兴起。该理论的发展和应用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以“先验图式(schemata)”储存在大脑中的。Cook(1994)以及Eysenck和 Keane(1990)都对图式进行了不同的定义,但都强调图式的知识性和内在性。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图式是一种认知框架,人以图式的形式贮存记忆。语言理解是一个动态交互的过程,外界输入的新信息同大脑中的“图式”联系起来时产生共鸣,从而达到理解新知的目的,由此,Carrell和Eisterhold(1987:218-230)指出:“任何语篇或篇章本身没有意义,只是给读者或听者以引导,指引他根据自己已有的先知来重新获取或构建该语篇的意义。”上述利用背景知识来解读语篇的学说就是图式理论。
心理学实验证明,知识图式在口译理解和记忆的提取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根据王立弟(2001)的研究,知识图式对于理解力的加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知识图式为解释篇章的内容提供参照。在信息的读取过程中,篇章中的内容与读者头脑中的知识图式交汇融合,构成新的、更为具体的图式,从而完成理解的过程。(2)知识图式有助于词义的确立和选择。许多词语都具有多义性,在不同的场合所表达的语义是不同的。(3)知识图式有助于对下文的预测。人们在接触某一语篇时,文章内容可以激活读者头脑中相关的知识图式,而这种图式一旦被激活,就有助于读者预测文章下一步可能出现的情景。
听力理解能力强是口译成功的前提,鲍刚(1998)指出:“口译‘思维理解’的技术是口译的一大基本功”。口译员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听懂原语,并对之消化理解、分析、重新组合。如果口译员在听的过程中总是把注意力停留在个别难点上,那么就无法抓住并且理解原文内容。因此,口译中的理解是发生在语篇层面上的,口译员不仅是听声学符号,而且要听内容。这一内容是建立在词、句子和语篇上的。图式的作用在口译中表现为能加强口译员对源语的理解,引起口译员对新信息的注意和旧信息的记忆,帮助口译员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推理并最终提高口译员对信息的处理速度。认知心理学理论认为,由于较丰富的背景知识为吸收新输入的信息提供了心理框架,所以口译员会对输入的新信息特别敏感,注意力也就容易集中。当口译员大脑中的相关背景知识与输入信息之间相和谐、匹配时,便实现了对输入信息的解码,就容易记住话语的要点。
根据图式理论,理解的方式有两种:自下而上(bottom-up)和自上而下 (top-down)。自下而上是指口译员从具体感知到的信息材料,如语音、单词、句子以至语篇,逐层上升达到理解的手段。由于这种方式是通过声音的识别、单词形象的建构、命题的编制等,层层激活口译员大脑中的语言知识而达到理解的,所以它被称为“数据驱动式”(data-driven)。在这一过程中,口译员的任务就是主动快速地检索大脑中的知识并与感知到的信息相匹配,排除不必要的和具有歧义的信息,遵循逻辑关系理解语篇,从而合成意义。自上而下的方式则相反。它是从宏观的角度利用口译员对感知材料的社会与文化语境、中心议题以及对话参与者的了解而对理解起主导作用的方式。口译员的知识加上推理会有助于其将预期的与新输入的信息吻合,从而理解语篇。由于这种方法是“高层次的普通常识,决定了对低层次的语言材料的知觉”(桂诗春,1991),故称“概念驱动式”(concept-driven)。当然,这一过程同样要求口译员积极主动地参与,而不是被动地等待两者的吻合。
纪康丽(1996)曾经指出:“在实际操作中,以上谈到的两种理解方式往往交互使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强调的是译者的语言知识,而自上而下的方法则强调译者的文化背景知识或称与主题相关的知识。其实,这两种方法应该是齐头并进的。”众所周知,一个口译员即使语言水平很高,如果对所译语言的社会文化背景一无所知,在碰到有关文化背景的具体问题时也会感到束手无策。同样,如果一个口译员对该语言的文化、历史、风俗等了如指掌,而语言功底却不很深,仅凭推测也是不能圆满完成任务的。因此,图式理论的两种理解模式对口译员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此外,由于有相关背景知识的帮助,知识图式能为口译员对新信息的提取提供导向。口译员有时不必细究输入信息中某个单词的意思或者某个话语的语法结构,他可以通过合理的推导、预测来达到理解的目的,从而加快自己在口译过程中对信息的处理速度。当口译员对某些具体的内容回忆不起来时,可以利用相关的知识图式对这些信息进行合理的补充和重建(Singer,1990)。
4.口译信息处理理论
从心理语言学角度来看,口译就是一个信息处理的过程。口译过程是由语言信号输入—转码—表达三大环节构成的。第一个环节是语言信息的接受,听清源语,分析理解源语的意思以及诸层意思之间的逻辑关系,即感知信息(语音的辨听、意义的归类);第二个环节是语言信息的处理,对源语的信息进行分门别类地整理和解意,强化记忆,转译成译入语(目标语),即理解信息 (图式理论对理解的作用)和记忆信息 (命题的储存);第三个环节是语言信息的表达,用译语编码后的信息来再现源语的意思,即信息的转换(信息提取的方式)等。
口译活动第一个环节便是“听”,即信息的输入过程。“听”就是口译员感知语音信息并把它转化为语言的深层含义(交际信息)的过程。在“听”的时候,口译员的大脑需要非常活跃,要全神贯注于语言的内部结构,即音、词、句,以及语言的外部结构,即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通过说话人使用的各种衔接手段找出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并联系语言和文化语境来理解整个语篇。事实上,“听”是听主要意思,而不是听某一个单词或者句子,是对输入的信息进行整体的摄入。
摄入信息后,口译员要马上进入理解阶段。所谓理解,并不是说口译员要一字不差地重复说话人的话语,而是指口译员通过对信息的解码,抓住它的内在涵义后能用译语将其准确地再现出来。词的意义包括三个方面: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和语境意义。由于一个词同时具有这三种意义,所以理解时就要将这几种意义都考虑在内,个别单词由于词义太多不能一听完就马上作出判断,只有等到整句话或一个语段结束后才能得出其意义。由此可见,口译中对语篇的理解就是对信息进行解码的过程。
解码后的信息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编码,所以需要口译员运用信息处理理论,发挥其在脱离原语语言外壳时记忆阶段中的作用。心理语言学认为,言语的记忆主要是以命题为单位的意义储存。命题是能够表达完整意念的最小意义单位,包括主项 (argument)和关系项 (relation)。“译者记忆的应该是经过抽象概括的以命题为单位的意义模块,而不是将每句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这种意义模块是由关键词体现的”(纪康丽,1996)。由于连续口译使用的是短时记忆,信息在头脑中保留 30秒左右随即消失,所以此时的记忆可以每个语段的主题或命题为中心,承担主语的主项只记一次,以后如有重复尽可以忽略不计,而当关系项与它之后的宾语主项关系十分密切时也可以不记,因为它可以通过宾语主项推测出来。这样,需要记忆的信息材料就大大地压缩了。由此可见,口译中的言语记忆是将命题经过压缩后由口译员重新编码而获得的。
在口译过程中,口译员接收到外来信息后,先使它们成为“感觉贮存”。这些信息中只有引起口译员注意的信息才会成为短期记忆内容,其余的则自行消退。成为短期记忆内容的信息如果得到训练,就会成为长期记忆的内容而得到保存。心理学家经过实验证明:短期记忆容量有限,只能储存七个左右“单位”。要扩大记忆单位的容量,就要按知识“块”来记忆,这样口译员就可以扩大知识“块”的容量,从原来的字母扩大到句子乃至篇章,这时他才可以借助“自上而下的篇章语义处理策略”来记忆。如果一个口译员有较丰富的语言知识和背景知识,那么他所划分的“块”就较大,所能理解与记忆的东西就较多,信息处理的速度就更快。
交替传译时,口译员尽管有熟练的笔记技术作帮助,但仍然要在听辨过程中调动自己的短期和长期记忆中的贮存内容,努力将持续数分钟的源语信息在大脑中保留至译语发布完毕。由此可见,有效地掌握记忆的技巧就能加速信息处理速度,从而提高口译员的工作效率。
由于经过简化、压缩的意义是以关键词的形式贮存于大脑之中的,“提取时就需借助联想、组织等手段将信息复原。联想就是通过关键词回忆当时的情景,包括语境和背景知识,由此及彼将漏掉的信息补齐。组织就是将复原的信息进行逻辑排列,找出内在的关系,使其符合原说话人的意图”(纪康丽,1996)。通过联想、组织等手段复原后的信息需要再一次编码将其转换成译语。此时的编码技巧涉及口译员对译语的构句方法、思维模式以及表达习惯的熟悉程度。口译员的熟悉程度越高,则经过转换的信息量保持得就越完整,表达的速度也就越快。
5.释意学派口译理论
在口译研究中,以塞莱斯科维奇教授为代表的释意学派理论是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作为该学派的创始人,达尼卡·塞莱斯科维奇在她的著作和文章中对口译理论有过多次阐述。她认为:“口译不仅是听懂词语,而且是通过词语听懂说话人所说的话,然后立即用易懂的话把它表达出来。因此,口译并不是把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而是理解言语,然后再用人们能够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传达给别人。翻译的优美和意义正在于它始终是沟通表达和理解的桥梁。”在谈到口译的目的和任务时,她说:“对口译来说,决不能忘记它的传送意义,不必拘泥于源语的词语和句子结构,不应当把它们逐一译出,因为它们只是指路的信号,而不是道路本身”。“口译的任务是传达话语所含的信息意义,而不是把表达意义的语言转换成其他语言……在话语所传达的意义与意义籍以形成的语言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这些差别说明言语功能并非语言功能,说明口译是一种交际行为,并非语言行为”。
总而言之,释意学派理论认为翻译是交际行为,是消除模棱两可、重新找到作者欲说之言。释意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翻译的主要目的是译意,而不是源语语言外壳,翻译的对象是信息的内容,而不是语言,其主要思想是提倡在翻译中进行“文化转换”(王东风,1999:59)。塞莱斯科维奇和勒代雷认为,交际中人们不是对语言本身感兴趣,而是想了解对方试图表达的思想和信息,这才是交流的根本目的之所在。翻译不是简单的代码转换,翻译的目的应为传递意思,亦即交际意义;口译员所译的东西应为篇章所传达的信息内容,是言语 (亦即语言的使用),而不是语言本身。口译并非基于对原语说话人语言的记忆,而是基于口译员对原语说话人所传递的交际意义的把握以及随后用译语对该交际意义(即说话人的意思)进行的重组,是通过释意来传递意义,是精神代码的传递。因此,塞莱斯科维奇曾说翻译学是介于注释和语言学之间的一门学科。翻译要把语言的潜在性变成语言的现实性,使作者所欲之言与读者揭示的意义尽量吻合,以便达到翻译的目的。
塞莱斯科维奇(1991,1992)还提出了三段式翻译模式:即理解语言—理解意义—复原意义。说到底,口译是两种语言间的意义转换的重新表达,不是建立在信息的语言结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信息内容理解的基础上,将一种语言中所包含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由此可见,口译是口译员在接收原语语音之后,启用语言外知识,使之与语言知识相结合,把源语的语音与语义转化为概念,理解源语的意义,然后脱离源语语言外壳,即摆脱源语的外在形态和语言结构等形式上的束缚,获取源语要传递的信息,最后以译语为载体,对源语进行编码并加以表达。这一过程可以表示为:理解原语一脱离原语语言外壳一用另一种语言表达理解了的内容和情感。
以上,我们根据口译的目的以及口译的交际特点,对于口译的理解阶段与表达阶段中所涉及到的各种跨学科理论,即,口译的目的论、口译的交际理论、口译的认知学理论、口译的信息处理理论以及口译的释意理论,进行了详尽地逐一梳理,以期能够为口译的实践与教学提供某些科学的理论依据,并从一定程度上揭示口译实践活动的内在规律性与特殊性。
[1]Canale,M.&M.Swain.TheoreticalBasesof Communica-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sting [J].Applied:Linguistics,1980(1):1-47.
[2]Carrel,P.L.&J.C.Eisterhold.Schema:Theory and ESL Reading Pedagogy[C]//M.H.Long&J.C.Richards.M ethodology in TESOL:A Book of Reading.Rowley, Mass:Newbury House Publishers,1987.
[3]Cook,G.D iscourse and Literatur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4]Eysenck,M.W.&M.T.Keane.Cognitive Psychology: A Student’s Hardbook[M].Hilladale,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90.
[5]Hymes,D.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C]//J.B. Pride&J.Ho lmes.Sociolinguistics.Harmondsworth:Penguin,1972.
[6]Singer,M. Psychology of Language:An Introduction to Sentence and D iscourse Processes[M]. H. Isabel New Jerse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90.
[7]Vermeer,Hans.J.Ein Ratunen fttr eine allgemeine Translationstheori[J].Lebende Sprachen,1978,23(3):99-102.
[8]Ver meer,Hans.J.A Skopos Theory of Translation(Som e A rgum ents for and against)[M].Heidelberg:TEXtcon TEXT-Verlag,1996.
[9]鲍刚.口译理论概述[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8.
[10]桂诗春.认知和语言[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1(3).
[11]黄忠廉.变译的性质及其宏观特征[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5).
[12]吉哲民.浅谈中国学生的外语交际能力 [J].外语界, 2001(3).
[13]纪康丽.口译与信息处理[J].外语研究,1996(4).
[14]刘和平.口译理论与教学[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15]梅德明.当代比较语言学与原则——参数理论 [J].外国语,1996(4).
[16]塞莱斯科维奇.口译技艺 [M].黄为忻,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17]塞莱斯科维奇,勒代雷.口笔译理论概述[M].孙慧双,译.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18]陶友兰.基于语料库的翻译专业口译教材建设[J].外语界,2010(4).
[19]王东风.谈当代翻译理论[J].中国翻译,1999(3).
[20]王立弟.翻译中的知识图式[J].中国翻译,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