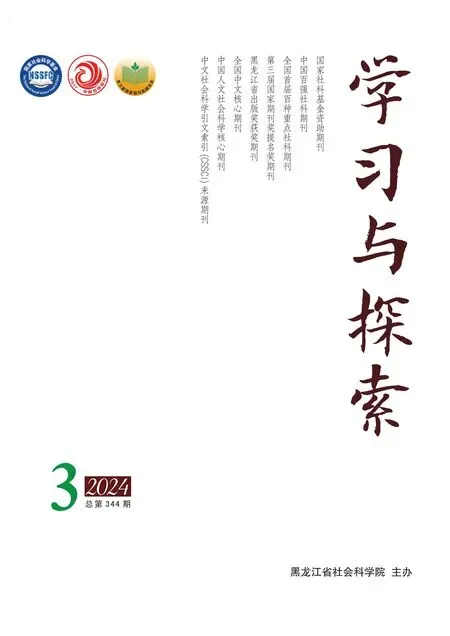思想史上的李梦阳与《空同子》
——兼评王昌伟《李梦阳:南北分野与明代学术》的几个观点
2024-05-23孙学堂
孙 学 堂
李梦阳作为明弘、正复古思潮的代表人物,一方面具有鲜明的儒者情怀和卫道意识,另一方面又高扬“自我”,有些言行被今人视为晚明思潮之滥觞(1)对于李梦阳代表的复古思潮、阳明心学与晚明重情思潮之关系,学界已多有讨论,笔者的基本看法是“阳明心学和复古思潮皆在凸显人的主体精神的同时压制了个性自由的发展”。参见孙学堂:《论明代文学复古的思想意义——兼与心学思潮比较》,《中国诗歌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2002年版。,其思想观念之复杂,理应得到全面、立体的描述。《空同子》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思想观念,但国内研究者往往只关注其论诗文的条目,对其他内容置之不顾。新加坡学者王昌伟(Chang Woei Ong)的专著《李梦阳:南北分野与明代学术》(以下简称王著)则把李梦阳视为“一个多维的思想家”,认为他“对于宇宙、伦理、政治、礼学和历史都有严肃的讨论”[1]8,尤其对《空同子》给予了重点探讨。该书以宋代以来的思想发展与士风、学风的南北差异为背景,作者成长于西方汉学研究的氛围中,研究视野又偏重哲学和思想史领域,故可以说,把李梦阳放在了古与今、南与北、中与西、哲学与文学等多重视域下,予以全面的比较和剖析,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看法。笔者拜读后获益很多,同时也有一些不尽相同的理解,谨向王昌伟教授和关注李梦阳研究的同仁请教。
一、《空同子》的基本面貌
《空同子》是李梦阳晚年撰写的子书,“其书分化理篇二,物理篇一,治道篇一,论学篇二,事势篇一,异道篇一,凡六目、八篇”[2]1654。梦阳去世前曾委托黄省刊刻自己的诗文集,并未将其包括在内。嘉靖十年(1531)聂豹将其单独刊行。到万历中,邓云霄、潘之恒重刻《空同集》,搜罗遗佚,见“民间多有之”(2)万历三十年邓云霄刻本《空同集》卷六六末附潘之恒笺云:“校甫完,有言《空同子》一册,民间多有之,而钱功父、张金粟各致一编,张有聂序,本尤善,遂合王百谷旧本订定而后杀青焉。”,遂拣择善本,分两卷刻入集中。《四库全书总目》谓其“已编入《空同集》中,此本乃后人摘出别行”,实未得其详。
按照朱安氵侃《空同先生年表》的说法,嘉靖六年“公闵圣远言湮,异端横起,理学亡传,于是著《空同子》八篇”,认为该书的写作意图是扫除异端、捍卫理学,具有严肃的目的性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其旨远,其义正,该物究理,可以发明性命之源,学者宗焉”[3]2090。聂豹《空同子小序》也谓其“文以见道,道以经世”,“见道者诣精,经世者识达”[3]2124,从儒家立场评价颇高。而清人纂修《四库全书》,则将其著录为“子部/杂家类/杂学之属”存目。按《总目》所言,子部“儒家类”所收书“大旨以濂、洛、关、闽为宗”,即恪守宋代理学正传者,且“无植党,无近名,无大言而不惭,无空谈而鲜实”[2]1193,而“杂学”的特点是“谈理而有出入,论事而参利害,不纯为儒家言者”[2]1574。李梦阳友人的著作被编入同类存目者有王廷相《雅述》、何景明《大复论》、郑善夫《经世要谈》、薛蕙《西原遗书》《约言》等;而编入“儒家类”存目的有顾璘《近言》、王廷相《慎言》、陆深《同异录》,收入“儒家类”的则有崔铣《士翼》、吕柟《泾野子内篇》。比较可知,四库馆臣把《空同子》视为文人笔谈,谓“其发明义理,乃颇有可采,不似其他作之赝古”,主要是从文章角度说的。此种认识,与聂豹和朱安氵侃之说形成了较大反差。
从《空同子》的基本面貌看,李梦阳并非坚定的理学维护者,反而有些反拨“宋儒”(“宋人”)的观点,如《物理篇》说:“宋人不言理外之事,故其失拘而泥。”[4]10a《论学上篇》说“宋人不知孟子”[5]6a,“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矣”[5]4b等。在宋儒中他特别推崇周敦颐和程颢,《论学下篇》说:“赵宋之儒,周子、大程子,别是一气象,胸中一尘不染,所谓光风霁月也。前此,陶渊明亦此气象,陶虽不言道,而道不离之。”[5]7a-7b将陶渊明与周、程并列,乃着眼于脱洒气象。但这又不太能代表李梦阳的论学宗旨,因为从许多言论看,他的思想确实深受朱熹影响(3)关于李梦阳思想观念受朱熹理学之影响,可参看黄果泉:《论李梦阳诗学思想的理学倾向》,《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空同子》中的言说方式大致可分两类,一是引经据典,二是结合自己的阅历和闻见谈论道理。后者尤其突出。如《化理上篇》说:“正德二年正月一日,日食既。空同子曰:予盖亲睹焉,月体不满规,日大而月小乎?凡月食既,则轮尽黑无余欠,乃益知月体小于日。”[4]1a这种立论,继承了《周易·系辞》所言“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6]77的观物方式,表现出对生活经验的重视,也表现了李梦阳作为诗人特别关注现象世界的特点。有些条目记录生活中所见事物的规律,如《物理篇》说:“空同子围炉而观铜瓶之水,热极则响转微。”这细致的观察,表现出近乎科学的观物态度,近人孙宝瑄称赞说:“斯言与西儒所谓‘河愈深,响愈小’意同。”[7]63a李梦阳还试图进一步生发出人生道理:“嗟!至宝不耀,至声无闻,天之道哉!天之道哉!凡欲人知者,非足者也;凡人不知而闷者,欲人知者也。”[4]13b从科学角度看,议论有点迂腐;而从理学角度看,又嫌疏阔而不够笃实。还有很多条目完全脱离了人生“义理”,如《化理下篇》说:“人之五脏各其喜生,肾虚者嗜咸,肝虚者嗜酸。凡食,脾胃喜之则味佳,不喜则咽之不下,亦自喜生之道欤?口,脾之属欤?”《物理篇》说:“橄榄为楫,拨鱼则浮,亦磁石引针、琥珀起草之类欤?骨鲠以玉簪花根汁滴之则化。”对于以“尊德性”为首务的儒家而言,这样的观察虽属“格物”,但终归与德性无关而嫌“支离”。
王廷相论学谓“必须主敬存诚,以持其志”[8]834,相比之下,《空同子》论德性、谈修养的成分较少,将其归入“杂学”是有道理的。通过下文的论述,我们又会看到李梦阳的思想比较重感性、重功利,重感性则难免驳杂;重功利则以“治道”为首务,于是也不乏“卫道”倾向,朱安氵侃所谓“闵圣远言湮”虽不免拔高,却也自有见地。王著从当代哲学研究出发,尤看重其谈论“化理”“物理”的部分,认为《空同子》写作目的是在《易》学影响下建立一种与当时学者不同的“理解天地及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理论”[1]116,更重视其知识体系和形上思考。而笔者则以为,形上思考实非李梦阳之所长,清晰的逻辑分析方法未必适合《空同子》。
二、重现象世界
《物理篇》有一条颇能代表《空同子》的撰述特点和思想方法:
宋人不言理外之事,故其失拘而泥。玄鸟生商,武敏肇姬,尹之空桑,陈抟之肉抟,斯于理能推哉?空同子曰:形化后有气化焉,野屋之鼠,酼瓮之鸡,其类已[4]10a。
这一论述既引经据典,又结合了自己的闻见,其结论则颇为“感性”。《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9]622言狄简吞服玄鸟之卵而生契。《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9]528言姜嫄踩到上帝的拇趾怀孕生了后稷。这些载于经典的神异传说,古人大都视为信史,而宋代理学家则不太深信。《朱子语类》记朱熹与门人关于《生民》诗的讨论:
问“履帝武敏”。曰:此亦不知其何如。但诗中有此语,自欧公不信祥瑞,故后人才见说祥瑞,皆辟之。若如后世所谓祥瑞,固多伪妄。然岂可因后世之伪妄,而并真实者皆以为无乎?“凤鸟不至,河不出图”,不成亦以为非?
时举说“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处。曰:履巨迹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诗》中亦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盖以为稷、契皆天生之耳,非有人道之感,非可以常理论也。汉高祖之生亦类此,此等不可以言尽,当意会之可也[10]2129-2130。
虽然不欲否定其真实性,但又认为其不合“常理”。
按儒家所言之“常理”,“气化”是万物化生的早期阶段,“形化”则比较晚。程颐说:“万物之始,皆气化;既形,然后以形相禅,有形化;形化长,则气化渐消。”[11]79但从“气化”到“形化”的转变发生在何时?却无明确说法。《吕览》《列子》都记载伊尹生于空桑,其说不见儒家经传;陈抟生于“肉抟”的说法更晚,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陈抟传》不载其事,而李梦阳却相信之。因为相信这些不合“理”之事,所以他批评宋人“拘而泥”。他提出“形化后有气化”来解释不合常理的现象,还拿“野屋之鼠,酼瓮之鸡”来类比,意谓野屋、酼瓮中可以“气化”生出鼠和酼鸡——这都基于他的闻见“经验”(现在看来并不可靠),由此可见,李梦阳是一个重闻见的“经验主义”者,当“经验”与儒家之“理”冲突时,他宁可相信前者。
那么,李梦阳批评“宋人不言理外之事”,是不是要反对或颠覆宋儒所重视的、具有思想统治意义的“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化理下篇》说:
或问海市。李子曰:此处偶有此怪异气耳。夫阴阳五行,气化不齐,滨海之邦,海错万殊。广之珠,滇之石,北之蛏,南之鮝,淮之蠏,吴之蛤,能尽究所来耶?事有不必辩者,以其非急也;有不能辩者,以其非理也。不必辩,如海市、鸟鼠同穴、象胆四时在四胫之类是也。不能辩,如豕立人啼、人死托生之类是也。人不能自见其脑与背,病之来也,忽而痛,忽而止,忽而寒,忽而热,自不能知之。而好奇者每每辩其非急,求之理之外乎?[4]5b
他承认宇宙中“气”的运行存在一些不合规律的现象,把“海市”解释为“气化不齐”所造成。“偶有此怪异气”与“形化后有气化”都是违反“常理”的,或者说,这些“怪异气”也都属于“形化”之后的“气化”现象。“豕立人啼”出自《左传》庄公八年,荒淫昏庸的齐襄公派彭生杀害鲁桓公,再杀彭生灭口,“遂田于贝丘。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队于车,伤足,丧屦”[12]190。“人死托生”如《左传》襄公三十年、昭公七年所记“伯有为厉”之事,子产释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凭依于人,以为淫厉。”[12]1432朱熹解释说:
死而气散,泯然无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气不散,又怎生去凑着那生气便再生?然非其常也。伊川云:“《左传》伯有之为厉,又别是一理。”谓非死生之常理[10]44。
看来,程颐和朱熹也都不得不承认这些不合“常理”之事,但他们的解决方案是说这些事“别是一理”;李梦阳则解释为“气化不齐”。李梦阳说它们“不能辩”,其实是呼吁人们不要怀疑其真实性。
在李梦阳看来,“人不能自见其脑与背”这个与生俱来的现象表明人的认知有其天生局限。《化理上篇》说:“北者至阴之地,阳之根窟,故日照三面,如人之背。至阴不自见,至静而动者出焉,非此则无根,无根则其用穷也。人五脏系在背,背有神舍,故膏盲病则无医。膏盲者,根也。”[4]4a背为至阴,人不能见,但又为阳之根,这说明人类的认知之外有十分重要的存在。只是李梦阳并不鼓励人们去发掘和探索这些不可知的领域,而是说不必辩、不能辩,主张回归常理世界,反对“辩其非急”和“求之理之外”。《异道篇》说:“释言怪主于有,故妄;宋儒言怪主于无,故泥。”他既承认“理外之事”存在,又要人们重视和尊重“常理”之运行。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只要遵循“理”即可,《论学上篇》说:“流行天地间即道,人之日为不悖即理。”[5]5a这最能体现出李梦阳立身处世的基本态度。
虽然从逻辑角度说,认可“理外之事”为反对或颠覆“理”(天理)的思想统治打开了一个缺口(因此从逻辑上也可以认为李梦阳的言论代表了明中叶“天理”信仰的轻微松动),但李梦阳的主观意图却不是反对“理”,而是要以更鲜明的态度去建设与理学家诉求完全一致的理想社会。同时代的吴中文人祝允明在《罪知录》中遍引六经中的神怪记载,又遍引宋儒关于鬼神的言论,提出:“历寻圣典,曷有无鬼无神之词哉!传师疏义,谨守承传,学者迄无异辞……迨宋之儒,每事务戾前闻,自标墙阈。然亦惟程氏、张氏,颇言无鬼。”[13]810其肯定神怪存在、敬鬼神而远之的结论与李梦阳一致,但其读书求理、注重思辨的思想方法和质疑程朱理学的思想倾向,却与李梦阳明显不同。
基于李梦阳认为宇宙不可知、无规律、斗争性等特点,王著以为在李梦阳看来“天地万物在本质上是多元的”。书中论证这一观点,主要用了《化理上篇》的两条材料。其一:
雨一也,春则生,秋则枯。风一也,春则展,秋则落。雪一也,冬六出则益,春五出则损。水一也,鹅鸭则宜,鸡濡则伤。土一也,夏至则重。炭一也,冬至则重。一物且尔,况殊哉![4]3a-3b
王著认为这段话表明,“在李梦阳看来,天地运行之理事实上证明了自然世界本质上就是充满差异的”。而笔者认为,李梦阳在此要阐明的是:本质上一致的事物(雨、风、雪、水、土、炭),在不同条件(季节)下或遇到不同的对象(鸡鸭鹅)会有不同的表现与功效。李梦阳强调的是现象世界的丰富性,而不是万物“本质上的多元性”。与此相联系的是,李梦阳提醒人们:要认知世界、认识到世界的统一性,是有相当难度的。其二:
天道以理言,故曰“亏盈而益谦”;地道以势言,故曰“变盈而流谦”;鬼神以功用言,故曰“害盈而福谦”;人道以情言,故曰“恶盈而好谦”。盈、谦以分限言耳,非谓消长升沈也。而俗儒不知,类以日月、草木等当之,悲哉!月有亏而无益,草木有益而无亏。若以凋落为亏,则谦者不凋不落邪?[4]2a-2b
这段话是对《周易·谦卦》彖辞的解释,并未明确表达李梦阳本人的观点。王著认为李梦阳以此强调:“首先,天地鬼神和人对于事物盈亏都有不同的反应,因为他们行为的本质是不同的。其次,自然事物比如月亮和草木,在盈亏消长上属于不同的类型。因此他们的变化也要遵循不同的‘理’,不能以一种普遍性的变化理论来解释。”[1]126而笔者的理解稍有不同。所谓“天道以理言”“地道以势言”“鬼神以功用言”“人道以情言”,是说《周易》在阐发“天道”“地道”“鬼神”“人道”时的言说(立论)角度不同,而对待“盈”和“谦”的反应(态度)则是一致的,无非都是《尚书》所言之“满招损,谦受益”。“盈”和“谦”指事物各自的“分限”——也就是“天分”“性分”,它是指人或事物的状态,而不是“消长升沈”(王著称为“‘气’的周期性升降”)的过程。李梦阳说“俗儒”总是拿日月、草木的“消长升沉”来打比方以解释盈、谦之理,那是讲不通的。他说的“俗儒”是指不懂装懂的人,而非指“宋儒”。在这段话中,李梦阳强调天道、地道、鬼神、人道对待“盈”“谦”表现出近似的态度,因此“君子”立身应该守“谦”而戒“盈”。
故上举两条材料,笔者以为李梦阳强调的是现象世界的多样性和认识世界的难度。从批评“宋人不言理外之事”看,李梦阳显然不把“理”视作世界之本体;他把许多难于解释的现象归为“气化不齐”,但从未像王廷相那样明言“元气之上无物,元气为道之本”[8]835,他说的“气”尚不具有本体论意义。他受《易传》阴阳思想的影响,谈论天下物理及人间事理,喜欢归结到阴阳的对立统一,就此而言似可以称之为“二元论”。实际上李梦阳缺乏关于世界本体的清晰思考。王著还认为,李梦阳“也会相信人类的知识也应当是多元的,这样才能正确学习各种不同的‘理’”,但对这一推断似又不能确信,于是提出:“退一步说,即便我们认同万事万物都可以或多或少地用一种一般的阴阳运行之理来解释,其核心仍然是‘争’而不是‘和’。”[1]127这是笔者赞同的。书中用《化理上篇》的一条材料证明这一结论:
或问化权。空同子曰:阴阳代更必争,而主之者行。如春主生,即恶风凄霜无损于拆萌;如冬主藏,非无晴和之辰,而黄落愈增。故曰化权。权者,谓主之也,有官之义焉。官之者权也,能推移轻重之也[4]3b。
关于“化权”,李梦阳并没有说清“主之者”是阴、阳中的某一方,还是阴、阳之外的第三方。“春”和“冬”在这里是仅仅表示时令,还是作为“权”的行为主体?他应该说清楚,但可惜没有。因此说,李梦阳关于本体的思考很不成熟。
《空同子》更关注现象世界。从理性的立场可以说,李梦阳为纷繁复杂的现象所迷惑,缺乏对世界本体及其运行规律的深入思考。这或许是许多人(包括吕柟、魏校、王廷相等友人)把他视为文人而不太看重其学术的重要原因(4)王廷相《雅述》有几条批评《空同子》的观点,如关于雷电为阴阳搏击之为、北为至阴之地、“人性上人”为阴阳必争之表现等,说得很不客气,谓梦阳“非独谈理未的,尤见气性不化”,“气性”犹言“气质之性”,乃直言李梦阳浅陋。参见王廷相:《王廷相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43-844页、第881页。吕柟和魏校对李梦阳的批评乃人所熟知,不赘言。。
三、皇权与“治道”之关系
促使李梦阳关注“理外之事”的,还有一些帝王的神异传说。《化理下篇》:
或问舜入井以孔出。空同子曰:既入井,顾安所得孔哉?即有孔,象独不之知邪?曰:若是,舜胡由出?曰:神为之也。汉高大风破围,光武六月之冰,宋康王泥马渡河,古来真天子怪异多矣,况舜哉?此等不可知,亦不可穷[4]9a。
问者肯定注意到《孟子》所载舜入井逃脱之事不合常理。对此李梦阳也坦然承认,但认为对“真天子”而言这不奇怪。结合“豕立人啼,人死托生”等事,可知李梦阳言“理外之事”看重其有助教化之功。《周易·观》卦彖辞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6]36其说与儒家思想结合,特别在汉代以后,结合“天人合一”观念而愈盛。李梦阳清楚,理性的认知在很多情况下不利于政教推行,《治道篇》说:“庄周‘齐物’之论,最达天然,亦最害治。使人皆知彭、殇、孔、跖同尽同归,则孰肯自修?或又知清浊混沌,金石销铄,孰彭孰殇?孰孔孰跖?肯自修乎?故曰害治。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4]17a为了政教需要,有些真相不必让百姓明白。《化理上篇》说:“予往在玉虚观,见其像设,问道士此何神,答曰:皆星也,虑人不敬畏,故假名像耳。”[4]4a借神的名义可以加强敬畏感。借助先祖、圣贤和“真天子”的神异传说,加强圣贤和帝王崇拜,从而有助于“治道”。也就是说,这样的“理外之事”对于维护“常理”运行的人伦世界是有积极意义的。
王著认为:“道学关于皇权的主流思想强调皇帝的道德责任而非权势,与之相反,李梦阳为皇帝享有的权势提供了理论基础,皇帝的名位由天决定。这赋予皇帝一种神圣的特质。”李梦阳认为“只要君主能够回应人情(‘民之所好好之’),他就应当被视为有德”[1]147。这一结论笔者基本赞同。但需要说明,李梦阳尊皇权与重“治道”有密切关系。
第一,李梦阳非但对皇帝不重道德修养,对于普通人、士大夫,也不像宋人那样强调“明明德”或“诚意、正心”。他更注重的是“元气”的养成和“士气”的鼓舞,将其落实于政教活动中的精神陶冶和信念培养。
第二,李梦阳也主张限制皇权。《化理上篇》开篇第一条说:
或问电雷。空同子曰:吁!胡叩渊于浅人!虽然,窃闻之矣,是阴阳搏击之为也。曰:有鬼神形者何也?曰:气动之也,气散则散。凡神怪随气之妖祥,亦有人物形者,皆变也。星之妖为欃枪、天狗、彗孛等,亦气之生散,唐一行北斗化七豕是也[4]1a-1b。
王著指出由这段材料还可以看出李梦阳“对天人感应论的信从”[1]125。这是对的。而“天人感应论”既主张天赋皇权,同时又以“天”的权威限制皇权。“欃枪、天狗、彗孛”皆为彗星之别名,从天人感应角度说为不祥之兆;唐代僧人一行“北斗化七豕”之事,也是以天人感应为途径限制皇权。
第三,李梦阳并不认为“名位由天决定”的皇帝无须努力就能完成使命。《治道篇》论述了帝王的许多行为准则,首先便是“人主以无为为威,有代天之相,则百官自正;有执法之吏,则百度自贞”[4]15a。“无为”看似容易,但对习惯于生杀予夺的帝王而言,其实是最难的。能信任贤明的宰相和法官,也绝非轻易之事。此篇提出的“治道”如“遏恶扬善”“真伪两在,不逆其伪;功罪具疑,则重其功”“包容中有鉴”等等,都是兼论帝王与大臣,属于求治之术;而“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一道德以同俗”,则关系到士大夫与平民的道德修养。他谈到帝王祭祀要“敦孝敬而防游佚”,则论及了皇帝的道德修养。《治道篇》还说:
“天不湎尔以酒,不义从式”,言酗酒者不制之义。酒伐德,故愆尔止;又乱性,故无明晦号呼。“俾昼作夜”者,靡明靡晦也。斯自事耳,非天湎之也。
“颠沛之揭”者,“本实先拨”也,非枝叶之害也。治天下有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也[4]17b-18a。
所举《诗经·大雅·荡》,诗小序云:“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然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10]552所谓“本实先拔”,朱熹《诗集传》引苏辙曰:“商周之衰,典刑未废,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其君先为不义,以自绝于天,莫可救止,正犹此尔。”[14]311“本”乃喻“义”。所谓“治天下有本”,出自周敦颐:“治天下有本,身之谓也;治天下有则,家之谓也。本必端。端本,诚心而已矣。则必善。善则,和亲而已矣。”[15]38由此可见,他虽然不像宋儒那样强调皇帝要修养道德,但对皇帝的德行也并未轻忽。《治道篇》还说:
“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如聚财强兵,非不为上,然非为德;拔引私昵,非不为下,然非为民[4]20b。
“上”指皇帝为核心的统治集团,“为上为德”则是强调“德”对于整个上层社会的重要性。
由以上论述可知,在李梦阳观念中“治道”为第一要务,尊崇皇权乃是为了维护“治道”,这也体现出李梦阳思想观念中的重功利而不够理性的特点。
四、申理欲之辨
李梦阳不像宋儒那样重视本体性的“理”,也不很强调修身养性,而是说“人之日为不悖即理”,诚如王著所说,“理在这里仅仅意味着人类行为的恰当性,与需要哲学基础的本体论无关”,李梦阳“在讨论道德伦理时,其中根本没有所谓‘本’的存在,只有具体的人类行为和经验”[1]152,他不像宋人那样“在天地与人性之中寻求道德的本体论来源”[1]153。此说极是。王著在阐发这一论断时,着重分析了“理欲同行而异情”的说法。《论学下篇》:
孟子论好勇、好货、好色,朱子曰:“此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无者。”是言也,非浅儒之所识也。空同子曰:此道不明于天下,而人遂不复知理欲同行异情之义。是故近里者讳声利,务外者黩货色。讳声利者为寂为约,黩货色者从侈从矜。吁!“君子素其位而行”,非孔子言邪?此义惟孔知之,孟知之,朱知之。故曰:非浅儒之所识也[5]9a-9b。
王著认为李梦阳这里所谈的是好恶之“情”的表达要得当,是“将胡宏的理论混入朱熹思想”,“篡改了朱熹的观点”[1]152。笔者则以为,李梦阳正是传承了朱熹的思想。其所谓“朱子曰”出《四书集注》:
盖钟鼔、苑囿、游观之乐,与夫好勇、好货、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无者。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循理而公于天下者,圣贤之所以尽其性也;纵欲而私于一己者,众人之所以灭其天也。二者之间,不能以发,而其是非得失之归,相去远矣[16]220。
其中“天理人欲,同行异情”之说,的确最早出自《胡子知言》:“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同行而异情,进修君子宜深别焉。”[17]3a朱熹针对胡宏的言论也确曾提出了辩驳,除《疑义》所言外,另有《答徐居甫》说:
寓向看五峰(引者按:胡宏之号)言“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同体而异用”两句,颇疑同体异用之说,然犹未见真有未安处。今看得天理乃自然之理,人欲乃自欺之情,不顺自然,即是私伪,不是天理,即是人欲,二者面目自别,发于人心自不同。……二者夐然判别,恐说同体不可,亦恐无同行之理。若曰心本为利,却假以行,与那真于为义者其迹相似,如此说同行犹可[18]2786。
朱熹断然否定了天理人欲“同体异用”之说,而在“其迹相似”的意义上肯定了“同行异情”之说。朱熹文集中多处运用了“同行异情”的表述,以强调天理和人欲貌同而实异。上引《孟子集注》中的话意在强调:第一,不可全盘否定“好勇、好货、好色”;第二,更要警惕人欲借此泛滥。李梦阳引其言,指出的两个极端,一是为求天理而泯好恶之念,二是逐好恶而远天理,都违背了孔、孟的原则。所谓“君子素其位而行”,语出《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16]24这正是李梦阳所言“日行不悖即理”之所本。它实际对“君子”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就是要在心心念念之间分辨出哪是“天理”,哪是“人欲”。
也就是说,李梦阳重申宋人“理欲同行异情”的命题,旨在呼吁人们严格区分理和欲,要求“守正”、警惕本心之不正。《论学下篇》又说:
理欲同行而异情,故正则仁,否则姑息;正则义,否则苛刻;正则礼,否则拳跽;正则智,否则诈饰。言正则丝,否则簧。色正则信,否则庄。笑正则时,否则谄;正则载色载笑称焉,否则辑柔尔颜讥焉。凡此皆同行而异情者也[5]8a。
“正”与“否”间不容发,是“仁”还是“姑息”,是“义”还是“苛刻”等,也都在一念之间。直指本心,而非论“好恶之情”,这与朱熹的论旨一样。朱熹《答徐居甫》以为“心本为利,却假以行,与那真于为义者,其迹相似”可以称作“同行异情”,“为利”是有意的,掩藏在“为义”的外表下,常人这样做是虚伪,学人如此便是伪道学。从这一角度说,李梦阳此论有反对伪道学及弘扬士气(重视信念的力量)之意图。
朱熹《答徐居甫》还说:“须是读书讲义理,常令此心不间断,则天理常存矣。”这是理学家的“存养”工夫。而李梦阳却并未强调这样的工夫,而要人们“素位而行”“日行不悖”即可。《论学上篇》说:“爱生于公则遍,生于私则偏;生于真则淡而和,生于伪则秾而乖,生于义则疏而切,生于欲则眤而疑。”[5]4b看起来都是“爱”,却有产生于公或私、真或伪、义或欲之不同。普通民众很难弄清其间的区别,洞明世事者可以通过其表现加以判断,而行为主体则是完全“自觉”的。从积极的角度看,这又与王守仁淡化“格物致知”工夫,以“致良知”为“体用一源”“发而皆中节之和”的为学进路相似。只是王守仁以讲学为手段,把这样的进路讲得易知易晓,从而接引无数后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李梦阳这些文字却是扁平的,沉埋于故纸中,至今尚被读者误解。
话说回来,在一个物质文明较为发达而道学家却普遍“讳声利”的时代,强调“理欲同行异情”,又似有为“人欲”张本的嫌疑。《化理上篇》说:“天地间惟声色,人安能不溺之?声色者,五行精华之气以之为神者也,凡物有窍则声,无色则敝,超乎此而不离乎此,谓之不溺。”[4]2b能够向声色世界敞开心扉且自信将不为所溺,本就表现出一种开放而有容的心态。而与严守“克己”之训而峻拒“人欲”的进路相比,又似对“欲”有所宽容。加之关于李梦阳晚年生活或近毫奢的记载,因此不少研究者将李梦阳对此一命题的重拾视为晚明重情思潮的先声。王著在谈这一问题时,用的标题是“‘情’的重要性”,结论是李梦阳“强调人应当注意以恰当的方式表达‘情’”[1]153,似与这种论调比较接近。
其实李梦阳所谓“同行异情”,意谓“貌似而实异”,呼吁人们由“貌”鉴“实”,而不是关注喜怒哀乐等“感情”的表达是否得当。在李梦阳看来,“理”“欲”本自分明,即使表现过激也无妨。其《大梁书院田碑》说:“故宁伪行欺世,而不可使天下无信道之名;宁矫死干誉,而不可使天下无伏义之称。”[3]1451就“情”的表现而言显然有过当之嫌,但出发点在“道义”,则不顾世人之毁誉。
五、诗学与政教之关系
王著第六章“‘学’的内容”中认为,“李梦阳对‘史’与‘诗’抱持着功利的态度,将它们视作为国家更为宏大的目标服务的‘学’的对象”[1]180。对此笔者深为赞同。尤其在“引言”的开头,作者征引英国人菲利普·西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所提出的诗歌优于历史和哲学的观点,以此引出李梦阳反对“后世谓文诗为末技”的看法,颇具启发性。按照笔者的理解,李梦阳和西德尼都十分重视诗歌在社会政治和道德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而不仅仅把诗歌视为一种抒写个体感情、虚构艺术形象的文学形式(“末技”)。但这一看法并未贯穿下去,就在“引言”接下来的部分,作者就把李梦阳倡导的“复古”定义为“一种形式主义(formalistic)的方法”,强调“其使用者相信古代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体裁、语言和文风,而非内容,因而它们的精髓能够被重现于当代”[1]5。这就出现了矛盾:与内容无关的“形式主义”不正是“末技”吗?如果它是李梦阳复古的核心要义,其“学”如何能为国家更为宏大的目标服务呢?
在李梦阳所谈的“治道”中,风教(风化)占重要地位。《治道篇》说:
《书》曰:“汝惟风,下民惟草。”又曰:“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政之行,风行之也。关羽威振华夏,陶侃千里不拾遗,亦其风耳。李斯论囚,渭水为赤,而关东盗愈繁;汉武令直指使者诛捕无道,而海内愈扰,以不知风耳。传曰:“知风之自。”[4]17a-17b
先引《尚书》《论语》之言,再证之以关羽、陶侃之事,复以李斯(引者按:应为商鞅)、汉武帝为戒,得出“政之行,风行之也”这一重要结论。重风化的观点在李梦阳的文集中反复出现。如王著也曾引用的《观风亭记》中的一段:
夫天下之气,必有为之先者而鼓之,则莫神于风。……诗者,风之所由形也。故观其诗以知其政,观其政以知其俗,观其俗以知其性,观其性以知其风。于是彰美而瘅恶,湔浇而培淳,迪纯以铲其驳,而后化可行也[3]1641-1642。
这段话理论性很强。“气”在李梦阳的哲学中具有(准)本体意义,而“风”为气之先锋,对民人起到形塑作用,这种形塑深入、微妙,但并非整齐划一。它因顺于民人之“性”,表现为各地不同的风俗与政事。诗(这里指“采诗”)则是一个地方政事与风俗的最直接体现。观诗而知政治、风俗,进而知民人之性,又进而可以探察到微妙的“风”。这样看来,“风”与“诗”具有直接的、内在的联系,或者说“诗”是“风”的表现形态,地方官可以通过“诗”把握到“风”的脉动,再对症下药,达到化感民众、治国安邦的目标。
李梦阳此处所言之“诗”是来自民间、表现了民人之“风”的作品,其《诗集自序》所谓“真诗乃在民间”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至于“文人学子之韵言”,既不能上承雅、颂的传统,离“风”更远,从治国理政角度说可不必作。《空同子·论学上篇》也表达了一样的看法:
或问:《诗集自序》谓“真诗在民间”者,风耳;雅、颂者固文学笔也。空同子曰:吁,《黍离》之后,雅、颂微矣,作者变正靡达,音律罔谐,即有其篇,无所用之矣。予以是专风乎言矣。吁,予得已哉![5]2b-3a
“文学”就是“文人学子”的省文。这里也是说,文人学子不能承继雅、颂传统,即使有一些效仿之作,也不能发挥雅、颂所起的作用。
王著第四部分以“自我表达”为题,概括李梦阳关于诗歌的主张,认为他呼吁学习民歌的意图是“帮助学诗之人通过学习民歌表达感情的方式,找到自己真实的声音”[1]245,如《郭公谣》细致描写鸟儿的啼鸣,“似乎提醒人们,人的情感可以被自然的声音唤起”。王著认为这是“李梦阳诗歌理论的核心观点”,“自我的在场是发现自我和表达自我中必不可少的第一步”[1]247。全书的《结语》部分还强调李梦阳有一种强烈的信念,“认为诗歌应当主要用于表达个人的感情”,“他坚信作者只有通过诗歌,而不是散文或其他诗歌之外的文学形式,才能表现其真实的个性,并被人观察到”[1]284。书中说的“自我”“个人”“个性”,应该是没有功利意图的。作者说:
尽管李梦阳理论中功利的方面强调文学创作能为国家提供反映当时的风俗的镜鉴,但他同样关心文学关于自我表达的审美面向。这两个方面彼此联系,但不应被混为一谈。这种关于自我表达的论断,创造出一个与国家对“文”的宏大目标分离的独立空间,在其中,自我的实现成为了“学”的终极关切。在其他思想活动中,李梦阳试图使士人之学成为国家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与之相反,他对“文”的理解鼓励个人重视“文”本身的价值[1]298。
这里的看法,用国内学界习惯性的表述,就是说李梦阳的诗论既有重政教的一面,也有重审美的一面。一般认为,这两方面不是彼此独立的。李梦阳对诗歌并不缺乏艺术方面的关切,但在理论表述上则从来没有放松对“因义抒情”的强调,他始终将所抒之情限定在“正”的范围,而不提倡抒写私人化、个体性的感情。《与徐氏论文书》拿“风”来比况朋友之间的唱和,直指其化感作用:“足下亦观诸风乎?浏浏焉其被草若木也,沨沨溶溶乎,草木之入风也,故其声輷礲轰砰,徐疾形焉,小大生焉。”[3]1911-1912对此王著也有论述,书中说:
李梦阳相信,尽管诗歌最初是用于自我表达,这也是它最重要的目的,但表达自我的方法与形式密切相关,而正确的诗歌形式是自然的产物。只有当“情”通过这些形式得以正确表达,诗歌才能产生共鸣,超越现实中的差异并创造和谐一致的契机,使个性彼此统合,走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因此,李梦阳的目标在于超越地区主义并建立一种诗歌理论,作为交流“情”的共同平台[1]299。
按照笔者的理解,这段精彩的论述是为了说明,李梦阳所追求的“自我表达”,其目的在于通过感情的“共鸣”“使个性彼此统合”,这就是李梦阳常提到的“鸣鹤在阴,其子和之”,以及“孔子与人歌,必反之而后和”,也就是在诗唱和过程中自然产生化感作用,使人们的感情达到“和”的效果。诗作为“自我表达”之方式,不自觉间担负着“风化”的任务。这样,“自我表达”也就不可能成为“与国家对‘文’的宏大目标分离的独立空间”。
因此在笔者看来,李梦阳的诗“学”正是为治国的宏大目标服务,或者换一种说法,他把诗视为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途径。这一途径要靠诗人去实现,而无法依赖官僚体系。王著认为李梦阳“将文学视为一种严肃的追求,即使它独立于日常行政事务,并且,它重视通过个人的努力而非自上而下的国家机制实现的共性”,这很对。诗人通过个人努力实现了“自我表达”,同时也就实现了“风教”的责任,在国家治理中尽到了自己的力量,而不需要案牍劳形或“鞭挞庶黎”。当然,这都是就理想状态而言的,《诗集自序》愧言自己弘、德间的诗都是“文人学子之韵言”,从愧悔的语气看,不能把这类脱离了政教理想的创作视为其对于诗“‘学’的终极关切”。
六、李梦阳的思想史地位
王著之所以认为李梦阳论诗“创造出一个与国家对‘文’的宏大目标分离的独立空间”,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李梦阳诗论本身很复杂,特别是与何景明论争时自称固守“先法”“尺尺而寸寸之”,给人“形式”本身即目的之印象;二是作者认为李梦阳“要求承认真理的多样性,以及为了不同的目标,‘学’应当具有不同分支的合理性”[1]251。后一方面着眼于古人关于知识领域划分的观念,尤能体现作者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独特视角。书的引言部分引包弼德的观点,指出胡应麟之博学表现出对追求“统一性与一致性的理想世界”的宋代道学的背离,表明其“更乐于去理解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原本面貌,而非它们应该呈现的面貌”[1]9,并由胡应麟上溯到王世贞,再上溯到李梦阳,指出“道学自明初被尊为正统以来,其思想本身及其界定士人之学的方法,正是在李梦阳所处的时代第一次遭到了强力挑战”[1]10,这是独辟蹊径的论述,颇有启发性。但笔者以为,就追求博学和知识领域的多元而言,李梦阳与王世贞、胡应麟很难相比。正如本文第一节所言,《空同子》在“杂学”的表象下也还贯穿着维护理学的意图。
王著一个最重要的结论,是认为李梦阳的思想观念与宋代以来的传统形成了差异:自欧阳修到李东阳,人们普遍强调在各个领域所具备的各类知识与所秉持的思想观念之间是统一的,如曾巩“关于道德、政治和‘文’的知识都统一于一个完美的体系之中,它建立在六经中记载的普遍性法则之上”[1]79;到李东阳,“最高的学术体系仍然是将经学、史学和文学统合为一贯的、道德的知识体系,以效力国家为最终目标”[1]110;而到李梦阳,便与前人“分道扬镳”了,他的复古主义挑战了宋人一直到李东阳所维护的知识的统一性,“严肃且积极地捍卫知识的多样性”,他“将政治与文学视为彼此独立的领域,各自有其不同的纲领、目标和知识类型,需要专门的学习理论和实践”[1]111。而本文则认为,在李梦阳的思想观念中,政治与文学仍然未构成“彼此独立的领域”,文学始终要为国家治理、政治教化的宏大目标服务。
从古人关于知识领域、知识类型的观念和态度入手,“采取长时段的视角,将李梦阳的追求置于始自宋代的思想转型语境之中”[1]6,以此作为思想史分段的主要依据,是王著最突出的特点,笔者对此十分赞赏。只是沿着这样的思路,要找出一个划时代的人物,笔者以为王世贞比李梦阳更有代表性。当然由王世贞也还可以上溯,到祝允明、文征明、唐寅等,他们崇尚博学而不以理学为尊,但都是南方人,且在晚明文学界的影响远不及李梦阳。
王著进一步从“南北分野”角度解读为何李梦阳在治国与文学两个不同领域的影响会出现巨大反差,认为其“学以治国”的思想“试图使士人之学成为国家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298,具有北方特点;而其文学观念则更强调自主性,“呼应着南方士人的关切”[1]300,“与王阳明对道德哲学的态度非常相似”[1]289,从而使他在晚明时代成为文学领域的重要人物。这一论断同样很有启发性,且颇具说服力。尤其通过李梦阳对刘健批评诗人为“酒徒”的反感等材料,敏锐地捕捉到李梦阳诗学中的南方文化因子,并将其提升为考察李梦阳思想及其后世接受的一个主要视角,是全书最具思辨性和趣味性、也最为精彩的环节。笔者深为作者的思辨所折服。但细思之下,似仍不无可商之处。比如同样主张“学以治国”、属于北方思想系统的吕柟、王廷相等人都在中晚明思想界产生了一定影响,李梦阳论学之被忽视,应与他太过重视现象世界、思想较为驳杂有更大关系。而李梦阳的文学观在中晚明反响较大,则与王世贞、李攀龙等“后七子”的诗文复古运动有关。后者扬弃了李、何复古论中重政教的因素,主要从“形式”(体调)方面推崇前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李、何诗论的宗旨,使追摹和复现汉魏盛唐诗风成为新的复古目标,无关“风教”的“文人学子之韵言”也就取代“在民间”的“真诗”理想而被推崇。也就是说,到王世贞的时代,诗学才真正成为与经学、史学等其他学术彼此独立的“学”的领域。而这样的变化,又要归因于:随着政局发展,人们心中不再抱持李梦阳那种“学以治国”的宏大目标。李梦阳在晚明的影响,多半与“后七子”的推扬有关,或者说,晚明人所接受的李梦阳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后七子”重塑过的,而未必是李梦阳本人诗学观的直接反响。
以上就《空同子》与李梦阳思想观念的几个问题,提出了与王昌伟先生不尽相同的看法。这些问题都很复杂,见仁见智,值得深入讨论。王昌伟先生对于中国思想史、对李梦阳的思想观念有着深入的理解,全书展现的思辨气质和宏阔格局令笔者十分敬佩,书中精确之论在在有之,限于篇幅,不再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