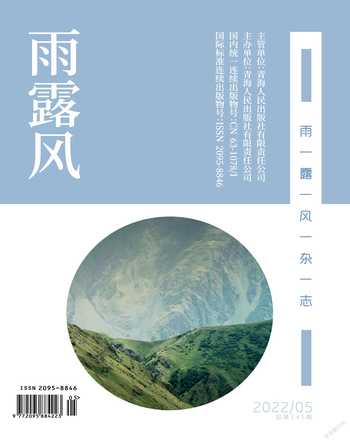试析李梦阳、沈德潜二人的诗学观
2022-06-19周晓丽

摘要:李梦阳、沈德潜是明清时期重要的诗论家,二人均以唐代诗歌为宗,推崇“格调”。本文首先分析二人诗学主张的历史语境,窥其诗学观发展的内在逻辑;其次阐述二人诗论中“格调”的内涵及实质,指出“格调”的差异所在;最后试图从诗之根本、诗格与人格之关系、新变方式这三个方面辨析二人的格调诗学观。
关键词:李梦阳;沈德潜;诗学观;复古;格调
一、诗学主张的历史语境
弘治年间,孝宗皇帝施行了一系列积极明智的措施,如罢斥奸邪、任用贤能、广开言路等,使得士大夫士气高涨,积极进谏。在文坛上,孝宗皇帝尊敬并鼓励儒士,以李梦阳为代表的诗文复古运动开始兴起。一方面,“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康海因文章创新被孝宗皇帝赏识,擢为状元,于是朝臣竞相追捧,热衷于诗歌创作。李梦阳在《朝正倡和诗跋》中提到:“诗倡和莫盛于弘治,盖其时古学渐兴,士彬彬乎盛矣。”[1]543以复古为中心的诗歌唱和逐渐成为社会的风尚。另一方面,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派在台阁之外关注到文学审美艺术,使文学慢慢由依附政治向审美特质过渡,强调诗学汉唐,从而为前七子复古运动提供了条件。因此,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复古运动是文学受到政治的支持,又开始独立于政治、重视审美特质的结果,这一时期的文学与政治是一种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状态。
在传统史学话语叙述中,中国古代封建王朝里的康乾时期是最后一个盛世。从康熙后期开始,“盛世”出现在清朝官方语言中,到乾隆时期,“盛世”被频繁提起,“华夷有别”的传统思想逐渐被打破,“天下一统,满汉无别”的民族关系逐渐被认同,遗民情愫不再强烈,用世精神日益增强。热爱诗歌的统治者大力提倡文教,采取“为政尚宽”的怀柔政策来笼络人心,塑造宽厚仁爱的统治者形象,且多以诗歌为媒介选拔人才。故这一时期诗歌多四平八稳,体现盛世文人的平和心态。沈德潜晚年与乾隆皇帝以诗唱和,均推崇唐诗,是当时主要的复古势力。
在诗坛上,为矫前后七子模拟肤廓之恶,纠公安派浅率空洞之弊,清初宋诗热出现,代表人物为钱谦益。但矫枉过正,产生流弊。为纠正宋诗热的流弊,“神韵”一词由王士禛正式提出,要求诗歌以“妙悟、韵味、禅趣”为审美取向,反对政治等因素对诗歌的影响,故“神韵说”存在“詩中无人”,脱离现实生活的明显弊端。沈德潜的格调理论的主要目的就是纠正宋诗派和神韵派偏失,故其肯定明七子的复古运动,认为“诗不学古,谓之野体”“诗至有唐为极盛”。
通过对李梦阳、沈德潜二人诗学主张的历史语境进行分析,不难发现二人的诗学观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原因,均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当时政治、社会的实际需要,同时也是明清诗歌史演进嬗变的必然结果,有其内在的深层逻辑,对当时诗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格调”的内涵及实质
“格”“调”是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中两个批评术语。《文心雕龙·隐秀》篇有“格刚才劲”,《才略》篇有“旨切而调缓”,南朝刘勰是较早以“格”“调”论诗的文论家。宋代严羽的诗学主张对明清格调理论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其《沧浪诗话·诗辨》道:“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2]1这是明代格调派“诗必盛唐”的理论依据。“格调”作为一个词语出现在文学批评中,并与复古派挂钩,源于明代李东阳。“眼主格,耳主声”,格是体格,可以通过眼睛看到;声是声调,可以通过耳朵听到。因此,“格调”一词偏重于诗歌的外在形式。
作为前七子的代表人物,李梦阳继承并发展李东阳的格调说,将“格古”“调逸”看作是诗歌创作最难的两部分,在此基础上,又提出“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1]477。由此可以发现,李梦阳的格调说指诗歌的体格和声调,并且与他尊唐黜宋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格调创作的实践中,李梦阳强调“尺寸古法”的创作原则,过分追求与古人已成之法的形式一致,在很大程度上使诗歌失去生命力。当然李梦阳也肯定诗歌言志、贴近日常生活之用,如称:“夫诗言志,志有通塞,则悲欢以之,二者小大之共由也。”[1]470于是,这就要求诗歌要一丝不苟地模拟古格,同时也要达到情感和古格的高度统一。但是古格仅是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下的抒情言志,一味套用只会湮灭个人的性情。所以日常性灵与模拟古人两者往往是冲突矛盾的,故在诗歌真实的创作实践中,李梦阳还是以“格调”为主,最后才考虑“情以发之”。
沈德潜是“格调说”的集大成者,继承并发展了明代的格调论。在体格声调方面,沈德潜和李梦阳的“格调”的内涵基本一致,沈德潜对“法”的理解稍有进步。比起李梦阳的“尺寸古法”,沈德潜的“以意运法”更符合诗歌创作的特点,避免将法变成僵硬死板的框架。沈德潜的“格调”还注入了一些新鲜的元素,如艺术风貌、品第水准方面的特征。“诗格清真”[3]894、“辞意新而风格自降矣”[4]540等是对个人风貌、时代风貌的评价。“兹取其格,不在语言之工”[3]700表明“格”不单指语言工美。他又指出:“王维、李颀、崔曙、张谓、高适、岑参诸人,品格既高,复饶远韵,故为正声。”[4]540这说明“格”还包括诗人的自我修养和道德风尚。
综上可知,李梦阳格调理论是一场“诗必盛唐”的复古运动,突出“格”与“调”,即体格声调在诗歌创作中的权威地位,其“格调”是狭义上的格调。沈德潜“格调说”包括体格声调、个人风貌、时代风貌多方面的要义,在前七子格调论的基础上有所修正,有一定的审美理趣和艺术价值。
三、格调诗学观的辨析
格调诗学观在明清时期盛行,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分析李梦阳和沈德潜对“格调”内涵理解的基础上,不难发现二人的格调论有很多相同点,同时也有各自的特点,故从诗之根本、诗格与人格关系、新变这三方面辨析二人格调诗学观。
诗歌本质论是诗歌理论的基础。李梦阳主张诗之根本是言情,是个人情感的真实表露,“故诗者,吟之章而情之自鸣者也”[1]473。在《鸣春集序》中,李梦阳借用春天鸟鸣这一自然现象来论述诗歌的本质特征,故其谓:“有窍则声,有情则吟。窍而情,人与物同也。”[1]473在《题东庄饯诗后》中,李梦阳对分离时的怅惘之情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所谓“天下有必分之势,而无能己之情”[1]473,分离已经是既定的事实,无法更改,只能产生离别之情。接着,李梦阳进一步指出,当一个人因为分离而发生情感波动时,就会在语言上有所表达,语言的表达再加上音律的配合,就会产生诗歌。因此,在李梦阳的诗学观中,个人情感的产生是诗歌的根本。而沈德潜的格调说是温柔敦厚的唐音“格调”,其核心是儒家传统诗教观,借助诗歌来加强正统封建文学的规范化,振兴正统封建文学。虽然,沈德潜也强调性情,如在《说诗晬语》中指出:“性情面目,人人各具。”[4]557沈德潜认为人人都具有性情,但各不相同,但他所谓的性情并非个人情感,而是合乎道德的情,如他在《清诗别裁集》中指出:“诗必原本性情,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5]2因此,沈德潜是借性情来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其诗之性情观具有强烈的保守色彩。BE50C0A0-D163-4D4C-9B31-4A728B0A0983
在人格与诗格二者的关系上,李梦阳认为诗歌反映人的思想感情,自然可以通过诗歌创作去评鉴一个人的品行,即“诗者,人之鉴也”[1]469。在《林公诗序》中,李梦阳对石峰陈子“人乌乎观也”的观点进行反驳,他指出人的语言不一定能够表现内心所想,但是诗歌的语言一定能展现其内在人格特质。诗歌可以用来“谛情、探调、研思、察气”[1]469,情调思气多方面的渗透,导致诗歌并不能像日常语言那样作假,而是人格的真实体现。因此,他从王维的诗歌中看出王维信奉佛教的个性特征。沈德潜则更加重视诗人的人格,并将人格放置于高出诗格的位置。他同样认为通过诗歌可以洞察人的内心、了解人的品性,并进一步地将诗人品格的高低与诗歌创作的优劣划勾。在评价诗作时,沈德潜经常将人格和诗格相联,如他对陶渊明诗歌的推崇就是因为陶渊明高尚的人格操守而形成“旷世独立”的诗歌风格。因此,沈德潜提出了真诗的标准,即“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4]524,只有高尚的胸襟与抱负,再加上优秀的学识,才能创作出一等一的真诗。可见沈德潜将人格作为诗歌创作品质的重要标准。
李夢阳和沈德潜二人是明清复古派的重要人物,在第二部分已经对二人诗歌拟古的方式进行了辨析,故不再累述。实际上,二人在探讨复古理论的同时也有一些新变。上文已经提到,李梦阳模拟古格的格调说和自然性灵的主情论是相矛盾的,无法实现兼顾。在不断涌现的思想矛盾和选择困惑中,李梦阳选择了拟古。但是到了晚年,李梦阳也发现了拟古存在的严重缺陷,尝试追求“真诗乃在民间”的新变。这一观点主要在他的《诗集自序》中,他评价自己的诗歌为“文人学子韵言之诗”,而真正的诗是天地自然之音,是“途粤而巷讴,劳呻而康吟”[6]102,也就是民歌。沈德潜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更加清晰地看到了格调论的弊端,因此他不佑于拟古,而是讲求“以意运法”,强调诗学法则在诗歌创作中的合理运用,使诗人的才情不被格调所拘束。此外,沈德潜也脱离了格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绝对主张,在诗歌上肯定中晚唐诗歌的价值。从他的《唐诗别裁集》选录诗歌占比来看,沈德潜并没有忽视中晚唐诗歌。他对中晚唐诗人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李商隐等的诗歌持赞赏态度,而非视而不见。此外,他也肯定了部分宋代诗人及其诗歌的价值,比如苏东坡和陆放翁,充分肯定苏轼闲适旷达、笔力豪迈的七言诗及陆游慷慨悲愤、言志抒情的爱国诗。
四、结语
作为明清两代格调派的重要人物,李梦阳和沈德潜的诗学观显示出高度一致性,二人对复古诗学的推进起着重大的作用。追溯二人诗学主张的历史语境,可以发现二人的诗学主张具有典型的时代意义。二人对“格调”的内涵及实质的理解稍显差异,其具体的格调诗学观也显示出同中有异的细微差别,并非简单的接受或者革新的关系。
作者简介:周晓丽(1998—),女,汉族,江苏盐城人,苏州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诗文。
参考文献:
〔1〕李梦阳.空同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2〕严羽.郭少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3〕沈德潜.清诗别裁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4〕王夫之等.清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
〔5〕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6〕蔡景康.明代文论选[M].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BE50C0A0-D163-4D4C-9B31-4A728B0A0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