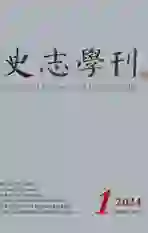阮孝绪《七录》“注历部”演变之考释
2024-05-21袁昆仑

摘 要 阮孝绪《七录》“记传录”对史书的分类,奠定了中国古代目录学史部分类的基础。“注历部”作为其中的一类,具体何指,历来说者不一。文章认为,起居注在魏晋南北朝大量出现,具备独立分类的条件。同时,这一时期,以“历”命名的史书数量较多。因二者体例、内容等相似,《七录》将其合称“注历部”。《隋书·经籍志》(简称《隋志》)将起居注独立,“历”类史书并入杂史类。其命名的变化,与《七录》“子兵录”相同,《隋志》统称子部。“注历部”的命名和改变,是魏晋至隋唐史学发展和史籍亡佚在目录学中的反映。
关键词 史部目录学 《七录》 《隋书·经籍志》 注历部
阮孝绪《七录》“记传录”类,即后来史部,有“注历部五十九种,一百六十七帙,一千二百二十一卷”(P323)。 “注历部”为何类史籍,历来说者不一,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将注历部和起居注类等同,如蒋元卿、来新夏和马开樑诸先生认为《隋志》中的起居注类指《七录》注历部(P52,169,151);二是认为“注历部”包括《隋志》中的“古史类”和“杂史类”,如王重民先生的《对于〈隋书·经籍志〉的初步探讨》一文;三是认为“注历部”等同于《隋志》的“古史类”,也即后来的编年体史书,如姚名达、文甲龙两位先生所作图书分类表格中,认为注历部即编年类(P78,38);四是对“注历部”收录为何书不作讨论,如余嘉锡、汪辟疆先生等。总之,目录学者多从目录学发展的角度,考察分类沿革相承,治史学史者也偶有涉及,但二者对“注历部”何以指此均不作解释。学术界既有如此多的不同看法,笔者想另辟蹊径,对其重新探讨,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七录》与中国古代史部目录分类
中国传统史学发展至魏晋南北朝,迎来了繁荣阶段,史书种类、数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与之相应,后世之史部逐渐在目录中独立,但目录学的发展却略显滞后。因此,《隋志》在述及汉至魏晋南北朝目录学发展时,称:
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自是之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博览之士,疾其浑漫,故王俭作《七志》,阮孝绪作《七录》,并皆别行。(992)
可以看出,劉向和刘歆之后,图书目录虽有编纂,但仅“记书名而已”,致使“不能辨其流别”。因此,“博览之士,疾其浑漫”,王俭因之作《七志》,阮孝绪撰《七录》,二书对典籍进行了细致分类。但《七志》中,史部并未完全独立,与六艺、小学等从属于经典志。《七录》则不同,记传录作为其中的一录,专门收史部书籍,并进行细致分类。
至魏徵修《隋志》,又“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离其疏远,合其近密”,撰成《经籍志》。从分类来看,《隋志》中史部分类更多地沿袭《七录》,姚名达称“实则《隋志》部类几于全袭《七录》”(P65),也即此意。后世的史志目录分类多因袭《隋志》,因此,《七录》记传录的分类为后世艺文志中史部类别奠定了基础。兹将《七录》和《隋志》史部分类列表对照如下:
可以看出,《隋志》中史部的分类,与《七录》有很大的渊源关系。而从中国古代史部目录发展的角度看,《七录》及其之后的史部分类,也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史部目录的分类随时代变化而变化,或增或减,皆与当时史学观念和史书状况有关。如“鬼神部”,后世史部目录鲜见其传承。而“诏令奏议类”因数量较少,很长一段时间并未单独分类,且属于集部。但随着此类书籍的增多,以及古人对诏令奏议性质认识的改变,渐入史部,至《四库总目提要》合称“诏令奏议类”。其次,《七录》和《隋志》在命名上具有很强的时代性。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制度充分发展,直接导致谱学盛行,与之相关的书籍大量出现。与此同时,与九品中正制相适应的行状这一文体对人物生平等进行写实,其也有大量典籍出现。“谱状部”正是这一政治文化特征在目录学中的体现。后世状类文体及谱学渐衰,谱状部先是改成谱系类,至《四库总目提要》,谱系类也被删除。最后,史部的分类也是当时史学观念的反映。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史观念虽已出现,但何种史书体裁为正史并未形成广泛认同,“国史”仍是当时对纪传体、编年体等重要史籍的称呼,因此,在分类上以国史部称之。这些特点相互交织,是政治文化、史学发展及史学观念等在目录学中的体现。
因此,对“注历部”究竟所收何书的探讨,不仅可以窥见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也可考察当时史籍现状、史书体例及目录分类所体现的社会文化意涵。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起居注”和“历”书
最早对“注历部”进行说明的是姚振宗,他在《隋书·经籍志考证》“起居注”后按语认为,《隋志》正史、古史、杂史、起居注四类,乃取于《七录》国史部和注历部(5302)。
从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及观念来看,姚氏对《七录》和《隋志》中分类关系的认定较为合理,但缺少深究,略显不足。因此,若以姚氏此说为据,将《隋志》起居注类等同于《七录》注历部,不当。而且,从现存史料来看,“注历”一词在魏晋之前并不常用。相反,“起居注”之名在魏晋南北朝却相当普遍,若“注历部”指《隋志》起居注类,命名上为何不直接称之?因此,笔者认为“注历部”具体何指,仍有探讨空间。根据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及《七录》相关类别的命名规则,“注历部”应包括《隋志》中的“起居注”以及名称为“历”的史书。
先秦至魏晋,随着史籍的不断增多和目录学的发展,对书籍的分类也越来越明细化。 “注历部”之称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图书分类细化在命名上的体现,这与当时起居注和“历”类史书的增多有很大关系。
从现存文献来看,“注暦”一词在隋唐之前很少合用,隋唐之后的文献中较常见,表示在历法上标注吉凶、干支、五行、气候等。而“注历”用于图书分类命名,除《七录》外,无记载。因此,从整体词意及目录沿革上探讨该命名所指为何种史书,似不恰当。将其拆分,分别探讨“注”和“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目录学中所能代表的史书种类,则较为合适。
“注”,“灌也,从水,主声”(P370),最初的含义与史籍无关。后来,逐渐引出其他含义。段玉裁称“释经以明其义曰注”(P555),表明含义在逐渐扩大。随着字义变化,与图籍相关的“注”意开始出现,如“注记”一词,有“国家不废注记之官”、御史掌“注记言行,纠诸不法”,以及“注记篇籍”“专管注记”等记载,表示记录、注解文献之意。《七录·序》对与注记有关的文献有说明,认为《谱》属于注记类,且“宜与史体相参,故载于记传之末”(P320)。若“注”指注记类,那么《谱》就应纳入注历部,这与《谱》单独分类明显矛盾。除史部外,《隋志》“子部”天文和历数类中收有“《太史注记》六卷”,不仅与史部有别,且种类较少。因此,从“注记”的角度考察“注历部”,不恰当。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史注解之风盛行,“南北朝以至于唐,注史的风气极为盛行,比如《汉书》,由汉至南北朝,据颜师古所列即有二十三家”(P235)。再如对刘向《列女传》的校勘注释,“东汉时期有马融为之训解,曹大家(班昭)作注;三国时有曹植、虞韪妻赵母(虞贞节)注本;晋代有皇甫谧、綦毋邃注本”(P1),注家众多。刘知几《史通·内篇》“补注第十七”对注经风气进行讨论时,将魏晋南北朝注史之风列出,可见当时注史之盛况。但是,史注书籍在分类上与原书类别相同,并不单独分类。因此,史注应排除在“注历部”中“注”之含义外。
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一类史书获得迅速发展,即起居注。《隋志》起居注类共收录44部,其中魏晋南北朝41部,足见数量之多(P51,P105-108)。刘知几《史通·外篇》载:“起居注者,编次甲子之书,至于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随事记录,言惟详审。凡欲撰帝纪者,皆称之以成功。即今为载笔之别曹,立言之贰职。”(P321)所谓“编次甲子之书”,是针对起居注体裁而言,以编年系之;“凡欲撰帝纪者”表明起居注是撰修国史帝纪的重要材料,但其本身并非国史。如《梁书》记载,以裴子野“为著作郎,掌国史及起居注”(P443)。魏收称自己“迁散骑侍郎,寻敕典起居注,并修国史”(P2324)。《隋书·百官志》载“秘书省……著作郎一人,佐郎八人,掌国史,集注起居”(P723)。《通典·职官》敘著作郎职责时,也称“掌国史,集注起居”。可以看出,史料中均将掌国史和注起居分开,表明二者非统属关系。就内容和性质而言,起居注作为帝王起居言行的记录,与国史有别,是纂修国史的重要材料。从数量来说,起居注大量出现,具备独立分类的条件。因此,在目录分类上将其独立,位列国史部之后,较为合理。
“歴”,“过也,传也,引伸为治暦明时之暦”(P68),二字常常通用。当指代图书文献时,往往与历法有关。《汉书·艺文志》中已存在与“历”有关的书籍分类,即“历谱类”,包括历法、算术、年谱、世谱类书籍。后世目录,如《七录》“历算部”、《隋志》“历数类”,也收录历法、算术类书籍。但《七录》外,史部与“历”有关的分类,较为少见。因此,从“历”字含义和目录分类沿革角度去考察《七录》“注历部”中“历”类为何种史书,不当。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类名称为“历”的史书,因后世留存较少,长期被忽视。《隋志》和两《唐志》史部收有不少此类史书。如《隋志》“杂史类”有“《魏武本纪》四卷,梁并《历》五卷……《陈王业历》一卷”(P960)。《旧唐志》“杂史类”载“《年历帝纪》二十六卷,姚恭撰。《长历》十四卷,《通历》二卷,徐整撰。《杂历》五卷,徐整撰。《千年历》二卷。《国志历》五卷,孔衍撰。《千岁历》三卷,许氏作。《年历》六卷,皇甫谧撰。《帝王年历》五卷,陶弘景撰。《通历》七卷,李仁实撰。《晋历》二卷”(P1996)。因亡佚,此类史书的具体内容虽较难得知,但仍可考察。如裴松之注《三国志》引胡冲《吴历》,《隋志》未载。笔者借助检索工具,共得《吴历》内容46条,多与东吴孙氏一族有关。其中和君主直接相关有24条,以孙策和孙权最多,其他22条中,与宗室相关7条、祥瑞4条,吴蜀交聘、曹操、刘备及日食等各1条。因此,该书很可能主要记东吴皇室事迹,并杂以天象等。
另外,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史部有魏晋南北朝时期徐整《三五历记》和皇甫谧《年历》,属“历”类史书。马国翰引《经编历》称《三五历记》主要记“三皇五帝事也,亦名《长历》”(P2461-2462)。《年历》与皇甫谧另一著作《帝王世纪》共十二篇,“起太昊帝,讫汉献帝”(P214)。马国翰辑二书内容均以天文为主,而将其归为史类,可见时人对二书性质的认识。笔者推断,因其记载内容久远,史事价值不大,遂逐渐失传,仅部分天文内容得以流传。
魏晋南北朝之后,“历”类史书虽减少,但仍有编撰。《旧唐书》卷149《柳登传》载:
父芳,肃宗朝史官,与同职韦述受诏添修吴兢所撰《国史》,杀青未竟而述亡。芳绪述凡例,勒成《国史》一百三十卷。上自高祖,下止乾元,而叙述天宝后事,绝无伦类,取舍非工,不为史氏所称。然芳勤于记注,含毫罔倦。属安、史乱离,国史散落,编缀所闻,率多阙漏。上元中坐事徙黔中,遇内官高力士亦贬巫州,遇诸途。芳以所疑禁中事,咨于力士。力士说开元、天宝中时政事,芳随口志之。又以《国史》已成,经于奏御,不可复改,乃别撰《唐历》四十卷,以力士所传,载于年历之下。(P4030)
可以看出,芳因“国史散落,编缀所闻”,及“以《国史》已成……不可复改,乃别撰《唐历》四十卷”表明,《唐历》与国史有别,二者性质不同。“载于年历之下”,说明《唐历》与笔者上文所列《吴历》《年历》一样,在性质上属于“历”类。此后,“崔龟从续柳芳《唐历》二十二卷上之”(P629),《新唐志》也载“柳芳《唐历》四十卷,《续唐历》二十二卷”(P1460)。而“芳以所疑禁中事,咨于力士。力士说开元、天宝时政事,芳随口志之”,表明该书内容是高力士口述,多为开元、天宝时禁中事,即与皇室相关,这与《吴历》中记载东吴孙氏一族事迹较多相似。因此,也可印证上文笔者对《吴历》内容的推测。
除《隋志》和两《唐志》当中收录,“历”类史书在魏晋南北朝之后的目录中也有反映。如郑樵《通志·艺文略》编年类下有“运历”门,专收此类史书,包括魏晋南北朝、唐、宋编纂,共“五十一部,一百四十八卷”(P1535),表明此类书的编撰和流传情况。此后,焦竑《国史经籍志》于编年类中仍有“运历”一门,与《通志》收书相同。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起居注”及“历”类史书,因其独特性和数量较多,在目录中具备了独立条件。且“历”类史书,内容以帝王或禁中之事为主,并将天文等内容融入,与起居注“录天子之言动法度”,且“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P1845)等,内容相似。加之“历”类史书与国史有别,这与“起居注”为修“国史”材料而非“国史”本身相同,以及二者体裁均是编年体。因此,《七录》将其合称“注历部”,位列“国史部”之后,较为合理。与之类似的分类有“子兵录”,兵书在《汉书·艺文志》为“兵书略”,《七志》称“军书志”。魏晋南北朝时期,“兵书既少,不足别录”(P320),《七录》遂将其合称“子兵录”,《隋志》则统一归为子类,命名上不再体现兵书,这是史籍消亡在目录命名上的体现。
三、“注历部”之名消失原因
目录学中的书籍分类,是目录学发展和一定时期图籍种类、学术发展及史学观念的反映。“注历部”在《七录》中出现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籍分类具有一定系统性,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即“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割析辞义,浅薄不经”,因此,魏征等“远揽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錄》,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P907-908),成《经籍志》,这是目录学在继承前史基础之上的创新发展。姚振宗以《七录》校《隋志》,称“唯史部之正史、古史、杂史、起居注四篇,不用阮例。余或合并篇目,或移易次第,大略相同”(P5043),这是魏晋至隋唐史籍亡轶严重,为保证新类目的纯正性及与当时史学观念相适应而作出的改变。“注历部”作为《七录》中的一个分类,因类例较为模糊,在后来的目录分类中没有明显的体现,与此有关。
书籍的消亡,在目录中表现为分类、命名的淡化,直至消失。牛弘“五厄论”,反映图籍散轶的严重情况,其中两次发生在魏晋南北朝(P1299)。唐武德时期,书籍再遭厄运,导致“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1](P908)。经过多次亡佚,修《隋志》时,很多图书已经不存,因此,《隋志》根据当时的图籍现状,参照前史及《七志》《七录》而成,并非完全因袭。“历”类史书,亡佚严重,《隋志》收录较少,为保证所属分类的纯正性,将其从《七录》有关部类中析出,散入它类。与此相似的“起居注”类史书,因内容以帝王起居生活等史实为主,在唐宋时期的目录分类中保留下来。但又因其性质为修“国史”的材料,在“国史”编纂完成后,此类史籍渐不被重视,亡佚较为严重,因此,明清目录中也鲜见有其分类。
总之,我们不应忽视,书籍数量的多寡,受特定时期学术文化、政治状况等影响,这也是其能否单独分类的重要因素。从《汉书·艺文志》将史部归入“六艺略”中“《春秋》类”,至魏晋南北朝史部逐渐独立,且在目录中的次序前移,分类明细化,这是中国史学繁荣发展的表现,也标志着中国古典目录学逐渐成熟。《隋志》因循前史,将图书分经、史、子、集四类,史部又分十四小类,既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繁盛在目录学中表现的继承,又是对经历战火之后书籍亡佚严重的总结反映。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发展表明,史籍的分类和命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魏晋南北朝时期,“起居注”和“历”类史书较多,因二书体例相似,内容重要,且“非国史之流”,《七录》将其列于“国史部”之后,称“注历部”。随着后世“起居注”和“历”类史书的纂修及消亡,“起居注”或独立,或并入它部,“历”类史书则散入编年和杂史之中,直至消失,这正是中国古代目录学分类、命名等因时而变的表现。史学是一定时期社会发展的反映,而史部分类不仅是史学繁荣的具体表现,更是特定时期对史籍性质认识、史学观念和政治文化的反映。因此,透过注历部的考察,也可看出中国古代史学、目录学和社会文化的关系。
(责编:张文娟)
Study of the Evolution on the "ZhuLibu" in Ruan Xiaoxu's QiLu
Yuan Kunlun
Abstract Ruan Xiaoxu's QiLu establishe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historical works in ancient China, particularly in the field of cataloging. The category known as ZhuLibu has been subject to varying interpretations over time.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large number of QiJuzhu has provided the conditions for independent classification in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Meanwhile, a large number of historical records called "Li" appeared. Because of the similar styles and contents, they are collectively referred as "ZhuLibu". In the book of SuiShuJingJiZhi(Abbreviated as SuiZhi), the QiJuzhu is independent, and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Li" is incorporated into miscellaneous history. The change of its name is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ZiBinglu” in QiLu, the SuiZhi are collectively referred to as the Zi.The naming and change of the "ZhuLibu" is the refl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y and the serious loss of historical records in the bibliography from the Wei Jin to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Key words Bibliography of History Department QiLu SuiShuJingJiZhi ZhuLibu
作者简介:袁昆仑(1988-),男,河南项城人,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中韩史学交流。
基金项目:本文为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东亚视野下的朝鲜王朝经筵讲史研究”(项目编号:L23BSS00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