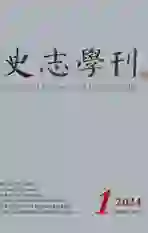虚实之间:后唐孔谦形象的生成与演变
2024-05-21贾发义闫卉
贾发义 闫卉
摘 要 20世纪70年代在山东省发现的孔谦家族墓群出土了四则墓志铭,分别为孔谦本人的《孔谦墓志铭》、其父母《孔昉夫妇墓志铭》、其兄《孔谨墓志铭》、其弟《孔立墓志铭》。除了孔谦本人的墓志铭外,其余三方墓志铭也都涉及对孔谦生平的描述。这些墓志塑造的孔谦形象与正史所载的孔谦形象截然相反:在正史中孔谦是盘剥民脂、蓄意敛财的苛吏,而在墓志中却摇身一变,成为竭力匡佐庄宗成就霸业的勋臣。这种反差除了可以解释为墓志撰写者受主家之托刻意美化墓主形象外,恐怕与庄宗、明宗之际的政治嬗变以及庄宗“中兴”脱不了关系。
关键词 孔谦 庄宗“中兴” 历史书写 政权华夏化
五代十国之“五代”主要是指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而这五个政权中后唐、后晋、后汉都是沙陀族人建立的政权,因此学界围绕这几个政权的研究多聚焦于民族融合,进一步说,学界对于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研究路径多统一于族源辨析与族群演变。然民族融合的进程既是刻意向无意的渐进,也是有形向无形的升华。庄宗夺取天下后,华夏化政权的建设以及明宗取代庄宗后即位合法性的构建,均是在这种胡汉融合的背景下展开的。孔谦作为历经庄宗“中兴”和明宗兵变的重要人物,能够为沙陀政权的华夏化进程还原历史情景的一角,孔谦家族墓志的出土无疑能为这种研究视角提供新的补充。孔谦的形象也正是在这种胡族政权华夏化的历史书写中,被反复地遮掩与塑造。
一、墓志中的孔谦形象——建国勋贵
在孔谦家族墓群出土的四则墓志铭中,《孔立墓志铭》(P230)成文最早,墓志主人是孔昉四子孔立,因疾病早亡于天佑十六年(919),后又于天佑十九年(922)与其父一同归葬于山东家族墓群。孔立墓志篇幅短小且行文多格套化,志文对孔谦的评价字数稍长于孔佶、孔谨两位兄长,运用“拔俗异禀”“佐命殊才”“居然国器”“终秉时权”的词汇形容孔谦,虽有溢美之嫌,却也透露出此时孔谦在晋王幕僚中的重要地位。成文于天佑十九年的《孔昉夫妇墓志铭》(P226),用全篇五分之一的笔墨着力描绘孔谦成就,重视程度明显超越孔谦诸位兄弟。其原因在于,在两方墓志间隔的三年间,孔谦就凭借出色的筹措军资之能从度支使升任度支司空,并逐渐得到晋王李存勖的重用。相较于以上两方墓志,孔谦本人的墓志对于孔谦在此期间所取得的成就有更为系统的阐述。
后梁贞明元年(915)三月,魏博节度使杨师厚去世,后梁末帝听从租庸使赵岩和判官邵赞的建议,将魏博军镇“分六州为两镇以弱其权”,但魏博自安史以来“父子相承数百年,族姻磐结,不愿分徙”,梁末帝贸然分镇,激起魏博士兵的反叛。魏兵劫持新任的天雄节度使贺德纶向晋王李存勖请降,李存勖以李存审为先锋成功进入魏县,收服魏博。与传世文献相照应,孔谦墓志也记载了晋王收服魏博的过程。墓志与史籍的出入之处在于,前者将晋王接受贺德纶的投降归为孔谦的谋划,碑文中载:“庄宗时为晋王,将固兴复之业,且以天授与人也,遂许之,则皆公始预谋而致于此。”除收服魏博的功绩外,墓志还记载了孔谦在收服杨刘中的过人表现。后梁贞明三年(917),后梁大将王瓒在黄河南岸的杨刘城铸垒窥伺魏州。孔谦为消灭这个窥伺点,为晋军南渡做准备,先是“公言于帝,使孙岳造船为浮桥”,后又“派其兄佶,密市荆笆五百扇送朝城”。等到晋王准备进攻杨刘时,黄河因天气寒冷“河冰流槎,一夕冻合”,晋王命人“铺荆笆进军”,晋军渡过黄河后一举拿下杨刘北镇。孔谦之所以遣其弟将荆笆先送朝城,是因为在正史记载中,晋王攻打杨刘城前“畋于朝城”(P7364)。所以,墓志关于晋军攻取杨刘的记载,战争细节及叙事逻辑与史籍高度吻合,可信度高。综上叙述可知,孔谦在李存勖草创初期所扮演的身份并不局限于度支使,在招降魏博贺德纶和攻取杨刘这两场重要的军事行动中,孔谦被塑造成足智多谋的智者形象。除军事才能外,墓志中的孔谦还极具理财之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军资的筹备。同光元年(923),晋军夺取郓城后,后梁派王彦章夜袭朱守殷,夺取景店、潘张、麻家口诸寨。为保杨刘,晋王命朱守殷“弃德胜北城”“徙其刍粮薪炭于澶州”(P7417)。据孔谦墓志记载,朱守殷的战略撤退仅拿走德胜城内“粮十五万,草十万”的军资,其余“悉焚之,所耗失殆半”。此次撤退虽保住了杨刘城,但烧毁的军资都是孔谦经年累月的蓄积。退保杨刘只还原了晋军军资耗费的冰山一角,在之后李周、李嗣源与王彦章在马家口的对抗中,军情急迫“日日不绝战”,所耗军费“比前之费又倍甚矣”。综上可知,孔谦在晋梁夹河争霸的诸多战役中,竭尽全力为晋军储备物资粮草来稳定大后方,即便是在将领失误损失过半粮草的危急情况下,也依旧保证了后续作战中粮草的正常甚至多倍供给,尽显“治财”之能。
其次是归降州镇的治理。如上文所提,魏博是“父子相承数百年”的军阀重镇,其各方关系利益盘根错节,晋王在接受魏博归降后,最难的是对于魏博州镇的治理。军事上,晋王任命李存进镇守魏州,经济上则“以度支使孔谦兼管”。后世对于孔谦诟病也多来自于此,认为其治理期间不恤民力,重敛苛税。但墓志所描绘的孔谦对魏博的经营又是另一番景象。据墓志所载,孔谦接手魏州之时,魏州“连岁遭大兵蹂躏,魏之四十三邑,其无民而额存者将十城,负疮痛而偷蚕垦者才三十余县”,故魏博百姓之穷困非孔谦盘剥所为,实是常年的战乱所致。另孔谦接手魏州以后,晋梁之间的战争并未停止,且魏州处于晋梁战场的大后方,此時孔谦对魏博的治理肯定是以战时经济“助军资”为优先,据战况不同协调各方利益。例如,在攻取让晋军痛失李嗣昭、周德威、李存进等五员大将的德胜镇时,孔谦为保证充足的物资供给,全力整顿魏州经济,“尽取魏之县邑、户口、田亩、桑柁、人丁、牛车之籍帐,役使以力,征敛以平”以助之,所以孔谦对魏州极尽“敛财式”的治理是迫于战时军费开支。与孔谦在军费方面的大手笔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孔谦的三餐饮食。在墓志记载中,孔谦是“止一食,无三四味,不取于公家,皆其二兄或出入利息,或服勤耕稼以资之”的节俭形象。
最后是庄宗称帝物资的筹备。李克用的河东集团虽以沙陀族为主,但与后梁朱温不同的是,李克用一生未有称帝之举,李克用的托孤大臣张承业也正是因为河东集团始终奉李唐为正朔,有复兴李唐的希望,才一直竭力辅佐李存勖(P7397)。但李存勖与其父面临的处境不同,一方面后梁朱温率先称帝斩断了李唐王室最后的血脉,另一方面河东集团不再是偏居太原的异族政权,而是越过太行山占领了黄河以北大部分土地的强阀,称帝是应时应势之举。同光元年(923)四月,晋王李存勖在魏州南面的牙城筑坛称帝,称帝时所需的天子旌旗、仗卫法物、中外羽仪等都由孔谦于三年前就“使临河尉韦可监护修之”。孔谦能在三年前就开始筹备晋王称帝之物,一方面是获得李存勖默许的迎合之举,另一方面也足以看出李存勖对孔谦信任至深,才放心将如此私密之举托付于他。综上,墓志此段所塑造的孔谦是晋王心腹能臣的形象。
二、庄宗明宗嬗代事对孔谦形象的重塑——从“失国罪人”到“天象昭雪”
同光四年(926)四月初一,后唐庄宗李存勖在兴教门之变中中流矢而死。四月初八,李嗣源以监国身份入住兴圣宫,接受百官朝见。四月初九,安重诲密杀通王李存确、雅王李存纪;十二日,李嗣源在洛阳斩杀元行钦;十四日,李嗣源下诏处死孔谦,同日,魏王李继岌行至渭南为仆人缢杀;二十日,李嗣源于西宫称帝,改元天元,史称后唐明宗(P490-491)。庄宗去世后半月有余,其宗亲、近臣就被诛杀殆尽。
李嗣源早年在李克用帐下效力,因在上源驿兵变中立下奇功,被李克用收为养子。李克用虽养子众多,但与诸养子多为凝聚军心的将帅关系。天佑四年(907),李克用身患重病,河东政权正处于后梁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天佑五年(908)正月,面对内忧外困的局势,李克用在弥留之际选择年仅二十三岁的李存勖承袭晋王位。此举可证明,在沙陀河东集团选任继承人时,血亲比养子更具优先权。同样,在庄宗去世后,后唐政权的顺位继承人应是皇长子李继岌和庄宗诸兄。李嗣源为构建其即位的合法性,必须将后唐帝位的潜在继承人皇长子、庄宗诸兄诛杀殆尽。相较于诸位宗室的隐晦死因,李嗣源为元行钦冠以“我儿何负于尔”(P272)的杀子之罪,但元行钦之死并非仅因其杀害李从璟。在继位前夕,除潜在继承人的威胁外,李嗣源还需对魏博兵变的正当性做出解释,所以在李嗣源构建的兵变故事中,正是元行钦屡次刻意阻挠,导致嗣源难以面见庄宗,申诉军情无果,进而被叛军拥立为首领。
解决了继位的合法性和兵变的合理性,李嗣源为何在继位前要急于处死一个无伤大局的租庸使呢?《旧唐书》完整地记载了李嗣源下令斩杀孔谦的敕昭。敕曰:
“租庸使孔谦,滥承委寄,专掌重权,侵剥万端,奸欺百变。遂使生灵涂炭,军士饥寒,成天下之疮痍,极人间之疲弊。载详众状,侧听舆辞,难私降黜之文,合正诛夷之典。宜削夺在身官爵,按军令处分。虽犯众怒,特贷全家,所有田宅,并从籍没。”(P492)
从敕昭中可以看出,孔谦被诛的罪责主要是“侵剥、奸欺”。结合庄宗宗室及元行钦之死,孔谦之死正是李嗣源继位计划的最后铺设——解释庄宗政权失势的必然性。唐末五代时期各藩镇割据久矣,庄宗虽征战几十载,但并未实现全国的统一,虎视后唐的敌对政权不在少数。此时一国之主骤然于英年死于兵变,若将亡国的罪责都归咎于庄宗,那庄宗建立的后唐天命也将无存,李嗣源即位后更难以自处。但若是将“侵剥、奸欺”的恶名加罪于孔谦,意在指明孔谦盘剥是导致庄宗政权倒台的罪魁祸首,那么庄宗失国的元凶就具象化到个人。这样的铺设既能凝聚因兵乱而离散的各方,也能证明后唐政权并未失去天命,为李嗣源不改国号继续承袭后唐名号张本。
孔谦死于天成元年(926)四月十四,墓志成文于天成二年(927)二月,即孔谦之子孔惟贞将孔谦遗骨自洛阳归葬山东永济县之时,墓志的撰写人是时任明宗谏议大夫的萧希甫。孔谦死后不到一年就能够被允许归葬祖茔,并有官方身份的友人为其撰写墓志铭,可以视为孔谦在官方层面默许下的小范围平反。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孔谦墓志的内容一改隋唐五代墓志格套化的写作思路,第一句就以“栾布哭彭越,汉皇不以为非”“李□哀单生,太宗不以为罪”为典故,开宗明义,写明萧希甫为身犯重罪而死的好友撰写墓志是“义之所在,礼亦无嫌”。若非上层对于孔谦之死的松动,孔谦这般前朝重犯又怎会有迁坟、写墓志这样大的举动。就撰写者萧希甫本人而言,为孔谦这样极具政治敏感话题的人物写墓志,若是私下行为早就会因此获罪或受牵连,可萧希甫此举并未影响其之后的仕途,后续还升任左散骑常侍。同时,孔谦墓志对于其死因的记载也与《旧唐书》相去甚遠,碑文中记载:“天成元年,有道主驭寰宇,初无罪公之旨,至是以人情归咎于公,为残虐之所,则不能违也。”在萧希甫看来,孔谦所犯的是“初无罪”“后以人情归咎”的欲加之罪。这篇极具平反意味的墓志甚至还大胆地点明庄宗失国的原因:“庄宗享国日浅,遽定中区,以有大功于庶民,遂怠于庶政。于是小人乘间魅乱荧惑,宰相备位偷贵,谏官钳口冒禄,俾我庄宗无节使之意,大侵民力,四海怨叛,以致失于天下。”这段叙述无疑是在为因“滥承委寄,专掌重权,侵剥万端,奸欺百变”而获罪的孔谦鸣不平,认为庄宗失天下是“小人媚乱”“宰相偷贵”“谏官钳口”所致。在萧希甫看来,孔谦虽然未能将主君侍奉成为超越尧舜的明君,却也“以身殉之”,不失为臣之道。
那官方又为何要选天成二年(927)二月这个时间点为孔谦尽归葬之仪呢?《五代会要》记载了明宗朝仅有的两次异常天象:“天成二年二月己酉,日中有黑气,壮如鸡卵,其年十二月壬辰酉时,西南方有赤气如火焰,约二千里。”(P140)古人对“日中有黑气”的天象又是如何认知的呢?《晋书·天文志》曾对这种天象做过解释:“日中有黑子、黑气、黑云,乍三乍五,臣废其主。”(P317)《五代会要》在异常天象后,又追加了占者“不出二年,其下当有大兵”的谶言。因此,“日中有黑气”的天象在古人看来是政权颠覆、天下大乱的前兆。五代政权更迭比较频繁,因此史官对于五代时期天象变动的记载亦有详略,所以能被史官明确记载的天象必对时局产生过影响。天成二年一月,荆南节度使高季兴截获川蜀地区运往中央的四十万钱帛,并出兵涪陵挑衅后唐中央(P7502)。无独有偶,天成二年二月,时任西川节度使的孟知祥杀害其兵马监使李严,似有反叛之嫌。高、孟二人的举动无疑都与“其下当有大兵”的天象相照应。同月,明宗决意先处置高季兴,削去高的一切官爵,并部署襄州节度使刘训、许州节度使夏鲁奇、西川节度使董璋分三路围攻荆南(P797)。同在二年二月,后唐官方还对庄宗雍陵所在地河南府新安县进行了级别调整,升新安县为赤县以奉庄宗雍陵。通过调整行政区划来侍奉当朝陵寝是唐代的惯例,玄宗朝就改同州蒲城县为奉先县以奉桥陵,后又升奉先县为赤县以奉陵寝(P255)。与二年二月陵祀变动相似,在同样出现异常天象的十二月,明宗对其嫡亲先祖进行了追封。《五代会要》有载:“明宗天成二年十二月,追尊孝恭皇帝聿,庙号惠祖,葬遂陵,追尊孝靖皇帝教,庙号毅祖,葬衍陵;追尊孝靖皇帝琰,庙号烈祖,葬奕陵;追尊孝成皇帝霓,庙号德祖,葬庆陵。”(P3)明宗两次陵祀变动的时间点与文献所载天象异常的时间点相吻合。后唐虽为沙陀族建立的政权,但在入主中原后,其首领就积极推进政权的华夏化建设。明宗对异常天象的回应,证实了胡族政权对中原王朝“天人感应”之说的信奉,即当天象发生异常时,嗣君通常会极尽山陵之事以乞求获得祖先庇佑。
在天成元年七月追封庄宗的册文中,载有宰相五人,使相二十三人。入册文的二十八人中,不乏因皇权交替而死的李继岌、李存渥、李存霸、元行钦,却唯独没有租庸使孔谦。所以孔谦能在天成二年(927)二月被允许归葬至祖茔,是获益于当时的异常天象,即明宗深陷负面天象舆论的弥补之举,通过默许为孔谦尽归葬之仪来安抚政权更替的亡魂。但当初诛杀孔谦所列罪状尤言在耳,当局不好仅因天象谶纬之说就为孔谦大肆平反。同时,唐官方深知墓志铭不同于神道碑,是随着墓主人的棺椁深藏于地下,除墓主家人及撰写者之外,所知之人甚少。所以,当局便选择为孔谦撰写墓志的方式,暗里稍尽祭祀之仪。如此看来,此次平反是极为机密的小范围“平反”,这份墓志也是写给早已去世的孔谦看的。正因如此,萧希甫在墓志行文时文风大胆,毫不避讳,墓志中的孔谦被塑造成建国贵勋的高大形象便不足为奇。
三、国史对孔谦形象的再塑——从“刻意丑诋”到“功过参半”
在孔谦家族出土的墓志中,成书最晚的是孔谦二哥的《孔谨墓志铭》(P234),该墓志成文于宋太平兴国九年(984)。与前三方墓志不同,孔谨的志文对孔谦的描述讳莫如深,只用“弟讳谦,丰财赡国臣、租庸使”几字简单介绍了孔谦在家中的排行和曾任官职。从前三方墓志对孔谦的记载,可以看出庄宗、明宗之际的政治嬗变对孔谦形象塑造的影响。从孔谨墓志对孔谦的隐笔,则可以看出天成二年(927)的“平反”并未让孔谦在宋初的恶名得以平反。与孔立墓志成书时间相近的《旧五代史》对孔谦的“恶”形象的再强化,便是很好的例证。
《旧五代史》对孔谦的记载主要集中在《旧五代史·孔谦传》,传记全篇七百余字,却有五百余字都在叙述孔谦谄媚求官的事迹。据《孔谦传》记载,孔谦屡次向郭崇韬求租庸使一职,郭崇韬却绕过孔谦先后将此职委任张宪、豆卢革、王正言。孔谦后又结交宦官景进,才最终获得租庸使一职。在此叙述中,豆担任租庸使后,孔谦为了将豆卢革从租庸使位置拉下来取而代之,“乃寻革过失”,将其从省库中挪用的数十万钱之事“以手书示崇韬”,革也因此被免去租庸使一职(P963-964)。此告发行径足以使得孔谦与豆卢革两人交恶,然在孔谦想力推王正言就任租庸使时,豆卢革全然忘记之前构陷之嫌,大方倾听孔谦“鄴都本根之地,不可轻付于人……诏书既征张宪,复以何人为代?”的意见,向郭崇韬进言委任王为租庸使。前后相悖的人物关系,打乱了孔谦反复横跳求官故事的叙事逻辑,降低了此事件的可信度。
除以上罪名外,《旧五代史》罗列的孔谦罪名与明宗赐死诏内容高度相似,昭书中的“专掌重权,侵剥万端,奸欺百变”关键字眼,在其他涉及孔谦的描绘时被反复提及。例如,同光三年(925)两河大水,庄宗问计孔谦未成,文献却评孔谦为“无保邦济民之要务,唯以急刻赋敛为事”[2](P453)的吏臣,全然不顾孔谦在治水前线“日于上东门外伫望其来,算而给之”[2](P453)的操劳。同样在为明宗时期的租庸使孟鹄作传时,为扬孟鹄而贬孔谦,对后者的评价是“孔谦专典军赋,徵督苛急”(P917)。最后在《职官志》和《食货志》中 ,描述孔谦形象的措辞也是“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敛怨于天下”(P1989)云云。如此雷同的负面评价,却没有具体的实证支撑,很难不让人联想孔谦的恶名是史官刻意的编排。如此看来,《旧五代史》中的孔谦形象在明宗下昭赐死的那一刻已定。
关于孔谦形象的记载,成书于宋仁宗时期的《新五代史》与成书于宋太祖时期的《旧五代史》稍有不同。《新五代史》同样也为孔谦作传,但此传记却分三七记载孔谦功过,且多用实例表现孔谦聚敛。传记开篇就以“谦为人勤敏,而倾巧善事人,庄宗及其左右皆悦之。自少为吏,工书算,颇知金谷聚敛之事”来记载孔谦巧于工算,是治财的良吏;后又以“晋与梁相拒河上十余年,大小百余战,谦调发供馈,未尝阙乏,所以成庄宗之业者,谦之力为多”强调孔谦在晋王时期所创的功绩。新史对孔谦在晋王时所创功绩的记载是孔谦墓志所载功绩的高度概括,由此也可反证墓志所载功績并非撰写者的刻意美化。反观《旧五代史》却将如上的功绩归为“谦能曲事权要”“设法箕敛”之故,用“军储获济”四字一笔带过。
除了对孔谦功绩的记载,《新五代史》还系统地罗列了孔谦聚敛的实证:
“谦无佗能,直以聚敛为事。庄宗初即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诸场务课利欠负者,谦悉违诏督理……又请减百官俸钱,省罢节度观察判官、推官等员数。以至鄣塞天下山谷径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算;遣大程官放猪羊柴炭,占庇人户;更制括田竿尺;尽率州使公廨钱。由是天下皆怨苦之。”(P281)
成书相差仅五十余年的两本史书,对同一人物的记载为何有如此大的差别呢?一方面是因为《旧五代史》虽是后朝人写前朝之事,但孔谦因庄宗、明宗的政治嬗变而获罪,对于孔谦评传的记载事关明宗兵变得位的叙述,宋太祖赵匡胤同样起家于兵变,因此出于对兵变即位的避讳,奉诏修史的赵宋史官便延续明宗的立场,谴责庄宗政权及孔谦。反观《新五代史》成书于仁宗时期,据赵宋建国已半个世纪有余,与太祖即位相关的话题也不如建国初敏感;再者,《新五代史》是北宋设馆修史以后的唯一私修正史,欧阳修因此能免于北宋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从相对客观的角度,来塑造功过兼有、立体丰富的孔谦形象。
从另一方面来看,继《旧五代史》而后的史官也意识到如此大范围、成系统的经济活动并非孔谦一人之力能达成。孔谦乖张行为的背后是庄宗为实现华夏化统一政权而做的经济的铺设,孔谦只是此次改革的实行者。
首先是征税权的回归。兴于割据势力的庄宗深知尾大不掉的藩镇割据政权对于皇权的危害性,因此迫切地想收回藩镇的军权和财权,以建立传统华夏政权所宣扬的大一统国家。据《旧五代史》记载,庄宗在同光二年二月在圜丘举行完祭祀大典后,大赦天下,同时下令有司“速检勘天下户口正额,垦田实数,待凭条理,以息烦苛”(P245)。政令中虽明确指出检勘户口、垦田的目的在于“待凭条理,以息烦苛”,但自安史之乱以后,天下被各藩镇势力瓜分,中央处于“赋不上供,如割据焉”的状态。因此,庄宗此举表面为轻苛减税,为百姓谋利,实际却是想重新丈量天下土地,清点在籍人口,掌握垦田与人口数据,进而将征税权从藩镇手中收回,为后续平定蜀国筹备军资。同理,在庄宗颁布“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诸场务课利欠负者”的利好政策时,孔谦却阳奉阴违“悉违诏督理”,也多是孔谦扮演白脸、庄宗扮演红脸的政治表演。
其次是削减行政支出。具体措施是“请减百官俸钱,省罢节度观察判官、推官等员数”。削减官俸常是战时政府为弥补军费不足的应变之策。在安史之乱时期,唐代宗就因为国家财政吃紧,下令“京师百寮,俸钱减耗”,但此举很快招致群臣的反对,并于大历十二年(777)“诏加其俸禄”(P2085)。代宗仅以京师局部官员的官俸补军用就招致群臣激抗,以失败收尾,而刚经历战乱的后唐官员尚未对新生政权产生信任,庄宗就下令裁撤冗官、削减群臣俸钱,君臣离心是必然。
最后是变相增加财政收入。孔谦“收商旅征算”“遣大程官放猪羊柴炭,占庇人户”“更制括田竿尺”的聚敛之行,均是庄宗为统一全国所做的经济部署。《资治通鉴》中有载:针对孔谦“贷民钱,使以贱估偿丝”聚敛之行,时任翰林学士承旨、汴州权知的卢质曾向庄宗弹劾孔谦。卢认为后梁的赵岩就因“举贷诛敛”而结怨于天下,而时下孔谦聚敛之行与赵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是“赵岩复生也”(P7446)。但庄宗听完卢质谏言后并未有任何回复。所以,孔谦毫无忌惮的“聚敛”是为庄宗所默许的,甚至是授意的。
总之,在庄宗激进地建设统一华夏化政权时,孔谦作为政策的执行者,处于各矛盾对立的风口浪尖,自然成为利益受损者们泄愤的对象。而为加强统一大业操之过急的改革,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转而反噬了新生的皇权,孔谦也成为此次改革的替罪者。
四、结语
根据以上论述,可大致勾勒出孔谦形象演变的脉络。庄宗朝时,孔谦集盐铁、户部、度支三司重权于一身,是炙手可热、深得圣意的治国能臣,更是家族内光耀门楣的标杆式人物。因此,成文于此时的孔谦家族墓志,对孔谦形象的塑造自然极尽美化、吹捧之功。自庄宗惨死于兵变后,孔谦的权势也随庄宗而去,兵变得位的明宗更是将孔谦丑化为弄权小丑,以迎合后唐政权华夏化过程中继位正当的诉求。赵宋初期的史官同样继承明宗的立场,在评价孔谦时,不遗余力地将其侵剥、奸欺、弄权的恶名刻板化、印象化。然一千年前的欧阳修虽只能看到孔谦铺天盖地的恶评,却还是从这些恶评的字里行间为后人还原了多面立体的孔谦形象。孔谦形象历经庄宗、明宗、宋初三朝的演变,终于在欧阳修的笔尖得到相对公允的书写。而千年之后,随着与孔谦相关墓志材料的出土,墓志所载内容再次证实了欧阳修的判断。
利用出土墓志重新解读孔谦形象,本意不单是为还原孔谦形象被塑造的过程,更是为我们重新定位庄宗“中兴”提供新的资料。与孔谦形象的反复塑造相似,庄宗的形象在后唐建国后,从年少英主转为穷兵黩武、穷奢极欲的昏君,这种反差一方面源于明宗夺权后“成王败寇”式的历史书写,另一方面也是庄宗在建国后急于建设统一政权的侧写。以“绍唐统续”自居的后唐,在庄宗的带领下,取得了灭后梁和川蜀的重要功绩,誓要恢复李唐疆域。但庄宗所建立的政权只强调模仿华夏政权对外的政治认同,并没有内化于德,也由此惹怒于天下人,兵败被杀。少数民族政权在入主中原后,积极推进自身政权华夏化是不变的主题。就政权建设而言,华夏化是渗透在治国日常当中的,并非朝夕之功。终五代十国之世,沙陀族人建立的四个政权在此进程中交替兴亡,沙陀族群在此进程中被磨合分解,最终反被融汇于赵宋政權当中。
(责编:王晶晶)
Between Virtuality and Reality: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Kong Qian's Image
in Later Tang Dynasty
Jia Fayi Yan Hui
Abstract In the 1970s, four epitaphs were unearthed from the tombs of Kong Qian's family in Shandong Province. They were the epitaphs of Kong Qian himself, the epitaphs of his parents, the epitaphs of Kong Fang Couple (his parents), the epitaphs of Kong Jin and the epitaphs of Kong Li, his brother. In addition to the epitaphs of Kong Qian himself, the other three epitaphs also involve the description of Kong Qian's life. The image of Kong Qian in these epitaphs is quite the opposite to the image of Kong Qian i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Kong Qian was a harsh official who exploited the people and accumulated welth, but in the epitaphs, he became a vassal who tried his best to help Zhuang Zong achieve hegemony. This contrast can be interpreted as the epitaph writers deliberately embellish the image of the tomb owner under the support of the owner's family, but it is probably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evolution during the reigns of Emperor Zhuangzong and Emperor Mingzong.
Key words Kong Qian Zhuang Zong's renaissance Historical writing Cathaysific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作者简介:贾发义(1970-),男,山西阳城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隋唐五代史。
闫卉(1994-),女,山西吕梁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隋唐五代史。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代边疆重镇北都研究”(项目编号:20BZS033)、山西省教育厅2023年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唐末河东地区碑铭所见的民族融合”(项目编号:2023KY093)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