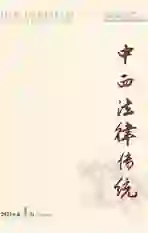史料新读:清前期规范豪族“违禁取利”的司法实践
2023-12-06于艳欣
摘 要|据《清代档案史料丛编》收录的材料,康熙三十年(1690),张恂如呈控昆山势豪徐乾学,状词显示其违禁取利。同在清前期,《红楼梦》中的豪门贾府被查抄出了重利盘剥的借券。两案均是豪族犯《大清律例》“违禁取利”条,司法实践程度都较低,但细究略有不同。比较同时期的其他同类案件,更能印证司法对待豪族违律放债有着特殊倾向,至此可引发对于相关律条的法律反思。而深入探究这些条文的实践逻辑,可知在“爱养民生”等恤民观念下,官府超越细故对民间借贷乱象进行治理,体现出司法实践的必要性;但同时,当清代前期君主面对诸豪族时,基于这一时期的政治需要而奉行“政贵宽平”的理念,又赋予了司法实践以灵活性,为其特殊性处理留下了空间。
关键词|违禁取利;豪族;司法实践;大清律例
作者简介|于艳欣,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21级法律史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法制史。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清代前期,高利贷和典当取息活动极其活跃,不乏豪族之流参与其中,“京师坊市,势豪多以私钱牟重息”[1]“京都利债,其风日长”[2]“富室大家,悍卒土豪,或开当网利,或放债盘占,吸髓吮脂,为富不仁”[3]。所谓豪族,既是家族显赫于当政的成员,在政治活动中占有一席之地,又是门第富庶于经济实力,累代优渥。徐乾学一门[1]、《红楼梦》之贾府[2]皆是豪门大族。徐氏三兄弟才学出众,简在帝心。康熙年间,昆山民间时有“九天供赋归东海”之谣[3],又有“京城三尺童子皆知‘万方玉帛朝东海”的说法[4],以至于江南各县,“具系徐府房屋田地”[5]。至于《红楼梦》中的贾府,亦是“诗礼簪缨之族”“安富尊荣”,正所谓“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清律有“违禁取利”律来处理钱债纠纷,徐乾学案和贾府案均涉及到“违禁取利”行为,相关材料能够呈现出清前期司法在豪族重利放债问题上的实践状况。《大清律例》诸债务条款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了规范,但其对于显宦巨族放贷的规制效果如何,尚未出现专门的研究。因此,本文意在以这两个案件作为研究中心,兼以分析其他类型案件,进行对比考察,从而从介入标准、实践后果等方面梳理其中的司法实践倾向,最终尝试挖掘规则运行的深层逻辑,为该时期司法处理豪族违律放贷的特殊性给出解答。
一、史料新读:两个豪族、同种犯罪
(一)问题的提出及内涵
纵观当前的研究成果,涉及到清代豪族违禁取利相关问题的研究并不多,且大多是对官僚放贷现象及其原因进行阐述,未作深入探究[6]。豪族不等同官僚,亦非富商大贾的代名词。豪门大族往往世代簪缨、成员众多,不仅具有政治上的威势煊赫,同样享有经济层面的丰饶自得,因此占据了放债取利的各种优势。清代前期豪族“违禁取利”及其司法实践状况的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清前期的政治、经济形态有其特殊性,置于该具体历史时期进行研究有利于深入理解影响清朝法律运作的各种因素。清入关以来,为使汉族士大夫诚心归附,一方面以暴力镇压反清斗争,摧毁明朝遗民的华夷观念,一方面待到政局稍显平稳,开始重视“文治”,转而拉拢汉族知识分子入朝为官。同时,受战争、动乱及人口增长等影响,清前期民间放贷渔利之风尤炽,“违禁取利”条的运行刻不容缓。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司法运作很可能遭受影响。
其二,清代“违禁取利”条有着明显的承袭性和社会必要性,以此为切入点探究法律实践效果有利于完善对清代法律及司法实践状况的认识。《大清律例》参照前朝司法体制而作,经多次编修,于乾隆五年(1740)修成,这些内容是在与社会生活的对话中不断生成的。研究“违禁取利”条的运作样貌,不仅能够展现清前期对于重利盘剥等社会常见违法行为的规制状况,同时也能够由此为基点对《大清律例》的适用性引发新的思考。
其三,豪族因自身特点而在该时期具有突出性,对这一群体的违律行为展开研究有利于通过个案分析,重点构建清前期的司法实践模式及其基本逻辑。豪族既富且贵,毋论具有从事高利贷行业的资本,其政治影响力也不容小觑。在他们身上,影响司法运行的各种因素将会得到倍数放大。当豪族犯“违禁取利”罪,司法将如何具体实践,是否会呈现出特殊的倾向,司法运作的背后又蕴含着何种逻辑,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既能展现清前期豪族违律放贷的司法实践状况,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内容,同时也将侧面反映帝制时期的法律运行面貌。
(二)清代史料的再利用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下称《史料丛编》)从宫中杂件选录了康熙年间清人控告徐乾学一门的呈状22件,其中与徐乾学违禁取利相关的有4件[1]。康熙三十年的一则“张恂如呈控徐乾学炙诈婪赃逼死父命状”[2]记载案情最详,是研究该时期豪族“违禁取利”的最佳样本。《史料丛编》出版后,《历史档案》对该辑内容进行了简介,指出了这些呈状对于清代社会政治经济研究的价值[3]。其后开始有学者对材料进行简单利用,亦有研究者将材料结合时代背景来探寻徐氏的家族兴衰[4]。学者王家范在2005年转介了徐乾学案的主要部分,并于次年进行了史料补缀,主要就《大清律例》相关条文梳理了部分法律问题[5]。随后,不断有学者从社会影响、法律运作等角度对相关史料加以深入分析[6]。
《史料丛编》所载徐乾學相关案件的内容丰富,其中“张恂如呈控徐乾学案”尤为生动地展现了清代前期豪族涉嫌“违禁取利”的具体行为,这些史料均可以为研究清代社会提供大量历史依据。总体而言,相关研究多着眼于社会、政治、经济层面的探索,缺少对清代法律实践效果、缘由等状况的深入剖析。可以看到,对于清代法律制度具体运作、司法实践状况等方面的研究,这些内容仍具有较大的史料价值,尚待进一步挖掘。
同在清代前期,江宁织造曹寅之孙曹雪芹历经世态炎凉,阅世颇深,于小说《红楼梦》中生动地刻画了贾府没落之因,经他人续作,贾府案传世至今。《红楼梦》第一百零五回中,贾府因另案遭受查抄之际,被抄出了一箱重利盘剥的借券,文中司官直指这箱借券“都是违例取利的”。这亦是目前清代史料中所能见到的较为完整、直观的豪族违律放贷案件,正好与徐乾学案构成“两个豪族、同种犯罪”,颇具有研究价值。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借空空道人之口,说本书“无朝代年纪可考”,从而隐去故事的年代背景。但鉴于曹雪芹历经康雍乾三朝,曹家在雍正五年(1727)获罪被抄没、史料与小说内容相互印证,且《红楼梦》成书于乾隆年间,故将相关文本置于清前期法律背景中予以解读,最为合理。
近年来,利用《红楼梦》文本研究法学论题的成果日渐丰硕,这些研究从清代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到刑法归责理论,从法律决策机制到清代法律体系等等[1],不一而足,充分彰显了小说的史料意义和法学研究价值。目前,对于《红楼梦》高利贷的相关研究大多着眼于故事情节和清代社会的分析,尚没有专门从司法实践角度进行的论述[2]。因此,和《史料丛编》所载“张恂如呈控徐乾学案”相同,《红楼梦》贾府“违禁取利”相关内容仍具有法学议题的讨论空间。有趣的是,徐乾学同《红楼梦》颇有渊源,他与曹家父子两人交好,曾对雪芹祖父曹寅作《赠曹子清》,诗中有“涓埃岂云报,感恩泪盈把”一句,又在《棟亭感旧》跋诗中留下了“交分纪群殊不浅,欲题奇木思悠悠”的感叹,纪念与雪芹曾祖曹玺之间的交情[3]。
二、徐乾学案中的“违禁取利”
(一)徐乾学案之内容
康熙二十九年(1690)五月,两江总督傅拉塔劾徐乾学及子侄借势招摇、竞利害民,并开列了其违法诈银、私建生祠等十四项罪行[4]。在此前后,即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1692)两年间,徐乾学一门遭到数次法律指控。本文基于《史料丛编》所载康熙三十年的“张恂如呈控徐乾学案”呈状及所附手札、禀帖的文本内容来探究势豪徐乾学可能存在的违律行为。同时,由于这些材料系清宫杂件,年代久远且相对孤立,不便验证原告所诉事实,故不做内容真实性的考察。
“张恂如呈控徐乾学案”发生在康熙十四年(1675),时值徐乾学经历降级归乡、捐复原级之际[5]。通览呈词可知:这一年,原告张恂如之父张希哲从太仓州学正升为山西平阳府稷山县知县,文凭到时因病而具文告病,意欲辞官,不久痊愈后又申文报痊,恰好昆山、太仓接壤,昆山大族徐乾学自称可以助其顺利做官,并提出为其营谋需要花费。七月初一日,徐乾学的族亲逼迫张希哲立下高额借券,使其凑献,又逼其变卖原籍田产房业。其后,徐乾学多次以手札催促张希哲偿还本利,并诉说其弟徐元文在京奔走之劳。殊不知,期间张希哲已经收到京中之报,徐乾学炙诈之意昭然若揭。徐乾学屡屡遣人横征,导致张希哲揭典变产,抱恨终天。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徐的同乡诓去张恂如手中的徐乾学亲笔十札,张恂如愤而起诉,于康熙三十年十月诉至两江总督傅拉塔。
(二)徐乾学案的法律分析
“张恂如呈控徐乾学案”的呈状内容详实,更有引用律法之语,与一般的游词废句相异,其中则有一段集中展现了徐乾学涉嫌触犯“违禁取利”条的行为:
……构伊亲吴升勒父逼写借券三纸一千五百两,从七月初一日为始,每月加五起利,又加平头六十两,亦按例起利勒索,连差虎仆任政、高大、張相等持札横征,踞父任所,百般逼炙,如数凑献。杨彩等付证。不意豪欲未满,复又致札伊族原任山西盐院徐讳诰武,威压势炙,顺生逆死,逼父将原籍田房产业变卖,前后共献纹银叁千壹百贰拾捌两。
这段告词暗含了三处与《大清刑律》“违禁取利”条相违背的行为,一是在借贷主体上,突破了“不许放债于赴任之官”的国家规定,侵犯了国家利益;二是在借贷利率上,超过了“月息三分”的利率红线,侵害了债务人的利益;三是在索债手段上,违反了律典对“豪势以私债强夺”的明确限制,亦是极大地损害了债务人的权益。
具体而言,《大清律例》卷十四《户律·钱债》中的“违禁取利”条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即年利率最高为36%。上述词状直指徐乾学“每月加五起利”,达到了年利率60%,远超律条限制,按律可能受到“笞四十,以余利计赃”的处罚。
同时,“违禁取利”条明令禁止放债于听选官吏,其规定“听选官吏,监生人等借债,与债主及保人同赴任所取偿,至五十两以上者,借者革职,债主及保人各枷号一个月发落,债追入官”。顺治五年(1648)有令:“……并不许放债与赴任之官……如违,放者、借者俱治重罪”。张希哲是即将赴任之官,徐乾学向其放债,属于该条文规定的主体情形之中。同时,在后文补词里,张恂如诉说徐乾学在遣人勒写借票后又多次横征:
遣仆高大、张相二人,随父赴任,续又遣仆任政踵至。三人出入衙署,恣行逼索,撮急借典,凑足司兑纹银一千两交去。未及,二使复至,又凑银七百两交去,……又致札于现任山西盐院徐讳诰武号孟枢先生,系健庵通谱之弟,追父本银二十两,利银一千五百两。
照此说法,徐乾学一方显然已满足同赴任所取偿五十两以上的犯罪构成条件,若按律法,双方都应当被惩以重罪,债主徐乾学应受枷号一个月发落、债追入官的处罚,至于究竟如何“发落”,并无明文。
此外,《大清律例》“违禁取利”条也对索债方式进行了限制,其中有“若豪势之人不告官司,以私债强夺去人孳畜产业者,杖八十”之规定。本案中,徐乾学先是派遣他的虎仆任政、高大、张相等持札横征,在张希哲的任所两次暴力索债,而后徐乾学的族亲徐诰武逼其变卖原籍田房产业,张恂如于后文中书呈:
徐盐院立差承差曹姓者,传父赴运城衙门。迫以上司之威命,又揭借挪移,于徐盐院当堂交割二千零六十两于任、高二使之手……父宰稷三年,水蘖自茹,两袖清风,只得撮之急项,借之典铺商家,后于原籍变卖住房田产,清偿此项。以致孑身无告,徒步南归。
徐乾学与其族亲、虎仆作为“豪势之人”,所夺价款早已超过借贷之本利,按律应当“计多余之物,坐赃论”,并“依数追还”。徐乾学等虽未直接夺去张希哲的孳畜产业,但以逼勒之势获得了变卖产业的价款,其恶劣程度与直接强夺相当,与出于本心、两相和同的“准折”相区别。
除上述三处可能存在的违律行为外,呈状所附手札及禀帖中的三处还反映了其弟徐元文欠下“旗债”的情况,一则为徐乾学的亲笔手札:
向日为年翁一片热肠,反负重累,至遘此闵凶,而犹受子母家气。此皆旗下之债,年翁必为恻然不安者也。
另两则为家仆高大的禀帖:
百计踌躇,托三老爷多方转贷旗债,方得斡旋其事。
前蒙所托,家老爷一片热肠,切嘱三老爷转贷于旗下……目下闻讣太夫人仙逝,家主奔丧在尔。债主闻知,画(昼)夜坐索,在宅哓哓,必要遣人同到贵治取索。大恐旗下之使有碍钧面,故大自认正月全楚。家老爷又多那借支持,苦不可言。
“闵凶”“画(昼)夜坐索,在宅哓哓”显示出了徐氏兄弟被追旗债的急迫情势。同时,欠下这份“旗下之债”,于他们而言是不光彩的,家仆高大只能在无奈之下答应正月偿还全部本利,并因此为由紧逼张希哲还债。《大清律例》未对旗债进行限制,只规定不得向八旗兵丁放转子、印子长短钱,但清前期“旗下之债”在民间已靡然成风。康熙二十三年(1684),杭州旗债泛滥,民不聊生,新任浙江巡抚赵士麟到任,叹道:“……吾莅容小邑,民借旗债,其本不多,吾代赔……捐数百金毕矣。今杭城旗债多至三十余万,我何以偿?”[1]
三、贾府案中的“违例取利”
(一)贾府案之内容
在《红楼梦》第一百零四至第一百零七回,贾家遭到官府查抄,王熙凤重利放贷之事曝光。实际上小说草蛇灰线,其违禁取利的事情在宁府家宴后就开始显露。第十一回,凤姐从宁府回家后,问平儿家中之事,平儿递茶并答道:
“没有什么事,就是那三百两银子的利银,旺儿嫂子送进来,我收了。”(《红楼梦》,第十一回)
到了第十六回,贾琏带黛玉回贾府后,又有旺儿嫂子为凤姐送利银的情节:
平儿道:“……奶奶瞧,旺儿嫂子越发连个算计儿也没了。”说着,又走至凤姐身边,悄悄说道:“那项利银,早不送来,晚不送来,这会子二爷在家,他偏送这个来了。幸亏我在堂屋里碰见了……”(《红楼梦》,第十六回)
首次描写旺儿媳妇送利银是在十一月初二日,而这次描写是在次年十二月,中间约间隔一年。而到了第三十九回螃蟹宴后,因袭人向平儿询问月钱发放的事,平儿趁醉向袭人透露了其主王熙凤暗自放账的事情:
“这个月的月钱,我们奶奶早已支了,放给人使呢。等别处利钱收了来,凑齐了才放呢。因为是你,我才告诉你,可不许告诉一个人去!”
“何曾不是呢!他这几年,只拿着这一项银子翻出有几百来了。他的公费月例又使不着,十两八两,零碎攒了,又放出去,单他这体己利钱,一年不到上千的银子呢!”(《红楼梦》,第三十九回)
旺儿媳妇在第十一回送来的是三百两利银,此处平儿说“一年不到上千的银子”,可见旺儿媳妇于年底送来的利银并非全部取利之项,从外收账是分多次进行。平儿被凤姐唤回去后,小厮向其告假,平儿让他带话给旺儿:
“就说奶奶的话,问他那剩的利钱,明日要还不交来,奶奶不要了,索性送他使罢。”(《红楼梦》,第三十九回)
此时平儿向旺儿索要“剩的利钱”正值中秋之际,距前文两次提到的年末之时较远,似乎收利时间没有定例,更加印证了凤姐向外发放多笔借贷的事实。至第七十二回,王熙凤向旺儿媳妇玩笑道:
“说给你男人:外头所有的账目,一概赶今年年底都收进来,少一个钱也不依。我的名声不好,再放一年,都要生吃了我呢!”(《红楼梦》,第七十二回)
这一命令随即被旺儿媳妇委婉推辞:“若收了时,我也是一场痴心白使了”,凤姐复道:“如今倒落了一个放账的名儿。既这样,我就收了回来。”这些对话意味着两种互不排斥的可能性,其一,凤姐放债并非短期营利,往往是留本取利,长久经营,一般不会将本利一并收回;其二,凤姐放外债的总数目多,导致各笔贷款的放账、收账没有统一时间,从而随时有利银可供取用。
综上,从以上文本可以推测,王熙凤放债多为长年借贷;借贷对象众多,辐射各地,大多为小额借贷;收息一般为一年一收,各项利银的收取时间不定,一部分为年底收取。凤姐及其心腹经营多年,直到第一百零五回,锦衣府堂官赵某带领司官查抄出一箱借券,其“违例取利”之行终于败露:
一會子,又有一起人来拦住西平王,回说:“东跨所抄出两箱子房地契,又一箱借票,都是违例取利的。”老赵便说:“好个重利盘剥!很该全抄!……”(《红楼梦》,第一百零五回)
(二)贾府案的法律分析
探究文学中的法律需要与该作品的时代背景相结合,除作者曹雪芹身历康雍乾三朝以外,用清代法律分析贾府“违例取利”、并从中考察清前期司法实践状况的合理性,另有三项主要例证。例证一是文本中的“违例取利”与《大清律例》之“违禁取利”条高度相似。曹雪芹为达到真事隐、假语存的目的,往往避实就虚,将法律相关的描写进行模糊化处理,例如小说中出现了石呆子案、张华案等数个公案,但仅后四十回的薛蟠人命案展现了较为完整的司法程序。“违禁取利”之名自明代时出现,清律沿用这一叫法,《红楼梦》虽弃“违禁取利”不用,但“违例取利”的说法明显是由其演化而来。例证二是曹家经营当铺,也从事取息活动。康熙五十四年(1715)七月十六日,曹頫奏报家产:“所有遗存产业,惟京中住房二所……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这仅是曹頫自觉上报的部分,至于曹家究竟有多少放贷产业,是否有违禁取利的行为,均不可知。例证三是雍正六年(1728)曹家被继任江宁织造隋赫德抄家时,亦被查抄出了放贷取利之证。隋赫德向雍正奏道:“余则桌椅、床杌、旧衣零星等件及当票百余张外,并无别项……又家人供出外有所欠曹頫银,连本利共计三万二千余两。奴才即将欠户询问明白,皆承应偿还,”《永宪录续编》也记载曹家被查出了千金质票。从主动上奏“本银七千两”到被查出“本利三万二千余两”,中间过去了十三年,若所奏内容皆属实,其渔利程度可想而知。
就贾府案而言,我们无法从《红楼梦》文本中得知王熙凤放债的具体利率,无法看到其借贷对象、索债方式等是否合法,更不知仆人旺二等人是否会在凤姐催促收账之时,对借方横加逼勒,以徐乾学案呈状中痛斥的“豪奴”形象出现。但通过司官的“都是违例取利”“好个重利盘剥”之语,以及后文中西平和北静二王的确证,可以知晓凤姐极可能是违背了《大清律例》“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的这条规范。仅触犯这一项,凤姐等人即应当按照其后规定的法定刑,承担不低于“笞四十,以余利计赃”的法律后果。
四、徐乾学案与贾府案的司法实践状况
(一)徐乾学案:“从宽免其审明”及史料的印证
康熙三十年十月,张恂如向傅拉塔呈控徐乾学的违法行为,于呈状结尾切切祈求:“泣血上呈总督江南江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操江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傅大老爷案下施行”“躬叩宪天大老爷以申遗憾”,以求官府的审理。其在告词中也屡屡表达了对法律的敬仰,希望得到法律庇护,如“计赃斩有余辜,难逃国法”,以及“健庵职居司寇,而行端若此,试问律例自当如何?”等语。
按呈状所载时间推算,犯罪行为发生时徐乾学正遇降职后复职,为六品以下官员。此后他屡次擢升,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迁左都御史,擢刑部尚书,升为从一品,后遭革职,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回籍编书。对于官员犯罪,《大清律例》“职官有犯”条规定应当上奏:“凡京官及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闻请旨,不许擅问。六品以下听分巡御史、按察司并分司取问明白,议拟闻奏区处。”本案因被告的身份而在审理程序上有其特殊之处,但要追踪案件后续处理的情况,却实为不易。除《史料丛编》录有该案材料外,其他史料未见分毫,无法直接知晓司法实践的程度、具体方式等状况。对此,只能利用相关史料从侧面加以研究。
回到张恂如控告之前,康熙二十九年五月,两江总督傅拉塔即上疏“原刑部尚书徐乾学、大学士徐元文并伊等子侄秽迹”,胪列十四项罪行,包括徐乾学二侄重利克剥贫民之事,并总结道“又复唆使争讼,重利累民”。但面对包含了“违禁取利”的各项指控,康熙仅处理了徐家老三徐元文,而对徐乾学网开一面,下旨“所参各欵,从宽免其审明,徐元文着休致回籍。”《清史稿》亦记载“上置弗问,而予元文休致”。“从宽免其审明”虽在“张恂如呈控徐乾学案”之前出现,但案发前后,康熙帝始终对徐乾学秉承宽仁之心,该案似乎未对其造成太大影响。
从康熙二十八年回籍修書,至康熙三十三年(1694)七月卒命,徐乾学在昆山著成《憺园集》《读礼通考》诸书,并撰写《一统志》。皇帝时刻挂念,在徐乾学逝前还让其去京修书。徐乾学遗疏献书,得复故官[1]。“张恂如呈控徐乾学案”恰好出现在这期间,试想,若案件按律进行审理,徐乾学如何有安然著书之心境,康熙怎能对其宽厚如常。至此,该案的司法实践状况可见一斑,甚至可以推测,这些案卷材料虽被送进宫中,但被康熙弃之不理,以至于从未进入司法审理程序,最终沦落为宫中杂件。
(二)贾府案:“一概照例入官”的可能性宣告
在贾府案中,司法介入“违禁取利”事项的起因是御史参奏贾赦“交通外官,依势凌弱”,皇帝命查抄贾赦家产,于是众司官秉承“分头按房,查抄登账”,在东跨所抄出一箱“违例取利”的借票。
北静王到后,认为应当厘清同房各爨之兄弟的家产,从而不至于祸及贾政:
“政老,方才老赵在这里的时候,番役呈禀有禁用之物并重利欠票,我们也难掩过。……独是借券,想个什么法儿才好?今政老且带司员实在将赦老家产呈出,也就完事;切不可再有隐匿,自干罪戾。”(《红楼梦》,第一百零五回)
文中记载:“房地契纸,家人文书,亦俱封裹”,可见这箱借券最终被收走。至于“违例取利”之事如何处理,文中则先有“并案办理”一说:
只闻二王问道:“所抄家资,内有借券,实系盘剥,究是谁行的?政老据实才好。”……贾琏连忙走上,跪下禀说:“这一箱文书既在奴才屋里抄出来的,敢说不知道么?只求王爷开恩。奴才叔叔并不知道的。”两王道:“你父已经获罪,只可并案办理。你今认了,也是正理。如此,叫人将贾琏看守,余俱散收宅内。” (《红楼梦》,第一百零五回)
此处贾琏见形势不好,已经自认犯有“违例取利”罪。书至下一回,北静王府中长史告知贾政“主上甚是悯恤,并念及贵妃溘逝未久,不忍加罪……所封家产,惟将贾赦的入官,余俱给还”,皇帝尽显宽宥之色,独独嘱咐查清借券。于是,对于如何处理“违例取利”,便又有“王爷查核”一说:
“惟抄出借券,令我们王爷查核。如有违禁重利的,一概照例入官;其在定例生息的,同房地文书,尽行给还。”(《红楼梦》,第一百零六回)
前文中赵堂官、二王均称这笔借券为重利欠票,甚至直接指其为“违例取利”,而到此处,皇帝却让北静王查核是否为违禁重利,并宣告了“一概照例入官”的处理可能性。而无论是“并案办理”,还是“王爷查核”,后文再无对后续处理结果的交代,但可以知晓四个事实,其一,借券入官后再没有归还;其二,贾赦、贾珍获罪是因为石呆子古扇案和尤三姐自刎案,并未受到重利借券的影响;其三,“违例取利”的主谋王熙凤、以及在二王面前承认“违例取利”的贾琏,均未受法律处罚;其四,贾府案后不久,贾政承袭荣国公世职。可见,对该“违例取利”案件的司法实践程度之低、后果之轻极有可能归结于皇帝的宽仁。
五、司法实践倾向以及刑律条文的法律反思
(一)类型案件所见司法实践倾向
徐乾学案和贾府案不约而同地展现出了司法对于豪族“违禁取利”行为的让行态势,司法实践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不同的是,前者是原告呼吁司法介入而未能如愿,后者则是官方力量在法律活动中直接发现违法行为,司法不得不短暂性地参与。总的来说,后者比前者司法实践的程度略深,较多地反映出了律条的运作情况。
徐氏一族在明代就已起家,清初时昆山三徐先后归附,成为清廷新贵,光焰甚炽;贾府一门亦发迹于清初,贾家祖上为披甲包衣,因战功而显赫,其后世代簪缨。小说第七回尤氏评价仆人焦大:“因他从小儿跟着太爷出过三四回兵,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出来了,才得了命……不过仗着这些功劳情分。”就作者曹雪芹的家族而言,明末曹家降为满洲包衣,清初时因军功而显贵,世代为满洲正白旗,与《红楼梦》贾府的境况明白对应。因此可以说徐乾学与曹玺、曹寅相交跨越了身份,也是汉官与旗人之交,而徐案与贾府案司法实践程度的细微差别亦显示了清廷对于满汉官员犯罪的不同处理。
与贾府案比较而言,徐乾学显然受到了更多的优待。他置于“违禁取利”的控告而自如脱身,早有先例。康熙二十八年,副都御史許三礼复劾徐乾学曰:
“徐乾学发本银十万两,交盐商项景元于扬州贸易,每月三分起利。本年七月间着伊孙媳史姓家人李(湘)[相]押同景元于八月二十四日到京算账,共结算本利[一]十六万两。又布商(程)[陈]天石新领乾学本银十万两,在大蒋家胡同开张当铺,契约银号钱桌发本放债,违禁取利,怨声载道。”
面对许三礼去而复返,康熙不追究徐乾学的罪过,反而质疑许三礼参劾有私心:“前参乾学疏内,何以不一并指出”。许有礼两次弹劾徐乾学,未伤其分毫。
跳脱出这两个案件,清前期“违禁取利”诸条自然也有运行之处,例如乾隆年间,武举戴麟瑞之父戴于和向土目安起鳌放债五百两,约定年息为米七十五石,22年来戴麟瑞屡次准折安起鳌的田土产业,安忍无可忍,赴州呈控:
经署州于良钧差提审讯:核计安氏仅欠戴麟瑞本银四百一十两,前后收过息米一千四百十石,照依该地时价,约计值银三千三四百两,利过于本数倍。断令安氏止还本银,田归安氏管业,旧欠息米免其追偿。
但戴麟瑞因不服审断、咆哮公堂,最终照“棍徒扰害”例被拟判改发极边足四千里,折责安置,而对于其放债取利事项,则被判为:
安氏所欠戴麟瑞本银四百一十两追缴给领,其四十年、四十一年拖欠息米六十四石五斗,利过于本,免其追缴,田产仍归安氏管业。
以上案件中,武举戴麟瑞取利过本、强行索债,明显触犯了“违禁取利”条款,但官府用律过慎,且因他罪更恶,钱债条文未能完全施展。从止还本银、原主管业、旧利免偿的处理结果上可以看到,该判决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债务人的利益,发挥了律条处理钱债纠纷的作用。再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二月,大学士马齐、学士蔡升元等以折本请旨之事:
覆请刑部汇题案内,以九钱作一两放债,骁骑校诺木图议革职,枷号两月,鞭一百一事……上曰:此内诺木图、傅云其情可恶,枷号鞭责完日,发往三姓处当差行走。
八旗骁骑校诺木图显然是触犯了“违禁取利”条款中的“违禁向八旗官兵放转子、印子长短钱”条,其内容为“佐领、骁骑校、领催等,有在本佐领、或弟兄佐领下,指扣兵丁钱粮、放印子银者,系佐领、骁骑校照流三千里之例,枷号六十日。系领催照近边充军例,枷号七十五日。倶鞭一百。”诺木图因“以九钱作一两放债”而遭革职,被判枷号两月,鞭一百,并流放至三姓处,基本符合了律文的相关规定。司法在此案中得到了充分的运作,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因素,康熙知晓后也未展现宽仁之态,直指“其情可恶”。
通览以上案例可知,对于“违禁取利”犯罪,清前期司法并非始终正常运作,具体而言,当政者对待豪族较之普通官吏、举人更加宽松,而在豪族之中,对待汉人较之八旗更加宽松。这种司法实践的宽松状态具体体现为司法介入的标准更高、实践程度更低、参与方式更加柔和以及法律后果更轻。
(二)“违禁取利”条的法律反思
户婚、田土、钱债等事项均属“细故”之事,当民间发生细故纠纷,若要引起官府的重视,往往会夸大词状,进行情感性的煽动。有学者认为,在这些道德宣泄的背后正是法律意识的体现,是人们对自我权利的捍卫。在这一认识下,清代的“违禁取利”条超越细故,对民间细事进行管理,便具有从国家层面保护借贷双方权利的意味。官方认为放债典当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可以“通缓急之用,取利之中,有相济之义”,同时也认识到“然必有乘人之急,而罔利无度者,亦必有迟欠违约,负赖不还者,故立此禁限也”。这些是“违禁取利”条存在于国家律法中的基本逻辑,其出发点是处理借贷乱象,保护借贷双方的利益。
债务条文既是以保护当事人权益、平复民间纠纷而立足,若增以单纯的惩治性内容,则会使得对国家利益的强烈保护需求改变原本的立法精神,从而扰乱基本逻辑。正如《大清律例》对“监临官吏放债于所部民人”“放债于听选官吏、监生人”等进行了限制,若一方违禁取利,国家并不会保护另一方的利益。一方面,条文中不再有余利还债务人、追本利给债权人的内容,可能仅是规定了“但犯即杖八十”“债追入官”等惩罚性条款;另一方面,债务双方甚至可能会一起受到处罚。换言之,不能单纯地将“违禁取利”条视为官方对于细故之事的治理手段,其中已倾注了国家对肃清吏治、维护统治的诉求,其内涵已远远超越了细故。上述徐乾学案、贾府案等均能体现这一点。
最后的法律反思是关于“违禁取利”条的适用性。条文第一句即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但凡民间借贷,均谓之私债,条文没有从本金数额等方面进行限制,霎时将无数借贷细故之事纳入司法考察范畴之中。在高利贷盛行的清代前期,民间违法行为势必不可胜数。而其后规定“违者,笞四十。以余利计赃重者,坐赃论。罪止杖一百”,设定的违法门槛低而法律后果相对较重,很可能影响司法实践的运行。清承明律,大多“违禁取利”条文的法定刑都规定为笞刑和杖刑,监临官吏犯律亦杖八十。但这样的规定在清代前期明显缺乏适用性,或许在大多情况下只能流于形式。清入关后待到局势稳定,便开始奉行休养生息之策,屡次免税,并笼络明朝学者为官,以示仁政。若官员的“违禁取利”罪行晓于中央,反而有可能因皇帝轸恤而免于处罚,徐乾学案和贾府案即是例证。
六、清前期“违禁取利”条的实践逻辑透视
(一)“爱养民生”与超越细故——司法实践的必要性
司法实践必要性背后是借贷行为存在的必然性。从古至今,借贷、典当都是维持社会运作的重要经济手段,历代律典均不禁止放贷,只是不允许征收重利,即“放债勿贪重利”。乾隆十年(1745),御史胡蛟龄在《推广辟荒疏》中谈到官府借钱于陕省贫民的做法有成效,希望可以沿用到其他地方:
窃查陕省之榆林、延安二府各属近边无业贫民,均赖出口种地,以资生计,而苦于牛具籽粮,无力措办,不得不向富民借贷。富民放债起利,贪得无厌,穷民被其盘剥,终年力作,所获无几。乾隆四年(1739),经前任督臣奏明,每年酌动官银,借给穷民,令于秋收照时价还粮。乾隆八九年(1743、1744),又经前任抚臣先后奏请,动项分发借领,照例于秋成还粮交官,共发银六万余两,共收粮约十余万石,造报户部在案。此陕省借粮收粮已试之成效也。
贫民因富民放债起利、终年盘剥而愈穷,国家施以援手之办法却仍旧是“借贷”。官府将官银借给穷民,让他们在秋收時照时价还粮,而不进行重利盘剥。如此一来,百姓有本钱得以耕作,官府有新粮得以收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借贷双方的相济之义,也足以表明借贷的价值所在。
但民间借贷行为众多,难免有不义之举,重利放贷导致民生凋敝,不得不制定并运行相关规则。正如张恂如在呈状中写道:“以微利之虚名,蹈莫大之实祸,宁不情极心惨耶!”清代前期,官方也尝试过其他治理民生凋敝的方法,如康熙三十五年(1696)稽察钱局刑科给事中刘荫枢在《请严利债之禁疏》中所奏,“窃见我皇上劝课臣工,必以清廉爱民为第一事……非世禄素封之家,常俸不足供其用。则取债于人,六七当十,六月转票,迟至三四年间,千金之本,算至二三十倍,既乏神输鬼运之能,又无点石为金之术,何从而清偿哉……伏祈敕下该部酌议变通,严立科条,一切负债,俱照实在银数三分计息,敢有折数转票,横肆勒索者,作何惩治,法在必行。则索者知所止,而偿者易为力,潜移而默转之,庶从前积弊,
可以渐杜矣。”[1]前文已述康熙年间官员赵士麟自填旗债之举,此外,清政府亦尝试自首免偿的方式:
雍正十三年(1735)都统李禧请旗民一体严禁,借债人自首免罪,并免偿放债人治罪,仍追利入官。民间争首告冀免。至是,照疏言:“八旗佐领等官盘剥该管兵丁,放印子钱者,仍遵例拟追外,如止重利放债,悉依违禁取利本律治罪[2]。
但“追利入官”“民间争首告冀免”侵害了当事人权益,该尝试以失败告终:
乾隆七年(1742)疏驳都统李僖所奏,重利放债,借债人自首免偿例,已经律例馆删除,不准引用[3]。
清代前期君主爱养民生,正如康熙二十八年十月,康熙谕直抚于成龙:“直隶地方,朕屡豁免钱粮,百姓竟无起色。今年荒旱比往年更甚,朕在深宫,俯念民生困苦,衣食艰难,宵旰焦劳,时欲流涕。”在爱养民生的观念下,为了治理因重利盘剥而带来的民生凋敝,君主自然重视“违禁取利”相关问题。顺治元年(1644)冬颁诏大赦天下,其内容有“势家土豪,重利放债,致民倾家荡产,深可痛恨,今后有司勿许追比。”[4]顺治五年十一月有令,强调“势豪举放私债,重利剥民”要按律严惩[5]。至康熙四十八年(1709)八月,巡抚赵申乔上疏永州镇官员唐之夔及李如松违禁取利之事,得旨:“该部严察议奏。”[5]到了乾隆九年四月,面对安徽巡抚范璨奏以民间违禁取利事项,乾隆旨意为:“其应查禁者,不谓汝能办此,勉力以实为之”[6]。
这一时期,官方在“爱养民生”的观念下,为改善民生困顿而超越细故,治理借贷问题,最终求诸于“违禁取利”法律规范,很好地印证了司法介入民间借贷的必要性。前文的诺木图、戴麟瑞等均按律惩治,受到了较为严格的处理,均是清代前期“违禁取利”条司法实践的例证。
(二)“政贵宽平”与政治需要——司法实践的灵活性
在“爱养民生”的观念下,“违禁取利”条的运行有其必要性,而基于清代前期实际政治需要而奉行的“宽平”理念,使得司法实践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这一时期,君主采取治下宽平的总政策,正如康熙二十六年四月,康熙在授田雯江苏巡抚时所谕之内容:“向闻江苏富饶,朕亲历其地,见百姓颇多贫困,尔当以爱养民生为务。至地方豪强为害于民者,不可不惩,然政贵宽平,不必一一搜访滋
事。”[7]再如康熙五十三年(1714)十二月,皇帝向浙江巡抚徐元梦道:“尔遵朕此旨,切切在念,惟以宽恕为本”,又谓云南巡抚施世纶曰:“尔等务宜每事宽恕,以体恤下属为念。”明珠贪擅、徐乾学与高士奇比昵,康熙皆优容待之,并告诉近臣:“诸臣为秀才,皆徒步布素,一朝得位,便高轩驷马,八驺拥护,皆何所来,可细究乎?”[8]甲子乡试时,徐乾学之子犯事,将送法司严训,康熙对阁臣说:“从宽如何?”[9]其宽平治下之心尽显。
清朝皇帝自顺治而下大权在握,成为司法运行的最后环节[10],因此,“宽平”的政策也最终体现到司法上。“违禁取利”规则的运行因政治需要而不得不具备一定的灵活性,这表现为具体案件中的特殊司法实践倾向,正如徐乾学案和贾府案所呈现的。君主因“爱养民生”而超越细故,对民间借贷俯身治理,反之,君主也会因为更重要的政治利益而将其重新归入“细故”,“政贵宽平”背后暗含了皇帝基于政治需要而对司法实践的潜在影响。透视其中的实践逻辑,不仅能够深入认识规则运行的灵活性,也能为豪族违禁取利案件中司法实践倾向的特殊性提供解答。
就贾府案而言,贾府受到查抄却能免受“违禁取利”条的惩处,既是由于祖先有护国之功,皇帝感念其功德,后人贾政勤慎居官,皇帝对其悯恤体谅,又有贾元春溘逝未久,皇帝念在贵妃不忍加罪。正如小说第一百零七回,有人在荣国府街上闲话:“听见说,里头有位娘娘是他家的姑娘,虽是死了,到底有根基的。况且我常见他们来往的都是王公侯伯,那里没有照应?就是现在的府尹,前任的兵部,是他们的一家儿。难道有这些人还护庇不来么?”再观作者曹雪芹的家族,确实俱有贾府之情状。据清人记载,“寅字子清,号荔轩,奉天旗人,有诗才,颇擅风雅。母为圣祖保母。二女皆为王妃。”[1]康熙曾六次下江南,江宁织造曹家就接驾了四次,《红楼梦》亦写江南甄家四次接驾,足见其承宠的盛况。
而就徐乾学案而言,皇帝对徐乾学始终秉持“从宽免其审明”之态,这样的态度与统治利益密不可分。总体而言,康熙无视对于徐乾学“违禁取利”等罪行的系列控诉,对其宽平以待,可能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其一,清代前期为巩固基业,奉行拉拢明朝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徐乾学之舅为明末大儒顾炎武,与众多明朝遗民相联系,清政府以科举延揽徐乾学之辈,自然优容以待。当徐乾学将一些官员的声势奸利之状告知康熙,康熙疑问为何没有其他人反映这些事,答曰不敢,康熙反问:“满洲不敢,汉官何惧?……有予做主,何惧?”[2]足见此时朝廷对于汉官的重视和保护。其二,徐氏一门三贵,家族势力庞大,社会根基深厚。徐乾学与其弟徐秉义、徐元文先后中举,此后均担任朝中要员,时人皆知昆山徐氏家族之显赫。其三,徐乾学门客众多,具有广泛的政治影响。正所谓“以文章被眷顾,领纂修数局,所邀与商略皆天下名士”[3],《清稗类钞》亦载:“徐乾学好延揽海内知名士”[4]。徐乾学主持考试时,起用韩菼等人,其后皆为当朝重臣,以至于“凡有文字,非经徐健菴改定,便不称旨,满、汉俱归其门。”[5]其四,徐乾学具有突出的个人才能,简在帝心。在他任左都御史时,告诉诸御史“惟当知有国,不知有身,愿诸公断苞苴之路,绝欺蔽之私,整肃台纲,宣誓天下”,切实为皇帝考虑,嘱咐官员进言应当凝练:“人臣进言,当识轻重,若毛举细过,以求称塞,非所望也”[6]。当徐乾学受许三礼弹劾即家编辑后,皇帝赞誉他“卿学博才优”,嘱咐其详核《一统志》,殚心参订,考据确实。其五,徐乾学承担了修史的重要政治活动。古代官方修史活动与政治利益息息相关,往往直接被纳入权力话语体系[7]。而徐乾学先后总领《大清一统志》《大清会典》及《明史》的纂修,康熙对其给予厚望,在他上疏乞归时,叮嘱他书籍随身编辑,并赐御书“光焰万丈”匾额[8]。直至乾学命卒前,康熙仍唤他回京修书。其六,基于平衡两党之争的需要。徐乾学先攀附于明珠一党,后声势日焰,遂自结一派,与其相抗。“明珠竟罢相,众皆谓乾学主之”。两党之争亦是满、汉官员之争,前文所述两江总督傅拉塔即为明珠党人,在傅拉塔殁后,有人将徐乾学欣喜之状上奏于皇帝,康熙深知其事,但未置一词[1]。
若豪族丧失政治价值,君主便可能不再施以“宽平”之策,此时规则复而起效,这亦是其灵活性的体现。以徐乾学为例,在其为官数年间,康熙并非始终内心欣然待之。傅拉塔参徐乾学兄弟之后,“王俨齐进密折,言徐氏害他。上又发与九卿看,曰:‘我看江南乱闹,不过徐、王两家。不如两家都教他住关东地方去,庶几清白。”[2]康熙二十八年,许有三复参徐,皇上谓:“汉人倾险,可恶已极。”[3]这些态度埋下了徐氏一族日后式微的種子。到雍正初,有人告发徐乾学幼子徐骏诗有“明月有情远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之句[4],最终徐家“以翰林累文字狱,处斩,家道遂微,移家安徽”[5]。
七、余论
借贷形式出现之初,是人们用来缓解手头之急,以达相济之义。历朝历代的借贷利率、借贷方式等并无定制,“高利贷”一词的具体内涵不尽相同,但一般来说,各种借贷形态中具有谋利性质的部分即属于高利贷资本,而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着高利借贷的问题。在唐宋时期,高利贷行业已发展得较为完备和发达,相关规制体系也渐趋成型。发展至明清,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财富不断向高利贷资本转化[6],自官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村,社会对于借、贷行为的需求日益膨胀,甚至不乏皇室、官员投身其中。在清代前期,已呈现出借贷形式复杂多样,参与主体众多的局面,参与者之间不仅有贫富、身份之别,也可能具有民族之分。同时,其中还有同乡会馆、合会等信用团体以及票号、钱庄等金融机构的广泛参与[7]。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对于借贷行业十分依赖,而相关法律规制与司法实践状况也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征。
比较清代前期与唐宋规范内容的不同,其在立法上总体沿袭了前代反高利贷的核心思想,同时更加细致化、严格化和去暴力化。一是就违契不偿行为的处罚而言,清代前期的管理更严。唐宋时期区分了非出息借贷和有息借贷(即“出举”),据唐《杂令》,出举任依私契官不为理,而对于官为理的非出息之债,负债违契不偿的最低刑罚是笞二十;但《大清律例》则规定,违背三分利率标准和一本一利利息总量的,“违者,笞四十……”,严格于前者。二是就放贷主体的限制性规定而言,清前期的规范更为细致。唐宋时期主要是对监临官员借贷进行了限制;而在清代前期,不仅对监临官吏从事借贷行为进行限制,同时也对豪势之人、听选官吏、监生、旗人等多种身份的人参与借贷进行了限制。三是就违法放贷的救济手段而言,清代前期法律所允许的救济手段摒弃了一些前代的非人性化内容,比如不再有役身折酬、以人质债等内容,而是明文规定不许豪势之人私自强夺孳畜产业,并不许准折人妻妾、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