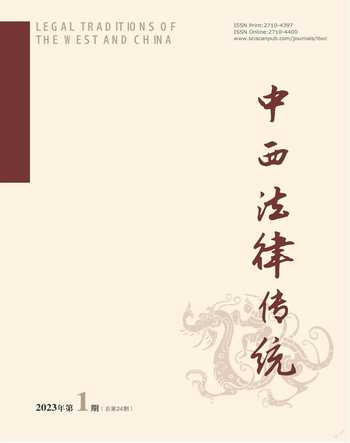民初汉口地方审判厅与商务总会的冲突及其影响
2023-12-06牛鹏
摘 要|自汉口地方审判厅成立以来,其与汉口商务总会之间的关系就十分紧张,拘押商务总会皮业议董张碧泉事件进一步导致两者间冲突的暴发。汉口商务总会在冲突中态度强硬,甚至不惜以解散为由逼迫民政长和司法司撤换了地方审判厅推事。从冲突的原因看,其直接原因在于商务总会的积怨暴发,间接原因在于汉口的地域特殊性,根本原因则在于商务总会意图藉此争夺商事纠纷裁判权。从冲突的影响看,冲突激化了本已紧张的地方审判厅与商务总会之关系,使两者难以合作化解纠纷,不利于商事纠纷的解决。民初汉口地方审判厅与商务总会分别代表着官方诉讼和民间仲裁两种不同的商事纠纷解决方式,它们之间的冲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司法与仲裁之间关系的反面视角,反思这一冲突对今日正确处理司法与仲裁之间的关系仍不失借鉴意义。
关键词|地方审判厅;商务总会;商事纠纷;裁判权
作者简介|牛鹏(1993-),男,河南鹿邑人,法学博士,郑州大学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法律史、法律文化。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根据清政府《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各省省城及商埠等处各级审判厅应于第二年筹办,并于第三年内一律成立[1]。据此,经报法部批准,汉口地方审判厅于1910年12月正式成立[2]。民国建立后,北洋政府并未全盘否定晚清司法改革的成果,汉口地方审判厅一直运行至1927年1月才改设为汉口市法院。以往学界虽对地方各级审判厅的设立、法官选任及运行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但基本集中于天津、京师及东三省等地[1],且多聚焦于审判厅自身,而较少关注地方审判厅与行政官厅、商会之间的关系[2]。本文拟从民国初期汉口地方审判厅与汉口商务总会之间的冲突入手,通过对冲突过程的还原探究一起简单的拘押事件缘何演变为两者之间的直接冲突,从而在丰富地方审判厅研究之余,为观察民初地方审判厅与商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微观而真切的视角。
一、汉口地方审判厅与商务总会的冲突
汉口地方审判厅与商务总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追溯至审判厅正式成立前的审判见习所时期。根据《汉口筹设审判厅之规划》,汉口地方审判厅在夏口厅署西边空地建造房屋,先行试办[3]。先行试办的汉口地方审判厅暂以审判见习所为名,于1909年10月19日正式开庭审案[4]。由于审判见习所人员并非正式法官,其薪水十分微薄,多不敷使用,故审理案件时常有贪贿行为,从而招致商务总会不满。比如在益大钱庄店东蔡东昌标的三万两的一起控告案中,蔡东昌本已缴纳讼费五百两及铜元三十串,见习所收纳讼费的底簿却仅记载收到印花费银二十两,并无收银五百两及铜元三十串之根据,商务总会为此极为愤怒,并要求审判见习所新任所长王国铎严加查办[5]。
审判厅正式成立后,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缓和。1911年1月30日,汉口地方审判厅正式成立不足两月时,《时报》就报道了一起汉口地方审判厅推事周德馨与商务总会平安社之间的冲突,平安社对周德馨不维护商人利益的行为十分不满,历数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多项违法行为[6]。此后,汉口地方审判厅与商务总会之间常因商事案件的审理发生纠纷,这些纠纷虽未激起太大波澜,但却使商务总会对地方审判厅的不满日益加深。1912年11月26日,汉口地方审判厅在“张碧泉与潘汉城施工合同纠纷案”的庭审中以“咆哮公堂”为由拘押了汉口商务总会皮业议董张碧泉,导致两者间冲突的暴发。汉口商务总会在冲突中态度强硬,多次向实业司、司法司等部门和黎元洪副总统反映情况,甚至以解散为由,逼迫民政长和司法司撤换地方审判厅推事和厅长。
(一)事件之起因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武汉三镇俱陷战火之中,汉口尤甚。战争给汉口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据载:“北军之焚汉口也,始自歆生路一隅,实为九月八日,于时全镇犹无恙也。迨十一日,而全镇皆火矣……所存者,下惟花楼一带,上惟硚口一带,不及全镇十之一焉”[7]。汉口商务因此备受摧残,市面凋零。1912年初,为招劝商人回汉口复业,汉口商务总会打算先将街道整理,以方便招徕。皮业议董张碧泉受商务总会总理李紫云和协理蔡文会之委托整理十垱一带街道。张碧泉与工头潘汉城签订施工合同,并在施工过程中因施工质量问题与潘汉城发生争议。张碧泉认为工头潘汉城偷减工料,所修未能合法,一遇天雨,仍如泽国,故欠付潘汉城工钱千余串未给,要求设法修好再行给付。潘汉城则认为施工符合合同约定,要求再修需要加工资。张碧泉拒不支付所欠工钱,潘汉城遂将张碧泉起诉至汉口地方审判厅。1912年11月26日开庭审判过程中,汉口地方审判厅推事向天钟以张碧泉“咆哮公堂”为由,将张碧泉拘押五日。
(二)商务总会之应对
张碧泉并非普通商会会员,他不僅是牛皮行业义茂隆公司经理,曾代表汉口商务总会参加渡日清国实业团,筹款筑建长乐畈堤院,创办道心女子学校等,更担任汉口商务总会第四届议董。因此,张碧泉被拘押后,商务总会极为愤怒,汉口商务总会总理李紫云立即致电汉口地方审判厅厅长贺德深,但并未得到满意之答复。李紫云本拟立即渡江至武昌向军民二府,实业、司法二司当面陈述,但因夜间不能开城,故采取电告之办法,请军民二府,实业、司法二司立即查办汉口地方审判厅相关人员。1912年11月29日的《国民新报》全文刊载了此次通电内容:
武昌副总统、民政长、司法司、实业司钧鉴:顷因本会议董张君碧泉为修街公益事,与工头潘汉城即天囚在地方审判厅审讯。该厅故意倾袒,经张碧泉层层驳复,无以相难,乃加以咆哮公堂之名,立即拘押,虽有旁听诸人代为分辩,而该厅出言狂悖,意在不押不休。以商界向有资格之人为地方承办公益之事,不知该厅是何局心,欲加之罪,全体震骇,人人自危,奔赴呼号,咸有同病相连之势。本会既恐愤激之生事,又苦维持之无方,亟思渡江,面受进取,因恐夜阑,有骇听闻,拟于明晨上谒屡陈,先此电闻,伏乞垂察。
张碧泉被拘押第二天,汉口商务总会召开全体会议议决对付办法,“一、贺、向不去职,本会即解散;二、贺、向不去职,不完纳一切税捐;三、贺、向不去,凡官厅交办各事,概置不理;四、将实情通电各省省会及大总统国务院。”全体会议结束后,总理李紫云立即率议董、帮董共八十人渡江,拜谒时任鄂督黎元洪和时任鄂民政长夏寿康,历陈汉口地方审判厅各官之劣迹,黎元洪极为震怒,谕令候会商民政长,一律撤换。夏寿康则称,接电后已行饬司法司查办,必能使诸公满意。
(三)地方审判厅和司法司之态度
汉口地方审判厅无意激化与商务总会之间的矛盾,拘押张碧泉后就有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汉口商务总会于1912年11月27日召集全体会议商议应付办法时,夏口县知事徐金声、汉口地方检察厅厅长袁凤曦就曾到会商于李紫云总理,请用公函具保,即将张碧泉释放,但汉口商务总会以不知张碧泉所犯何罪为由,拒绝用公函具保。时任司法司司长张知本接鄂民政长夏寿康的饬电查办此案,张知本与汉口地方审判厅厅长贺德深、推事向天钟均有留学日本法政速成科的同窗之谊,也欲和平了结此案。他命夏口县知事徐金声从中调和,徐金声乃自赴押所,手挽张君出外,张君本不肯出,被众推拥入轿,回商会。徐知事亦踵至,饬放鞭炮,以代为赔罪,并言不日必由司法司与贺厅长问判事以相当处分。然而,司法司意在调和,并非真要处罚贺德深厅长与向天钟推事二人,汉口商务总会未能得到期望之结果,不满情绪日增,称“现已数日,未见当道明文,致商人益动公愤,于五日复齐集商会会议,各团联合会亦派代表前往协议,佥谓共和时代官商应以诚信相待,既许以处分,何以事经数日一味支展……请即将该厅长、推事取消,交高等审判厅按律惩办,以肃法纪。若再延三日不理,是以律法为具文,商人为赘物,任意摧残,有何不可。要此,商会奚益?即行将关防送交实业司,全体解散,自由营业,别谋保护,所有税捐,概不缴纳。”
(四)民政长之处理结果
根据12月5日会议的决议,商务总会于12月6日正式停止办公。这迫使鄂民政长夏寿康不得不对汉口地方审判厅推事有所惩戒,但或许有被商务总会逼迫的不满,其于商务总会停止办公次日宣布的处理结果可谓将双方各打五十大板。1912年12月9日的《国民新报》节录了民政长的处理结果,“查该议董张碧泉被厅拘押,有无冤抑,当以有无咆哮公堂情事为断,当以供单言语为凭。如其果真咆哮,即是违法,虽为议董,亦应照法庭规则惩处。该法官处分正当,本府当为之保障,不许他项团体借众要挟,从旁干涉,以期巩固法权。如其未咆哮,则虽非议董,而法官滥用职权,本府有监察司法、用人行政之责,自当加以处分,不使人民怨愤,致为司法前途障碍。”此一段旨在宣布处理结果前表明自己中正无私,不受任何势力、团体逼迫的立场。然而,本系在商务总会解散逼迫下所做的处理结果却硬要加上此语,无疑给人“此地无银三百两”之感。在宣布具体处理结果时,民政长一方面认为:“承审官向推事遽照司法司頒行之《法庭规则》,将张碧泉判押五日,殊属滥用法权,饬司法司即将该推事撤换,以肃官方。”另一方面也指出:“张碧泉被潘汉城控诉指骗工价以及张碧泉辩诉,皆系个人名义,与商会无干。张碧泉纵被冤抑,自可照章申诉,而商会以全体名义极端争持,核与案卷不符。且商会呈文内有,如谓该厅并不违法,即乞饬命取消汉口商务总会,刻日解散之说,是以地方公共团体主持个人私事,权限未明,殊为本府所不取。”
(五)商务总会之不满
民政长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处理结果也未能使商务总会满意,这从如下两点可得到印证:第一,汉口商务总会并未因民政长公布处理结果就立即恢复办公,而是直至12月13日才因“商界事务繁多,恐日久致滋贻误”而恢复。第二,商务总会对民政长所称之与商会无干的说法尤为不满,发文为自己辩护称:“自该议董此事发生,商界诸人咸有朝不谋夕之势,谓该厅从此心粗手滑,为所欲为,愈复无所忌惮,号呼奔走,万人一心。此时安则俱安,危则俱危,何谓与商会无干,与商务亦无干?”“该厅到汉数月,如何行为,如何名誉,一江之隔,各当道未必不知。以汉口之杂处五方,而该厅又神人共愤,长此不改,一旦猝发难端,不可收拾,皆归咎于本会之作俑,彼时虽欲再求解散,而其悔已迟,此立言之理由也。”[4]“张碧泉亦商会中人,修沟为地方之事,既曰公益,即非个人之私。既曰议董,即为全体之一,当该议董之无辜被押也,本会即出面质问,亦不为过”凡此种种言论,皆表明商务总会在此次冲突中的强硬态度。
二、汉口地方审判厅与商务总会冲突的原因
汉口地方审判厅以“咆哮公堂”为由拘押商务总会皮业议董张碧泉本系个案,但缘何引发商务总会如此强烈的反抗,不仅将副总统、民政长、司法司等官员和部门牵涉进来,甚至在鄂民政长将汉口地方审判厅推事向天钟撤换后仍对处理结果不满。我们认为,拘押事件仅是冲突的导火索,而冲突的暴发则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一)商务总会的积怨暴发
正如《申报》在报道此次冲突时所总结的,“自共和成立以后,行政司法各官,多系新进少年,志傲气娇,每有蹂躏商界之事,平时积怨已深,故藉张案大起反抗也。”换言之,商务总会皮业议董张碧泉被拘押仅是冲突的导火索,而冲突的直接原因则在于商务总会对地方审判厅长期积怨。从汉口商务总会向副总统、民政长及司法司、内务司、财政司、实业司等部门反映情况的函件中也可以发现,汉口商务总会除描述汉口地方审判厅拘押皮业议董张碧泉事件的经过外,更对汉口地方审判厅审理商事案件多有不满,称“(审判厅各推事)皆系年少无知之徒,尤为贪横,明索贿赂,毫无廉耻,借讼费罚钱之名,行贪赃枉法之实。”“该厅成立以后,所有各商来会皆诉其枉晰徇私之案,指不胜屈”“该厅神人共愤,长此不改”。
事实上,商会对地方审判厅审理商事案件存有不满并非汉口特例。早在1911年,四川成都票帮联义分会就曾在《请设商事裁判所》的报告中称:“自审判厅成立后,公断失间接强制之效力,办理稍形掣肘,而原被告并有程度者,仍愿受公断处判断,不愿赴审判厅诉讼焉。”1912年11月1日至12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临时工商会议上,宁波商会代表盛在珦也力陈地方审判厅审理商事案件的弊端,认为法官对商业习惯不甚明了不能为正当判决,普通审判厅案件繁多致商事不能迅结,商事裁判不必拘泥于形式可口头决之,进而主张效仿法国成例在商业繁盛之区设立商事裁判所专司商事诉讼。
具言之,当时商会对地方审判厅审理商事案件的不满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审理效率较低;地方审判厅的案件审理程序主要参照《法院编制法》和《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之规定,程序复杂、耗时较长,商会认为地方审判厅依照这些程序审判商事案件的效率较低,没有考虑商事案件需要快速解决纠纷,商事裁判不必拘泥于形式等特殊性。第二,法律适用未考虑商事习惯;商会认为在商事法律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商事案件审判应主要依据商事习惯,而地方审判厅的推事多为留学归来的年轻法律人,对商事习惯往往不甚明了,很难做出正当判决。第三,公正性不高;北洋政府财政困难,地方审判厅的经费多依靠讼费补贴。商会认为审判厅各推事在案件审理中常有“借讼费罚钱之名,行贪赃枉法之实”的情况。第四,商人尊严难以保障;根据《法院编制法》之规定,地方审判厅审理案件时对两造有拘押、罚款等权力,商会认为地方审判厅常滥用此权力侵害商人尊严。出于以上几个方面因素,汉口商务总会对地方审判厅的不满和积怨日深,从而在皮业议董张碧泉被拘押事件中集中暴发。
(二)汉口的地域特殊性
如前所述,对地方审判厅商事案件审理的不满并非汉口商务总会所独有,那么缘何唯独汉口地方审判厅的一起拘押事件演变为两者的直接冲突,并进一步影响到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原因或许与汉口的地域特殊性有关。具体而言,首先,辛亥革命在武昌打响第一枪,汉口商人在其中出钱出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口商务总会与黎元洪副总统等都有着密切联系,其表达自身不满的渠道十分畅通,且往往能得到支持和同情。其次,汉口为九省通衢,商贾辐辏,素有“楚中第一繁盛处”之誉。清末开埠通商后,华洋杂处,商事益盛,更以“东方芝加哥”驰名中外,商业异常繁盛,使得汉口商务总会的势力十分庞大。据载,截至1927年,汉口商务总会“遵章入会者已达一百三十余帮,上而银钱行号,下而鲜鱼土果,无不举有会员入会议事”,甚至成立有武装力量协助政府进行治安管理,任何政治力量都不可能忽视汉口商务总会的诉求。最后,民国初期的汉口既是商业中心也是政治中心,受各方广泛关注,任何事件都极易发酵从而扩大影响。比如拘押事件发生后,当时的各大报刊包括《申报》《时报》《大公报》《新闻报》等都进行了跟踪报道,从而使事件影响越来越大。
(三)商事纠纷裁判权的争夺
无论是商务总会的积怨暴发还是汉口的地域特殊性都只能视为冲突暴发的表层原因,从更深层次看,冲突更寄托着商务总会争夺商事纠纷裁判权的期望。按法部奏定,凡省城、商埠已设各级审判厅处,其界内诉讼事件,地方官不得受理。1909年12月28日正式颁行的《法院编制法》第十九条进一步明确:“地方审判厅有管辖下列民事刑事诉讼案件及其他非讼事件之权:一是不属于初级审判厅权限及大理院特别权限内之第一审案件;二是不服初级審判厅之判决而控诉之第二审案件以及不服初级审判厅决定或命令而抗告之第二审案件。”据此,汉口地方审判厅的司法权已十分清楚,其有权管辖境内不属于初级审判厅权限及高等审判厅权限、大理院特别权限内之所有一审案件和不服初级审判厅或县知事判决、决定、命令之所有二审案件。此外,对于解散会社、破产等商事非讼事件地方审判厅也有权管辖[1]。同时,出于统一法权之目的,法部认为其他任何社会团体都不得分享地方审判厅的司法权,这就使地方审判厅的司法权不可避免地与商会的公断权之间产生冲突。
具体而言,商会依据《商会简明章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之规定享有公断商事纠纷之权[2],且这一权力甚至有排除行政官厅管辖的效力。以汉口商务总会为例,其根据清政府颁布的《商会简明章程》于1907年正式成立[3],并在成立之初就将公断商事纠纷的权力写入章程,同时设置了专职从事商事公断工作的理案议董[4]。根据《汉口商务总会章程》规定,理案议董负责监理钱债纠葛词讼诸事。当选理案议董应具备如下三个条件:一是应品行方正;二是应系行号巨东或经理人,每年贸易往来为一方巨擘;三是应谙熟公牍通晓事理。”理案议董在任期上与总理、协理及其他议董一样,任期一年,每年改选一次,连选可连任,但连任次数以两次为限。汉口商务总会设理案议董公断商事纠纷的权力也得到了鄂督的明文认可。1907年12月,《时报》刊载了《鄂督札汉口商务局文(为关涉商务案提归商会办理事)》,首次在官方层面明确商会商人及商务涉讼之案一律由汉口商务总会公议理处,不得径行前往官府控诉,即使已经提起之控诉也一律由商务局查明起数,提归商会办理[5]。
因此,晚清时期,汉口商务总会在公议理处商事纠纷方面曾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汉口商会史料汇编》的整理,1908年初至1910年8月,汉口商务总会几乎每天都有商会判案纪要刊发于报,其中仅1908年3月7日至1908年5月31日间,汉口商务总会受理案件已逾100件[6]。然而,1910年12月汉口地方审判厅设立后,汉口商务总会的理案结果不再具有强制执行力,理案数量大幅下降,商会期望能再度获得商事纠纷的裁判权[7]。
但地方审判厅并不愿商务总会分享其裁判权,其原因主要出于如下两个方面:第一,汉口地方审判厅受理案件量并不大,若再将商事纠纷裁判权让与商务总会,地方审判厅将陷入无案可办的尴尬境地;汉口地方审判厅虽名义上拥有辖境内一切民刑事案件的裁判权,但实践中由于“遵照部章,凡属华洋互控案件,仍暂照旧,由夏口厅衙门照约办理……在租界之华人不得传案备质者,亦得由审判厅移送夏口厅衙门办理。查汉口全镇,长不过二十英里,半属租界,半属华界。向来夏口厅受理词讼,华洋交涉居其四,华人与租界华人互控居其三,余则内地华人互控之案。”[8]若再将内地华人互控之商事案件交由商务总会办理,地方审判厅必将陷入无案可办之地。第二,汉口地方审判厅需要依靠讼费收入补贴日常运行;辛亥革命之后湖北财政困难,财政收入“惟恃武汉商店之运输,而汉口商铺已十焚其七,因不能建筑房屋之故,甚难复业,其存在者,又以时闻兵变谣言可骇,亦不敢多办货色,是该税局收数一时断难复旧。”财政困难导致汉口地方审判厅核发经费难以达到法部所定额度,审判厅不得不依靠讼费收入以作补给。
基于此,汉口商务总会与地方审判厅之间围绕商事纠纷裁判权展开了激烈争夺。比如汉口商务总会曾在1912年10月以“现在各级法官未尽通晓商情,往往有误会而误判者”为由,“提议仿照泰西成法,设立商事审判厅,专理商事纠葛”。拘押事件发生后,汉口商务总会更多次提议设立商事裁判所,希望遇有商务案件发生,即由该所裁判,以护商权。由此观之,汉口商务总会藉由拘押事件与地方审判厅暴发冲突的根本原因或是希望以此表明地方审判厅并不能高效审理商事案件,从而争夺商事纠纷裁判权。
概括而言,从一起简单的拘押事件演变为汉口地方审判厅与商务总会之间的冲突,其直接原因在于汉口商务总会对地方审判厅的积怨已深,故借此案而反抗;间接原因在于汉口的地域特殊性决定商务总会有充足的渠道和途径表达自身诉求;根本原因则在于汉口地方审判厅的司法权剥夺了商务总会裁判商事纠纷的权力,商务总会希望通过拘押事件的冲突重新夺取商事纠纷裁判权。
三、汉口地方审判厅与商务总会冲突的影响
从后续发展看,冲突最直接的影响在于汉口商务总会藉此要求鄂民政长撤换了汉口地方审判厅推事向天钟,地方审判厅厅长贺德深也在冲突后不久被调任浙江高等审判厅推事。同时,汉口商务总会也更加积极探索设立商务裁判所以获取商事纠纷裁判权,并化解商事纠纷。拘押事件发生不久,汉口商务总会就称:“汉口商务日见繁盛,唯有纠葛案件多由行政官厅裁判,往往不得其平,甚至缠讼不休,损失愈多。汉口商务总会近接农工商部来电,饬设商务裁判所以保商权。刻正筹办一切,不日即行开办。”不久后发生的另一起冲突进一步坚定了商务总会设立商事裁判所的决心。“汉口商务总会自帮董张碧泉因为公益被审判厅推事拘押,全体公愤。近复因山货帮董镇建亭因公被诬,反受法官凌辱,商权日受蹂躏。刻已决议,遵照部章设立商务裁判所,遇有商务案件发生,即由该所裁判,以护商权。”农工商部与商会联系紧密,出于保商护商之目的可能支持汉口商务总会设立商事裁判所,但设立商事裁判所并与地方审判厅共享司法权显然不可能得到司法部的同意。作为妥协之产物,1913年,北洋政府农工商部与司法部共同颁布《商事公断处章程》,禁止各地设立商务裁判所,而应设商事公断处。因此,汉口商事裁判所并未能真正设立,汉口商务总会虽通过此次冲突要求鄂民政长撤换了地方审判厅推事,但未能实现其争夺商事纠纷裁判权的目的。
当然,此次冲突的影响并不仅在于地方审判厅的推事被撤换,更在于它进一步激化了汉口地方审判厅与商务总会之间的矛盾,导致两者难以合作化解纠纷,限制了此后汉口商事公断处职能的发挥。根据《商事公断处章程》和《商事公断处办事细则》之规定,公断结果的强制执行需要禀请管辖法院宣告,若地方审判厅不愿配合或不尽心配合,公断结果的可执行性将大打折扣,公断的认可度也将因此大受影响。从此后汉口商事公断处的运行情况看,汉口商事公断处设立于1924年8月1日,至1928年1月7日被裁撤,设立不足四年,其公断案件数量虽无明确数据统计,但从公断经费收入可见汉口商事公断处受理案件并不多。据载,汉口商事公断处成立第一年共花费薪水辛工伙食及一切杂费等约八千五百余元,而全年公断费收入仅一千元[1],显然不复清末汉口商务总会理案之盛况,也不如京师、苏州、上海等地商事公断处运行良好。比如京师商事公断处在1915年6月8日成立至1925年12月7日的十年时间里受理商事纠纷776件[2],在化解商事纠纷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与京师商务总会与京师地方审判厅之间的良好关系是分不开的,比如在京师商事公断处成立时,京师地方审判厅便称“该处多尽一番劝解之心,即人民少受一番诉讼之累,总期减少讼事为惟一之目的”,并规定“起诉案件经商事公断处调处,本厅认为平允而又无别项办法者,得采据所议办法以为判决”[3]。
此外,受此次冲突的影响,在一些具体案件审理过程中,汉口地方审判厅也不愿再对商务总会通融,完全秉持公事公办的态度。比如在审理辛亥革命后的债权债务案件时,汉口商务总会曾恳请汉口地方审判厅能够暂缓判决与执行,俟各帮议筹偿还划一办法,再行判决或执行。时任汉口地方审判厅厅长邹麟书称:“据称困苦各节,自系实情。惟本厅职在司法,凡诉讼当事人一方面有不顾和解者,勒令和解,實与现行法相悖……该代表果能请商会召集钱商各帮公认暂缓追诉,本厅采不干涉主义,缓于判决。否则,仍旧进行,以全天职而重法权。”[4]厅长之答复或许有鄂政府催偿官钱局等欠项甚急的因素[5],但在各地纷纷暂缓判决、执行并对欠款减成分期的背景下,汉口地方审判厅如此官方的答复显然没有任何照顾汉口商务总会的意思。
四、结语
民初汉口地方审判厅与商务总会之间的冲突为我们观察地方审判厅与商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微观而真切的视角。虽然从法律层面看,商会的商事纠纷公断权并非裁判权,本不应与地方审判厅之间就商事裁判问题发生争议;但从实践层面看,商会希望从地方审判厅手中夺取商事纠纷裁判权的努力从未停止,导致两者之间的关系紧张。汉口地方审判厅拘押商务总会皮业议董张碧泉事件成为冲突的导火索。从一起简单的拘押事件演变为两者间的直接冲突,既有历史的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其背后所反映的问题远比冲突本身更值得关注。
一方面,从汉口地方审判厅与商务总会之间冲突的处理结果可以看出,民初商会所拥有的势力已十分庞大,不仅在武力上拥有保安团以作保障,在政治上甚至可以左右政府的决定。汉口地方审判厅推事向天钟因此次冲突被撤换后不得不回乡开办律师事务所,厅长贺德深虽未因此被撤换,但不久后也被调任浙江高等审判厅推事。由此可见汉口商务总会在当时的影响力和优势地位,也从侧面证明商会在维护商人利益方面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汉口地方审判厅与商务总会之间的冲突亦可视为两种不同商事纠纷解决方式的交锋。汉口地方审判厅历任厅长、推事多是日本法政速成科留学归来的年轻法律人,代表的是司法权,是严格按照法定程序,依据法律裁判的官方诉讼模式。汉口商务总会的议董多是商事领域的巨商、经理,代表的是仲裁权,是以解纷为目标,依据商事习惯仲裁案件的民间裁决模式。两者理应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而,民初的地方审判厅为争抢案源、收取讼费,不支持商会的理案活动,而商会为保商护商则极力争取商事纠纷裁判权,排除地方审判厅的管辖,两者互不相让、互不配合,导致其纠纷解决功能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因此,民初汉口地方审判厅与商务总会之间的冲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司法与仲裁之间关系的反面视角,反思这一冲突我们应当认识到承认仲裁权并不会损害司法权的统一和独立,而仲裁权也不可能完全排除司法的监督,只有两者密切配合才能互相促进。这一认识对我们今日正确处理司法与仲裁之间的关系仍不失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