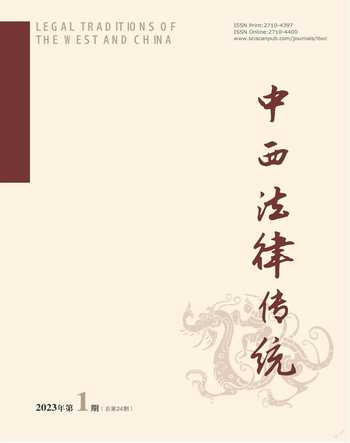厌女:马基雅维利政治观的社会性别剖析
2023-12-06汤怡琳
摘 要|马基雅维利在政治思想史上取得了极其显赫的地位,因此学界往往专注于对马基雅维利政治观的理论分析,而缺少对其政治观的社会性别剖析。从社会性别角度看,马基雅维利的作品,尤其是其喜剧作品《曼陀罗》中充满着浓厚的厌女色彩。这不仅仅体现在他对女性形象的扁平化描写里,而且还体现在他对两性关系的理解中:女性作为他者,对作为政治主体的男性产生了隐含的威胁。基于此种对女性的歧视,马基雅维利通过划分公共政治领域与私人道德领域,将女性排挤出了公共政治领域,使女性成为了政治的“失语者”。
关键词|马基雅维利;曼陀罗;政治观;社会性别
作者简介|汤怡琳,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2021级法律史硕士研究生。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马基雅维利被誉为现代政治科学之父。在他生活的时代,意大利内部邦国林立,众多公国与王国之间互相斗争,国家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的政治真空状态。外部则虎狼环伺,时刻面临着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大国的威胁。因而,如何在纷乱的政治生态中构建统一的民族国家,就成为了马基雅维利终其一生思考的问题。反映在他的政治作品中,便是波谲云诡、暗流涌动的权术斗争与厉兵秣马、战鼓雷鸣的战争场景。在马氏笔下,在这样一个被血色沾染的灰色世界中,男性是唯一的主宰,历史的目光聚焦在男性围绕权力而展开的斗争中。在这样一个明显男性化的世界中,“他”是主体,“他”是绝对,而“她”是他者,是与男性、政治二元对立的“失语”角色。男性以权力的代表自居,女性作为“非人”或至少是不完美的人而受到歧视与压迫。
然而,正是由于马基雅维利在政治思想史上的瞩目成就,目前学界有关马基雅维利的已有论著,往往以其政治理論为根据而展开探讨[1]。但却鲜少有学者关注到马氏笔下的女性。就笔者所检索到的中文文献而言,仅有一篇论文以社会性别为切入点解读马基雅维利[2]。外国学者虽然给予了社会性别理论足够的重视,但在谈及马基雅维利时仍是一笔带过[3]。可以说,迄今学界对马基雅维利笔下的女性形象及由此衍生的相关内容的关注是极其匮乏的。
若要深入探讨马基雅维利对女性的态度,仅仅关注《君主论》与《论李维》等作品是不够的。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作品进献对象为君主,因而文本中对女性的评论仅是只言片语,难以展现其性别观的全貌。因此,笔者将研究的主要目光投向了其喜剧作品。马基雅维利的喜剧作品围绕着男女主人公而展开,对女性的描写更丰富,更便于完整把握他对女性的看法。同时,马基雅维利喜剧作品的主题常常与其政治观相挂钩,也益于进一步探究马氏性别观与政治观之间的动态关系。
在马基雅维利的喜剧中数《曼陀罗》的成就最高、影响最广。《曼陀罗》讲述了一位年轻人通过诡计得到一位已婚之妇的故事,主题虽荒诞不经,但一经上演便获得满堂喝彩,即便五个世纪过去,如今该剧仍活跃在西方的舞台上。可以说,《曼陀罗》在马基雅维利的喜剧中具有代表性。而且,马基雅维利对女性、两性、政治的看法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在这短短的五幕戏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符合本文的研究意旨。因此,本文拟从社会性别角度出发,以《曼陀罗》为中心,兼及《君主论》与《论李维》等作品,旨在通过文本分析,尽可能展现各作品内部的相互关联,从而揭示马基雅维利的作品中一以贯之的厌女色彩。
一、马基雅维利笔下的女性形象
在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作品中,很少能够看到女性的身影。即使极少数女性人物的登场,也几乎无一例外地作为“丑角”,目的在于警示君主避免女性在政治生活中带来的灾厄[4]。女性角色更多地出现在马基雅维利的戏剧或诗歌之中,而这样的艺术形式往往描绘的是一种荒诞的幻想世界或带有隐秘的私人属性,相较于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作品,题材显得更为轻飘[5]。但即使是“轻”的喜剧,也蕴含着马基雅维利“重”的政治主张。几乎所有评论家都注意到《曼陀罗》剧中女主角Lucrezia的名字是建立罗马共和国的故事中Lucretia的意大利拼法。而喜剧中的人物名字,往往有特定理由与词源上的根据[6]。马基雅维利通过对戏剧中人物的取名,刻意让这一荒诞喜剧与罗马的政治主题相挂钩。也正是基于马基雅维利“夹带私货”的个人引导,后世的评论家往往侧重于探求马基雅维利喜剧背后的政治主张,而忽视了其作品中本身存在的性别角色问题。换句话说,正是马基雅维利在政治思想史上的显赫光辉,掩盖了他畸形的社会性别观。
当读者重新调整目光,将重心转移到马基雅维利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就会发现马基雅维利对女性作为弱势性别(weaker sex)显而易见的蔑视:在其政治作品中,马基雅维利通过对君主性格的负面评价,影射了女性在公共政治领域的“无能”;在其艺术作品中,马基雅维利对女性的扁平化认知则反复表达了他对女性的轻贱。
Virtus(拉丁文词根vir,男子)在罗马早期的用法中指向“男子气概”,尤其是战争中的勇敢[1]。马基雅维利继承了罗马古典理论中virtus(德行)的内涵,将其改造为virtú(能力),并一再告诫君主通过virtú以获得荣耀(gloria)。virtú这一概念在马基雅维利的文本中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后世的评论家始终喋喋不休地围绕着virtú的具体内涵而进行热烈的探讨[2]。
但是,却鲜少有学者关注到,在马基雅维利文本的遣词造句中,反复出现了一个与virtú所代表的男子气概相对立的概念——effeminate,即“娘娘腔的”或者“女人气的”[3]。虽然“女人气”并不等同于“女性”,即便人们轻视“女人气”的男性,也不意味着会去贬低女性。但是在马基雅维利这里,他一再告诫君主应避免的“女人气”性格,正是他所认为的典型女性。马基雅维利提到,君主如果被人认为变幻无常、愚蠢无聊、阴柔女气、软弱怯懦、优柔寡断,就会受到轻视。君主应该努力在行动中表现得伟大、英勇、庄重、坚韧[4]。作为一组劝谏君主如何为人处世的对照词,那些负面性评价的品质无一例外地可散见于马基雅维利对女性描述的文本中[5]。换句话说,作为执政者的君主,为赢得人民的尊重与个人的荣耀,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与女性相似。其中被以女性指称的语词在价值判断上低于被以男性指称的语词。后者被认为是正面的、重要的、主导的,前者则是负面的、次要的、从属的。它使上述与性别无关的现象和概念通过这种象征手法被等同于“女性的”和“男性的”,从而在它们之间建立起“隶属——统辖”的等级制关系[6]。
无论如何,马基雅维利政治作品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进献给统治者,得到统治者的垂青,因而在政治意图的笼罩下,其社会性别观的轮廓体现得还不甚明晰。然而在《曼陀罗》等以女性角色为中心的艺术作品中,可以说是实实在在地暴露了马基雅维利的女性厌恶。《曼陀罗》这部戏剧的基本情节很简单,不过是描述了一位年轻人(加利马可,Callimaco)在食客(李古潦,Ligurio)的帮助下,通过欺骗一位求子心切的老人(尼亚,Nicia)来得到一位女性(卢克莱西亚,Lucrezia)的故事。但令人感到复杂难解的是,马基雅维利在其中对女性体现出的极度扁平化的认知。
在马基雅维利的作品中,女性被简单地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年轻的女儿或者是未婚的在室女,另一种则是年长的母亲或是已婚的妻子。《曼陀罗》中的两位女性角色,卢克莱西亚与其母索斯特拉塔就是这样的经典配对[1]。
马基雅维利戏剧中的年长女性与年轻女性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她们并不具有性吸引力或诱惑性,但她们往往对年轻女性形成了一种掌控力。在《曼陀罗》中,索斯特拉塔甫一出场就被描绘为情场上的高手,她世故而又精明,有着曲折的过去[2]。她不仅欣然同意加利马可的全部计谋,而且极力劝解自己的女儿以促成此事。马基雅维利对索斯特拉塔的描写较少,除去剧中交代的她本身的性格,唯一可解释她如此行事的动机就是她所阐明的一条理念——两害相权取其轻。在索斯特拉塔看来,没有孩子的女性等同于没有家,如果她的丈夫去世,就失去了唯一的庇护,会如牲口一般被所有人抛弃[3]。
年轻或未婚的女性则常常被描述为性对象,她们和财产一样都是男性的所有物。每个女性都至少依附于一个男性,或许是丈夫与父亲,也可能是兄弟[4]。同时,这一类的女性还必须是处女或是贞洁的,马基雅维利就曾因西庇阿将他人妻子完璧归赵而声名鹊起一事,对他赞赏有加[5]。
卢克莱西亚,《曼陀罗》的女主人公,就是美德与贞洁的典范。如李古潦所言,“她贤明知礼到足以统治一个王国。”[6]她的丈夫因为卢克莱西亚所具有的德行,而允许她来“统治”自己[7];加利马可也正是因为卢克莱西亚审慎贞洁的品质而饱受煎熬[8]。但是,很多时候一个人走上邪路,并不是因为太“坏”,而是因为太“好”[9]。自然与命运的存在保持着事物的平衡,“好”与“坏”总是相生相伴[10]。这一带有悖谬色彩的理论,既给了加利马可得到女主人公的可乘之机,又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同时也在马基雅维利的信件中也得到了印证:
任何注意到我们信件内容差异的人都会大吃一惊,因为他们认为我们都是严肃的人,只会考虑国之大事,琐碎小事根本不会入我们的眼。但当他们翻过这一页,就会发现我们和他们是同一种人,一样的轻浮、不忠、好色、关心无用之事……对我而言,这无可指摘,因为我们模仿的是自然本性,自然本就是多变的[11]。
因此,卢克莱西亚所谓的道德德性,也即马基雅维利笔下的“好”,与腐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
系[12]。据加利马可说,卢克莱西亚腐化的原因是他和她一起睡的方式,但更准确的说法是力量:不仅是肉体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心灵的,或者说智慧和意志的力量。卢克莱西亚的所谓美德,所谓美好的自然,面对真正的德性,或者说"力量"(virtus),是很容易改变的,或者说是可塑的。
卢克莱西亚德性的易变不仅仅体现在,她在其丈夫、母亲、修士的诱哄下,轻易地放弃了坚守的底线,同意夺去一个无辜男子的性命,而且还体现在与情人共度一夜后,她就变得乖乖归顺于情人。她没有任何良心上的痛苦,她引人称赞的智慧被用来制造假象,蒙骗其丈夫,以便继续与情人偷情。当她在诱哄、欺骗中被拉下圣坛、得知真相后,又全然不见懊悔、愤怒等常人应有的情绪,她仍能继续毫无怨恨地爱慕始作俑者,成为不会对男性带来丝毫威胁的依附物。在卢克莱西亚第二天对加利马可的告白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并没有用到“爱”,而代之以“主人”“父亲”“向导”“保护者”等一系列明显带有父权色彩的语词称呼加利马可,乞求加利马可对她继续进行统治。
如果将卢克莱西亚视作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有着自己权利的人来看,即便考虑到戏剧的情节服务于作者的政治主张,这样一位审慎贞洁的女性,仅一夜之间就做出的突兀转变仍然让人难以接受,而这最终却是《曼德拉》的结局。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当对卢克莱西亚品质难以挂钩的描写被生搬硬套到她身上时,这难道不更像是一个满足“加利马可们”自尊心的故事吗?因为在加利马可们看来,使卢克莱西亚乖乖就范最简便快捷的途径就是性征服,但令人疑惑的是,这样的手段是否真正可行。用更低俗的话说,这样的戏剧无论从政治意义上,还是社会性别意义上来看,都是马基雅维利的吹擂的谈资,精神的自慰品,是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幻想与性幻想。
二、两性关系下的女性“力量”
虽然在马基雅维利的作品中,女性常以男性欲望的容器,被征服的目标而出现。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基雅维利也同样认识到,男性正被一种模糊不明、幽幽萦绕的女性力量所控制影响。女性在愚蠢、软弱的同时,也莫名地拥有对男性构成威胁的可能,被征服者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征服者,两性关系是一场充满张力的军事战争。
李古潦在实施诡计时,反复用到了军事术语:我来担任指挥官,指导今晚行动中的巡逻队。加利马可负责右翼,我负责左翼,尼亚老爷守在中间,西罗抄后路,哪边吃紧增援哪边。此次行动的代码是圣布谷。可见,在马基雅维利看来,爱是一场政治活动,是一场军事演练,若想成功取得征服女性,则首先必须做好严密的排兵布阵,以便一旦时机成熟,就能够成竹在胸地去实现既定目标。
虽然两性关系涉及支配与占有,但这并不意味着男性永远是支配者,而女性则是被占有者。在剧中,加利马可正是因为想同卢克莱西亚一夜尽欢的强烈欲望而饱受煎熬:我的腿在颤抖,五脏六腑像在油锅中,心像是要从胸膛中跳出,我的胳膊無力,舌头打结,眼神涣散,脑子也在发晕。正如这一幕独白所暗示的,两性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即便男性最终成功征服了他追求的女性,在征服的过程中他也可能是受害者。
国家事务和情爱事件之间的区别,与庄严凝重与轻佻戏谑之间的区别相对应,而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品质的交替转换,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素质之间的结合统一,就构成了马基雅维利的自然生活。因此,马基雅维利正是认识到女性在情爱事件产生了对男性潜在的威胁,才在政治生活中反复告诫君主,禁止女性在政治领域出现。《论李维》中有整整一章的内容,论证了国家因为女性而衰落:女性是祸殃的源头,为统治者带来大害,使得他们分崩离析。马基雅维利试图通过列举一些年轻女子的例子,来增强其论点的说服力。其中一个,就是塔昆王子因与罗马的卢克莱西亚有染而断送了家族政权。但罗马的卢克莱西亚在整个故事中唯一的“罪行”,就是她成为了强奸罪的受害者。而且,为了证明自己灵魂的无辜,她甚至走向了死亡的归宿。
即便马基雅维利在文本中不停强化“女性是国家衰落原因”的观念,也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无论是意大利的卢克莱西亚还是罗马的卢克莱西亚,她们在故事中的角色定位都是消极的,她们始终是被动的承受方,被卷入灾厄的不幸受难者。无论是加利马可还是高傲者塔昆,他们所遭遇的麻烦,皆因未能克制自身膨胀的欲望而导致,卢克莱西亚们实际上并没有做任何事。然而马基雅维利认为,卢克莱西亚们自身的存在就激励着男性去制造政治麻烦。也就是说,是卢克莱西亚们本身的美德(一位审慎贞洁,一位勤于女工)才导致了一切的混乱。女性“好”的德行被解释为男性加害行为的动机,这既是受害者有罪论,也是一块为男性开脱的遮羞布。罗马君主制的破灭,并不是因为卢克莱西亚受辱这一突发事件就能导致的,而是它本就行将就木。所以,当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作品中涉及两性关系时,马基雅维利要求统治者完全不沾荤腥,不得玩弄臣民妻女。这并不是因为马氏崇尚贞洁,或将其视为基督教的美德,而完全是因为它的政治意义,是为了避免国家政权被女性颠覆的危险,但其实质是对卢克莱西亚们的“欲加之罪”。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导致国家毁灭的并不仅仅因为女性自身的美德,他认为女性毁灭政权的“力量”并不局限于此。正如上文所提及的,女性品质象征着愚蠢、懦弱、优柔寡断,当男性与女性相联系时,就隐含着男性会被这些劣等品质所感染的危险。性征服可能证明男性的virtú,也可能破坏virtú,它会将和女性在一起的男性也变成一个缺乏男子气概的人,从而转移男性在政治领域的注意力,降低他们的警惕。那么,马基雅维利既认为女性以其低劣的品质而感染男性,又以美好的德行而引诱男性,“低劣”与“美好”共存于女性身上,这是否是一种自相矛盾?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马基雅维利在这里还隐藏了一层更深的意味:女性的美德在被男性力量改变之后,已不再是美德。
马基雅维利借加利马可的独白道出了这一点:
你这是在干什么?你难道失心疯了?就算你得到她,又怎么样呢?你就会知道你错了,你会后悔你付出的劭劳和心机。
加利马可当然明白,得到卢克莱西亚的好处与自己为之付出的行动与心机相比,根本微不足道。因为此次行动最终的胜利,会毁灭行动所追求的目标的价值,也即卢克莱西亚的贞洁。加利马可的诡计腐化了自己所追求的美德,他最终得到的已不再是最初想要的,甚至是永远也得不到自己最初想要的。但他的欲望依然促使着他清醒地走向必然的毁灭之路,也即《克莉琦亚》中所说的,士兵死于沟渠,情人终于绝望。
所以,女性的德行对男性、国家而言是一颗有毒的诱饵,其“力量”就体现在引人堕落。但当完成了这一使命,她们的美德也就归于了虚无,从而失去了任何价值。如果说,这只是马基雅维利对女性“力量”在政治领域中消极作用的警示,那么他对女性在政治中的积极行为则可以称得上是充满了敌意。
高傲者塔昆之妻,是前任国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的女儿。在她的唆使和怂恿之下,塔昆夺去了塞尔维乌斯的性命,成为了新的王。马基雅维利对塔昆夺权的行为并没做过多的描述,仅仅详细分析了他失去王国的原因。但对塔昆之妻篡位行为的评价,却是一反常态地带有强烈的谴责意味,马基雅维利将她评价为“利欲熏心,不顾亲情伦常”。众所周知,马基雅维利在政治斗争中倡导的正是功利性原则,主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但原来低劣的手段也分了三六九等。同样是夺权,塔昆的行为就理所应当到无需一提,而当其妻表现出对权力的渴望时就成为了批判对象。甚至在这一故事中,塔昆是行动的实施者,其妻只是教唆者。低劣手段的高下之分,似乎全因性别而定。究其原因,只因男人是“人”,从此可以远离性别干扰,堂堂正正做人做事业。女人却因为性别之“差”被判为人的“异类”,终生背负着她的性别强加于她的命运,退归家庭,成为私和隐私,在社会上在历史中消失了。历史也就名正言顺地成为了“his”“story”。而且,正是因为女性在政治领域的积极行动是极少见的,所以一旦出现,就会被认为是要与男性夺权,削弱男性之间传统的政治纽带,威胁整个社会以父权制为核心的政治结构,导致国家的不稳定。因此,相较那些沉默被动的女性,马基雅维利对像男性一样野心勃勃的女性,给予了更深的敌意。
三、政治传统下的“失语者”
马基雅维利对女性的看法与古代中国的“女祸论”极度相似,“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两者都不约而同地将国家覆灭的责任推卸给女性,从而顺势将女性赶出了政治舞台。
为达到男性获得政治话语霸权的目的,马基雅维利提出,应当将女性活动的场所囿于一个私人道德领域。这一领域需要不惜一切代价地与政治领域相分离。君主在私人领域的行为不应受到评判,但女性的评判标准只能根据私人的道德。在这里,家庭是私人领域的代名词,政治被划归为公共领域。男性和女性处于政治和家庭这两个完全隔绝的领域,遵守的也是完全相异的道德规范。活跃于公共领域的男性不必受制于道德的約束,他们需要学会虚与委蛇、蒙蔽人民,出于国家利益的目的可以为一切卑劣手段辩护。因此,一位表面上雄才大略的君主,在背后也可能是一位卑鄙无耻的小人。
但被囚禁于家庭这一方天地的女性,她的尊严在于不为人知,光荣在于她的丈夫对她的敬重,快乐在于她一家人的幸福。当她们被要求严格恪守私人领域的道德规范,承担起贤妻良母的角色时,就会面临着一个进退维谷的局面:当一个私人领域的好女人,就肯定成为不了公共领域的合格公民。因为,当她们完成了因性别而加诸于其身的义务,严格遵守了私人领域的道德规则,这也只是证明的是她们具有一定的道德优势。但政治领域是毫无道义可言的,政治要求一个人必须不择手段。当女性在私人领域做的越好,就越是证明了她们在政治领域的无能。
所以,女性属于私人领域这样的话术,既是马基雅维利设下的别有用心的圈套,也是对父权机制的隐秘保护。他通过维持一个根本错误的大前提,来保证男性在政治领域的绝对霸权。一旦这样的制度和原则被当作理所应当,女性就会被迫满足他人对自己在私人领域的特定期待。实际上,当女性陷入以男性为核心的政治话语体系的那一刻起,无论她们以何种方式行为,都意味着丧失了自己本应享有的政治权利。
虽然马基雅维利对公私的简單划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现实主义的国际理论。但并不能由此反推出,如今政治领域中女性受歧视与压迫的局面,仅仅由马基雅维利一人造成。事实上,如果将政治思想史以时代为标准划分,马基雅维利仅仅是上承古代,下接近代的枢纽。政治的厌女症并不因马基雅维利而患得,也没有在马基雅维利这里得到治愈,而是贯穿了整个政治思想史的长河,如沉疴痼疾般持续不断地影响着我们,直至今日。
政治的厌女症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在古希腊时期,根据柏拉图在《斐多》中的记载,苏格拉底在临终前特意遣走其妻任娣,然后才与友人们进入到灵魂与生死的探讨中去。这是女性被男性从公共领域驱逐出去的第一个信号。但对现代影响最深远、最重要的信号则隐藏在近代霍布斯与洛克这些自由主义政治家的著作中,他们的政治理论被现代国家大量吸收,因此在对待女性与权力的态度上,他们的思想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霍布斯并没有像马基雅维利那样赤裸裸地宣扬男女之间的等级关系,他笔下的自然状态让读者有理由相信,霍布斯至少在理论上坚持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在谈及对子女的管辖权问题时,霍布斯认为这一权力应当平等地属于父母双方,因为“男人与女人在体力和慎虑方面并不永远存在着那样大的一种差别。”虽然在表面上霍布斯并不排斥将子女交给母亲养育,但实际上他只将这种权利赋予给了具有男性特征的妇女——亚马孙国的妇女、“不知有父”时代的母亲,或者是极少数女王。其中,亚马孙国妇女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她们能够担当通过武力保家卫国的责任,这恰恰与马基雅维利所推崇的男子气概不谋而合。
在论述完宗法上的管辖权后,霍布斯进一步提到了家族主权的权利归属:不论这家族是由一个人及其子女组成的,还是由一个人及其臣仆组成的,抑或是由一个人及其子女与臣仆组成的都是一样;其中父亲或家长就是主权者。
这可以理解为,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签订的社会契约之外,实际上家族内部也存在一份契约,一份关于屈从的契约。当女性被男性所统治而获得在自然状态下的保护后,他们之间就缔结了契约,使得女性的身份转化为了主人的臣仆。因此,霍布斯虽然极其有限地给予了女性抚养者的身份,他同样将女性放在父权制家族中被统治与服从的地位。霍布斯将主权者比喻为家族中的男性家长,这就意味着被主权者所代表的国家也就具有了男性家长的男性特征,家族中的臣仆契约被隐晦地推及到了整个国家层面。
洛克的理论与霍布斯在很大程度上有重合之处,洛克同样在理论上主张人人平等,他写道:
为了正确地了解政治权力,并追溯它的起源,我们必须考究人类原来自然地处在什么状态。那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这也是一种平等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切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互的,没有一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利。极为明显,同种和同等的人们既毫无差别地生来就享有自然的一切同样的有利条件,能够运用相同的身心能力,就应该人人平等,不存在从属或受制关系。
但显然,洛克所说的“人”并不是一切人,而是特指人类中的男性,他在驳斥菲尔麦的过程中,常以亚当与夏娃为例证明自己的观点: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这里所引用的《创世纪》第三章第十六节的这些话……是对夏娃的一种惩罚……那就不能说这里存在着什么勉强妇女要接受这种压制的法律,如同若有办法避免生儿育女的痛苦,也没有什么法律规定她非受这种痛苦不可,这也是上面所说的对她的同一诅咒中的一部分。原文全文是这样的,“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
因此在洛克看来,女性对男性的服从既不是法律规定的结果,也不是由上帝意志和权威所确立的惯例。确切地说,女性的服从地位源自上帝对她们的惩罚。上帝对女性的惩罚使得她天生处于不利地位,这种不利地位被具象为了女性的生育能力。事实上,只有女性才能生育孩子,这种自然的劣势,导致了两性之间的自然不平等。尽管洛克认为性别不平等是偶然的,这是基于两性在生殖方面的自然差异,但他仍然由此确立了男性的优越性:夏娃作为诱惑的一方和共同犯规者,虽然被置于亚当之下,而亚当因为她受到较大的处罚,偶然地取得了比她优越的地位[1]。所以,洛克既没有质疑也没有批评所谓的不平等基础,而是支持了这样一种假设,即性别之间的自然差异导致妻子有义务服从丈夫的意愿和权威:这是她对其丈夫的责任。
可以看到,当这些政治家在为国家制度构架提供理论范式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将厌女情绪带入了政治领域。无论是中世纪的马基雅维利,还是近代的霍布斯、洛克,虽然他们对女性的态度根据自己的理论需要而表现得有所不同,但在实质上并无差异。这些政治理论家,都在试图打造一套男性寡头政治的体系,这种政治体系非常直接地服务于男性利益,并把女性排斥于权力结构之外。在他们的影响下,直到今天,国际政治的竞技场也常常只为男性开放,或者是为那些能够成功地扮演男性以及至少是不会动摇已有政治结构的极少数女性而开放。在一些国家,女性特征在政治话语的规训下,早已形成了不适合领导职位、不适合运用权力的刻板印象,她们仅仅可以在自己变得像“男性”的情况下,搏得政治生活的一线生机[2]。
但即便当女性发现政治权力的真相,呼吁两性的真正平等,她们也会被告知,“现在还不是时候”。国家积贫积弱,外敌虎视眈眈,她们必须要有耐心,必须等到民族主义实现的时候,才能解决男女关系问题[3]。“现在不行,以后再说”成了推诿逃避的绝佳借口,也成了保持现有权力结构的减震器。这种话语的生成土壤,可以在马基雅维利对“国家理性”的认识中找到——女性不公正、不平等的待遇需要为国家利益而让步。这从反面来说也意味着,即便不去考虑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新生民族共同体面临的问题也能得到解决。
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呼唤着新君主的到来,希冀实现祖国统一、摆脱外来干涉,现代的“马基雅维利们”也始终在追求一个最理想的国家,一个最统一的国家。但可悲的是,无论在哪个时代,统一的国家形成无不以女性为男性领导而集体牺牲自己欲望、自己权利为手段。
四、结语
在马基雅维利生活的时代,文艺复兴运动在欧洲如火如荼地开展。在这个被誉为“人的发现”的时代,法国作家克里斯蒂娜·德·皮桑(1365—1430)写下了代表女性文学的开篇之作《妇女城》,反对女性天然低劣的观点。但显然,作为中世纪欧洲为女性呐喊的一匹独狼,皮桑并未成功撼动父权制下的权力结构。这在几乎与她同时期的马基雅维利(1469—1527)的著述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通过对《曼陀罗》的文本研读,我们可以看到马基雅维利对女性的理解:女性既是天生低劣的第二性,也是对政治的潜在威胁。在《君主论》与《论李维》等作品中,这种理解被具象为有关公私领域的政治理论:女性属于私人家庭领域,男性属于公共政治领域。因此,马基雅维利将女性排挤在政治权力结构之外的做法就被赋予了正当性。
但研究马基雅维利的女性观,并不仅仅为了展现他个人对女性的态度,更在于以马基雅维利为切入点,洞见整个政治领域由来已久的厌女情绪。在政治思想史的长河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哪个时代都可以找到女性歧视的影子。霍布斯、洛克等自由主义政治家的著作,更是在很大程度上为当今国家提供了排挤女性的政治理论基础。在这些政治家的共同影响下,直到如今,在一些国家中,女性在政治领域仍未掌握话语权,她们要求获得政治权利的合理诉求也并未得到正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