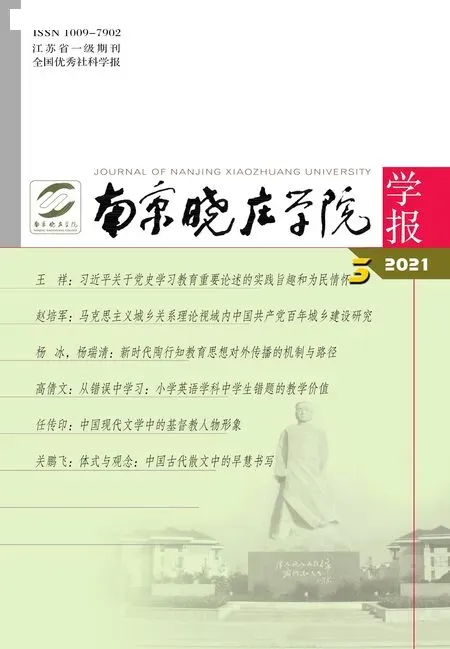一幅描摹六镇豪帅的工笔画①评介
——《5—6世纪北边六镇豪强酋帅社会地位演变研究》
2021-12-31张小稳
张小稳,戴 伟
(1.南京晓庄学院 旅游与社会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2.南京市金陵汇文学校,江苏 南京 210036)
北魏末年的六镇起义是北魏分裂灭亡的主要原因,也是北朝政治史的重要转折点。领导、参与六镇起义的主要当事人——六镇豪强酋帅因此作为一个政治群体在北朝后期的政治舞台上崛起,逐步发展成为北朝后期的政治主导力量。虽然研究六镇问题的学者和成果很多,但还未有学者对之进行系统性的研究。青年学者薛海波敏锐地抓住了这支政治力量,对之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纵向分六镇起义时期、加入尔朱荣军事集团、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四个历史时期,横向从政治、制度、经济、婚姻等四个方面,对六镇豪强酋帅的各个发展阶段进行细部勾勒,既波澜壮阔又细致入微,可谓是一副精心描摹六镇豪强酋帅的工笔画。《5—6世纪北边六镇豪强酋帅社会地位演变研究》2020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视野宏阔,视角独特,新见叠出,读之颇受启发。(1)笔者按,下文凡引及该书,不另外出注。
一
自1930年代陈寅恪提出“关陇集团”理论,对北周隋唐史劈波斩浪以来,地域集团的研究方法成为“研究中古政治史的重要利器”和“风景线”,“汉唐之间的各个时期,学人几乎都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地域集团加以考察”,(2)范兆飞:《中古地域集团学说的运用及流变——以关陇集团理论的影响为线索》,《厦门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似乎题无剩义。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简牍、墓志的大量发表,新出材料成为研究的热点,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史、医疗史、环境史也日益被学者们所青睐,政治史研究渐被冷落。薛海波先生追随自己的学术兴趣,甘于寂寞,在扑朔迷离的政治史中发现了六镇豪强酋帅这一政治群体,深耕十余年,运用地域集团的研究方法,将六镇豪强酋帅的兴衰史及其对北朝后期政治史的影响展现在读者眼前。
薛氏用“六镇豪强酋帅”(简称“六镇豪帅”)来指称主导六镇秩序的地方势力。《魏书》《北齐书》《北史》在不同的语境中多次使用“豪强”或“酋帅”之语,但没有“豪强酋帅”连称之词。薛氏从六镇地域社会的特点出发,将之连称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两点考虑:一是用“豪强”来涵盖六镇地方势力具有武力(强力)、一定政治地位、控制地方社会秩序的普遍特征;二是用“酋帅”来突出六镇地方势力中胡族酋长占相当比重、其群体社会组织为胡族部落或部落化、拥有部落组织和依附部众的地域特点。全书分四个阶段对之进行描述:
第一阶段:北魏后期六镇豪帅的形成与六镇暴动的原因。与以往研究不同,薛氏细致区分了六镇豪帅的两种类型:胡族部落豪帅和良家豪帅。胡族部落豪帅来自以高车为主的胡族部落,他们被北魏征服而被迫迁至六镇,处于六镇社会的底层,是六镇兵役和经济生活的承担者;良家豪帅来自北魏统治集团中家世不高的部落酋帅和地方豪强、陆续投附的胡族部落酋长、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乃至刘宋的降官豪帅等,他们大多具有部落酋长和军镇官吏的双重身份,是六镇拥有权势的豪帅群体。由于六镇地处边境,资源匮乏,良家豪帅利用手中的权力将有限的经济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从而形成了以胡族部落豪帅为代表的被征服者和以良家豪帅为代表的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北魏迁都洛阳之前,依靠来自中央的赏赐和补给尚能将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迁都洛阳之后,由于战略中心南移,朝廷官员的腐败,北魏财政处于崩溃边缘,对六镇的物资补给大为减少,六镇社会矛盾加深。正光四年(523),北方柔然大掠六镇,成为压在胡族部落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胡族部落生存无望,攻打镇城和良家豪帅,掀起六镇暴动。
第二阶段:六镇豪帅加入尔朱荣军事集团时期。暴动后,六镇沦为废墟,北魏朝廷将六镇豪帅及20万降户整体迁往河北。此时的河北,亦是“饥荒多年,户口流散”(3)魏收:《魏书》卷十五《元晖传》。,根本无法容纳如此庞大的外来人口就食、定居。为争夺有限的土地、粮食资源和生存环境,六镇豪帅、降户与河北当地政府、居民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原先站在政府一边镇压暴动的良家豪帅也因生存之需而不得不与反叛的胡族豪帅联合起来,先后发动了杜洛周、鲜于修礼、葛荣等大规模的河北暴动。由于组织松散、缺少军粮,暴动很快被北魏权臣尔朱荣镇压,六镇豪帅和降户亦被其收编,成为尔朱荣麾下的主要军事力量,在其南下洛阳、发动河阴之变、讨平各地反叛势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之同时,六镇豪帅也实现了政治上的华丽转身,从北魏政府的反叛者摇身一变而成为北魏军队的将领,借由尔朱荣军事集团的政治活动,参与到北魏政局中来,逐渐成为北朝后期的政治主导力量。由于尔朱荣的有意分化,以贺拔岳、宇文泰为首的武川豪帅与以高欢为首的怀朔豪帅之间有着较深的隔阂和矛盾。尔朱荣去世后,随尔朱天光西征入关的贺拔岳、宇文泰杀掉尔朱天光,占有关中之地;留守关东的高欢从尔朱兆手中取得了六镇降户的控制权;六镇豪帅分化为武川豪帅和怀朔豪帅两支政治力量。
第三阶段:东魏北齐时期。在关东,高欢以讨伐尔朱兆为契机,取得了河北地区的控制权,拥立孝武帝元修建立东魏政权,并在东魏政权中担任大丞相一职。在孝武帝及其心腹挑起的政治斗争中,高欢被迫南下驱逐孝武帝。高欢去世之后,其子高洋篡魏自立,建立北齐政权。东魏北齐政权中,怀朔豪帅摇身一变而成为勋贵集团,高欢及其子孙则成为政权的主导者。虽然高欢、高澄及北齐皇帝对怀朔勋贵有意打压,但因为怀朔勋贵一直是东魏北齐国家征讨作战、与西魏北周对峙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所以在东魏北齐政权中,怀朔勋贵地位仅次于高氏宗室,而远高于河北大族、胡汉士族和代地勋贵等其他政治势力。北齐后期,高湛、高纬父子利用恩倖打压甚至诛杀怀朔勋贵,怀朔勋贵逐渐凋零。怀朔勋贵的子弟,大多蜕化为既无军事才能、又无行政能力的军功寄生阶层,北周灭齐之后,便湮没无闻,退出政治舞台;仅有少数怀朔子弟如斛律孝卿、独孤永业等因立有军功而在北周获得官爵,融合在周隋政权之中。
第四阶段:西魏北周时期。占据关中的贺拔岳,不久被部将侯莫陈悦所杀,以赵贵为首的武川豪帅推举宇文泰为首领。恰逢高欢驱逐孝武帝,宇文泰奉迎孝武帝入关,取得了“匡辅魏室”的政治优势。拥有一定政治军事实力的孝武帝试图限制打压宇文泰,宇文泰为维护自己在关中的统治,鸩杀了孝武帝,拥立傀儡皇帝元宝炬,建立西魏政权。宇文泰去世后,其子宇文觉在宇文护的辅助之下代魏自立,建立北周政权。西魏北周政权中,宇文泰及其子孙是政权的主导者,其他的武川豪帅成为开国元勋和勋贵阶层。
宇文泰为融合武川豪帅、关陇土豪、关陇士族以及随孝武帝入关而来的河东胡汉士族、河南河东土豪等政治势力,推行了以周礼六军为主导的军制改革和以周礼六官为指导的官制改革。在大统初年的十二军制中,武川豪帅在12位将领中占8位,拥有绝对优势。543年在与东魏进行的邙山之役中,武川豪帅所率领的六镇士兵几乎全军覆没,武川豪帅失去了赖以搏杀战场的军事力量;随着宇文泰“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4)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二《文帝本纪下》。、赐胡姓、建立起隶属于自己的府兵体系,武川豪帅虽然在八柱国中占六位,但也仅仅是“地位极高、没有根基、军事实力受宇文泰指挥的高级将领而已。”六官体系中,武川勋贵虽位居六卿,但实权却掌握在宇文泰的心腹手中。
魏周禅代,在宇文护和周武帝的打压之下,武川勋贵在柱国层面的多数地位被北周宗室取代,勋贵元老先后去世或被杀。武川勋贵子弟大多数通过袭父爵的方式,“成为关陇集团内没有军政实力、具有较高政治地位的食封贵族”,只有杨忠、尉迟氏等少数武川勋贵子弟因与宇文氏的姻亲关系,掌握军政实权。北周皇帝与宗室之间的军权之争使得勋贵子弟杨坚趁机代周建隋。周隋之际,除李渊等少数武川勋贵家族凭借姻亲等社会关系维持家族地位外,“大多武川勋贵家族则融入乃至消失在隋唐关陇集团重整的大势之中”。
二
为工笔勾勒六镇豪帅的发展兴衰,薛海波先生走入历史的细部,钩沉索隐,于字里行间中寻求历史的信息,对北朝政治史上的诸多具体问题探微发覆,颇多创获,试举例如下。
其一,对六镇镇民的来源、构成、社会地位与六镇暴动原因、性质的分析和判断。自西向东设于北方边境线上的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是北魏用于拱卫京都平城、抵御柔然南侵的军事重镇;北魏末年的六镇暴动又是导致北魏分裂灭亡的重要原因,所以六镇一直是北朝后期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清代学者沈垚、顾祖禹、钱大昕等就已经开始关注六镇的具体设置和地理位置;20世纪三四十年代,周一良、严耕望先生继而对六镇的军镇体制、分布种类、组织体系等进行了细致考察。1930年代之后,学者们开始关注六镇镇民的来源与六镇暴动的原因等问题。
关于镇民的来源,影响较大的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日本学者滨口重国认为六镇镇民主要包括四类人:鲜卑贵族、汉族豪族、徙边罪犯、高车柔然等部族降民,其中前三类是镇兵的主要构成部分;(5)滨口重国:《正光四五年之交的后魏兵制》,原载于《东洋学报》第22辑第2号,1935年,后收于《秦汉隋唐史の研究》上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版,第120-125页。一种是陈寅恪先生认为六镇兵中主要者似为部落没有解散的高车人。(6)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272-274页。但这两种观点都没有对各类镇民前往六镇时的具体情况和社会地位进行详细考察,从而使得对六镇镇民的认识不够清晰。薛氏从六镇的军镇体制入手,详细考察了六镇镇民的来源、构成与社会地位。六镇的军镇体制是由六镇、连接六镇的长城和分布在长城沿线的30多座戍堡组成。为了充实、维护、守卫这一庞大的军事防御体系,北魏政府将征服的以高车为主的胡族部落迁往六镇,他们承担着六镇的兵役来源和经济供给,处于六镇社会的底层。六镇的军镇长官分为高层和中下层两个群体,镇将等高层将领由北魏宗室、鲜卑勋贵和高门士族担任,但他们只是在这里短期任官,并不常驻;常驻六镇的是担任长史、司马、军将、军主等官职的中下层官吏。他们来自北魏统治集团中家世不高的部落酋帅和地方豪强、北魏初建时的部落大人、陆续投附的胡族部落酋长、父祖没有官职的代地下层豪帅和十六国乃至刘宋的降官豪帅等。迁往六镇时,北魏政府赐予其“良家子”的身份,他们拥有部落酋长和军镇官吏的双重身份,是镇守六镇的主体力量,也是六镇最有权势的豪帅群体。
关于六镇暴动的原因与性质,有三种主要的观点,陈寅恪先生从胡汉冲突的角度加以观察,指出“六镇之叛,就基本性质来说,是对孝文帝汉化政策的一大反动”(7)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280-281页。;周一良先生观之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视角,提出不同观点,“北镇人之起兵并非对汉化的反动,乃是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如匈奴敕勒羌人等和被摒于清流以外的鲜卑和汉人的府户联合起来,对于统治者压迫者的反抗”(8)周一良:《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页。;1980年代,朱大渭先生试图调和这两种观点,但仍认为“六镇豪强酋帅同胡汉士族当权派之间的矛盾的形成和发展,主要由于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实行汉化,以及太和定族姓按照祖先官职编定族姓高卑,分别亲疏,凭以规定仕途清浊和受荫免疫的范围,实行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的结果。”(9)朱大渭:《代北豪强酋帅崛起述论》,《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43页。薛氏从军镇体制下经济生活的角度分析了六镇暴动的具体原因。他指出,六镇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农业为补充;因为资源有限,良家豪帅往往会侵夺胡族豪帅的土地,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六镇土地贫瘠、气候恶劣,因而无论畜牧业还是农业,都非常脆弱,经济上无法自给,大半要靠北魏政府补给。孝文帝迁都之前,六镇的补给主要是来自掠夺柔然的战利品、政府的赏赐和内地的粮食物资等;孝文帝迁都之后,政府的物资供给转向以洛阳和南方战场为主,六镇所能得到的物资补给骤减。良家豪帅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六镇有限的经济资源如官俸、赈济物资等据为己有,胡族部落不仅得不到这些经济资源,而且还要承担修筑城戍、抵御柔然的劳役和兵役负担,生活状况堪忧。正光四年(523),柔然阿那瑰率十万大军对六镇进行了毁灭性掠夺,彻底断绝了胡族部落的生路,镇将又不肯开仓赈济,以破六韩拔陵为首的胡族部落攻打镇城,掀起六镇暴动。因此,六镇暴动的性质是“由在六镇内部没有政治地位,面临生存危机的匈奴、高车部落豪帅所领导、发动的,求生存反抗军镇压迫的抗暴斗争。”
其二,对宇文泰渐夺武川勋贵兵权历史过程的再现。对于宇文泰继贺拔岳任武川军将领、迎立魏帝、创制府兵制之后,渐夺武川勋贵之兵权,陈寅恪先生曾有论述:“又宇文泰分其境内之兵,以属赵贵诸人,本当日事势有以致之,殊非本意也。故遇机会,必利用之,以渐收其他柱国之兵权,而扩大己身之实力,此又为情理之当然者。”并举一例,柱国李虎去世之后,最有资历接任的达奚武却让位于西魏宗室元子孝,陈氏分析说:“武之让柱国于子孝,非仅以谦德自鸣,殆窥见宇文泰之野心,欲并取李虎所领之一部军士,以隶属于己。元子孝……从容禁闼,无将兵之实,若以之继柱国之任,徒拥虚位,黑獭遂得增加一己之实力以制其余之五柱国矣。”(10)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3-144页。至于其他更多更具体的过程,则没有论及。薛氏将之放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中,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再现了这一历史过程,深化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根据薛氏的考察,宇文泰对军队的控制从其继任贺拔岳军将领后就开始了,主要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吸纳大量关陇土豪进入西魏军队并逐步将其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大统前期(535—541),西魏军队的主力来自宇文泰亲随、贺拔岳军、侯莫陈悦军、孝武帝西入关中所带禁卫军,宇文泰将之整编为十二军,十二军将领中武川勋贵占8人,明显处于核心地位。但是武川勋贵因为在关中没有乡里根基,很难解决兵员补充和军资供应问题,而且大统九年(543)的邙山之役,西魏军队被“俘斩六万余”,武川勋贵所率主力几乎丧失殆尽。为解决兵源问题,宇文泰从继任贺拔岳军首领那年(534)就开始征募关陇土豪从军;大统八年(542),又“仿周典,置六军”,将关陇土豪及所率乡里武装和拥有的经济资源,整编到由其指挥的中央军中;大统十二年(546)至十四年(548),宇文泰又通过“选当州首望”“置当州乡帅”等措施,增强其在军队和地方州郡的势力;废帝二年(553),宇文泰去大行台设中外府,将原先由关陇土豪乡帅征募统领的乡兵转变为国家军队,集军权于己身。而在此过程中,“赵贵等武川勋贵既没有掌握与之关系密切的军队,也没有把持到地方的军政权力”,在“军中的地位无法与其(宇文泰)相比。”
第二,通过建立府兵的军资供应系统来控制府兵。宇文泰自占据关陇起,就非常重视经济、财政、地方行政管理等制度的建设,先后推行了“二十四条制”“十二条制”“六条诏书”等旨在提高地方行政效率、解决赋役征发问题的措施,同时“广置屯田以供军费”等(11)《周书》卷三十五《薛善传》。,因此,“在大统十六年府兵形成之时,宇文泰和西魏国家已建立了均田、赋役、屯田、武器制造、粮食调拨等一系列制度,具体解决府兵大部分军资的能力。这无疑使府兵完全处于宇文泰和西魏国家的控制之下”。而赵贵等武川勋贵则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供养军队,亦不能通过经济供给来控制军队。
第三,通过复胡姓、赐胡姓在军队中建立起拟血缘的关系来控制府兵将士。大统十五年(549),“初诏诸代人太和中改姓者,并令复旧”(12)李延寿:《北史》卷五《西魏文帝纪》。;恭帝元年(554),“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13)《周书》卷二《文帝本纪下》。。薛氏对大统十五年至恭帝三年间,赐胡姓的将军进行了统计分析,认为在此期间被赐姓的42例中,有30例的军阶是开府仪同三司或仪同三司,占总数的71%,可见宇文泰赐姓主要是以府兵中开府和仪同级的中下层将领为主;有17例被赐姓宇文氏,占总数的40%,所属群体主要是拥有乡兵的关陇、河东等地土豪。因此,“宇文泰复姓、赐姓的意图,主要是通过建立拟血缘的同宗关系,将担任府兵中下级将领的关陇等地土豪变成宇文氏的宗族成员,使宇文氏势力延伸到府兵基层。”因此,建府兵、设八柱国之时,宇文泰实际上已经掌握了兵权,赵贵等武川勋贵只是位高而无实权的将领。宇文泰去世之后,其子宇文觉在宇文护的辅佐下,代魏建周,宇文护为了使辅政权不受干涉,诛杀赵贵、逼死独孤信、赐死侯莫陈崇,加之大统十七年去世的李虎,柱国元老纷纷凋零。宇文护辅政期间,共任命了48位柱国,其中武川勋贵及其子弟只有9人,因此,“在宇文护的打压和限制下,武川勋贵群体在府兵形成时柱国所占的多数地位,已被北周宗室所取代。”同时,薛氏还辅之以武川勋贵在六官体系中的地位、经济产业、和宇文泰家族的婚姻关系等方面的考察分析,使得武川勋贵在西魏北周的地位变化更加丰满,具体可感。
其三,对高欢迎立孝武帝和驱逐孝武帝的解析。以往的研究,对这两个问题措意不多,薛氏从当时的政治大势着眼,从史料的细致解析入手,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韩陵之战,高欢消灭了尔朱氏主力,进入洛阳,表面上成为北魏朝政的主导者,实际上却形成了“高欢军事集团与关中的贺拔岳等武川豪帅,洛阳朝廷的胡汉士族,原尔朱氏降将代地豪帅斛斯椿、樊子鹄等派别共享权力的政治格局。”为了争取各派政治势力的支持,高欢主动迫使自己所拥立的废帝元朗逊位。在立谁为新帝的问题上,各派莫衷一是。原先的节闵帝、孝文帝之子汝南王元悦都曾是考虑的对象,但最后为什么是孝武帝元修被高欢和各派选中、拥立为皇帝呢?薛氏从《北史·魏孝武帝本纪》中的一则史料分析入手:
又诸王皆逃匿,帝在田舍。先是,嵩山道士潘弥望见洛阳城西有天子气,候之乃帝也。于是造第密言之。居五旬而高欢使斛斯椿求帝。椿从帝所亲王思政见帝,帝变色曰:“非卖我耶?”椿遂以白欢。欢遣四百骑奉迎帝入毡帐,陈诚,泣下沾襟。让以寡德。欢再拜,帝亦拜。欢出,备服御,进汤沐。达夜严警。昧爽,文武执鞭以朝。使斛斯椿奉劝进表。椿入帷门,罄折延首而不敢前。帝令思政取表,曰:“视,便不得不称朕矣。”于是假废帝安定王诏策而禅位焉。
这则史料记述了孝武帝元修被发现、称帝的过程。薛氏分析:孝武帝本身拥有强烈的称帝企图,他和洛阳城中的王思政、斛斯椿有着密切的联系;斛斯椿作为原尔朱氏的降将怕高欢将之除掉,因此需要取得对高欢的政治优势,二者一拍即合,共同上演了一幕“洛阳城西有天子气”的政治双簧。因此,“孝武帝即位实际上是斛斯椿为代表的原尔朱氏集团成员、洛阳朝廷的胡汉士族等派系妄图消灭高欢军事集团的政治圈套。”
接着薛氏从任官的角度分析了以高欢为首的怀朔豪帅在权力格局中所处的地位,指出高欢虽然高居大丞相一职,但实际权力却掌握在以孝武帝为首的北魏宗室和以斛斯椿为首的原尔朱氏集团成员手中,怀朔豪帅则处于被排挤和压制的地位。继而孝武帝又采取诛杀、驱逐和离间的方式削弱高欢集团在朝中的势力。永熙三年(534)五月,孝武帝下诏让高欢处死怀朔豪帅孙腾,高欢无奈之下只好与之兵戎相见。因此,“高欢南下驱逐孝武帝,实际上是孝武帝、斛斯椿步步紧逼的结果,也是高欢维护自身集团利益的无奈之举。”
三
薛海波先生在勾勒六镇豪帅地位沉浮的过程中,对前人的研究观点颇多纠正,甚至对陈寅恪先生的“关陇集团”“胡汉冲突”等视角和结论提出疑问,显示了超越前人的学术勇气和胆略,但也存在着对前人观点理解不确、缺乏全面关照等问题,试举例如下。
其一,对陈寅恪认为赵贵等人以“等夷”取得柱国地位、府兵领兵权的疑问。在薛著第三章第二节中,薛氏先例举陈氏观点:“陈寅恪先生认为赵贵等人成为‘分统府兵’的柱国原因有二:一是宇文泰关陇诸军统帅是被赵贵等人所推举的;二是宇文泰在被推举为统帅之前与赵贵等人处于同等地位,即‘等夷’。”然后详细列举宇文泰被贺拔岳拥为统帅后地位的变化:
永熙三年(534)正月,孝武帝下诏确定宇文泰与贺拔岳军中诸将的统领关系:“贺拔岳既陨,士众未有所归,卿可为大都督,即相统领。”(14)《周书》卷一《文帝本纪上》。五月,宇文泰被授兼尚书仆射、关西大行台;七月,孝武帝入关,加授宇文泰大将军、雍州刺史,兼尚书令;八月,进位丞相;大统元年(535)正月,进督中外诸军事;大统三年六月,加录尚书事,总揽朝政;十月,授柱国大将军,位在丞相之上。薛氏据此得出,“从永熙三年至沙苑之战后,宇文泰完成了由与赵贵等武川勋贵军阶相当的将领、至关陇军统帅,到掌握西魏国家军政大权统治者的跃升。赵贵、李虎、侯莫陈崇、独孤信等武川勋贵在大统三年还仅是受宇文泰指挥的将领,其军阶在大统四年河桥之战后才达到开府级,在政治地位和身份上与宇文泰存在着巨大差距……因此,陈寅恪先生认为赵贵等人以‘等夷’取得柱国地位、府兵领兵权的观点似缺少依据。”
检视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的相关论述,陈氏论及西魏北周府兵之制的创设乃是杂糅鲜卑八部和周官六军之制的产物,对于宇文泰与赵贵等其他柱国之关系,陈氏如是论述:“宇文泰初起时,本非当日关陇诸军之主帅,实与其他柱国若赵贵辈处于同等地位,适以机会为赵贵等所推耳。”并引述《周书·赵贵传》“初贵与独孤信等皆与太祖等夷”、《周书·于谨传》“谨既太祖等夷”以证之。最后,笔锋一转,指出:“八柱国之设,虽为模仿鲜卑昔日八部之制,而宇文泰既思提高一己之地位,不与其柱国相等,又不欲元魏宗室实握兵权,故虽存八柱国之名,而以六柱国分统府兵,以比附于周官六军之制。此则杂糅鲜卑部落制与汉族周官制,以供其利用,读史者不可不知者也。”(15)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40-142页。陈氏认为宇文泰与赵贵等人最初都是贺拔岳军中的将领,处于同等地位,即“等夷”;但是宇文泰建府兵设八柱国时,已经全然不同,宇文泰为了“提高一己之地位,不与其柱国相等”,虽设八柱国之名,但只有六柱国掌兵,一则架空元魏宗室元欣,一则突出自己高于六柱国、统领六柱国的地位,与薛氏所论宇文泰地位高于其他武川豪帅的观点并无龃龉之处。薛氏以宇文泰后来之地位推翻武川豪帅当初之“等夷”地位,源于对陈氏观点理解不确。
其二,对陈寅恪府兵八柱国仿鲜卑八部制的疑问。薛氏从西魏军制变化现实需要的角度论述府兵八柱国之设,认为八柱国之设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西魏奖励军功的需要。邙山之役使武川勋贵所率六镇兵几乎消耗殆尽,宇文泰为了扩充军事实力和基础,广募关陇土豪,选置乡帅,并通过奖励军功的方式给其以上升通道,使其为己所用,从而建立起一支强大的、能征善战的军队。这些乡帅土豪最初以帅都督的身份进入府兵体系,随之而来的军功使其快速升至大都督、仪同三司,乃至开府仪同三司的高级军阶;这对原先府兵中拥有仪同三司或开府仪同三司军阶的高级将领造成了重大冲击,开府仪同三司已经不足以体现他们在军中的资历和政治地位,因此,“宇文泰必须将以前不轻易授人的柱国大将军,在短时期内有计划地授予一些将领,才能使因大批乡帅、中下层将领军阶晋升引发的军队等级秩序变动稳定下来。这也应是宇文泰将大统三年(537)及其之前就已经是开府仪同三司的独孤信、侯莫陈崇、李弼、李虎4人没有经过大将军,直接升为柱国大将军的原因之一。”二是团结各派政治势力的需要。薛氏认为“宇文泰授予柱国的对象,必须要是当时西魏军队中某一群体、派系的代表人物,且要具有相当的资历和地位。元欣是北魏宗室,且在朝中地位最高;于谨是宇文泰众多亲信中军功和资历最高的;独孤信是西返关中的贺拔胜军诸将中地位最高的领袖性人物;李弼是侯莫陈悦军的主要将领;李虎、赵贵是原贺拔岳军中资历最高的将领;且他们在朝中多任诸公职。“因而,从资历、军功、威望、所任行政官职及平衡各群体将领的政治势力等因素出发,于谨、李弼、赵贵、李虎、独孤信、侯莫陈崇实为‘功参佐命,望实俱重’,宇文泰必须将上述六人在大统十四年至十六年间提升为柱国。”
由此,薛氏得出如下结论:“可见,宇文泰建立八柱国的原因,不是如陈寅恪先生所论要单纯追求鲜卑八部旧制的形式,也没有要回报赵贵等人拥戴他为关陇军统帅的意图,更非赵贵等武川勋贵政治势力所迫使,而是出于稳定大批关陇土豪、乡帅军阶晋升所带来的西魏军队内部等级秩序的剧烈变化,协调西魏军队各群体、各将领的政治地位和利益、创建一支等级有序、推崇军功、资历的中央军的现实考虑。”薛氏所论,还原了八柱国之设的历史场景和现实需求,推进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但并不能以此来否定陈氏八柱国仿鲜卑八部制的观点,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设八柱国,而不是十柱国或其他数量的柱国。陈氏是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论述这一问题的,并且将之放入当时文化潮流变化和天下三分鼎立的大背景下进行论述:
北魏晚年六镇之乱,乃塞上鲜卑族对于魏孝文帝所代表拓跋氏历代汉化政策之一大反动……高欢、宇文泰俱承此反对汉化保存鲜卑文化之大潮流而兴起之枭杰也。宇文泰当日所凭借之人材地利远在高欢之下,若欲与高欢抗争,则惟有于随顺此鲜卑反动潮流大势之下,别采取一系统之汉族文化,以笼络其部下之汉族,而是种汉文化又须有以异于高氏之下洛阳邺都及萧氏治下建康江陵承袭之汉魏晋之二系统,此宇文泰所以使苏绰、卢辩之徒以周官之文比附其鲜卑部落旧制,资其野心利用之理由也。(16)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40页。
即府兵八柱国之设,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顺应六镇之乱反汉化的潮流,模仿鲜卑八部旧制,以笼络六镇将士;二、采汉族文化之传统,以笼络治下汉族人士;三、与高齐、萧梁所承汉魏晋文化相区别。因而八柱国是外仿鲜卑八部旧制,内衬周官六军之制,杂糅胡汉之制,以收关陇胡汉之心,而将其团结为一整体。陈氏所论文化上的认同与薛氏所论现实的政治军事需要并不矛盾,反而能够互相补充,使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不必以事情的一个面相去否定另一个面相。
概而言之,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关陇集团理论是观察西魏北周隋唐历史的一个宏观框架,六镇豪帅、特别是武川豪帅是关陇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薛海波先生对六镇豪帅的系统研究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同时也展示了将关陇集团研究和北朝后期政治史研究推向深入的一条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