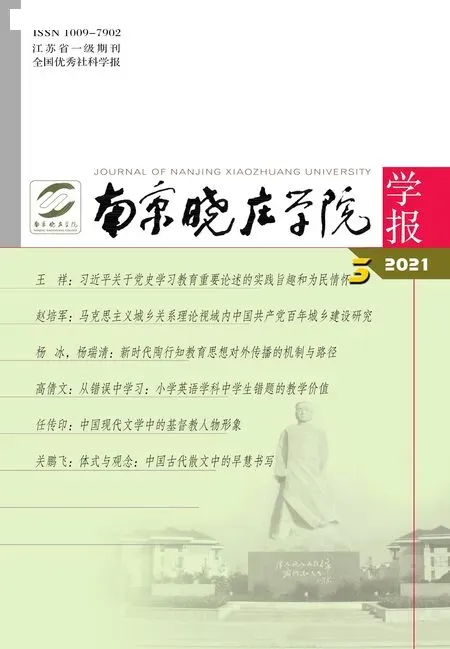《理想国》中的幽灵:弗洛伊德与柏拉图灵魂观念的比较
2021-12-31杨仁兵郭本禹
杨仁兵,郭本禹
(南京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理想国》是柏拉图最重要的一部哲学对话,同时也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巨著《论灵魂》之前最为系统、全面地考察灵魂的一部著作。而提及对灵魂(心灵)及其结构的探讨,首屈一指的当属弗洛伊德了。令人意外的是,在相隔两千余年的时空中,弗洛伊德对灵魂的洞见式的探索与柏拉图的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即便弗洛伊德早年通过翻译米勒(J.S.Mill)的文章间接接触过柏拉图的思想,但也只是零碎的了解(1)Price A W..Plato and Freud.In C.Gill(Ed.)The Person and the Human Mind: Issues in Ancient and Modern Philosophy.US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pp.258-267.;且前者对后者关于心灵的划分未曾表露过明确的态度。(2)Sunde C..Plato’s Super-Ego.Philosophical Practice. 2016, 11(1), pp.1711-1726.但正是因为近乎“潜意识”的内在联系,引起了不少研究者对二者的灵魂结构进行比较研究的兴趣。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弗洛伊德的“自我”与柏拉图《理想国》(第四卷)中的“理智”类似,(3)Price A W..Plato and Freud.In C.Gill(Ed.)The Person and the Human Mind: Issues in Ancient and Modern Philosophy.pp.258-267.(4)Ferrari G R F.The Three-Part Soul, In G.R.F.Ferrari(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lato’s Republic.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pp.165-200.而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自我”更像是“意气(精神)”,而“超我”对应后者的“理智(理性)”(5)Sunde C..Plato’s Super-Ego.Philosophical Practice.pp.1711-1726.(6)刘同辉:《柏拉图之人格心理思想研究及启示》,《心理科学》2007年第5期,第1259页。。所以二者提出的灵魂结构之间关系如何,需要进一步对《理想国》全篇进行考察,尤其要考虑个体灵魂的目的。而这种理论考察和比较,一方面,对于“认识自己”有着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当代心理科学发展就是对人本身认识的发展,而对人自身的认识,是涉及历史的、时间的。另一方面,亦提供了以心理学的视角来阅读《理想国》。此外,《理想国》是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与一行人的对话撰著而成,所以下文出现的“苏格拉底”若无特殊说明,仅指代“柏拉图的苏格拉底”。
众所周知,《理想国》中对灵魂及其结构的考察是以个体或城邦的幸福为目的的,为此柏拉图依次考察了正义、理想城邦和个人与城邦的类比,并且以不正义灵魂的不幸加以说明和谐正义的灵魂是幸福的。基于前人研究,本文试图对上述两者的灵魂构造进行重新考察,逻辑思路与《理想国》一致,即在人性论上,考察个人(灵魂)正义及其来源和建立理想城邦;在灵魂或心理结构上,重点考察灵魂的类比;最后探讨不正义灵魂的发展及其转向,以及二者对模仿艺术的主张。
一、个人与城邦的灵魂
“灵魂的作用是管理,而它的品德是正义”,苏格拉底说道,“正义的人是幸福的人,是生活的好的人。”(7)柏拉图著,顾寿观译:《理想国》,岳麓书社2018年版,第58-59页。关于为什么要正义或道德及其来源,苏格拉底对特拉需玛科的回答并没有让人信服。为此,格劳康和阿黛伊曼特再一次向苏格拉底提出挑战,他们认为人们都喜欢做不正义的事,无限满足自己的欲望,但却都不愿意成为他人的不正义行为的受害者。出于自保,人们相互之间签订契约,即凡是为法律或合约所规定的便是合法和正义的,也就是说选择正义(道德原则)是非出本愿的,(8)柏拉图著,顾寿观译:《理想国》,第74页。并不是因为正义本身是好的。正如弗洛伊德指出的,文明必须借助恢弘的道德价值观念以保护自身免于个体本能破坏倾向所带来的毁灭,(9)让-米歇尔·奎诺多著,陆泉枝译:《读懂弗洛伊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423页。它的第一要求就是公正,也就是说,保证一项法律一旦制定就不会为任何个人的利益而遭到破坏。(10)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载车文博编,《弗洛伊德文集》第十二卷,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页。弑父的儿子们设立禁忌以免重蹈覆辙,非本愿的强制使得建立起的伦理道德或文明强迫个体作出沉重牺牲、放弃自己本能的满足。可见,尽管弗洛伊德与格劳康和阿黛伊曼特关于“文明”的具体描述不同,但他们的思维方向是一致的,即文明社会产生之前,人类处于自然状态。人对人是狼,为了追求生存,便建立契约并由此形成了施行正义的国家或社会团体。
与之不同的是,苏格拉底认为没有一个人是自足的,人的需要是多样的,人们因此生活在一起,互相提供援助,进而形成一个所谓的“城邦”。(11)柏拉图著,顾寿观译:《理想国》,第230页。城邦的正义则是各阶层做与自己本性相适应的那一份工作,对于一个城邦而言,最大的恶是把它撕裂,而最大的善(正义)是把它团结在一起,使它变成“一”。(12)柏拉图著,顾寿观译:《理想国》,第73-74页。也正是关于国家或社会起源的不同观点,导致对于灵魂有着不同方向的关注,即柏拉图注重和谐和秩序,而弗洛伊德更关注的是压抑。为什么对于人的灵魂的探讨却指向城邦呢?柏拉图认为,“正义,有存在于一个单一的个人之中的,又也有存在于一个整体的城邦之中的。所以在这个更大规模的事物中,正义的规模也就更大,并且更易于辨认。”(13)柏拉图著,顾寿观译:《理想国》,第186页。在建立了理想(最好的)城邦以探索正义和不正义如何产生之后,“我们知道在一个好的城邦里会有正义的,而凡是在城邦里所发现的,我们就把它转移到个人中去……把这两者互相对比观察。”(14)柏拉图著,顾寿观译:《理想国》,第205页。虽然在“更易于辨认”的模式中,弗洛伊德认为那些异常的灵魂相较于正常更加容易辨认,但是两者的方法是一样的,即从更加“突显”和“更易于辨认”来考察灵魂的结构,而“单一的”和“正常的”个人灵魂是不容易辨认的。
建立理想城邦过程中涉及的对护卫者的教育和诗歌审查问题在此先不做讨论,而关于前述个人和城邦的类比的观点,弗洛伊德应是赞同的。他认为个体心理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可参照人类种系的产生、发展和变化,(15)车文博,郭本禹主编:《弗洛伊德主义新论》第一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325页。且他在其自传中也提及:“在调查宗教和道德起源时……我更加清楚的看到,那些人类历史事件——那些在人类本能、文化发展和原始积淀(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宗教)之间的相互作用,只不过是精神分析在个体身上所研究的自我、本我和超我之间的动力冲突的反映,是这一非常相同的过程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上的重复。”(16)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第236页。所以,城邦的正义是各阶层做本性相适应的工作,各部分和谐一致,那么个人的正义则是灵魂各部分的协调统一。在弗洛伊德看来,如果人格(灵魂)的三个部分处于和谐、协调、统一的状态,那么个体的精神活动就是健全的;反之,如果人格的三个部分处于背离、矛盾、冲突的状态,那么个体的精神活动就是失调的,甚至会导致神经症。(17)车文博,郭本禹主编:《弗洛伊德主义新论》第一卷,第345页。虽然苏格拉底仅涉及了不正义者的痛苦和不幸,而没有过多谈及神经症的问题,但是这两位思想家都关注精神健康,并都按照欲求的权力结构对精神健康进行了分析。(18)Ferrari G R F.The Three-Part Soul, In G.R.F.Ferrari(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lato’s Republic.pp.165-200.正如苏格拉底在把正义比作健康时指出,正义和健康都是一种自然的、和谐的秩序。“在任何灵魂里产生正义,也就是说,在灵魂里的各因素之间建立一个顺应它们本性的秩序,使之相互管辖和受管辖;而产生不正义,就是违逆它们的本性而使一个因素统治或受统治于另一个因素。”(19)柏拉图著,顾寿观译:《理想国》,第232页。神经症患者并没有与健康人不同的、独特的心理内容,至于冲突的斗争是以健康告终或以神经症告终,(20)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新论》,载车文博编,《弗洛伊德文集》第八卷,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04页。则是取决于相互冲突的力量的对比。弗洛伊德认为,“我们是通过研究心理失常来理解正常的心理生活”,(21)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新论》,第285页。而精神分析的目的是使“自我”重新控制失控的“灵魂”。
二、心理结构的比较
苏格拉底为解答为什么要正义和如何理解个人灵魂中的正义而建立了理想城邦,并基于城邦和个人的类推来考察灵魂。对应于城邦的统治者、护卫者和劳动者三个阶层,灵魂由理性、意气(精神)和欲望三部分组成。同样,弗洛伊德亦提出人格的三分结构模型,指出人格包括本我、自我和超我。那么,柏拉图对心灵或心理结构的划分,也就是他那个时代对灵魂结构的论述和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模型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灵魂中的欲望部分与弗洛伊德人格结构中的本我最为相象,柏拉图和弗洛伊德分别在《斐德罗篇》和《自我与本我》中提到驭马者的例子。他们都将劣性的、难以驾驭的马比作欲望或本我。在内容上,欲望是多样的,既包括饥、渴等生理欲望,也包括对金钱和性的欲望。然而,不管柏拉图的欲望涉及多少内容,它总是相对于理性而言,本质上是一种冲动,只是不断地要求满足。这如同弗洛伊德的本我,是没有组织、没有意志约束的各种盲目的冲动,表达个体有机生命的真实目的,且满足它的先天需要。(22)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新论》,第69页。尽管本我的大部分内容是属于潜意识的,即使是在梦中也通过伪装来获得欲望的满足,与《理想国》中在梦里直接满足的欲望或属于能够察觉的欲望不同,(23)Price A W..Plato and Freud.In C.Gill(Ed.)The Person and the Human Mind: Issues in Ancient and Modern Philosophy.pp.258-267.但它们都寻求快乐,遵循快乐原则。在划分欲望和理性时,与弗洛伊德一样,柏拉图在冲突中发现了最能解释灵魂结构的现象。根据对立原则,“同一的东西不会在同一个部位,就同一对象去承受正好相反的事件,”(24)柏拉图著,顾寿观译:《理想国》,第203页。即同一灵魂不会同时既要又不要做同一件事,如果灵魂中经受这样相反的冲动,那么灵魂必定存在不同的部分或力量把它往相反的反向拉。为了进一步说明欲望和理性是两个不同的部分,“是不是我们说,有这么一些人,正当在他们口渴的时候,他们却不愿意去喝饮”,那么“这就是在他们的灵魂里一方面存在着一种命令他们去,而在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一种阻止他们去喝饮的力量”。例如,当你口渴时,别人给你拿来一瓶毒药,此时你虽然有喝的欲望,但是理性却阻止你去喝,这也说明了灵魂中包含不同的力量或部分。
对此,有研究者反对上述欲望是独立于理性的部分,认为只有在灵魂内在冲突时才能构成一种非理性的欲望,并以理性为先导而成其所是;当灵魂未有冲突时,人按理性的方式行事,不存在非理性的欲求。(25)余友辉:《〈理想国〉的灵魂划分与理性主体》,《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第125页。按照这一观点,理性是作为先导先判断好坏,然后才允许个体的行为,而之所以存在非理性欲望,是因为理性的判定。那么,对于个体来说,理性是否可知呢?当理性悬置时又该如何解释行为?例如,“我饿了去吃饭”与“我馋了去吃饭”是不一样的。“我馋了”是基于某种兴趣或喜好,并不一定是饿了这种身体或生物因素引起的,它并没有生理的基础。所以,如果是因为臆想或信念的原因而不是身体器官的原因去吃,那么这种对快乐的渴望与判断好坏或应该的理性是不同的。又比如,小孩和野兽不具备理性,那么儿童的冲突和欲求是不是存在呢?即在道德价值和理性之前的欲望是如何归属的?梦中、酒醉和独处时的情不自禁的非理性行为,尤其是弗洛伊德关注的神经症患者的非健康行为等,又该作何解释?所以,并不能取消欲望存在的独立性,不管它是不是与理性相冲突。
正如一个又困又饿的人,困和饿只能说明存在两种欲望的冲突,理性在选择睡或吃时只是起到了筹算的作用。由此,对于理性,欲望除了自己选择对象,缺乏任何规范自身的手段,它只是追求满足。(26)N.帕帕斯著,朱清华译:《柏拉图与〈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页。非理性不是来自欲望的存在,因为很多非理性是生命所必需的,非理性(或非道德)的产生来自对属于理性的统治权的篡夺。这里并不是说欲望的存在分裂了个人的主体性,而是说它虽是灵魂的最大部分,但理性对于整个灵魂负有监护督导的责任,要统治和管理欲望的部分。像是灵魂的支流,我们专注于其中一个,那么相对于其他的就会变得薄弱。对理性(理智)和意气(精神)的培育使得灵魂专门流向一方。(27)柏拉图著,顾寿观译:《理想国》,第197-200页。
正如在《理想国》第四卷中所描述的理性(理智)忙于灵魂中欲望的“拖”“拉”“拽”,它首先被刻画成一个协商者或者是管理者的角色,而自身无须任何独特的目标。就此而言,有学者认为弗洛伊德的自我就像《理想国》(第四卷)中的理智,并不追求自己独立的利益。(28)Ferrari G R F.The Three-Part Soul, In G.R.F.Ferrari(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lato’s Republic.pp.165-200.“自我代表我们所谓的理性和常识的东西,它和含有情欲的本我形成鲜明的对照。”(29)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载 车文博 编,《弗洛伊德文集》第九卷,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67页。它的任务就是延迟或压抑本我欲望的满足,作为奴仆奔忙于三个主人(即本我、现实和超我)之间,就像城邦的护卫者,既要抵御来自外面的敌人,又要防止城邦内部的敌人,还要服从统治者的命令,而超我对应于柏拉图三分灵魂中的意气(精神)部分。(30)Price A W..Plato and Freud.In C.Gill(Ed.)The Person and the Human Mind: Issues in Ancient and Modern Philosophy.pp.258-267.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的意见,认为理性(理智)代表的是弗洛伊德模型中的超我,而意气(精神)则和自我相似。超我是整个灵魂(人格)的监控者,代表了人格的最高层次,其功能是压制本我的欲望,而这压制是通过自我来实现的。(31)刘同辉:《柏拉图之人格心理思想研究及启示》,第1259页。“当一个人违背他的理性(理智)原则,而被他的欲望所控制时,他狠狠地责备和数落自己……。这个人的意气(精神)就和他的理性站在一起而成为一致战斗的战友。”“就像狗受牧人的召唤一样,他受他自身之中的理性的召唤。”(32)柏拉图著,顾寿观译:《理想国》,第197-198页。即当苏格拉底谈论意气(精神)部分时,他把重点放在它是理性的助手,有勇气(没有胆怯的狮子)去遵循理性的指引,并以愤怒的反应来对抗任何不公。(33)Sunde C..Plato’s Super-Ego.pp.1711-1726.那么该如何理解意气、理性与超我、自我之间的关系呢?
首先,我们看一个例子,据说莱盎蒂奥看到在刑场附近躺着多具尸体,一时产生想去观看的欲望,但同时又感到一种厌恶,并且把身子背转了过去。许久,终于敌不过欲望的力量,他用手指撑大了眼睛说:“现在你看吧,你们这些邪魔且把这美景看个够吧!”(34)柏拉图著,顾寿观译:《理想国》,第197页。显然,莱盎蒂奥的行为与他想要维持的好形象不符,违背了自己想要成为的一种人,而说自己是恶魔,所以产生了意气的愤怒。除各种愤怒之外,意气部分在《理想国》中还表现为道德羞耻感、争取荣誉时的激越等。“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做错了,他越是一个高尚的人,他就越是不可能产生愤怒,相反,当他觉得自己是遭到了不正义的待遇,他的意气就沸腾起来,愤激怨怒。”(35)柏拉图著,顾寿观译:《理想国》,第447页。意气是一种自尊,而愤怒是个人感到自己的价值和重要性受到威胁的标志。(36)Cooper J M.Plato’s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2001, pp.91-100.所以,有着价值或者是“好”目标的意气更像是超我。弗洛伊德把超我分为良心和自我理想,良心是内化了的道德规范,是衡量自我为恶的尺度,指出我不该做什么;自我理想来源于重要他人,是自我为善的尺度,指出自我应该做什么及努力实现自己的完美状态。(37)车文博,郭本禹主编:《弗洛伊德主义新论》第一卷,第331页。如此,意气更像是灵魂中超我的部分,使个体有着维护自己价值的愿望和违背自己理想时的愤怒和惩罚,它像是一位严厉的父亲或者是暴君驱使着自我。
其次,为什么超我不能够认为是《理想国》中的理性呢?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超我作为俄狄浦斯的继承者,是内化了的父母及其权威他人的理想典范,它与本我有着更紧密的关系,弗洛伊德甚至把它看做是一位暴君,所以它更像是苏格拉底所说的一头情感激越的狮子——不具有反思性,有待于教育进行驯化。(38)柏拉图著,顾寿观译:《理想国》,第203页。那么理性又该如何理解呢?前文在讨论欲望时提及理性能够筹算、做计划和推论,对整个灵魂有监护督导的责任。然而,这样的理性像是休谟所说的,它自身没有动力,只是欲望的奴隶。欲望告诉我们要什么,确立目的;而理性告诉我们如何得到,决定获取目的的有效手段与途径。(39)余纪元:《〈理想国〉讲演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6页。与之相反的是,这更像是弗洛伊德式的“自我”灵魂(人格)与柏拉图提出具有正义灵魂的人不相符。后者是他自己的主人,他使他自己秩序井然,并从而自己成为自己的朋友……灵魂的三个部分和谐一致,就像一个(八度)音阶中的三个音符。(40)柏拉图著,顾寿观译:《理想国》,第472页。为了使自己成为主人,关注整个灵魂的正义和幸福,苏格拉底提出理想城邦应该由“哲学王”统治,而理性应该欲求智慧、真理。如此,哲学家渴望知识,荣誉式的人(意气)渴望杰出,寡头式、民主式和僭主式的人由欲望操纵。(41)Blössner N.The City-Soul Analogy.In G.R.F.Ferrari(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lato’s Republic.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345-385.基于此,理性的一部分是寻求管理和筹算、计划,另一部分则是追求或者是渴望知识、寻求完善的目标和幸福的生活。也正是亚里士多德后来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区分了的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42)余纪元:《〈理想国〉讲演录》,第96页。“我们将来最好的希望是能够逐渐建立起理性在人类心理生活中的主要地位,理性的本质是一种保证,保证它以后不会忘记给予人类情感、冲动以及给予所决定的东西以它们应有的地位。”(43)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新论》,第154页。而这样的人是低、中、高音和谐一致的人,它并不取消必要欲望的满足。
最后,《理想国》中灵魂的欲望和弗洛伊德的本我相当,意气(精神)更像是超我,而作为筹划和协调者的理性(实践理性)与自我相仿。如果自我理想是以真理和善为典范,目的是整个人的幸福和个体人生的目标,那么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灵魂中的理性(理论理性)了。但是,我们的灵魂充满千千万万的矛盾和冲突,弗洛伊德的灵魂就是一个忍受着持续的内在压抑的灵魂,与苏格拉底所叙述的那个绅士一样,他在剧场或孤独一人时作出很多令人羞赧的事,而这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需要努力压制的。较之被潜意识本能控制的灵魂,《理想国》中的灵魂更注重理性整合,正因如此,柏拉图在考察正义和不正义的城邦和个人时重视意气和理性的培养。同样,弗洛伊德也主张,作为一个精神分析者,我们使病人的自我上升到正常的水平,并把潜意识和压抑的内容转变成前意识资料,使其重归自我所有。(44)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新论》,第71页。
三、灵魂或心灵的转向与发展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给出了一个具有深远影响且引发历代学者思考的比喻——洞喻,(45)柏拉图著,顾寿观译:《理想国》,第325页。或者说是一个思想实验。从弗洛伊德的灵魂或人格的角度来予以解释的话,假设洞穴里的某一个人由于机缘巧合发现了平日意识不到的潜意识并觉得痛苦且挣扎时,就像见到什么光亮时那样刺眼。当这个人见识了之前从未发觉的潜意识之后,并准备告诉其他人时,如“弑父娶母”等,却遭到了强烈的反对,甚至引来杀身之祸。与之不同的是,柏拉图的洞喻是向上追求超越性的意识,即理性知识,而弗洛伊德的洞喻解释了个体经过精神分析这个“机缘”见识了深层的潜意识内容,而接受这些东西是现实或超我所不能接受的,尽管也错失了更正自我理想和增强自我的机会,但方向是向下探究潜在性的意识,即潜意识。
由上可知,洞穴之喻生动地说明了精神分析的重要性。即精神分析是使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个体发现“庐山”的“真面目”。更准确的说是精神分析治疗过程中的“教育”使得个体对灵魂或心灵结构的发现、认识或者是产生转向。柏拉图认为,“教育这件事,它并不是像有些人在宣讲中所说的那样,即如果在灵魂里缺少知识,他们就去把它灌注进去,就像是在盲瞎了的眼睛里,他们去把视觉灌注进去一样。”(46)柏拉图著,顾寿观译:《理想国》,第325页。教育促使灵魂发生转向,将整个的灵魂从关注黑暗的事物转身朝向光亮,直到灵魂能够坚定、持续地观看“是”。(47)柏拉图著,顾寿观译:《理想国》,第416页。弗洛伊德亦提及教育,也是“因为它极端重要,它充满着关于未来的希望,它很可能是所有分析活动中最重要的。”(48)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新论》,第131页。尤其是教育在儿童时期发展中的作用,如果教育失调,儿童便不能实现对本能的理想控制,妨碍儿童人格的正常发展,甚至引发神经症。(49)车文博,郭本禹主编:《弗洛伊德主义新论》第一卷,第463页。也就是说,在弗洛伊德看来,教育必须对儿童的冲动进行约束、禁止和压抑,让儿童学会能够恰当地控制自己的本能,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灵魂中理性和意气部分的培养,也即是在人格中对自我意识和超我的培养。
如果缺少相应的培养或教育,仅仅依靠压抑本能和欲望,那么个体就会如荣誉城邦堕落至僭主式城邦那样被欲望所控制。按照城邦和个人的类比,即城邦的类型特点和个人灵魂的类型特点相似,(50)Blössner N.The City-Soul Analogy.In G.R.F.Ferrari(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lato’s Republic.2007, pp.345-385.那么,一个人幼时以父亲为榜样,不追名逐利,不干涉他人事务,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听到了母亲对父亲的不断抱怨以及周围环境对这种生活方式的不尊重,他逐渐变得争强好胜,由于缺乏教育,他只是用强力抑制他的欲望,而不是通过理性的驯服。(51)余纪元:《〈理想国〉讲演录》,第96页。当他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他加入了一个多彩迷人的群体,并结识了各式各样的人。他开始偷偷地享受之前被禁止的欲望,最终变得不再感到羞耻,而是觉得自由、慷慨和勇敢,甚至是赞赏那些不必要的欲望是某种程度的文明。此时,这个年轻人不再约束任何的欲望,变得内心躁动不安。(52)Parry R D.The Unhappy Tyrant and the Craft of Inner Rule.In G.R.F.Ferrari(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lato’s Republic.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pp.386-413.这种“民主式”的人试图回答自己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但危险就在于过度追求自由,满足遇见的所有欲望,没有理性的管制,使得他完全被欲望奴役,而欲望中最强大的是“爱欲”,“爱欲”使他疯狂,驱使他做一切可耻的事情。(53)柏拉图著,顾寿观译:《理想国》,第476页。
由此,对儿童的教育不在于完全压抑欲望和本能,而是培育理智和意气,控制不必要的欲望。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二、三、十卷)中提到了对诗歌、戏剧和神话故事的审查和批判,他反对诗人,认为诗人败坏了人的心灵。“灵魂的那个被克制下来的部分,它渴求能够尽情地哭泣和呼号,并力求得到满足,现在,它也就正是那个在诗人们的影响之下得到满足并感到畅快,而灵魂中的最好的部分就放松了监守。”(54)柏拉图著,顾寿观译:《理想国》,第447页。观众在诗歌和戏剧中放纵自己的欲望,加强了心灵中低贱的部分,使之成为他们灵魂中的主宰,而不是理性和礼法,于是他们的理性思考陷入瘫痪,心灵受到了危害。(55)Moss J.What Is Imitative Poetry and Why Is It Bad? In G.R.F.Ferrari(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lato’s Republic.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415-443.同样,弗洛伊德也认为,艺术家充满愿望本能冲动的幻想在艺术活动中得以实现,而观众也毫不犹豫地释放那些被压抑的冲动,在各种辉煌的场面中发泄强力的情感。但与《理想国》中的批评态度不同的是,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家可以凭自己的升华作用,在创作中实现本能希望得到的快乐和满足,从而减轻现实带来的痛苦;而观众可以在艺术中获得安慰从而暂时抵消加在生活需求上的压抑。(56)车文博,郭本禹主编:《弗洛伊德主义新论》第一卷,第463页。
柏拉图和弗洛伊德都认为艺术是灵魂中欲望部分的表达,虽然弗洛伊德关注的是灵魂中被压抑的部分以及灵魂各部分之间的冲突,并使得本能正常化或升华,而柏拉图是取消“低贱的”欲望,以“最好的”灵魂部分代之。但总体上来说,他和柏拉图的目的相同,即用知识来弥补无知,使得理性或自我重新控制失控的精神生活。(57)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新论》,第306页。比如,在儿童性教育方面,弗洛伊德主张要像其他问题一样对待和探索,不要大惊小怪、有所隐瞒。(58)车文博,郭本禹主编:《弗洛伊德主义新论》第一卷,第465页。柏拉图认为“是”的知识带来的快乐是真实和长久的,而“色欲”等无序、易变的欲望所带来的快乐是虚假、短暂的,并主张提出斧正诗歌中关于欲望的夸张表达,且通过数学等知识的学习培养儿童的理性。
四、结语
根据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九卷)中塑造的灵魂的模型,可以说凶暴的多头怪兽与本我相仿,超我像代表意气(精神)的待驯化的狮子,那第三个属于人的形象则与自我对应代表实践理性,最后把三个部分联结成一个人的则是关注整体幸福和真理的自我理想。如此,作为主体的人不仅仅只是“理性的”或“本能的”,而是“多元的”。灵魂中不同比例的结合有着各自不同的幸福,但是正义的人,即和谐统一的人是一切幸福中最为完美的类型,也正是这个类似中庸的人是需要培育和学习才能达到的。另一方面,由于两者对人的理解不同,也正是关于国家和社会起源的观点不同,导致他们对灵魂有着不同方向的关注。首先,关于正义和健康,柏拉图向上注重和谐秩序和理性,提出了和谐一致的灵魂的标准,而弗洛伊德则向下关注潜意识欲望和压抑,主要通过研究心理失常来理解正常或健康的心理生活。由此,柏拉图对于理性和完美生活的关注,使得人在追求幸福或正义灵魂时,力不从心,望洋兴叹。而弗洛伊德式的理解则让人背负着深渊,自我在各种冲突中疲于奔命。其次,在灵魂结构的起源上,弗洛伊德做了更为细致的工作,但是相较于柏拉图对理性或自我在灵魂中的地位的重视,便要留待之后的精神分析学派来完成了。再次,在灵魂的转向方面,虽然二者都强调了教育对人及其之后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也都关注儿童理性和控制能力的培养,但是在教育方法上,《理想国》重视对诗歌的审查和数学及辩证思维的训练,消除灵魂中坏的部分。弗洛伊德则强调要学习和掌握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方法,(59)车文博,郭本禹主编:《弗洛伊德主义新论》第一卷,第466页。面对潜意识欲望,使之重归自我所有。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待艺术上,弗洛伊德关注的是艺术对灵魂压抑部分的相应释放,而柏拉图则是关注艺术——那些属于模仿性质的诗歌或戏剧,而不是那些描述勇气、节制和理性的朴素诗歌或戏剧——满足非理性部分之后会怎么样。
总之,关于心灵,不管是柏拉图还是弗洛伊德,都认为个人或者心灵是一个冲突、复杂、混乱的东西,是需要使之有条理和有秩序的。虽然理解从“混沌无序”到“有序”的问题,经验派和理性派各自有不同的思路,但是他们都认为有一个背后的、永恒的东西存在,有一个规律和不变的“一”在:柏拉图的理念、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科学心理学的普遍标准(规律)。完美的或者完善平和的心理结构是唯一的永恒“真理”吗?对“一”或“同”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回忆”,而“回忆”的真理意味着是沉溺于“过去”,它掩盖了相异的和个体的可能性,这方面柏拉图和弗洛伊德是相同的。而相异的和个体的、冲突的和斗争的,正是使得“创造”成为可能的条件。弗洛伊德作为研究“异常”心理的开创者,在这方面仍然带有时代的烙印,即潜意识最终只是扩展了理性的领域。另一方面,属于“历史的”“经典的”心理学思想在既“连续”又“断裂”的反复中绵延,或产生新的理解、新的创造。上述,不管是对人性论,还是对心理结构的考察和理解,弗洛伊德似乎重复了前人(柏拉图)的工作。但也正是所谓的“重复”工作的意义,使得“创造”成为一种可能,才能产生关于心理学的新观点,也即是暂时的倒退是为了长久的发展。历史不仅仅是后人对于前人的“回忆”,而是继续创造自己的历史。因为时间不可重复,那些表面“重复的”考察或思考,实际都有新的因素,更甚是发现新的解决问题的视角或理路,而这也正是当下应该做并继续做下去的事情,如带着心理学的视角去阅读或理解“经典”等。最后,前知大古,后能精明,即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科学(文化)的存在和进步是因为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60)Watt, D..The Dialogue between Psychoanalysis and Neuroscience: Alienation and Reparation.Neuropsychoanalysis. 2000, 2(2), pp.183-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