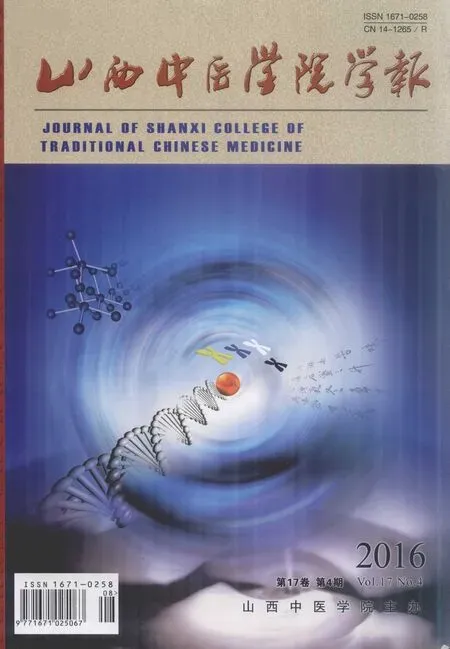薛雪痰饮证治探骊
2016-04-05翟志光
郑 齐,翟志光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北京100700)
薛雪痰饮证治探骊
郑 齐,翟志光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北京100700)
薛雪医案中对痰饮的诊治,在病机方面主要有两点:其一为阳虚不运、痰饮内停,其二为郁热炼液、液聚为痰。根据其病机确定治法,寒痰水饮重在温阳化饮,热郁痰凝重在清热化痰解郁。通过研究发现薛雪辨治痰饮有两点重要的特色:其一是倡温通阳气,其二是重三因制宜,反映了其诊治痰饮的学术思想。
薛雪;痰饮;学术思想
中医学痰饮证治自仲景肇始其端后,代有传承,及至丹溪立百病兼痰之论,彰显了从痰辨治杂病的学术特色之后,痰饮证治理论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清代崛起的温病学派,虽然其学术的着力点在于中医外感病的诊治,但他们从来也没忽视对内伤杂病诊疗规律的探索,甚至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薛雪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其名著《湿热论》阐发了湿热类温病的发生、发展、辨治的一般规律,不仅成为指导湿热类温病诊疗的圭臬,而且对于丰富内伤杂病中湿热证的治法也有很强的实践意义。而痰湿同源,细绎其医案会发现,他对痰饮证治的诊疗亦独具匠心、颇成体系,这也许是其开创中医湿热病诊疗理论的基石。薛氏的医案经后人辑录的主要有《三家医案合刻·薛案》与《扫叶庄医案》,与痰饮证治的相关内容散见于各篇,但在《扫叶庄医案》中专有“痰饮喘咳水气肿胀”一篇,有一定系统性,现将薛氏痰饮证治的思想,总结如下。
1 病机择要
痰饮是人体津液代谢障碍所形成的病理产物,一般以较稠浊的为痰,清稀的为饮。痰因生成原因之不同,有寒痰、热痰、湿痰、风痰、郁痰、顽痰之异;饮则依停聚部位之差别,有痰饮、悬饮、溢饮、支饮之分。历代医家对痰饮的论述侧重点不同,有的痰饮分论,有的详及一端,而薛氏是痰饮合论,并未对二者做很严格的区分,“痰饮皆阴浊”[1],病理性质相同,所以治疗上也有趋同性。但是二者在致病特点上仍有差异。对于哮症,薛氏多从饮论;而对于一般的喘嗽、颈部的结节,薛氏多从痰论。总起来看,病机不外寒热二端。
1.1 阳虚不运,痰饮内停
由于肺脾肾三脏阳气亏虚,不能蒸腾气化津液,致使津液停聚,变生痰饮,这是痰饮形成的主要病机。在薛氏《扫叶庄医案》痰饮病篇的治疗中,大部分医案皆属此类。薛氏尤其重视脾肾二脏对于本证形成的重要性,强调“脾阳鼓运水谷之气,何以化湿变痰,肾阳潜藏,斯水液无从上泛而为痰喘”[1],“仲景论饮非一,总以外饮治脾,内饮治肾为要法”[1],“再论痰饮,莫详仲景,由水液上泛者治肾,食减不运者治脾”[1]。可见,薛氏认为脾阳不运和肾失摄纳,是本证形成的重要机制。
1.2 郁热炼液,液聚为痰
由于各种原因导致阳热内郁,煎熬阴津,日久液炼为痰。具体而言,又有两端:其一为阴虚火旺、炼液为痰,主要见于其虚劳病的治疗中,薛氏谓其“真阴亏损,五液蒸痰”[1],多为气血阴阳本虚与痰浊痰湿标实互见;其二为气滞津凝、热郁痰结,主要见于颈部、咽部痰结病证的治疗中,薛氏谓其“气结在上,津不运行,蒸变浊痰,由无形渐变有形”[1]。热聚痰凝遂使气机郁滞,气机郁滞又会加重津停痰阻,二者互为因果、矛盾错杂。
2 治法钩玄
因机立法,方从法出。既然薛氏对痰饮病机的认识有寒热两端,其治法也不外从此两端入手。寒痰水饮重在温阳化饮,热郁痰凝重在清热化痰解郁。
2.1 温阳化饮
因阳虚不运、痰饮内停,视肺、脾、肾三脏病位之不同,分别施以温肺化饮、温脾化湿、温肾纳气诸法。温肺化饮法多仿仲景痰饮病篇治疗阳虚支饮的小青龙汤及其五加减法;温脾化湿主要针对痰湿中阻之证,芳香化湿、通阳化气、淡渗利水诸法合用,此乃薛氏最擅;温肾纳气主要针对肾阳亏虚、水泛为痰之证,摄纳浮阳、补肾助藏。
2.1.1 寒饮伏肺法仲景 寒饮伏肺之证,患者阳气素弱,痰湿内盛,加之感受外寒,郁闭肺气,肺气失宣,导致寒饮伏肺。薛氏多取法《金匮要略》痰饮病篇治疗外寒内饮的小青龙汤及其五加减法,灵活化裁。
寒天痰嗽,乃阳气微弱,不能护卫,风冷来侵而起,久则饮泛上逆,入暮为剧。饮属阴浊耳,仍发散清肺,仿仲景饮门议治(桂枝、五味、杏仁、茯苓、炙草、干姜[1])。
本案病机叙述较为清楚,显系外寒引动内饮之证,饮为阴邪,午后阳气衰减,阳不化饮,诸证加剧。薛氏亦明言“仿仲景饮门议治”。从方药来看,本方是五加减小青龙汤的第一方——桂苓五味甘草汤加干姜、杏仁。桂苓五味甘草汤原是仲景为服用小青龙汤后发生冲气变证而设,薛氏并未拘泥于此,而将其化裁应用于外寒内饮之治。该方较小青龙汤,少了麻黄、半夏、细辛之温燥,同时亦去除了白芍之阴柔,散与收的力量都较为缓和,且多了茯苓淡渗水湿。在此基础上,薛氏加干姜温阳散寒,加杏仁宣降肺气(这两味药也是五加减小青龙汤的其他加减法),共奏外散风寒、内化寒饮之功。如果“脊骨中冷,深夜痰升欲坐”,属“少阴寒饮上泛”,则桂苓五味甘草汤加淡干姜、北细辛,用药重在入少阴,温化寒饮。如咳喘较重,不能安枕,薛氏则在桂苓五味甘草汤加干姜、白芍,这就基本上是小青龙汤去麻、辛,小青龙汤去麻、辛也是薛氏在寒饮伏肺一证常用的处方,他很注重方剂中发散与收敛之间的配伍,白芍与桂枝一收一散、与干姜一阴一阳,使全方刚柔相济,燥湿得宜。总之,薛氏治疗本证,取法仲景,而又师古不泥,值得深究。
2.1.2 痰湿中阻重分消 痰湿中阻之证,多以平素脾胃不健,水湿内停,湿聚日久为痰,痰湿日久亦可化热,遂为湿热郁遏中焦,每于夏秋,外湿引动内湿,诸症加重。薛氏于此证调理,多从三焦入手,宣湿、化湿、燥湿、渗湿、胜湿,诸法合用,分消湿滞。
脉濡,中宫阳不主运,湿浊聚痰,不饥不渴不食(桂枝木、草果、广皮、茯苓、厚朴、炒谷芽[1])。
本案是较为典型的痰湿中阻之证,在薛氏医案中极为常见。其以桂枝通阳化湿,以草果、厚朴芳香化湿,以陈皮苦温燥湿,以茯苓淡渗水湿,诸法合用,阳气得化得展,痰湿得以分消走泄。痰湿中阻之证,极易化热,遂为湿热中阻,“湿多热少,则蒙上流下”“湿热俱多,则下闭上壅,三焦俱困矣”,而三焦气化、水行又皆以中焦脾胃为枢纽,“夏季之湿郁,必伤太阴脾,湿甚生热,热必窒于阳明胃脉,全以宣通气分,使气通湿走热清”[1]。治疗当抓住要害,以调理气机,恢复三焦正常气化功能为主要宗旨。于此类病证,薛氏最喜用厚朴、广皮、苓皮、茵陈相伍。茵陈、茯苓皮共同点是利湿退热而不伤阳气,厚朴和陈皮均偏温燥,似与湿热病证不合,但湿邪终属阴邪,得温始化,尽管此时与热邪纠结一处,亦应在清热的同时,辅以温燥之品,相伍而行。否则一味清热利湿,阳气受损,湿邪终不得化。后世吴鞠通“徒清热则湿不退、徒祛湿则热愈炽”之语,可谓深得薛氏三昧。
2.1.3 阳虚水泛培肾气 肾阳亏虚、水泛为痰之证多见于久病咳喘,肺虚及肾,耗伤肾气,摄纳无权,导致气不归元,虚喘痰嗽。治疗的重点在于补肾助藏,由于肾阴肾阳互根互用,所以薛氏注重滋补阴精以摄纳阳气,如七味都气丸、薛氏加减八味丸等是其常用之方,已寓阴中求阳之义。即便温补肾阳,也倡柔剂养阳,避免用过于刚燥的温阳药耗伤阴血。
2.2 清热化痰解郁
本法主治病证多因郁热炼液,液聚为痰。如属阴虚火旺、炼液为痰,则重在补益下焦、填精益髓;如属气滞津凝、热郁痰结,则以行气解郁、咸寒软坚为法。
2.2.1 虚火炼痰 虚火炼痰多见于薛氏医案虚劳篇中,此时真阴亏损为本,痰浊内盛为标,重在补益下焦、填精益髓以治其本。
奔走动阳失血,继而咳嗽吐痰,由真阴亏损,五液蒸痰。趁此胃口颇旺,以静药填阴摄阳(熟地、阿胶、女贞子、天冬、米仁、刮白龟板、咸秋石、知母、霍山石斛[1])。
本案为虚劳患者,因劳倦耗气,气不摄血,失血后则阴虚更著,虚火上炎,炼液生痰。方中以熟地、阿胶、石斛滋阴养血,女贞子、天冬、龟板、知母皆为滋阴降火而设。本证的治疗,难在如何处理滋阴与化痰之间的矛盾,薛氏也认识到“滋阴血药多腻,为痰树帜矣”[1],“从来酒客喜食爽口之物,不用滞腻甜食……滋阴如地黄、萸肉,皆与体质不相投矣”[1]。本案中值得注意的是“趁此胃口颇旺”,这是薛氏治疗本证的尺度,“胃旺能纳谷,当专理下焦,不必以痰为虑”[1]。另外,方中亦有苡仁,意在渗湿泄热,一来祛湿以绝生痰之源,二来防止滋阴药助湿酿痰。无论是虚火炼痰,还是痰热伤阴,都会造成湿热和阴虚两类具有矛盾性的病机共存一处。前文已述及湿热并存就具有一定的矛盾性,此时又添阴虚与痰湿一对具有矛盾性的病机,处理起来更加棘手。此类证候治疗关键在于清热、燥湿、养阴三种治法的比例与各自切入时机的把握,另外对具有这三类功效的药物也需要认真选择。清热多以甘寒养阴之品,或苦寒配以甘寒,一般少用淡渗水湿,多以燥湿之品应对湿邪;养阴尽量使用味薄不腻之品,避免助湿。
2.2.2 气郁痰凝 气郁痰凝一证,多因情志不畅、肝气郁结,气郁津停,津聚为痰,多在肝经循行部位如颈部、咽部、乳房,结成痰核。治疗上一面要行气解郁、条达肝气,一面要咸寒软坚、化痰散结。
肝虚痰病,结在项下(海石、香附、连翘、夏枯草、土贝母、天花粉、青黛、金银花[1])。
本案记述较简,但为典型的气郁痰凝、颈部痰结的病证,当今临床亦十分常见。薛氏以香附疏肝解郁,以海石咸寒软坚,以连翘、夏枯草、土贝母、天花粉化痰散结消肿,以青黛、金银花清泄肝热,全方组方严谨,配伍全面,且选药精当,颇有实用价值。
3 特色撷英
除了以上提到的两大类治法外,薛氏治痰饮还有两点重要的特色:其一是倡温通阳气,其二是重三因制宜。
仲景明训“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薛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温通阳气、化湿行气之法,这也是他基于对湿证诊疗经验基础上的理论总结,“阳微湿聚成利,必温通其阳,斯湿可走”[1]。该法与温阳法有所不同,主要针对湿遏气机、清阳被郁的病机,是对“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这一原则的实践。小便通利则说明阳气得通,升降有序,气化有权。薛氏也将这一法度应用于痰湿证的治疗,或是单独应用,或是将桂枝、薤白等通阳散结、走而不守之品伍于温阳燠湿之剂之中,使温中有通,寓通于温。
三因制宜是《内经》法天则地、从容人事思想在养生与治疗理论方面的体现。即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是指治疗疾病要根据季节、地域以及人体的体质、性别、年龄等不同而制定适宜的治疗方法。历代的著名医家皆将其视为治法的大则,薛氏也不例外。在痰饮病辨治过程中,他很注意这方面的因素。比如他治疗一个自幼年间罹患哮喘的患者,认为是饮邪深伏于络脉之中,此时再用一般的发散、温补之法都无效,所以主张“宜夏月阴气在内时候,艾灸肺俞等穴,更安静护养百日。一交秋分,暖护背部,勿得懈弛”[1]。在夏月阳气发散之时,用艾灸穴位,以期温通经气、化饮祛湿。而到了秋分,阴阳匀平、阴气始长、阳气始衰之时,注意调护,防寒保暖。于此,其因时制宜的思想可见一斑。
[1]薛雪著.扫叶庄医案[M]∥裘吉生辑.珍本医书集成(第四册).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669,670,658,675,670,670,686,658,661,657,652,687,665,670.
(编辑:翟春涛)
Research on the treatment of phlegm syndrome by Xue Xue
Zheng Qi,Zhai Zhiguang
(Institute of Basic Theory,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ine Science,Beijing 100700)
There are two points in his pathogenesis academic thought o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hought of phlegm from Xue Xue′s medical records.Phlegm fluid retented because Yangqi was not working and pathogenic heat stew Yin Fluid so phlegm formed.Treatment principle aimed at pathogenesis,reflected two distinguishing features,one was warmming and passing Yangqi,the other was three suiting measures to different conditions.
Xue Xue;phlegm syndrome;academic thought
R221
A
1671-0258(2016)04-0004-03
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YZ-1415);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YZ-1423)
郑齐,E-mail:826279078@qq.com
翟志光,副研究员,E-mail:zzgvvv@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