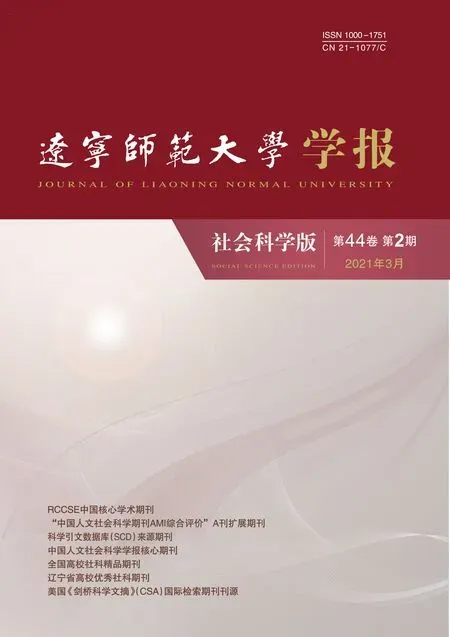避世、抗争与重建
——象征主义视角下叶芝诗歌爱国主义的主题变奏
2021-12-29谷野平
谷野平, 刘 颖
(辽宁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本文从象征主义视角出发,对叶芝的青年时代和中老年时代的诗篇做鉴赏和分析,认为青年时代的叶芝将故乡斯莱戈人民欢快美好的田园生活等感性经验和源远流长的爱尔兰神话与传说相结合,表现出爱尔兰人民通过回归古老文化以寻求避世和增强民族的自信心;中年的叶芝将理性思考融入现实因素,摒弃暴力革命,推崇文化救国;老年的叶芝秉承自己的历史循环认知,认为爱尔兰文化循环往复,每个阶段都是上一个阶段的升华,以此鼓励爱尔兰人民摆脱英国殖民文化的压迫,走向伟大的民族复兴。
一、叶芝与象征主义
爱尔兰文艺复兴旗手威廉·巴特勒·叶芝1865年生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1939年卒于法国曼顿,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文学艺术瑰宝,在世界文坛赢得了高度赞誉。192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对这位文学巨匠的褒奖。叶芝诗歌大量使用象征主义手法诠释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怀,对爱尔兰民族和文化独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叶芝1900年发表的《诗歌的象征主义》深度阐释了他对于象征的理解:“一种感情在找到它的表现形式——颜色、声音、形状或某种兼而有之之物——之前,是并不存在的,或者说,它是不可感知的,也是没有生气的。”[1]象征有时将感情融入于形式,有时将具体事物附着上或具体或隐秘的感情。因此,诗歌有了象征便被赋予了更多的魔力,也更能激发读者的联想和深度思考。“象征主义”是19世纪80年代以来在欧美国家出现的一种艺术思潮、流派与方法。文学上的象征主义,主要指由波德莱尔、兰波、魏尔伦等人所开创发展出来的文学流派。它在创作方法上尤其强调作家内心的主观感受,与象征不同,象征主义艺术手法不仅强调作家的直觉和主观性,还常常运用意象来暗示、表达那种远离现实的永恒世界。叶芝是否是象征主义诗人一直在学界存有种种争议。但是从事实出发,尤其从叶芝爱国主义诗歌本身出发,我们认为象征主义恰恰是其重要的艺术特质所在。考察叶芝爱国主义诗歌作品中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有助于发现叶芝创作主题的生成与流变。
在叶芝心中,爱尔兰是独特而耀眼的,他的一生都在为爱尔兰的独立与自由呐喊和奔走。在这片神奇而充满诗意的热土上,叶芝正是以其象征主义的手法在不同的人生时期建构了心中的诗意世界。青年的叶芝借爱尔兰神话传说,开启了避世之旅,走回故乡同精灵生活在一起以寻求短暂的庇护,找到心灵得以安慰的场所;中年的叶芝则主张文化救国,力求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举起民族文化复兴的大旗,与英国殖民者进行殊死抗争;老年的叶芝对历史展开反思,带领爱尔兰民族走向文化循环的灿烂起点,向文化殿堂拜占庭进发。叶芝一生的文学创作和整个民族的独立、解放紧密相连,展现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担当,力求带领爱尔兰人重拾历史记忆和文化身份,以找到自己的心灵归宿。总体而言,叶芝的作品表现出他炙热的爱国主义主题。
二、青年时代:回归古老文化来寻求避世
叶芝青年时代的诗歌特点是回归古老的文化之源以寻求暂时的避世。那时爱尔兰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但古老的爱尔兰民族在高压的状态下反而强化了民族的主体意识,升华了自我价值和群体认同。逃避英国殖民文化的压迫是青年时代叶芝诗歌的主题。叶芝母亲的故乡斯莱戈是爱尔兰的文化之源,也是他诗歌创作灵感的源泉,更是诗人和读者获取短暂安慰的庇护之所。这也间接说明了爱尔兰文化可以使人们获得精神上的安顿。斯莱戈有着绮丽的风景、蔚蓝的天空、碧绿的湖水与坚硬的峭壁。斯莱戈西侧宽阔而幽静,人们过着园牧歌般的生活,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叶芝将诗歌中美好的神话传说和妙趣横生的生活细节相结合,吟咏爱尔兰人火热的生活,展示出爱尔兰文化古老的意蕴,同时也揭示了隐秘的避世情结。《十字路》(1889)诗集中一首名为《拐走的孩子》充满了自然和神话传说的元素:“斯利什森林的陡峭/岩岸浸泡入湖水处,/有一个蓊郁的小岛,/那里有振翅的白鹭/把瞌睡的水鼠惊扰;/在那里我们已藏好/满盛着浆果的魔桶,/偷来的樱桃红通通。人类的孩子啊,走!/跟一个精灵,手拉手,/到那水上和荒野里,/因为人世溢满你不懂的哭泣。”[2]90诗歌中每一个自然元素都附着着神奇,也融入了诗人对故乡的深切眷恋。这是一片诗人挚爱的土地,它纯净无瑕,没有机器的轰鸣,没有恼人的污染,没有资本的剥削和压榨,也没有日益膨胀的物欲与贪婪。幽静深邃的斯利什森林、静静地躺在岩岸臂弯里的湖水、神秘葱郁的临湖小岛、湖中嬉戏的白鹭、水鼠甜蜜的梦乡等,都呈现出可爱的颜色、优美的声音、美好的形状,……所有这一切都令人向往和爱恋,就连红红的樱桃都被注入了魔力。
叶芝诗歌中神话元素的介入,更展示出爱尔兰文化的源远流长。那些与精灵牵手的孩童其稚嫩、可爱的样子能够使人们感受到爱尔兰民族与古老神话的密切关联。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透过柔和的月光可以看到与神灵一起载歌载舞、无忧无虑的爱尔兰人民。他们和精灵共处,与精灵共舞,并得到神灵的庇护。精灵带着孩童从“斯利什森林”走到“罗西斯角”游玩。皎洁的月光静静地倾泻在灰暗的沙滩上,仿佛蒙上一层薄薄的面纱。海浪袭来,沙滩渐渐显现出清晰的模样。趁着月色,人们在沙滩上欣然起舞,挽起手臂,踩着步点,畅快地释放自我。尽管月光渐渐消退,他们仍然兴致不减,旋转跳跃,追逐嬉戏。他们在这个浪漫的夜晚,在泛起泡沫和浪花的海边跳起美妙的精灵之舞。然而,神秘的“飞溅的水泡”稍纵即逝,人们的欢乐也伴随着内心隐秘的苦痛和烦忧而转瞬即逝。为了逃离现实的苦难,精灵带着“孩童”走进这伊甸园,去享受人间本该有的幸福。这种幸福就像泡沫,神秘而虚幻,虽然难以留住,却可以暂时享受。诗歌中充满神秘色彩的“水泡”与“精灵”象征着转瞬即逝的美好。梦回斯莱戈,叔且聊以自慰。湖光山色可治愈人生的苦痛。在湖光山色间与神灵共舞的人们可纵情高歌,暂时忘却英国的殖民统治和压迫所带来的苦难。叶芝接下来用细腻的笔触呈现给读者宛若仙境的快乐生活场景。人们闲来捕鱼的场景在诗人笔下妙趣横生:蜿蜒静谧的泉水蜿蜒流淌,杂草疯狂生长,水中泛着波光,茂密的芦苇叶上挂满了晶莹的露珠,水下藏匿着肥硕的鳟鱼。人们悄悄探出身子,寻觅鱼儿的踪迹,他们轻声呢喃,扰乱鱼儿的美梦。这是诗人梦中的伊甸园,这里的生活恬静而生动,无忧无虑,无拘无束。人们偶尔和大自然捉个迷藏,偶尔和鱼儿们开个玩笑。在这个最原始最纯净的自然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没有城市生活的喧嚣与浮华,有的是人们返璞归真的心灵净化。在这里,人们成就了真实的自我,实现了美好的田园诗意生活。在本诗中诗人模仿了爱尔兰文化中精灵偷走孩子的神话传说:森林里的精灵充满魔力,他诱惑了人间的孩子,带着孩子远离人间。孩子和朝夕相处的动物们说再见,和平静温馨的生活说再见,跟随精灵去往心中快乐的天堂:“人类的孩子啊,走!/跟一个精灵,手拉手,/到那水上和荒野里 /因为人世溢满,你不懂得哭泣。”[2]90-92“哭泣”象征着爱尔兰人的生活艰辛以及个人内心的痛苦。
叶芝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伟大的诗人不曾借用民间传说来进行创作[3]。民俗学者都对诗歌中神话的起源产生怀疑,可是当地民众则说精灵是来到人间的天使。爱尔兰古文化研究者则认为有“爱尔兰异教徒信仰的神灵”[4]80的存在。带领读者走进文化传说来实现人们的文化自信在诗歌创作中是常见的,但是带领读者走进文化世界来避世却不常见。诗歌中“被偷走的孩子”象征着避世的爱尔兰人民。他们就像被神灵偷走而进入深山的孩子,幸运地走进了没有血污的童话世界,并开启了一段幸福的生活。但是他们刚刚幸福不久,就像“透明的泡沫,最后注定要消失”[4]80。神话世界虽然美丽,却不能替代现实的苦难。“透明的泡沫”转瞬即逝便说明了这一点。暂时的逃避虽然幸福,但是现实的苦难依然存留,“对痛苦视而不见产生的幸福最终将破灭”[5]。诗人借此表达了他对历经磨难民族的忧思和重拾希望的决心,毕竟古老的民族尽管受到英格兰殖民文化的压迫,但依然可以通过重建悠久灿烂的文化来走出困境。
三、中老年时代:波澜壮阔的民族抗争与文化重建
叶芝中年的诗歌更多地加进了对于现实的理性思考,诗歌主题从而转向了文化抗争,这便与青年时期感性的避世主题有所不同。20世纪20年代,爱尔兰历经了动荡的时局:崛起的新芬党、方兴未艾的民族解放运动、英爱战争等都充斥血腥和暴力。他认为“面对爱尔兰人的种种艰难处境”[6],“一个挚爱祖国的人必然要投入民族独立的斗争中”[7],尽管他不赞成暴力革命,但他仍然对起义者由衷地抱以同情和钦佩。这个时期叶芝的抗争意在为爱尔兰实现文艺复兴与文化重建。
这一时期的诗歌充分表达了诗人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怀。《一九一六年复活节》(1916)表达出叶芝对革命先烈的敬佩。诗歌使用了大量的象征主义手法,比如他用“马蹄溅水”“松鸡潜水”“天上乌云翻滚”等意象来象征战斗的激情,从而与“灰色的大楼”所象征的爱尔兰历史和文化悠久相照应;把社会各种职业的人员积极投身革命的自我牺牲精神和爱尔兰生命的绿色相照应,认为英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以生命为代价,出其不意地侧身其间”[8],他们心如磐石,视死如归。“牺牲已太长太久/足以把心灵变成顽石。”[2]392叶芝将没有生命的“顽石”与结尾代表着爱尔兰的“绿色”相呼应,强调爱尔兰民族文化顽强的生命力,也象征着其“新生”[9]。表面上诗歌讴歌了暴力革命者的英勇无畏,实则强调爱尔兰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决不能屈尊于英格兰的殖民统治,必将再一次迎来新生。暴力革命虽然值得敬佩,却也像马蹄溅水之后的水面瞬间平静那样,都无济于事。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应是文化层面,文化的独立才是革命者的首选。
老年的叶芝在诗歌创作上尤为关注爱尔兰文化的重生问题,对民族独立的理解日臻成熟,内容也涉猎广泛。他作为爱尔兰文艺复兴的旗手,认为古老的爱尔兰文化正处于螺旋上升的历史节点,正在浴火重生。尽管身体渐渐不堪,他生命中的缪斯却年轻起来。叶芝在诗歌《在布尔本山下》这样写道:“爱尔兰诗人,把艺业学好,/歌唱一切优美的创造;/……把你们的心思抛向往昔,/我们在未来岁月里可能/仍是不可征服的爱尔人。”[2]648-649在他看来,文艺是立国之本,可以歌唱民族和国家,可以和殖民历史说再见,可以重建自己民族的文化,可以颠覆殖民者文化,从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926年诗人创作出脍炙人口的名篇《驶向拜占庭》。当时尽管一战的热浪并没有席卷到爱尔兰本土,然而它却变革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战后的年代里,在欧洲各国原先被公众普遍接受的权威迅速的丧失了自己的合法性”[10],英帝国主义正走向衰落,英国文化对爱尔兰的压迫正在逐渐减弱,这正是爱尔兰民族振兴的时机。同时,爱尔兰内战也如火如荼。自1922年起,爱尔兰内部矛盾便不断激化,集中表现在不同派别的政党和宗教势力的冲突。人们的思想产生波动,国家的权威不再,人民的信仰丧失,寂寥的爱尔兰文化之花即将枯萎!此时脆弱的爱尔兰人民急切需要心灵的抚慰和前进的动力。叶芝深刻明白爱尔兰必须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进而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于是诗人挺身而出,试图通过诗歌带领人民走向美好的未来。《驶向拜占庭》是收录在诗集《塔楼》中的名篇,充满了象征主义哲思,抒发了老骥伏枥的雄心。作为爱尔兰文化复兴的旗手叶芝为国家的独立、解放奠定了文化和思想基础。《驶向拜占庭》像一面镜子,描画出爱尔兰混乱动荡的时局;同时它却又像燎原的星星之火,能够通过振兴文化从而带领人们走出迷茫与恐慌,重拾面向未来的信心和勇气。诗人满怀激情,将世间万物注入活力和灵魂,来颠覆英国的殖民主义文化。诗歌中建构的世界尽管充满了哲理象征,却有如青春洋溢的少年,他们热情迎接着新的世界。那里有葱翠欲滴的花草,林间鸟儿婉转地鸣叫,似乎所有的生物都在歌唱。这美好的世界里,“一切全都沉湎于那感性音乐,/而忽视不朽智力的丰碑杰作。”[2]415
诗歌中的“老人”意象既象征衰老的作者,也象征古老的爱尔兰文化,这和爱尔兰文化的历史进程恰恰形成了对比。古老的爱尔兰文化在殖民文化的压迫下看似行将就木,却恰恰处于新的历史循环的起点,迎接着生命的轮回,等待着爱尔兰文化的将是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高雅的拜占庭艺术殿堂象征的是走向新生的爱尔兰文化,这对当时混沌的爱尔兰文化界无疑注入了新的认知和活力。诗中第二节写道,衣衫褴褛的“年老之人不过是无用之物”,写尽了爱尔兰民族由盛转衰的曲折历史。随后,叶芝转而写道“拍手歌唱,愈唱愈响”[2]415,他相信古老的爱尔兰民族绝不会衰败,也绝不会向命运低头,而是甩开“破衣裳”孕育崭新的民族精神:“因此我扬帆出海驾舟航行,/来到这神圣的都城拜占庭。”[2]415于是他将精神寄托于遥远的神圣国度——拜占庭。那里是艺术的永恒之所,也是精神的神圣殿堂。“叶芝寻找的是宁静、灵动、永恒、整体和统一。”[11]尽管“拜占庭是历史上关于东方的想象的圣地……他却重建了这座城市,从而适应他自己的理想,并选择性地找到了能够反映他的意象的艺术形式。这不是拜占庭,而是新拜占庭”[12]。当然,这里的拜占庭在诗人的笔下是不朽的、永恒的,它是叶芝心中的天堂,也是爱尔兰民族的精神家园——没有疾病、痛苦、衰老和死亡。虽然拜占庭承载了东方的想象,但诗人认为艺术不分国界,一切都是平等的、包容的、自由的,拜占庭是天堂和乐园的化身,是文明与永恒的代名词,爱尔兰民族也将在这里复兴古老而灿烂的文化。
叶芝又使用“宗教”意象来重建民族信仰和信心。诗歌中的“上帝”“圣火”和“圣人”在爱尔兰宗教里是信仰的对象,是英雄和神灵的符号。这说明有着这样英雄和神灵的民族是神圣、高贵和不可征服的,也凸显出爱尔兰民族独一无二、不可侵犯的民族品格与气节。叶芝诉说道:“请耗尽我的心;它思欲成病,/紧附于一具垂死的动物肉身,/已经迷失了本性;请把我收集/到那永恒不朽的艺术作品里。”[2]416叶芝不惜自我牺牲以重建民族文化:“我不再采用/任何天然物做我的身体躯壳。”[2]416
叶芝希望唤起人们的民族意识,摆脱英国殖民文化,从而找回属于自己的文化。叶芝的身体虽已衰老,然而内心却充满激情、智慧和顽强的生命力,他不像“少年”只在乎即时的享乐而忽视文化的功能,他要在古代爱尔兰的文明上精雕细琢,以备后来人的留存与继承:“而要那形体,一如古希腊匠工 /运用鎏金和镀金的方法制作”“或置于一根金色的枝上唱歌。”[2]416因此他通过无形的身体“把过去、现在或未来发生的事情/唱给拜占庭的诸侯和贵妇听。”[2]416当然,这里的“贵族”并不仅仅指代祖先,也将勇敢、热情的爱尔兰人民奉为圣明,其爱国热情可见一斑。他用古老工匠的打磨技法来历炼塑造金身,化身为高贵而不朽的金鸟,为民族的文化歌唱,为被压迫文化中的人民敲响晨钟,警示他们不忘初心,要深深地扎根于爱尔兰这片文化热土,要怀揣爱尔兰文化记忆,向着美好的未来勇往直前。不仅如此,叶芝迫切渴望祖国“能再度拥有昔日拜占庭文明那样的辉煌与荣耀”[13]。诗歌中的拜占庭帝国象征着爱尔兰,她有着光辉灿烂的文明。叶芝试图在历史中为爱尔兰寻找一块可资借鉴的模板[14],他认为民族的文化不应该仅仅被埋藏在过去,也不应该止步于“丰碑杰作”,而是希望人们将个人与民族联系在一起,共同将独特而灿烂的爱尔兰文化发扬下去,再现爱尔兰的伟大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