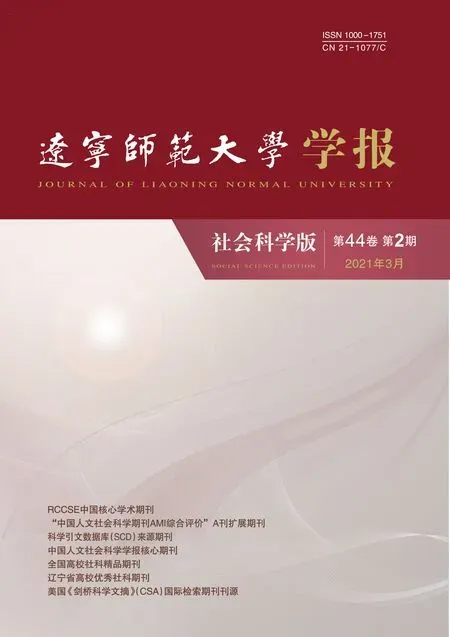乡村社会变迁视域下的困惑、思考与创作转型
——以贾平凹《带灯》为例
2021-12-29王卫平王晓晨
王卫平, 王晓晨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建设步伐日益加快,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衰败与新生的变革,以乡村原有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为土壤根基的传统乡土小说已经开始动摇。如何在乡村现代化背景下,发掘出新视野、新视角,书写出有别于传统经验的新乡土,成了中国文坛急需思考的问题。
乡村建设需要现代化,乡村居民的思想意识和文化理念更需要现代化,而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乡土小说作为对乡村文化生活的一种再现,既面临着意识形态和审美选择的挑战,同时也面临着重新整合“乡土经验”,使其走向新辉煌的契机。在这样一个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相互交融、碰撞的乡村文化背景下,中国乡土作家尝试对乡土文学进行大胆地开掘,对如何建构和谐乡村社会中新的道德、新的秩序进行多方探索。他们在真切地描写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同时,也注重洞察乡村社会的问题与危机,通过对各式各样乡村人物进行深入刻画,揭示出乡村整体的历史脉动及未来的发展路向,为中国乡土小说注入了新的生机。关仁山的《大雪无乡》、何申的《年前年后》、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张继的“村长系列”“乡长系列”都是此类小说中的佳作。但在表现乡村变革方面最典型的作家莫过于贾平凹。其作品《带灯》把目光聚焦于基层乡镇,以细腻的笔触向读者全方面地展现了乡村变革背景下乡镇一线干部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极具代表性。
从1978年以《满月儿》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为文坛所瞩目,到2013年的《带灯》、2014年的《老生》,再到2018年的《山本》,贾平凹一直以笔耕不辍的韧劲来践行自己的文学理想。40多年的持续性写作,证明了贾平凹文学创作的耐心、耐力,也表明了作家对中国社会的持续关注。在《带灯》这部作品中,贾平凹改变了以往惯有的写作方式,以一种迥异于《秦腔》《古炉》的手法,创造性地阐释着自己内心的“中国经验”并塑造了“带灯”这一鲜活的女干部形象。文本中“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依旧让读者深陷其中,但古炉村清风街的“鸡零狗碎”已变成了樱镇的“繁忙泼烦”。这部作品与贾平凹以往长篇小说的创作风格截然不同。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秦腔》《古炉》是那一种写法,《带灯》我却不想再那样写了,《带灯》是不适合那种写法,我也得变变,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1]360他想“转身”,“可这稍微地转身就何等地艰难”,在“常常能听到转身时关关节节都在响动,只好转一点,停下来,再转一点,停下来”[1]361。贾平凹如此执拗地要以“伤筋动骨”的“转身”来完成一部揭示当下社会隐痛的作品,只是“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去突破和提升”,为了去“突破那么一点点、提高那么一点点”[1]365。这就是贾平凹 “固执”的原因,也正是凭着这份“固执”,贾平凹带领读者走进带灯,见证着自己创作之路中的一次“转身”。
一、乡村社会变迁语境下的新形象
贾平凹的这次“转身”的最大特点就是塑造了带灯这一“女同志”形象。纵观贾平凹的小说创作,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贾平凹是善于塑造女性形象的,从性格各异的满儿和月儿,到《废都》中的唐婉儿以及《秦腔》中的白雪,或美丽善良,或野性叛逆。在作家看来“女性的美是多方面的,各式各样的。世上最美的风景不在名山大川,而是人,尤其是女人,女子是世上人间的大美”[1]359。相信读过《带灯》的人一定会对带灯这一形象留有深刻的印象。作家阿来曾说过关于界定好小说的两个标准,其中一点就是“有没有创造出一种新的人物形象,并通过这样的形象表达了作者对于某一个时代社会生活的感受与思考。”[2]莫言更是多次说过人物之于作家、之于作品的重要性。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中他说:“一个作家,如果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政治的和经济的历史上,那势必会使自己的小说误入歧途。作家应该关注的,始终都是人的命运和遭遇,以及在动荡的社会中人类感情的变异和人类理性的迷失。”[3]在回答记者“什么才是好的小说”的提问时,莫言回答:“好的小说要有深刻的思想,要有精彩的故事,要有令人难以忘记的人物形象,还应该有富有个性的语言和巧妙的结构。”[4]在与马丁·瓦尔泽的对话中,莫言说:“作家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描写他的人物。”“一部好小说的标志应该是写出一个让人难以忘记的人物形象。这样的人物形象在过去小说没出现过的,生活当中可以有很多类似的人,能在人物身上看到自己的小说,这就是好的小说了。当然还要有好的语言、结构。”[5]由此可见,在很多经典作家看来,人物形象都是小说的重要元素之一,不可或缺。带灯与以往贾平凹笔下的女子都不同,她是一名有些“特性”的基层干部,是乡村社会转型下的特有存在。这在贾平凹以前,甚至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中都不多见,是一个崭新的形象。
带灯的身份是一个“外来者”。她毕业就来到樱镇,带着初入社会的“外来者”的特有的视角观察、打量着周遭的一切。这种与镇政府老同志们截然不同的视角是源于其内心对社会、人生的美好憧憬。初到樱镇的带灯对于身边的一切都充满了陌生的新鲜感:“带灯看到了猪耳朵草的叶子上绒毛发白,苦苣菜开了黄花,仁汉草通身深红,苜蓿碧绿而苞出的一串串花絮却蓝得晶亮,就不禁发了感慨:黑乎乎的土地里似乎有着各种各样的颜色,以花草的形式表现出来了么。”[1]10对于生活在农村的人来说,猪耳朵草、苦苣菜、苜蓿,这些都是再寻常不过的,然而在带灯的眼中,这一切又都是如此新鲜和美好,这份美好不仅是对于自然界的观察,同时更是对未来生活的期盼。带灯的这段感叹,与其之后给元天亮写信的口吻极其相似。这种最初的美好正是她自身所特有的“小资”情调,只不过随着现实的逼仄与折磨,带灯的这份最初的美好受到了挑战,甚至面临毁灭。
怀揣着这一份新鲜感,带灯开始了她的樱镇生活。现实与想象似乎永远都无法重合,正是带灯的“外来者”身份,使得她与别人的交往总是有些“隔”,似乎无法融入樱镇的生活。最明显的表征就是,带灯无法接受身上有虱子,而身上有虱子似乎又是樱镇人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个生活中的琐碎细节是两种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外在“能指”。带灯在试图扭转这个陋习中第一次败下阵来,她起草的灭虱子的文件,成了村主任的卷烟纸。她似乎也意识到乡土中国的“集体无意识”的强大以及自身与外界的融合之难。其实,在文学史上不乏带灯这样与环境相冲突的“疏离者”。如《在医院中》的陆萍,《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中的林震,《女同志》中的万丽,他们或与主流妥协,或在作品中留下了光明的尾巴。如鲁迅先生所言“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正是这样最终被“规训”的结局才能更容易引人深思。而带灯的夜游症似乎更让人心痛,这种“惩罚”也更让人刻骨铭心。
“出事了”之后,带灯生病了,也许这是读者最不愿看到的结果,“夜行自带了一盏小灯”的带灯似乎已无力飞翔,更遑论去照亮那黑暗的夜,樱镇再不会出现“偏收拾打扮了一番,还穿上高跟鞋,在院子的水泥地上噔噔噔地走”[1]11的美丽女子了吗?依笔者揣测,并非如此。当已成为幽灵一般的带灯游走于樱镇的夜晚中时,樱镇也出现了令人惊异的萤火虫阵:“看着这些萤火虫,一只一只并不那么光明,但成千的成万的十几万几十万的萤火虫在一起,场面十分壮观……就在这时,那只萤火虫又飞来落在了带灯的头上,同时飞来的萤火虫越来越多,全落在带灯的头上,肩上,衣服上。竹子看着,带灯如佛一样,全身都放了晕光。”[1]352
“一只在暗夜里自我燃烧的小虫”只不过是“螳臂当车的抗争”,但“成千的成万的十几万几十万的萤火虫在一起”那不就成了星火燎原了吗?小说以“镇政府还有着故事”收束,在开放性的结局中,作者并未交代樱镇的未来,对于一直都深信“天气就是天意”的贾平凹,借马副镇长之口说出:“这天不是个正常的天了,带灯,这天不是天了!”[1]353变天之说虽不可信,但人在做,天在看。带灯这位樱镇新来的“女同志”的所作所为,不仅使她获得了一群老伙计的支持与爱戴,也使上访专业户王后生改变了对带灯的看法,正如带灯自己所说:“农村么,当有矛盾冲突时,是少有人出来公正的,也少有人明白地说谁是谁非,但你相信,在以后的日常生活中像风吹着田地一样,人气却还是一股梢地向着正经一边的。”[1]151在这里,贾平凹明确地告诉读者,比权力更大,也更为重要的是人心。
如果留意贾平凹所写的《秦腔》后记,读者一定会看到“我感激着故乡的水土,它使我如芦苇丛里的萤火虫,夜里自带了一盏小灯”。虽然带灯是有现实原型的,但这“夜里自带了一盏小灯”却是带灯与作者的共同点,这“一盏小灯”正是对于乡土的眷恋与不舍。相信很多读者在初读过程中,都会有一个疑问,当与环境无法融合时,带灯为什么没有选择回城?但如果细细品味文本,其原因不难发现。在无法与镇政府的人和气一堂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带灯与她的老伙计的深情厚谊,看到了她对闺蜜竹子的细心呵护。当读到带灯自学中医,尽自己所能地帮助樱镇的父老乡亲时,笔者想,也许正是这份惦念与善良,促使她留在了樱镇。在贾平凹的散文随笔中有太多诸如《寻找商州》《走了几个城镇》《定西笔记》这样的题目,他不厌其烦地游走于乡村底层,相信他也同带灯一样,不仅流连于自然界“海风山骨”的鬼斧神工,还有着对故乡风土人情以及生于斯,长于斯的眷恋与不舍。在这里,带灯与贾平凹二人对农村的态度,对农村固有顽症的焦虑都是重合的,在带灯的背后,我们也看到了贾平凹的深邃思考。带灯这一形象的塑造,倾注了贾平凹对“乡土中国”的“中国经验”的忧思。在带灯身上也寄托着贾平凹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企盼。也正因此,塑造了“这些人天生为天下而生,为天下而想,自然不会为自己的私欲而积财盗名好色和轻薄敷衍,这些人就是江山社稷的脊梁,就是民族的精英”[1]358。“贾平凹的小说写作往往都是凿通自己和小说之间壁垒的过程,因而贾平凹写带灯是要‘写心’的”“贾平凹《带灯》的写作恰恰表明,所谓‘典型化’的过程,本身就应该是作家面对历史和自己所处的时代深刻观察和反思的文学炼金术”[6]。带灯在樱镇综治办的工作,每天面对的都是鸡毛蒜皮的民事纠缠以及维稳劝解的东奔西走,正如书中所写“带灯在现实中无处可逃的时候,她把理想放在了情感想象之中,远方的乡人元天亮成了她在浊世中的精神寄托”,这份近似于柏拉图式恋爱的精神寄托,使得带灯没有在现实的蝇营狗苟的污泥浊水中沉沦,“人不单在物质上活着,活着需要一种精神”[7]241。带灯的精神依靠究竟是元天亮,还是带灯自己?因为在小说中元天亮这一人物并不真切,甚至有些形而上的虚无缥缈。
二、隐藏于文本背后的乡村变革新问题
贾平凹构思这部小说时想“稍微地转身”,从文本中我们能看到作者“转身”的努力,同时我们仍可看到昔日作品中的影子以及他一直思索的城乡现代化的问题。贾平凹一直坚持表现当下乡村现实问题的创作理念,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是在书写乡村改革的艰难,抑或传统文化的流失。在《带灯》中,贾平凹以一位乡村基层女干部的视角,反映现下中国乡村的境况。他一方面表现着基层干部的奉献和不易,另一方面又将“永远没法维稳”的乡村所隐藏的种种问题暴露于读者眼前。基层的治理存在着太多的矛盾冲突,乡村的改革面临着太多的问题困境,乡村的传统意识中残留着太多的落后思想。
小说中,元天亮的祖辈元老海带人因阻止高速公路的修建而保全了樱镇的风水,他就像是《秦腔》中对土地的热爱甚至达到以土为食的夏天义,元老海也有着对于土地的深厚眷恋。然而作者在《带灯》开篇就写到“高速路修进秦岭”“这年代人都发了疯似的要富裕,这年代是开发的年代”[7]3。时过境迁,人们的观念早已日新月异,因而“元天亮动用了他的人脉和权力资源而促成的”大工厂的引进,似乎就“合情合理”了。代与代之间的隔阂上升为城乡二元对立的矛盾,城市化进程的这种“合情合理”也许只是乡镇领导积攒政治资本的手段,不论王后生是出于什么用意,但是连他都知道大工厂会污染环境,而这样的大工厂还是元天亮动用关系才谋得的。元天亮这张樱镇的名片,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像祖辈那样的家园守护者早已逝去,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开路先锋与“始作俑者”。当建厂的消息传到樱镇,与元天亮沾亲带故的元黑眼说:“他们(拉布和换布——引者注)凭什么就能多揽到活?元天亮是西街村的,没有元天亮哪有大工厂,他镇政府又不是瞎了眼?!”[7]62这位“一直心系着家乡”的元天亮是否知道他的族人打着他的旗号,在樱镇横行霸道?元天亮对于樱镇上下来说,是形式大于意义的,“名片”除了介绍自己之外,就别无他用了,在元天亮为家乡办事的故事中,有这么一件:“元天亮通过省扶贫办拨了十万元加固镇前的河堤,但两年过了,镇政府却没有在河堤上增加一个石头,也没栽一棵树。”[7]8并不允许随便进出的镇政府,因为提了元天亮的名字,“门就开了,门卫还给敬个礼。”这样一个简单的细节,便将乡村政府存在的拉关系、搞特权的官僚主义之风跃然纸上。樱镇上下对于元天亮的依赖,与带灯对元天亮的依赖似乎是“异曲同工”的。带灯是喜欢樱镇的山山水水而留在了樱镇,而元天亮则有意无意地充当着樱镇现代化的推手,二人的立场也是不相容的,因此元天亮也无法对带灯的倾诉给出答案,由此推之,带灯的精神依靠依然是她自己。带灯与元天亮之间只是一场“虚构性的象征叙事”。小说中最具反讽意义的莫过于“县委县政府办公室指示”这一节。这一节以公文的口吻详述了八条接待指示,甚至严禁俯拍,以免因“暴露”市委书记谢顶而有损“形象”,此类无关痛痒的事情也出现在了公文指示当中。在这份匪夷所思的指示中,读者看到的只有下级部门对上司的逢迎嘴脸以及人浮于事的政治作秀,无法想象这份指示与我们现实生活中乡镇政府的红头文件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差别。在情节构造上,贾平凹的笔法十分老练,很多负面的问题都被从正面去写,韵味十足。南河村要建沙场,但这又不是村民自己所能决定的。当带灯通知几户村民去河滩筛沙时,这几户村民简直不敢相信,认为是不可能的,在反复确认这是真的之后,又感恩戴德地要请带灯吃饭,又要放鞭炮以感念政府。一件小事引发出如此夸张的感恩戴德,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乡村多么需要公平公正。在文本末尾,贾平凹安排了一节凶狠的打斗(元家兄弟和拉布兄弟的打斗),这段乡村暴力既是小说的高潮部分,也是女主人公的落幕之处。打斗过后,带灯因处理不力被处分,进而患上了夜游症,从此一蹶不振。变了质的乡村社会的内部矛盾严重激化,欲望与仇恨让它变得面目全非、难以辨认。而这样一种危险又难以掌控的局面,绝非单凭某个人的一己之力就能起到扭转作用的。这场打斗也就成了带灯理想破灭与彻底失败的宣告。
身处农村政治体制中的带灯面对上访村民的死缠烂打、面对经济纠纷的明争暗斗、面对乡邻仇视的暴力事件,她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初,她幻想通过发挥自己的光和热去为乡村发展铺平道路,使这个复杂的体系制度得以更好地运转。但现实弊病由来已久,矛盾难以调和,正如作品中所喻,“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乡村变革背后所隐藏的问题远不是靠一个人努力所能解决的。
20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乡村进入前所未有的快速转型期,乡村文明在急剧变迁,随之相伴生的乡村治理问题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错综复杂。改革中的乡村并不是风平浪静的,政治体制的弊端、家族之间的仇视、利益引发的争斗、机遇面前的不公、贫穷之下的欲望都是种种乡村问题爆发的导火索。读《带灯》的后记可以看出,贾平凹在小说中所设计的人物和情节都是有真实原型存在的。上访、蒙冤、计划生育、工厂建设、宗族争斗这些故事都是贾平凹走进乡村后所亲身经历的,是活生生的乡村现实。《带灯》是贾平凹“贴着泥土”写出的又一力作,透过文本,读者可以窥探出中国乡村变革的冰山一角。城乡一体化、工业现代化、经济市场化的发展冲击着乡村原有的社会、政治、文化结构,致使乡村的治理、发展出现了混乱,进而引发了种种危机。小说对中国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产生的矛盾进行了原生态的揭露,传达出贾平凹对现代化背景下乡村社会的改革方式选择和群体意识转变的忧虑。
三、乡村变迁背景下乡土作家的思考及转型
李遇春在与贾平凹的一次对话中谈到,贾平凹以往的小说都贯穿着“一条精神线索”“这就是徘徊在现代城市文明与传统农业文明之间。您一方面对现代城市文明感到厌倦,为现代人的精神异化和自我失落痛心疾首,另一方面,您又对传统乡村文明保持着足够的警惕”。贾平凹也自言“是在这种‘绞杀’中的呼喊,或者是迷惘中的聊以自救吧”[8]。“这一本《带灯》仍是关于中国农村的,更是当下农村发生着的事。”[1]354在这部“转身”之作中,贾平凹并没有忘记自己文学的“根据地”,依然写着农村中的日常琐碎。只不过与以往小说不同的是,这一次在小说中反映的是切实的当下,而且贾平凹选择了一个全新的切入口——综治办。上访与维稳是当下的一个敏感的政治现象,而贾平凹一直“徘徊在现代城市文明与传统农业文明之间”的矛盾与疑惑在综治办得到了一次“大爆炸”。一方面,农民的土地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减少,切身利益得不到保护,无地可耕的农民无法生存;另一方面,政府部门的一些不当之举,也深深地伤害了农民,无依无靠的农民只能通过上访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像秋菊一样“只想讨个说法”。然而,现实中的事实却并非这样一分为二的简单明了。“现在讲究起法制了,过去的那些东西全不要了,而真正的法制观念和法制体系又没有完全建立,人人都知道了要维护自己利益,该维护的维护,不该维护的也就胡搅蛮缠着。”“村寨干部又多作风霸道,中饱私囊;再加上民间积怨深厚,调解处理不当或者不及时,上访自然就越来越多。”[1]39
对于现代性的持续性关注,促使贾平凹不断思考与追问——乡土中国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创痛?文学创作又如何重新把握现实问题,找到新的叙事空间?《带灯》就是这样一部在思考后应时而生的探索之作。正如小说中所述“真正的法制观念和法制体系又没有完全建立”,农民包括那些村镇干部,他们像“失根”的浮萍,旧有的道德体系与伦理观念、“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被现代化冲击的七零八落,而新的体系又没有形成,现代化猝不及防的到来,他们都难有招架之力,“改革么,就和睡觉一样,翻过来侧过去就是寻着怎么个能睡得妥。”[1]32在这种“翻过来侧过去”的现代化尝试中,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中,没有人知道答案,农民没有,村镇干部没有,贾平凹自己也没有。农民有自身的劣根性,某些村镇干部的胡作非为,连带灯、竹子在非常时期也会采取一些非常手段(在张膏药家对于王后生的“整治”)。在这里贾平凹并未像道德法官那样臧否人物,他只是对这混沌的樱镇以及中国的农村深切地关注着,在小说中元老海阻挠在樱镇修筑高速公路,这虽然保护了樱镇的风水,但却让樱镇一直受穷,这到底对不对?文本中我们很难找到确切的答案。“这既不是一种批判的眼光,也不是认同,而是一种边缘立场和态度上的自觉。”“《带灯》的意义正在于呈现了一个既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或各类媒体的叙述和塑造,也不同于学术研究中的枯燥冰冷的描述之外的另一种别样丰富的景象。”[9]
在这部“转身”之作中,读者看到了很多贾平凹在文学创作上的新突破。其中有对基层乡镇女干部这样新的形象的塑造,有对乡镇综治办这样新的叙事空间的发掘,也有对条例、工作指示等非文学元素介入的探索。但真正让贾平凹完成转型的是其在《带灯》中对于审美理想的重建。众所周知,贾平凹骨子里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但此次他却一反常态地在乡土小说创作中对政治浪漫美学进行了尝试。这种一反常态是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浪漫想象的重构,也是在某种程度上与当下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契合。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到五六十年代冯雪峰提出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再到后来的“文革”文学,都是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作为文学创作的根本追求。但这个理想却一直没能得到真正地实现。自身理论的不成熟,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人物形象设置标签化、概念化等原因成了阻碍其发展的绊脚石。面对社会的变迁、历史的难题,贾平凹在《带灯》中摒弃了以往的绝对性批判书写,尝试在政治浪漫想象下重构出具有现代性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带灯》的主人公不再是腐败、堕落的反面干部形象,也不是现代主义创作一贯刻画的局外人、边缘人形象,而是在政治理想性的积极意义上去塑造的代表着当下体制内具有先进性、未来性的正面女干部形象。在过往的文坛中,政治想象下的女性形象始终没有被真正地塑造出来,贾平凹这次努力填补的意义和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在《带灯》中,时代和女性都获得了新生。贾平凹是一位极具前瞻眼光的作家,他的《废都》曾准确地暗示出中国即将再次兴起传统文化复兴的潮流,而这次《带灯》又以惊人的预见性实现了与时代精神的完美同步。时代的发展变化给了贾平凹新的动力与灵感,他意欲重新链接起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想象脉络,创作出与颓靡文学完全不同的正能量文学。
但乡土小说毕竟是以现实主义为土壤,如果仅仅停留于浪漫想象,而没有关注现实问题,那么《带灯》将不可避免地重蹈革命文学“人物理想化、空洞化”的覆辙。贾平凹是意识到了这一关节的,他给予了带灯该有的“党性”,但却没能让其身上的阶级属性朝着政治的方向升华,小说中的带灯是一个有着自己喜怒哀乐的栩栩如生的人。读者在带灯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伦理、道德的内在品格,而非政治品格。贾平凹在塑造带灯这一形象时,是从审美和想象层面开始的,但当他回归自己的现实乡村经验,他看到了不可能性,这样一个理想形象在面对乡村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纠纷矛盾、欲望争斗时,无论如何都是维系不下去的。于是,贾平凹选择了让带灯在现实中落地,在械斗中完成了自己可怜的救赎,最终成了一名梦游症患者。《带灯》是一场现实与理想的调和,贾平凹在这部作品中表达了自己对乡村发展的憧憬,但他深知乡村变革尚未完成,而这一过程是必然要经历伤痛和苦难的。在这场调和中,贾平凹有过困惑,浪漫的济世情怀和冷静的批判思维在他灵魂中相互碰撞,让他举棋不定。但最终贾平凹还是选择了将理想让位于现实。在他的笔下,带灯这样一个“江山社稷的脊梁”“民族的精英”仅仅是照亮了现实,却没能改变现实。或许这才是贾平凹“伏在书桌上痛哭”的真正原因。
在这部“转身”之作中,贾平凹顺应时代的潮流,尝试在以往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完成政治浪漫想象在美学上的投射,将理想与现实有机结合,为读者生动地呈现了一个当下乡村现实的样板与参照,引起读者对于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思考,为传统乡土小说打开了新的创作视域。“六十而耳顺”的贾平凹从未停下过脚步,他始终关注着“乡土中国”的发展变化,一直努力地探寻着文学创作的前进方向。他的“中国经验”仍在酝酿,六十年一甲子、一轮回,站在新起点上的贾平凹,他的“转身”、他的“思考”也许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