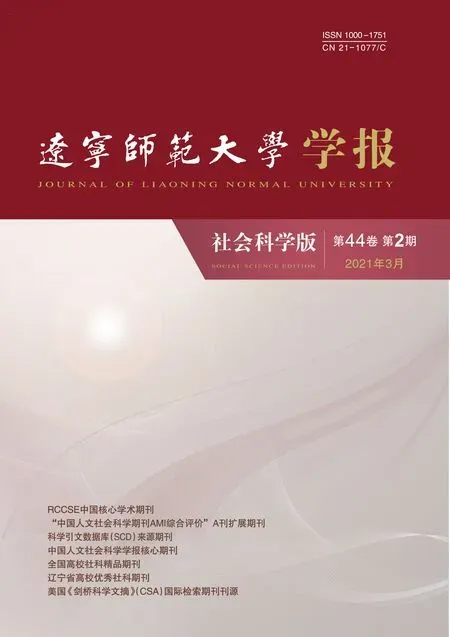于黑暗世界透出一抹亮色
——从鲁迅的小说《明天》到李时建的戏剧《小夜曲》
2021-12-29胡斌,张璐
胡 斌, 张 璐
(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提起鲁迅小说的戏剧改编,研究者们往往较多关注《阿Q正传》的改编,它出现了田汉、许幸之和陈白尘等数个改编本,影响较大。近期笔者在剧艺出版社1940年刊行的《独幕剧创作月刊》第2期上读到了署名为李时建的独幕剧《小夜曲》,剧名后明确标注“由鲁迅先生的《明天》改编”,显然这是被学界长期忽视了的鲁迅小说改编剧本。
改编者李时建鲜为人知,但他的另一笔名胡导却时常出现在现代戏剧史上。胡导,原名胡道祚,安徽泾县人,生于1915年。自20世纪30年代起开始活跃在戏剧舞台上,后由演员转为导演,成为当时上海著名的“四小导演”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上海戏剧学院任教。胡导以导演“流线型喜剧”见长,代表作有《甜姐儿》(魏于潜编剧)等,“以‘发噱’‘滑稽’为特色的表现手段吸引上海的市民观众,在坊间很有一点影响”[1],并获得“喜剧圣手”的美誉。胡导自1939年在《文心》上发表剧本《蓝眼睛》起开始使用李时建这一笔名,后来他的一些导演作品也常署此名。作为资深的戏剧人,胡导集演、编、导于一身,编写的剧本主要有《眼儿媚》等。近年有学者论及胡导时指出,他“曾根据鲁迅小说改编过一个剧本,早已散佚不存”[2],我们这里要讨论的《小夜曲》无疑就是这个剧本了。鲁迅的《明天》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无望的黑暗世界,经过李时建的再创造,我们可以从这个黑暗世界里窥见一抹亮色。
一、从几近都是“吃人者”到人性尚存
鲁迅笔下的人物性格鲜明,各具特色,几乎每个人物都被赋予了深远的内涵与意蕴。借助这些人物的塑造,作者大多是为了揭示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在将小说改编为戏剧时,剧作家往往会对其中的人物进行再创造,以期达到一定的戏剧效果。李时建在《小夜曲》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便与鲁迅的小说《明天》中的人物形象存在差异,改编者为这些“吃人者”保留了一丝人性。
在鲁迅的小说《明天》中,除了悲剧主人公单四嫂子与她可怜的儿子——宝儿,剩下的差不多都是“吃人者”。“吃人者”的身份各不相同,有被人们视作“救命稻草”的何小仙,有帮闲红鼻子老拱、蓝皮阿五之流,还有的多是叫不出名字的愚昧百姓。何小仙无行医能力,却开馆看病,这无疑是草菅人命,加速了宝儿的死亡。何小仙四寸多长的指甲与贾家济世老店的店伙计翘着的长指甲暗示着两方的暗中勾结。红鼻子老拱与蓝皮阿五时常坐在单四嫂子家隔壁的咸亨酒店喝酒,两人暗中将身为寡妇的单四嫂子作为性幻想的对象。蓝皮阿五更是借着帮忙抱孩子的名义,占单四嫂子的便宜,达到目的后,又急忙将孩子还给单四嫂子。而在宝儿下葬那天,“蓝皮阿五简直整天没有到”。鲁迅曾多次深刻地指出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3]红鼻子老拱与蓝皮阿五之流就是这种具有国民劣根性的代表。他们作为帮闲,身份卑贱,精神上孤单空虚、麻木不仁、得过且过,物质上更是极度匮乏。小说结尾出现的戏曲唱词:“我的冤家呀!——可怜你,——孤另另的……”[4]479,从戏词的表意来看,是对单四嫂子现状的写照以及同情,但在红鼻子老拱与蓝皮阿五二人嬉笑打闹中唱出,意味便完全不同了。这是两个被扭曲的灵魂,在被人“吃”的同时也在“吃”着别人。其他叫不出名字的,在宝儿下葬那天“凡是动过手开过口的人都吃了饭”[4]478。在这样一个充斥着“吃人者”的环境中,不难看出,《祝福》里的祥林嫂就是单四嫂子的“明天”。
李时建的《小夜曲》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对其中某些人物进行了少量改动,可以看到他们身上留存着些许人性,于黑暗世界中透出一抹亮色。这抹亮色的最大来源便是王九妈。在小说中,单四嫂子带着宝儿看完病后返回家时,“早看见对门的王九妈在街边坐着,远远地说话”,询问宝儿的情况,带着些漫不经心的态度。当单四嫂子请王九妈看看宝儿的情况时,“王九妈端详了一番,把头点了两点,摇了两摇”[4]476。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也没讲些宽慰单四嫂子的话。而在改编戏剧中,单四嫂子是在深夜高声叫喊,敲开王九妈家中的门的,“王九妈已有六十多岁,她刚警醒起来,外面的衣服还没有穿好,一手扣着扣子,睡眼朦胧地眯着一双老眼”[5]。深夜被突然叫醒,王九妈并未感到不悦与不耐烦,而是关切地询问宝儿的情况。当看到宝儿的情况极为不乐观时,王九妈嘴里念着“阿弥陀佛!菩萨保佑!”其仁义之心,可见一斑。宝儿去世后,小说中的王九妈还算有些情谊,帮着单四嫂子料理宝儿的后事。但在单四嫂子哭着不愿合上棺木盖时,“王九妈等得不耐烦,气愤愤的跑上前,一把拖开他,才七手八脚的盖上了”[4]477。在经过改编的戏剧中,剧作家对王九妈的形象进行了“柔化”处理,当单四嫂子哭得厉害时,“王九妈也陪着揩眼泪”,并提醒单四嫂子要注意身体,宽慰单四嫂子对宝儿已经尽了心,生老病死是没有办法的事。而后仗义执言,替单四嫂子赶走欲占便宜的红鼻子老拱与蓝皮阿五并提醒她要提防他们。看到单四嫂子孤身一人,怕她太过孤独,王九妈还提议她去抱个孩子来养。
红鼻子老拱与蓝皮阿五虽然依旧打着占便宜的主意,但也不失其善心。例如,夜里宝儿的哭声停了以后,红鼻子老拱说道:“唔!睡了就好了,睡了宝儿的病就要好啦!”[5]并且在宝儿下葬那天,红鼻子老拱与蓝皮阿五两人也实实在在地出了力。单四嫂子向二人的热心帮忙致谢,红鼻子老拱答道:“这不算什么!我们多年的老街坊,这一点算得了什么!”蓝皮阿五更是说道:“单四嫂子,你下次再要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蓝皮好了!”[5]虽然依旧是冷漠与猥琐,但与鲁迅的原作相比,李时建赋予了二者更多的怜悯与同情。剧作家们在改编《阿Q正传》时,习惯于在阿Q故事的基本构架上添加鲁迅其他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因此,红鼻子老拱和蓝皮阿五二人成为田汉、许幸之和陈白尘等改编本中的典型角色,他们是咸亨酒店的惯常客人,是鲁镇众多冷漠看客中的一员。有意思的是,李时建于1939年参与了许幸之自编自导的《阿Q正传》,并饰演蓝皮阿五一角。或许正是饰演蓝皮阿五的经历,促发了李时建对《明天》的改编。
鲁迅在谈及自己为什么提笔写作时,曾指出是为了给身在寂寞中的战士们呐喊助威,但“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6]。可见,鲁迅在《明天》中“吃人”环境的设置是为了暴露国民的劣根性,暴露旧社会的弊病,借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而李时建在改编的《小夜曲》中,让这些“吃人”者保留了些许人性,不致使读者或观众感到太过无望。
二、从再见无望到“梦”中相见
无论是在鲁迅的《明天》还是在李时建的《小夜曲》中,关于单四嫂子最后的“梦”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情节。对于单四嫂子而言,“梦”意味着与宝儿团聚,是希望的象征。
在小说中,“单四嫂子虽然粗笨,却知道还魂是不能有的事,他的宝儿也的确不能再见了。叹一口气,自言自语的说,‘宝儿,你该还在这里,你给我梦里见见罢。’于是合上眼,想赶快睡去,会他的宝儿”[4]479。虽然鲁迅在小说结尾并未叙述单四嫂子是否做到梦见宝儿的梦,但其在《〈呐喊〉自序》中坦言:“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7]。可见,鲁迅构思的小说结尾原本是想叙述单四嫂子并没有与宝儿在梦中相见,但即便是删掉了这一结尾,小说所显示的色彩也是全然黑暗的。
而在改编戏剧中,单四嫂子则通过白日梦实现了与宝儿的团聚。小说中,鲁迅对宝儿的着墨并不太多,主要是对宝儿病态的描写,满是痛苦与挣扎。但在戏剧中增加了单四嫂子与宝儿梦中互动的情节,突出描绘了宝儿的活泼可爱、天真无邪,为这个悲剧增添了一些温情。戏剧的背景音乐也在此时由沉重抑郁转为轻松快乐。“这杂在音乐的旋律中叫妈的声音好像更近了,好像一直到了她身边。她好像发现了什么,脸上露出笑容,伸手抱住了一个小孩子一样,紧紧地抱在她自己的怀里。”[5]单四嫂子在幻想中再一次紧紧抱住她亲爱的宝儿,这使她暂时忘却了丧子的痛苦。改编者还在此处增添了单四嫂子给宝儿唱自编儿歌的情景:“太阳高高照,妈妈爱宝宝!妈妈纺纱宝宝笑!宝宝笑得好,妈妈乐呵呵!看着太阳照得高,不及妈妈爱宝宝!”而宝儿呢,则是给妈妈一边做着手势,一边唱着:“虫虫飞!虫虫飞!两个虫虫在一堆;三个虫虫来打架,四个虫虫一块儿飞!飞!飞!飞!飞到天上去喽!”[5]这是生活中所常见的充满温馨的亲子场面。此场面的添加可以使读者或观众暂时忘却宝儿已经逝去的事实,沉浸在单四嫂子与宝儿共享天伦之乐的氛围中,不觉露出会心的微笑。弗洛伊德认为白日梦(或幻想)的动力是未被满足的愿望,每一个白日梦(或幻想)都是一愿望的满足,都是一次对令人不能满足的现实的校正[8]。与宝儿相见即是单四嫂子此刻最为重大的愿望,在现实生活中宝儿已经去世,因此,单四嫂子在白日梦中使自己的愿望得到替代性满足。当在梦中,宝儿说自己长大以后要像爸爸一样卖馄饨挣钱时,单四嫂子否定道:“不,宝儿不要去卖馄饨!宝儿长大了,妈妈送宝儿进学堂去念书识字”[5]。可见,单四嫂子已经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侧面突出单四嫂子是一个既坚强又有远见的母亲,宝儿的逝去势必会给她带来沉重一击,但自身顽强的性格以及周围有像王九妈这般真正关心她的人,单四嫂子的“明天”并不是全然黑暗的。但这也使单四嫂子这一人物形象所包蕴的悲剧性打了些折扣,当然,作品的深厚意蕴也有所削减。
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曾提道:“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9]李时建在延续了鲁迅悲剧观念的同时,增添了单四嫂子与宝儿母子二人共享天伦之乐的情节,于黑暗之中透出一丝光亮。原本,单四嫂子只能强迫自己直面宝儿已经去世的真相。一个原本幸福的三口之家,随着男人与孩子的相继死去,只剩下一个女人在人世独活,女人生活的精神支柱已然坍塌,等待着女人的是更为严峻的生活状况与社会环境。然而,通过白日梦,单四嫂子还能和宝儿相见,这无疑给单四嫂子带来了莫大的安慰。
三、一个是“黑暗中的独行者”,一个是“喜剧圣手”
黑暗书写,是鲁迅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主题之一。蒋蓝曾将鲁迅与博尔赫斯二人进行比较,他认为“可能再没有什么人,能够比他们更多地书写过黑暗,让人感到黑暗才是他们生生不息的给养,甚至,黑暗就是他们的全部所在”[10]。鲁迅在黑暗中呐喊,他是黑暗中的独行者。
对于文学创作而言,鲁迅是极力反对“瞒与骗”的,他极力主张真实再现黑暗的社会现状,深刻描绘中国民众悲惨的生活境遇,尤其是在社会底层挣扎着的农民、妇女与知识分子。抱着这样的创作理念,鲁迅愤而做《明天》。他在其中描写了当时如同铁屋子一般的社会,而且“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黑暗不见一丝光亮。鲁镇,这个看似僻静而又带着些古风的小镇,实则是个“吃人”的地方。被视为“救命稻草”的何小仙实际上并无行医能力,因而,求医无门。何小仙与贾家济世老店暗中勾结,“医”商相护,因而,求药不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麻木而毫无同情心,赏玩他人的苦痛。更加绝望的是,国民深陷囹圄却没有觉醒更不知反抗,这便造成了一个个平凡人“无事的悲剧”。宝儿生病,单四嫂子不是带着宝儿去医馆看病,而是去求神签、许愿心,最后剩下的一条路是去给无行医能力的何小仙看诊。当单四嫂子早早抱着宝儿去何家时,里面已经坐着四个病人了。看来,宝儿的悲剧会不断在其他人身上上演。“无事的悲剧”所描绘的即是平常人的事,他们对于发生在自身的悲剧,麻木而不知抗争。这样经过一代又一代,民众依旧是待在密不透风的铁屋子里,没有光明也不去追寻光明。因而这些“无事的悲剧”更加压抑,也更令人绝望。
1939年,当左翼戏剧演出繁荣之时,夏衍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状“题材的枯窘,剧情的公式化,都只是剧作者不能正当地发挥他们自己的才能,企图侥幸成功而走错了路子的表现”[11]。这一论断引起了李时建的共鸣,本着扩大戏剧题材,创新演出风格的目的,他开始着手剧本改编,但喜剧对其的影响是很难摆脱的。李时建在担任《春去也》导演期间,曾有小文介绍:“导演是李时建,他就是喜剧圣手胡导……他是以技巧的新颖与演出的轻松著称的”[12]。作为导演的李时建,是以喜剧作品闻名剧坛的,并借此跻身“四小导演”之列。在正式成为导演之前,李时建还有数年的戏剧演员经历,他擅长饰演怪派,逗趣的表演常常引得观众捧腹大笑,气氛很是火热。喜剧性以及良好的舞台效果是李时建所追求的戏剧至高境界。康心在谈到胡导的导演时,曾指出:“然而他对喜剧性的把握也许太纯熟了,难免在处理悲剧的时候,也技痒起来,暂时收起悲剧的节奏,叫观众乐上一乐”[13]。这点在改编《明天》时也有所显现,李时建为这个悲剧增添了不少喜剧色彩。例如,蓝皮阿五喝完酒,用醉得厉害的声音说:“喂,老拱!得走啦!回家挺尸去吧!”[5]以“挺尸”代替“睡觉”,显示出底层民众语言的幽默之处。再如,当老拱喝多站不稳,“啪”的一下摔倒后,阿五“(拍着掌)哈哈哈!元宝翻身了!哈哈哈!”[5]通过动作上的逗趣表演,让观众有了笑点。这样改编不仅增添了作品的喜剧性,还营造了良好的舞台效果。
此外,流畅而又轻快的戏剧节奏,柔美而又明朗的舞台布置也一直是喜剧导演李时建俘获人心的“利器”。在改编《明天》时,李时建也不忘将这两大特色融汇其中。鲁迅的小说《明天》是一篇仅有三千余字的短篇小说,且人物互动较少,多是对单四嫂子的心理描写。要将其改编为戏剧,势必有些单薄。因而改编者增添了不少原作里未有的情节,如单四的死因、宝儿的葬礼、王九妈安慰单四嫂子、红鼻子老拱和蓝皮阿五争论抱哪个孩子给单四嫂子养以及单四嫂子最后的梦等。这使得整个戏剧的情节比较完整,戏剧节奏也比较流畅明快。李时建对于舞台的布置也有较为详细的介绍,例如戏剧一开始“是深夜的时分,屋外一片乌黑,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树上有猫头鹰在哇哇地嚎叫,树叶儿给秋风吹落着在地上索索地响,沉寂,像死一般地沉寂——忽地,秋风从远处送来了几声破锣在敲着三更”[5]。这时的舞台背景营造出秋天萧瑟的气氛,是单四嫂子阴郁忧愁的心境外化,也暗喻宝儿的生命即将走向终结。而在戏剧结尾处,单四嫂子与宝儿在“梦”中团聚时,舞台布置则转变为“是春天的早晨,阳光融融洩洩地煦浴着。树枝头全抽出嫩芽,小马儿在叫着跳着喧嚣着。一切都带着春意,一切都是快乐的样子”[5]。彼时的舞台布置弥漫着春的气息,万物欣欣向荣,是单四嫂子愉悦欢快、充满希望的心境外化。前后的舞台布置形成鲜明的对比,精准地反映了主人公单四嫂子心绪的变化,以此来弥补戏剧难以像小说那样展现人物心理的不足。
文学作品的题目多是作者对于文本含义的一种映射。“明天”本是蕴含着光明与希望的,但鲁迅的小说实际上却是全然黑暗、毫无希望的。以鲁迅小说原来的题目作为戏剧名,势必能引起更为广泛的关注,而李时建却放弃这一做法,将其易名为《小夜曲》,究其原因,大致是《小夜曲》更加贴合改编后戏剧的整体风格。小夜曲原是西洋乐曲的体裁之一,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因而更符合李时建改编时的“柔化”处理与温情体现。
总体而言,李时建对于《明天》的改编大体上是忠于原著的,但通过对人物形象的“柔化”处理、对“梦”中相见情景的添加以及作者本身忠于喜剧性和舞台效果的创作理念,使得《小夜曲》又与原作有着明显的差异。如此改编,削弱了鲁迅披露现实的程度与批判社会的力度,因而作品意蕴也就不及鲁迅的深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