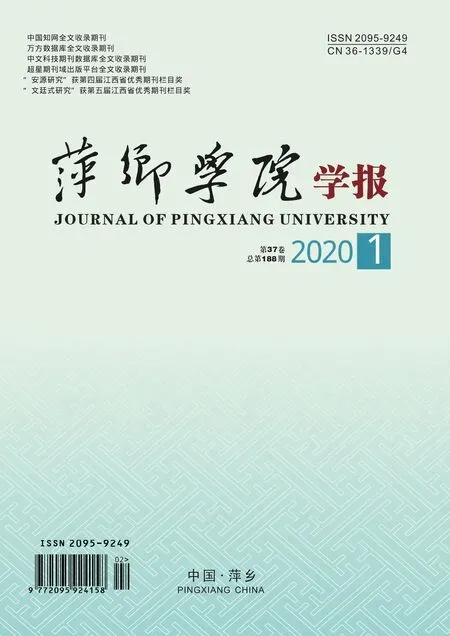梁启超对孟子人生哲学的阐释——关于梁启超的一篇重要遗稿《论孟子》
2020-12-19彭树欣彭雨晴
彭树欣,彭雨晴
梁启超对孟子人生哲学的阐释——关于梁启超的一篇重要遗稿《论孟子》
彭树欣1,彭雨晴2
(1. 江西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2. 内蒙古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1517)
《论孟子》是梁启超的一篇重要遗稿。但自1983年公布以来,却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其实,这是梁氏阐释孟子人生哲学的一篇长文。在此文中,梁氏建构了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的修养体系。这一体系既有对人性问题的形上阐发,又有对修养功夫的具体展开。他阐释的主要目的是指导其子女具体修行,该文对于现代人提升道德修养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梁启超;孟子;人生哲学
梁启超《论孟子》一长文是他一篇重要遗稿,生前未全部发表,故《饮冰室合集》未收录。其中《孟子之教育主义•性善论》的一部分,发表在1919年2月4日至8日和10日至13日的《时事新报》上,题为《读孟子记(修养论之部)》,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收录了该文。1983年收藏者李建整理遗稿全文,发表在该年《学术研究》第5期上,题为“梁启超论孟子遗稿”(按:其实应题为“梁启超《论孟子》遗稿”,下文简称《论孟子》),约2万字(2018年新出版的《梁启超全集》收录了该文);并撰有《关于梁启超论孟子遗稿》一文,对该文的来源、收藏、鉴定和主要内容等作了简要介绍。同年,《学术研究》第6期,发表了李锦全《评梁启超关于教育思想和人才学观点的重要遗稿》。该文从教育学和人才学的角度对《论孟子》的内容进行了评述。2007年,汤志钧在《史林》第3期上发表《梁启超论孟子》一文,对《论孟子》的主要内容加以介绍,并作了一些考证。据汤氏考证,《论孟子》比发表在《时事新报》上的部分多了9千多字。尽管20多年来梁启超研究持续升温,但《论孟子》自从公布以来,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真正从思想上进行专门研究的实际上只有李锦全一篇文章,甚至相关的研究也很少提到或引用。虽然《论孟子》是一篇研究孟子的未完稿,但从哲学的角度看,却是一篇相当完整而系统地阐释孟子人生哲学或修养论的文章,值得深入探讨。
一、《论孟子》产生的思想背景
晚清民国,随着西学东渐以及现代学术和教育体系的逐步建立,中国古代人生哲学日渐衰落,逐渐被西方哲学取代了其主流思想的地位。然而,仍有人(如文化保守主义者)坚信其在现代的价值,并努力将其转化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文化资源。后期梁启超在思想上总体上回归传统,致力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化①。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对中国古代人生哲学的现代阐释,挖掘其在修养身心、培养人格、提升生命境界方面的现代价值。《论孟子》正是这类研究成果之一。《论孟子》是1918年梁启超在家为子女讲《孟子》而作的,目的是为子女未来的人格形成奠定一些基础,所谓“予以一模糊之印象,数年之后,或缘心理再显之作用,稍有会耳”[1]864。他从体验躬行的路向出发阐释孟子人生哲学②,即主要阐发孟子的人生修养论。对此文,哲学家贺麟有很高的评价:“任公谈义理之学的文字,以‘五四’运动前后,在《时事新报》发表的几篇谈孟子要旨的文章最为亲切感人。对于“先立乎其大则小者不能夺”之旨,发挥最为透彻。”[2]4
二、梁启超论孟子人生哲学之总纲
关于孟子的人生哲学或修养论,《论孟子》首先有一个精要而又有体系的概括:
(孟子)以为人所以能弘道者,由其有良知良能,故言性善。此善性当务自得而有诸己,故言存养。此善性当博极其量,故言扩充。其教人在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故与曾子一派专务致谨于容貌辞气颜色之间者有异,与子夏一派专讲进退应对之节传章句之文者亦有异,其示人入道之途有二:曰狂,曰狷。狂者进取,故勇于自任,以圣人为必可学,以天下事为必可为;狷者有所不为,故尚名节峻崖岸,不屑不洁,终未尝枉道以徇乎人也[3]77。
此为梁启超论孟子人生哲学之总纲,即孟子人生修养论大纲。具体言之,孟子修养论的理论根基是性善论,既持人性本善之先验论、本体论,那么修养即依此而立,故其修养方法讲立乎其大(立志)、存养、扩充,修养途径也相应有狂者之路和狷者之路。梁启超即依此大纲对孟子人生哲学或修养论展开详细论述。
三、梁启超论孟子的性善论
性善论是孟子人生哲学思想(甚至整个孟子思想)的理论根基。这应该是民国学界一种共识。郎擎霄说:“孟子之人生哲学,根据其性善论,盖性善论为孟子全部哲学之中心思想,亦其人生哲学之关键也。”[4]79钱穆说:“今当推求其学说之本源,则不可不明孟子性善之旨。性善者,孟子学说精神之所在,不明性善,即为不知孟子。”[5]100其实,在郎、钱之前,梁启超已提出了这一观点。他说:“孟子之学,出于子思,其特标性善为进德关键,则《中庸》之教也。‘孟之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滕文公》上)此孟子一生论学大宗旨。”[3]79~80又说:“人皆有同情心,而心皆有善端,人人各将此心扩大而充满其量,则彼我人格相接触,遂形成普遍圆满的人格,故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也,此为孟子人生哲学、政治哲学之总出发点。”[6]85在具体论述性善论时,梁与郎、钱不同,郎、钱主要重在客观的学术梳理,梁则作了更多哲学上的发挥,并融进了佛学和西方哲学的内容。他主要从三个方面来阐述孟子的性善论:一是对性善基本义的解释,二是对性善圆满义的阐发,三是对五家论“性”(包括孟子性善论)的论断。
关于孟子性善的基本义,梁启超认为,孟子所谓“性善”,即人先天所具有的仁义礼智之本性,这是人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从孟子所举乍见孺子入井而怵惕,见亲死而委之于壑而颡泚来看,此皆人性自然之反应,而非为外在的目的。这是一种先验人性论。梁氏进而认为,孟子所谓“性善”是人类的本性,具有共通性,凡圣皆同,人人具有;不过这只是一种善质或善端,只是萌芽,是待完成者。如此,性善论为修养论奠定了根基:修养只不过是肯认此善质或善端,将其存养、扩充而已。
关于性善的圆满义,梁启超认为,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尽心》上),是《孟子》全书的最精到之语,此为性善的圆满义。对此,他解释道:
孟子“万物备我”之义,所谓“我”者,必非指此七尺之恒干甚明,此恒干至蹙陿至惉懘,何以能容万物,备我者亦备于我心而已。我心非他,即人类同然之心也,即天之所以与我之心也,亦即佛典所云众生心也。是故虽我也,而与物同体与天同体也。然则不云我备于万物,不云万物备于天,而必云“万物备于我”者何也?宇宙万有之现象,皆由我识想分别而得名,苟无我则天与万物且不成安立也。昔法人笛卡儿,以怀疑哲学闻,其言谓一切万有之存否皆不能无疑,惟必有我存,斯无可疑。何也,若疑我不存,则能疑之主体既先亡矣,万物则皆我心体中所函之象,而我之心体,则超乎此七尺恒干之上(此恒干亦万物之一也)。与万物为一体,与天为一体,因其为我意识所体认,则名之曰“我”,故曰“万物皆备于我”也。我意识能体认真我,则万物立备矣,故曰:“反身而诚,乐莫大焉。”[3]81
梁启超对孟子“万物皆备于我”之义的发挥,可谓透彻:融佛教唯识学和笛卡尔哲学于一炉,而又彰显孟子之本义。在梁氏看来,孟子所谓“我”,即“本心”“本性”,此本心、本性,与万物合一,天人共贯,圆融无碍(即所谓“圆满义”是也)。梁氏盛赞孟子此义实千圣真传、同条共贯第一义,孟子直揭之以示人,群儒莫能及。梁此处的阐释,实是为了说明孟子之“本心”“本性”能开出其修养功夫,所谓修养功夫,即立其“本心”也,立其“本性”也。
最后,梁启超对各家论“性”进行了论断。他先总结古代论“性”之五家:其一,孟子言性善;其二,荀子言性恶;其三,告子言性无善无不善;其四,世子等言性有善有不善;其五,有性善有性不善。然后以《大乘起信论》的“一心开二门”加以判别。所谓“一心开二门”:一心即众生心,此心总摄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依此心有二门,即心真如门、心生灭门,此二门各总摄一切法而又不相离。梁氏依此义判各家之论“性”:
告子所谓无善无不善者,盖指此众生心,即所谓一心法也。此一心法超绝对待,不能加以善不善之名。孔子所谓性即指此,故只能概括其辞,曰性相近也。然依此一心法能开二种门,故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也,孔子则言习相远也……孟子言性善者,指真如相,即一心法下所开之心真如门也。荀子所谓性恶者,指生灭因缘相,即一心法下所开之心生灭门也……两俱得谓之性者,以是二门各总摄一切法,是二门不相离故。不宁惟是,生灭门所显示之体相用,千状万态,故谓性有善有不善可也,谓有性善有性不善亦可也[3]82。
梁启超认为,五家论“性”似相反,实则各明一义,如果要论品次优劣,则告子所说,与孔子合,义最圆融;孟子指真如为性,所以劝向上,其义精;荀子指无明为性,所以警堕落,其义切;后二说则粗浅不圆。梁氏之判别,以佛学格中国哲学之“性”,其相关阐释不一定完全切合。如以“众生心”解告子之“性”,似不合告子本义,告子之“性”意指人的自然本性,即生之谓性,无超越之形上义;而《大乘起信论》之“众生心”,亦指如来藏心,具超越之形上义。但总的来说,其判别还是相当精彩的,如对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并没有判其高下,而是辨析他们“性”之内容实质上不一样,一指真如为性(故性善),一指无明为性(故性恶),各有指向。不过,梁启超剖判的目的不是为比较而比较,而是与修养论联系起来:性虽善而可习于不善,如何才能免于不善?曰修养。性虽恶而可习于善,如何才能进于善?曰修养。故孟子、荀子论性虽相反,而其归本于修养则一。孟、荀于性因持论不同,故修养之法也异:孟子言性善,故其修养之法在于发挥本能;荀子言性恶,故其修养之法在于变化气质。二者各有所长,而孟子尤能先立乎其大者。以佛法比,荀子为小乘法,乃渐教;孟子则为大乘法,为顿教。
四、梁启超论孟子的修养方法
对于孟子的修养方法,梁启超总括为:《孟子》教人修养者千言万语,两言以蔽之:“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推其如何能立乎其大,孟子概括为三者:“曰立志,曰存养,曰扩充。”[3]P84梁氏对孟子修养方法的概括,实依其“性善论”之理路而出。盖“性善”既为人性之价值根源,故修养即在确认、确立并发挥、充实此人性之本根。所谓“立乎其大者”,即立此也;相应地,具体修养方法——立志、存养、扩充,亦皆依此而出。
孟子的具体修养方法实为存养、扩充二法,但欲为此二者,需先确立人性之本、生命之基,即立志。故孟子首重立志,并以此教学者,亦将其视为一种修养方法。关于立志的重要性,梁启超认为在孟子的“尚志说”:志一立,则肌肤筋骸皆挺举,神明自发皇;不然者,奄奄若陈死人,直一齐放倒。如何立志呢?梁氏认为,孟子之教在志为圣人而已:孟子教学者,时时以尧、舜、文王自比,无丝毫躲闪之余地,亦永无满足之一日。其理论根基在于,人人既具有仁义礼智之本性,那么均具备成为圣人之可能。故志为圣人,即是使人直往上顶,挺立人格、生命之根本。至于如何为圣人,一方面孟子教人模仿古人,所谓闻伯夷、柳下惠之风而兴起;另一方面又教人不依傍古人,所谓“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尽心》上)”。后者重在尊自力,这与荀子不同,荀子教人尊他力,此与其性恶之旨一贯。盖人性既恶,则非藉他力不能矫正;而孟子言性善,故尊自力。故孟子对于不以自力向上者,苛之曰“自暴”“自弃”“自贼”。在此,梁启超将孟子的立志与性善论贯通起来了。
梁启超认为,孟子教人立志,即在确立道德自我,目的在导人具体修养;而志立之后,如何具体修养,孟子提撕二义:第一曰存养,第二曰扩充。
关于存养,梁启超认为,孟子教人修养之第一义,为存养,所谓“存其心、养其性是也”(《尽心》上)。因人性本善,能常存其善性而使之勿失,能常养其善性而使之日长,如此人格乃具。简言之,存养即存善性、养善性而已。梁氏首先从孟子“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离娄》下)之观点出发,来讲“存”之功夫。梁氏认为,人类合神明和躯干两部分而成,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人有神明,而惟此神明,能审量、能别择、能比推、能扩充。但人之神明寓于躯干之中,常受其牵缚。一旦为躯干所束缚而失去自由意志,就变成躯干的奴隶,与禽兽无异。然而神明虽为躯干所牵缚,但毕竟未尝泯灭。故孟子惟标举一“存”字。所谓“存”,即存人所本有之神明(善性、本性),也就是唤起人本有之自觉心(本心)。
梁启超又认为,孟子存、养并举,盖不养则不能久存,故孟子教人自养。那么所养者为何呢?在梁氏看来,孟子重在养大(即神明),强调不以小(即躯干)害大。但孟子也看到,人们往往为小者所夺,为了耳目口体而成为物欲的奴隶。故须“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当然,大者即立,则小者固不能夺,然必无以小害大,然后大乃能久立。所以孟子又教人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尽心》下)多欲必至以小害大、养小失大,只有寡欲才能不以小害大、不养小而失大。但如何能做到寡欲,根本工夫仍在务立其大。同时,孟子又将养性转换为养气。因为性是形上的,气是形下的,在具体修养上,养气较养性易为着手。梁氏认为,孟子所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即其养性之具体工夫,是其道德之得力处。
关于扩充,梁启超认为,孟子存养在求自得而勿失,然非此即足;其大作用处则在扩充,此为孟子教人修养之第二义。什么是扩充呢?即扩充人先天具有的仁义礼智“四端”。此“四端”只是始基、端倪,属于未完成状态,需进一步发展、扩大、充实。梁氏认为,以孟子扩充为教,是因势而利导之,是发挥本能之教,是尽心尽性之教,所谓“充类至义之尽”也;自修养者务在发挥自己的本能,教人者务在发挥他人的本能,为国民教育者务在发挥国民的本能。梁氏认为,《孟子》中言扩充的地方甚多。对此,他加以了归纳、总结:
山径蹊间,介然成路,扩充也;原泉混混,不舍昼夜,扩充也;掘井九仞,而务及泉,扩充也;城门之轨,非两马之力,扩充也;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扩充也;养气由于集义,扩充也;知天由于尽心,扩充也;反约由于博学详说,扩充也;大任由于增益不能,扩充也;以友天下之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扩充也[3]91~92。
五、梁启超论孟子的修养途径
关于修养途径,梁启超认为,孟子分为狂者和狷者二途,即从学狂者或狷者之路出发,皆可成为圣人。此实为梁氏对前面孟子“立志学为圣人”之意的进一步发挥,即立志为圣人之后依何途径成为圣人的问题。梁氏认为孟子依狂狷二途入圣道,是在述孔子之言。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孟子认为,孔子并非不欲中道,然其不易行,故退而求其次,取狂狷二途,渐次进入圣人之道。孟子对孔子“狂狷”之义加以进一步丰富,梁氏说:“其(孟子)释狂之义,则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按:“者”字原缺)也。’其释狷狷(按:后一个‘狷’为‘之’之误)义,则曰‘不屑不洁’。”[3]92梁氏认为,凡《孟子》教人以发扬志气、坚信自力者,皆为狂者之言;凡《孟子》教人以砥厉廉隅、峻守名节者,皆为狷者之言也。
梁启超认为,孟子尊狂者和狷者,于孔子之外,最尊伯夷和伊尹。尊伯夷即尊狷者,尊伊尹即尊狂者。孟子为什么尊狂者和狷者呢?狂者进取,由狂而入圣,可以为圣之任者;狷者不屑不洁,由狷而入圣,可以为圣之清者。也就是说,遵循狂者或狷者之途进入圣人之道,是方便之途径,故孟子推尊之。在梁氏看来,孟子本人既是一个狂者又是一个狷者,他正是从狂狷二途来进入圣人之道的。故学孟子之学,即可从此二途而入。故作为修养受用来读《孟子》,“第一,宜观其砥砺廉隅,崇尚名节,进退辞受取与之间竣立防闲,如此然后可以自守而不至堕落。……第二,宜观其气象博大,独往独来,光明俊伟,绝无藏闪,能常常诵习体会,人格自然扩大。第三,宜观其意志坚强,百折不回,服膺书中语,对于环境之压迫,可以增加抵抗力。”[7]8第一,是学孟子之“狷”,第二三,则是学孟子之“狂”。
结论
通过对孟子人生哲学思想的阐释,梁启超建构了孟子性善主义的修养体系。这一体系既有对人性问题的理论上阐发,又有对修养功夫的具体展开。此前,还未有人如此系统地梳理过孟子的人生哲学。此为梁启超研究孟子的重要贡献。梁氏充分肯定孟子性善主义的学术价值,认为孟子“高唱性善主义,教人以自动的扩大人格,在哲学上及教育学上成为一种有永久价值之学说”[7]7。同时又确信孟子的修养功夫可确立做人之根基:“《孟子》为修养最适当之书,于今日青年尤为相宜。学者宜摘取其中精要语熟诵,或钞出常常阅览,使其精神深入我之‘下意识’中,则一生做人基础可以稳固,而且日日向上,至老不衰矣。”[7]P8当然,梁启超最重视的还是孟子的修养工夫,发掘其修养工夫在于使人真实受用,即指导自己的子女或现代人践履、躬行。在古人修身养性的学问几乎丧失的今天,梁启超所挖掘出的孟子的人生哲学或修养论,于人们浮躁、焦虑、迷惘的心灵仍不失为一副良药。
注 释:
① 梁启超前期(即戊戌变法时期和流亡日本时期)主要致力于引进和传播西学,并在思想感情上对西学有相当的认同,而后期(1912年归国后至1929年病逝时期)则主攻中学,并渐渐在思想感情上认同和回归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其实梁启超一生从未完全离开过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②梁启超阐释古代人生哲学的最大特点,是从体验躬行的路向着手。所谓“体验躬行的路向”,是指把中国古代哲学视为生命的学问、行为的学问,侧重阐发古人如何修养身心,培养人格,提升生命境界。这与“知识论的路向”不同。后者侧重以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方法对中国古代哲学重新整合,加以思辨、分析。当然,前者也对古代人生哲学作一定的理论分析,但这只是为了阐述人生修养的理论根基,重点还是在如何修养问题。民国前期,这两条路向,前者以梁启超为代表,后者以胡适为代表。
[1] 丁文江, 赵丰田. 梁启超年谱长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2] 贺麟.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3] 梁启超. 梁启超论孟子遗稿[J]. 学术研究, 1983,(5).
[4] 郎擎霄. 孟子学案[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8.
[5] 钱穆. 孟子研究[M]. 上海: 开明书店, 1926.
[6] 梁启超. 先秦政治思想史[M]//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7] 梁启超.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M]//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LIANG Qi-chao’s Interpretation of Mencius’ Philosophy of Life——, an Important Manuscript of LIANG Qi-chao
PENG Shu-xin1, PENG Yu-qing2
(1. School of Humanities,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Jiangxi 330013;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 011517, China)
, an important manuscript of LIANG Qi-chao, hasn’t attracted enough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ommunity since its publication in 1983. In fact, LIANG expounded Mencius’ philosophy of life in this long essay in which he constructed Mencius’ self-cultiv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theory of original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 This system has not only the metaphysical elucidation of human nature, but also the concrete development of self-cultivation. The main purpose of his interpretation is to guide his children’s specific practice. This essay also has an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modern people to improve their moral cultivation.
LIANG Qi-chao; Mencius; philosophy of life
B259.1
A
2095-9249(2020)01-0046-04
2019-11-0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7BTQ082)
彭树欣(1968—),男,江西莲花人,教授,博士(后),研究方向:梁启超研究、阳明学。
〔责任编校:吴侃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