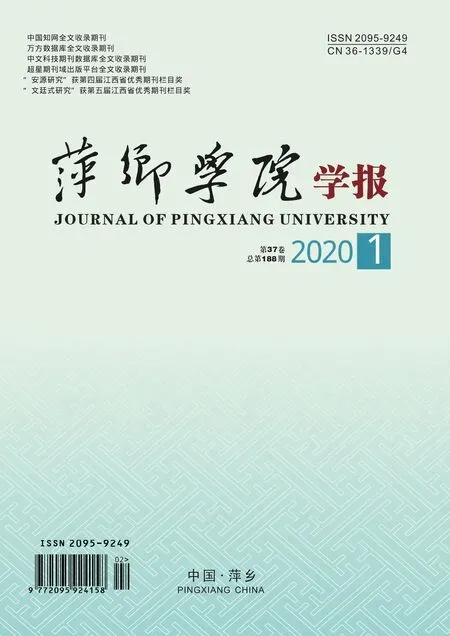略论民法典的制定对经济法的影响——围绕《民法典(草案)》总则编第一章展开
2020-12-19章光园林芳
章光园,林芳
略论民法典的制定对经济法的影响——围绕《民法典(草案)》总则编第一章展开
章光园1,林芳2
(1. 华东政法大学 经济法学院,上海 200042;2.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9)
相较于《民法通则》,《民法典(草案)》“总则”编第一章在公、私法界限的划定、“绿色原则”的确立、法律渊源的调整、法的适用安排等方面均作出了与时俱进的新规定。这些新规定、新变化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法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理念转变,强调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整体维护,总体上契合了经济法的内在理念与价值追求,必将对经济法未来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总则编;经济法;公、私法;“绿色原则”;法律渊源;法的适用
2019年12月23—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对首次“合体”成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进行了审议,民法典的出台进入倒计时阶段。职是之故,本文拟围绕草案总则编第一章“基本规定”章,具体分析民法典的制定对经济法产生的影响。之所以选择“基本规定”章作为分析对象,是基于该章的地位和重要性考虑。作为总则编的第一章,“基本规定”章可以说是总则的总则,虽然该章条文数量不多,一共只有12个条文,但其意义与价值却极大,集中体现了民法典的立法理念与价值追求,必将对经济法的未来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公、私法界限的划定
总则编第3条规定:“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本条规定明确了民事主体的权益保护,而且这种保护还是开放性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些新型的民事权益将会逐渐出现,需要在法律制度层面建立导入机制。而且,本条规定与近来反复强调的加强产权保护有着内在关联,本条的规定再次释放出强烈信号,私权(包括产权)神圣,任何人不得侵犯,这有利于经济社会稳定,有利于人心稳定,因为“有恒产者有恒心”。再次宣示民事主体合法权益保障,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当下,更有积极意义,更有利于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打造。
然而,虽然该条强调了对私权的保护,但是,我们认为,作为总则编的总则,本章仍然缺乏对于“公”“私”界限的明确划分,容易给公权侵害私权留下口子。顾功耘教授认为,“法治的思维需要战略思维,经济法治尤其需要战略思维。”[1]而“实施经济法治战略的本质要求是要用法治约束政府的权力,规范政府的经济管理行为,保证市场充分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2]为此,我们主张,应该在总则编“基本规定”章增加一条,“非因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不得干预民事主体的合法行为。”考虑不打乱条文编排序号,建议将该条作为总则编第3条第2款,以划清公法与私法的界限。
而且,关于这一点,总则编民事权利章第117条就有对应规定,该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征收、征用不动产或者动产的,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第130条规定:“民事主体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行使民事权利,不受干涉。”如此一来,“基本规定”章与“民事权利”章的规定就更好地相互衔接起来,做到了前呼后应。这实质也是划清公权与私权的界限,明确公权不能肆意干预私权。
二、“绿色原则”的确立
总则编第9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这即是“绿色原则”的规定,是总则编前身《民法总则》新确立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创举。“这是中国民法不同于境外民法的最大亮点,是中国民法对世界的贡献。”[3]101本条作为一般性宣示条款,属于一般规定,具体贯彻落实还需要其他实体法甚至程序法的配合。具言之,“绿色原则”的规定,是贯彻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对于环境法、能源法、公司法、税法甚至诉讼法等的未来发展都将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绿色原则”对环境资源法的影响
将“绿色原则”确立为“基本原则”,是环境法学界呼吁多年的结果。“绿色原则”作为环境资源法的上位原则,通过民法与环境资源法的分工配合,将对环境权的确立、修复生态环境规定、资源节约的规制、废弃物处分的规制、废弃物处置约定的规制、废弃物污染防治法等等产生重大影响。正如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关于民法总则草案的说明时提到的:“这样规定,既传承了天地人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又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发展理念,与我国是人口大国、需要长期处理好人与资源生态的矛盾这样一个国情相适应。”[3]422020年年初开始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肆虐,更加凸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极端重要性,而“绿色原则”的确立,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立法者的远见卓识。
(二)“绿色原则”对税法的影响
“绿色原则”的有效贯彻,需要激励措施配合,而税法是有效的调整手段。“绿色原则的确立对人类生存发展有重要意义,值得税收立法学习,也需要税收立法配合。”[4]“根治环境问题,适当的国家威慑力和约束力作为后盾必不可少。税法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中重要的领域法之一,应协调、补充民法的绿色原则,构建绿色税制。”[4]例如,关注生态文明建设,在资源税、消费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立法过程中加大对环保问题的调控力度,通过激励、引导、制裁等诸多调控手段,将“绿色原则”的理念真正贯彻落实到日常的生产生活中。
(三)“绿色原则”对公司法的影响
我国《公司法》第5条明确规定公司应承担社会责任。“由于现代经济活动中,公司的行为成为环境问题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研究公司应承担的环境民事责任,对保护自然环境,贯彻‘绿色原则’至关重要。”[5]“绿色原则”的确立,将进一步明确公司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内涵,有利于《公司法》第5条规定真正落地实施。而且,总则编第86条亦规定:“营利法人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守商业道德,维护交易安全,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可见,“绿色原则”的规定,必将进一步深化和丰富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对公司的市场竞争行为将产生重大影响。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意识、没有环境保护理念的公司很难赢得公众好感,也难以在竞争激烈的市场浪潮中生存发展下去。
(四)“绿色原则”对经济法实施的影响
本条作为一般性宣示条款,与诉讼法的规定遥相呼应,为公益诉讼的开展奠定了实体法基础。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5条、《行政诉讼法》第25条都明确规定了环境公益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均明确规定了环境公益诉讼。所以,总则编将“绿色原则”确立为民法基本原则,也有利于从基本法层面为环境公益诉讼提供法律支撑。基于公益诉讼的目的都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与经济法强调追求的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是相一致的,二者具有内在一致性,所以,我们认为,公益诉讼将成为今后经济法实施的重要手段与途径。
三、法律渊源的调整
总则编第10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本条规定了我国民法的正式法律渊源,与《民法通则》第6条相比,此条最大的变化就是删除了“国家政策”,增加了“习惯”,只是作了“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的限定。
(一)将国家政策从法律渊源中删除
总则编第10条来自于《民法总则》第10条。《民法总则》将“国家政策”从法律渊源中删去,不仅对民法未来发展影响很大,对经济法亦是如此,而且可能更多的是消极影响,故而部分经济法学者对此抵触很大,这也反映出不同学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存在很大误解与隔阂。
与民法学者对《民法总则》取消“国家政策”作为法源的做法普遍持赞同态度不同,史际春教授明确表达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政策和法律是交融的”,“政策与法本质上相同”,“在司法实践中,政策事实上发挥着实实在在的作用”,“与问责制融合的政策,还可弥补狭义法律的机械教条僵化,防止公权力主体被不必要且很容易规避的程序绑住手脚”[6]。我们认为,政策作为法源问题,还存在一个法律领域分布问题,在民商事领域,随着民法典的逐步编撰,法律体系日趋完善,政策作为法律适用的情况将会越来越少,即使适用,也往往与国家的宏观决策紧密相关,例如购买商品房时的限购限贷政策,而在经济法等具有较强公法性质的领域,政策作为法源确是大量存在的,这本身也是经济法一大特色,因为经济法很大程度上就是经济政策法。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史际春教授主张的“法的政策化与政策法治化”才更具有正当性。
实际上,在经济法领域,由于立法本身的滞后性,很多经济活动的开展,一开始并没有系统的法律进行规制,往往都是政府部门先制定有关政策进行指导,立法再慢慢跟上。例如,对于公私合作的PPP问题,一直都是靠相关政策调整,至今还没有制定一部专门的全国性法律。而且,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活动受外在影响因素增多,不确定性增大,而法律的制定、修改不能及时跟上经济变化的节奏,此时政策又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在经济法一些具体部门法中,例如竞争法,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等,政策也起着关键性作用。
在当前民法法典化的背景下,对民法的法源做出规定,有利于民法维护自身的地位,避免行政权力的侵蚀,同时也回应了司法实践的需求。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总则编中的法源类型应当保持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才能保证对执法、司法活动的有效制度供给。正如学者所指出的,“我国目前的民法法源规定几乎是最狭窄的。”“这种取消(指取消国家政策)虽响应了学者的长期呼吁,但是也减少了可资适用的法源类型。”[7]
(二)将习惯明确规定为法律渊源
作为总则编前身的《民法总则》将习惯增加为正式法律渊源,是吸收借鉴了《瑞士民法典》、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等的规定,也是对我国长期社会生活、司法实践做法的正式确认,值得肯定。社会经济法活动中,确实存在大量习惯,这些习惯事实上也发挥着法律规制的功能。例如,在金融法领域,习惯的规制功能就表现较为突出。当然,现代金融法领域,纯粹的不成文的习惯已经很少见,大量的习惯都已经表现为“自律规则”。“我国的银行业协会、证券业协会、基金业协会、保险业协会均制定了大量的行为规范。承认其在一定范围内的约束力和强制规范力,对于稳定金融秩序十分重要。”[7]由此可见,“习惯”对于现代经济活动的规制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四、法的适用安排
民法典的制定施行,涉及到与已有法律如何衔接适用的问题。对此,总则编第11条、12条作了相应规定,在确立了民法典一般法地位的同时,也为特别法的规定及适用保留了制度空间。
(一)特别法的优先适用
总则编第11条规定:“其他法律对民事关系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条是关于民事一般法与特别法适用关系的规定,是法的适用特别规定优先于一般规定的基本原则在民事领域的具体体现。一方面,由于我国实行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民法典之外,目前来看暂时不会再专门制定商法典,所以本条的规定为民事特别法包括商事单行法等的适用作出了指引。另一方面,民法作为市民社会基本法,对经济法亦有深刻影响。所以,此处的“民事关系”,不仅仅指一般意义上的狭义的民商事关系,还包括其他与社会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关系,例如税收法律关系、劳动法律关系等。
苏永钦教授认为,“民法典除了建构自治的原则,对于国家在各领域实施的管制也不能视而不见,因此立法者必须在法典内适当的地方架设通往其他法律领域的管线,甚至区隔主线、支线,从而把常态民事关系和特别的民事关系,把民事关系和前置于民事关系或以民事关系为前置事实的公法关系,连结起来。”[8]总则编第11条正是融通民法与经济法等相关部门法的“管线”,它在民法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越来越凸显。
(二)法的空间效力
总则编第1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条承认法律地域适用的一般做法,但没有否认例外存在,这为经济法等的特殊规定留下了制度空间。随着经济贸易全球化的发展,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越来越普遍,在具有涉外因素的情况下,可以适用对我国生效的国际条约以及相关国际惯例。同时,为了有效应对贸易欺凌和霸权,在遵守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在特定领域内,适当保留法的域外效力还是有必要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加快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我国《反垄断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济活动中的垄断行为,适用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垄断行为,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影响的,适用本法。”此即反垄断法域外适用规定,可以视为对总则编第12条规定的补充。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有极为严格的限制条件,必须是该境外垄断行为影响到了境内市场公平竞争,才有适用的可能。此外,我国《破产法》第5条规定:“依照本法开始的破产程序,对债务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财产发生效力。”这条规定也体现了法的域外适用效力。不过,总的来说,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体现法的域外适用、域外效力的条款并不多,这与美国所谓的“长臂管辖”不同,后者实质上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法律领域的表现。
此外,本章第1条规定的“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7条规定的“诚信原则”,第8条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都内含着维护和促进社会整体利益提升的立法目标,带有一定的公法色彩,与经济法的理念与追求存在内在一致性,必将对经济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但限于文章篇幅,此不赘述。
[1] 顾功耘. 经济法治的战略思维[J].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4,(5): 74~76.
[2] 顾功耘. 论重启改革背景下的经济法治战略[J]. 法学, 2014,(3): 3~15.
[3] 沈德咏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条文理解与适用(上)[M]. 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7: 101.
[4] 杨城, 刘剑文. 民法总则之光与税收的良法善治[N]. 中国税务报, 2017-3-29(B1).
[5] 潘素梅.“绿色原则”视野下公司环境责任法律完善[J]. 云南警官学院学报, 2017,(6): 120~123.
[6] 史际春. 法的政策化与政策法治化[J]. 经济法论丛, 2018,(1): 51~56.
[7] 贾翱.《民法总则》中二元法源结构分析及改进对策[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2): 51~56.
[8] 苏永钦. 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6.
Influence ofon the Enactment of Economic Law——Based on Chapter 1 of the General Rules of
ZHANG Guang-yuan1, LIN Fang2
(1. School of Economic law,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42;2. Jiangxi Tourism and Commerce Vocational College, Nanchang Jiangxi 330039, China)
Compared with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has made new provisions on the demarcation of the boundaries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law,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reen principle”, the adjustment of legal sourc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law. To some extent, these new regulations and changes refle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vil law from individual standard to social standard, emphasize the overall maintenance of social public interests, and generally conform to the internal concept and value pursuit of economic law, which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and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law.
general principles; economic law; public and private law; green principles; sources of law; application of law
D923
A
2095-9249(2020)01-0033-04
2020-02-14
章光园(1982—),男,江西铅山人,博士研究生,法官助理,研究方向:民商法、经济法及司法理论与实务。
〔责任编校:王中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