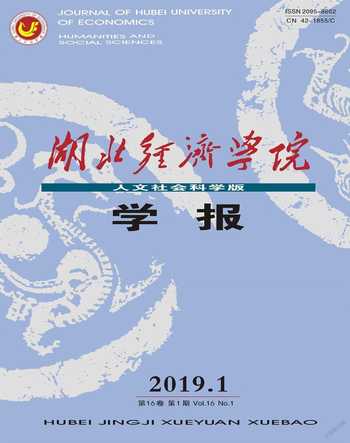外宣翻译的多维度“对等”
2019-09-10却正强陈志凌
却正强 陈志凌
摘要:“对等”一直是传统翻译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外宣翻译有着自身的特殊性,虽然它有着翻译的“共性”,但是更多的是自己的“个性”。考虑到外宣文本的特点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传统意义上的“对等”仍然是外宣翻译所要遵循的首要法则。外宣文本是一种实用文本,外宣翻译就要最大化体现这种实用性。外宣翻译不太追求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艺术性”和美学价值。它需要准确、简洁、精炼,没有“言外之意”,避免引起歧义,造成误解,从而使国外受众充分理解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信息,引起他们的积极回应和认同,达到交流的目的。鉴于此,可以从文化、语言、风格、读者反应等四个方面探讨外宣翻译所要遵循的“对等”,强调“对等”仍然是外宣翻译研究所要关注的重点,以期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参考。
关键词:对等;外宣翻译;读者反应
一、引言
“对等”长久以来一直是中外翻译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我国翻译话语中,有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玄奘的“五不翻”,严复的“信、达、雅”,以及近现代的“神似”、“化境”、“信、达、切”、“三美论”和“竞赛论”等等,这些说法从不同角度历时地论述了翻译的标准和目的等问题,体现了我国译论中根深蒂固的一种观点:即追求译文和原文在形式和内容上达到对等或者“忠实”,反映出了原文的地位高于译文,所以译文尽量以原文为参照。不管是直译还是意译,其最后的目的殊途同归,达到对等。在西方译论中,也有类似的观点。有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施莱尔马赫的“翻译的两种途径”,德莱顿的“翻译三分法”,塞弗瑞的“翻译六原则”,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奈达的“动态对等”和“功能对等”,韦努蒂的“异化”和“归化”,这些说法也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对等”,强调的是“等”(e-quivalence),即“等值”和“等效”。当然,由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后,新的翻译理论层出不穷,如描写翻译派、结构主义派、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在这些新的翻译理论影响下,译界研究的重点逐渐从原文转移到译文以及影响译文产生的种种外部因素,出现了对原文的“解构”,或者不再看重单纯译文对原文的“对等”,译本不再是对原文的亦步亦趋。这些新的理论拓宽了研究视野,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当然,它们关注的重点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翻译。相对于文学翻译的种种新理论来说,本文要讨论的外宣翻译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它和所有的翻译包括文学翻译有着翻译的“共性”,但是更多的是自己的“个性”。考虑到外宣文本的特点和所要达到的目的,本文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对等”仍然是外宣翻译所要遵循的首要法则。毕竟,外宣文本是一种实用文本,外宣翻译就要最大化体现这种实用性。换言之,外宣翻译不太追求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艺术性”和美学价值。它的侧重点应该是“表层结构”的“对等”,“深层结构”上涉及的不多。它需要准确、简洁、精炼,没有“言外之意”,避免引起歧义,造成误解,从而使国外受众(包括国内的外籍人士)充分理解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信息,以引起他们的积极回应和认同,达到交流的目的。鉴于此,本文将从文化、语言、风格、读者反应等四个方面探讨外宣翻译所要遵循的“对等”,强调“对等”仍然是外宣翻译研究和实践所要关注的重点,以期为我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参考。
二、文化上的“对等”
文化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它渗透在人类社会交往的各个层面,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当然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历史的积淀中所特有的文化内涵意义。外宣文本作为介绍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种宣传材料,必然涉及到具体的中华文化因子,这些文化因子体现了中国人长久以来形成的固化思维和认知世界的方式方法。但是由于人类的思维有某种程度的共通性,有些中华文化因子可以直译到英文中去,不会引起国外受众的误解。比如,“功夫”的英译为"Kung fu";“纸老虎”的英译“paper tiger”;“一国两制”的英译“one coun-try,two systems”;“光阴似箭”直接译为“Time flies like anarrow”,这些已经为英美人士所广泛接受。而“狗抓老鼠一多管闲事”也可直译为“A dog shouldn’t chase mice-that’s thecat's job”,相信也会得到国外受众的积极响应。但多数情况是特有的中华文化因子根植于特有的中华文化中,国外受众并不了解,或者由于中华文化在国际文化格局中长期的边缘化地位,他们不愿意主动去了解,如果直译只能引起误解。所以在“文化旅行”中,译者需要熟悉中外文化的不同所指和能指,做出某种变通,达到意义上的“对等”。在这里,我们可以说,翻译的重点是文化层面而不仅仅是文本。换言之“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1]翻译家许钧说:“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流活动。”[2]翻译家奈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3]巴斯奈特说:“如果把文化比喻成人的身体,那么语言就是这个身体的心脏,只有身体与心脏协调才能保持肌体的生机与活力。同样地,外科医生在给病人心脏做手术时,绝不能忽视病人心臟周围的身体状况。所以,译者从事翻译时绝不能把文本与文化隔离。”[4]以上各位译家的观点说明了文化意识的重要性,译者需要有翻译的文化观。可见,做翻译实践必须通晓不同的文化,有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在外宣翻译中也是如此。比如,我国白象电池的英译。在中文里,“白象”含有“吉祥如意”的意思,如果照字面意思译成“White Elephant”,语义信息对等了,但文化信息对等却很差。因为在西方国家里,“白象”给人的联想是“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因为白象比较尊贵,养在家里不干活),所以,将“白象”牌电池直译成“White Elephant”,恐怕消费者不会买账。与此相反的是,有一种外来的Poison香水,没有直译成“毒药”,而是根据其英语发音,译成“百爱神”,这样的译文让人感到该产品是好产品,反映出了香水这种产品的特点,达到了营销的目的。另外,众所周知,龙在中国文化里是吉祥富贵的象征,但在西方神话中,dragon(龙)却是邪恶的象征,这与中国人关于龙的想象完全不同。因此,在翻译经济上曾经高速增长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亚洲四小龙”时,不宜译成“Four Asian Dragons”,比较好的译文应该是“Four AsianTigers”,因为,tiger(老虎)在西方人心中是一种强悍的动物,至少不会让人想到某种可怕邪恶的动物。总之,外宣译者必须站在跨文化交流的高度,树立文化意识,提高文化因子识别的敏锐力,用文化思维来统领考量翻译实践。只有这样,外宣译者才能避免机械的看似字面对等,实则是误译和“假朋友”现象的发生,从而使译文和原文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对等,促使交流能够顺利进行。
三、语言上的“对等”
文化上的考量是宏观的形而上的,语言上的考量则是微观的和形而下的。语言的对等包括字、词、短语、句子等层面的对等。从实践来看,微观上的“对等”占据外宣翻译的大多数,因而语言上的“对等”应该是外宣翻译中的重中之重。我们说文化上的“对等”总览全局,但最终要落实到语言层面,通过语言上的“对等”达到文化上的“对等”。比如,上文提到的白象电池的翻译,不直译成白象,那该译成什么动物呢?译成白猫,白狗或者白虎什么的可以吗?翻译的文化转向后,需要有文化意识来统领翻译实践,包括语言上的对等。白象牌电池的英译可以用Lion(狮子)一词来表示,因为狮子在西方人眼里是强大有力的动物,这样的电池威力无比,自然大家都爱买了。如果在外宣翻译中最基本的语言“对等”做不到的话,那么翻译所要承担的使命就达不到。比如外宣翻译中的商务翻泽类,它一般不允许译者自由发挥,创造什么新奇的说法来彰显自己,或者是体现什么“创造性的叛逆”和“创造性的对等”。它所要的就是译者按照基本的文体特点和语言特点准确无误的传达原文的意思。特别是其中的法律文本更是容不得译者擅自删减和添加额外的材料,并且为了体现法律文本的严肃和权威性,一些约定俗成的古体英语还在大量使用.这就大大减少了翻译中误译的发生,从而避免纠纷等法律后果的发生。比如,“本合同自买方和卖方签署之日生效”,其英译为“This Contractshall come into force from the date of execution hereof bythe Buyer and the Seller”;另外,“本协议所规定商品的数量、价格及装运条件等,应在每笔交易中确认,其细目应在双方签订的销售协议中作出规定”,“The quantities,prices andshipments of the commodities stated in this Agreement shallbe confirmed in each transaction,the particulars of whichare to be specified in the Sales Confirmation signed by thetwo parties hereto.”可见外宣翻译中语言层面的“对等”容不得半点马虎,大多数时候直译是最好的选择,翻译家纽马克也主张直译,只不过有的时候译者需要对文字的表达润色罢了。
四、风格上的“对等”
简单地说,风格指的是不同的文体。诗歌等文学体裁的文本偏重于创造性和审美意识的启迪,在翻译实践中译者有较大的个人发挥空间来体现自己的翻译个性,即“创造性的叛逆”,因而是“阳春白雪”类的高雅品。而作为“下里巴人”的外宣文本和译本也是一种风格特点明显的文本材料。它们有自己的写作特点。它们的选词、造句、行文和谋篇都有一套既定的格式和要求。例如,“This contract is signed by and be-tween Party A and Party B","I’d like to draw your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等,这些译文都是外宣文本对事实的客观写照,不加任何渲染,体现出了明显的商务英语文体特点,并不体现出译者的创造性。那么在翻译实践中,我们说要最大化的传达意义,就不能不注意到风格的传递,因为风格已经成为了外宣文本内化的一部分。如果忽视了风格信息,译文就显得不得体。“语言好像服饰,不同的场合穿戴不同。不同的语言文体就像不同场合的服饰。”[5]比如,一句简单的公示语“请勿践踏草地”如果直译成“Don’t Stamp on the Grass!”显得生硬牵强,号召力不强。为了充分调动受众的积极响应,应该译成“Keep off the Grass,Please!”这体现出了西方社会中广泛的“礼貌原则”。还有一例,“为了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国需要进一步了解美国,美国也需要进一步了解中国”,其英译为“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U.S.relation-ship,China needs to know the United States better and viceversa.”显然,“美国也需要进一步了解中国”并没有机械地重复翻译,而是巧妙地译成“and vice versa”,这符合外宣译本的简洁和精炼的特点。上文提到的法律文本,其文体风格非常正式。它是书面语中最正式的文体。例如,“以下规定的每项款额需用美元支付”,其英译为“Each payment to be madehereunder shall be made in American currency.”以上例子都不长,但是原文的文体风格都较好地在译文中得到了体现,达到了交际的目的。
五、读者反应的“对等”
前面讨论的三种“对等”其实都有一个前提,就是要照顾到译文读者的实际阅读需求。为了达到交际的目的,我们会希望“译文读者读译文时所获得的感受应该和原文读者读原文时所获得的感受相同”,这其实就是“读者反应对等论”或者是“等效论”。翻译家奈达提出过“读者中心论”,强调的就是读者反应“对等”。应该说,一开始中外传统译论并不重视对读者的关注,其关注的焦点是原文和译文在形式和意义上的“对等”和“对应”,关注的是“作者”和“译者”,读者是被排除在翻译的主体之外的。后来,大家意识到没有读者的阅读和参与,译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最多也就是译者的“孤芳自赏”。在这样一种理念下,我们开始有了“作者,译者和读者”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意识。鲁迅先生在论述翻译时曾谈到了把读者分成“甲、乙、丙”三类,他说,“但我想,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将这些大众,粗粗的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q西方翻译理论家也开始关注到读者的重要性和作用。塞弗瑞提出了四类读者,即“第一类读者对原文一窍不通;第二类是学生,他们借助译本阅读原文作品;第三类读者过去学过原文语言,但现在已经忘记;第四类是学者,对所学语言仍很熟悉”。对读者的关注和译文的可读性有关,没有可读性便没有最广泛的读者参与,因而译本就不会有市场和价值。现在我们回头看当时严复和林纤的翻译也就知道他们之所以“归化”翻译甚至是改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照顾到当时中国读者的实际,为了可读性他们部分地牺牲了准确性。因此有学者说,可读性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准确性[7]。在中华文化外宣翻译中提出可读性是因为我们面对的严峻现实是:虽然中国已经融入世界一體化格局中,经济地位持续上升,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也远非昔日可比,但在世界文化格局中,中华文化依然处于边缘化和小众化的地位。中国翻译年鉴2011-2012中指出,“截止到2011年年底,在世界文化市场的格局中,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家所占比重依次为43%、34%、10%和5%,中国仅为4%,位列第五”。面对这样一种窘境,外宣译者深感责任重大。现在几年过去了,中华文化的边缘化地位也应该不会有大的改观。在这样的现实中,我们寄希望于国外的汉学家来扭转这样一种不对称的局面应该是不现实的。的确中国的事还是主要靠中国人自己来办。针对这一点,余光中说,“汉学英译,英美学者已经贡献不少,该是中国学者自扬汉声的时候了。”伟按照韦努蒂的说法,由于西方读者被惯坏了,他们已经习惯于阅读过度“归化”的译本,因此,我国外宣译者不得不要照顾他们的阅读需求和期待,否则我们再怎样追求用原汁原味的“异化”译本来传播中华文化,但是西方读者并不买账,那我们只有碰一鼻子灰。想到外国产品和文化进入中国市场时,都有很好的包装和营销策略,也就是充分满足中国受众的需求,比如“可口可乐”在中国的巨大成功。我们也不妨学习国外的做法来向国外推介中华文化。的确,既然可用“糖衣”向中国输入外来文化,我们何不也裹着“糖衣”向外输出我们的本土文化?当然,在中华文化与国外文化的互动加深中,我们可以逐渐增加原汁原味的中国英语。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外受众会越来越对古老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感兴趣,他们也会越来越接受“异化”的英译中华文化。一定程度的异国情调,译入语读者会接受也会欣赏的,这是我们的良好期待和愿望。但就现实来看,还得以“归化”为主,也就是体现出译本的可读性,即照顾到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期待。比如,“赔了夫人又折兵”这则含有中华文化底蕴的说法如果直译,要加上一大堆的解释才会让国外受众明白,这增加了他们的阅读负担,而他们并不一定感兴趣,因而可读性不强,所以可以简单的译为“a double loss”,即简洁又达意,何乐而不为呢?还有,“我们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一般的译者很可能会绞尽脑汁地想怎样直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与其这般吃力不讨好,不如译为“The 56 ethnic groupsshare the same lot”。译文中的划线部分很好地解决了这个翻译难题,关照了西方读者的阅读需求。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总之,译者要研究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和阅读要求,要有说“全球话”的思维,增强译文的可读性,从而把握国际话语权,实现中华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弯道超车”。毕竟,外宣文本的英译在当下的现实中不是只针对某一特定人群,而是要最大化的扩大西方读者群,等到他们对中华文化变得耳熟能详的那一天我们就可以加大“异化”译本的生产。让我们期待这一天尽快到来!
六、结语
“对等”作为翻译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各种新的翻译理论层出不穷背景下,说服力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有被进一步打压的可能。但是在追求实用主义的外宣翻译中,“对等”理论将继续发挥理论的统领作用,并且在实践中将一直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希望外宣翻译以“对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8):18.
[2]许钧.从翻译出发——翻译与翻译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6:140.
[3]Nida Eugene A.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109.
[4]Susan Bassnett.Translation Studies[M].Lon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0:14.
[5]翁凤翔.当代国际商务英语翻译[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68.
[6]罗新璋.翻译论集(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6):345-346.
[7]孙艺风.翻译与跨文化交际策略[J].中国翻译,2012,(1):16.
[8]余光中.翻译乃大道[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1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