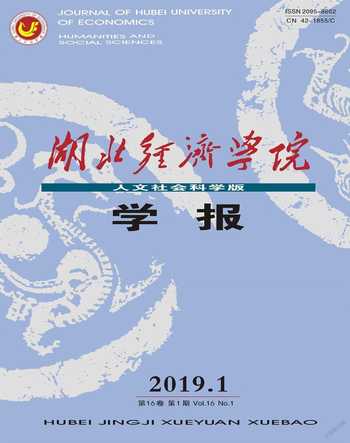哲学理性视野下对“动物权利”的思考
2019-09-10王璐赵昆
王璐 赵昆
摘要:“动物权利论”是西方环境伦理学中的重要理论之一,主张动物与人类一样享有不可被剥夺的权利,应该得到人类的尊重和道德关怀。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直存在着有关“动物能否享有权利”的争论,其中一部分哲学家认为动物不具有理性,只是被人利用的工具,只具有工具价值而不能享有权利。另一部分哲学家则认为动物具有同人类一样的“理性”能力,因此与人类一样平等地享有权利。从哲学的角度出发,权利的获得始终与理性密切相关,而通过从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三个角度对“理性”概念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动物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理性”能力,因此动物不能够享有权利。动物权利论的提出,虽然使动物保护获得了更多关注,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动物保护面临的困难,而且动物权利论自身的实现过程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因此“动物权利论”的提出更多的只是一种口号上的意义。
关键词:理性;权利;动物权利;动物保护
一、问题的提出
“动物权利论”是西方环境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第三次环境保护运动之后。其基本观点是:动物与人类一样,享有不可被剥夺的权利,应该得到人类的尊重和保护,人与动物的关系也适用于原本只属于人类之间的道德。在今天,面对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人们对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关系进行了更加深人的思考,动物保护已经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对动物进行人道主义的保护,实现人与动物和谐共处也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动物权利论”的提出虽然是以保护动物为出发点,但其合理性依旧引发了人们的深刻思考。
“动物能否享有权利”一直是西方哲学界思考的重要问题,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梳理思想史可以发现,西方哲学家以“理性”为出发点,认为理性能力是获得权利的基本前提,由此形成了关于“动物能否享有权利”的两种基本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动物不能够享有权利,因为动物不具有理性能力。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们普遍支持这一观点,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学派都将“理性”视为人类所特有的区别于动物的一种本质,只有“理性”的人类才具有自身的价值,才能够享有权利,而不具有理性的动物则没有权利可言。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非理性的动物为人而存在的……大自然是为了人的缘故而创造了所有的动物。”[1]不具有理性的动物,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只是成为人类的工具,这就为人类利用动物提供了理论支撑。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和近代唯理论哲学家笛卡尔继承了古希腊哲学家的观点,坚持动物不具有理性,且明确否定动物享有权利。他们认为动物只是供人类使用的工具,人类利用动物是正当的,动物没有权利可言也无需得到人类的道德关怀。阿奎那直言利用动物是合法的,人类无需爱护动物——“动物是为人而存在的,它们没有理性,与人不是同类;取用动物是合法的,博爱不涉及动物。”[2]笛卡尔把人的肉体和不具有理性能力的动物比喻成机械运动的机器,认为机器是没有权利可言的,而人类之所以能够获得权利,则是因为人类实现了肉体与理性灵魂的结合。笛卡尔进一步指出,即使动物拥有权利,也只不过是被人类利用的权利,人类对动物不负有道德责任。理性主义是康德道德哲学最鲜明的特征,康德把理性视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作为理性存在物,能够“为自己立法”——制定道德法则,人既是立法者也是守法者,既能制定道德法则又能自觉地遵守道德法则。然而动物并不具有理性,既不能制定又无法自觉地服从道德法则,因而不能被纳入到道德体系之中并享有道德权利。同时康德认为动物只具有作为手段的价值,因此人对动物只有间接的道德义务。但是由于人类对动物的态度会影响到人类之间交往的态度,因此人类应该友善地对待动物。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他们都把理性视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与动物的关系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动物不具有理性,它们只是被人类利用的工具,并不能够不享有权利。
另一种观点认为动物具有与人类相同的理性基础,因此动物与人类一样平等地享有权利。早在古希腊时期,泰奥弗拉斯托斯就明确指出动物具有一定的推理能力,柏拉图也认为动物与人类一样都有灵魂,因此动物也具有理性。后来,哲学家休漠更是直言:“最明显的一條真理就是:畜类也和人类一样赋有思想和理性。”[3]这些哲学家的观点为“动物权利论”奠定了思想基础,正因为动物具有理性能力,因此能够与人类一样享有权利。与此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许多科学研究表明动物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有记忆也有目标,为动物具有理性能力提供了科学依据,部分现代西方“动物权利论”的倡导者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动物与人类一样享有权利。亨利·萨尔特、汤姆·雷根和弗兰西恩都坚持,动物与人类都具有理性能力而没有质的区别,动物享有权利也应该得到人类的尊重,人与动物的关系同样适用于人类的道德。萨尔特曾说:“认为动物生命没有任何道德目的的思想……是同我们的本能常识、当今科学相违背的。我们必须摆脱那种古老过时的认为人和动物之间有着巨大鸿沟的观念……”[4]同时萨尔特强调只有部分高级的动物才能获得权利,因为科学证明只有高级的动物才具有的理性能力和自主意识。汤姆·雷根认为动物与人一样,既能够感知到快乐和痛苦,也具有记忆、思维和认知等能力,人与动物都是能够获得权利的“生命主体”。继雷根之后弗兰西恩提出,很多认知行为学家已经证明了某些动物也有认知能力和自主意识,其实并没有某一种特征能够被视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所谓人类特有的理性能力在动物身上也有所体现,而那些用来说明动物低于人类的缺陷,最后也都能在人类身上找到。
基于上述关于“动物能否享有权利”的两种争论,笔者发现在西方哲学史上,许多哲学家都把权利的获得与理性能力联系在一起,认为“理性”是获得权利的基本前提,动物能否获得权利的关键在于动物是否具有理性能力。因此,要想得出关于“动物能否享有权利”这个问题的科学结论,必须深入研究哲学中的“理性”概念,并结合实际情况考察动物是否具有理性能力,由此来判断动物能否享有权利。
二、哲学中“理性”的内涵
从词源上来看,“理性”(reason)最早起源于希腊语中“λoγoS”(逻各斯)这一词语,在罗马时期被翻译为拉丁语“ra-tio”,原意是计算金钱。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理性”概念受到了哲学、政治学、文学、法学以及经济学等不同领域的思考和解读。通过梳理思想史可以发现,“理性”是贯穿于西方哲学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不同历史时期的哲学家对“理性”做出的解释各不相同,反映出不同时代背景下人们对理性概念的认知程度和水平。思想史上对“理性”概念的不同解读,给当今学术界对“理性”概念的研究带来了不少难度。今天,许多学者认为对哲学理性概念的研究,应从多视角、多层次来进行,由此才能形成对“理性”这一概念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例如学者胡敏中[5]提出“理性”可以从意识论、认识论和人性论这三层意义上来解释——意识论层面的“理性”是指包括人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内的受人的意识支配的全部主观心理活动;认识论层面的“理性”是指人类所特有的够认识事物的本质以及事物发展的科学规律的逻辑思维形式;人性论层面的“理性”是指人类在逻辑思维能力支配下理智自觉的、节制克制的存在属性。学者张雄[6]则提出对哲学“理性”的理解应从认知理性、实践理性和评价理性三个角度深入。他把认知理性解释为一种人类所特有的能够把握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运用概念和推理判断的思维能力以及能够运用规律来预见和规划未来实践活动的能力。把实践理性解释为人类特有的一种能够规范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审时度势并且能够进行自我否定和变革的实践意识和审慎精神。把评价理性解释为人类运用理性逻辑来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并对自身行为的目的、过程以及结果进行价值评价的能力。还有学者张澜n队本体论、认知论、伦理观以及实用性四个方面来界定“理性”,本体理性产生于人类探索世界的始基和本源的活动中,并认为世界的本质是合乎理性的,是可以被人的理性所认识和发现的;认知论理性具有功能性和实体性两个层面的含义,功能性是指理性是人类的一种认知能力.人凭借理性就可能认识世界.实体性是指这种能力是上天赋予人类的,是人的本质属性;伦理理性则把理性的内容定义为包括真理、公平正义以及至善等在内的价值取向,伦理理性表现为对道德真理的全部占有;实用理性强调理性的特性是实现最有效的行为选择的手段,理性只有在产生具体的实用效果和功利之时才具有价值。通过上述关于哲学理性的界定,笔者发现从多个角度对哲学理性的内涵进行分析是必要的,能够对理性形成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在笔者看来,对哲学理性的理解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三个角度进行。
(一)本体论理性
作为本体论范畴的理性的提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希腊时期的自然哲学家们展开了对世界的本源的思考,并提出了Logos(逻各斯)和Nons(奴斯)等概念。当时Logos(逻各斯)和Nons(奴斯)都有“理性”的含义,赫拉克利特把“逻各斯”解释为宇宙万物永恒的运动和变化的规律,他曾界定说:“理性不是别的,只是对于宇宙的安排(结构)的方式之阐明。”[8]阿那克萨戈拉把“努斯”解释为一种与“种子”一起构成世界本源且独立于事物之外的,能动而绝对的本质。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以及阿那克萨戈拉的“努斯”,都被看作是世界的本源和事物运动的规律。斯多葛学派坚持自然哲学家们的观点,把“理性”(逻各斯)解释为万物的始基、上帝和人的本质,并且强调从伦理角度来看人的美德就是“顺应理性”、“顺应自然发展的规律”。简单来看,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们大多都将“理性”视为世界的本源以及人的本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
(二)认识论理性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理性”是人类最高层级的認识能力,是能够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本质以及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古希腊埃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是把“理性”概念从本体论引入到认识论的开创者,他曾说:“决不能证明非存在存在……要用你的理智(logos)去解决我告诉你的这些纷争。”[9]在巴门尼德看来,感官和感觉是骗人的,只有通过理性才能分析和认识万物的始基和事物的本原。由此可见理性是一种认识能力,是一种能够认识万物本原的能力。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将“理性”看作是人类所特有的能够认识世界本质的能力,是人的德性的表现。柏拉图将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理念世界,只有理念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而只有人的理性才能企及和认识理念世界。同样,柏拉图也把理性定义为认识真理的能力,而这一能力只属于人类灵魂的理性部分。亚里士多德将古希腊时期的“理性主义”发展到了顶峰,他把理性划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所谓理论理性就是一种认识论理性,是对必然是的事物或者事物的本性进行思考的能力,是一种认识事物本质的能力。
古希腊时期的理性主义被后代西方哲学家继承和发展,近代唯理论哲学的开创者笛卡尔提出“理性”是人的思想,是一种能够辨别是非的能力,理性思考是人们发现真理的唯一途径,世界上存在的所有事物,都必须用理性的标准和尺度来校正,因为只有理性才能确定事物存在和发展的逻辑规律、才能指明事物存在必然性和科学性。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使人们对理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康德将认识论范畴划分为“感性一知性一理性”三部分,明确指出“知性”和“理性嘟是一种逻辑思维的能力,“理性”是最高环节的认识能力,是能够认识“本体”的能力。康德还把理性看作是人的本质和道德价值之所在.正是基于理性人才能够做到意志自律.才能既为自己立法的又能自觉遵守道德法则。与康德类似,黑格尔也将理性视为人类认识的最高阶段和最高能力,是能够把握事物内在的对立统一以及发现“绝对精神”的认识能力。
(三)实践论理性
实践论理性是把理性解释为一种人类所特有的,能够指导人类实践活动的思辨精神。实践论理性是马克思在对西方理性主义哲学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西方哲学史上,实践论理性总是与道德哲学相联系,人类只有运用理性才能实现道德上的自由,人的德性是一种理智和智慧的体现。最早,苏格拉底就明确肯定“理性知识在人的道德行为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就在古代希腊以至整个西方哲学中首次建立起一种理性主义的道德哲学”[10],这是实践理性的一种体现。后来亚里士多德把理性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两个部分,实践理性是指人可以运用理性来处理生活和交往中的事务,实践理性的德性就是明智,“明智是沟通伦理和理智的桥梁,它们的关系是明智以伦理德性为本原,伦理德性以明智为准绳。”[11]亚里士多德还强调人能够理性的做出行为选择,人类的理性是区分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志。十八世纪,康德撰写了《实践理性批判》,并指出理性不仅是一种最高的认识能力,同时它也是一种实践能力,正是因为这种实践能力,人类才能够实现意志的自由。也正是因人类具有理性,人才能够为自己和全人类立法——确立行为准则,并且能够自觉遵守准则,成为道德的人。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实践理性观是西方哲学史上“实践理性”的思想源泉,不仅对西方实践理性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为马克思实践理性的提出提供了借鉴。
马克思所说的实践理性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所谓现实的人是指具有社会性的人,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的实践理性具有两方面的含义。首先,理性是实践的理性。所谓“理性”,它被视为一种人类所特有的能力,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主体性”的能力。“理性”能力的形成是漫长的,是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变化和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其次,实践是理性的实践。实践是人类的“主体性”行为,人类的实践活动总是在理性的指导之下、根据理性所认识的客观规律和科学方法进行的实践。人类实践的目的是在理性的指导之下认识和改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马克思认为只有人类才具有实践理性,正如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12]由此看来,动物并不具有这种实践理性。
三、不具有理性的动物不享有权利
通过对哲学“理性”概念的梳理,可以发现理性始终与人类相联系,理性是人类的理性。从本体论理性来看,理性被视为世界的本源和人的本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从认识论理性来看,理性是人类所特有的最高层级的认识能力,只有理性才能认识世界的本源和事物发展的规律;从实践论理性来看,实践理性是人类所特有的,理性能力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只有人类才能够运用实践理性来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然而很多学者认为动物也具有理性能力,并指出许多科学实验和真实案例都能够证明。例如大猩猩可以使用简单的工具;某些哺乳动物具有一定水平的智商,犬类经过训练可以从事导盲工作,猴子、黑熊等能够学会骑自行车;美国心理学家戈尔敦·格朗通过镜子实验测试出黑猩猩能够从镜子中认出自己,说明黑猩猩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然而通过上文中对理性概念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动物具有理性能力”这种观点并不科学。首先,从本体论理性的角度看,自“逻各斯”和“奴斯”这两个概念提出以来,它们就被视为世界的本源和事物发展的规律,从斯多葛学派开始,理性被视为上帝本质,而上帝只把理性赋予了人类,理性由此也成为了人类的本质。但是思想史上却没有思想家将“理性”视为动物的本质。其次,从认识论理性来看,理性被视为一种最高级的认识能力,是能够认识世界的本源和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虽然有的学者和科学家能够证明动物具有一定的认识能力,但是动物所具有的认识能力是低水平的,它们并不能够认识世界的本质,也不能够归纳总结出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它们也许能够认出镜子中的自己,却不能够掌握镜子反射影像的原理。最后,从实践论理性来看,虽然有的动物能够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能,但是它们并不能够运用掌握到的知识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实践,不能够进行理性的实践活动,他们通过训练所获得的技能实质上只是一种动物本能的条件反射,如果停止训练这种反射也会随之消失,而人类的实践理性一旦建立起来是永远不会消失的。综上所述,动物并不具有真正的理性能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民主与法制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权利”作为“善”与“正义”的代名词频繁地出现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一时间似乎任何能够体现正义、公正和善的诉求都可以通过“权利”的获得来实现。因此动物权利论的倡导者也将动物保护的实现寄希望于诉诸“动物权利”。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权利”的获得是有前提条件的,即便是最基本的“人权”也不是生来就有的。而“理性”能力是正是获得“权利”的必要條件,“权利”的获得始终与理性密切联系在一起。首先,自权利提出以来,理性就被视为权利的正当性基础。正如霍布斯所强调的:必须取得理性的认同权利才具备正当性。其次,理性是权利实现的根本保证。道德规则不像法律条例那样具有强制性,因此道德权利的实现需要依靠理性人的自觉。黑格尔也指出权利的实现需要三个条件:意愿的表达、对物的占有和他人的承认,他坚持理性对权利实现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只有理性才能实现这三个条件。最后,理性的至上性决定了权利的至上性。在道德哲学的发展中“自然法”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人生而就有的且寓于人的理性之中,凡是理性的人都自觉地受其支配,同时它也是永恒不变的,即使上帝也不能将其改变。人类的理性决定了自然法的至上性,正如格劳秀斯所言“由于这种性质的自然法不仅与人类法而且与成文的神法也不相同……自然法能禁止人们去做非法的行为,支配人们去做必须履行的行为。”[13]而至上的自然法正是为了维护人的自然权利,由此可以推导出道德上权利具有至上性,也就是说在人类生活中,权利是正义的、至高无上的,它既符合人的理性又受到自然法的保护,高于法律权利。“权利”的获得是以理性能力为前提条件的,人类之所以能够获得道德和法律上的权利,是因为“理性”是人之为人的本性,人类天生就具有获得“权利”的理性能力,而动物却并不具有获得权利的必要前提条件——真正意义的“理性”能力。
在这里,部分“动物权利论”的支持者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理性”并不是获得权利的必要条件。因为现实中享有权利的人并不都是“理性人”,人类群体中存在着一部分如刚出生的婴儿以及植物人、智力低下者等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理性能力的人。他们与动物一样,并不能够认识世界的本源和事物发展规律,也不能够运用所学知识来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但是这部分不具有理性的人类群体却同样能够获得与“理性”人一样的权利,由此我们同样有理由赋予动物同样的权利。事实上,“动物权利论”的支持者只是忽视了“理性”始终是人类的本质这一关键问题。尽管一个婴儿暂时并不具备获得权利和行使权利的理性能力,但是“理性萌芽”自其出生起就根植于他的内心之中,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其理性能力会不断完善;而植物人、智力低下者只是因为各种不可抗力而导致其理性能力的丧失,其潜在的理性能力仍有恢复的可能性,“理性”始终是其作为人的本质。因此,我们无法因为婴儿以及植物人、智力低下者等不具有理性能力而将其与动物等同起来,并由此赋予动物与人类一样的权利。权利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人类运用理性能力,在理性的实践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入,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涉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样的观点自然是非常古老的。但是近代的平等要求与此完全不同:这种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性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贫乏等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入,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该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14]简单来说,人——无论是“理性”的人还是不具有理性能力的人,都享有道德权利,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都属于人类社会中的一员。
在笔者看来,“动物权利论”的提出是为了应对和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出现的生物多样性不断减少、虐待和杀害动物等问题,其目的符合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需要,应该得到支持。但是笔者认为,动物保护的实现并不依赖于对动物权利的诉求,盲目地宣称动物拥有与人类一样的权利,并呼吁从道德和法律上确立其权利主体的地位,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动物权利要在社会生活中真正地付诸实践也会面临许多不可避免的困难。首先,因动物与人类具有同样的理性基础而赋予动物权利,这样的观点不仅降低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也使得人类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尊严。达尔文的进化论说明人类是由动物进化而来,但是由于自然界充满了优胜劣汰的竞争,自然界的生物由此划分为不同的等级,而人类则处于生物链的最顶端,是万物之灵,人类所特有的崇高的“理性”正是人类高于动物的根本原因,恩格斯也把理性的人类比喻成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15]正因如此,如果承认动物也有理性,就抹杀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差别,从而降低了人在自然界生物种群中的地位。当人类与其他动物除了外形的不同而不再具有质的区别的时候,人也就丧失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其次,如果要赋予动物权利,就必须解决“哪些动物具有权利”以及“动物具有哪些权利”的问题。然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动物权利论”的倡导者们各持己见,雷根认为一岁以上精神正常的哺乳动物能够享有权利,而玛丽沃伦则认为所有具有感知(感觉快乐与痛苦)能力的动物全部拥有权利。雷根将动物具有的权利限定为生命和身体不被伤害,自由不被干涉的权利;玛丽沃伦则认为动物具有的权利是不受痛苦,享受快乐和生存的权利;而詹姆斯·理查尔则提出动物也拥有财产权这类复杂的权利。这些不同的回答,很难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让动物权利的实现之路变得更加崎岖。由此不难看出,这些争议使得倡导动物权利并不能够成为实现动物保护的最佳途径。
四、反思与展望
由于动物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理性能力,因此不能与人类一样平等地享有权利。但是动物不享有权利并不意味着动物不需要人类的保护。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虽然动物不能够成为道德权利的主体,但是这并不妨碍人类对动物进行道德关怀,并不妨碍人类尊重和保护动物,正如康德所言,由于人类对待动物的态度会影响到人类之间交往的态度,人类能否履行对动物的间接义务也直接影响到人类之间道德义务的履行,因此人类应该友善地对待并保护动物。圣雄甘地也曾说:“从一个国家对待动物的态度,可以判断这个国家及其道德是否伟大与崇高。”[16]当前,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和自然界生物的多样性,构建生态文明,促进全人类的持续健康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共同使命,动物保护势在必行。事实上,尊重和保护动物不仅仅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更是人类道德文明进步的一种体现,从道德义务论和美德论范畴都可以为动物保护找到合理性支撑。
首先,从道德义务论中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来看,由于动物不能够履行道德义务从而不能够成为享有道德权利的主体,但是这并不妨碍动物获得道德客体的地位,不妨碍动物成为人类进行道德关怀的对象。现代入类中心主义认为,从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关系来看,对动物进行道德关怀实际上是人类应该履行的一种间接的道德义务,其根本目的是尊重与保护人类自身的权利。其次,从美德论的范畴来看,善良、仁爱是人类的美德,人类的美德是出于人的善良意愿,它无需像权利一样得到相应的回报。而人类的美德要求人们应该仁慈地对待和关爱弱势群体以及生物圈内全部的生命个体。因此,对动物的尊重与保护来自于人类的美德,而并非是因为动物享有道德权利。
事实上,动物的命运掌握人类手中,动物保护的实现,并不依赖于动物能否获得道德和法律上的权利,而在于人类对人与动物关系的科学认识,在于人类能否认识到动物对整个自然界和人类自身发展的重要作用。虽然“动物权利”不能成为人类保护动物的理由,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其他方面出发为“动物保护”进行辩护。笔者认为,麦金泰尔提出的——“人的脆弱性与依赖性”这一观点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麦金泰尔在《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为什么人需要德性》(DependentRational Animals--Why Human Beings Need Virtue)一书中提出,人类之所以需要道德是因为人的动物性的基本状态——脆弱性与依赖性。正是由于人类生命的脆弱性以及人类生存的依赖性需要,使得人类只有在具有德性的状态下才能实现和谐的共处。由此我们可以找到人类尊重和保护动物、对动物进行道德关怀的理由,那就是“人的脆弱性与依赖性”。人类的生命是脆弱的,人类的生存需要依赖他人、社会和自然界,自然界中的所有动物都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正是因为这种依赖性,才需要人类对自然界和动物进行保护,需要人类对动物进行道德关怀。介于篇幅有限,在这里笔者不对“动物保护”的理由和实现展开详细的论述,但是总而言之,动物保护的关键不在于“动物权利”的实现,而在于改变人类的观念和规范人类的行为。我们要做的是加强宣传和教育,让人们对保护动物在保证自然界和人类永续发展以及促进入类社会道德水平不断提高等方面产生的积极作用形成深刻的认识,呼吁人类主动承担道德义务,切实加强动物保护。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3.
[2][澳]彼得·辛格,[美]汤姆·雷根一动物权利与人类义务[M].曾建平,代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
[3][英]休谟.人性论(上册)[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01.
[4]曹菡艾.动物非物——动物法在西方[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31-132.
[5]胡敏中.论非理性因素的个体发生[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3):89.
[6]张雄.哲学理性概念与经济学理性概念辨析[J].江海学刊,1999,(6):84.
[7]张澜.理性的界域[J].社会科学辑刊,1994,(2):24-29.
[8][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315.
[9]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632.
[10]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434.
[11][古希臘]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9.
[12][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74.
[13][荷]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M]//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139.
[14][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4.
[15][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4.
[16][美]彼得·辛格.动物解放[M].祖述宪译,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封底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