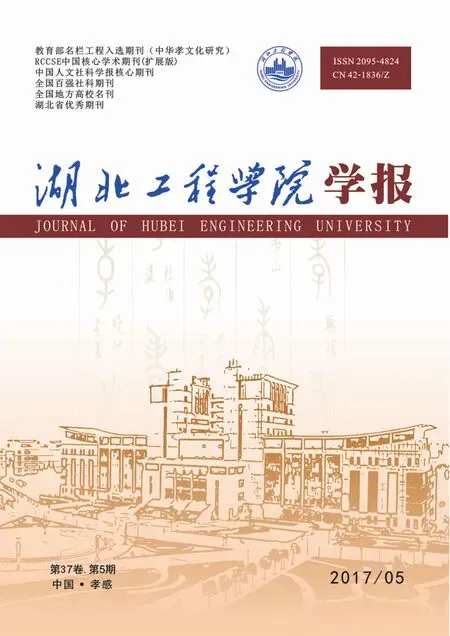论“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法律庭审语言发展的启示
2017-03-09马丽娅
马丽娅
(长治学院 法律与经济学系,山西 长治 046011)
论“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法律庭审语言发展的启示
马丽娅
(长治学院 法律与经济学系,山西 长治 046011)
我国的法律语言学研究一直处在世界相关研究的较低层次,很难有中国特色的重大研究成果出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法律语言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研究视角,沿线国家间法律语言的选用问题必将是我国将来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势必对司法领域的语言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语言学的角度探究司法领域中语言学家的作用,法庭口译在未来庭审中的发展方向,从法律文化的角度诠释中国法律语言的特点,增强各国间的文化交流和沟通,完善中国法律制度建设,减少各国因文化不同而引起的法律纠纷,对于加强和深化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国家贸易联系,同时促进法律语言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庭审话语;法庭口译;法律文化
“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一种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该政策一经提出便受到沿线国家的热烈欢迎,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从“引进来”迈向了“走出去”的新阶段。实现“一带一路”的建设目标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其中,法律是最重要的保障之一,“法律外交可以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建构国际法制秩序的中国话语体系”[1]。纵观西方法律语言学的发展,其研究重点已经从专注于语篇特点的立法领域转向专注于语音识别、法庭口译等的司法领域,法律语言学研究逐步与司法实践相结合,其中具代表性的例子如Fishman 通过分析录音对话间接为法庭提供证据[2];Cotterill 凭借语言学家的身份屡次帮助辩护律师找寻证据,出庭作证。[3]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发展,沿线国家间法律语言的选用问题必将是我国将来法制建设与研究的重要内容,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势必对司法领域的语言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国与各国在司法领域接触机会增多,对中国了解各国法律文化提供了机会,也促进了本国法律语言学家对庭审语言的研究,丰富了目前该领域比较匮乏的法律语言学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试图从国际法律语言学研究的视角,尝试探究语言学在司法中的应用,分析庭审中的法庭口译发展现状及前景,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机会了解与借鉴各国法律文化,完善我国法律制度建设。
一、国内外法律庭审语言研究现状
近几十年来,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们从法律本体已经发现了大量的数据资源进行他们的学术研究,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法律语言的研究跨学科性和挑战性。他们开始探究其中的语言问题,其中法律语篇成为了社会语言学家、语篇分析学家、翻译学家等最感兴趣的研究热点。
西方的法律语篇分析主要围绕庭审对话,而相对忽视其他法律领域中的各种语言现象。律师与证人间的质询、警官与犯人间的讯问,庭审过程中的话轮的转换等等都是目前西方语言学家们热衷研究的问题。因此,他们对权力的研究很自然地就集中到司法过程中参与者的身上,如法官、律师、证人、警官和犯人等。这种动态性的研究使得权力体现的过程更直接、更透明。在西方有很多研究法律语言的学者如梅林科夫(Mellinkoff)、梯尔斯马(Tiersma)、吉本斯(Gibbons)、古德里奇(Goodrich)、康力和奥巴尔(Conley and O’Barr),其中康力和奥巴尔将目前法律语言的研究分为三个基本类型:语言作为对象(language-as-object),语言作为过程(language-as-process),语言作为工具(language-as-instrument),这三个类型也是语言研究的三种方法。[4]
第一种类型研究主要集中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研究法律和语言的学者绝大多数研究的是书面语言,特别是各种法条和其他法律文件中所使用的语言。1963年,戴维·梅林科夫出版了一本在该领域具有纪念意义的著作,即《法律语言》。在书中他总结了法律语言的九大特征,分析了书面法律语言的结构,指出法律语言的四大怪僻(冗长,含糊,华而不实,呆板),主要也是从法律语言的词汇方面出发的。[5]在这样一个从静态的角度研究法律语言的阶段来说,梅林科夫贡献非凡。另外一位值得一提的语言学家是梯尔斯马,他在文章“法律的文本化”中归纳出书面法律语篇的两大重要地位:第一,书面法律语篇被推定为其制定者交流意图的清晰完整的表达;第二,书面法律语篇便于相对字面或去语境化的被进行解释。梯尔斯马还指出,格式化或者仪式化的内容和结构便于我们清楚地识别所写材料,使我们确信这就是我们旨在完成的。此外,同梅林科夫对法律语言细致深入的描写相比较,吉本斯的《法律语言学》罗列了一些语言和法律问题,可以被视为对法律语言学的概括性的研究。
第二种类型涉及对法律语言的动态研究,诸如法庭会话,庭外审讯等都是研究的热点。越来越多的学者曾被该种语言现象所吸引,试图为人们的辩护方式提供佐证。奥巴尔聚焦于“在律所,警局和全国各大法庭每天都要上演的微型剧场。几乎每个微型剧场的核心成分就是语言”[4]。有权力一方的说话方式比无权一方更有说服力。
在第三种类型研究中,学者们尝试探究人们如何运用语言来实现或者维护法律的权力。第二种类型仅将权力因素作为法律过程的一部分而不是使用语言的一个工具,后者即是第三类型研究中学者们关注的方面。正如古德里奇所说,法律是一个证明其权力的分等级的组织。法律这个语域充满着“分等级的,有权威的,专有的和外来的语言”[6]。因此古德里奇正是从哲学家的角度分析法律语篇。另外两位有影响的学者是康力和奥巴尔。他们合写的一本书《法律,语言与权力》阐述了法律语言如何被分析以便揭示社会的不平等。他们认为“法律语篇的细节很重要,因为语言是法律权力得以实现、运用、复制以及有时受到挑战和被推翻的根本机制”[4]。
与国外活跃的研究状态相比,我国研究法律语篇的语言学家就逊色得多了。研究汉语法律语篇的语言学家首推王洁和潘庆云,他们运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分析法律语篇,即从词汇、句法或风格角度进行分析研究。以杜金榜为首的语言学家们则对法律英语和法律汉语的对比研究感兴趣,在分析法律语篇方面有突出的贡献。杜金榜的法律语言学理论来自于西方法律英语的研究成果。在其著作《法律语言学》中,杜金榜不仅从语言本身研究法律语篇,还从修辞、语用、语篇分析、语言心理学、翻译等方面研究法律语篇。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一个新术语:树型信息结构(Tree Information Structure)。这种信息结构理论以兰波夫(Lobav)的信息分类法为基础,是分析法律语篇的一个重要方法。“法律语篇是制度化的。信息加工过程是语篇产生和理解的核心。”[7]
目前,我国对法律语言的动态研究尚处在初级阶段,司法领域、庭审场合等出现的语言现象为其特点逐渐进入法律语言学家的研究范围,但是成果不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廖美珍教授。他对汉英法庭话语深入研究,在其专著《法庭语言技巧》一书中,他分析了庭审中出现的各种问话技巧与功能,法庭语言答话技巧,应答行为及应对行为,非常全面地介绍了庭审语言的结构和特点。[8]这些研究成果非常珍贵,为以后年轻学者的研究打开了思路。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法律语言学家在语言对庭审方面的应用还未能开发出来,这与我国不成熟的法律制度有一定关系。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贯彻,涉外法律领域会逐渐完善,语言学家们会发现自己的研究成果对法律工作者帮助很大,下面笔者具体分析一下语言学家的研究如何作用于司法领域。
二、语言学在司法中的应用
根据国外法律语言学研究,司法过程中出现最多的语言材料是辩护律师提供的各种录音材料[9],而对录音材料认真进行语言分析的则大多是刑事案件中的被告律师,因为他们想从材料中得到可以减轻当事人刑责的语言证据。具体来说,语言学家可以在司法过程中对录音材料进行分析、语音识别、方言辨认等,解决商标运用中出现的多种语言使用纠纷,对产品警告标志上出现的语言问题等辨别分析从而帮助律师。与律师在司法角色不同的是,语言学家只是陈述所研究的材料反映出的客观事实,不参与庭审的最终结果。
所以,语言学家的角色多为“合作者”,而非“证人”。律师可以借用他们的分析进行开庭陈述,或者在盘问过程中用来对控方进行质疑,例如话题分析。“话题转换”是一个语言现象,语言学家可以利用这个现象推断出案件中所涉及事件发展的前后顺序、当事人的立场、作案意图等。例如,原告律师如果在讯问中对被告有潜在的诱导倾向,致使被告突然转移话题,至少说明被告对所涉及话题感觉不适,其回答也相应缺乏客观性和真实性,不应将该讯问材料作为证据呈送给法官。
回应/应答分析。控方可能拿出讯问被告时的录音,当被告回答时出现“嗯,哦”之类的词的时候,控方马上认定其为同意或者承认。但是,从语言学的角度讲,这样的应答不是正面回答问题的方式,控方想当然地解释也就站不住脚,反而转向主观臆断。
总之,语言学家对语言现象的敏感性、专业性可以弥补律师在该方面的不足,帮助律师提高工作效率,从语言的角度拨开迷雾,用客观分析佐证律师的主观判断。
三、庭审中的法庭口译
“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必然加快沿线各国间的经济贸易联系,而贸易引发的各种法律争端也会层出不穷,这会大大丰富我国庭审语言的研究内容,加快与国际法律语言学发展同步的节奏。我国对法律语言的动态研究之所以不多是因为参与到司法领域的语言学家很少,甚至没有。语言学家完全可以参与到庭审过程中,利用所长推动庭审进程。实际上,廖美珍教授的研究成果经常成为许多法律实务工作者如法官、律师及检察官的必读书目,可见法律语言层面的研究对实现司法公平正义有益,对开拓新的法律研究领域有启迪。
此外,“一带一路”使更多的涉外案件成为可能,法庭口译的需求会大大增加。一般来说,法庭口译适用的条件为三种,即少数民族语言、地方罕见方言和不同国家的语言,所以它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实现法律平等的重要工具和确保控辩双方公平竞争的语言手段。[10]但是,不仅仅是国内,不少西方国家的法庭、警署或者监狱非常排斥口译人员的介入,即使案件调查非常需要他们的帮助,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第一,在口译过程中,嫌疑人被给予更多的时间进行思考,随时可能产生应对策略,对警察讯问结果不利;第二,口译者传递信息时会破坏或者影响嫌疑人即时产生的微表情所映射出来的信息量,不利于下一步的心理防线攻克;第三,口译人员自身素质不高,有碍司法公正。本人认为这些因素不能掩盖或者抹杀口译员对案件进展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而且暴露出当今口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指明了日后口译工作的发展方向。
举个例子来说。国际著名法律语言学家John Gibbons曾经对警察讯问中涉及到的口译工作进行过研究,[11]其中一个事例是讲一名男子从黎巴嫩移民到澳大利亚,他被捕的原因是警方怀疑其与朋友、亲属进行毒品交易。在审理过程中,警方提供给法庭两份讯问材料,纸质版和录音版。由于嫌疑人语言水平不高,法庭要求警方出具第三份讯问记录,即口译人员介入的书面讯问材料,结果,口译人员介入的这份材料相比之前的两份供词有着明显的优势:第一,口译员的介入为该案件提供了大量新的信息,案件的细节被挖掘了出来;第二,口译员提供的材料内容更清晰,带有一定的总结性;第三,目击证人的表现前后迥异。因为语言不通,证人的言语表述非常的笨拙,不成熟,没有达到一个成人语言表达的标准;而在口译员的帮助下,证人信心十足,表达深刻,思路清晰,并了解到他是黎巴嫩籍的阿拉伯人,为案件的审理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避免了法庭的错判。
故而,口译人员可以在案件庭审中帮助司法实务人员,规避讯问中许多因语言不通、文化不同等带来的各种误解,使司法更公正,执法过程更透明,证据解释更具说服力,司法机关更具公信力。
四、庭审语言中体现的法律文化
著名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不尔指出:“语言基本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的产品,它必须从文化和社会上来理解”。[12]法律文化同样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密不可分,被它们所体现,理解不同国家法律需要从理解不同的法律文化开始。中国法律文化的核心是“礼法”,“礼”的主导是儒家思想,强调从道德层面约束人的思维,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通过“法”的形式传达出来,所以,“礼”可以理解成一种深层次的法律意识,而“法”是实现这种意识的法律制度。“礼者,圣人之法制也。……有仁义智信,然后有法制”[13],“礼法合一”的法律文化对法律语言进行着渗透和控制。例如,西晋著名律学家张斐指出“理直刑正”的法典总原则,“理直”即从道德层面量刑,遵循传统的纲常礼教,这种情况下的刑罚要准确,宽严相济,轻重得当,才能称之为“正”[14]。在司法实践中,张斐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判断罪的轻重,例如,一位80岁的老人如果犯了杀人以外的罪,他便没有刑事责任,因为根据儒家思想,老人和幼童的犯罪动机不大,社会危害性小。但是,如果是私人的一匹马在闹市中将人踏死,马的主人则要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因为人和马对社会已经造成了危害,并存在极大的潜在危害性,严重威胁到无辜者的生命安全。
“礼法一体”的法律儒家化倾向对一些犯罪概念的定义,立法原则和审判原则的揭示都有不少科学的成分,或多或少影响着现代中国法律制度的建设和法律语言的发展。同样,“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有着不同的法律体系,渗透着不同的法律文化。沿线一些较发达的欧洲国家如俄罗斯等,他们的法律根源不是道德,而是自然法,因为西方多数国家在古代崇尚畜牧文明,单打独斗的丛林生活使得自由主义泛滥,民主和保护私有财产成为必然选择。沿线还有许多发展中国家或经济不发达国家,如阿富汗,这里的人们信奉伊斯兰教,政府实施的法律依据来自《古兰经》,所以阿富汗的法律文化建立在宗教上,与我国历史上传统的“人治”,欧洲的“法治”又存在差异。这样的法律文化差异造成各国有贸易争端时庭审中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要谨慎处理,弱化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处理贸易争端和法律纠纷。
五、结 语
中国庭审话语研究与静态的法律篇章研究相比发展相对滞后,一是因为我国缺乏分析动态材料(多为录音)的经验,二是因为国内需求不大。“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我国法律语言学的研究带来了挑战和机遇,大量的国际经济纠纷将要挑战现有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语言研究,客观上为语言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我国的语言学家和法学家应该培养一批掌握沿线国家语言的高素质法律人才和法庭口译人才。如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需要有熟练掌握俄语和新蒙文的法律人才做后盾,将法律精英送到相应国家继续深造。他们的法律实践会为我国的法律语言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1] 谷昭民.中国开展法律外交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J].现代法学,2013(4):173-180.
[2] Fishman C.Recordings, Transcripts and Translation as Evidence[J].Washington Law Review,2006(3):103-112.
[3] Cotterill J.Language in the Legal Process [M].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4.
[4] Conley J M, O’ Barr W M. Just Words: Law, Language and Power [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
[5] Mellinkoff D.The Language of the Law [M].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04.
[6] Goodrich P.Legal Discourse [M].MaCMillan Press, 1987.
[7] 杜金榜.法律语篇树状信息结构研究[J].现代外语,2007(1):40-50.
[8] 廖美珍.法庭语言技巧[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9] Shuy R W.Dialect as Evidence in Law Cases[J].Journal of English Linguistics,1995(23):195-208.
[10] Mikkelson H. Introduction to Court Interpreting [M].Manchester:St. Jerone Publishing,2000.
[11] Gibbons J.What got lost? The Place of Electronic Recording and Interpreters in Police Interviews [M].Sydney: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1995.
[12] 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13] 崔永东.中西法律文化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4] 苗文利.历代法律[M].沈阳:辽海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胡先砚)
D925
A
2095-4824(2017)05-0119-04
2017-08-17
马丽娅(1978- ),女,山西长治人,长治学院法律与经济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