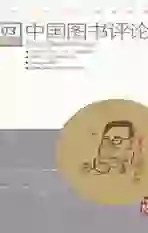从异化的社会走向健全的社会
2016-04-15王天保
王天保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主要建立在对个体的心理分析的基础之上,所以人们往往把他的无意识概念称为个人无意识。个体的童年经历、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与父母的关系是其关注重点。而弗洛姆的精神分析理论主要建立在对群体、对社会的心理分析的基础之上,关注群体性的心理取向,以及社会生活方式与心理活动的关系。弗洛姆的社会批判理论经常以复杂的心理分析的形式出现,社会群体精神层面上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是其关注的重点。正是以这种思路为基础,弗洛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批判与反思,而美国则被选作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代表。
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
与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相比,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社会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工人阶级的生活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工人与老板的关系、孩子与家长的关系也更加平等,社会民主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但这种社会结构仍然导致了各种异化现象的产生,只是这种异化现象与马克思所说的异化有所不同。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包含的矛盾非常尖锐。而弗洛姆所理解的异化主要是指心理体验上的一种陌生感:“所谓‘异化,就是一种经验方式,在这种方式中,人像一个外人(analien)体验自身。可以说,他疏远了他自己……异化了的人同自己失去了联系,就像他同他人失去了联系一样。他感到自己同他人都像物一样被感受;他虽然有各种感觉和常识,但是同时却与其自身、与外部世界失去了生产性的联系。”[1]这种异化表现在偶像崇拜(idolatry)中。所有的屈从性崇拜(submissiveworship)都属于偶像崇拜,无论这个被崇拜的对象是金钱还是某个具体的他人。在这种崇拜中,由于崇拜者不把自己视为爱和理性的生产者,导致他自己以及他崇拜的对象都变成了“物”(thing)。人本来应该具有生产性人格,具有创造性,但是在偶像崇拜中,他必须依赖于某种外在的力量才能获得生存的意义,他不但使自己变得极度空虚,而且把具有丰富人性的他人也简化为某种品质的象征物。正是因为弗洛姆是这样理解异化的,所以他认为异化也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有的现象,以往的社会形态中也有异化。只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广度”(thoroughness)与“深度”(completeness)进一步发展了,异化更加全面。在生产与消费的过程中,在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在休闲娱乐中,异化无处不在。
现代社会中的异化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数量化”(quantification)和“抽象化”(abstractification)的不断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数量化与抽象化不全是坏事,现代化的生产也离不开具体的量化指标。但数量化与抽象化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它们的影响也不仅仅停留在经济领域,而且影响到了人们看待人与事物的方式。在日常生活语言中,抽象化和数量化遮蔽了物的实际价值和人的具体经验。当人们远离具体经验时,他们的破坏性行为也很难引起他们良心的不安,因为他们可能完全看不到其行为的结果。“在现代战争中,一个人能够造成数十万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死亡。他只要按一下按钮就做到这一点;他可能感觉不到他的所作所为在情感上有什么影响,因为他没有看见,并不认识那些被他杀害的人,就好像他按下按钮的行为与那些人的死亡几乎不存在任何联系。同样是这个人,他可能不忍心打一个无助的人,更不用说去杀人了。在后一种情况下,具体的情境会在他身上唤起一种良心中的不安,这是普通人所共同具有的;而在前一种情况中,就没有这种反应,因为他的行为和目标与动作的发出者分离了,他的行为不再是他的了,也就是说,行动本身有自己的生命和责任。”[2]弗洛姆批判异化的意图可以理解,但在这一段论述当中,他的论述似乎过于简单。具体经验是否有利于减少一些人的罪恶行为恐怕还很难说。坚持正义的善良的人肯定会拒绝使用现代杀人机器,普通人在使用现代杀人机器时照样会受到良心的谴责,邪恶的人即便是面对面地杀人也会毫不手软。
社会异化也导致现代社会性格出现了一些新的迹象。公开的权威被削弱,但是无名的权威的作用得到了加强。“无名的权威的运行机制是求同(conformity)。我应该做每个人所做的事,所以我必须求同,不要不同,不要‘出位(stickout);我必须随时准备和愿意随着模式的改变而改变;我不允许问我是对还是错,而应当问我是否适应了,是否不‘特殊,不是不同的。对我来说唯一永恒不变的事情就是随时准备着适应任何变动。除了我居于其中的、必须屈从的群体之外,没有谁具有支配我的力量。”[3]弗洛姆以伊利诺伊州(Illinois)的森林公园(ParkForest)社区的生活为例探讨了居民的求同性格取向。这个社区表面上充满友爱,但实际上也是一种异化的表现。居民们不仅用“精神病”(neurotic)这样攻击性的语言惩罚不求同的行为,还用“放逐”(ostracism)的方式惩罚违反求同规则的个人。他认为,“这种妥协的生活”,“开朗”(outgoing)的生活,是禁锢的、“无我性”(selflessness)的、绝望的生活。[4]
现代社会需要不断地刺激大众消费,这一经济特征导致现代社会性格出现了这样一个特点:“每一种欲望都必须立刻被满足,任何希望都不能受挫。”弗洛姆将其称为“不受挫原则”(the principleofnonfrustration)。[5]这种社会性格使得美国社会中人们的欲望很少得到节制。弗洛姆认为这一现象同样是异化的表现:“欲望之无节制,与缺少公开的权威一样,都会导致同样的结果———自我的瘫痪,以及最终的毁灭……大多数欲望都是合成的(synthetic);甚至性欲也远远不是本该那样‘自然。在某种程度上,性欲也受到了人为的刺激。”[6]如果人们总是生活在欲望和欲望的满足之中,那么他们就像永远也长不大的婴儿,总是期待着从外界得到满足。缺乏生产性的人格总是很容易陷入焦虑之中,但是现代人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源是他们缺乏生产性,他们采用“自由联想”(freeassociation)和“自由交谈”(freetalk)形式来克服心理焦虑,殊不知这种方式仍然是非生产性的。在弗洛姆看来,如果我们把想法埋藏在心中,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困扰,但在我们深思熟虑之后也会产生新的思想。自由联想与自由交谈固然能够让我们免去一时的苦恼,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心理问题:“你有什么就说什么,你不让你的想法和感觉形成压力,那么你的想法就决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益处。这简直如同无节制的消费。你形成了一个系统,系统内的事情一直在进进出出———而体系里什么也没有,没有紧张、没有消化、没有自我。”[7]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理性也在不断退化。为了表明自己的意思,弗洛姆对理性(reason)与智慧(intelligence)进行了区分。“智慧就是根据事物的本来面目去看事物,把事物加以综合,从而更有助于使用它们。智慧被认为是生物生存的需要。”“理性的目的则在于理解,找出表面现象背后的东西,认识我们周围的现实世界的核心和本质。理性并非没有功能,但是其功能并不是促进肉体的生存,而是推动思想和精神的存在。”[8]现代人的智慧确实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们的生存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在理性层面上,情况却恰恰相反:“从19世纪至今,人类的愚昧程度日渐加深。”[9]
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工作环境得到了改善,但这种工作仍然是一种异化劳动。这种异化主要表现在工人与机器的关系上:“不是机器代替人力,而是人成了机器的代用品。他的工作可以被定义为完成机器还不能完成的工作。”[10]这种理念没有把工作视为展示个人潜能的舞台,而是把劳动者视为工作程序中的一个环节。就连商人的工作也是一种异化劳动,他与员工、顾客、竞争者之间的关系经常是对立的。异化的工作环境让社会中的很多人都渴望一种懒惰、消极的生活。现代社会中的民主选举制度与商品的营销方式也越来越相似:“重要的是销售和选举的效果,而不是销售或选举呈现的理性和有用性。”[11]一个全面异化的社会不是健康的社会。
弗洛姆所说的“异化”跟他在《为自己的人》中提出的“非生产性人格”表达的意思非常接近。异化的社会不能培育人们的生产性人格,而异化的人则不具有生产性和创造性。
二、通向健全社会之路
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呢?弗洛姆总结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三种解决方案:极权主义理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刺激性管理”(incentivemanagement)的方法和社会主义理论。但极权主义是一条不归路,它加深了社会的异化程度。“刺激性管理”只能激励工人的工作积极性,对社会的普遍性异化无能为力。弗洛姆所说的“社会主义”包括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他关注的重点。弗洛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总体上持肯定态度,不过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马克思忽略了建立一套新的道德观念的复杂性,过于重视经济转变的重要性。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如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缺乏预见性,对未来过于乐观。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对人性的复杂性缺乏认识,忽视了人性中非理性的、破坏性的因素。[12]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Socialism)必须回归到关注社会问题中的人性因素,必须从资本主义对人性品质、对人的灵魂和精神的影响的角度来批判资本主义,必须用人性的术语来思考一种社会主义观念,追问社会主义社会将以何种方式为消除人的异化以及经济和国家中的偶像崇拜做出贡献。”[13]为了建立这种新型的、健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整个社会必须在经济、政治、精神与人格结构、文化等层面上同时发生变化。如果只是其中的某一个方面发生了变革,而其余的方面被忽略,那么整个变革就不可能成功。在此,弗洛姆对“激进主义”(radicalism)与“改良”(reform)两个概念的关系进行了辨析:“改良可以是激进的,即触及了根本的改良,也可以是表面的,只是试图去修补一些症状而不去触动病因。在这个意义上,不激进的改革决不能达到其目的,最终事与愿违。另一方面,相信可以通过强力来解决问题的‘激进主义,在需要观察、耐心、不停地努力的时候,如同肤浅的改革一样,是不切实际的、虚幻的东西。”[14]比如说,俄国的革命是激进的,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斯大林主义体制与革命者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20世纪30年代初的德国,在各种诱人的口号的欺骗下进行社会改良,希特勒借机上台,但这一结果与当初人们的期待南辕北辙。因此,激进与改良这一组二元对立有时是虚假的:激进可能是虚假的,改良也可能是彻底的。
弗洛姆认为:“社会主义指的是一种新的生活形式,一种充满团结和信任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能找到他的自我,摆脱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固有的异化。”[15]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才是健全的社会。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都未能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健全的社会在经济上也不应该迷信自动化的作用,不应该迷信金钱、地位等外在因素的激励作用,而要关注劳动者的心理感受。当然,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需要细致的社会分工,现代科技成果的应用也需要细致的分工。分工就意味着每个环节中的工作可能是单调的。如何才能使劳动者对这种单调的工作产生兴趣呢?弗洛姆认为,每一种工作都有两个层面:技术层面和社会层面。“社会性令人满意的话,各种类型的工作都是富有吸引力的;工作的技术方面没有趣味的,它的社会性也能够使它富有意味和吸引力。”[16]他觉得,人们的兴趣千差万别,所以不必担心人们会厌弃某种工作;任何一种工作,只要能够消除工作环境、社会评价方面的不利因素,就一定会有人对这种工作产生兴趣。在理论上,弗洛姆这一观点可能具有合理性,但在现实层面上,一些工作的“不利因素”不可能被彻底消除,劳动者不可能单靠兴趣就会乐意去做这些工作。因此,异化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被彻底消除。不过,人们还是应该积极探索能够减少异化的新型社会关系。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很多劳动公社(CommunityofWork)在改善工作、管理中的人际关系方面进行了非常有益的探索。这些探索可能没有完全成功,但弗洛姆认为这些探索仍然是人类的创造性的表现,而否定、怀疑这些探索则“反映了人们的懒惰心理和固有的信念,那就是过去未实现的东西,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实现”。[17]他还以这些劳动公社所积累的经验为基础,提出了在整个社会中进行改良的建议,其核心观念是培训工人并让工人参与管理,让工人与管理层共同决策。弗洛姆为工人设立的培训目标既有知识方面的,也有道德方面的,让很多人都达到这一目标无疑是非常艰难的。虽然弗洛姆的这些建议未必能够解决问题,但探索健全社会的模式仍然应该得到鼓励。
在通往健全的社会的道路上,现代社会不仅需要经济转型,也需要政治转型和文化转型。弗洛姆认为必须对现有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进行改良:“必须得承认,真正的决策不可能在大众选举的气氛中做出,而只能在比较小的团体中制定,这种小团体大概与过去的市民会议的规模相当,不超过500人。在这样的小团体中,重要的问题才能得到全面的讨论,每个成员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并理性地听取、讨论其他观点。人们相互间均有个人联系,这就使煽动性的及非理性的影响很难对人们的思想起作用。”[18]此外还需要一个政治上独立的文化机构公开真实的信息资料。在弗洛姆看来,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文化的核心理念都是一致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让这种核心价值观念以其本来的、真正的面目在人们的心中生根发芽:“心灵的革命并不需要新的智慧(new wisdom)———而是需要新型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和献身(newseriousnessand dedication)。”[19]文化转型首先要求对教育进行改革。现有的教育只是让学生掌握一些实践性的知识,培育学生的市场取向的人格,但健全的社会需要培养具有批判思考能力的健全人格。现有的教育主要关注青少年的教育,但健全的社会还需要成人教育,使一个30岁或40岁的人能够“有机会进行重新的学习”,能够“自由地改变他的职业”。[20]文化转型的第二方面是倡导“集体艺术”(collectiveart)与“仪式”(ritual)。弗洛姆所说的集体艺术与仪式的意思是一样的,只是因为仪式这个词“带有宗教的意味”,而他想要表达的是更具普遍意义的文化内涵,所以他才使用了集体艺术这个词。集体艺术的意思是指“利用我们的种种感觉,以一种有意义的、熟练的、创造性的、积极的、与人共享的方式,对世界做出反应”。“与人共享”这一特点使集体艺术与“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概念区别开来”,“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在创作和消费上都是个人化的”。集体艺术“使一个人感到与其他人联系起来”,它不是“附加于生活”之上的个人消遣,“而是生活的组成部分”。[21]集体艺术是一般人发展其生产性取向人格的重要途径。虽然弗洛姆提出了集体艺术的概念,提到了一些建立集体艺术的尝试,但这些尝试从未获得人类早期仪式的那种凝聚力。现代仪式无论是“在质量上或者是在数量上”都“不能满足人们对集体艺术和仪式的需要”。集体艺术肯定不同于现代社会中大众文化,集体艺术也不可能被“人为地创造出来”。[22]全面复兴集体艺术只是一个美好的蓝图,只有在社会改革全面推进时才可能真正产生。文化转型的第三方面是新宗教的出现。这种新型宗教的普遍性特点“与这个时代所出现的人类的统一相适应”,“包容了东方和西方所有重要宗教所共有的人道主义学说”。[23]新宗教也是属于未来的宗教。
弗洛姆提出的通向健全的社会的道路只是一种理论设想,但这种理论设想的某些特征是可以被现实生活“分享”的。如果现代社会能够将其中的某些设想(如发展集体艺术)有选择地实施于现实生活之中,还是有可能取得一些积极的社会效应的。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悲剧理论研究”(12CZW00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弗洛姆:《健全的社会》,王大庆、蒋重跃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104页。参照英文版(Routledge&Kegan Paul,2002)第117页改动了引文。
[2]同[1],第103—104页。参照英文版(Routledge&KeganPaul,2002)第116页改动了引文。
[3]同[1],第133页。参照英文版(Routledge&KeganPaul,2002)第149页改动了引文。
[4]同[1],第141页。
[5]同[1],第142页。
[6]同[1],第144页。
[7]同[1],第145—146页。
[8]同[1],第147页。参照英文版(Routledge&KeganPaul,2002)第165页改动了引文。
[9]同[1],第149页。
[10]同[1],第157页。
[11]同[1],第161页。
[12]ErichFromm,TheSaneSociety,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2,pp. 257—258.前文中参阅的中文译本在此漏译了很多页。
[13]同[12],第261—262页。前文中参阅的中文译本在此漏译了。
[14]同[1],第228页。
[15]同[1],第235页。参照英文版(Routledge&KeganPaul,2002)第273页改动了引文。
[16]同[1],第252页。
[17]同[1],第273页。
[18]同[1],第291页。参照英文版(Routledge&KeganPaul,2002)第333页改动了引文。
[19]同[1],第294页。
[20]同[1],第295页。
[21]同[1],第297页。
[22]同[1],第299页。参照英文版(Routledge&KeganPaul,2002)第341页改动了引文。
[23]同[1],第3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