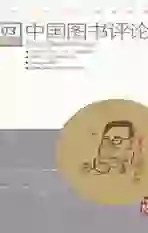疾病体验与文学热度
2016-04-15王鹏程
王鹏程
疾病是每个人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在普通人的世界里,疾病改变了个人的生存方式和世界的关系,是包含着痛苦、抑郁、孤独等种种身体不适的生活事件。而在患病的文学家那里,疾病不仅仅成为他们的身体感受,同时成为重要的精神事件和认知世界的方式。征之于中外文学史,许多著名的文学家都饱受各种疾病的折磨,国外如荷马是个盲人,陀斯妥耶夫斯基患有癫痫病,索尔仁尼琴患有恶性肿瘤,波德莱尔、福楼拜、乔伊斯等作家患有梅毒,契诃夫、卡夫卡、劳伦斯等患有肺结核……中国如卢照邻染有风疾,杜甫患有消渴症,鲁迅、郁达夫、巴金、萧红等作家曾患肺结核,史铁生身体残疾,食指有精神性疾病等。程桂婷的博士论文《疾病对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影响研究———以鲁迅、孙犁、史铁生为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5月)即是从作家的疾病体验入手,剖析他们的精神体验和文学热度。她将作家的疾病与深层的心理意识、内在的思想活动、表层的文学文本、外部的行为方式以及外在的社会环境综合起来研究,对作家的创作心理和文本形态进行了深度的发掘和深刻的洞悉。对现代文学研究而言,这一尝试可谓开辟榛芜,同时又充满了挑战。
程桂婷早年学医,并有短暂的从医经历。加之她对自己儿时生病经验的不断回味和咀嚼,成为她展开研究的有利条件和独特优势。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基于医学病理并综合性格及环境的分析常能“于无声处听惊雷”。如,她从鲁迅长期的发热症状入手,细致梳理了鲁迅日记中记载的1912年5月9日到1936年10月15日的发热记录,在分析体温变化示意图的基础之上,阐述了自己的发现:“为什么在‘受虐与攻击的双重心理倾向中,鲁迅会更突出地表现出攻击性倾向呢?我以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鲁迅长期处于一种发热状态有关。应该说,鲁迅这种压抑、敏感、多疑、易怒的个性的确与他的少年经历有关,但在成年鲁迅的身上,长期的发热很可能是起到了一种催化剂的作用,这种因体温升高而造成的‘内燃状态及其所引起的急躁情绪,使鲁迅个性心理中具有攻击性的一面表现得更为强烈了。”(第44—45页)如若停留在此处,不过是简单的病理或者生理决定论。她进一步指出:“我常说鲁迅处于一种‘内燃状态,这不仅是指他的结核性低热而言,更是指在结核性低热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情感的炽热,那里的温度大概是比38℃的低热的体温还要更高一些的。这种炽热的情感的生发,当然不仅仅是因为结核性低热的关系,在本质上还是出于鲁迅对国家、对民族、对人世、对个体生命的深深的爱,也正是因了这份爱,鲁迅对社会的黑暗和黑暗势力的憎恨才会那么强烈,而结核性的低热不过是更加促进了这份爱与恨的积聚和燃烧。”(第54页)这颇令人信服。但我们不禁要问,鲁迅自己曾经学医,又有着应该说不错的医生和医疗条件,那么怎么会长期处于“体温升高而造成的‘内燃状态”呢,这又为何?程桂婷运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我们解开了这一疑问。她从鲁迅日记中发现,鲁迅吃得最多的药是规那丸和阿司匹林,规那丸、金鸡纳丸等丸药其实都是奎宁。奎宁“是一种在金鸡纳树皮中提取的生物碱,在20世纪初是治疗疟疾的主要药物。奎宁能杀灭各种疟原虫红内期滋养体,也有较弱的退热作用和抑制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鲁迅起初在发热时经常服用此药,但鲁迅的发热并非是因为疟疾所引起的,所以服用规那丸退热的效果并不好。查日记可知,鲁迅最初一次只服一至二粒,后渐增到一次四粒,最多时一次吃十粒,如1920年11月25日、26日两日,日记均记:‘病,休息。夜服规那十厘。服用规那丸原本就有很大的副作用,诸如恶心、呕吐、皮肤瘙痒等,鲁迅这样超剂量地服用,一定遭受了不小的痛苦。大概是由于规那丸解热镇痛效果差而副作用又大的缘故,1923年后鲁迅发热时多服阿司匹林,规那丸则吃得极少”(第61—62页)。那服用阿司匹林的效果如何呢?“在20世纪之初,对阿司匹林的发现仅限于解热止痛。鲁迅大多是在发热时服用,偶尔在牙痛或胁痛时也服用。此药口服易吸收,能迅速与血浆蛋白结合,作用于人体下丘脑前部的热敏感神经元,增加散热,从而达到降温目的。……鲁迅的胃病愈到晚年愈为严重,应该也与他经常服用阿司匹林有关。虽然阿司匹林的退热效果极好,又有一定的抗炎和止痛作用,但面对结核菌却无能为力,因此对鲁迅的病来说,阿司匹林是治标不治本的,往往是服药的当晚大汗淋漓,体温骤降,疼痛的感觉亦一并消失,病人神清气爽,安然入睡,然而一觉醒来之后,结核菌并未停止的活动又使体温升起来了。所以,鲁迅有时连服几天阿司匹林,体温升了又降,降了又升,总不见平稳,情急之下,又吃起规那丸来,不见效,又再吃阿司匹林……”(第62—63页)这种专业而恰切的解释,使人眼前一亮。程桂婷用“药”和“酒”楔入鲁迅的文学,在与魏晋社会、名士及文学的比较中,理解鲁迅的矛盾与痛苦、希望与绝望,贴切地洞悉了鲁迅的心灵及文学世界———“对鲁迅的病体而言,如果说吃药是鲁迅的自救的话,那么饮酒则是鲁迅的自虐了,吃药是因为希望,饮酒是源于绝望,而这种希望与绝望交织、对抗的情绪也如迷雾般氤氲在鲁迅1926年之前创作的小说里。‘药与‘酒不仅是鲁迅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文学意象,更是鲁迅小说中隐喻和象征系统的一部分。”(第65页)
孙犁的文学创作在1956年戛然而止。他搁笔的直接原因是1956年3月,午休后起床晕倒,左面碰破,血流不止,自认为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死亡将至,很难提笔。学术界多以为孙犁的“病”没有严重到搁笔的程度,这不过是“‘写与‘不写之间的睿智选择,是一种‘策略”,他不过借此“假病”“托病”而已(叶君:《论孙犁的病》)。那么,孙犁是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吗?程桂婷厘清了中国医学界长期对“神经衰弱”和“抑郁症”的混淆。在考查“神经衰弱”源流的基础上,她指出了“神经衰弱”和“抑郁症”在病理认知模式上的差异:“……无论是神经衰弱,还是抑郁症,都无非是对某种病痛的医学命名,同一病痛在不同时段、不同国度、不同语言中,也可以有不同的命名。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在神经衰弱与抑郁症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建构中,它们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神经衰弱是指一种神经性障碍,是由于大脑或神经功能的减退、衰竭、丧失引起了人体的不适,包括疲惫、疼痛、易怒、情绪不稳定、失眠、多梦,等等。抑郁症则是指一种社会性的情感和障碍,是由于一些社会问题如工作、家庭等原因导致长期精神压抑,而出现了一系列躯体化症状,也包括疲惫、疼痛、失眠,等等。两者所指的生理症状是相似的,但认知模式则完全相反:前者是生理—精神的生物学建构,后者是社会—精神—生理的人类学建构;前者将病因归结为人体组织的病变,后者将病因归结为社会问题;前者将治疗的对象指向人体,后者将治疗的对象指向社会。”(第107页)孙犁的症状主要是“精神不好、不振作、不能集中精力工作、易怒、不能控制情绪,等等。对于造成这些病痛的原因,主要是长期的心理压抑和几次强烈的精神刺激”。这显然不是“神经衰弱”,而是“抑郁症”。程桂婷阐述了自己的独见:“假使现在请一位美国医生根据这些病因病症来诊断孙犁的病,那他就会给出另一个诊断:重性抑郁障碍。也就是比较严重的抑郁症。抑郁症主要是社会原因所导致的精神、情感上的问题,而不是神经组织的功能性病变,病人所感觉到的头疼、头晕、心慌、疲惫等病痛体验,是精神问题躯体化的结果,因此这些躯体化症状既会随着精神问题的解决而消失,也会随着精神问题的加重而加重。”(第109—110页)也就是说,孙犁所患的中国特色的“神经衰弱”,实际上是“抑郁症”。抑郁症“会随着精神问题的解决而消失,也会随着精神问题的加重而加重”。她结合孙犁1945年的发病、1956年的病重、1962年的好转以及后来的变化发现,他的抑郁症有一个“累积”的过程。早在1945年,孙犁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家里经商且雇有长工)在革命队伍中的处境微妙,并因赞美进步富农遭到批判,已经患上了抑郁症;1951年因《村歌》被批判为“小资情调”,1955年因目睹鲁藜被捕而深受刺激,“可能脸色都被吓白了”;1956年碰伤后表现出重度抑郁;1962年因为文艺政策的调整,孙犁的抑郁症有所缓解,写了17篇文章,并最终完成了《风云初记》的创作……通过详细的举例分析,程桂婷证明了孙犁所患的是有着复杂社会根源和政治压力的抑郁症,主要源于内心持守和外部现实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同他的遗传基因、成长经历、抗压能力、审美洁癖等也不无关系。正是洞悉了孙犁“抑郁中退守”的复杂心理,她对晚年孙犁的解读才能入幽探微,切中问题,独见迭出。如《黄鹂———病期琐事》一文,向来被视为孙犁爱护小生灵的积德行善的美文,程桂婷综合时代环境和孙犁的“惊弓之鸟”的抑郁心态发现,孙犁是以黄鹂自况,托“鸟”言志:“与黄鹂孤而不傲的身姿相似的,是孙犁平和无争的‘离众姿态;对黄鹂的啼叫的喜爱,是孙犁对自己作品的自珍;对黄鹂‘互相追逐‘互相逗闹的和睦生活的驻足观望,是孙犁对抗战岁月中人们无私互助的珍贵情谊的回望;对受惊吓而一去不返的黄鹂的无限同情,则是孙犁对自身命运的黯然神伤。”(第125页)这样的研究,立足于翔实的材料和缜密的分析,在完整凸显时代背景的基础上,关心幽微的细节和作家心灵的深处,揭开文本背后的精神蕴藏与时代症结,给人带来新颖的学术见解和思维上的冲击。
相对而言,对于史铁生的分析较孱弱,程桂婷觉得残疾主题、宿命思想和宗教精神已被许多研究者关注,因而有意避开。如此一来,史铁生加缪式的超越荒谬,在荒谬中获得生活意义的存在主义思考和个人本位主义的理想情怀就无法穿透,他写作的内心驱使和精神景观就很难全部展现。抛开这些,关注史铁生“作为他者的身体”和“性爱中的身体”时,我们总觉得有买椟还珠的嫌疑。但这并不是说这一章没有独到的发现,《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阐释就很有创见。史铁生笔下的陕北,民风淳朴、人情美好,恶劣的生存环境、落后的生产方式和贫穷的生存状态被虚化为饶有诗意的背景,落后、穷困、闭塞的黄土地成了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这是真实的陕北吗?程桂婷给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解释:从心理原因看,陕北农村的阶级斗争没有北京那么强烈,“以史铁生的‘灰五类出身,他在激烈的阶级斗争遍布每一个角落的北京,一定是有压力、受冲击的。因出身问题而带来的自卑心理、思想压力和尴尬处境,在他颇有自传色彩的另一篇小说《奶奶的星星》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所以,当史铁生在阶级斗争意识淡薄的陕北农村插队时,他很可能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精神上的轻松和愉悦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了他在贫困的农村所遭遇的饥饿、寒冷、劳累等生理体验”。另一方面,她指出了个人心理变化对记忆的干预作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写作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离插队已十年有余。因此“与其说史铁生描写的是他的体验,毋宁说他讲述的是他的回忆。曾经的体验与现在的回忆是不一致的。……除社会变动的因素之外,个人心理的变化也是干预回忆的一个重要原因”(第152—153页)。这两点,解答了不少人包括我阅读《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心理困惑,也推进了对史铁生的研究。
《疾病对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影响研究———以鲁迅、孙犁、史铁生为例》独辟蹊径,视角新颖,论述有力,通过扎实的文本细读和相关材料的悉心梳理辨析,剥茧抽丝般地沟通了这几位作家疾病体验与文学热度之间的关联,新见迭出,有力地推进了对鲁迅、孙犁和史铁生的研究。其荣获南京大学文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可谓实至名归。但这并不是说该论文并没有可以商榷或者讨论的地方。如果我们顺着作者整体阐释努力来看的话,他们三个人的“病”是三种完全不同的类型,作为博士论文或许缺少逻辑上的内在性。第二点作者也在《自序》里谈到,即“疾病不是直接影响到创作的,而是通过影响作家的生活习惯、心理状态和精神风貌从而影响到他的创作倾向和创作风格的,那么我的困难就在于,从疾病到心理状态之间,再从心理状态到创作倾向之间,都不是一个可以实证的过程”。这不是她一个人的困惑,应该说是她向学术界提出的一个研究难题。从疾病到心理状态到创作倾向,既需要扎实的材料,同时也需要合理的论证和想象。如果把握不好,不是蜻蜓点水,就是过度阐释。作者在分析鲁迅时就把握得比较好,分析孙犁时过多强调外在的因素,对孙犁的个性、这样的“文化人”性格以及集体无意识等的分析力度不够。值得肯定的是,程桂婷利用自己的医学背景,并以她认真的研究和扎实的思考,将疾病体验与文学热度这一课题推至可喜的境地,给人启发,令人欣慰。我们期待这一课题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长足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