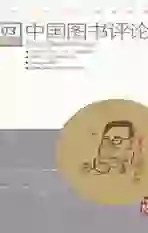80年代的“寻找男子汉”
2016-04-15张伯存
张伯存

20世纪80年代,在影视、文学、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种“寻找男子汉”、呼唤硬汉气质、表征阳刚之气的文化现象,它的出现有深刻、复杂的原因,本文试分析之。
1985年2月,《中国青年》杂志在栏目总标题“一扫混沌平庸,扬我阳刚之气”中发表一篇署名水竹的文章《到哪儿去寻找高仓健》,文章对高仓健的评价是:“刚毅,勇敢,百折不挠,把感情埋得很深,又爱得那么热烈”;“沉静,坚忍,从不诉苦。他就像一座山那样有力量”。这是作者心目中的男子汉,她在现实中寻找理想中的人生伴侣几经挫折后,发出这样的呼告:“到哪里去找高仓健?”她的结论是:“中国的男子退化了!”[1]此文发表之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中国女性对中国男子汉的呼唤要借助一个外国男演员的名字道出,这本身是个有意思的问题,确切地说是这个男演员所扮演的银幕形象,迷住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女性,这说明她们对男子汉的审美评价和情感寄托是超越国界的。当然,对高仓健的钟情、痴迷涉及复杂、微妙的媒体表象、女性心理、公共生活等各种因素,“到哪儿寻找高仓健?”这一强烈的情感诉求里,“高仓健”已不再指代一名日本演员,也不再是他所扮演的银幕形象,而是有着固定所指的飘移不定的能指符号。在滚滚奔向现代化的浩荡洪流下面,私人的情感暗流也是无处不在的,说到底,不论是女性的“寻找男子汉”还是男性的“成为男子汉”“作为男子汉”必须落实在每一个个体的情感认同和伦理担当上。
20世纪80年代前期引进的一批境外电影、电视剧中的男主人公,无论对女性寻找“另一半”还是对男性自身的主体建构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不断树起一个个全新的、复合的标尺。这批影视剧主要有高仓健主演的日本电影《追捕》《远山的呼唤》,美国电影《第一滴血》及其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和《加里森敢死队》,中国香港电视剧《霍元甲》《上海滩》《射雕英雄传》及电影《少林寺》《英雄本色》,法国电影《佐罗》等。
这批影视剧在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掀起一浪又一浪热映、热播狂潮,如此“声色犬马”的缤纷世界深深刺激了长期闭塞视听的国人,民众徜徉在这些影视密林里,无异于一次“破冰之旅”。
高仓健使中国观众第一次产生了偶像的意识和概念。影片中,竖起衣领、寡言少语的高仓健具有冷酷的面容,冷峻的眼神,沉默、坚韧的仪表,刚毅、深沉、内敛的性格;他表现柔情时,也是男性所特有的拙朴,是私人化的,他就像一座大山屹立在那儿。高仓健一时间赢得众多中国女性观众的青睐,致使当时社会大众对男人的审美观一夜之间骤变。成为当时中国女性寻找伴侣的一道标杆。有意思的是,高仓健的出现,使国内那些所谓的“奶油小生”一时没了市场,演过电影《孔雀公主》中的王子、扮相漂亮的唐国强因此事业受挫,很长时间抬不起头来。在中国当代大众文化中,可从发生学的意义上在此找到“硬汉”“酷”话语的源头。继“高仓健热”之后,法国电影明星阿兰·德隆以棱角分明、俊朗的面庞、黑袍白马的扮相迅速俘获了不少年轻女影迷的心。一部《佐罗》使他成为中国女影迷心目中当仁不让的现代“阿波罗”(太阳神)。在女影迷眼里,他是一位潇洒、从容的来去匆匆的西方侠客,一位英俊多情的浪漫骑士,一位高雅的风度翩翩的绅士,他更是中国人心目中西方国家浪漫和高贵的完美象征。这一形象上面寄寓着国人浓厚的西方想象。高仓健扮演的杜丘警官和阿兰·德隆扮演的佐罗,一个是自我救赎,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一个是单剑匹马拯救世界,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个人主义的英雄。在这一点上,无疑助长了或普及了20世纪80年代思想界的个人主义思潮。
中央电视台1980年10月开播美国26集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该剧讲述的是美国中尉加里森从监狱里找来一些杀人犯、骗子、强盗、小偷组成一支前所未有的敢死队,和纳粹德军奋勇作战的故事。该剧引起很大的轰动效应。它完全颠覆了“十七年”文学和样板戏塑造的革命英雄形象。英雄可以有污点,可以是罪犯,在特定时刻,人人都能成为英雄。对在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少年来说,这部电视剧使他们在对“好人”“坏人”“英雄”“人”之类概念的重新理解中,逐渐建立起自我的认同,也影响他们世界观的形成。
美国科幻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1980年年初开播,主人公麦克·哈里斯在全国青年观众中掀起旋风。他戴的蛤蟆镜,成为20世纪80年代城市青年追逐的时尚。“蛤蟆镜”也成为当代流行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符号。这是20世纪80年代男性形象消费的又一个成功个案。英俊的麦克·哈里斯的登陆同时兼具双重意味:首先,他是大西洋底来的人;其次,他更是太平洋彼岸来的人。双重身份营造了双重的传奇,对当时的国人来说,无论大西洋抑或美利坚,距离他们的日常生活都同样遥远,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观赏效应:当麦克·哈里斯潜入深海的时候,观众享受了科幻的奇妙;而当他登陆上岸的时候,观众领略了西方异域风情。前者正迎合、呼应了新启蒙的科学精神,所谓“科学的春天”;后者令国人对西方生活的想象乘上了翅膀。该剧正如一副蛤蟆镜照出了一个大千世界的“西洋景”———原来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国家竟有如此的无限风光、如此的生活、如此的人。小小荧屏里闪烁的那个陌生而遥远的太平洋彼岸旖旎世界就这样悄悄融解了民众心理上的意识形态冰封层。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开放首先通过媒体的西方展示和西方想象获得了大众心理驱动力。
每一个男儿心中都有一个英雄偶像;每一个少女心中都有一个白马王子。关于男性主体建构问题,下面是发表在一份男性时尚杂志上的回忆文章的片段:
电视里每放一集《霍元甲》,我们就凭记忆演一集。
我们经常打架,打架的起因,大多是谁骂了谁一句“东亚病夫”。骂娘骂祖宗,都不会跟人急,骂别人一句“东亚病夫”,绝对要和你打架,追你几条街……
只有霍元甲是我们崇拜的英雄。当我们的英雄被毒死的时候,心里好难过,很多人都在流泪,流泪是要被嘲笑的,但坐在电视机前,看着心目中的英雄痛苦地死去而落泪,并没有人嘲笑。那时,心目中只有英雄,没有爱情。霍元甲,是我的英雄,也是他们的,他是我们整整一代人,或者一拨儿人的英雄。[2]

首先,这是一个私人化的生命独白,是关于一个(代)男孩成长的故事。而他(他们)成长中的喜悦、快乐、忧伤,命中注定地和一个叫霍元甲的人(荧屏形象)密不可分,霍元甲成了他生命记忆里不可磨灭的存在,犹如一面镜子烛照了他的生命,犹如一位教父引领了他的人生起点。其次,从这个关于男性主体建构的回忆文本中也能够看出民族话语对主体认同的深深介入。也许年少的他们不知道“东亚病夫”的确切含义,但他们知道这是洋人骂霍元甲、骂中国人最厉害、最恶毒的一个词,一个幼小的心灵怎能承担这个百年沉重的骂名?霍元甲影响着他们主体形成的同时也伴随着催生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小我”即“大我”,“我”愿意成为霍元甲———千万个神勇的中国人的代表/集合体。
电视剧《霍元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本,对当时国人的影响非同寻常,在此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通过将“国技”修炼到化境,以一个人凭身体的技艺打败一个个洋人,暗喻的是中国打败“洋国”完成“扬我国威”“振兴中华”的20世纪8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该剧将中国带入尚武时代,注入了尚武精神。电影《少林寺》更是推波助澜,有意味的是出家人并非不谙世事,十八罗汉救李王的故事不也蕴含着“历史的正义性”吗?出家人恰在国家之内并挽救了盖世明君(国家),也隐隐暗合20世纪80年代的宏大叙事: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全民总动员,改革开放,实现“四化”。金庸武侠小说盗版登陆和1983年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的播出,更掀起了武术热,新创刊的《武林》杂志非常抢手,全国各地城镇书摊上兜售各种门派的武术图解小册子。总之,民众的一个朴素的意识是,先从体魄上强健起来,做一个孔武有力的中国人,从有形可感的身体出发,从身体的搏击之技出发,振兴中华;对身体的形塑,是对身体即国体的一次“言说”。
一个/代男性主体建构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以及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等方面。通过上文的分析,大致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男性形象消费和男性主体建构的过程,“后文革”时期,旧的神殿坍塌了,革命英雄神像倾毁了,梦醒之后走向何方?国人陷入认同危机之中,一批外来影视剧的引入适时地填补了心理空白、情感空白和信仰空白。高仓健、阿兰·德隆、麦克·哈里斯、霍元甲……这一个个当时激动人心的名字,这一个个来自异域的形象、符号担负起重建人们精神认同的历史重任,这是20世纪80年代特有的文化现象。他们阳刚、潇洒、英俊、多情、强健、另类……他们身上没有僵硬的意识形态盔甲,被作为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来塑造,这些外来影像符号为国人打开了几十年不曾目睹的“想象的异域”和“异域的想象”。这些形象在无数受众心理中叠合、杂糅成一个个魅力十足、光彩照人的外来男性气质复合体,而它们直接通向“世界”。另一方面,即使是民族精神代言人的霍元甲,其“重整山河”“振兴中华”叙事也在20世纪8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心理之间找到最佳交会点,那么熨帖、舒畅。西方和未来这两个维度正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和中国人前行的“时空型”,所谓“面向世界”“走向未来”。在社会转型期,人们在认同的危机中,在认同角色紊乱中,捡拾、撮合、连缀起经验碎片,调适心理与社会关系,重建认同的对象和机制并由此发现自我、重构自我认同和主体意识,更主要的是建构起一种新的自我主体意识和民族国家主体意识的新型关系以及新的人生价值观。这样,从高仓健到霍元甲这些外来男性形象通过一种心理情感机制的隐秘逻辑转换获得了合法性建构。伴随新的影像世界产生的新的世俗生活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世界图景、精神情感世界,更主要的是由这些因素形塑的新的一代主体实在是无法禁锢的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改革开放铺展开来,势不可当。
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一份文学刊物动辄发行量数十万册,全国各地无数文学青年、文学爱好者做着作家梦,文学对20世纪80年代社会生活的影响不容小觑。改革文学塑造了一批“改革英雄”,他们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们被赋予为国家民族前行开辟道路的急先锋的大众形象,是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沙叶新的话剧《寻找男子汉》1986年在上海舞台演出,引起较大轰动。女主角最终找到意中人———一位充满改革锐气的年轻厂长。
因蒋子龙、张承志、张炜、张贤亮、邓刚、梁晓声、柯云路等一批男性作家创作了一批“硬汉”小说,上海女作家王安忆曾风趣地说:“近来,颇时兴男子汉文学。北方的一些男性作家,真正写出了几条铮铮响的硬汉。令人肃然起敬。令人跃跃欲试。”[3]这番话道出了当时一个客观文学事实、文学现象的存在。
这些小说中的硬汉往往具有如下性格特征:一、冷漠的外表下蕴含着深沉的情感;二、富有理想主义激情和坚忍不拔的意志;三、他们在精神上永远是不可战胜的。这类似于高仓健的银幕形象。
有学者注意到:“阳刚之美成为20世纪80年代主要的美学倾向”,一些小说“活生生地透露出一股使人灵魂震颤的阳刚之气”。“80年代,中国社会也将阳刚之气奉为上品。硬汉、男子汉,这些带着精神的名词,进入了中国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男性公民以自己豁达的、坚韧的、强劲的男子气质为荣耀”;“令人不可思议,整个社会都在崇尚这种性格”。[4]
的确,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似乎整个社会都在议论、呼唤、崇尚阳刚的男性气质,这并非“不可思议”,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背景。
“文革”后国人追求的是一种非崇高、非政治化、非英雄主义的世俗生活以及“走向未来”的现代性文化,这些男子汉品性体现了新的社会文化对男性气质的新规范。新的历史时空需要新意识形态来发动、引导民众以及进行新的制度设计,这就是改革话语和民族话语,而“寻找男子汉”是其在性别认同、情感认同以及人性化方面的突破口。
刊发《到哪儿去寻找高仓健》一文的编辑在编发该文后深有感慨地写了一篇《编者沉思》,其中写道:
她的失望,并不仅仅是对某些男人的失望,同样也包含了更深刻的内容———对我们民族素质的忧虑。
过去的经济体制,使得整个社会的人们在一个无忧无虑、有依靠的摇篮中度日,在这种摇篮中能成长出男子汉吗?……缺乏竞争的“大锅饭”经济体制,不仅降低了社会的生存能力,也同样降低了民族的、个人的生存能力。一个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跨入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一个这样的民族,怎么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创造生活?
今天,在涤荡平庸、锐意进取的今天,我们的民族还会缺乏男子汉吗?[5]
《中国青年》随后不久在《读者·作者·编者》栏目编发了三篇关于寻找男子汉专栏的读者讨论文章。《编者的话》指出:“我们中华民族要振兴、要腾飞,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不断优化我们的民族素质,不断发展我们优秀的民族精神,要更好地造就80年代的铮铮男儿。”在题为《奶油脂粉气影响下的男性素质》署名文章中,作者写道:“我们这个民族以往过多地宣扬了同高仓健形象相反的角色”;“奶油脂粉气影响我们民族的男性素质久矣!”“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我们若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需要重新锻造和倡导我们民族优秀的素质———首先是男性素质!”[6]
那位编辑将一位女读者的私人情感诉求转换、“升华”为“对我们民族素质的忧虑”,由个人问题而转化成民族、国家问题,在《编者沉思》以及随后的讨论文章中频频出现“民族素质”“民族精神”“民族的男性素质”“民族优秀的素质———首先是男性素质”等词语,还有其他有关的词语:“挑战”“崛起”“振兴中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在表现了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忧虑,表现出现代性的焦虑、开除球籍的危机感。这是一种集体意识的共同诉求,私人话语转换、汇集成整体性话语,20世纪80年代的男性气质实在表征了当时的现代化意识形态和强烈的民族意识。
无论是文学文本还是其他文本,都暗含着这样的推定:“男性素质”即“民族素质”,这流露出男性霸权意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对女性构成了遮蔽,而这一点在当时是被社会广泛认可的,包括女性。饶有趣味的是,“男子汉”话语是被女性呼唤、“寻找”出来的,《中国青年》那封引起广大讨论的女读者来信、小说《北方的河》、话剧《寻找男子汉》莫不如此,遵循着“缺失———寻找———找到”这样一个叙事链条。女性在男性主体建构中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她们的态度、立场、行为加快推动主流男性气概的形成。
综上所述,无论是影视、文学还是社会话语,都推崇男子汉担当起特定时期的历史使命。这样,无论是改革英雄还是平民男子汉,都凝聚着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国民心理的显要符号,是各方力量、话语交织、会合、形塑的显要符号。这一符号建构有着内在的历史逻辑的运作,通过它对接私人与大众、个体与民族的通道,发动各方社会力量汇入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这是一种迥异于“十七年”“文革”的20世纪80年代的新意识形态建构策略。从“男子汉”话语、“男性素质”话语到“民族素质”话语的转换,在“后文革”的特定历史时期完成了社会认同危机的摆渡和社会再出发的动员。“男子汉”不仅是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国民形象,而且更是国家形象、民族形象。男性主体某种意义上就是民族国家主体,重振“男子汉”雄风的男性化的民族国家主体意识在话语传播中获得一种新的自我定义和生命意义:扬我国威、振兴中华。20世纪80年代的寻找男子汉、塑造男子汉风潮其实是在隐喻的意义上呼唤百废待兴的中国尽快强健、“雄起”。就在男性和国家隐晦的叠合中,中华民族的腾飞梦想产生了,阳刚的男子汉气概就这样隐晦地参与到民族国家话语中来,参与到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意识形态构建中来。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
时过境迁,自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逐渐进入消费社会,一些沿海大城市已经很“后现代”。男性形象消费、男性气质话语和男性主体建构也逐渐脱离民族前途、国家命运和时代风潮等宏大叙事和主导意识形态,进入个体生命的“私人生活”,私人情感的隐秘领地,变得私人化、多元化、类型化、消费化。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20世纪80年代遭受唾弃的“奶油小生”“奶油脂粉气”的男性形象与气质,成为当今社会的宠儿,受到青睐。他们获得了新的命名,例如“花样美男”“中性男”“粉男”之类,还有所谓“暖男”“小鲜肉”等,甚至有人在媒体上鼓吹现在已进入“男色消费”时代。真是令人感叹今非昔比,社会变化如此之快。当然,这是一个新的关于男性气质的故事了。
注释
[1]《中国青年》1985年第2期,第20—21页。
[2]安然:《19年后,已经不是一条好汉》,《名牌》2003年第9期,第195页。
[3]王安忆:《我们家的男子汉》,《文汇报》1985年4月15日。
[4]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270—271页。
[5]同[1]。
[6]《中国青年》1985年第4期,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