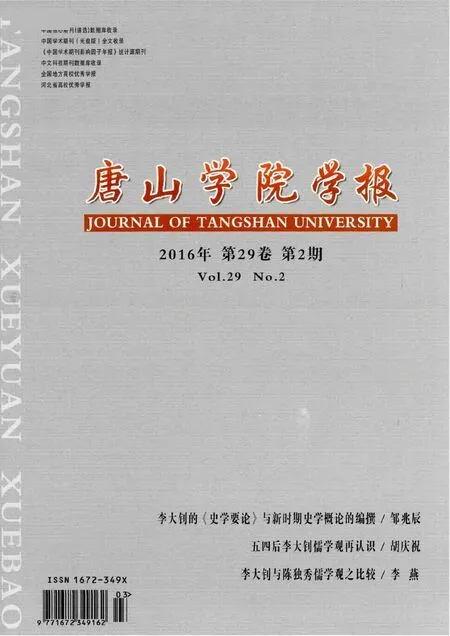试论陕北民歌对路遥小说艺术风格的影响
2016-02-13赵忠富
赵忠富
(唐山学院 文法系,河北 唐山 063000)
试论陕北民歌对路遥小说艺术风格的影响
赵忠富
(唐山学院 文法系,河北 唐山 063000)
摘要:陕北民歌是陕北人苦乐生活的艺术结晶,对生于斯长于斯的现实主义作家路遥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路遥的绝大部分作品都被陕北民歌所浸淫。在路遥的小说中,贯穿着理想与现实、浪漫与悲情的矛盾与纠结,悲情基调与浪漫气息的交织便成了路遥作品最显著的风格特征和艺术张力之所在。文章探讨了陕北民歌在路遥小说这一风格特征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陕北民歌;路遥小说;悲情基调;浪漫气息
通过对路遥小说和陕北民歌进行深入观照,可以发现作为陕北精神与风俗艺术结晶的陕北民歌,对于路遥小说创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就像陕北黄土高原开出火红的山丹丹花一样,陕北民歌的文化厚土也孕育了路遥的小说。路遥小说有两种迥异的风景:“壮士拂剑,浩然弥哀”的沉郁、悲慨之美和“如将白云,清风与归”的出尘、超诣之美。细心寻绎,不难发现,路遥小说所表现出的这种审美特质,都是可以从陕北民歌中找到依据的。
一、陕北民歌与路遥小说的悲情基调
沟壑纵横、黄沙漫天的陕北,自古以来便是兵燹不断、灾荒连连的“焦苦”之地,苦难出诗人,于是陕北民歌便应运而生了。学者吕政轩探讨陕北民歌起源时说:“如果有人问我,陕北民歌起源于何?我个人的回答是:陕北民歌起源于苦难。从根本上说,陕北民歌就是一种苦难的艺术。是人们在苦难的环境,苦难的生活中抒发出的一种苦难的情感。”[2]这一结论比较符合陕北民歌的原旨。不仅从起源论来说陕北民歌具有悲苦的色彩,单就陕北民歌的现状而言,“诉苦歌,在陕北民歌中也占有一定的数量,这是一个泪的海洋”[3]27。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沉潜于陕北民歌的话,就会发现几乎所有陕北民歌在格调上都带有“悲”的色彩:悲凉、悲壮、悲凄。
陕北民歌里有陕北人生存的悲凉。陕北近代以来就是一个地瘠民贫的所在,再加上水旱、蝗虫、鼠疫等灾害频仍,“穷百姓,把糠吞,沙蒿籽,当山珍。房舍塌,草枯干,树皮剥尽难生存,食无着,衣亦空,及儿女,且裸身。去冬冻,风更凶,饥寒饿毙近千名”(《榆林灾情歌》)。陕北人生存的艰辛是其他地方的人所无法想象的。陕北民歌《卖老婆》《卖孩子》便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展现了陕北人生存的悲凉。
陕北民歌里有陕北人抗争的悲壮。严酷的自然条件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悲苦生活,激发了陕北人对抗苦难的勇气和力量,他们以各式各样的营生来艰难挺进自己的人生旅程。《艄公谣》《父子揽工》《赶脚调》等陕北民歌正是陕北人生命抗争的悲壮歌行。
陕北民歌里有陕北人相爱的悲凄。由于生存的悲凉、抗争的悲壮,陕北人的爱情也往往是悲凄的。许多父母出于各自的利益打算,棒打鸳鸯,致使痴情男女相爱而不得其爱,就像陕北民歌《兰花花》《大女子要汉》中所记录的那样。即使个别人能够冲破封建桎梏而结合,但婚后贫寒困顿的生活,也使得相爱之人不能长相厮守,为了生计他们常不得不天各一方。《走西口》《绣荷包》便是他们离别时执手相看泪眼的无奈和隔绝中望穿秋水的无尽煎熬。
古人说民歌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饥寒劳顿的陕北人即是用民歌来描绘他们生存的艰辛、与苦难生活抗争的决绝,以及爱情的凄婉与无奈。悲凉之雾,遍披陕北民歌,呼吸而领会之者,陕北人也。路遥作为一个苍凉悲壮的陕北汉子,由于个人不同寻常的人生阅历(童年因家贫被过继于伯父、求学阶段的艰辛困顿、红卫兵运动前后的大起大落、初恋的不堪回首等等),最能体味陕北民歌悲苦的精神内核。路遥也将此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精神源泉,于是,他的作品总是弥漫着厚重的挥之不去的悲情气息。
和陕北民歌相仿佛,路遥作品的悲情基调也体现为主人公生存的艰辛、抗争的悲壮、相爱的无力。路遥的作品不仅在隐性方面具有陕北民歌的悲情基调,而且在显性方面有时还将陕北民歌作为营造悲情氛围、传达悲剧意蕴的手段。
《平凡的世界》中农民艺术家田万有唱的《祈雨调》:“晒坏的了呀晒坏的了,五谷田苗子晒干了,龙王的佬价哟,救万民!柳树梢呀水上飘,清风细雨洒青苗,龙王的佬价哟,救万民!水神娘娘呀水门开,求我神灵放水来,龙王的佬价哟,救万民!佛的玉簿玉皇的令,观音老母的盛水瓶,玉皇佬价哟,救万民!”他那“悲戚的音调”“哭一般的祈告声”,其实是陕北人于大旱之年对于上天的绝望呼告。路遥借助这首民歌,写出了陕北“十年九旱”的恶劣气候,正如流传于陕西榆林地区的民谣所描绘的那样:“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虽然已经解放二十多年,但陕北农民许多时候还是过着靠天吃饭、衣食无着的日子。于是,在实行责任组使温饱问题得以解决时,老农民孙玉厚就大发感慨道:“对于农民来说,不愁吃饭,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这是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啊!”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陕北农民所曾经历过的漫长的艰辛年月。
面对如此恶劣的生存状态,陕北人要么迎难而上,与焦苦的环境作殊死搏斗;要么另寻突破,以“出走”的方式完成个体生命乃至整个家庭命运的救赎。在路遥的作品中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孙少安,后者的代表人物主要是高加林、孙少平。但不管是哪一种抗争方式,等待他们的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平凡的世界》中写到孙少安从山西柳林买回大青骡子,经过黄河大桥时听到了陕北民歌《黄河船夫曲》:“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湾?几十几道湾里几十几条船?几十几条船上几十几根杆?几十几个艄公来把船扳?我晓得,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九十九道湾里九十九条船,九十九条船上九十九根杆,九十九个艄公来把船扳!”再加上听到歌曲前,路遥对周遭环境的淋漓铺陈:野兽般翻滚的浪头、刀削般的峭壁、黑青似铁的岩石、漫无边际的黄土山、艄公撕脑裂胆的叫喊、纤夫手脚并用的爬行……陕北汉子浪里觅生的情形如在目前。借助这首民歌,路遥写出了全体陕北人抗争命运的悲壮。同时,也预示了孙少安等坚守在陕北这块贫瘠土地上的有志青年,在走向成功的征程上必定会遭遇诸多的坎坷与磨难。后来孙少安在创办砖瓦厂过程中的一波三折,即是对于这首民歌的回应。
在窘迫的自然环境里,坚守固然不易,而在更加残酷、冰冷的城乡壁垒面前,“出走”又谈何容易。孙少平黄原揽工所经受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磨砺,虽然路遥一直是持着圣徒自我献祭的崇高感来对此进行描述的,可是孙少平肿胀的双手、被石头打磨得透明的皮肉、脊背上溃烂之后的干痂……却每每令读者不禁战栗而心生悲凉。城乡二元制社会结构之下,孙少平们进军城市的成功几率应该比旧时的“走西口”还要低。他们是否能够挺进城市?路遥也是心怀忐忑,于是在小说中路遥有意让孙少平的人生奋斗止步于大牙湾煤矿这样一个“城乡交叉地带”,甚至于为了实现这个结局,路遥不惜为孙少平制造矿下事故,剥夺了他完美的形象。其实路遥对于孙少平结局的忧虑,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就已露端倪。黄原揽工时,路遥借揽工汉“萝卜花”之口唱了一首“走西口”题材的民歌,来暗示孙少平未卜的前程:“格格英英天上起白雾,没钱才把个人难住。二绺绺麻绳捆铺盖,什么人留下个走口外?黑老鸹落在牛脊梁,走哪达都想把妹妹捎上。套起牛车润上油,撂不下妹妹哭着走。人想地方马想槽,哥想妹妹想死了。毛眼眼流泪袄袖袖揩,咱穷人把命交给天安排。叫声妹妹你不要怕,腊月河冻我就回家……”“把命交给天安排”七个字真实地展现了孙少平黄原揽工的朝不保夕,同时也预示了大牙湾掏煤的命悬一线。在改革大潮蓄势而起、城乡体制坚冷如故的年代里,孙少平等励志有为的农村知识青年好似风飘之絮、雨打之萍,其命运有时确是由“天安排”的。
说你情商低,是提醒你还有许多上升的空间;说你不够自律,是看到了你自律后的无限未来;叫你要自觉,其实是在说你被监督下表现还是不错的,但监督人最好是你自己……
因为自己悲苦初恋的切身体验,路遥对陕北民歌里的爱情悲剧最能感同身受。他在作品中所着力刻画的爱情故事大都以悲剧散场,而少有圆满的结局。《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开头,在介绍双水村由来的时候,路遥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玉皇大帝的一个女儿游玩凡间时,爱上了这里的一个金姓后生,并因此推迟了归天的期限,被玉帝变成了一座黄土山,后来当地人谓之神仙山。她那金姓的爱人,便日日跪在山脚之下呜咽啼哭直至死去,眼泪化为一条小河,是为哭咽河。这样一段凄美的爱情,感化着双水村的每一位多情男女,同时也如同谶语一般牵引着一出出爱情悲剧的端绪。于是乎,神仙山下、哭咽河边,双水村的性灵儿女都在演绎着各自的爱情悲歌。孙少安与田润叶的擦肩而过、金波与藏族姑娘的天涯两隔、孙少平与田晓霞的人鬼殊途、孙兰香对王满银的无悔守候……甚至像孙少安与贺秀莲风雨久同舟、田润生与郝红梅两情已相许的夫妇,还要遭受命运黑手的摆布与世俗偏见的排斥。为了增强爱情悲剧的感染力,路遥还有意援引陕北民歌作为对悲剧爱情的催化与升华。比如在孙少安与田润叶的爱情悲剧里,路遥前后五次援引陕北民歌《正月里冻冰立春消》:“正月里冻冰呀立春消,二月里鱼儿水上飘,水呀上飘来想起我的哥!想起我的哥哥,想起我的哥哥,想起我的哥哥呀你等一等我……”这首民歌一方面展现了田润叶对孙少安的一片痴情,另一方面也充当了两人悲剧爱情的预言与挽歌。
二、陕北民歌与路遥小说的浪漫气息
陕北是一片焦苦的土地,“生活在黄土地上的陕北人民,面对黄土背朝天,耕黄土,喝黄水,吃黄米、黄豆,死后留下的是一抔黄土埋尸骨”[4]。不过单调的自然、单调的生活并没有泯灭陕北人对于理想的执着追求,“这一点,可以从很多陕北窑洞里的炕围子画中得到启示。陕北人从不把瘦水寒山安置在自己的居室中,也不把陕北的地方花种山丹丹花,连同俯拾皆是的豆类植物用艺术的形式再现出来。相反,与这块土地相隔甚远或毫无挂碍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奇山怪石却纷至沓来。陕北人不尚黄色,也不尚蓝色,却极力推崇红色,裤带是红的,腰带是红的,头绳是红的,汗衫是红的,就连小兜肚也是红的。这尽管与上古谶纬有一定关系,但也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陕北人颇为红盛的生命理想”[5]。
单调的环境、贫乏的生活非但没有损伤陕北人对于理想的追求,反倒催生助长了陕北人的丰富想象力。弗洛伊德说:“我们可以断言,一个幸福的人从来不会去幻想,只有那些愿望难以满足的人才去幻想。幻想的动力是尚未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都是对令人不满足的现实的补偿。这些充当动力的愿望因幻想者的性别、性格和环境的不同而各异。”[6]61陕北民歌便是陕北人对于自己贫瘠单调生活、生命的艺术补偿,因而极具幻想色彩和浪漫气息。
秧歌舞出美好生活。陕北秧歌是流行于陕北榆林、延安等地的传统的集体性娱乐活动,最初起源于迎神赛会,与屈原的《九歌》相仿佛。王克文先生指出:“陕北人过去称闹秧歌为‘闹红火’。长期艰苦的劳作和单调的生活,养成了陕北人喜好红火的习惯,‘烂裆裤子漏水锅,没钱还爱些穷红火’。”[3]245称秧歌为“红火”,本身就传达了陕北人想借此闹出理想生活的美好愿望。关于陕北秧歌,吕政轩在其《民歌·陕北》一书中有专章探讨,在该书中作者为我们展现了陕北秧歌演出的全过程:谒庙-转院-大场-小场-路遇-彩门-过街-转九曲,其中所列的许多秧歌歌词都蕴含了对美好生活的希冀。
揽工揽回娇美佳人。陕北民歌的幻想色彩与浪漫气息,一方面体现于对富足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体现于对美好爱情的期待。弗洛伊德曾经虚构过一个“孤儿的白日梦”:“我们以一个贫穷的孤儿为例,你已经给了他某个雇主的地址,他也许在那里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在去看雇主的路上,他可能沉湎于与产生当时的情况相适应的白日梦之中。他幻想的事情或许是这类事情:他找到了工作,并且得到新雇主对他的器重,自己成为了企业里举足轻重不可缺少的人物,进而被雇主的家庭所接纳,与这家的年轻而又妩媚迷人的女儿结了婚。随后又成为了企业的董事,初始是作为雇主的合股人,再后来就成了他的继承人。”[6]62从《五哥放羊》这首民歌里,我们发现中国西北部黄土高原上的揽工汉们也做着同样的幻梦。
受陕北民歌的影响,路遥的作品中也氤氲着浪漫的气息。并且与陕北民歌相似,路遥小说的浪漫特质也突出地表现在诗性的生活和传奇的爱情两个方面。
对严酷生活的诗性超越。在路遥的笔下,由于频仍的自然灾害和“极左”的政治路线,陕北百姓的生活许多时候处于“苦焦”的境地。但“苦焦”的陕北人对这生活却有着无限的热爱。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不厌其烦地为我们描绘了双水村正月里的秧歌盛会:“一旦进入正月,双水村的人就像着了魔似的,卷入到这欢乐的浪潮中去了。有的秧歌迷甚至娃娃发烧都丢下不管,只顾自己红火热闹。人们牛马般劳动一年,似乎就是为了能快乐这么几天的。”秧歌能够叫大人忘记自己生病的娃娃,连那些他乡的游子也像逢年过节似的不辞辛劳地往家赶。“这几天,双水村几乎所有在门外工作的干部和出嫁在外的女人,都赶回到亲爱的故乡来——他们有的情不自禁地上场露两手;不上场的就挤在人群中间如痴如醉地观看。”像孙玉亭这样立场分明的革命同志,在秧歌排练中“也临时放弃了阶级立场,和地主的两个儿子坐在了一条板凳上闹‘五音’”。在陕北,秧歌舞一般要求本土群众人人都要参与进来,在秧歌里抒发自己的欲求与情感,进而使自己低沉的灵魂得到抚慰和升华。
除过闹秧歌,双水村还有一个盛大的节日——“打枣节”。“农历八月十四日,双水村沉浸在一片无比欢乐和热闹的气氛中。一年一度打红枣的日子到来了——这是双水村最盛大的节日!这一天,全村几乎所有的人家都锁上了门,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提着筐篮,扛着棍杆,纷纷向庙坪的枣树林里涌去了。在门外工作的人,在石圪节和县城上学的学生,这一天也都赶回村里来,参加本村这个令人心醉的、传统的‘打枣节’……妇女们头上包着雪白的毛巾,身上换了见人衣裳,头发也精心地用木梳蘸着口水,梳得黑明发亮;她们一群一伙,说说笑笑,在地上捡枣子。所有树上和地上的人,都时不时停下手中的活,顺手摘下或拣起一颗熟得酥软、红得发黑的枣子,塞进自己的嘴巴里,香喷喷,甜咝咝地嚼着。按老规矩,这一天村里所有的人,只要本人胃口好,都可以放开肚皮吃——只是不准拿!”“田万有也能俏地爬到枣树上去了!他拿一根五短三粗的磨棍,一边打枣,一边嘴里还唱着信天游,把《打樱桃》随心所欲地改成了《打红枣》——‘太阳下来丈二高,小小(的呀)竹竿扛起就跑,哎噫哟!叫一声妹妹呀,咱们快来打红枣……’地上的妇女们立刻向枣树上的田万有喊道:‘田五,亮开嗓子唱!’爱耍笑的金俊文的老婆张桂兰还喊叫说:‘来个酸的!’田五的兴致来了,索性把磨棍往树杈上一横,仰起头,眯起眼,嘴巴咧了多大,放开声唱开了——‘叫一声干妹子张桂兰,你爱个酸来我就来个酸!绿格铮铮清油炒鸡蛋,笑格嘻嘻干妹子你硷畔上站;绒格墩墩褥子软格溜溜毡,不如你干妹子胳膊弯里绵……’妇女们都笑得前伏后仰,张桂兰朝树上笑骂道:‘把你个挨刀子的……’。”对于终年辛劳、贫苦的陕北人,几颗红枣便能够带来如此巨大的欢乐,陕北人的乐天精神于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平凡的世界》中还有一首孙少平工友元宵节所唱的“酒曲”,更能体现陕北民歌的浪漫特质:“人穷衣衫烂,见了朋友告苦难,你有铜钱给我借上两串,啊噢唉!我有脑畔山,干阳湾,沙蓬黄蒿长成椽,割成方子锯成板,走云南,下四川,卖了钱我再给老哥周还!”在民歌里“人穷衫烂”“伸手借钱”的窘境,借助“沙蓬黄蒿长成椽,割成方子锯成板”的浪漫幻想便得到了飘逸的飞升与超越。
路遥在作品中虽然极力渲染陕北人的乐天精神,但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笔下的人物对于现实生活的超越过程又往往是艰辛而悲壮的,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等等莫不如此。可以说,面对同样艰辛的现实,陕北民歌往往是飘逸的飞跃,而路遥的小说则一般是顿挫的攀援。
对于世俗爱情的传奇演绎。如果说在对待严酷生活时,路遥是现实胜过理想、理性多于感性,那么在对待爱情时,则常常是感性与理想胜出。可能是出于对主人公悲苦命运的一种平衡,也可能是对于作家本人爱情缺憾的弥补,在路遥的笔下主人公的爱情总是具有传奇色彩,甚至有时落入才子佳人的窠臼而不辞。《人生》中高加林在民办教师职位被大队书记的儿子高三星挤占后,却得到了被誉为“盖满川”的俊俏女子刘巧珍的追求。做了县委通讯干事以后,又得到了“有文化,聪明”且出身于干部家庭的漂亮姑娘黄亚萍的垂青。高加林的爱情完全是古代才子佳人小说中,“才子落难,佳人相助”“金榜题名,相府招亲”的浪漫而陈旧的套式。另外,灵转姑娘——旅店老板的女儿爱上了青年脚夫(德顺),并且私下相许,可谓是一场真人版的《赶牲灵》。《在困难的日子里》中,来自贫苦农民家庭的马建强,受到了班里生活委员县武装部长的女儿吴亚玲细心的关怀与帮助。《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中,老实巴交的农村教师高广厚,在被妻子抛弃后,得到了教育局副局长的妹妹卢若琴的同情与帮助。虽然马建强和吴亚玲、高广厚和卢若琴的关系被作者严格限定在朋友的范围之内,但这份弥足珍贵的友情对于马建强和高广厚而言同样是浪漫而温馨的。
《平凡的世界》中,路遥更是将爱情的浪漫演绎到了极致。为了给笔下的浪漫爱情一个文化和文学的依据,在小说开始时,路遥为读者讲述了神仙山和哭咽河的古老传说,如前所述这是一则以悲剧告终的凄美爱情故事,但玉帝之女不顾一切地与凡俗男子相恋、相守,这种身份的悬殊把爱情的浪漫推向了极致。受此精神感召,神仙山下、哭咽河旁,上演了一幕又一幕以双水村性灵儿女为主角的爱情传奇。孙兰花爱上了游手好闲的“二流子”王满银;在县城工作的公办教师、大队支书的女儿田润叶爱上了泥腿把子孙少安;大学生、省报记者、省委副书记的女儿田晓霞,爱上了揽工汉、掏煤工孙少平;大队书记的儿子、长途汽车司机田润生爱上了带着孩子的寡妇郝红梅;大学生金秀将学识、家境都很优秀的顾养民拒之于心扉之外,而向身体已残的掏煤工孙少平敞开了少女的情怀;金波更是因一首民歌爱上了言语不通的藏族女孩;等等。路遥将一些在世俗眼光看来匪夷所思的童话般爱情,讲述得“振振有词”,铿锵有力。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路遥笔下的这些传奇爱情最终少有圆满的,或因无情的生活现实(田润叶和孙少安)、或因顽固的世俗偏见(金波和藏族姑娘)、或因作者的有意而为(贺秀莲的积劳沉疴、田晓霞的意外牺牲),相爱之人最终擦肩而过或阴阳两隔。在路遥的作品中,总是充满着理想与现实、浪漫与悲情的矛盾与纠结。路遥的文学创作肇始于悲苦的现实,又将浪漫的理想、爱情作为补偿与点缀,不过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这浪漫的理想和爱情最终又化为深深的喟叹。总之,悲情也好,浪漫也罢,不可否认的是,路遥小说的艺术风格都可以从陕北民歌中找到端绪。
参考文献:
[1]丹纳.艺术哲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
[2]吕政轩.民歌·陕北[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113.
[3]王克文.陕北民歌艺术初探[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4]姬乃军.黄土魂[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24.
[5]惠雁冰.无力的出走:历史上陕北民歌的精神主题[J].广西社会科学,2003(2):122-124.
[6]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第七卷[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
(责任编校:白丽娟)
法国艺术理论家丹纳曾指出:“如果我们想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我们就必须要认真考察他们所生活时代的精神与风俗状况。可以这么说,时代精神和风俗状况是产生艺术品、艺术家的根本,它起到决定性的作用。”[1]2艺术品和它所产生的时代的精神及风俗状况的关系,就如同植物与地域的关系一般,“从南方走到北方,可以看到,每个不同的地域都有自己独特的作物与草木,这是因为这些地域的气候决定了什么样的作物与草木可以生活在这里,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用时代的精神和风俗状况来考察某种艺术出现的原因”[1]2。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Northern Shaanxi Folk Songs on the Artistic Style of Lu Yao’s Novels
ZHAO Zhong-fu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Law, Tangshan University, Tangshan 063000, China)
Abstract:The North Shaanxi folk songs are the artistic crystallization of the Northern Shaanxi bitter-sweet life and have deeply influenced the native realistic writer of Lu Yao,most of whose works originate from the Northern Shaanxi folk song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idealism and realism, romanticism and sentimentalism runs though Lu Yao’s novels.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tragic tone and romantic atmosphere is a striking feature and artistic tension of Lu Yao’s works. This paper is meant to explore the role of the Northern Shaanxi folk songs in the formation of this style in Lu Yao’s novels.Key Words: Northern Shaanxi folk songs; Lu Yao’s novels; tragic tone; romantic atmosphere
作者简介:赵忠富(1982-),男,河南商丘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6)02-0054-06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6.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