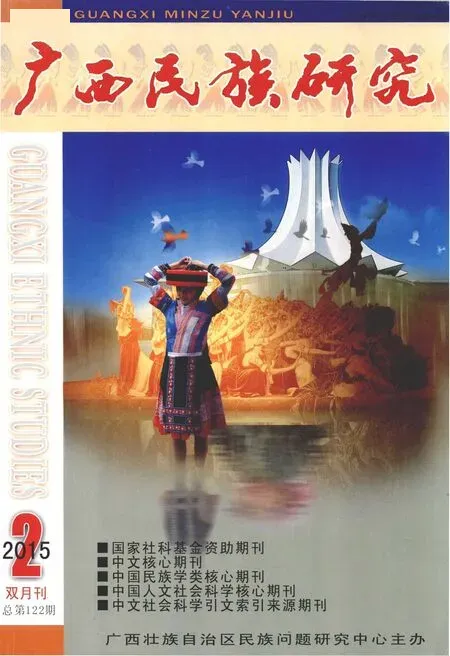明代烟瘴对广西土司区经略的影响
2015-12-12赵桅
赵 桅
烟瘴,又称为“瘴气”“瘴疠”“瘴虐”“炎瘴”等,文献记载中名目不一。学者们对于这些不同的名称含义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瘴气多为恶性疟疾,有人认为是一种热带疾病,还有人认为高原反应也属于瘴。周琼老师对瘴、瘴气、瘴疠做了辨析,认为瘴有各种不同的种类,分为气体形式的瘴气和液体形式的瘴水,人因为感染瘴而在身体上显现出不适等疾病症状,被称为瘴疠。[1]42-82本文赞同周琼老师的看法,以烟瘴一词来统一称呼在南方地区因自然环境而呈现出瘴的现象。烟瘴曾在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区域性突出,对我国南部边疆民族及社会产生较大影响。自20 世纪90年代以来,渐成热点,在疾病史、环境史、社会史等方向的研究中均有涉及,成果不断涌现。国内关于瘴气的研究,以周琼、张文、左鹏、于赓哲等学者建树为多。已有的研究大概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关于什么是瘴的辨析,有恶性疟疾、热带病、高原反应等多种看法。①周琼.藏区“冷瘴”新辩[J].中国藏学,2008 (1);梅莉,晏昌贵,龚胜生.明清时期中国瘴病分布与变迁[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 (2);朱力平.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疟疾流行史概述[J].思想战线,2009 (S1);朱建平.我国古代关于地理环境与人类疾病的探讨[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1 (12);左鹏.瘴气之名与实商榷[J].南开学报,2011 (5);冯翔.关于宋代至明代南方的瘴病及其历史的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 (2);于赓哲.中国古代对高原(山)反应的认识及相关史实研究——以南北朝、隋唐为中心[J].西藏研究,2005 (1).二是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分析不同时期烟瘴的消长变化,比如龚胜生等人的论文就总结出瘴病的分布呈现逐步南移和缩小的趋势,其分布与地理环境、土地开发、经济发展等因素有关。①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J].地理学报,1993 (4);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疟疾地理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6 (4);张轲凤:从“障”到“瘴”——“瘴气”说生成的地理空间基础[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 (2);周琼.清代云南潞江流域瘴气分布区域初探[J].清史研究,2007 (5);周琼,李梅.清代云南生态环境与瘴气区域变迁初探[J].史学集刊,2008 (5).三是从环境和疾病史出发,对瘴以及由此引起的疾病进行研究,探讨成因和影响。②周琼.清代云南瘴气环境初论[J].西南大学学报,2007 (5);于赓哲.疾病与唐蕃战争[J].历史研究,2004 (5);于赓哲.疾病、卑湿与中古族群边界[J].民族研究.2010 (1).四是从文化角度入手,将瘴及其相关事务视作一个符号进行再诠释,比如左鹏、张文等学者的文章,认为瘴是中原中心观之下的产物。③刘祥学.当今边疆地区环境史视野下的“瘴”研究辨析[J].江汉论坛,2013 (6);张文.地域偏见和族群歧视:中国古代瘴气与瘴病的文化学解读[J].民族研究,2005 (3);左鹏.汉唐时期的瘴与瘴意象[C]//唐研究(第8 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左鹏.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2004 (1).五是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瘴气进行论说,比如黄冬玲对于壮族瘴气流行的考察。④黄冬玲.壮族地区瘴气流行考证[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1999 (2);黄冬玲,壮族对瘴气防治的贡献[J].广西中医药,1991 (5).六是从瘴对于地区影响来看中央治边政策,边疆人口分布等问题。⑤张陈呈.试论明清时期瘴气对广西社会产生的影响[J].广西地方志,2007 (1);马强.唐宋西南、岭南瘴病地理与知识阶层的认识应对[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 (3);苍铭.烟瘴对乾隆时期西南边防政策的影响[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9 (1);马强.地理体验与唐宋“蛮夷”文化观念的转变——以西南及岭南民族地区为考察中心[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 (5).
但专就烟瘴与土司制度相联系的论文还不多见。明代广西土司区烟瘴盛行,成为明朝经营和管理的主要障碍。本文拟以广西土司区为例,借助文献资料,探讨烟瘴与明朝对于土司区治理的困难以及相应举措,反映明朝对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的客观性。以及烟瘴作为一种现象,对于南方少数民族及社会的重大影响,试图表明烟瘴与明朝在南部少数民族地区继续实行土司制度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也是广西地区土司制度长存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明代广西土司区的烟瘴分布
明洪武初年,对前元归顺的土司、土官,均采取了原官授之的策略。对于广西土司区的分布,大家意见不一。《明史·广西土司》记载:“广西惟桂林与平乐、浔州、梧州未设土官。”[2]8202其他地区均有土司设置。《古今图书集成》记载:“广西布政司领长官司三,隶兵部武选司。土官一百九十七,其中知府四人,知州三十三人,同知一人,知县六人,县丞一人,主簿一人,典史二人,巡检十三人,副巡检一百二人;嘉靖初年,设知州一人,吏目一人,巡检二十八人,改流知州二人,流知县二人,以上均隶吏部验封司。”[3]20446-20447但据龚荫先生考证,他认为有明一代,广西地方曾设置土官340 多家,其中桂林府设置土司12 家,平乐府有土官32 家,梧州府设置土司24 家,郁林直隶州设置土司22 家,浔州府设置土司32 家,柳州府设置土司67 家,庆远府设置土司30家,南宁府有土司14 家,上思直隶厅有土司两家,思恩府有土司15 家,百色直隶厅曾有土司27家,泗城府设置土司12 家,镇安府设置土官6 家,归顺直隶州有土司4 家,太平府有土司42家。[4]798-914这些土官设置时有存废,改流、复土反复不断,但广西土官以文职土司为主,以土知州、土知县、土巡检、土驿丞为多,分布区域比较广泛,但仍以广西西部左右江和红水河流域比较集中。

表一 广西土官分布及隶属
这些广西土司分布区恰恰也是广西烟瘴严重的地区。据章璜《图书编》卷40 《广西各府州县烦简》所载,直到明末,广西左右江土官中的太平、思恩、思明、镇安等都是瘴区,瘴区与土司分布区基本一致。

表二 广西土司区烟瘴情况描述
东部地区烟瘴相对较少,但各个府县均有分布,甚至北部的桂柳地区也有烟瘴存在,比如桂林府下的永福县、柳州府的罗城县等。甚至出现因瘴而使得官兵在两地轮流驻扎的情形,比如明英宗时期,广西柳州府知府曹衡奏:“比年镇守总兵等官皆屯兵桂林府,去柳州府窎远,蛮贼出没卒难援救。每年九月至次年三月天气清和,宜于柳州府操备,四月至八月天气炎瘴,回桂林府驻劄为便。”[5]11-12而为明英宗采纳。这种烟瘴肆虐的情形一直延续到清代,直到清乾隆年间,太平府下辖的佶伦、结安、都结、茗盈、宁明、凭祥,泗城府下辖的凌云、平乐以及庆远府的东兰,思恩府的百色以及镇安府的向武州都是朝廷认定的水土恶劣之区。[6]849
二、烟瘴与明朝对广西土司区经略的困难
明代广西土司区烟瘴盛行,成为明朝经营广西土司区的一大障碍。烟瘴的长期存在,使得明朝在官员选派、地方治理程度、卫所防御等多方面表现出与中原不一样的特点,从而导致明朝在土司区的治理和经略上呈现一定的困难。
首先,面对的第一个难题便是官员派选。派驻官员是朝廷对地方实行管理的第一步,只有人员到位,才能传达朝廷政令,有效开展工作。然而,广西是中原士人眼中的蛮烟瘴雨之区,因此被派官员普遍存在畏瘴情绪,同时,官员因触瘴而身亡的情形也频频发生。这类事例很多,广西监察御史舒晟曾上奏说:“广西地方病,故官员多因水土不服,瘴疠易侵,见任官员气息奄奄,朝不及夕。”[7]181大臣孔镛“历仕三十余年,皆在边陲”,结果“触瘴成疾”。[2]4601又比如正德年间,胡尧元“以功擢升广西参政,以征思恩”[8]261,结果触冒烟瘴,卒于桂林。官员的不服水土,使得外来汉官在土司区任职常常忧心性命,畏瘴情绪严重,因瘴而不赴任,因瘴而亡的情况不少,使得广西土司区外派官员流于形式,流官入职率相对较低。
其次,烟瘴的横行使得广西土司区地方治理程度薄弱,突出表现在明朝的地方官吏在日常事务,比如审案治狱上存在一些困难。史载:“广西左右两江,旧设土官衙门大小四十九处,蛮性无常,仇杀争夺往往不绝。朝廷每命臣同巡按御史三司官理断,缘诸处皆是瘴乡,兼有蛊毒,三年之间遣官往彼,死者凡十七人,事竟未完,今同众议,凡土官衙门,除军务重事径诣其处,其余争论词讼宜就所近卫所理之。左江太平、思明、龙州、崇善等处于太平千户所,右江田州、镇安、泗城、上林等处于奉议卫,思恩州于南宁卫,南丹、东兰、那地三州于庆远卫,各令土官及应问之人克期来集,以俟理断,庶免瘴患,事亦易完。”[9]1936而明朝廷对此也深以为是,认为抚驭蛮夷当从简略,如果事情艰难,亦当择便。“议者既以为宜,其从之。”[9]1936由于烟瘴,原本设在地方佐贰的流官官府职能在一定程度上缺位,而一些官员畏瘴又寓居府城,不在任区履职,更是削弱了对地方的治理。比如广西荔波县的正官就因为所管地方有烟瘴,而且道路险阻,又无城郭,一直以来居住在郡城。此事被人劾奏,认为“僦居郡城,殊非设官之意,应责令县官即入县驻扎”[10]3-4。
第三,广西土司区卫所迁移现象不时发生,官军因瘴或逃或亡的现象较多,卫所的守御戍守之责削弱。明朝在平定广西之后,建立了大量的卫所,驻军屯戍。史载“明代广西领府十一,州四十七,县五十三,又羁縻长官司四,而卫所参列其中”[11]4791。据嘉靖《广西通志》记载,明朝先后在广西设立了11 个卫,21 个千户所和许多巡检司,[12]卷2其中一部分卫所设在土官周围及其辖地范围内。比如洪武二十八年(1395),“南丹土官莫金叛,帝命征南将军杨文,龙州平后,移师讨南丹、奉议等处。……大军进征奉议,调参将刘真分道攻南丹,破之,执莫金并俘其众。后遣宝庆卫指挥孙宗等,分兵击巴兰等寨,蛮僚俱,焚寨遁去,官兵追捕斩之,蛮地悉定。诏置南丹、奉议、庆远三卫,以官军守之。”[2]8208由此可见,朝廷设置南丹卫的目的还是在于防范该地土官叛乱。其他设置在土司区的卫所也一样,洪武二十一年(1388),“广西布政司言向武州叛蛮梗化。时都督杨文佩征南将军印,讨龙州、奉议等处,复奉命移师向武。文调右副将军韩观分兵进讨都康、向武、富劳诸州县,斩世铁。以兵部尚书唐铎言,置向武州守御千户所。”[2]8267-8268显然,向武守御千户所的设立也是为了防范土官叛乱之用。然而因为烟瘴,使得卫所守御屯戍之职责大打折扣,兵员缺乏,难以久驻。突出表现在两点:一是因瘴而迁卫所现象不时发生。明英宗时期,黄润玉擢升广西佥事,提督学政。就因“南丹卫处万山中,戍卒冒瘴多死,为奏徙夷旷地。”[2]4386因此为朝廷采纳,迁广西南丹卫于宾州千户所,奉议卫于平南县,向武千户所于守御贵县中前千户所。而理由正如安远侯柳溥所奏:“广西所属南丹、奉议二卫,向武千户所城池俱在烟瘴之地,气候不正,官军相继死亡者不知其数,而存者百有二三,亦多疲病,不堪备御,乞迁南亢地方以免其患。”[5]4-5正因为烟瘴,官兵死亡,所以不得已需要迁离原处,以避瘴患,或者让官兵在两地轮流戍守。二是部分官兵水土不服,触瘴身亡,以至损耗严重,兵员缺失。永乐初,“调湖广、贵州军征广西蛮,遂留戍其地。……然水土不习,多至病死,间逃亡不赴者,法不能尽绳也。”[13]1050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内管领旗军潘新三等一百五十四名前往广西,听副总兵征蛮将军都督武毅调拨郁林州等处哨守。景泰元年(1450)至景泰二年(1451)八月内,瘴疫传染,陆续病故六十名,在逃二十名,只有七十四名回卫。[7]180在一年半的时间内,一半以上的士兵因为烟瘴或死亡或逃匿,使得卫所士兵的驻守变得艰难。英国公张辅等就曾向朝廷表明,“广西官军每因瘴疠死亡逃窜,比之国初十无二三。”[14]189由此可见官兵的伤亡情况。一方面是官兵因瘴而亡、而逃的大量损耗,另一方面是驻扎在卫所的官兵因为烟瘴而无法久驻的困境,使得广西兵员缺乏,因此时常有将领向朝廷要求增员补充。比如明宣宗时,总兵官都督山云言:“广西武宣守御千户所城池低洼,瘴疠特甚,原伍官军一千五百八十二人,今存四十七人,力难守备,乞以法司问发充军罪囚益之。”[9]1692湖广都察院右都御使李实也奏称:“递年轮班广西征进官军每年蒙拨哨守浔、梧等州,大藤等峡,为因感患山岚瘴气,死者一年每卫所一班不下百十余名,不免要军拨补。”[7]180
三、烟瘴与广西土司区的以土治土
正是由于烟瘴的存在,使得明代对于广西土司区的经略呈现跟中原不一样的特点。元明以来,中央王朝对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任用少数民族首领管理地方,世长其土,世有其民。但一旦条件成熟,都希望改土归流,纳入中央直接管理范围之内。有明一代,广西土司区在改流与设土之间多次反复,朝堂内“设土派”与“改流派”论争不已,“设土论”者论据之一便是土司地区的烟瘴问题。正因为烟瘴肆虐,使得明朝很难对于土司区建立直接有效的统治,派驻的官员畏瘴情绪严重,卫所守御职能削弱,地方的有效治理很难触及土司腹地。这些都使得明朝对于广西土司区的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只能倚靠土官,以土治土。
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明中期以来不断增设品秩小的土官,甚至将流官所管地方也改设土官进行管理。正统四年(1439),土官莫祯曾奏云:“本府所辖东兰等三州,土官所治,历年以来,地方宁静;宜山等六县,流官所治,溪峒诸蛮,不时出没。原其所自,皆因流官能抚字附近良民,而溪峒诸蛮恃险为恶者,不能钤制其出没。每调军剿补,各县居民与诸蛮接纳者,又先漏泄军情,致贼潜遁。及闻招抚,诈为向顺,仍肆劫掠,是以兵连祸接无宁岁。臣窃不忍良民受害,愿授臣本州土官知府。流官总理府事,而臣专备蛮贼,务擒捕殄绝积年为害者,其余则编伍造册,使听调用。据岩险者,拘集平地,使无所恃。择有名望者立为头目,加意抚恤,督励生理。各村寨皆置社学,使渐风化。三五十里设一堡,使土兵守备,凡有寇乱,即率众剿杀。如贼不除,地方不靖,乞究臣诳罔之罪。”[2]8209明英宗阅览之后,极为赞赏,“即敕总兵官柳溥曰:以蛮攻蛮,古有成说。今莫祯所奏,意甚可嘉,彼果能效力,省我边费,朝廷岂惜一官,尔其酌之。”[2]8209由于朝廷的赞许,明中期以来,陆续增置了不少土官。比如增置广西浔州府桂平县大宣乡巡检司、平南县大同乡巡检司、秦川乡巡检司、南宁府武缘县那马寨巡检司、镆铘寨巡检司、平乐府恭城县白面寨巡检司土官副巡检各一员。这一地区因为地处大藤峡区域,瑶、苗、壮等少数民族较多,起义不断,于是广西总兵官镇远侯顾兴祖就曾奏言:“广西桂平、平南、恭城、武缘诸县地近猺贼,出没不时,各处流官巡检多死瘴疠,若增置副巡检,选土人相兼莅事,庶几可以镇服。”[9]149-150希望以土治土,流土兼治。“韩襄翼移上隆知州于藤峡,置武靖州及五屯之设土吏目周冲等司,设副巡检。王文成不欲废田州,又置九巡司,令各以其俗自治,皆有深意。今异类所盘踞,至百数十里,全无名村相错者,良自不少。诚立之君长,署为部落,使自为政,而守令于司土者,可以省郡县钳制之力,可以需征剿调发之令。其策似为更变。”[12]卷60
甚至在一些已经设置流官管理的地方,因境内族群众多,烟瘴盛行,流官并不能很好地建立起统治,于是就有官吏上奏,建议在流官地方也改设土官来进行管理。如明英宗时期,广西左布政使揭稽等奏:“所属土官地方夷獠帖然安靖,惟流官地方内多猺、獞、狑、蛮数种,散居深山不入版图,专事劫杀,虽有官军哨守,严则暂时退伏,缓则辄出攻掠。况兼岚瘴毒沴,戍卒染病死亡无算,军民日渐消耗,蛮贼日加猖獗,究其所由,盖无土官钤束故也。乞遣在廷重臣一员来,同布、按二司堂上官遍历取勘,因其地方择其类所信服者,立为世袭土官,开设衙门,庶为长治久安之计。设有顽梗不服土官统理者,就调土兵剿捕,以夷攻夷,万无不克,将见数年之后,尽为良民,军民可以安业,总戎亦可以班师矣。”[5]6-7从上述言论可以看出,本着以夷制夷的目的,设置土官才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二是重用土官,倚重土兵。有明一代,广西境内起义叛乱频发,面对卫所官兵缺员严重,战斗力较弱的情势,明朝廷就对土兵格外倚重。早在明太宗时,就有臣下上奏:“臣往广西抚谕桂林诸郡,蛮寇皆已归化,窃谓此辈多是徭、僮,已尝作乱未尽歼夷,穴处岩居,惟事剽掠,今虽革面,终然异心,如理定县首贼韦香等先皆向化,今复为非,重劳官军深入剿捕。臣思此贼别无技能,惟倚恃岩险,出没不时,兵至则散匿溪洞,兵退时出劫乡村。官军皆非本处之人,不能深知动静,且触冒岚瘴多至疾病,难以有功,惟彼土兵熟知道路,谙识贼情,若资其力可以收效。今后如遇窃发,则命土兵与官兵合势击,凡其有得就以与之,彼慕利争先勇于用力,可以倾其巢穴绝其党类,既免转运供给之劳,又无损失军伍之患。”[15]6-7看到土兵熟悉地形、气候和贼情的优势,建议动员土兵来辅助征讨。而延续多年的大藤峡起义中,这一点表现更为突出,烟瘴成为官兵难以克服的一大障碍,也成为起义者赖以保存实力、长期作战的一个工具,也正是如此,在制定策略时,就有大臣提出要发挥和动用土兵的优势。比如洪武二十年(1387),浔州知府沈信言:“府境接连柳、象、梧、藤等州,山溪险峻,瑶贼出没不常。近者广西布政司参议杨敬恭为大亨、老鼠、罗碌山生瑶所杀,官军讨之,贼登岩攀树,捷如猿狖,追袭不及。若久驻兵,则瘴疠时发,兵多疾疫,又难进取,兵退复出为患。臣以为桂平、平南二县,旧附瑶民,皆便习弓弩,惯历险阻。若选其少壮千余人,免其差徭,给以军器衣装,俾各团村寨置烽火,与官兵相为声援,协同捕逐,可以歼之。”[16]2743-2744主张动员浔州府下已经归顺的瑶民组织团练,与官兵一同剿捕。正统二年(1437),总兵官山云奏:“左右两江土官,所属人多田少,其俍兵素勇,为贼所畏。若量拨田州土兵于近山屯种,分界耕守,断贼出入,不过数年,贼必坐困。”[2]4483
三是优恤和厚待在烟瘴区做官的流官官员。一方面,对因瘴而亡的流官官吏,优恤其家属。如湖广给事中何海就曾上奏,“布政司、府、州、县官到任之后,间有不服水土瘴疠而死,遗下家属,道路遥远,贫难无力不能还乡,诚可怜悯,准律故官家属有司应付脚力,给与行粮递送还乡。如蒙准行,则存殁感恩。”[15]1-2并被皇帝采纳。另一方面,对于在烟瘴区任职的官员也给予一定的奖励措施。明朝规定:“天下府、州、县有邻近边夷,或地方瘴疠者,请于除选之际,随宜斟酌”。在升迁方面,烟瘴区官吏与无烟瘴区官吏的升迁待遇不一样。洪武十二年(1379)正月丁亥,儋州仓副使李德言:“天下有司,例满九年,而两广瘴疠,乞减一,考从之。于是虽两广,非瘴厉者仍九年,汀、漳、郴、赣、龙南、安远亦瘴疠,通叙。”[16]1973表明官员正常情况下均是九年考满之期,但处于烟瘴区的官员则可视情况有所优免,减少一年,而广西土司地方正是烟瘴区域,享受此优待。
四、结语
明代,广西是比较典型的烟瘴区域,在西部的左右江、红水河流域烟瘴盛行,东部的大藤峡地区也有烟瘴分布,而这些地区都是少数民族分布比较集中的地方,自元代以来,这些地区相继设立土司进行管辖,实行土司制度。明代承袭,个别地区还在改流与设土之间反复多次,而影响因子之一就是烟瘴。因为烟瘴的存在,使得明代派驻广西的官吏大部分都存有畏瘴情绪,一些官吏甚至触瘴身亡,明朝因此有了优恤瘴亡官吏家属的人文之举。因为烟瘴,明朝很难对土司地方建立直接有效的统治,只能以土治土,倚重土官。甚至在烟瘴严重区域,还将流官管理地方改由土官代为直辖。也由于烟瘴的盛行,使得广西不少地方的府治、卫所需要迁移或者两地轮流,造成地方治理效率的低下。也因为烟瘴,使得卫所官兵伤亡虚耗,战斗力相对不强,在明代广西此起彼伏的起义和反叛镇压中,官兵常常为烟瘴所阻,这种情势也迫使朝廷在平叛中大量使用土兵,利用其优势。由此可见,烟瘴与明代广西土司地方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使得明朝中央在对该地的治理和经略问题上,不得不考虑此一因素,从而使得其统治呈现出与中原不一样的特点,即因地制宜,以土治土。但同时为了避免土司势力的过于强大从而威胁到中央的统治,明代在广西土司的设置上,一般以中小土司为主,不断地在一些地区推进改流,多封众建,以削弱其势力。而烟瘴在广西地区一直存在,直到清朝乾隆年间,广西西部一些地方仍是烟瘴重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土司制度在广西得以延续,即使在清雍正年间大规模改流之后,广西仍有数十土司存在,一直持续到了民国十七年(1928)才全部完成改流。
[1]周琼.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清〕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广西总部总论二之七[M].成都:巴蜀书社;北京:中华书局,1985.
[4]龚荫.中国土司制度史:下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
[5]明英宗实录[G]//明实录:第15 册.上海:上海书店,1982.
[6]清会典事例[M].北京:中华书局,1991.
[7]〔明〕于谦.忠肃集[G]//四库全书:第1244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G]//续修四库全书:第53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9]明宣宗实录[G]//明实录:第10 册,第11 册,第12 册.上海:上海书店,1982.
[10]明神宗实录[G]//明实录:第60 册.上海:上海书店,1982.
[11]〔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广西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2]〔清〕汪森.粤西文载[G]//黄盛陆等校.粤西文载校点.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13]〔明〕谢肇淛.百粤风土记[G]//黄振中等校注.粤西丛载校注:下.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7.
[14]〔明〕徐日久.五边典则[G]//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五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
[15]明太宗实录[G]//明实录:第6 册.上海:上海书店,1982.
[16]明太祖实录[G]//明实录:第3 册,第4 册.上海:上海书店,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