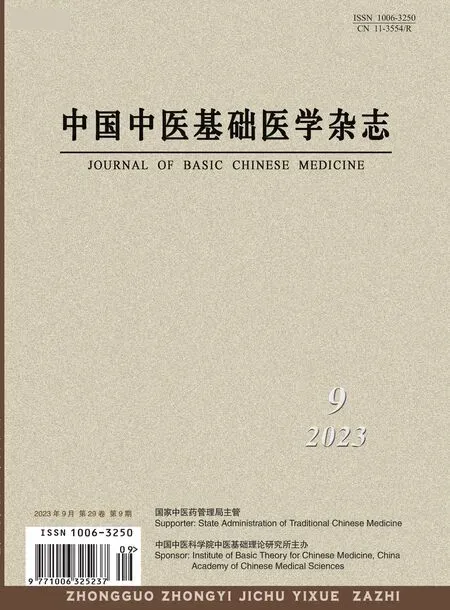中医湿、瘴、疠邪源流合考❋
2023-11-19殷鸣,张琦,金钊
殷 鸣,张 琦,金 钊
(成都中医药大学,成都 610075)
湿邪、瘴气、疠气是中医病因理论中三种外感邪气。湿邪属六淫之一,理论发源最早,瘴气、疠气是后世医家在六淫之外另立的特殊邪气。现代中医外感病因被分为六淫和疠气两类,瘴气往往被归属于疠气,但在历史源流中,瘴气是瘟疫病因从六淫说向疠气说发展的中介,瘴气带有湿邪的属性,而疠气脱胎于瘴气。湿邪、瘴气、疠气三者既有各自独立的概念,又有相互交叉的源流。在瘟疫流行的今天,若不考察三者源流之合,则中医外感病理论的发展无由体现,瘟疫治疗的思路也会受到制约。揭示湿、瘴、疠邪三邪内在关系,汇通其治法,能为今天论治瘟疫提供新的启示。
1 湿、瘴、疠邪概念考
1.1 湿邪:六淫之一
湿邪作为六淫之一,主要见于《黄帝内经》。《黄帝内经》中六淫均属外界气候异常,当其超过人体承受能力时就会致病。在《黄帝内经》中,六淫是在运气学说中进行定义的,系统的六淫致病内容主要见于运气七篇大论。六淫的流行与季节、气候密切相关,“夫六气者,行有次,止有位”。太阴湿土为主气四之气,见于长夏至初秋。《黄帝内经》描述了湿邪致病的特点,“因于湿,首如裹,湿热不攘,大筋软短,小筋弛长”“湿盛则濡泻”“诸痉项强,皆属于湿”。《金匮要略》对湿邪致病理论有了进一步发挥,指出“湿伤于下”“湿流关节”的侵袭部位,在“痉湿暍篇”对湿病的症状、治疗作出较全面的论述。“痉湿暍病篇”为仲景杂病论之首篇,其中痉、湿、暍三病与伤寒仍有密切关联。湿病为湿邪从肌表侵袭而来,症状以疼痛为特征,并会出现与伤寒类似的恶寒、发热症状。在《黄帝内经》《金匮要略》中,湿邪仅仅作为六淫之一,地位与风、寒、暑、燥、火相近。后世湿邪概念则在不断发展,如朱丹溪认为,“六气之中,湿热为病,十居八九”[1]23。宋代杨士瀛曰“湿之入人,行住坐卧,实薰染于冥冥之中,人居、戴、履,受湿最多”[2]。医家们逐渐认识到湿邪致病的广泛性与隐匿性,且湿邪易与其他邪气夹杂,各类疾病中都常见湿邪的身影。后世医家也没有拘泥于六淫致病的季节性,六淫与气候不存在绝对的对应关系。判断六淫的依据在于“因发知受”,在辨别湿邪时,病人的症状、舌脉远比所处节气重要。清代温病学派进一步补充了湿邪的致病途径,认为湿邪可以从口鼻而入,造成湿温与瘟疫,“一人受之,则为湿温,一方受之,则为疫疠”[3]。这是湿邪概念在后世的发展。
1.2 瘴气:以地域性立名
瘴者,障也。“瘴”字系“障”字演化而来,“障”以阻塞不通为意。“障气”一词首见于西汉《淮南子》[4],指“土山之气”[5]。瘴气作为中医术语首见于《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在升麻条中记载其“辟温疾,瘴邪,毒蛊”[6]。可见“瘴气”一词在汉代已有运用[7]。其后晋代《肘后备急方》载有专篇“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在度瘴散条记载“辟山瘴恶气。若有黑雾郁勃及西南温风,皆为疫疠之候”[8]。该条说明两个信息:其一,瘴气盛行于山岭地带;其二,瘴气可导致疫疠流行。后文又出现“瘴疟”病名,说明瘴气致病症状以寒热往来为特征。元代《岭南卫生方》是研究瘴气的专书,书中解释了瘴气流行于岭南的原因,“岭南既号炎方,而又濒海,地卑而土薄。炎方土薄,故阳燠之气常泄;濒海地卑,故阴湿之气常盛。而二气相薄,此寒热之疾所由以作也”[9]1。瘴气以山峦间雾气为具体表现形式,“雾者瘴之本,以雾始必以瘴终”[10]。它从口鼻呼吸而入,具有传染性,与传统的六淫从肌表而犯有区别。《圣济总录纂要》曰“不论老少,或因饥饱过伤,或因荣卫虚弱,或冲烟雾,或涉溪涧,但呼吸斯气,皆成瘴疾”[11]159。可见,瘴气是一种具有地域特色的邪气,在传统的六淫邪气理论之外独立存在。蒋宝素曰“瘴气者,经旨所无,乃岭表方隅之疾”[12]。正因瘴气在岭南广泛流行,以至于“南方凡病皆谓之瘴”[13]。这种对瘴气的模糊、泛化固然不对,但现代一些学者根据古代“瘴疟”之名,将其简单对应为疟疾[14],这显然是片面的。古代的疟病仅仅是指寒热往来、憎寒壮热的症状[15],瘴气致病常见这种症状,但是不能说其导致的疾病就是疟疾。
1.3 疠气:以传染性、致病特异性立名
疠者,厉也,指疾病的严重性。《说文解字》曰“疠,恶疾也”[16]。“疠”字多与“疫”字连用,疫疠指严重传染病[17],可以由前文所述六淫、瘴气导致。明代吴又可首先提出“疠气”这种特殊邪气。在他看来,疫疠与六淫、瘴气无关,是由特定的疠气引起,“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18]27。在其《温疫论》中也将这种“异气”称为“疠气”。其云,“疫者感天地之疠气,在岁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时有盛衰。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18]1。疠气致病具有特异性,会产生“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18]225的现象。其具有强烈的传染性,众人皆病,发病症状基本相同,“众人有触之者,各随其气而为诸病”[18]214,病情凶险,传变迅速。由此,吴又可推测有一种具体物质致病,命名为“疠气”。疠气“其来无时,其著无方”[18]214,它与气候、地域关系不大,因此吴又可否定了前人六淫致疫、瘴气致疫的观点,并痛斥时医沿用伤寒方治疗瘟疫的做法。吴又可为瘟疫寻找到全新的病因,并归纳出这种疠气侵袭的规律。邪气从口鼻吸入,病位在于半表半里的膜原。既然瘟疫病因是全新的、具有物质性的疠气,感受途径、发病部位都与传统六淫不同,那么治疗上就“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18]226。吴又可认为瘟疫治疗应摆脱传统中医六淫理论,寻找专解特定疠气的药物,“以物制气,一病只有一药,药到病已”[18]225-226。但中医无法研究具体邪气,无法找到专药,“杂气无穷,茫然不可测也”[18]216,吴又可只有“勉用汗吐下三法以决之”[18]225。可见,吴又可的疠气说已接近现代病原体的概念,是对传统外感病理论的极大创新。
2 湿、瘴、疠邪源流合论
通过对三种邪气概念的考察,可以发现:湿邪作为六淫之一,是以季节、气候立名;瘴气是以地域立名;疠气是以传染性、致病特异性立名。这三种邪气定义的角度不同,其内涵有很大程度的交叉性。湿邪并非严格限制在特定季节,瘴气本属湿邪;瘴气在地域上的限制也并非绝对;疠气的提出与瘴气关系密切。湿、瘴、疠邪的源流可以在相互印证中得到澄清。
2.1 瘴气是特定地域下的湿邪
《黄帝内经》中六淫起源与运气学说密不可分,湿邪最初虽然是从季节、气候定义,但这并不是绝对的,湿邪也具备明显的地域特征。《素问·异法方宜论篇》曰“南方者,天地之所长养,阳之所盛之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南方多湿,瘴气本具湿性,这已为历代医家公认[19]。《圣济总录纂要》曰“冬令蛰虫不伏藏,寒热之毒蕴积不散,雾露之气易以伤人。此岐伯所谓南方地下水土弱。盖雾露之所聚也,故瘴气独盛于广南”[11]159。自然界中,岭南山嶂阻隔,雾气弥漫,聚而不散,与湿黏腻之象相符。所谓“瘴气”,以成因而言曰“障”,以区域而言曰“嶂”,以病邪而言曰“瘴”,以本质而言曰“湿”。瘴气的概念看似独立于六淫,是因为它从地域的角度定义,其实质并不能脱离六淫之湿。瘴气具传染性,随呼吸而入,这一点是以往六淫所不能解释的。清代温病学派医家则补充了湿邪可以从口鼻而入,吴鞠通曰“吸受秽湿,三焦分布”[20]。丹波元简明确提出“瘴即温湿之气。特以南方岭嶂之地,此气最为酷烈,故谓之瘴气”[21]。
2.2 “疠气”的提出系受瘴气的启发
瘴气、疠气是独立于六淫体系之外的特殊邪气,所不同者,瘴气流行于岭南,疠气则各地皆可。事实上,吴又可提出疠气这一特殊邪气概念时,极有可能是受瘴气的启发[22]。在明末瘟疫流行期间,稍早于吴又可,有医家郑全望率先在江浙一带使用瘴疟治法治疗瘟疫,疗效显著[23]。他在《瘴疟指南》中提出“天气流转,山泽通之,以时验变,以人验时。奥气不藏,时之变也,物直槎夭,人直疾病。山川不必同,而气至则行之矣”[24]2。郑全望最初接触《岭南卫生方》时,也认为该书仅适用于岭南一带,后来在面对江浙一带的瘟疫时,认识到这种瘟疫与岭南瘴疟在症状、治疗上高度一致。郑全望认为,瘴气虽然从地域角度定义,但不应机械,在气候反常时瘴气可流行到全国各地,“曰北方伤寒病多、南方瘴疟病多则可,若曰北方无瘴疟、南方无伤寒,则不可。盖天道无常,假令北方暑热过多,秋时暴热数日,北人感此气,亦多病瘴”[24]9。同为江浙人,吴又可所提出的“疠气”正是突破岭南地域限制的“瘴气”。他描述当时瘟疫的症状为“先憎寒而后发热,日后但热而无憎寒也。初得之二三日,其脉不浮不沉而数,昼夜发热,日晡益甚,头疼身痛”[18]21,与郑全望所论瘴疟极为接近。他率先提出疠气所入的病位是膜原,但《素问·疟论篇》中已提到“邪气内薄于五脏,横连募原”。他制定瘟疫主方达原饮,其中诸药尽是瘴疟常用之品。槟榔尤是岭南瘴疟之专药,郑全望曰“岭表之俗,多食槟榔,盖谓瘴疟之作,率由饮食过度,气痞痰结,而槟榔最能下气消食去痰”[24]31。李时珍曰“草果与知母同用,治瘴疟寒热,取其一阴一阳,无偏胜之害,盖草果治太阴独胜之寒,知母治阳明独胜之火也”[25]。郑全望治瘴疟主方为不换金正气散加草果,与达原饮较相似,这些都表明了瘴气与疠气内涵上一脉相承的关系。吴又可认为,特定疠气引发特定瘟疫,疠气“种种不一”[18]214,瘴气是一种疠气,而疠气则不尽是瘴气,但在他提出“疠气”概念时,很可能是受同时代、同地区郑全望的启发,他所面对的疠气与瘴气性质基本一致。
2.3 吴又可面对的瘟疫是湿疫
吴又可所论疠气与瘴气接近,瘴气性质属湿,但如果说疠气的性质也属湿,这本身就与吴又可的理论相冲突。吴又可强调,疫疠不是由六淫引起,而是由特殊的疠气导致。吴又可抛开六淫而另创疠气说,其合理之处在于,六淫不足以解释瘟疫的强传染性,不足以解释“众人之病相同”[18]215。尤为重要的是,既往中医理论中六淫是从表而犯,需用汗法外解,而当时瘟疫若使用汗法,往往加重以至于死亡。因此,吴又可提出全新的“疠气”概念,强力抨击传统六淫致疫的观点。
但其也有不合理的地方,疠气致病与六淫致病并非矛盾。疠气与六淫定义角度不同,在讨论瘟疫病因时疠气说更为合理,但讨论治法时六淫说却无法被抛却,因为中医对六淫的判断并非拘泥于具体的感邪过程,而是基于身体的表达,即所谓“因发知受”。钱潢曰“外邪之感,受本难知,发则可辨,因发知受”[26]。从“因发知受”的角度看,吴又可描述瘟疫的症状为头痛、憎寒壮热、胸膈痞闷,舌象以积粉苔为特征,这都是湿邪之象。从用药的角度看,达原饮是以辟秽化浊、宣通气机为主,也符合湿邪治法。因此,在清代温病学派看来,吴又可所面对的瘟疫为湿温,吕震名曰“(吴又可)论中所指三阳表证,而兼胸膈痞闷,心下胀满……舌胎满布如积粉而渴者,此确是今之湿温病”[27]。疠气多种多样,不尽属湿,但导致明末瘟疫的特定疠气确属湿浊,湿可致疫,前人早有“湿疫”的说法[28],吴又可显然忽视了这一点。如果要将疠气与六淫完全割裂,则中医治法全无着落。吴又可借用瘴气治法创制达原饮,但达原饮并非专解疠气之药,而是化湿辟秽之剂。从起源上看,疠气与湿邪具备相通性。
3 湿、瘴、疠邪治法汇通
湿、瘴、疠邪源流相通,治法也具有一致性,明清瘟疫、湿温治法都是对瘴气治法的借鉴。在《金匮要略》中,湿邪系从肌表而犯,主要治法是发微汗,主方是麻黄加术汤、麻杏苡甘汤,“发其汗,汗大出者,但风气去,湿气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风湿者发其汗,但微微似欲出汗者,风湿俱去也”。朱丹溪将湿邪病位分表里,指出“外湿宜表散,内湿宜淡渗”[1]96。淡渗的治法通用于各类湿邪致病,《后汉书》记载马援进军岭南时即以薏苡仁避瘴[29]。发汗表散的治法在清代温病学派看来则是大忌,他们治疗湿邪常用芳香化湿、宣畅气机之法。在温病学派与前人治湿法之间,起衔接作用的是瘴气治法。芳香化湿法其实是在前人面对瘴气时总结出的,其代表是不换金正气散、藿香正气散。这二方首见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虽归属于伤寒方,其所谓“治四时伤寒”[30]21显然属广义,真正治疗的是条文中所言“瘴疫时气”“山岚瘴气”[30]21-22。《岭南卫生方》在不换金正气散中加草果,作为治瘴气之首选方,认为“凡过岭南,此药不可缺”[9]36。在岭南“晨兴盥漱后,先服平胃散,间或投以不换金正气散”[9]11-12,可作为预防之法。清代吴鞠通辨治湿温时,创制五首加减正气散,这正是对瘴气治法的发扬。湿邪可以作为瘴气内涵的解读,治瘴诸方又反哺了清代湿温病治法的形成。
吴又可治瘟疫创达原饮,该方与既往治瘟疫方相比可谓别开生面,但这并非完全是吴又可自出心裁,其组方亦有所本。宋代《圣济总录》记载有常山散,“治瘴疟寒热往来,二三日一发”[11]162。该方由常山、厚朴、槟榔、草豆蔻、乌梅、甘草组成,在当时草豆蔻与草果存在混用的情况[31],所以达原饮三味主药草果、槟榔、厚朴已尽在常山散中。吴又可在达原饮方下自评“槟榔能消能磨,除伏邪,为疏利之药,又除岭南瘴气”[18]21,其制方所本可见一斑。其所以不用常山者,以常山为涌吐之药,针对有形的痰食,而当时瘟疫为无形湿邪伏于膜原,涌吐并不能予其出路。又因当时瘟疫热象突出,吴又可用知母、黄芩、白芍清热滋阴和血,用甘草和中,且言此四味“不过调和之剂”“非拔病之药”[18]21,可见化湿除瘴法才是吴又可治瘟疫的关键。与正气散类方相比,达原饮所治之湿更为凝滞,更易化热,更为严重,后人称之为“湿热秽浊”之邪,寻常的芳化药已无法撼动,吴又可用槟榔、草果破结之品,使盘踞之湿邪速离膜原,这既是对瘴气治法的借鉴发扬,也是对湿邪治法的一大创新。
4 结语
现代外感病因被分为六淫和疠气两类,二者关系往往被忽略。如果单纯将六淫作为普通外感的病因,将疠气作为瘟疫的病因,这不但不符合临床实际,还会割裂完整的中医外感病理论。湿邪、瘴气、疠气源流相通,瘴必属湿,湿不必为瘴;湿可致疫,疠气不尽属湿;瘴可致疫,疫疠治法也可借鉴瘴气治法。在中医外感病因中,从六淫到瘴气、疠气是历史的发展。地域性造就了瘴气概念,传染性、致病特异性造就了疠气概念;同时,疠气致病与六淫致病并不对立,从瘴气、疠气回归六淫也是历史的必然。“因发知受”是中医判断邪气性质、拟定治法的依据。吴又可认识到疠气的物质性,希望寻找专解疠气之药,这种思路与现代医学研究病原体相吻合。但即便在现代科技下,寻找特效药也并非易事。根据对疠气相关源流的梳理,可以判定吴又可所面对的瘟疫性质;根据“因发知受”原则,可以将六淫说与疠气说统一起来。吴又可面对的瘟疫是湿疫,其治法是对瘴气治法的借鉴,“疫气多湿”,由湿邪造成的瘟疫历来不少。合考湿、瘴、疠邪,才能将三者治法汇通,为今天论治湿疫提供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