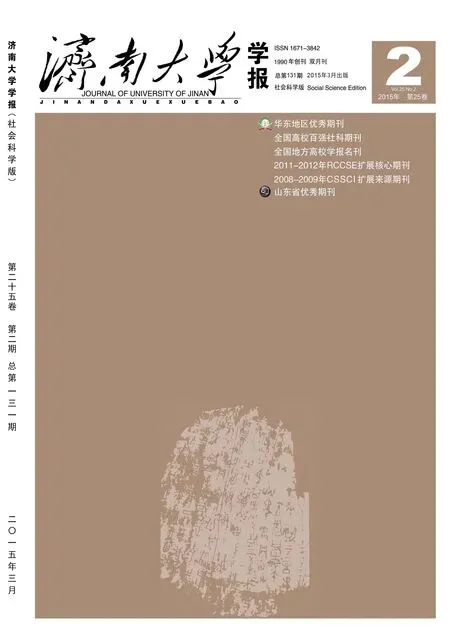藩镇平衡政策在唐后期的实施
2015-04-15李志刚
李志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北京100732)
李志安先生主编《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指出,安史乱后,唐廷中央与地方关系转变为外重内轻。中央政权如何有效控制地方,是中国封建社会诸王朝在国家结构形式方面,一直在探索和实践的重大课题。[1](P97)有唐一代近三百年,安史乱后,唐廷又延续了近一个半世纪的统治,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知道,唐后期是藩镇林立的时代,唐廷对藩镇的有效控制,应是其能维持统治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唐后期是如何控制藩镇的?其控制方式有哪些?
张国刚先生《唐代藩镇研究》从进奏院的设立、宦官监军、藩镇财政收入与分配方面,谈及唐廷对藩镇的控制。[2](P102-145)陈志坚先生《唐代州郡制度研究》认为唐后期注重从州郡的财政分割、中央对州的检察方面,加强对地方的控制。[3](P178-221)冯金忠先生《唐后期地方武官制度与唐宋历史变革》认为,唐后期中央成立了以神策军为代表的禁军,希望与藩镇相对抗,同时限制藩镇对支郡的控制,以扩大支郡的独立性等。[4](P104-111)王凤翔先生《唐代西北藩镇与地域社会》重点谈及了唐廷对西北藩镇的控制,其方式诸如在政治经济上给予优待,注重对节帅的选拔,其次是禁军监控,再次是绝不姑息西北藩镇的叛乱。[5](P30-31)唐后期,唐廷对藩镇的具体控制方式多样。本文认为,藩镇是中央控制地方的载体,唐廷通过控制藩镇,以维护中央统治。唐廷通过利用藩镇,竭力维持藩镇间势力的均衡,在唐后期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总体上实现了对藩镇的有效控制,从而也维护了中央统治。藩镇因此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在唐后期中央控制战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中央维持藩镇势力平衡的努力
安史乱后,在藩镇林立格局势难改变的情况下,如何利用藩镇,维护统治,是唐廷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正如宋人所说:“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6](P13082)唐廷君臣对此早有认识,具体也是如此作为的。在唐后期藩镇林立格局下,保持藩镇间势力的均衡,使其相互钳制,是维护唐廷统治的重要方式。对此,《新唐书·方镇表》记曰:“唐自中世以后,收功饵乱,常倚镇兵。”[7](P1759)《唐语林》亦记曰:“盖其先也,欲以方镇御四夷,而其后也欲以方镇御方镇。”[8](P683)安史乱后,藩镇林立格局业已形成,短期内罢黜藩镇,恢复唐初中央直辖州郡的统治模式,实际已无可能。为此,如何在藩镇林立的基础上,有效控制藩镇,以维护中央统治,是当时的首要任务。而中央通过维持藩镇间势力的均衡,造成犬牙相制之态势,是有利于统治的。一定程度上来说,唐后期藩镇的存在,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在一定时期内,确实起到了维护中央统治的作用。
肃代之际,唐廷忙于平叛,无暇顾及藩镇间势力平衡问题。如当时由北而南的刘展叛军,冲击了江淮地区,造成严重破坏。这是安史之乱爆发后,唐廷忽略南方藩镇军力建设的结果。乾元中,刘展为淮西副使,因刚愎自用而被节度使所恶,唐廷决计除掉此人。但忌于刘展手握重兵,惧其生变。因此,肃宗假令刘展代李峘为江淮都统,同时密令李峘与淮南节度邓景山设法对付。此时,颜真卿为浙西节度使[9](P3404),预先作军事准备,以备不虞:“公(颜真卿)虑其侵轶江南,乃选将训卒缉器械,为水陆战备。”[9](P4020)李峘却认为颜真卿行之过早,易引起刘展怀疑,打乱中央预定计划,因而密奏肃宗,令杭州刺史侯令仪,代颜真卿为浙西节度使。其后李峘等处置失当,刘展率军南下广陵。在润州抵抗失败后,李峘出奔宣州。刘展渡江占领润州后,浙西治所昇州,有军士公然响应叛军,攻打金陵。侯令仪万分恐惧,未能设法挽救危局,反将镇事交予部属,弃城逃跑。随后,昇州守军开城降敌,叛军轻松占领昇州。刘展又派兵相继攻陷浙西境内苏、湖、杭等州,“所向无不摧靡,聚兵万人,骑三千,横行江淮间”[10](P7100),对当地造成巨大破坏。由于东南藩镇军力薄弱,唐廷急调屯于任城的平卢田神功军南下平叛,很快击败刘展,赶过长江。刘展之乱反映了江淮、两浙藩镇力量之薄弱,难以抵御其他藩镇的侵扰。这为唐廷此后注重在江淮地区,培植某些雄藩大镇,以平衡其他藩镇奠定了基础。
建中初,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反叛。建中二年(781)七月,唐廷封李希烈为南平郡王,令其督兵进讨。李希烈觊觎山南东道土地,决计出兵。九月,梁崇义连战连败,困守襄阳。大势已去,守门军士争出投降。梁崇义最终败亡,传首京师。其后,李希烈霸占襄阳,意欲吞并山南东道,这是唐廷难以容忍的。在唐廷新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李承的坚持下,李希烈未能如愿。唐廷维持藩镇间势力平衡的政策初见成效。又如元和四年(809)三月,成德王承宗自为留后,锐意消藩的宪宗坚决不予任命。王承宗恐惧,请献德、棣二州。朝廷随即在德、棣二州,置保信军节度使。[7](P1848)王承宗献地,遭河朔藩镇的反对:“然邻道皆不欲成德开分割之端,计必有间说诱而胁之。”[10](P7665)于是,王承宗扣留保信军节度使薛昌朝,开始对抗唐廷。唐廷迅即削王承宗官职,令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镇讨伐。然平叛却久无进展,加之淄青李师道、幽州刘济等为之说情,无奈之下,唐廷遂复其职,并废保信军,德、棣二州复隶成德。即《通鉴》元和五年七月记:“王承宗遣使自陈为卢从史所离间,乞输贡赋,请官吏,许其自新。李师道等数上表请雪承宗,朝廷亦以师久无功,丁未,制洗雪承宗,以为成德军节度使。复以德、棣二州与之。”[10](P7677-7678)
但宪宗一直没有放弃肢解藩镇,以求均衡的策略。一旦时机许可,这种政策还是要贯彻执行。元和十二年(817),唐廷平定淮西,威权大增。忧惧之下,王承宗再献德、棣二州,表示归顺。王承宗请魏博田弘正,转达中央“请以二子为质,及献徳、棣二州,输租税,请官吏。(四月),魏博遣使送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徳、棣二州图印至京师”[10](P7749)。为平衡成德镇的势力,唐廷割“徳、棣二州隶横海节度”[7](P1848)。自此横海领有沧、景、德、棣四州,实力大增。实力增强后的横海镇,自能有效制衡和威慑其他藩镇。元和末,削藩战争成功后,在唐廷威慑下,横海程权自以世袭沧、景,心不自安,全族归朝。唐廷命乌重胤为节度使,横海镇的归服,使唐廷从东面,又多了一枚制衡河朔藩镇的棋子。中央威权是保证藩镇归服,避免相互兼并,使其势力均衡,以维持唐廷统治的有效方式。
元和十四年(819)二月,平淄青李师道后,唐廷遣杨于陵分其故地:“于陵按图籍,视土地远迩,计士马众寡,校仓库虚实,分为三道,使之适均:以郓、曹、濮为一道,淄、青、齐、登、莱为一道,兖、海、沂、密为一道,上从之。”[10](P7761)据各州地理位置、经济军事实力,在“使之适均”前提下,通过分割州郡,重组藩镇的方式加以控制,而非将这些州郡通过直辖的方式,收归中央,这体现了唐廷维持藩镇间势力均衡理念的贯彻与实施。柳宗元《贺分淄青诸州为三道节度状》也认为分割三镇,起到了“分其形胜”[11](P1034),互相制衡的作用。穆宗即位后,藉元和余威,削藩政策继续实施。长庆元年(821)三月,幽州节度使刘总主动奏请分幽州为三镇:以幽、涿、营为一道,请除张弘靖为节度使;平、蓟、檀、媯为一道,请除平卢节度使薛平为节度使;瀛、莫为一道,请除权知京兆尹卢士玫为观察使。刘总如此分镇,可谓煞费苦心。说明其充分揣摩透了唐廷均分各镇实力,以相制衡的理念。瀛、莫二州,位置在最南边,与成德相毗邻;幽州为治所所在地,涿州距之最近,可为一体,但却加上并不毗邻的营州,反映了牵制该镇的理念;平、蓟、妫、檀为一道,四州列置于缘边战略要地,护卫幽州外围,抵抗外族入侵,与幽、涿、营相互钳制。张弘靖、卢士玫皆为文儒之士,这说明中央认识到了武人多跋扈难制,宜以文儒控制藩镇的理念。
唐后期在南方藩镇,藩镇均衡战略亦有实施。如大中时,南方藩镇屡遭内乱,但这些叛乱旋由邻镇平定。大中三年(849)五月,武宁军军卒逐节度使李廓。唐廷命义成节度使卢弘止赴镇武宁。“武宁士卒素骄,有银刀都尤甚,屡逐主帅。(卢)弘止至镇,都虞候胡庆方复谋作乱,弘止诛之,抚循其余,军府由是获安。”[10](P8039)大中九年七月,浙东军卒逐观察使李讷。大中十一年五月,容管军士逐经略使王球。大中十二年四月,岭南都将王令寰囚经略使杨发。大中十二年五月,湖南都将石再顺逐观察使韩琮。大中十二年六月,江西都将毛鹤逐观察使郑宪。这些藩镇的内乱,多由邻镇出兵,迅即平定。此因唐廷贯彻了藩镇均衡政策,诸镇互成制衡态势,一旦有急,即可相互援应。
安史乱后的藩镇割据,大致可分为几个时期。安史之乱爆发后,藩镇迅由边疆地区,向广大内地蔓延开来。安史乱平后,自唐廷裁撤藩镇动议无果而终后,以至德宗削藩战争失败,这一时期主要是藩镇地位巩固阶段。元和时,宪宗藉德宗拱墨无为所积攒的经济力量,削藩战争大都获得成功,一时出现了藩镇割据式衰的景象。宪宗死后,至懿宗末年,藩镇势力似乎得到恢复。僖宗后,经晚唐农民战争等动乱的涤荡,中央威权不行,藩镇间互相兼并,均势终被打破,致唐王朝彻底倾覆。但在唐后期的大部分时段内,因中央威权存在,藩镇间并未发生大规模兼并,互成均势,相互制衡,基本维持了中央统治。可以说这一时期,藩镇主要起到了维护唐王朝统治的作用。
二、地方藩镇维持势力平衡的努力
维持藩镇间势力的平衡,不仅是唐廷的希望,也是地方藩镇的潜在要求。大历十年(775),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攻击相、卫、洺、磁四州,意图吞并四州,破坏河朔维持已久的平衡,遭到众镇反对。成德李宝臣联合幽州、淄青等同讨魏博。只因后来田承嗣割让沧州,贿赂成德镇,又使用诡计,诱导李宝臣,转而攻打幽州,诸镇对魏博的围攻方才告罢。沧州自此隶属成德镇管辖。魏博将沧州赠予成德,就是力图维持与其他藩镇的均势,避免成为众矢之的。成德此时已统恒、赵、定、深、易、冀、沧七州。既然成德实力壮大,也就缓冲了魏博镇的力量。
另外,河朔藩镇为保持联合对抗唐廷的实力,对唐廷的削藩战争,往往虚与委蛇,并不尽心尽力,存在着养寇自尊的心理。上述魏博田承嗣遭四面围攻时,成德将王武俊献计李宝臣说:“‘赵兵有功尚尔,使贼平,天子幅纸召置京师,一匹夫耳。’曰:‘奈何?’对曰:‘养魏以为资,上策也。’宝臣曰:‘赵、魏有衅,何从而可?’对曰:‘势同患均,转寇雠为父子,咳唾间耳。朱滔屯沧州,请禽送魏,可以取信。’宝臣然之。”[7](P5945)王武俊的意思是,成德现在军中新立大功,寇平之后,唐廷以一纸诏书征召,马上就成为一百姓匹夫,任人宰割。不如现在放田承嗣一马,还能恃此为重,得到朝廷依仗,朝廷也不敢对成德轻举妄动。“势同患均,转寇雠为父子”,暗含之意是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因此,维持藩镇联合对抗唐廷的态势,以避免兔死狗烹的可悲结果,始终考虑本镇利益的最大化,是当时很多藩镇的真实想法。
大历十一年(776),汴宋留后田神功病卒,都虞侯李灵曜作乱,唐廷无奈,下诏授其为汴宋留后。不料,李灵曜变本加厉,竟仿效河朔藩镇,自授辖州刺史。唐廷派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河阳三城使马燧等征讨。为维持联合抗衡唐廷的局面,魏博田承嗣派其侄田悦引军数万,援救李灵曜,在汴州被李忠臣等击败,田悦只身逃走,李灵曜被擒斩。因此前田承嗣一直逗留不入朝,又派兵助援李灵曜,代宗不得已令诸镇讨伐。“承嗣乃复上表谢罪”,时叛时降,如同儿戏。“上亦无如之何”。代宗听之任之的原因在于,诸镇人马各自心怀鬼胎,中央难以绝对控制,无奈之下“悉复承嗣官爵,仍令不必入朝”[10](P7241)。诸镇虽未明目张胆协助魏博,但在讨叛时,诸镇并不积极,虚糜钱粮,意在养寇自尊。正是明晰这一点,代宗这才被迫对田承嗣释罪不问。长庆二年(822)二月,王庭凑围攻牛元翼于深州,唐廷派军三面解围,但终因缺粮,诸镇消极避战,而未能解围。唐廷不得已赦免王庭凑,仍授其镇州大都督府长史、魏博节度使,以之羁縻。此次围攻未下,皆因诸镇并不尽心尽力,以养寇自重、自肥。
河朔藩镇势均力敌,互相依存,常联合对抗唐廷,某种程度上,形成河朔与唐廷的均衡态势,以维持并存局面。如大历十四年(779),魏博田承嗣死,成德李宝臣上表力请田悦代之。建中二年(781),成德李宝臣死,田悦投桃报李,上表力请李惟岳袭位,德宗不准。于是,李惟岳暗中联合田悦、李正已,阴谋抗拒。其后,李惟岳束鹿城被朱滔、张孝忠攻下,唐军进围深州。李惟岳忧恐,参谋邵真劝其秘密请降,先派其弟李惟简入朝,然后诛违命诸将,再亲自入朝谢罪。李惟岳听计。田悦获悉李惟岳首鼠两端,派衙官扈岌去李惟岳处,劝说道:“敝邑暴兵,本为君索命节,岂为叛逆耶?虽见破于马燧,而感激士大夫乘城拒守,以为后图。今君信邵真谗间,欲归悦之罪,以自湔荡,何负而然!若能诛真以徇,请事公如初。”李惟岳犹豫之际,参谋毕华也进言:“大夫与魏盟未久,魏虽被围,彼多蓄积,未可下。齐兵劲地广,裾带山河,所谓东秦险固之国,与相持维,足以抗天下。夫背义不详,轻虑生祸。且(魏博)孟佑骁将,王武俊善战,前日逐滔,滔仅免,今合两将,破滔必矣。惟审图之!”[7](P5948)李惟岳最终被说服,打消了归朝投降的念头。唇亡齿寒,田悦坚定联合成德的目的在于,互相联合,保持并立格局,以共同对抗唐廷。建中三年,王武俊杀死李惟岳后,唐廷肢解了成德镇。王武俊因功劳最大,仅任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心存怨言。幽州朱滔亦怨求深州而不得,魏博田悦趁机游说朱滔:“且今上志欲扫清河朔,不使藩镇承袭,将悉以文臣代武臣,魏亡,则燕赵为之次矣;若魏存,则燕赵无患。”[10](P7320)河朔藩镇之间,要维持对抗唐廷的实力,不被中央吞并,互保共存是情理之中的事。
建中三年(782)十一月,田悦、王武俊等准备推朱滔为主,欲“称臣事之”。朱滔明白四镇基本势均力敌,为维护团结,联合对抗唐军的态势,坚拒曰:“惬山之捷,皆大夫(田悦)、二兄(王武俊)之力,滔何敢独居尊位!”于是幽州判官李子千、恒冀判官郑濡等共议:“‘请与郓州李大夫(李纳)为四国,俱称王而不改年号,如昔诸侯奉周家正朔。筑坛同盟,有不如约者,众共伐之。不然,岂得常为叛臣,茫然无主,用兵既无名,有功无官爵为赏,使将吏何所依归乎!’滔等皆以为然。滔乃自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仍请李纳称齐王。”[10](P7335)四镇的意图是仿东周故例,奉李唐正朔,四镇互利共存。此因四镇势均力敌,维持联盟局面,是四镇的基本思路。德宗罪己后,四镇去王号,表示归服。但朱泚称帝后,朱滔意图吞并整个河北州县。朱滔的野心,破坏了河朔藩镇并存的格局,故成德、魏博等又助唐攻讨朱滔。这反映了河朔藩镇最关心的问题是,维持相互之间势力的均衡和共存局面。
河朔藩镇也有内在矛盾,彼此之间相互防备,以维持势均力敌和并存局面。建中初,因措施不当,河朔藩镇重又联合抵制唐廷的削藩战争。李怀光、马燧败后收军,退入营中不敢出战。当夜,王武俊、朱滔掘永济渠,断绝官军粮道和归路,平地水深三尺多。马燧忧惧之下,派人向朱滔服软:“‘老夫不自量,与诸君遇。王大夫(王武俊)善战,天下无前,吾固宜败,幸公图之,使老夫得还河东,诸将亦罢兵,吾为言天子,以河北地付公。’滔亦阴忌武俊胜且不制,即谓武俊曰:‘王师既败,马公卑约如此,迫人以险。’答曰:‘燧等皆国名臣,连兵十万,一战而北,贻羞国家,不知何面目见天子耶?彼行不五十里,必反拒我。’滔固许之。燧至魏县,坚壁自固,师复振。滔惭谢,嫌隙始构矣。”[7](P5951)朱滔担心王武俊大胜后,难以钳制,所以停止继续攻击马燧。河朔藩镇并非铁板一块,彼此之间,存在着互相猜忌的心理,以免势力失衡,损害当镇利益。时朱滔、王武俊与官军隔水相持,李纳获悉朱滔、王武俊、田悦等联兵的消息大喜,派人求援,朱滔派军奔赴。一直困守濮州的李纳,竟也放胆猛攻宋州。朱滔放弃对河东马燧的围攻,转而援助李纳。此因之前李纳被宣武刘洽打得大败,跪在城墙上向唐廷投降,表示归服,颜面尽失。只因唐廷决策失误,拒其投降,李纳方不得已,继续抵抗。当李纳穷蹙之时,形势岌岌可危之际,所以朱滔出兵,扶持淄青,以维持四镇均衡并存的态势。
泾原之变后,兴元元年正月,德宗下诏罪己后,更坚定了魏博、成德对抗幽州,维持均势,避免为朱滔兼并的想法。朱滔在攻击贝、魏州时,谋士贾林劝王武俊侧击朱滔,避免其各个击破,吞并二镇:“朱滔此行,欲先平魏博。更逢田悦被害,人心不安,旬日不救,魏、贝必下,滔益数万。张孝忠见魏、贝已拔,必臣朱滔。三道连横,兼统回纥,长驱至此,家族可得免乎?常山不守,则昭义退保山西,河朔地尽入滔。”[12](P3875)本年五月,在魏博坚强阻击下,成德、昭义联合攻击,朱滔大败而归。其吞并河朔的想法彻底破产,河朔重归平衡并存格局。经过建中和兴元年间的战争,河朔藩镇意识到维护相互之间力量的均衡,才能避免被吞并。所以当魏博田弘正请入朝时,相对于河朔而言,无异于失一臂助。为保持平衡,联合对抗唐廷的格局,成德、幽州镇坚决反对田弘正入朝。其最希望的是,在奉唐正朔的格局下,保持势均力敌的态势。于是建中四年十二月,唐廷联合魏博、成德,共同对付朱滔。五月,朱滔败归幽州。河朔重回到战前的均势和并存状态。
在处理与魏博等镇的关系上,如谋士贾林曾说王武俊曰:“且胜而得地,则利归魏博;丧师,即成德大伤。大夫本部易、定、沧、赵四州,何不先复故地?”利益的不同,导致河朔藩镇之间,并非无隙可乘。在与幽州的利害关系上,贾林复说王武俊曰:“大夫冀邦豪族,不合谋据中华。且滔心幽险,王室强即藉大夫援之,卑即思有并吞。且河朔无冀国,唯赵、魏、燕耳。今朱滔称冀,则窥大夫冀州,其兆已形矣。若滔力制山东,大夫须整臣礼,不从,即为所攻夺。”河朔藩镇实力的平衡,是维护本镇利益的重要因素。故王武俊断然决定助唐抗幽:“二百年宗社,我尚不能臣,谁能臣田舍汉(朱滔)。”[12](P3875)河朔藩镇间的利益冲突,及其奉唐正朔,确保均势的心理,给朝廷控制藩镇提供了契机。之所以需要奉唐正朔,此因藩帅地位之稳固,尚籍中央册封和道义支持,“若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则立为邻道所齑粉矣”[10](P7693)。藩镇要互保并存格局,势必需要维持均势状态。各镇实力不过于雄厚,也不过于单薄,彼此牵制,既不能相互兼并,又能对抗唐廷。藩镇间因利益的不同,彼此之间的矛盾,也是唐廷可资利用的。
唐廷削藩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必须考虑到普通军卒的利益。维持藩镇间平衡并立格局,也是当时将士的愿望。兴元元年德宗罪己诏中,李希烈、朱滔都在赦免之列。但此后李希烈不仅不去王号,反且称帝,成为全国公敌。中央和其他藩镇,也失去了与李希烈妥协斡旋的余地。即使是淮西军将也认为称帝行为,破坏了与其他藩镇的平等关系,难为天下所容。贞元二年(786)四月,李希烈部将陈仙奇发动兵变,杀死李希烈:“三月,李希烈别将寇郑州,义成节度使李澄击破之。希烈兵势日蹙,会有疾,夏,四月,丙寅,大将陈仙奇使医陈山甫毒杀之;因以兵悉诛其兄弟妻子,举众来降。”[10](P7469)陆贽早前就建议,不必对淮西镇遽然加兵,缓图之,必能引起淮西内乱。[10](P7469)其依据就是,陆贽料到李希烈所为,已损害到当镇军民的利益,其为众所不容是理所当然的。总之,德宗时李希烈称帝,破坏了与其他藩镇平等的关系。其部属也认为称帝行为,得罪天下,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淮西镇的军心士气。
维持唐后期藩镇间势力平衡和并存的格局,也是唐廷不得已而为之。因维持当时藩镇间的林立状态,是藩镇军民的普遍想法。经过多年与中央对抗之后,河朔军卒也只是想保持现状,维持藩镇的并存态势和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穆宗时,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调任成德镇,其后,田弘正为成德军所杀,田布被任命为魏博节度使,率军攻击成德,但遭到了魏博军卒的集体反对。田布因指挥不动军队,而羞愤自杀。其后魏博将史宪诚控制了魏博镇,根据士卒的需要,退归本镇。河朔重新回复到战前的并存状态。唐后期的藩镇动向,很多时候并非仅由节帅所能掌控。藩镇军卒的利益,也成为其和战的重要考量因素。即使是唐廷任命的节度使,也适用于这一点。如违背镇兵的利益,则会出现杀帅、逐帅的现象。不仅朝廷无力控制河朔藩镇,即使河朔藩帅也得顺势而为。是和是战,军卒利益是考量的重要标准之一。
建中初,唐廷因采取的措施失当,河朔三镇又重新联合起来,一致应对唐廷的削藩。为动员军卒攻击河东马燧军,朱滔召集部伍,激众曰:“‘士蹀血斗,既下坚城,朝廷乃见夺,奏赏不报。君等疾趋,破马燧军以取赀粮,可乎?’军中不应,三号之,乃曰:‘幽人死于南者,骸撑不揜,痛藏心髓,奈何复欲暴骨中野乎?司徒兄弟受国宠,士各蒙官赏,愿安之,不恤其它’。”[7](P5968)幽州士卒不想激化与唐廷的矛盾,只想保住眼前利益,所以两次拒绝攻击马燧。维持现状,保住已有利益,不想激化与唐廷的矛盾,是河朔军卒参与战争的基本考虑。
其后朱滔分兵,联合王武俊屯赵州,威胁康日知,矫诏发其粮贮,即引兵救田悦。朱滔部下军卒得知其意图后,大噪曰:“‘天子令司徒北还,而南救魏,宁有诏邪?’滔惧,走匿传舍。裨将蔡雄好谕士曰:‘始天子约取成德,所得州县赐有功者。拔深州者,燕也。本镇常苦无丝纩,冀得深州以佐调率,今顾不得。又天子以帛赐有功士,为马燧掠去,今引而南,非自为也。’军中悔谢,复曰:‘虽然,司徒南行违诏书,莫如还’。”[7](P5968)幽州军卒多次拒绝朱滔的出兵要求,这说明军卒有较强的趋向性,基本目的是维护本阶层利益。在此事件中,朱滔军卒的觉醒意识,自然是有利于唐廷的。但一般情况下,藩镇整体利益和军卒利益是一致的。得不到广大叛镇军卒和民众的支持,这也是唐廷削藩战争多旷日持久,难以取得实效的根本原因。如所周知,杜甫《石壕吏》、柳宗元《捕蛇者说》等,描述的就是安史乱后,唐廷控制下普通民众的悲苦生活。与其受中央和藩镇的双重压榨,不如自成一镇,奉唐正朔,但经济自主,如此可少一层中央层级之盘剥。藩镇军卒维护本镇的自主性,其实是在为自身利益而战,故其往往众志成城,唐廷难以予以彻底击败。
又如建中时,四镇称王后,为壮大对抗唐廷的实力,四镇讽劝李希烈称帝,企图祸水南引。李希烈旋即自称天下兵马大元帅,派兵攻击汝州和郑州,威胁洛阳。当时李希烈劳师远征,同时与唐廷关系彻底破裂,也损害了当镇军卒利益。所以,一时出现了李希烈属下将卒或逃或降,军心离散的景象。故其只得引兵还蔡州。这表明当藩帅逞一己之私利,损害到普通军卒利益时,可能会导致军心涣散,士不用命。李希烈攻击汝、郑,威胁东都,无异于要彻底和唐廷决裂,成为唐廷首先和重点打击对象,这自然不利于维护普通军卒利益。唐代藩镇林立局面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藩镇军民希望维持藩镇格局的存在,藉此保证本镇利益的最大化,当是其中原因之一。我们知道,唐后期除东南八道财赋外,其他藩镇多不申户口[13](P377)。大量藩镇不申户口,不必缴纳过多赋税,减轻了当道军民负担,军民也是受益者。
忠于唐廷的藩镇也在尽力维持藩镇林立格局,以从中捞取好处:“旧制,诸道军出境,则仰给度支。帝优恤将士,每出境,加给酒肉,本道粮扔给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给,故将士利之。”[10](P7345)元和九年(814),唐廷调十六镇兵马,讨伐淮西。鏖战四年,在李愬出奇兵的情况下,方才擒获吴元济,彻底解决淮西问题。“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当时藩镇乐于因循现状,尽力维持藩镇势力均衡和并存局面,以从中渔利。维持藩镇互立共存的局面,是实现藩镇利益最大化的前提,这也是当时各镇的普遍想法。经过多年战争后,军卒多厌战,只是想保持现状,轻易不愿与中央武力对抗。保持藩镇之间势力的均衡,维持好本镇现状,过安稳日子是其最大期望。
长庆时,幽州、成德发生兵变后,唐廷令田弘正之子田布出镇魏博,攻击成德。田弘正为魏博节度使,时间长达十年之久。贞元十二年(796)至元和七年(812),田季安为魏博节度使时,田弘正已是魏博牙内兵马使,其祖父田延恽为田承嗣季父,其父田延玠在田悦时,已出任节度副使。田布一族可谓与魏博渊源极深。田布履任魏博节度使后,尽力笼络将士:“其(田布)俸禄月入百万,一无所取,又籍军中旧产,无巨细计钱十余万贯,皆出之以颁军士。”[12](P3852)但出镇为唐廷作战,损害了军民利益,所以遭到魏博军卒一致反对:“(田布)会诸将复议兴师,而将卒益倨,咸曰:‘尚书能行河朔旧事,则死生以之;若使复战,皆不能也’。”[12](P3852)所谓“河朔旧事”指的是希望魏博继续维持实际独立状态,与成德、幽州等镇保持均衡共存局面。如此,军民利益可保实现最大化。维持藩镇均衡共存的局面,也是军卒利益推动的结果。
出于维护利益的目的,唐后期的藩镇,不时竭力维持均衡和并存格局,一定程度上,这与唐廷削藩政策的宗旨是一致的。无论通过温和方式,还是战争方式,中央和地方的基本目的都在于,力求维持藩镇之间势力的平衡,而不是废黜藩镇,重新恢复到中央直辖州郡的统治方式。藩镇是唐后期中央统治的载体,没有这种管理地方的模式,唐后期中央对地方的统治,难以维持下去。所以,藩镇适应了唐后期形势的需要,起到了维持唐廷中央统治的作用。
三、结语
自安史之乱以来,值多事之秋,中央难以顾及地方事务,藩镇自我管理体制逐渐形成。唐廷由此渐渐丧失了唐初那样强有力的集权。如中央财政控制范围,主要限于顺从藩镇。肃宗上元年间,刘展乱平后,“支度租庸使以刘展之乱,诸州用仓库物无准,奏请征验。时仓猝募兵,物多散亡,征之不足,诸将往往卖产以偿之”[10](P7116)。对于雄藩大镇专擅财赋,中央往往也无可奈何。正如杨炎所言:“河南、山东、荆襄、剑南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吏职之名,随人署置;俸给厚薄,由其增损”,以致于形成“朝廷不能覆诸使,诸使不能覆诸州”[12](P3418)的混乱局面。
尽管如此,唐后期以藩镇为载体,贯彻了藩镇平衡战略,所以在唐后期的一定时期内,较好地维护了中央统治。其后,随着唐末农民战争等动乱的涤荡,中央威权式衰,藩镇互相吞并,弱肉强食。藩镇之间势力失衡,逐步形成了区域性强藩,继续保持着相互制衡的局面。如以宣武、河东、浙西、淮南等镇为中心,各自兼并了周边较为弱小的藩镇,形成了区域性的割据势力。而唐廷此时能有效控制的地区寥寥可数,最终在强藩的摆布下,归于灭亡。五代十国时期,藩镇林立的格局继续维持下去,但中央集权的趋势愈臻明显。至宋,因不断强化中央集权,对地方势力防范甚严,巩固了国家内部统治,终结了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林立局面。但宋代因集权过甚,地方往往又难以起到支援中央的作用,“宜乎靖康蒙难,心脏受病,而四肢便如瘫痪不可复起”[14](P550)。
没有一劳永逸、永久有效的制度,能应对一切形势的需要。只有根据时势的变化,不断革新制度,使其适应形势的需要,才能不断起到维护中央统治的作用。藩镇之间势力平衡并立格局,作为唐后期中央统治地方的一种模式,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在一定时期内,因唐廷总体上控制得当,所以起到了维护中央统治的作用,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但制度也是一把双刃剑。唐后期因动荡不断,中央威权衰微,藩镇平衡并存格局失控,最终又损害了中央集权。
[1]李志安.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
[2]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陈志坚.唐代州郡制度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冯金忠.唐后期地方武官制度与唐宋历史变革[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1).
[5]王凤翔.唐代西北藩镇与地域社会[J].唐都学刊,2010,(5).
[6]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8]周勋初.唐语林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
[9]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1]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2]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3]岑仲勉.隋唐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4]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