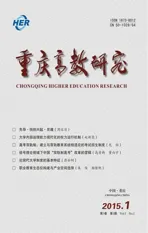论高校“强制发表”制度的合理性
2015-03-19卢凌宇
论高校“强制发表”制度的合理性
卢凌宇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浙江金华321004)
摘要:强制发表对于科学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强制发表极大地降低了学术评价的成本,非常有助于遴选学术人才并激励学者做出学术贡献。因此,应该改革的不是强制发表制度,而是不合理的行政干预、低水平的学术期刊、研究人员的低待遇以及研究型院校与教学型院校不分的现状。
关键词:强制发表;学术评价;学术发展;分层管理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4-06-18
基金项目:广东省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2013年度课题“广东省城市转型升级与高职教育协同发展研究”(GDXLHYB045);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重点课题“基于城市功能分区的重庆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研究”(14SKM04)
作者简介:朱俊(1983-),男,湖北洪湖人,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职业教育、教育管理和教育计量研究;
DOI:10.15998/j.cnki.issn1673-8012.2015.01.014
国内绝大部分高校都要求教师周期性地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这一制度被称为强制发表。在近年的学术和社会讨论中,强制发表制度始终是千夫所指。本文主要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为例,论证了强制发表本身是一个值得尊重和保留的学术制度。它对评价学术成果、遴选学术人才和促进学术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强制发表的反对,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小概率原则的无知。尽管如此,强制发表制度要发挥对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积极影响,必须实施与之配套的一系列改革,主要包括减少行政对学术不恰当的干预、提升学术期刊质量、提高研究人员物质待遇以及划分研究型院校和教学型院校。
一、谁反对强制发表?
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反对强制发表的理由主要有两个:第一,强制发表会扼杀那些具有卓越学术潜力的学者,因为潜力的开发需要厚积薄发。第二,强制发表不利于从事中长期研究。第二个理由的不充分性相对容易识别。不能否认有许多学者在从事中长期课题的研究,但是中长期研究与强制发表并不矛盾。研究人员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通常不会长年或数年只研究一个课题,更常见的情况是多课题齐头并进。即使其中某一个课题需要多年的研究才可以出成果,其他的课题未必如此。不仅如此,中长期项目常常会产生阶段性成果,这些成果可以作为论文来发表或上报,以达到强制发表的要求。
值得深入探讨的是第一个理由,即强制发表会扼杀学术天才,这个观点在国内学术界有着广阔的市场。没有人会否认,古今中外的学术经典,几乎都是精心打磨的思想力作,是需要“十年磨一剑”的[1]。2012年9月去世的新制度经济学大师科斯(Ronald Coase)是经常被援引的一个案例,科斯在一年中发表的成果可能还不如国内三流大学的一位普通教授。贺卫方对钱钟书的低产与当代教授的高产做了对比后指出:“我觉得原创性、思想性的这种事业跟工农业生产不一样,它不是说像工人每天计件工资,每天要做几个齿轮,可是,做学者你要思考问题。”[2]然而,这个观点有两个逻辑缺陷:
第一,批评者往往只提产出很少的学术大师,却忽略了那些著作等身的学术大师。例如,在经济学领域,堪与科斯比肩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其成果就既高产又高质。贡献稍逊的布坎南(James Buchanan)、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和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等人同样非常高产。从统计学上看,只提科斯而不提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犯了按因变量选样的错误(case selection on dependent variable),即只选择能够证实“强制发表扼杀天才”这一理论猜想的案例,其推论是很成问题的。
第二,违背了学术能力的分布规律。在任何一个学科领域,学术能力都基本呈正态分布。学术共同体越大,这个规律就越明显。按照此规律,具有卓越能力的学者位于分布的一极,而能力极端低下者在另一极。绝大多数研究者都位于两者之间,有些人相对强些,有些人相对弱些,他们共同构成学术共同体的主体。由于才能平庸者占学术群体的绝大多数,对学术共同体的整体判断,应该以这个群体为基础,否则就会演绎出以偏概全的推论。但是,反对强制发表的第一个理由恰恰违背了这个原理。至少物理学史表明,是相当少一部分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奠定了未来发现的基础,而大部分科学家作为一个整体虽然对科学进步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但个人的边际贡献可以忽略不计[3]248。如果当年有强制发表制度,可能真的出不了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维特根斯坦终其一生,也就写了《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两本小册子以及少数几篇论文,但他对西方哲学却有着划时代的影响。如果仅看成果数量,维特根斯坦要在今天国内一流大学做教授,恐怕是没有机会的。不过,更重要的是,维特根斯坦只有一个,绝大多数哲学家无论怎么努力也不可能达到他的水平。
因此,当我们说强制发表会扼杀天才的时候,我们的假定是人人都是天才。这个假定无疑是违背事实的,它体现了中国学者潜意识里对小概率事件的偏好,这也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郎咸平曾经对此进行过批判:四两拨千斤这种明显违背物理规律的事件,居然被捧为传统智慧[4]。具体而言,在学术才能的分布中,出现卓越天才的概率是极低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成为论理的前提。过于强调这个命题,往往掩盖了绝大多数学者学术上的低能和思想上的懒惰。
二、为什么强制发表?
如果建立在小概率前提下的“强制发表扼杀天才”这一命题不能成立,那么我们就不能轻易地否认强制发表制度,而有必要探讨这个制度的价值。笔者认为,强制发表至少有三个积极作用:
(一)确保学术评价的公正性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知识的扩张和学术分工的细化,学术群体在不断壮大,知识的生产在加速进行。任何职业都需要一个评判标准,否则无法给从业者分层和分配资源。以学术为职业,最可靠的评价机制就是学术著作。而在门类众多的学术著作中,发表于业内广泛认可的期刊的论文是学者实力最重要的体现。相对于出版专著、会议论文、专题报告等形式,经匿名审稿发表的论文在形式上最具规范性和权威性。匿名评审者往往都是学有所成的专家,他们紧跟学术前沿,最有资格评判具体论文是否为本专业领域知识的增长做出了值得肯定的边际贡献。同时,由于是匿名,评审者原则上不会受社会关系和个人感情的影响,最有可能做出客观和公正的判断。相较之下,无论是出版专著、会议论文,还是专题报告,都达不到同等的公正性和规范性。
有学者提出学术评价应改变“以刊评文”的时弊,同时要“坚决排除学术评价中的非学术因素,特别是人际关系因素、长官意志因素”[5]。其实,要排除人际关系和长官意志的影响,最有效的途径恰恰是匿名评审。如果刊物能够有效地履行为学术成果分层的功能,“以刊评文”是效率最高的学术评价机制。鉴于人际关系在中国社会中的巨大影响以及我国法治传统的缺乏,我国现阶段不适宜大面积地推广委员会来评价学者的学术水平。
(二)甄别和选拔真正有热情、有能力的学者
学术创作是很艰苦的事业,在上档次的期刊发表论文尤其困难。“从直觉上看,研究卓越至少反映了才能、潜质甚至天赋上的差异,而教学能力是后天的,可以培养和提高。”[6]进一步说,要在学术界生存下来,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强大的热情或敬业精神,二是足够的学术能力,三是良好的健康条件。假定学者的健康水平可以支持其事业,那么,敬业精神和学术能力就成为学术生存的决定性因素。设计恰当合理的强制发表制度,可以把不适合从事科学事业的人淘汰出去,把热情高、潜力大的学者保留下来,从而优化学术资源的配置。
反对强制发表的人经常把高产量和高质量对立起来,他们对我国近十多年来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就是“数量繁荣,质量平庸”[1]。所谓“质量平庸”, 是就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共同体整体而言的,具体到个别学者,这个规律并不完全适用,否则就违反了统计学上的“生态谬误”(ecological fallacy),即把集体的特征化约到所有个体[7]90。实际上,从经验上看,高产量与高质量并不矛盾,反而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重要的贡献更有可能是由高产者做出的,两者其实是相互促进的[3]124。在理论上,这个关系也不难理解:对于有着足够热情和能力的学者来说,高产量不是问题。敬业的学者总是渴望自己的才华和贡献得到同行的承认,而获得承认的最佳途径就是在有影响的刊物发表文章。
(三)激励学者为学术做出贡献
学者的基本职责是为知识的增长做出贡献。我们历来赞赏那种“不用扬鞭自奋蹄”的学术奉献精神,但是在现实中,这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学者既然是人,就有人性的缺点,从总体上,懒惰和敷衍塞责是常态。如果没有强制发表制度,学者的理性选择就是由大学养着,什么研究也不做。由于信息不对称,每个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己的研究需要十年或者更长的周期,一个本来半年可以完成的研究项目耗费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是不足为奇的。
有学者认为国外尤其是美国学术发展水平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存在强制发表制度。“在国外,大多数高校对教师和研究生没有论文发表数量的要求,对教师的学术水平大多采用同行评议的方法,既要看他们的学术论文数量,更要看他们论文的质量。”[8]这个说法并不准确。以美国研究型大学为例,它们对研究生发表论文确实没有数量的要求,甚至可以说,没有哪所大学强行要求研究生发表论文。但是,如果学生决定以学术为职业,那么在寻找教职尤其是研究型教职时手头有已经发表的论文就是必要的。这是学界通行的规则,对于顶尖名校毕业的学者也很少例外。随着名校培养的博士越来越多,学校的声望(pedigree)越来越难以保证学生能够在学术市场上找到一个工作。论文才是学术市场的硬通货,对于有志于学术的博士生来说,发表的文章越多越好。
同样在美国,对教师尤其是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学术水平的判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文的数量。这就是所谓的“发表还是出局”(publish or perish)的制度。美国大学教师分为三级: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和教授(professor)。副教授以上就是终生教职(tenure)。在研究型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五至六年后要接受系里的考核,讨论是否授予终生教职(tenure)并提拔为副教授。这个制度的设定与美国学术期刊的严格分层相互呼应,期刊的档次通常能反映其所刊文章的质量。例如,在美国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在《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美国政治学研究》(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或《政治学研究》(Journal of Politics)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在学术评价的时候其权重超过中低档刊物三四篇文章。这是因为,绝大部分政治学家终其一生,也没有机会在上述顶尖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反过来说,既然绝大部分人只有在中档或中低档的刊物发文,那么,文章数量就变成衡量学术水平主要的判断标准。应该说,美国学者在人类知识领域做出的巨大贡献,与强制发表制度的存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可以设想,如果取消了强制发表,美国的科学成果产出会急剧下降,科学发展会发生极大的倒退。
日本虽然没有美国的终身教职制度(tenure track system),但同样高度重视教员的发文数量。据日本《新华侨报》报道,近年来日本大学剽窃他人成果的事件屡见不鲜。产生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大学看重教授论文数量。“在日本的大学里,教授们课上的授业内容充不充分,课下的解惑态度好不好,学校并不关心。学校最看重的是教授们的论文数量,而不是教学质量。教授们发表的论文越多,自己的业绩越多,学校的知名度也就越高。正是这种方针促使教授们不得不想方设法地‘早产’‘多产’。”[9]学术剽窃本身必须严厉打击,但这些事件也反过来证明了发文对于日本大学教师发展的重要性。
三、怎么办?
上文论证了强制发表对于学术共同体的积极意义。但在现实中,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是近些年我国学术成果在数量上升的同时,出现了总体质量下降的趋势。在我国的1 100多所公立大学中,目前从事人文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的教师至少有35万人。这些高校教师每年发表论文约25万篇,出版著作两万余种[10]。一方面,那些周期长、风险高、难以在短期内出成果的研究很少有人愿意去承担;另一方面,学者们在“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压力之下,机械地重复一些低水平的学术研究”[8]。尽管如此,这个悖论并不是强制发表的结果,而恰恰是强制发表无法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原因。
如前文所述,强制发表制度异化的深层次原因至少有三个,其中之一是行政对学术的过度干预。这个问题学术界已经做了很多深入的探讨[10],这里不再赘述。除了减少不必要和不适当的行政干预以外,还有必要进行以下改革:
(一)大力提高学术期刊的质量
学术期刊既是学者展示学术能力的平台,更是区分研究水平的尺度。所谓尺度有两个含义:一是识别并剔除不合格的学术成果;二是对合格的学术成果进行分层(stratification)。由于我国学术发展的滞后,能够切实履行这两个职能的学术期刊数量还很少。
据统计,中国有2 000多份人文社会科学刊物、1 000多份以书代刊的连续性出版物(学术集刊),期刊数量和发文数量都远远超过美国。但是,相当比例的刊物达不到学术期刊应有的水平。规范的学术论文需要严格的论证和检验,以确保为知识的增长做出贡献,因此论文的篇幅通常都比较长。美国很多学术刊物,每期仅发表3~5篇学术论文,其余的篇幅用于刊载学术评论和新书评论。相反,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刊文篇幅普遍较短,权威和一级期刊情况稍好,二级以下期刊一期登载二三十篇论文的并不罕见。例如,《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120页的篇幅就刊登了22篇文章,2014年第4期的《丽水学院学报》共计128页载文25篇。而国际主流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一篇两万字(词)很常见。相反,国内学术刊物一万字以上的文章都很稀缺,而只有4页5 000字左右的文章随处可见[11]。国际学术刊物一般没有篇幅限制,而国内的很多刊物在征稿启事中声明不超过5 000字。严谨的科学研究往往需要较长的篇幅来论理和验证,篇幅限制的代价之一就是削弱了学术论文的规范性和科学性。而大量这样较短篇幅的文章得以刊出,是因为有不合格期刊的供给存在。
要大力提高学术期刊质量,有必要引入淘汰机制,让不合格的期刊退出学术市场。例如,我国的高校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学报,这往往成为本校教师发文的捷径,但绝大多数学报刊登的文章质量低劣,实际上起着干扰学术评价、破坏学术发展的反作用。不仅期刊发文的数量要大量减少,而且应该大力裁减跨学科学术期刊。除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外,我国还存在大量跨学科的综合性学术期刊。这类期刊通常隶属于各级社会科学院或社科联,其刊名通常是“XX社会科学”。虽然《中国社会科学》刊载的文章代表了我国文科研究的最高水平,但地方层面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往往缺乏明确的学科定位,从文学、历史、哲学到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无所不包。由于各个学科发展水平不均衡,刊发的不同学科文章水平也参差不齐。由于缺乏明确的学科定位,给国际学术交流和学术成果评价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二)切实提高研究人员的物质待遇
我国长期以来提倡“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个规则在学术事业上不适合,英年早逝是我国学者群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对北京地区2 500多名中年(45~55岁)高级知识分子做的一项统计调查表明,截止2004年初,北京地区中年高级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为53岁,中科院系统为52岁。在全国范围内,中年高级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仅为58岁,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岁[12]。这个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学者长期生活条件太艰苦,工作压力太大。《科技日报》有文章指出,高校老师平均日工作时间为11个小时[13]。“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以及“只有马儿跑快了,才给草吃”都是错误的做法。学者如果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很难静下心来做学问。即使能够埋头做学问,其结果也必定是竭泽而渔,透支生命。
美国学术的繁荣,与研究人员生活无忧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在研究型大学获得一个助理教授职位,尽管收入因为地域、专业和所在学校财政状况而有所不同,但无一例外都足够维持体面的生活。只有这样,出成果才有了基本的物质保障。研究表明,受到奖励的科学家会越来越多产,而没有受到奖励的则产出日益减少[3]128。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我国相当比例的高校教师生活和待遇已经有了较大的提高。
(三)实行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的分层管理
我国大学教师物质待遇长期过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所有大学教师都要从事学术研究。在我国高校系统,从超一流大学到师范专科学校,无论是否具备科研条件,为了升职和捍卫已经获得的职位,所有教师都生活在申请课题和发文的压力之下。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实际上并没有从事学术研究所需要的热情和才能。因此,对研究的投入虽然不算小,但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现象严重。
尽管在理论上教学可以相长,但在实践中,教学和科研的关系更可能是相冲突的关系。那些长年教授大量本科课程尤其是低段课程的教师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去寻求学术上的突破。反过来说,那些在科研上取得重大进展的人,通常很难从脱离学术前沿的本科课程的教学中获得研究的灵感。正因为如此,美国研究型院校通常要求教师一学期讲授一门研究生课程、一门本科生课程。本科生课程配备数名教学助理,此外还为教师配备一至数名研究助理。供职于研究型院校的教师每教学三学期,会有一个学期的带薪休假,实际上是脱离教学全职做研究,以便把用于教学的时间弥补回来。此外,一些著名高校的政策公开地重研究轻教学。例如,麻省理工学院(MIT)关于授予终身教职的政策指出:“被授予终身教职的人员必须被经由本领域杰出的学者判定其为一流学者,且承诺继续献身于学问。终身教职员也必须在教学和大学服务方面表现突出,但是教学和服务方面的表现并不足以构成获取终身教职的基础。”[14]
在这个问题上,我国也可以学习德国和美国等西方先进国家,把研究型大学和非研究型大学区分开来。在德国,高等教育机构分为四类:综合性大学及其同等级的高校(包括科技高校/大学、高等师范学校和高等神学学校、高等艺术与音乐学院以及职业学院)。这些大学在“培养目标、办学层次、专业设置、教学、科研、师资、招生”等方面均有明确的区分,只有综合性大学及其同等级的高校才从事科学研究。相应的,研究型教授周授课学时平均为8小时,教学型教授则至少18小时[15]。美国的大学大致分为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或称一般综合性大学)、教学型大学(即文理学院)和社区大学四种[7]。科学研究主要由研究型大学的教师承担。教学研究型大学的教师虽然也从事研究,但授课量和教学要求有了明显的提高。通过这样的制度设计,那些学术能力低或对教学更有热情的教师便可分流到教学型大学去。对于教学型大学的教师,可以不做发文的要求,研究资源一般也不配置到这类院校。相反,研究型大学的教师只上很少的课,他们是美国科学进步的主力。这些教师热情高、能力强,能够自觉地紧跟国际学术前沿,主动地致力于学术创新。在美国,这样的研究型大学也就100来所,剩下的2 000多所大学以教学为重,两者各司其职,相得益彰[10]。
其实,我国在《国家中长期教育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已经提出了“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的改革发展目标,强调要“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当然,鉴于我国特殊的国情,也可以在现有高校体制内把教师分为教学型和研究型两种,对这两个群体在业绩考核、资源分配等方面区别对待。日本的研究型大学就有类似的制度设计。日本高校教师被分为教授、准教授、讲师和助教四档,其中教授和准教授从事研究,而讲师和助教是教学型教授[16]。 这样,学术产出减少了,学术刊物接收的稿件减少了,效率反而提高了。经验证明,减少科学家的人数不会降低科学进步的速度。减少科研人员的规模使供求更平衡,最终也许会增加科学事业的吸引力[3]254。
四、结语
目前学界主流的看法,是以数量为主要考核标准的学术评价制度,导致“只求著作数量不求质量,其症结在于没有一个合理的方式来评价学者的学术水准和学术贡献”[17]。本文的论证表明,数量与质量并不必然矛盾,现在的矛盾是学术制度设计和运行不当的结果。本文的立论基础主要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但文章的结论同样适用于自然科学。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的知识激增固然是知识演化和学术群体增长的结果,但强制发表制度功不可没。美国也有学者批评强制发表制度,但从整体上看,学者们还是尊重并维护这一制度的。前文提及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助理教授面临强大的发文压力,这种压力并不限于助理教授。即使已经获得了终生教职,发文的压力始终存在。获评助理教授之后,从法律上讲学校没有权力因为不发文而解聘一个副教授或教授。但在很多大学,副教授和教授每5年必须发表2~3篇文章,否则给研究生上课的资格就会被剥夺,这是明文规定的要求。另一方面,学者们还面临着强大的同事竞争压力(peer pressure),这就形成了美国教授间相互赶超的现象。不仅如此,那些有进取心的系别是不能容忍教授多年不发文的。系里可以通过课时安排、研究资源分配等方面给不思进取的教授施加压力,甚至迫使其自动去职。
虽然强制发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有成本。正如杨小凯所言,强制发表尤其是匿名审稿对新思想的产生很不利。新思想都产生于现有知识体系的边缘,主流的期刊很难接受这些思想[18]。值得庆幸的是,开创性的思想总是极少数。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拓宽了言路,原创性的成果即使没有机会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还可以通过出书、网上发表等方式流传下来,不会轻易地被埋没掉。2002年佩雷曼(Grigori Perelman)在互联网上投递了对彭加勒猜想(Poincare Conjecture)的证明,虽然他的证明没有在匿名评审的权威数学期刊上发表,但仍然获得了国际数学界的普遍认可,被授予“菲尔兹奖”[19]。
综上所述,强制发表不仅不应该放弃,反而应该建设性地加强。当然,对于不同阶段的学者,在发表制度设计时应该区别对待。教授级研究人员是高校科研的中坚力量,对于他们的评价,就不必要求“五年产出十篇”,以避免教授们“选择那些很快有确定结果的研究课题,而不去解决该学科中重要的和困难的智力问题”[3]18。
参考文献:
[1]臧峰宇. 学术评价不妨尝试“代表作”制度[N] . 光明日报,2012-03-21(2).
[2]杨春胜. 直面学术溃疡:李强、贺卫方、陈洪、杨玉圣对话录[J] . 社会科学论坛,2002(6):33-49.
[3]乔那森·科尔,斯蒂芬·科尔. 科学界的社会分层[M] . 赵佳苓,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4]郎咸平. 用理念引导理念[EB/OL]. [2014-09-23]. http://www.langxianping.cn/langxianping/langxianping_linian.html.
[5]杨玉圣. 为什么必须改革目前的学术评价机制[J] . 社会科学论坛,2009(4):73-84.
[6]阎光才. 要么发表要么出局:研究型大学内部的潜规则?[J] . 比较教育研究,2009(2):1-7.
[7]CHARLES M Ess, SUDWEEKS, Fay. Culture,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 Towards an Intercultural Global Village[M]. Herd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8]姜乃强. 学术考核不应以论文数量论英雄[N] . 中国教育报,2009-09-23 (2).
[9]日本大学的“文盗教授”为什么越来越多?[EB/OL].[2014-09-15]. http://www.chinanews.com/hb/2012/02-22/36882
72.shtml.
[10]杨玉圣. 高校科研《去GDP化》刍议[J] . 社会科学论坛,2010(8):73-84.
[11]李强,陈平原,孙立平,等. 大学改革 路在何方?[J] . 读书,2003(9):33-49.
[12]《科学中国人》编辑部. 英年早逝——中国知识分子之痛[J] . 科学中国人,2005(8):6-9.
[13]王会,李凝,仇方. 应警惕高校教师英年早逝现象反弹[J] . 科技日报,2004-10-19(2).
[14]MIT.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A Guide for Faculty and Staff Members [EB/OL] . [2007-08-27]. http://web.mit.edu/policies/index.html.
[15]孙进. 德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分类与办学定位[J] . 中国高等教育,2013(1):61-67.
[16]陈斌. 日本的终身教职制度[EB/OL] . [2014-09-14].http://blog.scientist.cn/home.php?mod=space&uid=504218&do=blog&id=502676.http://blog.scientist.cn/home.php?mod=space&uid=70942&do=blog&id=502583.
[17]朱振岳. 走出人文科学学术量化考核困境[N]. 中国教育报,2010-07-28 (2).
[18]杨小凯. 也谈张五常[EB/OL] . [2014-02-14]. http://view.news.qq.com/a/20070423/000002.htm.
[19]GESSEN M . Perfect Rigor: A Genius and the Mathematical Breakthrough of the Century[M]. 2ndedition.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09.
(责任编辑杨慷慨)
The Logic of Compulsive Publication in Universities
LU Lingyu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4, China)
Abstract:Compulsive publication plays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It would greatly reduce the cost of academic evaluation, help discriminate among scholars, and promote scholars to make academic contributions. Consequently, reform should be directed at excessive 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 unqualified academic journals, low payment of researchers, as well as the mingling of research and teaching oriented institutions.
Key words:compulsive publication; academic evaluation; academic development; leuel administration
杨慷慨(1972-),男,侗族,湖北恩施人,重庆文理学院职业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和职业教育管理研究。
引用格式:朱俊,杨慷慨.职业教育生态位构建与产业空间选择[J].重庆高教研究,2015(1):71-74,88.
Citation format:ZHU Jun, YANG Kangkai.The Niche Construc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ir Space Choice[J].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2015(1):71-74,88.
■ 高等职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