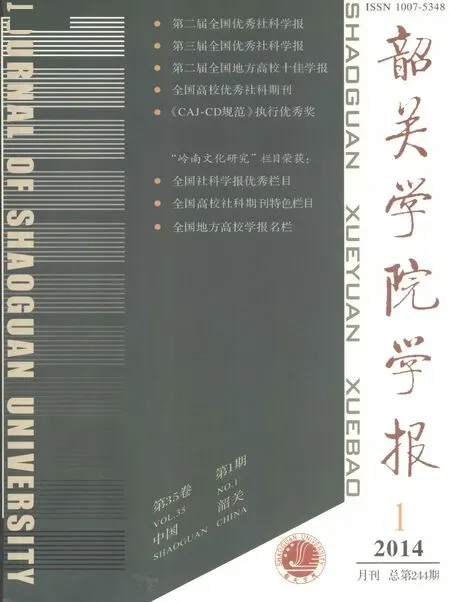我国民事简易程序选择权的反思与进路
2014-04-10谢振声李晓琼
谢振声,李晓琼
(广东财经大学 法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
是否存在民事简易程序选择权是一个一度引起争议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我们可以简单地分为支持和怀疑两个基本立场。支持者的出发点是基于当事人程序自治理论,认为当事人有权选择适用简易程序,以回应程序的自治性和主体性。而这些观点受到了怀疑者的质疑并认为民事诉讼法具有公法性质,诉讼程序不应该由当事人合意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然而,2012年8月31日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民诉法)通过后,意味着民事简易程序选择权在法律层面上得到了认同。因此,我们应当明确的是赋予当事人简易程序选择权并非超前于现实的需求,问题的关键是在于现有法律框架下的制度设计能否保证该程序的有效运行。
一、民事简易程序选择权的立法现状
赋予当事人民事简易程序选择权的其中一个主要初衷是“承认当事人一定范围内合意选择程序的权利,使当事人在追求发现真实和促进诉讼的不同诉讼程序的程序保障中,有平衡追求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的机会”[1],而这一初衷的实现需要得到立法的保障。
最先赋予当事人简易程序选择权的是2003年《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其第2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当事人各方自愿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经人民法院审查同意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因此,司法解释所赋予的简易程序选择权是受到法院约束的,有着很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而正式在法律位阶层面上确立了当事人的民事简易程序选择权的是新民诉法,其第157条第2款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前款规定以外的民事案件,当事人双方也可以约定适用简易程序。仅从这一条款看来,新民诉法似乎是赋予了当事人简易程序选择权。
其实不然,新民诉法第157条的规定仍然是一条宣示性的规定。它并没有赋予当事人自己寻找正确答案的程序权利,主要理由有二:其一,就该条款而言,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原则性的规定,它缺乏了具体细化的规定。我们知道,要想程序的繁简能成为一种可选择、可处分的对象,其前提必须要赋予作出选择权利人充分的知情,不知情难以谈选择。其二,新民诉法第163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即使是当事人双方约定适用简易程序,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于法院。这明显是披着程序选择权外衣的职权主义,从而架空了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
二、民事简易程序选择权的完备性条件
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我国还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简易程序选择权。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才能称为民事简易程序选择权?针对此问题,笔者意图做这样一种分析:民事简易程序选择权的完备性条件包括当事人的充分知情、选择作出前的限制规定和选择作出后的责任承担。其中,当事人的充分知情为总的前提性条件,它所表达的是应对程序进行细化以保证当事人充分知情;选择作出前的限制规定所表达的是一种限制性的选择,简易程序选择权并不是当事人的随心所欲;选择作出后的责任承担所要表达的是一种自责性的后果,是权利与责任共存的结果。
(一)当事人的充分知情
民事简易程序选择权的首要条件应当是当事人的充分知情,作为总的前提性条件,它要求立法者应当制定明确的有关程序选择的规定,使得当事人在作出选择时依法有据。同时,这些规定要为当事人所知道。在理性的社会中,公民只有充分地享有和行使了知情权,才能据以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并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2]。在简易程序选择权中,充分知情所主要涉及的问题是:第一,当事人对行使程序选择权相关规定的了解程度;第二,当事人对所要选择的程序之间异同的了解程度;第三,当事人对选择作出后的法律后果的了解程度。为此,只有程序细化后当事人才有选择的余地,这也是充分知情的价值所在。
我们很难想象,在当事人对程序选择事项一知半解或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赋予当事人简易程序选择权能否具有实质性价值。有学者在分析程序选择权实施所面临的制度困境时认为,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当事人无力行使选择权利。由于诉讼知识匮乏,相当多的当事人并不了解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有何区别,选择简易程序有何利益,加之法官并未对此进行释明,即便其想行使这项权利也不知如何行使[3]。哈耶克在谈及自由时,他十分重视一个人的自由与其所掌握的知识的关系,他认为“某人因无知或迷信而不去做他在获致较佳信息的情形下会去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时也会视他为不自由;据此,我们宣称‘知识使人自由’(knowledge makes free)”[4]8-9,折射到简易程序选择权上就是“知情使人选择自由”。而知情亦即意味着规则要为当事人所知悉。富勒在谈及法律必须颁布时,他提出“在许多活动中,人们遵守法律不是因为他们直接知道这些法律的内容,而是因为他们会效仿那些据其所知更加了解法律的人的行为模式。通过这种方式,少数人对法律的了解往往会间接地影响许多人的行为”[5]。类似于富勒的表达,我们可以得出在简易程序选择权的问题上无须一百人当中有一百人阅读过对程序选择事项的规定,但前提是要有对其规制的具体规定,而不是单纯的原则性规定。
纵观新民诉法第157条的规定,在法律层面上也只是个原则性规定,没有详细的条文,不能形成一个系统的条文、一种有序的规定。由此而带来的问题便是简易程序选择权是在不充分的知情下作出的,那么当事人程序自治理论的出发点也就难以体现,在缺乏充分知情下的程序选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程序选择权。
(二)选择作出前的限制规定
民事简易程序选择权的第二个条件是选择作出前的限制规定。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充分知情下的一个子项,把它单独作为第二个条件来看待是因为程序选择权的“私”性质与民事诉讼“公”性质利害衡量的结果。简易程序选择权并不是当事人的随心所欲,当事人程序自治并不意味着当事人有完全无限制选择的权利,否则这将会是一个可怕的司法。那么我们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应该在哪个阶段对程序选择权的进行限制。对该问题的回答有两种,而该条件所反映的是第二种回答,也是笔者所倾向的限制方式。
第一种回答认为简易程序选择权是受到限制的,这种限制是要通过法院自由裁量权的干涉,通过法院的审查或者是在庭审过程中的发现来进行限制,笔者称其为当事人作出选择后的限制。以法院的审查进行限制的最好例证则是2003年的 《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这一司法解释,从上文也得知,该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各方自愿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的要经人民法院审查,同意与否取决于法院的审查结果。而以法院在庭审中的发现进行限制的最好例证莫过于新民诉法第163条的规定,主要指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当事人双方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不适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法院有权裁定转为普通程序,选择的权利名存实亡。
第二种回答也认为简易程序选择权是受到限制的。不同的是,它认为这种限制来源于作出选择之前的立法明确规定的限制的条件,笔者将其称为当事人作出选择前的限制。这种限制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表现为静态下细化的条文规定。这些规定先于当事人程序选择的作出。换言之,当事人在作出简易程序选择时已包含了对这些限制的考量,在考量后才作出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选择。这样一种有限性,它首先表现为“当事人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选择,而允许当事人在多大范围内选择则取决于立法者的意志”[6]。
笔者倾向于第二种回答。第一种回答只不过是披着程序选择权外衣的法院职权主义。一方面想顺应当事人程序自治的大流,赋予当事人双方简易程序选择权;另一方面,又想加强法院自身的程序控制权,扩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最终架空了当事人的简易程序选择权。而该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必须把对简易程序选择权的限制通过立法的形式前置于当事人的选择,成为当事人作出简易程序选择的考量因素。
(三)选择作出后的责任承担
作为第三个完备性条件,选择作出后的责任承担是一种责任性的后果担当,这是对当事人合意作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选择的一个责任性后果,因为“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人拥有并承受选择的重负,而且还意味着他必须承担其行动的后果,接受对其行动的赞扬或谴责,自由与责任实不可分”[4]83。这种责任性要求当事人自我责任的承担和法院公权力干涉的远离。
当事人自我责任的承担在民事简易程序选择权中的表现,主要是承担放弃接受程序保障更高的普通程序而有可能带来的适用简易程序的不严谨以及资源有限性所带来的偏颇,比如接受法官的独任审判。另外有学者认为,诉讼的民主和对当事人意志的尊重的前提和目的都是为了最大化地实现诉讼的公正[7],但我们所看到的是,当事人双方约定适用简易程序的目的并不是旨在追求公正,他们也有基于成本与效率的考虑。譬如,对于某情节简单、争议不大的借贷纠纷案件,因其标的额达到了一审普通程序所规定的标准,按理应以普通程序进行审理,但是有以下因素使得当事人愿意选择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第一,案情简单能用一般方式就能很好地解决;第二,当事人更愿意花更少的金钱与时间审结;第三,对此类简单案件若适用普通程序则会导致司法资源浪费,对更需要适用普通程序的利用者会造成不公。对于这样的案件不一定都出于公正的考虑。然而,无论是基于公正的考虑还是成本与效率的考虑,只要当事人作出相应的选择则须承担相应的后果。
法院公权力干涉的远离实质上与上文所提及的当事人作出选择后的限制是相同的,即排除法院对当事人自愿适用简易程序并承担相应后果的情况下进行干涉。要注意的是,这种干涉的远离是建立在当事人作出选择前的限制规定和自愿承担相应后果之上的。换言之,一种简易程序的选择是在满足前两个条件之下作出的,那么法院则无需对其进行干涉。不受法院的这种干涉也是当事人作出选择所应承担的后果,因为这意味着当事人要面对诸如虚假诉讼所带来的风险。
三、关于民事简易程序选择权进路的思考
在思考关于民事简易程序选择权的进路上,我们基于这样一个立足点:相信民事简易程序选择权并没有超出现实的需要,只是由于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的制度设计存在的不合理,难以保证该程序的运行。因此,关于进路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在立法上进行考量,从满足三个完备性条件出发进行制度设计。
第一,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程序细化。这是对民事简易程序选择权第一个完备性条件的回应,我们只有在充分的知情下才能更好地行使程序选择的权利。而充分知情则源于程序细化的一系列条文规定。当事人只有深人了解不同程序或不同程序规定之间的差异,才能作出真正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6]。而程序细化所要回答的问题:一是简易程序具有何种优势,即简易程序相比于普通程序具有哪些实质意义上的效率与便利;二是当事人双方在何阶段能合意选择简易程序;三是如何提出约定适用简易程序。
对于第一个问题,现行的状况使人难以分清二者之间的实质意义上的效率与便利,譬如简易程序是独任审判,但是普通程序虽为合议庭审判,然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承办法官以外的两位法官只不过是陪坐,这样起码在审判组织上模糊了二者的实质便利。另外,虽然新民诉法第159条对简易程序的简便方式进行了完善,但是总体上而言简易程序的简化程度还是难以明确。为此,在立法上应明确简易程序的简化程度,使其在便利上能区别于普通程序。对于第二个问题,新民诉法第157条并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双方在何阶段能合意选择简易程序,该条文只是个原则性的规定。笔者认为,对于作出合意的阶段不适宜在庭审过程中作出,因为这会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而理想的阶段应当是在举证期间届满之前,因为在这阶段双方当事人对案件的性质有了充分了解,容易达成选择简易程序审理的合意。对于第三个问题,新民诉法更没有涉及,会容易导致当事人对程序选择了解的不充分,在立法上应明确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主体、对象和期限等内容。
第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对当事人双方约定适用简易程序的限制性规定。简易程序选择权是有限制的,但是这种限制不应当表现为在当事人作出选择后的干涉,而是要把这种限制作为当事人作出选择之前的利害考量。为此,笔者不赞同新民诉法第163条的规定,部分理由前文已叙述,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该条的规定在司法实践当中容易沦为法官不能按期审结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而转为普通程序继续审理的回避责任的工具。为此,在选择作出前进行限制所需要考虑的问题有:一是简易程序的审限及司法资源能否容纳简单的民事案件以外的案件;二是是否有必要对当事人双方约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进行限制;三是采取哪一种立法技术对这些限制进行规制。
其实第一个问题涉及责任承担的问题,如果将情节较为复杂的案件选择适用简易程序审理,那么当事人双方需要承担由此而带来的后果,包括认定事实标准的降低和程序的简化。一般情况下,由于降低标准和简化程序,法官是可以在审限内审结案件的,只是当事人双方需要放弃部分正义。但是,正如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我们认为是有必要对当事人双方约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进行限制。民事简易程序选择权主要是基于当事人程序自治理论,体现了自治性。相反,当案件涉及到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利益时就无须自治性的体现。因此,立法应当把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利益的案件排除在当事人可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的范围。为此,在第三个问题上,建议采用法定反向排除的方式,如可以在新民诉法第157条第二款后增加 “但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利益的民事案件除外”。
第三,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当事人在作出选择适用简易程序后的责任承担问题。在此,我们主要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即对于当事人在作出选择适用简易程序后反悔的情况如何处理。我们不可避免存在这样的情况,当事人在约定适用简易程序后,案件已进入简易程序审理,但此时当事人反悔,提出要转换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存在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假如是双方当事人反悔,那么基于权(权利)责(责任)一致原则,立法上应该禁止此情况的发生。第二种情况是一方当事人反悔,在此情况下需要考虑其反悔的原因,如果不存在欺诈、胁迫等违反当事人意愿的情节,基于权责一致原则不允许反悔,如果存在上述情节,则应当明确该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提供上述情节的证据,在不能提供下不允许反悔。万一存在上述情节而又无法提供证据的,其救济途径可以是上诉、执行异议等其他途径。要注意的是,在此情况下虽然也是简易程序向普通程序转换,但是该转换并不同于新民诉法第163条的规定,前者是经当事人申请并提供证据下的转换而后者则由法院直接决定。因此,立法应当从权(权利)责(责任)一致原则出发,禁止当事人在作出选择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后反悔,除非有正当理由并能提供证据证明。
[1]马登科.论民事简易程序的基本法理[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1):116-121.
[2]汪习根.论知情权[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2):62-74.
[3]汤鸣.放权抑或限权——民事简易程序选择权之反思与重构[J].法学,2007(2):82-89.
[4]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邓正来,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5]富勒.法律的道德性[M].郑戈,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5:61.
[6]李浩.民事程序选择权——法理分析与制度完善[J].中国法学,2007(6):78-91.
[7]张晋红.完善民事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立法分析[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5(3):74-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