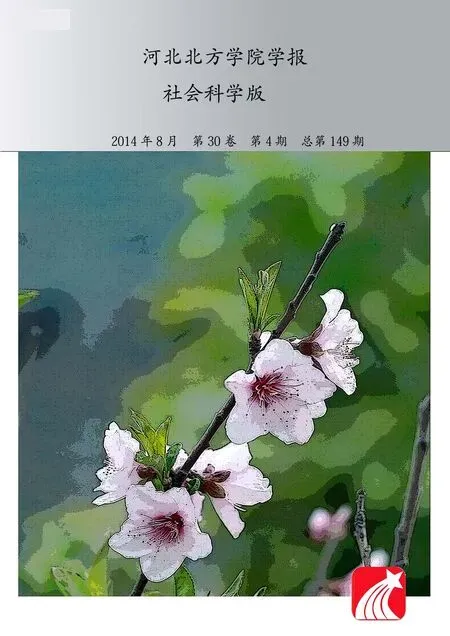顾实与姚明辉《汉书·艺文志》研究刍议
2014-04-05钟云瑞
钟云瑞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273165)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也是中国第一部史志目录。《汉志》根据刘歆的《七略》增删改撰而成,唐宋间,《七略》亡佚,《汉志》便成为了解中国先秦至西汉时期学术发展变化最重要的目录学典籍。王鸣盛评价《汉志》时,引清代经学家金榜的话说:“不通《汉艺文志》,不可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1]125历代学者对《汉书·艺文志》或作考证,或作注解,足以看出它在学术史上的独特地位。
姚明辉的《汉书艺文志注解》[2]与顾实的《汉书艺文志讲疏》[3]便是两部近代注解《汉志》较为杰出的著作,在民间流布甚广。
姚明辉(1881—1961年),字孟埙,江苏省嘉定县(今属上海市)人。著有《反切源流考略》、《中国近三百年国界图志》、《中国民族志》等。《汉书艺文志注解》是其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讲课时的讲义。该书成于1917年,重印于1924年,改名《汉书艺文志姚氏学》,今常见者多为此本。
顾实(1878—1956年),字惕生,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古文字学家。民国期间执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高校,著有《中国文字学》、《说文部首讲疏》、《中国声韵学》、《校定等韵三书》、《中国文学史大纲》、《重考古今伪书考》、《庄子天下篇讲疏》、《穆天子西征传讲疏》、《老子道德经解诂》、《图书馆指南》等。《汉书艺文志讲疏》,成书于1921年,后多次重印。书中附有《见存六艺今古文表》、《见存百家真伪书表》、《黄侃七略四部开合异同表》。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成书晚于姚明辉《汉书艺文志注解》,但姚氏《注解》之中却有两条引用顾实之说(详见下文),或是顾实辗转讲学于各大学,其说流布甚广,故为姚氏所录。下文试就两者的注解特点进行比较,分析它们在体例及学术思想方面的异同,并对其学术价值略作评议。
一、顾、姚两书相同之处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与姚明辉《汉书艺文志注解》在体例与内容上均有相同之处;姚明辉在书中有两处直接引用顾实的观点。
(一)注释体例相同
对图书都采用标注存亡的方法。顾实在每书之下首列“存亡残疑”,姚明辉则用“今存佚阙”等标注。如:
1.《诸子略》儒家类“《子思》二十三篇”[4]1724
姚明辉注“今阙”[2]91,顾实注“残”[3]97。
2.《六艺略》书类“《周书》七十一篇”[4]1705
顾实注“残”[3]29,姚明辉虽未明确标注存亡情况,但在注解中称“中阙十一篇,存六十篇”[2]18。两者文字虽有异,但其实质内容却相符合。
(二)注解内容相同
《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师古曰:“《家语》云孔腾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书》、《孝经》、《论语》于夫子旧堂壁中,而《汉记·尹敏传》云孔鲋所藏。二说不同,未知孰是。”[4]1706
姚氏引《隋书·经籍志》云:“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其末孙惠所藏之书,字皆古文。”[2]21顾实认为,今《孔子家语》、《孔丛子》皆王肃依托,颜师古引孔壁藏书之事,非也。又引陆德明《经典释文》曰:“孔惠藏之。惠即《史记·孔子世家》之孔忠。忠、惠形近而讹。”[3]31
两人虽征引文献不同,但都质疑颜师古旧注,考证所得孔壁藏书者乃孔惠。
(三)姚明辉引顾实的说法
姚明辉在其书中虽未明提到顾实的《汉书艺文志讲疏》,但在行文议论时却有两处征引顾实的观点:
1.《诸子略》道家类“《黄帝铭》六篇”[4]1731
姚氏注:“顾实谓《黄帝金人铭》见于《太平御览》三百九十,《黄帝巾几铭》见于《路史·疏仡纪》。”[2]108顾实原注:“《黄帝金人铭》见于《荀子》、《太公金匮》、刘向《说苑》。王应麟《考证》据《皇览》,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据《太公阴谋》《太公金匮》。《黄帝巾几铭》见于《路史·疏仡纪》。”[3]124
2.《诸子略》小说家类“《鬻子说》十九篇”[4]1744
姚氏注引顾实曰:“道家名《鬻子》,此名《鬻子说》,必非一书。《伊尹说》与此同例。礼家之《明堂阴阳》与《明堂阴阳说》为二书可比证。”[2]137顾实的原注本在“《伊尹说》二十七篇”与“《鬻子说》十九篇”之下,姚明辉把两条注解合二为一。
二、顾、姚两书不同之处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与姚明辉《汉书艺文志注解》注释体例的不同主要表现在标注古籍存亡情况与对待旧注方法方面,注解内容的不同是本篇文章的论述重点,体现出两者在学术史方面的不同旨趣,其中对于章学诚“互著法”的不同态度更是其集中表现。
(一)注释体例不同
1.标注存亡不同
顾实在《汉书艺文志讲疏·例言》中说:“每书首释存、亡、残、疑,俾可一览而瞭。存者篇帙未亏,亡者原书已湮。残者流传有自,无间多寡。疑者论证未定,以俟博考。”[3]1顾实《讲疏》注解《汉志》存亡情况以“存、亡、残、疑”为标识,使读者对于书籍的存亡情况一看便知。姚明辉《汉书艺文志注解》则以“今佚、今阙、今存、不详”标识,同时,亦有不标明古籍存亡情况的例子。下面试举几例:
(1)《六艺略》春秋类“《左氏传》三十卷”[4]1713,顾实注“存”[3]58,姚明辉注“今存”[2]43。
(2)《诸子略》道家类“《鹖冠子》一篇”[4]1730,顾实注“残”[3]122,姚明辉注“今阙”[2]107。
2.对待旧注方法不同
顾实注解体例仍依旧注,《汉志》原文之下列班固自注,后列颜师古的注解,顾实因为班《志》原文与颜《注》“附行既久”[3]4,并未将其删去。姚明辉《汉书艺文志注解》保留了班固自注,但并未将颜师古注解附行在班《志》之下,而是在注解中加以引用。比如:《六艺略》诗类“《鲁故》二十五卷”[4]1707,姚氏注:“今佚。师古曰:‘故者,通其指义也。它皆类此。’”[2]25
(二)对待章学诚“互著法”态度不同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提出目录学著录有所谓“互著法”之说:“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其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著,以便稽检而已。”[5]15并且以《七略》与《汉志》为例:《七略》兵书权谋家有伊尹、太公、管子、荀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9家,而儒家有荀卿子、陆贾,道家有伊尹、太公、管子、鹖冠子,纵横家有苏子、蒯通,杂家有淮南王;兵书技巧家有墨子,而墨家复有墨子之书。这10家1书两载是“互著法”的明证。姚明辉对章学诚的“互著法”是肯定的,而顾实则持有异议,他认为,班固的注解有省重篇的例子,这便与互著法存在矛盾,并且《礼记》中的《明堂阴阳》与《明堂阴阳说》,道家的《伊尹》、《鬻子》与小说家的《伊尹说》、《鬻子说》均为不同之书。因此,就“互著法”一说,两家存在分歧,试举一例:《诸子略》杂家类“《尉缭》二十九篇”[2]1740,姚氏注:“《志》有两《尉缭》,一入《兵略》形势家。《四库·兵家》著录《尉缭子》五卷,《提要》谓此杂家之《尉缭》。案《志》本有互见例,疑此与形势家《尉缭》是一书也。”[2]130顾实注:“《兵》形势家有《尉缭》三十一篇,盖非同书。”[3]153就此例而言,姚明辉认为杂家《尉缭》与形势家《尉缭》是同一种书,而顾实断定两者“盖非同书”。
(三)注解内容不同
1.存亡情况有异
姚明辉《注解》与顾实《讲疏》最明显的区别在于,两者在标注古书存亡情况时多有不同之处。如:《六艺略》礼类“《王史氏》二十一篇”[4]1709。
姚氏注“今阙”[2]32引《隋书·经籍志》礼类叙论云:“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2]32顾实注“亡”[3]47,引材料反驳此种说法,即:“《隋志》作王氏、史氏,似误。《广韵》曰王史,复姓。”[3]47按两者注解存亡情况不同,且顾实认同《广韵》的说法,即“王史”乃复姓,非《隋书》所谓的“王氏、史氏”。
2.对班固序文提出异议
《汉志》的著作体例是先作大序即总序,述说汉代求书、藏书、校书源流及其部类划分依据;其后依六分法编排书目,各小类后有小序;类后有类序,考各类典籍流传、存佚。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4]1701
姚氏征引齐召南《汉书考证》:“此二句指高祖时萧何收秦图籍,楚元王学《诗》,惠帝时除挟书之令,文帝使晁错受《尚书》,使博士作《王制》,又置《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博士。”[2]4并且认为“皆为汉初开辟文学之先河。”[2]4顾实亦引齐召南说,但认为这是“汉人自崇本朝之言”[3]6。他根据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指出汉代初兴,当时只有儒家学者叔孙通为朝廷制定礼仪,《周易》作为卜筮之书未遭秦火,得以流布天下,而“班《志》曰‘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恐未必然。
两人对于汉初是否“广开献书之路”存在不同的见解。顾实认为,汉初并没有“广开献书之路”,或者说“献书”的程度远没有班《志》描述的那样恢弘壮阔。
3.对古籍篇数持有异议
《汉志》中《数术略》各类下著录为“卷”,其余各略各类下均著录为“篇”,具体书目更是“篇”“卷”不分。钱基博在《版本通义》中指出:“《汉志》称篇称卷,不一其辞。所谓‘篇’,竹书也。‘卷’,则帛书也。后世书不用竹帛,虽仍沿用旧称,但含义已新矣。”[6]1姚、顾两家在对具体的篇卷数注解时,存在不同的意见。举例如下:
(1)《诸子略》墨家类“《墨子》七十一篇”[4]1738
姚氏注:“今存五十三篇,佚十八篇。”[2]124顾实注:“残。其书宋世已亡九篇。”[3]144按今本孙诒让《墨子间诂》[7]共十五卷七十一篇。
(2)《诗赋略》屈赋之属“《宋玉赋》十六篇”[4]1747
姚氏注:“今考《楚辞》载《九辩》十篇,《招魂》一篇,《文选》载《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四篇,凡十五篇。”[2]145顾实注:“《楚辞·九辩》十一篇,《招魂》一篇,文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四篇,凡十六篇。”[3]170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楚辞》载《九辩》10篇或11篇的差别。按今洪兴祖《楚辞补注》[8],《九辩》共10篇。
4.注解人名、书名不同
(1)《六艺略》礼类“《军礼司马法》百五十五篇”[2]1709
姚氏注:“旧题齐司马穰苴撰。”[2]34顾实注:“《七略》本列在兵权谋家,班氏出彼入此也。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3]49按姚振宗:“《司马法》一书,自太公、孙、吴、王子成父皆有所论者。至穰苴,又自为兵法申明之。齐威王又使大夫论述,并穰苴所作附入其中。合众家所著,故有百五十五篇之多。”[9]28根据姚振宗的论述,则《司马法》并非司马穰苴一人而作,而是历代兵家附益增长而成。
(2)《六艺略》书类“《周书》七十一篇”[4]1705
姚氏注:“今《四库》著录《逸周书》十卷,入别史类。”[2]18顾实注:“残。清《四库》史部别史类著录《周书》十卷。后世或题曰《逸周书》,亦题曰《汲冢周书》,均失之。”[3]29顾实对《逸周书》之称持有怀疑态度。
5.顾实批驳颜师古注
如《六艺略》书类“《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4]1705,颜师古注曰:“孔安国《书序》云:‘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承诏作传,引序各冠其篇首。’郑玄《叙赞》云:‘后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篇。”[4]1706顾实注曰:“师古引伪孔安国《书序》,妄也。”[3]22引用桓谭《新论》说:“《古文尚书》旧有四十五卷,为五十八篇。”[3]22顾实因此对《古文尚书》的篇数详加解释:“于今文同有之二十九篇,加得多古文十六篇,此《新论》所以曰四十五卷也。于今文同有之二十九篇中,出《康王之诰》于《顾命》,是为三十,加多十六篇,此班《志》所以说四十六卷也。十六篇中,《九共》为九,三十篇中,《盘庚》、《泰誓》各为三,是为五十八,此《新论》、《别录》所以皆曰五十八篇也。《武成》逸篇,亡于建武之际,班据见存,此班《志》所以曰为五十七篇也。”[3]23
姚氏注解全依颜师古的旧注,而顾实对于师古引用孔安国的《书序》作注解,评价其为“妄也”,并为此详细解释。
6.对《汉志》条目注解的方式与内容不同
姚氏常常将《汉志》多个条目合为一条注解,如《六艺略》礼类“《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4]1709,这本是两句话,顾实分作两条,《礼古经》五十六卷,顾实注 “残”[3]41;《经》七十篇,顾实注“存”[2]31。而姚氏并为一条作注,且并未注明存亡情况。需要指出的是,此处姚氏引宋人刘敞说,谓“此七十与后七十皆当作十七,计其篇数则然”[2]31,而顾实误记作“刘歆”[3]41。又如《六艺略》孝经类“《小尔雅》一篇,《古今字》一卷”[4]1718,顾实分作两条,《小雅》下注“存”,《古今字》下注“亡”。姚明辉则作一条解,注云“今皆佚”[2]67。
7.每略统计家数、篇数不同
(1)凡六艺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入三家,一百五十九篇;出重十一篇[4]1723。
姚氏:“如目实三千八十五篇”[2]83;顾实统计:“适符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之数。”[3]92关于班固自注“入三家,一百五十九篇;出重十一篇”,两家见解不同:
姚明辉:“《书》入刘向《稽疑》一篇,《礼》入《司马法》百五十五篇,小学入扬雄、杜林三篇,实四家一百五十九篇。”[2]83姚氏认为班《志》较刘歆《七略》新入刘向、《司马法》、扬雄、杜林4家。
顾实:“《书》入刘向《稽疑》一篇,并入《五行传记》,则不记家。故《礼》入《司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小学入扬雄、杜林二家,三篇;适符三家,一百五十九篇之数。”[3]92顾实因为刘向《稽疑》并入《五行传记》,并不算做一家,所以只有《司马法》、扬雄、杜林3家,这样就与班《志》家数符合。
(2)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4]1727
姚氏注:“如目实八百四十七篇。”[2]102顾实注:“今计五十二家,八百四十七篇,家数与后总数合,明是‘二’误作‘三’,但多十一篇耳。”[3]110姚明辉与顾实统计的篇数相同,而顾实总计家数为52家,按张舜徽引姚振宗的说法:“所载凡五十二条,条为一家,实止于五十二家。《穀梁序疏》引此条亦云五十二家。此云五十三家,三当为二。其篇数则缺少十一篇。”[10]280
8.两家注解详略不同
姚、顾二家在注解上各有特点,具体到各篇更有详略的差别。例如:《诸子略》道家类“《筦子》八十六篇”[4]1729。
姚氏注“今存”[2]104。顾实注“残”[3]114,引严可均《铁桥漫稿》说:“八十六篇至梁、隋时,亡《谋失》、《正言》、《封禅》、《言昭》、《修身》、《问霸》、《牧民解》、《问乘马》、《轻重丙》、《轻重庚》十篇,宋时又亡《王言》篇。”[3]114
9.顾实较姚氏注重辨伪
如《兵书略》兵权谋家“《吴起》四十八篇”[4]1757,姚氏注:“今阙。存六篇。”[2]196顾实引王应麟的说法:“《隋志》《吴起兵法》一卷。今本三卷六篇,《图国》至《励士》所阙亡多矣。”[3]194并对王说进行批驳:“王说未谛。今本六篇,成一首尾,辞意浅薄,必非原书。”[3]194顾实认为今存《吴起》6篇并非原书,所以注“疑”。
综上所述,姚明辉《汉书艺文志注解》与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在体例和内容上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诸多不同之处。这些不同之处,恰恰体现出姚氏和顾氏的不同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旨趣。姚明辉的《汉书艺文志注解》在注解体例上仍依循旧注,在内容上广泛征引前人对《汉志》的注疏,如南宋学者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清代学者王先谦《汉书补注》等。顾实在注释中则更注重学术史的阐述,对学术史上的今古文之争等问题作了精详的考辨,使经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清晰地呈现出来,对存在异议的学说追根溯源,以明其流变。通过对两家著作的比较分析,以期能对学者深入研究《汉志》提供一些帮助。
[1]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陈文和,王永平,张连生,等,校点.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2]姚明辉.汉书艺文志注解[M].上海:江南印书局影印本,1924.
[3]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章学诚.校雠通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6]钱基博.版本通义[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7]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
[8]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9]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M].北京:中华书局,1955.
[10]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