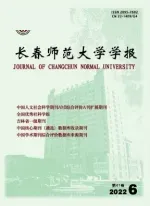改写他者的性别想象
——论凌叔华的女性情感书写
2012-08-15陈静梅
陈静梅
(贵州财经学院文化传播学院,贵州贵阳 550004)
改写他者的性别想象
——论凌叔华的女性情感书写
陈静梅
(贵州财经学院文化传播学院,贵州贵阳 550004)
在杨振声的短篇小说《她为什么忽然发疯了》中,同性恋爱的题材仅仅是批判社会的一个工具,目的是呼吁营造良好的男女恋爱环境。凌淑华的《说有这么一回事》从淡化女主人公的“男子气”和深入刻画女性心理活动两个方面对其进行了改写,这种改写不仅肯定女性具有自主开发情欲的可能,同时通过模仿新女性对性别规范的自觉遵守,讽刺性地揭示出其所遭遇的自由解放困境。
性别想象;男子气;困境
在五四时期最显著的“人”的声音的呐喊中,涌现出一批描写女性情感的作品,这当中,也有或隐或显地关于同性之间亲密感情的抒发。许多男女作家都曾涉及这一题材,如庐隐的《海滨故人》、《丽石的日记》,丁玲的《暑假中》、《岁暮》,凌叔华的《说有这么一回事》,叶绍钧的《被忘却的》等。这些作品都对女女之间情感纽带的缔结以及所遭遇的传统性(别)规范秩序的破坏进行了描写。然而,相较于庐隐与丁玲作品所受到的重视,凌叔华的创作并未受到太多关注。对于这位以“闺秀”派风格闻名文坛的女作家而言,这种题材选择与其深具传统的婉约气质是否形成矛盾?另一方面,《说有这么一回事》是在男作家杨振声同题材小说《她为什么忽然发疯了》基础上进行的改写,那么,男女作家关于女性之“性”的想象是否有差异?本文立足对凌叔华的《说有这么一回事》的解读,以期对五四时期有关女性之“性”的多样化表达,以及女作家对自我的思考与男作家想象女性的差异及其原因进行回答。
一、五四时期女同性爱书写的时代背景
清末到“五四”时期,对国家民族存亡问题的思考,占据着知识生产的主流位置,尤其是中国必须图谋强盛才能在世界舞台上继续存在,这一观念已然深入人心。有识之士纷纷利用报章、杂志、文学作品等文化媒体,营造出复兴民族国家的文化想象。既有的器物和典章制度改革均无法达到抵御列强、重振纲纪的目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思考一条可能的富强之路就成为20世纪初叶中国朝野人士的新作业。[1]不限于此,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在1895年后的流行,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受到影响,由生物界的竞争而衍生出来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等观点,透过严复、谭嗣同、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的翻译、推介,大部分有识之士确信,对现代国家的首要资产——人口——尤其是被视为国家未来中坚的青少年——进行有效维护与掌控,是国家兴亡的基础。于是乎,国民身心的改造在清末民初成为新的改革焦点,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在这样的文化脉络下,不健康的身体及行为如畸形人、同性情欲行为等,自然受到知识分子的关注。
另外,在大城市中,新女性走出传统家庭,她们对婚姻的抗拒态度,引发了男性知识分子的焦虑,也促使同性情欲成为关注点。“由于传统家庭制度是家长统治式的——即建立在男性可以公开群交或多妻,而女性则须性稳定、守贞以及忠实的基础上——新的自由首先意味着一种新的女性性意识的产生”[2]。换言之,女人们可以用异于包办婚姻的方式选择她们自己的性对象,她们也可以享有独身的自由。在这一意识背景下,有关“同性恋”(homosexuality)这一性学概念的翻译及讨论文章,开始在各类报刊杂志、性教育手册上出现,并在20世纪20年代达致高潮。19世纪以来欧洲性学研究领域对同性情欲问题开展过研究的重要理论家,比如德国赫希菲尔德(M.Magnus Hirschfeld,1868-1935)、奥地利克拉夫特·埃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1840-1902)、英国霭理士(HenryHavelock Ellis,1859-1939)、奥地利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 等,通过知识分子的介绍、翻译或讨论,一一出现在了中国知识阶层的读者视野中。
这些现象意味着,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在处理同性情欲问题上,与西方科学知识的接轨非常迅速。如果这一论断可以成立,那么,它也同时说明,有关同性情欲的翻译材料是广泛的、多样的,而在这一时期,诚如学者桑子兰的研究所指出的,尽管也开始出现对同性情欲实践进行医学矫正的意见,但它并不表示“同性恋”这一概念在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被简单地理解为属于个体的一种本质的、病态的性倾向,其中反而是围绕着新词语“同性爱”出现种种的矛盾甚至争论,这一新词语后来成为“homosexuality”这一英文的汉语翻译,它也为文化界、文学界的知识分子以及读者提供了一个讨论场域,使他们由此探讨、思考民国时期有关性、教育以及个人主体性等议题的现代意涵[3]。
这一议题也出现在作家们的关注中。批评家赵景深对之进行的总结颇具代表性。他首次将性学术语用于文学批评的文章——《中国新文艺与变态性欲》,在其中,他融合弗洛伊德以及霭理士关于变态性欲的理论,粗略地列举了“五四”时期文学创作所涉及的变态性欲类别,如母子恋、父女恋、自我恋等。他提出,在这些作品中,描写得最多的要算同性恋爱,他并且开出了包括庐隐、叶绍均、章衣萍、张资平、叶鼎洛、黄慎之等在内的作家名单[4]。这种对文学范畴中的情感关系所作的简单分类,虽然表面上可视为批评家运用性学话语解释文学创作的试验,但它同时透露这样的意思,即批评家或作家同样试图引导城市受教育的读者,去认识并理解同性亲密关系的意义。
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比阅读男女作家的同题材作品,来探讨“五四”时期文本书写所建构的关于“性”的想象,以及男女作家在表达女性情感方面的差异及原因。
二、作为一种社会问题存在的女女情爱
在杨振声的短篇小说《她为什么忽然发疯了》中,同性恋爱的题材成为批判社会的一个切入点,其目的是呼吁营造良好的男女恋爱环境。原文发表于1926年1月11日《晨报副刊》上,它以女校为背景,记录了女学生顾影曼与邓云罗之间从相恋到分手的过程。小说受到了性学理论中从性别倒错角度理解同性爱观点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作者用男女配的模式来处理影曼与云罗的情爱关系,并且强调这份爱情是在缺乏异性的环境情况下“被迫”而生。
叙述者这样评价两人:“她们二人平素就是很要好的,经过作戏(即参加学校周年的戏剧表演——笔者注)之后,更形亲密了。顾影曼本来性情豪爽,有些男子气的;邓云罗又是正当十八九女性发皇要求爱情的时候。正巧生在个礼仪之邦,她们得不到男女正当的交际,就免不了同性间钟情起来了。”[5]需要注意的是,他的这种刻板想象与他对女女肉欲的堵截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在小说开头的戏剧表演场景中就已显露。在表演“离别”片段之时,云罗偎在影曼怀里,面对她那“微启要求接吻的口唇”,叙述者描写影曼对云罗“丰盈娇软身体”产生了反应:“心里真个嘣嘣跳起来了”,“暗想道:‘可惜我不是个男子,不能消受这个可怜虫!’”[5]这一心理反应进一步在表演结束之后由影曼亲口向云罗说了出来:“你这个不要脸的丫头,今天晚上作出那种可怜的调调儿,真把我的心都弄软了。可惜我不是个男子,不然,现在我可要真个消魂了。”[5]云罗则回答“呸!谁教你不是个男子来!”当影曼提出再抱她时,她是“一面挣扎”,一面“似怒非怒”地拒绝了影曼。影曼对自己不是“男子”的强调以及云罗对身体接触的拒绝,表明文本试图对女女之间存有欲望发生之可能的否认,换言之,作者字里行间力图传达的信息是:女女之间并不存在男女之间的那种情爱,她们只是对异性情爱关系的模仿而已。
另外,这种模仿性还体现在两人对待异性婚姻的不同态度上。尽管父母为云罗所安排的包办婚姻,直接破坏了两人同性爱关系的维持与发展,但当影曼要求云罗答应自己不嫁人时,文本描写云罗的反应是“含泪看了影曼半天,半嗔半叹地说道:‘谁叫你不是真的Romeo呢!’”云罗对影曼“假/扮男人”身份的指认,与她放假离开影曼回家后对影曼感情的冷淡表现是统一的。例如,她很少给影曼写信,即使写也就短短几句问候话;更为重要的是,她写信告诉其他同学自己订婚的消息,却并不告知影曼,还在信中嘱咐同学不要让影曼知晓。文本通过她的这些行为一再强调了同性爱只是暂时的,一旦面临异性婚姻的选择,女性就会毫不犹豫地奔向它。因此,就文本对云罗的刻画而言,父母包办的异性婚姻似乎成为她脱离同性爱的一条“救赎之道”,在此,她对影曼的忘情并非凸显她的“薄情”,而是从一个侧面强调:女女同性爱仅仅是环境限制下的产物。这在故事结尾中得到更加强烈的印证:正在焦灼等待云罗返校的影曼,无意中从同学的谈论中得知其订婚的消息,她当即变得疯癫,表现形式是将自己投射为舞台上她所扮演的男性罗密欧。事实上,从杨文的题目“她为什么忽然发疯了”可以看出,小说试图引发读者去思考的重点是造成影曼疯癫的社会原因,换言之,作者关注的焦点在于“是什么”使影曼陷入同性爱而不能自拔,而非影曼与云罗所实践的同性恋爱本身。
因此,在作品中,影曼的疯癫下场指向的是对社会未能实行男女社交公开的控诉。与此同时,它也暗含了一种担忧,即女性有可能将同性恋爱作为最终的情感选择和归宿,而不把同性恋爱仅当作一种暂时的情感过渡。于此,疯癫的结局影射了这种感情势必受到的惩处。
三、女女情欲的自然流露
1926年5月3日,《晨报副刊》刊发了凌叔华同题材的作品《说有这么一回事》。在小说正文的前头,题有杨振声的几段话,他表明,由于自己的写作是在一天内完成的,非常草率,“尤其是故事结尾对主人公疯了的处理显得太匆促,所以请凌叔华重写。”[6]尽管在凌叔华笔下,故事背景与情节基本与原作相似,但仔细对照原作,凌叔华对女性之间自发性情爱的肯定却是原作不具备的。这在小说中体现为两方面:
第一,尽管凌叔华小说的背景仍然是单一性别的女校环境,但作家明显淡化了女主人公之一的影曼的“男子气”。影曼仍然在话剧中扮演男角罗密欧,但文本暗示她担任这一角色的原因是基于她“比云罗高一班”,性格比较活泼(“平日很爱说笑话”),且又是高个子的北方人。这种淡化其“男子气”的处理,目的在于表明影曼与云罗的情爱,产生于两人情感上的互相吸引,而并非是由于处在一个缺乏异性的环境中而让一个有男性气质的女性充作临时的替代。
第二,凌叔华的小说细致刻画了云罗在与影曼相处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并突出描写了她与影曼情欲互动的愉悦。
云罗对影曼的感情经历了从“局促”到“感觉舒服”的发展过程。在演戏之前,她从不敢与影曼说话。二人因排练结识之后,影曼喜欢当着许多同学取笑她,文本形容云罗的反应是“非常局促,觉得有些厌恨她;但是不知为什么,每逢听她高声喊朱丽叶的时候,她心里就有些跳,却不是生气的暴跳。”[6]二人最后排完戏的那天晚上,影曼送她回宿舍,云罗换上睡衣倒在床上,影曼面对妩媚动人的云罗以及帐子里传出的醉人香气,不禁搂紧云罗,要求闻她的身体。当时两人的亲密情形遭到了宿舍同学的取笑,然而,影曼还是“趁人笑的当儿,把脸伏在云罗胸口,嗅个不停”。
云罗如何反应呢?叙述者这样说道:“不知云罗是因为真没力气抵抗,还是喜欢胸口有样暖绵绵的东西盖着,她此时也不嚷了,只低声笑说:‘压断气了!’”[6]到此,如果说云罗的反应仅仅是暗示她对影曼有好感,那么,文本接下来通过云罗主动留影曼同床的行为以及云罗的心理感受,暴露出这种好感实乃基于一种爱的心理。第二天晚上演完戏后,因为下雨的关系,云罗主动拉影曼到自己宿舍避雨并劝其留下同宿。文本对她半夜醒来的心理进行了如此描述:“云罗半夜醒来,躺在暖和和的被窝里,头枕着一只温软的胳臂,腰间有一只手搭住,忽觉到一种以前没有过且说不出来的舒服。往常半夜醒来所感到的空虚,恐怖与落寞的味儿都似乎被这暖熔熔的气息化散了。她替影曼重新掖严被筒,怕她肩膀上露风。”[6]
这段对云罗的心理描写表明,云罗对影曼的爱是出于自发与自愿。文本还透过影曼醒后吻云罗的额头、摸其腮颊等动作,以及云罗不仅不反感,反而“把腮贴在她的脸上”等行为,进一步补充说明了两人恋爱的真挚与热烈。在小说后半部分,云罗因兄长安排的包办婚姻而陷入忧愁,影曼为鼓励她,特意以一对同性伴侣为例(生活了五六年的学堂教习陈婉真与Miss Chu),要求云罗与自己应该以她们为学习的榜样。
可见,凌叔华的同性爱书写明显区别于杨振声,这种不同在于,凌叔华不仅呈现出女同性爱的多样化面貌,而且也确切肯定了女性在同伴之间进行性实践的自发性与可能性。
尽管凌叔华肯定女性之间存在自发的情欲,但是,正如小说中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所指涉的悲剧意味,她也预先为云罗与影曼的关系埋下伏笔,即只能是悲剧收场。尤为反讽的是,云罗并非莎士比亚笔下的朱丽叶,敢于为爱而选择自杀,成为反抗封建包办婚姻、追求个人幸福的叛逆者,相反,她屈服于社会压力,接受了家庭对其婚姻的安排;影曼的下场也只是在得知云罗结婚的消息后晕倒而已。表面上看,凌叔华所安置的这一结局,似乎暗示了女性对父权制及其异性恋体制的臣服。
在同时代及之后的男性批评家眼里,凌叔华一向被视为所谓的“新闺秀派”的代表作家[7]。这一称谓表明,凌叔华写作具有明显的女性风格与日常性特点。她的确关注旧式家庭中女性的日常生活,但是,恰如史书美所言,凌叔华成长于传统家庭,她接受的教育主要是中国经典的教育,并深受传统文人画影响,因此,在考虑她的经历与表述风格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可以看到,选择以温文的女性风格写作,这对于女作家来说显得不那么具有威胁性;她的“闺秀”风格看上去是自愿选择了父权制的写作制度,并将女性作品归入女性气质的范围,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她也同时通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模仿破坏了这种写作制度[8]。从这一视角出发,凌叔华对女女相爱结局的处理,正是利用一部分新女性对性别规范的自觉遵守,讽刺性地揭示出新女性在“性”方面所遭遇的自由解放困境。
云罗与影曼的悲剧主要来源于云罗家兄为其安排的包办婚姻。叙述者插入云罗暑期寄给影曼的书信,揭示了云罗面临的处境:
……你怎样能疑惑到我忘了你呢?我只怕你将来倒顶容易忘掉我呢!我自己知道我没有一样可以永远使人爱慕的,第一我的知识比你差得远了,我又不好用功,又爱玩,那天赶得上你呀?我在家更不能用功了。自从我回家后,天天有客来找母亲又要见见我,讨厌极了。每次他们要来,母亲就千嘱咐万嘱咐我换衣服匀过粉,昨天我觉出不是好事来,不听她的命令,她吃夜饭时总泪汪汪地说,现在女儿大了心也大了,老娘说的话都是腐败要不得的。我只好忍泪陪笑听她唠叨。咳,自从爹爹死后,她为哥哥同我受的苦恼真不少了。
你别怪我信迟,我这是回家后第一次与人写信。我昨夜望了月儿后面的星发痴有好久好久。你在家中多乐,不会有工夫望着月儿吧?我的星,光明烂漫的星,你瞧见我的泪光吗?[6]
在此,第一人称的叙述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陷入主体分裂的女性形象。类似的这种分裂,我们还可以在凌叔华小说中那些同属新女性的妻子们身上看到,例如《春天》中的霄音、《酒后》中的采苕等,造成分裂的原因在于旧有生活方式规定的性别角色与新的主体价值观念之间的分裂。就云罗而言,其内心的割裂同样对应于她所面临的两种角色冲突:理想的性别自我(即做影曼的爱人,在此她是情感、意志的发动者)与社会规定的性别自我的冲突。在此,这一社会规定的性别自我包含两重含义:第一,它是旧文化的社会性别角色的体现,这一性别角色排除了女性作为主体的一切可能性,于是,遵从父母之命完全取代自我选择的可能;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属于异性恋体制下的性别角色,即贤妻良母的角色标准尽管在“五四”时期已作为旧价值体系的一部分而被废弃了,但“女性”的性别定义仍然密切联系着男婚女嫁的现实人生。
所以,云罗最终还是认同母亲为自己所安排的包办婚姻的命运。这一结局一方面表明新女性其实无从基于女性的立场来树立自己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它也暴露出在社会强大的“恐同”压力之下,新女性们不得不选择性别顺从作为出路。在小说的最后,作者并未如杨文那样将影曼处理为疯妇,而是作了这样的描述,即影曼从同学谈话中得知云罗结婚,晕倒在地:
一会儿她便被同学抬到一张床上躺着,睁着眼看见来了许多人,人人都象要说许多话,她听不清楚,也不耐烦听,只好闭上眼,一会约摸似乎云罗哭……又似乎在笑,又似乎在哭……
她不耐烦看了。“咳!”出了一口气,站在旁边的人都说:“好了,好了,她醒过来了!”[6]
这一结局颇富象征意味,它真实地呈现出“五四”时期一些扮演着社会性别角色的女性,尽管接受了新式教育,却反而陷入双重困境:一方面,她们无法彻底摆脱旧伦理观念的束缚;另一方面,她们也无法完全认同反抗者的姿态,做一个无惧世俗任何压力的新女性。所以,在小说中,她们最终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的摆布。可见,凌叔华通过对杨振声同题材作品的改写,揭示了“五四”时期一部分女性的被动人生及其背后所隐藏的父权制机制,正是这一机制使得女性即使在能够获得现代教育,甚至得到更大的社会自由的前提下,仍然会将传统的性别规范内在化,自觉遵守着贤妻良母的家庭原则所指导的人生之路。
[1]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17.
[2]周蕾.原初的激情[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1:113.
[3]Tze-Lan D.Sang.The EmergingLesbian:Female Same-SexDesire in Modern China[M].Chicagoand London:UniversityofChicago Press,2003:100.
[4]赵景深.中国新文艺与变态性欲[J].一般,1928(1):204-207.
[5]杨振声.她为什么发疯了[M]∥中国现代文学馆,编.杨振声代表作.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99,98,98,.
[6]凌叔华.说有这么一回事[M]∥中国现代文学馆,编.凌叔华代表作.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1,75,76,78,82,84.
[7]毅真.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M]∥黄人影.当代中国女作家论.上海:光华书局,1933.
[8]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251.
Rewriting Male Writer’s Gender Imagination:An Analysis of Female Affection in Lin Shuhua’sA Hearing Story
CHENJing-mei
(School ofCultural Communication,Guizhou UniversityofFinance and Economics,Guiyang550004,China)
Yang zhenshen’s short story,Why She Suddenly Mad,used female same-sex love to criticize society and call on buildinga good environment for love between man and woman.LingShuhua had changed this storyfromtwoaspects:one is to devalue heroine’s masculinity,the other is present the internal workings of female minds.The rewriting is able to not only confirm female autonomy on sexual desire,but also reveal the new women’s freedom liberation dilemma through intimatingtheir obedience togender normal.
gender imagination;masculinity;dilemma
I206.6
A
1008-178X(2012)01-0114-05
2011-09-22
陈静梅(1979-),女,贵州瓮安人,贵州财经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从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外文学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