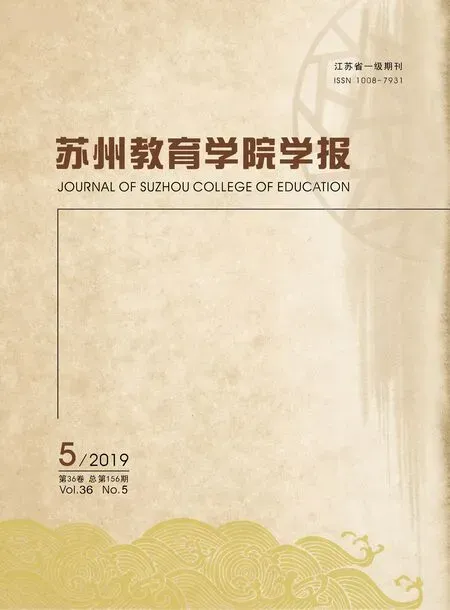读凌叔华一组佚信
——关于凌叔华集外文札记之四
2019-02-21陈学勇
陈学勇
(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人一生书信之无数可以想见,文人勤于尺牍更不必说,但得以留存下来的则少之又少,凌叔华亦是。幸胡适有收存来信的习惯,《凌叔华文存》[1]得以辑入二十余通,为所辑凌氏信函的大半。尚有若干散佚于他人著述,有些仅存片段。现就几个“片段”略作释读。
一、致徐志摩信(片段)
凌叔华与徐志摩一度书信往还频频,然未留存一纸,唯《爱眉小札》[1]中幸留痕数语,见诸1925年8月23日徐志摩致陆小曼信的转述:
我觉得自己无助的可怜,但是,一看小曼,我觉得自己运气比她高多了。如果我精神上来,多少可以做些事业,她却难上难,一不狠心立志,险得狠。岁月蹉跎,如何能保守健康精神与身体!志摩,你们都是她的至近朋友,怎不代她设想设想?使她蹉跎下去,真是可惜。我是巾帼到底不好参与家事……[2]
其时,徐陆正处在热恋阶段,而此前外人盛传凌叔华与徐志摩之间有恋情。这个片段或可证明所谓的恋情是捕风捉影——当然事出有因,不赘。只说凌叔华是陆小曼闺蜜,两人已有过多次长谈,陆也曾经写四五千言长信向凌叔华倾诉心声,凌也自诩陆小曼“引我为至友”,这几句并无大碍的话,凌本可和陆面叙,她俩当面说过的话肯定远胜于此,何劳徐志摩转述?或可设想,凌叔华委婉劝说陆却没有奏效,所以不得不敦促诗人再行规劝,其与陆友情的真挚可见一斑,也不妨说,是对徐的间接规劝,也可看出她对徐志摩情感的热忱。但谨慎细致的凌叔华,这回措词却很不贴切,指徐志摩为陆小曼的“至近朋友”,与事实上两人热恋的关系相去甚远;同样,言“家事”也欠妥,不论如何亲密的关系,婚前总不能这么说的。这个书信片段显示了三个人两两之间的微妙关系,似可玩味。
这里值得关注的,不只是凌叔华对陆小曼的关心,更可留意凌叔华本人心态的流露。说自己无助、可怜,怕是虚晃一枪的自谦,自信才是本意。写此信的年初,她因《酒后》名噪一时,此后又连连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上发表作品,赢得“闺秀派”代表作家的美誉。凌叔华对朋友表示关心,潜意识里隐含着成功人士的自信和成就感。
二、留给林徽因的便条
徐志摩突罹空难,朋友们拟为他出套作品“全集”,故多方搜罗诗人的著述、信函、日记。凌叔华、林徽因均有数量可观的诗人来信,然而又均不愿公之于众,仅数年后凌叔华在她主编的《武汉日报》副刊“现代文艺”上选登过几封掐头去尾的书信。徐志摩生前将一批文稿归置小匣,世人谓之“八宝箱”,他将其托付给凌叔华保存,以作日后自己传记的资料。其中有徐志摩旅英期间单恋林徽因而作的“康桥日记”,有徐陆热恋时的陆小曼日记。此皆公器,遭操理“全集”事务的胡适等人追逼,凌叔华不得不交公,但过程并不爽快。约空难发生一周后,凌叔华交出八宝箱给胡适,但却扣留了“康桥日记”。1931年12月6日,凌叔华与林徽因都参加了徐志摩追悼会,翌日,凌去林家,她想编集《志摩信札》,便要求看看徐志摩写给林的英文书信,林说在天津的住处,凌叔华认为这是不肯示人的托词。林徽因说,交胡适的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日记均在林这里,顺势要求借阅“康桥日记”,凌叔华应允林差人后天来取。凌叔华对胡适将“陆小曼日记”给林徽因寓目很是不满,因为里面有陆对于林的微词。但至12月9日林徽因亲自登门之时,凌叔华竟爽约出门,留下前一日拟就的便条:
昨归遍找志摩日记不得,后捡自己当年日记,乃知志摩交我乃三本:两小,一大,小者即在君处箱内,阅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满写的)未阅完,想来在字画箱内(因友人物多,加意保全),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书物皆堆叠成山,甚少机缘重为整理,日间得闲当细捡一下,必可找出来阅。此两日内,人事烦扰,大约须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寻也。[3]143
林徽因为此大为不快,疑其延宕时日,以便复抄留底。过数日,凌叔华才送“康桥日记”到林府,但仍只是前半册。半月后再经胡适追逼,她才补交了后半册,还是裁截几页。胡适当天日记写道:“我真有点生气了。勉强忍下去,”[3]145林徽因当然更生气,致长信给胡适大大发泄了一通,以至稍稍失态,有悖闺秀风度。尽管最后交出后半册日记时凌致信胡适:“此事以后希望能如一朵乌云飞过清溪,彼此不留影子才好。”[4]几年后,林徽因编选《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小说选集,不咎嫌隙选入凌叔华作品,而凌叔华直到晚年仍耿耿于怀,乃至迁怒胡适,“如此卖力气死向我要志摩日记”[5]。凌叔华与林徽因的“八宝箱”事件,其中的是是非非至今仍不大说得清楚,明白无误的是,凌与林由此交恶不再往来,这张便条正提供了当年芥蒂的一些细节。
三、致张秀亚(片段)
凌叔华在国内成名,在国外终老,而张秀亚是去台湾后才享得盛名。两人的年龄相距差不多二十个春秋,属文坛隔代才女。许多人都不知晓这两位女作家曾经过从数十年,忘年交的起始便是下面这封信:
……我已来到北平家中,你要不要来玩玩呢,你可于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搭车由津来平,在我处住一晚,我们仔细谈谈,第二天下午再回天津,不会耽隔(搁)了你星期一上课的。……这两天春当真来了,丁香开了,杏花也在打苞儿,我的院后有很多的花木,清香满庭,你来了一定会喜欢……我有的是诚挚的性情与坦率的谈吐,也许不会令来看我的朋友失望的……[6]
此片段引述在张秀亚的《我与文学》[6]里,信写于1936年春天。那时张秀亚还是个中学生,早慧且富于文学才华,十四岁即涉足诗坛,十六岁就登上影响不小的《益世报》副刊和《国闻周报》副刊。张秀亚偶读凌叔华的小说集《花之寺》,激赏其“如同隔了春潮薄雾,看绰约花枝;又象是一株幽兰,淡香氤氲,使人在若醉若醒之间”[6]407。心仪其人,致信求教。凌叔华的这封回信亲切温暖,提携后进之情颇为感人。见面迟在夏天,张秀亚印象深刻:“她很会谈话,亲切、从容,使一个生客听了感到舒舒贴贴。在言语中,她并不自炫所学,掉弄书袋,但她的机智与才华,闪动于词句中,如同松间明月,流照出一片清辉。”[7]408凌叔华的当面鼓励,无疑给驰骋文学道路上的张秀亚加了一鞭。她更以笔名“陈蓝”在凌叔华编辑的《武汉日报》副刊“现代文艺”上频频亮相,不久她考入北平的辅仁大学,张秀亚身为学生,却行校刊《辅仁文苑》编政,约请凌叔华撰稿,发表了凌的《〈椰子集〉序》。共和国建立之时两人暌违伦敦和台北,张秀亚常思念凌叔华,写过多篇怀凌文章。陈西滢病故那年,凌叔华去台北,张秀亚闻讯伙同林海音、谢冰莹、琦君、王怡青去看望前辈,留下一帧难得的合影。
四、致陈美芳信(片段)
凌叔华父亲娶过好几房太太,子女十多人。她生母除一男孩夭折,余膝下四个全是女娃。凌叔华在父亲所有的子女中排行第十,同胞排行第三。两个姐姐不思上进,又早早嫁了出去,相处疏远。唯妹妹凌淑浩和她一起长大,最为亲密,收信人陈美芳便是淑浩女儿。叔华、淑浩性格悬殊,一个矜持内敛,一个外向豪爽,但成年之后两人渐行渐远,尤其对家事的认识发生过激烈冲突,致陈美芳信正是见证。1956年随淑浩定居美国的陈美芳,往英国跟从凌叔华学习国画。姨母和侄女自然会叙叙家常,但这竟触怒淑浩引来责难。于是凌叔华给回到母亲身边的陈美芳写信辩解:
昨天我正要写信给你,就接到了你妈妈的信。九个月以来,我给她写了不下五六封信,她一封也没有回。可现在她却用一种气势汹汹又粗暴无礼的语气给我写信。我当然很生气,但平静下来之后,我决定给你写信。或许我应该告诉你,她说了些什么,也希望你好好告诉我,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她这么生气和无礼。我相信你很了解我们,我也同情你的处境。我不会告诉你妈妈你说了她些什么。我很担心她的健康,如果她健康的话,她也不会忍心如此伤害我的感情。
下面是我从她的信中抄录的话。“至于写信,想到你对美芳说的那些关于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太祖母以及关于我的话,我根本就没有兴趣提笔。我简直难以想象,特别是母亲已经去世,不能够亲自辩解了。我们的太祖母不是西班牙人。你是听谁说的?我很爱妈妈,你说她,就是跟我作对。像你这样的上等人,没有必要为了自己的成功而贬低家人。美芳从伦敦回来后,变得那么困惑,我真后悔让她跟你学画。”
我不记得我曾经向你提到过我母亲的事,因为你从没见过她。我也没有谈过我们的太祖母,我是听父母说起过,说我们的太祖母有一头金黄色的鬈发,所以家里人叫她黄毛太。没有人把她当成外国人,而且即便她是西班牙人,头发也应该是黑色的。我们都知道,许多杰出的美国公民祖上都是欧洲人,他们也并不为自己的血统感到羞耻。所以我真不知道你妈妈为什么对我这么大惊小怪的。至于我母亲,我一点儿也不会因为她不是正室就觉得没脸见人。在东方,一个男人可以有好几个妻子,这是一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几千年来,这是名正言顺的。在中国,妾也是家里的一员,过去如果家里庶出的儿子中了状元,这个母亲就可以请求皇上御准,穿上特制的礼服,和原配夫人一样平起平坐……
接到你妈妈的信后,我无法相信她会说这样话。她将我和我对她的情分看得一文不值,我不相信她会这么无情。这辈子我没对她说过谎,也没从她那儿得到过什么好处。每年圣诞节,我都给她寄礼物,尽是挑好的、贵的买,因为我希望她从一个最亲的亲人那里得到礼物而感到快乐,而且,也是因为从小时候我就爱这个妹妹。如今,我很羞耻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做傻事,尤其是这九个月以来,我写信给她,寄礼物给她,她不仅不领情,相反,还写了一封粗鲁、无情的信来骂我。[8]
这桩家务事比起“八宝箱”纠纷愈加难断是非。凌叔华疑问姐妹俩反目“究竟是什么原因”,但这实属明知故问。矛盾原因在不久前出版的《古韵》[9],凌叔华以家事为题材写的这本自传,虚虚实实,多有小说笔法,却不肯承认它是小说体裁,以致大家都以为这本书是实实在在的家族史。《古韵》里的传主“十儿”,被虚构成母亲最小的女儿,而她明明有个妹妹即凌淑浩。特别是关于母亲身世的描述,最不得凌淑浩容忍。至于信里凌叔华说:“也没从她那儿得到过什么好处”,只能作气话来听,至少20世纪50年代淑浩帮助她在美国办了画展。而淑浩指责她“为了自己的成功而贬低家人”,则分明令她受了委屈。这对同胞姐妹至耄耋也未能尽释前嫌,十分孤寂的凌叔华依旧不接受淑浩让她移居美国予以照应的邀约。凌叔华临终,凌淑浩表示欲来中国,其实并无最后一别的诚意。凌叔华与丈夫、独女均不甚和谐,和“最亲的亲人”妹妹亦生分如此,事业成功的她尚不乏友情,而家庭、情感生活却太过失败,她后半生的孤寂十分显然。
陈美芳之女魏淑凌所著的《家国梦影:凌叔华与凌淑浩》写及,陈美芳没有收到此信,那么或许未曾付邮。是明白了即使辩解也无济于事,只能这么猜测。此信引用在《家国梦影:凌叔华与凌淑浩》中,魏淑凌录自凌叔华死后其女儿陈小滢收存的打字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