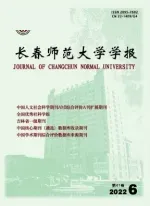从抄本到刻本的清整
——北宋国子监本《文选》研究之一
2012-08-15郭宝军
郭宝军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 475001)
从抄本到刻本的清整
——北宋国子监本《文选》研究之一
郭宝军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 475001)
以《文选集注》本中的李善注与北宋国子监本进行全面的对校,推测《文选》李善注从抄本到刻本清整的一般过程。监本编纂者首先从众多版本中选择一个注释比较规范、比较齐全的本子作为底本,是为清理;在此基础之上,参校李善所引原书,以及其他不同的注本,对底本的字形、讹误、衍文、夺文等诸方面进行更正,比较科段的不同、注释的详略,参校他本作个别订正,增加注释,是为整理。监本李善注对抄本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整,从而结束了抄本时代纷繁不一的传播样貌,给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李善注的定本,同时亦加剧了抄本的佚亡。
《文选集注》;国子监本《文选》;清整
在雕版印刷未被普遍运用于书籍传播之前,口耳相传与传抄是古籍最为通行的传播方式。因此,唐代《文选》抄本众多,有白文本,有李善注本、五臣注本,还有众多的他家注本,敦煌吐鲁番发现的《文选》诸种版本可证。①单就李善注本而言,有唐一代,数目颇夥。李济翁《资暇集》卷上《非五臣》条中记载了中晚唐传播流行的李善注的数种本子,“代传数本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复注者、有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之。其绝笔之本皆释音、训义、注解甚多。余家幸而有焉。尝将数本并校,不唯注之赡略有异,至于科段,互相不同,无似余家之该备者也”。[1]从《资暇集》的记载来看,李济翁至少看到或了解五种李善注本:初注本、复注本、三注本、四注本、绝笔本。这五种李善注是存在差异的:注释详略不同,注释分段也不一样,总体趋势是注释由简至繁,从单纯释事到附事见义。这种趋势也可以通过一则史料得到进一步证明,《新唐书·李邕传》云:“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选》,释事而忘意。书成以问邕,邕不敢对,善诘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试为我补益之。’邕附事见义,善以其不可夺,故两书并行。”[2]根据年龄推测,李邕在李善生前即补注《文选》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李邕后来是否增补父注是另外一回事),但此记载暗含着这样的史实:李善注本在当时至少存在两种区别比较大的本子:一种只是征引故实,一种则是征引之外,尚有释义,此推测也能得到现存的敦煌本李善注与集注本李善注的版本实物证据。敦煌本抄写于李善在世之时的永隆二年(681),离其上表时间的显庆三年(658)仅20余年时间,代表的可能是李善注的早期形态;《文选集注》虽然由于编纂体例的因素,可能会对李善注有所删节,但仍能看出比早期注本的简明单一增添了不少释义的成分。
唐代李善注抄本的众多也完全可以通过其传播方式、传播途径进一步推测。李善流放归来先在江都,后于汴、郑之间讲学,诸生来自四方。李善讲学内容中就有《文选》。诸生授业于其门,对李善《文选》的讲授记录因各自程度不同、关注不一,自然会有差异,会有删减、增添。李善针对不同的生员也会进行详略不同的传授,临时发挥与串讲大义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传播的方式造成的结果是李善注本的纷繁面貌,诸生的记录如果再经过进一步传抄,抄写者又根据自己的学习作增减,差别自然又会增添。这些记录或者再次传抄本,根源于李善,称之为李善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所以,从根本上讲,有多少次讲授就有多少种李善注,有多少个学生就有多少种李善注,有多少次抄写就有多少种李善注;况且,李善在讲学过程中还可能对自己早年的注本进行过有意识的修订。因此,当宋代雕版印刷应用在典籍传播中需要对李善注进行刊刻的时候,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对众多的抄本进行清理,编纂者找出他们认为比较翔实的而实际上不一定就完全代表李善注的本子作为底本,然后参校其他本子进行整合,从而确立写板的样本。
宋人在刊刻善注时首先须对其进行清整,从当时具体的校勘时间中亦约略得到反映。今知宋代刊印最早的《文选》注本是北宋国子监天圣年间的刊本,今尚存残卷。据《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三、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四、程俱《麟台故事》卷二中的记载②得知,对李善注《文选》的清整从景德四年八月至大中祥符二年十二月(1007-1009),共两年零四个月,覆校又花了约一年左右的时间,虽校勘不止《文选》,还有《文苑英华》一书,但《文苑英华》编纂于当朝,只是进行覆核与部分增减,虽卷帙庞大,其花费的时间甚或要远远少于李善注《文选》。时长的背后隐含着李善注抄本的复杂与对其进行清整的努力。
宋人对《文选》李善注进行清整所依据的某个底本已不可知。实际上,越是依据哪个本子,或者说,与哪个本子的差距越小,这个本子亡佚的可能性反而会越大,因为前者已经没有了存在之必要,抄写本自不如刊本适用。唐代李善注的抄本流传至今,是非常偶然的事情。敦煌本传承至今是因为敦煌的地处一隅并且进行了有意识的封藏,集注本的李善注流传至今首先是因为集注本本身的采录,其次是成于异邦之故。从抄本到刻本的这个演变过程,只能以这两种抄本作为参照,而集注本的李善注一般认为成于晚唐时期,③与刊本的时间距离更近,相对而言,所存卷帙又稍多,故为考察唐末至宋初的演变提供了参照依据。敦煌本所存的《西京赋》残卷部分,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监本全存,这虽然为二本的对校提供了可能,但是,敦煌本代表的是李善注的早期形态,从初唐至晚唐包括李善本人都对《文选》注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宋初的编纂者即使能够看到李善的早期注本,也不会以之为底本,当会选择一个中后期的比较翔实的本子。所以,如果考察从敦煌本的《西京赋》到监本《西京赋》的变化,对于研究宋代编纂者对抄本的清整似乎意义不大。基于此方面的考虑,本文主要以集注本李善注为考察对象,比较此本善注与监本的差异。必须说明的是,宋代监本的李善注的底本显然不是来自以上两种抄本,随便比校一下就会得出这种结论。但是,在目前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假定宋初刊本来自集注本的方式来进行考察,即通过集注本的参照,意欲从中寻找由抄本到刻本清整的一般过程。
为了推测从抄本到刻本的李善注被清整的一般过程,笔者对集注本李善注与监本进行了全面的对校,在此基础上,随机选取集注本所存最后一篇作为本文主要例证,即选择集注本卷一一六王仲宝《禇渊碑文》,从文首至“属值三季在辰,戚蕃内侮”部分(此后部分残缺,不便对校),与监本《文选》卷五十八相关部分进行对校,由此可以得出以下数点认识。
第一,监本底本不是来自集注本李善注的底本。在对校的《禇渊碑文》前半部分中,二本注释完全相同者不足5处,不同者足有53处。另有11处科段划分不同,即注释句群的划分不同,如“所以子产云亡宣尼泣其遗爱。隨武子既没,赵文怀其余风,於文简公见之矣”,监本《文选》分两部分进行注释,而集注本则合二为一出注。此种状况的存在,能够进一步印证明李济翁《资暇集》记载中所见诸本不仅注释详略不同、科段也不完全一样说法的正确性。
第二,通过对《褚渊碑文》前半部分的对校,可以作出如此推测:集注本的底本来自讲学的记录之本,监本的底本来自一个比较正规的本子。这种推测的证据是,集注本在句末大量增加“也”字,此残篇共有9例,“也”字在句末作用在于语气的收束,具有明显的口语特征。如“以父忧去職”句,监本注为:“萧子显《齐书》曰:渊父湛之,骠骑将军。”而集注本在注末增加“也矣”二字,似乎增加“也矣”两个虚字并无实际意义,可能是讲课时不自觉的语气词被学生记录所致。经过对集注本与监本所存相同部分进行了全部的比校后,发现在此篇中,集注本句尾增加“也”的现象尚不是很突出,其他有个别篇目几乎有句句增“也”字者;另一种可以推测的例证是,集注本此部分有重出现象,如“神茂初学,业隆弱冠”句下注、“金声玉振,寥亮於区寓”句下注,监本遵循“已见”例,而集注本重出。而且,集注本在标明已见的部分中,并未如监本惯用的“已见上文”,而是多作“已见××篇”,给出具体的篇目,这明显可以认为是讲学方便学生查阅而为。监本《文选》注在这方面的体例更加整齐,可能有编纂者的整理因素,不过更多的可能是底本方面的原因所致。
第三,从抄本到刻本进行清整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文字字形的整理,这在集注本与监本的比校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写本因手写的缘故,使用大量的俗字与饰笔,行书也很多,这不仅在集注本中表现明显,在敦煌本中亦如此。如含有“土”字的,大都加一“丶”作为饰笔,成为“圡”。“友”写作“犮”,“叔”字及含有“叔”的均写作“”,《干禄字书》中“犮”为俗体,“”为通行字,但正体当为“叔”。[3]监本的底本虽然是一个比较正规的本子,但作为抄本,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俗体字之类的现象,进行清整时必须对这些字形进行规范。
第四,与上条相联系,抄本不可避免地存在衍文、脱文、讹误等现象,整理者必须对这些内容进行规范,可能要覆检原书,甚至也会由此导致新的讹误。当然也有一些仍然承袭讹误的地方未能发现。如“有识留感,行路伤情”句下注,监本作“《说文》:雍门周说孟尝君曰:有识之士莫不为足下寒心酸鼻”,所引内容明显不是出自《说文》,而集注本作“说苑苑”,显为衍一“苑”字,当为《说苑》。后来的本子如尤刻本等又依据所引之内容改为《新序》,《新序》与《说苑》故事多有近似者。这种现象其实是善本逐渐变异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五,由以上的比校还发现,监本的注释内容远远多于集注本,即相对于集注本而言,监本有明显的增注现象。如“风仪与秋月齐明,音徽与春云等润”句下,监本注为:“音徽,即徽音也。《毛诗》曰:太姒嗣徽音。”而集注本无注。与集注本相比,监本此篇中明显增注的有15处,总共增加了205字,这还不包括共有的相同条目的注释个别字句的增加。这种现象的差异首先应该考虑底本的不同,监本的底本可能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本子,但同时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即监本的编纂者同时参校了不同的本子,对其底本所缺者有所增补,这两种情况应该是都存在的,这也是清整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
第六,集注本作为代表抄本时代流传至今的重要本子,可能保存了较多的注释旧貌。作为一个参校本,可以对其他版本有疑问或扞格不通之处有所补正,价值自不能轻视;但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其作为集注本的特征所造成的注释内容的缺省④,作为抄本所造成的诸多讹误等等也在削弱其价值。对集注本的价值不能作过高的估计。监本作为李善注的第一个刻本,校勘、覆校都比较严格,后来的本子都是在其基础之上而形成的,在《文选》版本史上,监本的价值更大一些。
由此,以集注本为参照,我们可以对李善注从抄本到刊本的清整过程作一归纳推测。监本编纂者首先从其能看到的众多版本中选择一个注释比较规范、比较齐全的本子作为底本,选择这个底本需要对不同的本子进行简单的比对然后才能确定,一是要尽量保存李善注,二是要尽量齐全,这就是清理的过程;在这个基础之上,参校李善所引原书,以及其他不同的注本,对底本的字形、讹误、衍文、夺文等诸方面进行更正,比较科段的不同划分、注释的详略不一,参校他本又作个别订正,增加一些注释,这就是整理的过程。经过清整的李善注又经过校勘,然后才写板、刊刻。监本李善注对抄本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整,从而结束了抄本时代纷繁不一的传播样貌,给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李善注的定本,同时亦加剧了抄本的亡佚过程。
[注 释]
①敦煌吐鲁番发现的《文选》诸种版本,可参阅饶宗颐《敦煌吐鲁番本文选》 (中华书局,2000年)、罗国威《敦煌本<文选>笺证》 (巴蜀书社,2000年)、《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等书。
②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三:(景德四年)八月,诏三馆、秘阁、直馆、校理分校《文苑英华》、李善《文选》,摹印颁行。《文苑英华》以前所编次未精,遂令文臣择古贤文章重加编录,删繁补阙,换易之,卷数如旧。又令工部侍郎张秉,给事中映,龙图阁待制戚伦、陈彭年校之。《李善文选》校勘毕,先令刻板,又命官覆勘。未几宫城火,二书皆尽。至天圣中,监三馆书籍刘崇超上言:“《李善文选》援引该赡,典故分明,欲集国子监官校定净本,送三馆雕印。”从之。天圣七年十一月板成。又命直讲黄鉴、公孙觉校对焉。中华书局,1957年,页2232。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四云:“景德四年八月丁巳,命直馆校理校勘《文苑英华》及《文选》,摹印颁行。祥符二年(1009年)十月已亥,命太常博士石待问校勘。十二月辛未,又命张秉、薛映、戚纶、陈彭年覆校。”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影印浙江书局光绪七年本,1987年,页1022。程俱著、张富祥校正《麟台故事校正》卷二云:“四年八月,选三馆、祕阁直馆、校理,校勘《文苑英华》、《李善文选》,摹印版行。”张氏校正云:“本书此条不书年号,竟似大中祥符四年事,误,应与上条互换位置;且所载过简,似传抄有脱漏。”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2000年,页285-286。
③目前对《文选集注》编纂成书的区域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成于中土,一种认为成于东邦,笔者持后一观点。《文选集注》成于东邦日本,但是,其采用的众家之本,如李善注、五臣注等代表的确是晚唐流行的状貌,故文中讲到《文选集注》本的李善注时,径视为晚唐李善注。
④一般认为,集注本是以李善注本为底本再增加他家之注而形成的,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李善注的全部注释,这种推测是正确的。但同时不应该忽视集注本的编纂特征,比如,在对现存监本与集注本相同篇目的全部比对中发现,监本有些存在音注的条目,在集注本中并不存在,而是存在于《音决》中。这种现象不应该视为监本的编纂者吸取了《音决》的条目,毕竟编纂者是在进行李善注的编纂,而是集注本的编纂者对与音注方面多依《音决》,李善注中与《音决》相同的部分,多删李注,存《音决》。所以集注本的李善注虽然相对《钞》以及《五臣注》要全面,但也不是最完整的。
[1]李匡乂.资暇集[M].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5.
[2]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3:5751.
[3]颜元孙.干禄字书[M].后知不足斋丛书本.
The Selection and Compilation from Transcript to the Carving Copy——AstudyonWen XuanCarved byDirectorate ofImperial Academyin the Northern SongDynasty
GUOBao-jun
(College of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enan University,Kaifeng475001,China)
Check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Wen Xuan Ji Zhuand the copy carved by Directorate of Imperial Academy,we can predict the common procedure of the selection and compiling ofWen Xuanfrom transcript to the carving copy.Firstly,the editors chose a more normative and complete copy from excessive copies,which was known as Selection.Secondly,referring other copies,the editors corrected mistakes and added comments,the process of which was called Compilation.Through the all-round checking,it ended the differences,produced a complete copy,and promoted the die ofthe transcripts.
Wen Xuan Ji Zhu;Wen Xuancarved byDirectorate ofImperial Academy;Selection and Compilation
I206.2
A
1008-178X(2012)01-0008-04
2011-11-1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1YJA751015)。
郭宝军(1970-),男,山东淄博人,河南大学文学院讲师,国学研究所兼职研究人员,博士,从事《文选》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