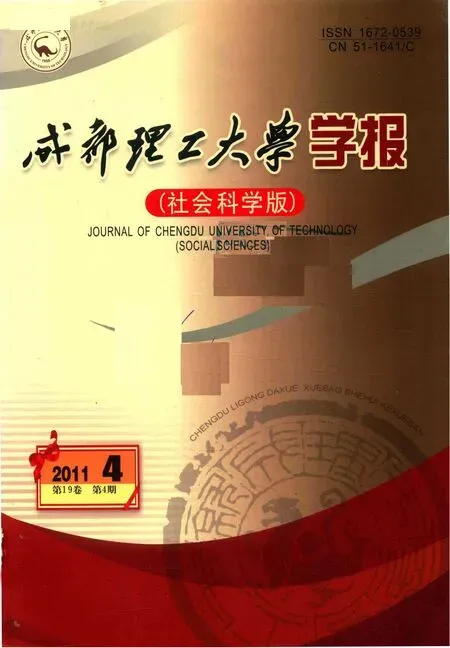打开一部判决制度之门
2011-03-31马德志
马德志
(上海交通大学 凯原法学院 ,上海 200240)
打开一部判决制度之门
马德志
(上海交通大学 凯原法学院 ,上海 200240)
一部判决,即法院对当事人主张可分的权利义务或实体请求之一部分做出的终局性判定,是特定诉讼情境下具有终结诉讼系属效力的终局判决的其中一类。作为一种裁判方式,一部判决体现了诉讼中当事人诉权与法院审判权的共同要求,有助于诉讼及时高效、从容稳健地顺利谢幕。然而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9条相关规定过于笼统、“含蓄”,令研究者因法条“犹抱琵琶半遮面”深觉“意犹未尽”,司法实务中亦难以准确适用。追求诉讼效益与程序正义的当代民事诉讼实务,期盼民事程序立法对一部判决裁判制度更具针对性的清晰规范。
一部判决;诉讼合并;裁判脱漏;中间判决;一部请求
一、一部终局判决内涵阐述
从诉讼理论上概括地讲,法院就系属中的事件之全部或一部以完结该审级的审理为目的所作出的裁判称为终局判决。而作为终局判决之一种,一部判决又称部分判决,是诉讼标的之一部(或数诉讼标的之一)达到可裁判之程度,法院以终结该部分诉讼在该审级之系属为目的的判决。[1]在民事诉讼中,如果当事人所提之诉讼请求已达到可以裁决的程度,法院通常应当不迟延地终结辩论并做出终局判决,而在争点繁杂、举证困难、标的合并的诉讼案件中,法院常常将当事人之一部诉求分离出来先行裁判,如此,可以力避诉讼延宕,明晰案件争点,使当事人之权益尽快通过确定终局判决获得救济。民事一部终局判决作为终局判决,其不同于法院在诉讼程序中对特定事项进行确认性裁决之中间判决,亦区别于受诉法院因疏漏而对当事人主张之诉讼请求的一部分于裁判中未予意思表示之裁判脱漏,迥异于受诉法院于裁判中对当事人为支持诉讼请求而提出的攻击防御方法部分未作判定之判断脱漏或称事实认定的脱漏。一部判决本质,即是将一个诉讼分解成若干后先行就特定部分做出与终局判决效力相同的部分判定。该部分判定一旦做出,已判决部分即不得再进行辩论。因此法院于一部判决做出前应明确释明,以保证程序之安定性与可预期性。同时,该部分判决亦独立于诉讼余部之判决。除不得发生判定结论相互抵牾之“矛盾自由”外,[2]二者既判力无涉。
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382条对一部终局判决适用情形规定为“诉讼标的之一部或以一诉主张之数项标的,其一达于可为裁决之程度者,法院得为一部之终局判决;本诉或反诉达于可为裁判之程度者亦同。”主要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例之一部判决亦主要适用于上述三种情形。此外,双方或一方当事人缺席审判时的终局判决也可以援用一部终局判决制度进行处理。[3]此可谓一部判决的第四种适用情形。虽然一部判决制度主要指向客观的诉讼标的部分的分离,但对于因主观的当事人所发生的诉讼分离亦可适用一部判决制度。如普通共同诉讼中可对部分共同诉讼人部分判决,其余共同诉讼人继续诉讼直至余部判决。
如上所述,一部判决制度通常在前述四种情形下适用。(1)但同时,一部判决亦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不能适用:(1)诉讼标的不可分,亦或关联紧密,分开裁判有矛盾判决之虞的。如本息给付之诉,不可就本金先行一部判决。(2)数形成权指向同一目的的本诉与反诉中,二者相互排斥,或其中之一为先决问题,一部判决会使诉讼余部丧失裁判机会。如夫妻离婚之诉中,一方又向对方提出离婚之反诉,必须为全部终局判决。须指出的是,若夫或妻主张数个离婚原因,而法院仅对其中部分离婚原因做出认定后做出驳回离婚请求判决,此应为判断脱漏,不属一部判决。(3)当事人合并的数个诉讼,依其性质不得或不宜为一部终局判决的情形。例如,必要共同诉讼,必须合并审理、合并辩论,并在裁判中对诉讼标的合一确定。(4)诉之客观合并场合,在预备合并与选择合并时,法院不可以做出一部判决[4];诉之单纯合并通常可为诉之部分裁判,惟单纯合并中各诉讼请求主要争点共通时(属于不允许辩论分离的情形)法院也不宜部分判决。[3]532
就一部判决而言,如性质上不当为一部判决,但法院做出一部终局判决时当如何处理呢?日本学者通说认为该判决为有瑕疵之判决,虽形式上为一部判决,其实质仍应认定为全部判决,法院不得对剩余部分补充判决,只得视为判决瑕疵以上诉方法救济。对于该瑕疵一部判决上诉,全部诉讼均移审而受上级法院管辖。
诉讼合并场合下的一部判决,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概括地讲,诉讼合并包括诉之主体合并与诉之客体合并。诉之主体合并包括普通共同诉讼与必要共同诉讼。如上所述,必要共同诉讼场合,法院必须合并审理合一裁判,不得一部判决。普通共同诉讼,共同诉讼人牵连性相对较弱,为可分之诉,即使合并审理,亦应对各共同诉讼人分开裁判,因此可为部分裁判。事实上,此处之部分裁判即将合并了的普通共同诉讼又分开,就部分共同诉讼人的案件作出的裁判。
诉之客体合并相对复杂,也是本部分论述之重点。诉之客体合并包括诉之单纯合并、预备合并、选择合并、重叠合并等。(2)单纯合并为独立诉讼请求的简单结合,此时由于各请求是相互独立的,法院在必要时可以分别进行审理,也可以分别做出判决。因此,该种合并允许一部判决。惟单纯合并中数诉讼请求主要争点相通时,分开辩论与分别裁判不但可能造成对同一争点诉讼资源的重复投入,并可能造成因新证据新事实的发现而产生矛盾判决并发动对先行一部判决的审判监督程序。因此,此种诉讼背景下宜对合并诉讼持续不延迟地审理直至全部终局判决而不宜一部判决。预备合并场合,同一诉讼程序中原告同时提出先位请求和后位请求。当法院认可先位请求时,后位请求即无需审判(后位请求作撤诉处理);当驳回先位请求时,法院即必须对后位请求予以审判。诉之预备合并不适合做一部判决。首先,法院认可先位请求并做出判决时,后位请求作为诉讼余部即告消失,此时先位判决即为全部判决自不可能为一部判决。在法院驳回先位请求时,是否可做驳回先位请求的一部判决呢?首先,由于先后位请求在诉讼进行及审理过程中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为实现判断统一不适宜进行一部裁判。其次,能做出部分判决的,则仅限于诉讼对可分的情形。而当驳回先位请求时,此时诉讼即时进入后位请求审理,二者并没有分开,一旦分开也不成其为诉之预备合并,即不再属于此处预备合并能否一部判决的问题。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如视驳回先位请求为一部判决,法院便立刻在本级法院系属下进入后位请求审理,而所谓先位请求的一部判决具独立既判力可对之直接上诉,此时当事人提起的一个案件最终系属两个审级,这将造成程序上之严重混乱。因此,预备合并中不能做出一部判决。诉之选择合并,即同一诉讼程序中原告提出数个给付不同的诉讼请求,要求法院选择其一做出裁判并合并数请求提起的诉讼 。在这一诉讼形态中,法院只要认可一个请求即无需审理其他请求而可视为原告胜诉,反之法院为排斥原告的请求,必须一一审理原告全部请求并全部驳回。可见选择合并中,一部判决并无制度空间。因为诉讼终结前个别诉讼请求的判决不具结论意义或终局意义,对个别请求的认定因其余请求仍系属原审级而无法取得既判力,亦无法上诉,因此选择合并中也是不存在一部判决的。诉之重叠合并是一个请求与当此请求被认可时才可能成立的其他请求合并的诉讼形态。例如,原告要求确认其与被告间未到期债权的确认之诉,经确认后又追加诉讼请求使诉讼变为将来给付之诉。诉之重叠合并可以在作为先决问题的请求审理完毕后作出一部判决,而使对下一个请求的审理进入余部诉讼。
二、基于关联制度的进一步探究
在民事裁判体系框架下,一部终局判决在表象或实务操作中常常与中间判决以及诉讼裁判脱漏发生重叠或龃龉。这主要因为一部判决与后二者事实上皆属对诉讼请求的部分认定。因而,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分析这三者的个性,从而进一步从外延上界定一部判决。
(一)一部终局判决与中间判决
探讨一部终局判决与中间判决,实质上不如说在探讨终局判决与中间判决。在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与我国台湾地区存在中间判决制度。中间判决是为整理正在审理中的案件,就终局判决的前提问题做出的认定结论。由于某些大陆法系国家的裁判制度与我国并非完全对位(如日本裁判形式中并不包括裁定),因而在我国的裁判理论内把这种诉讼过程中的中间认定结论称为“中间判决”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由于大陆法系这种中间裁判形式实质上属于结合我国判决与裁定两种裁判形式对诉讼前提性事项做出的“确认性裁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将中间判决改称为“中间裁决”是更加合理的。
一部判决作为终局判决的一种,与中间判决制度相比有几个显著特点。第一,一部判决包括给付、确认、形成判决等三类,而中间判决只是对诉讼前提性事项进行确认,不能有给付内容。第二,一部判决裁决事项与全部判决一致,而中间判决裁决范围则限定在特定范围内。①独立的攻击防御方法,如就某可分离的独立争点提出的证据的合法性的争议。②中间争议,如有关各诉讼要件存在与否、撤诉的效力如何、诉讼行为追补的有无、诉讼承继有无等争议等[3]458。③对请求原因及数额的争议。所谓请求原因,即指有关诉讼请求之权利关系存在与否的争议(该请求原因不同于作为诉讼标的识别标准的原因事实)。当诉讼认定请求原因存在时,即可接着进入对数额争议的审理。例如,在侵权损害赔偿诉讼中,请求原因即侵权是否存在在侵权事实中间确认后即可进入对侵权损害赔偿额的审理。第三,作为终局判决,一部判决具有既判力,而中间判决没有既判力和执行力,不能单独对之提起上诉,只能在终局判决做出后在对终局判决上诉时一并对中间判决主张不服[5]。
(二)一部终局判决与裁判脱漏
根据2007年10月28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款“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十二)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之规定,裁判脱漏属裁判瑕疵之一种,属于应判未判可申请再审救济的情况。具体地说,就是指法院对诉讼标的一部分于判决理由与主文中均未作判定。可见其与一部判决本质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前者为受诉法院有意识地对当事人所提的诉讼请求选择已达到终局判决程度之部分诉讼请求并进行狭义上的先行判决,而剩余诉讼请求则另待条件适宜时再做出判决,其目的在于明晰案件争点,确保当事人权利救济的时间效益,避免诉讼勉强合并审理而导致程序滞延紊乱。从民诉法理上讲,一部判决是受诉法院对当事人基于诉权而以起诉方式请求司法保护之取效性诉讼行为的部分回应,它明显地体现出了审判法律关系与争讼法律关系的交叉与牵制以及法院审判权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互动与平衡。民事判决脱漏则是受诉法院一方因主观疏漏误认为已对当事人所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做出结论性认定而事实上判决书主文、事实与理由相较当事人诉讼请求意思不完整而导致的裁判瑕疵,这是一种必须救济、纠正并要极力避免的不正常和不合法的状态。《民事诉讼法》对申请再审救济裁判脱漏认定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理。再审申请人之撤销利益基于确定终局裁判存在重大程序瑕疵、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显著错误或其他法定事由,即再审以生效确定裁判存在且再审申请人对确定判决既判力存在异议权为前提。而裁判脱漏情境下原判决对当事人该部分诉讼请求未做判定,再审客体根本不存在,遑论确定判决既判力的异议权。这种情况下的再审或上诉审即是就案件部分诉讼标的剥夺了当事人审级利益,则直接由上级法院做出裁判而缪使当事人受该裁判既判力拘束。在此,应当修法改正裁判脱漏时当事人的权利救济方式,同时参考德日等国家立法例,以补充判决方式补正脱漏裁判瑕疵,维护民事诉讼裁判制度、级别管辖制度的系统性、兼容性与和谐性。
上文从概念上明确区分了一部终局判决与裁判脱漏,并阐述了裁判脱漏时判决追补的正当性。但事实上是否认裁判有脱漏,与原告是否可以一部请求或法院是否可一部判决密切关联。补充判决本质上就是一部判决,因此凡裁判脱漏的部分,性质上均属可为一部判决者(此时方可补充判决)。反之脱漏部分,性质上不得为一部判决时,无法为补充判决,此时亦不得认属裁判脱漏。[1]119如法院对必须为全部终局判决之必要共同诉讼对部分共同诉讼人误为一部判决,此时剩余必要共同诉讼人,裁判未做认定,但因为这属不可为一部判决情形,因此判决脱漏未对部分共同诉讼人做出裁判却不属裁判脱漏,不得补充裁判,只得上诉救济。
三、一部判决与一部请求
所谓一部请求,通常仅就量之一部请求而言,[6]是在以给付数量可分的金钱或其他可替代物为内容的债权的诉讼中,债权人分割其中一部分而单独提出诉讼请求。一部请求无疑是民事诉讼理论中一个相对复杂的领域。它涉及到该诉讼标的是否特定;涉及到既判力客观范围仅及分割一部债权抑或包括余额债权之全额债权;涉及到既判力客观范围是否因原告胜诉败诉而差异;涉及到时效中断是否仅及一部请求;涉及到诉之变更与撤诉制度。对于上述许多问题,至今民事诉讼理论未有定论(3)。本文将尝试结合一部请求对一部判决浅作分析。
在诉讼系属中增减请求之数额,肯定地说,原则上发生的是诉的追加或诉的撤回,而不是诉的声明之扩张与减缩。[7]诉的声明之扩张与减缩,必须以诉讼标的之法律关系不因此而生变更或追加为前提。因此,法院就此分割的一部请求诉讼,得分割而为一部判决。反之,如采否定说,即否定债权之分割请求,原告之分割请求,或被视为原告划定给付判决之最高限额,或被视为原告抛弃余额部分请求,其诉讼标的仍被视为包括余额请求之全部债权,判决既判力及于全部债权,如在诉讼系属中增减请求之金额,只发生诉的声明之扩张与减缩,而不发生诉之追加或撤回问题。[8]就一部请求判决即及的全部债权,性质上不得为一部判决。例如,原告请求损害赔偿十万元而提起诉讼,法院行使阐明权告知部分法律关系性质或民事行为效力认识有误等,原告主动请求就胜诉希望较大的8万元部分做出判决,在实施一部请求肯定说的国家,原告上述诉讼行为是被支持的,法院就该8万元部分做出一部请求“部分判决”后,剩下2万元诉讼阶段本质上可视为原告撤诉后再起诉两个案件的合并审理,该部分请求的裁判即成了因原告一部请求而形成的与前一个一部判决相独立的另一个部分判决。如采否定说,无论是因证据原因,或法院行使阐明权,当事人提出一部请求,则余部请求2万元即视为原告放弃或处分私权利将10万元债权划定实际给付最高额8万元,8万元给付请求判决不是一部判决,而是全部终局判决。
法院在特定情形下有权做出一部判决,但当事人是否有请求法院先行一部判决的适时裁判请求权?后文将就这个问题结合我国民事诉讼法与司法实践专门展开论述。这里要讨论的是所谓适时裁判请求权本质上就是“一部请求权”的问题。一部请求制度并非仅局限于关注后诉余部请求是否受前诉“一部请求”既判力拘束。在同一个诉讼内,当事人请求法院就全部诉讼请求部分先行判决,剩余诉讼请求继续审理再做出不受前面部分判决既判力拘束的另外部分判决,这里的部分裁判请求权实质即一部请求权,这个一部请求权不发生于前后两诉间,而是于一个诉讼内两个阶段间。民事诉讼法理相互贯通,当事人之适时裁判请求权与一部请求诉讼既判力客观范围辅车相将,表里相依。诉讼系属中变更可分诉讼请求为一部请求,所得出的相应判决即成为一部判决,而后对案件的余部请求继续审理。这一制度在我国具急迫性与现实性。因为除大陆法系国家诸如因伤害后遗症所致后发损害赔偿等情形外,更重要的是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被告因资信低下欠缺履行能力而致被迫于诉讼过程中分割全部诉讼请求。正是由于部分请求于本土出现这一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在一部请求问题上态度明显有所变化。(4)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9条第2款也承认了部分请求。它规定:“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需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一部请求制度在本土的新发展无疑最终使诉讼中分割诉讼请求与因此适时裁判一部判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地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中。
四、本土一部终局判决制度的构筑与完善
我国《民事诉讼法》13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这是目前司法实践中法院做出部分判决唯一的规范标准与法律依据。
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中,法院对当事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中已发生的事实清楚的部分先判决,对尚不能确定的或当事人于诉讼请求中未提及的部分,如后期的治疗康复费、长期护理费、被赡养人生活费等需等待原告症状显现、治疗终结后再作认定,这是目前部分判决司法实践中相对比较常见的领域。但由于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实践中存在的如部分判决范围的界定、部分判决的上诉、部分判决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剩余部分程序上应如何处理、整个案件诉讼费的分担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含糊不清,莫衷一是,最终导致法院回避部分判决而做出全部终局判决,纵使部分诉讼可为一部裁判亦鲜有此举。
立法与司法对一部判决的漠视与回避,说明其制度价值在我国并未被准确认知。民事纠纷纷繁复杂,千头万绪,单靠全部终局判决包打五湖四海最终将会折戟沉沙。立法者或司法者更应考虑的是(作为正义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平等原则的另一面,即不同事物应当不同对待,[9]而一部判决制度即是因应特殊的诉讼情境的特殊处理。概括地说,一部判决制度最核心的制度效用在于其对诉讼效益的巨大助益。现代民事诉讼追求严格的“程序正义”,为此需当事人与国家投入大量时间与财力、物力、精力,这于诉讼各方主体而言均是资源的巨大消耗。在一部终局判决制度下,当事人在辩论程序终结后,对部分诉讼标的已无争议,法院便可就该部分及时做出一部判决,使该部分诉讼与审级脱离,使通过庭审已经明晰的案件事实与法律关系尽快得到认定,使当事人的权利及时得到救济。分开来谈,对国家与法院而言,首先通过一部判决使案件得到整理与梳理,明晰案件剩余争点,为法院下一阶段审理做好准备;其次要避免对已经确定的部分诉讼审判力量的重复投入,尽快做出判决结论,就已做出判决的诉讼标的而言,这无疑可以缩短诉讼周期,避免诉讼拖延;再次,通过先行做出的一部判决,部分缓和当事人双方的犹豫、怀疑和对抗,进一步提高法院的可信度与公信力,迅速树立法律的尊严,从而实现诉讼的伦理效益;最后则是在集团诉讼或群体诉讼案件中,由于案件案情复杂、牵涉多方利害关系、对抗尖锐,容易升级演变而成群体事件,法院常常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与社会压力。先行部分判决可以使这种巨大的压力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使紧张危急的气氛得以缓解,从而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对于当事人而言,一部判决价值意义更加不言而喻,一部判决使当事人间进入诉讼不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部分提前确定,权利人的权利提早得以救济或实现。事实上,一部判决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财产保全或先予执行制度的价值功用,却不存在前两者因非终局判决而需财产担保甚至执行回转的不稳定状态,这对整个民事诉讼制度体系大有裨益。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一部终局判决的规定,不仅概念内涵模糊,而且对做出一部终局判决的前提要件、程序细则以及剩余部分的处理均未明确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在对一部判决制度价值进行分析后,我们即应考虑如何具体贯彻这一立场,即从程序技术方面构筑本土一部判决制度。
(一)严格明确适用要件
作为成文法国家,法条规范之构成性规则不清晰不明确,则法官适法即可能狐疑不决,畏首畏尾,且判决结论亦名不正言不顺。斟酌《民事诉讼法》139条,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然而如能一部判决,尚需虑及诉讼成本、时效中断范围、案件部分诉讼标的已辩论终结且法律依据充分、本余部诉讼判决不会相互矛盾、前后既判力无涉、预期审级不致纠扰等问题。诸多因素决定一部判决适用条件尚需细化,诸多配套制度亦需落实。
(二)赋予当事人一部裁判请求权
长期以来,我国民事诉讼是一种政策实施型的程序,在程序终结问题上奉行程序的终结应当由官方(或公权力)来加以控制的理念,[10]因而法院有权依职权而为部分判决,这点勿庸赘述。但当事人是否拥有请求法院做出一部终局判决的权利,即当事人是否拥有要求法院一部终局判决的适时裁判请求权?笔者认为,应当赋予当事人要求法院一部终局判决的适时裁判请求权。
不断追求诉讼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是现代民事诉讼一个重要的价值目标。完善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制度”有利于消除我国诉讼框架内的“权力本位”观念,是我国建立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当事人有权按照处分原则的要求自由地确定请求司法保护的范围。赋予当事人请求部分判决的适时裁判请求权,不仅与民事诉讼处分原则一脉相承,而且有利于讼争法律关系与审判法律关系的衔接,有利于当事人诉讼权利与法院审判权的平衡,最终在诉讼框架下以制度性、技术性的方式扩张当事人诉讼权利,改变民事诉讼当事人客体化的现状,弱化民事诉讼的强职权主义色彩。
当然,人民法院有权根据诉讼的实际情形对当事人之部分判决请求做出决定。当可能显著增加诉讼成本、违反级别管辖并易致矛盾裁判或全部裁判明显更佳时,人民法院有权驳回当事人的部分裁判请求。
(三)一部终局判决前法院的释明义务
一部终局判决作为终局判决,意味着该部分诉讼脱离该审级系属,具有独立既判力,一旦做出,当事人即不可再就该部分诉讼进行辩论或攻击防御。因此在做出一部终局判决之前,该诉讼必须已经过开庭审理,且当事人均已经过充分言辞辩论。法院认为该部分诉讼已达到可以裁判的程度时,应向当事人明确告知说明,特别是部分判决的法律后果及其相关救济方式,否则即为违反程序公正。
(四)诉讼余部的处理
一部判决做出后,余部诉讼应按正常程序继续不迟延地推进,当事人仍有权行使相关诉讼权利,包括和解、申请调解等。惟在程序上一部判决书需明示此为部分判决,剩余诉讼留待日后处理。相应剩余诉讼判决亦须明确部分诉讼标的已先行裁判,界定本部分剩余判决拘束的诉讼标的范围,对先行判决已予裁判之事实主张、证据推理、法律依据可以简化处理。对诉讼费用、上诉期间等问题,应完全独立于先行做出的部分判决于剩余部分判决书中清晰表述。
五、结语
归结而言,立足本土之完善的判决制度需要重新审视一部判决理论。在鉴别、认同、调适、整合基础上,我们应当以独特的中国视角采纳、吸收、摄取、同化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一部判决理论,通过立法对一部判决制度做出统一、明确、细化、刚性的规定,进一步完善现行诉讼裁判制度。
注释:
(1)除上述一般适用情形外,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规定有必须适用一部判决之两种情形,即第24条以一诉请求计算及被告因该法律关系所应为之给付者,得于被告为计算之报告前,保留关于给付范围之声明:第384条当事人言词辩论时为诉讼标的之舍弃或认诺者,应本于其舍弃或认诺为该当事人败诉之判决。
(2)[日]中村英郎著,陈刚、林剑锋、郭美松译,常怡审校,法律出版社,第124页。另外部分学者认为除上述种类外还包括诉的竞合合并。事实上竞合合并是旧诉讼标的理论支持者为了处理请求权或请求原因竞合而形成的一个概念,在新诉讼标的理论下,事实上只存在一个请求,而被竞合的各个请求权及形成原因,不过是使请求具备理由的事由,因此无需承认诉之竞合合并或将其并入诉之选择合并。
(3)是否承认一部请求诉讼,概括地可分为肯定说,否定说。肯定说又有通说与少数说之分。多数派的肯定说主张不分明示一部请求与默示一部请求,均将一部请求诉讼既判力限定于改一部请求,而不涉及剩余部分请求。参考伊东乾[一部请求]民商事杂志48卷5号765页以下,木川统一郎[一部请求〤モ]民事诉讼政策序说182页以下,石川明[请求异议诉と个别的执行の排除]法学研究35卷4号177页以下等。少数说仅承认明示一部请求诉讼,如为默示一部请求,不得于判决确定后再诉求剩余部分。参考菊井维大[民事诉讼法下]391页。少数说现为日本最高裁判所所采,参考最判昭和三四年二月二零日民集一三卷二号二零三页、最判昭和三七年八月一十日民集一六卷八号一七二十页。否定说亦可分为三类,第一种观点否认一部请求可诉性,但在具体处理上,要区分原告部分请求胜诉还是败诉,如果胜诉,则余额请求可以进行诉讼。参考兼子一《民事诉讼法体系》,370页。第二种观点限定否定说主张由于某些法律上的障碍,如履行期不同、有担保权之设定、条件之存否等而允许将债权分开进行一部请求。参考冈伸浩,《民事诉讼法の基础》171页。最后一种观点即所谓全面否定说即部分情形全面否定部分请求再诉的观点。高桥宏志,《重点民事诉讼法讲义》上,90页以下。我国许多民事诉讼法学者亦支持此说,如张卫平:《既判力的客观范围》,载樊崇义主编:《诉讼法学研究》2003版,第157页。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此并未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出台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第6条规定,当事人在侵权诉讼中没有提出赔偿精神损害的诉讼请求,诉讼终结后又基于同一侵权事实,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法院之司法解释似乎属于上述“否定论”中的第三种观点。
(4)(2008)民二终字第79号判决书。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与新疆华电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华电红雁池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华电苇湖梁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即默许了这种一部请求。该案中原告根据借款合同要求偿还本金及部分利息,并交纳了相应的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称对其未缴纳案件受理费部分的利息1700181元请求部分,不予受理,但案件可以另案起诉,即准许原告单就利息债权进行分割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在二审中默认了一审法院的做法。
[1]范光群.民事程序法制问题及发展[M].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117.
[2][德]奥特马·尧厄尼希.民事诉讼法 [M].周翠,译.第27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11.
[3][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M].林剑锋,译.第三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456.
[4]邱联恭.民事诉讼法讲义(二)[Z].许崇宦,整理.2009笔记版:230.
[5][日]兼子一,竹下守夫,等.条解民事诉讼法[M].弘文堂 ,1986 :494-504.
[6]李木贵.民事诉讼法(第四篇)[Z].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07:48.
[7]骆永家.既判力之研究 [M].第五版.台北:三民书局,1981:157-158.
[8]陈宗荣.一部请求之判决与既判力客观范围[J].台湾国立大学法学论从,1976,6(1):213-228.
[9][德]考夫曼.法律哲学[M].刘幸义,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228.
[10]王福华.正当化撤诉[J].法律科学,2006,(2):108.
Open the Door to A Sentencing Regime
MA De-zhi
(Kaiyuan Law School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China)
Civil p rocedural part-judgment,is just the court’s final ruling about a divisibl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 r part of the entity requesting from the Parties,One type of the final decision under specific litigation circumstance which could end the action dependence effect.As a way of ruling,part-judgment reflects the joint requirements from the parties’rightsof action and the court’s jurisdiction,takes a bow fo r the p roceeding duly and unhurriedly.But the relevant p rovisions of Civil Procedure Law A rticle 139 are indeedly too general and implicit,so the reseachers usually feel vague and obscure because of the defective clause which can hardly be applied in judicial practice.Seeking law suit efficiency and p rocedural justice,Contempo rary Civil Practice is in dire need of nichetargeting and lucid criterion on part-judgment system.
a decision;combined action;referee lacuna;Interlocutory;a request
D915.2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672-0539(2011)04-066-06
2010-11-11
马德志(1986-),男,山东临沂人,上海交通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事诉讼法。
刘玉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