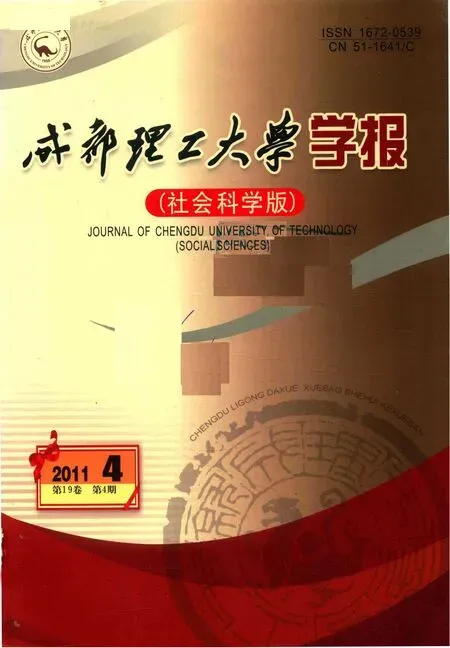从责任的悬搁到责任的显身——西方责任观念叙事
2011-03-31程关松张知干
程关松,张知干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南昌 330077)
从责任的悬搁到责任的显身
——西方责任观念叙事
程关松,张知干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南昌 330077)
文艺复兴以前,立基于人的社会性或社会中的人,西方建构了以责任为中心的治理体系。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和新教的传播,自然权利学说建构了以权利为中心的法治体系,并成为西方社会生活的合法性根基。当西方遭遇现代性危机,社群主义在反思个人主义的权利体系时表达了提升个人与社会责任的强烈诉求。追问西方责任观念演变的历史境遇和甄别西方责任观的内涵及其实现路径就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演变;负责任性
一、西方责任观念的演进
(一)责任的语义学
在西方传统中,责任一般和义务相关联,但从先后顺序上考察,责任概念出现要比义务概念早得多。
一般认为,与权利对应的义务概念的提出始于霍布斯。[1]137义务概念的这一起源表明,自霍布斯开始西方才关注到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对应性与平衡关系在社会建制中的重要价值。施特劳斯认为,“自由主义的创立者乃是霍布斯”[2]185。这一论断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在霍布斯以前的格劳秀斯和普芬道夫所开创的古典自然法,其传统本质上是主张自然义务本体论的,自然权利居于修辞学地位。
尽管责任概念在中西方出现得很早,但至今没有一个能够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普适概念。在汉语体系中,责任有三个相互联系的词义:(1)分内应做的事,(2)特定的人对特定事项的发生、发展、变化及其成果负有积极的助长义务,(3)因没有做好份内的事情或者没有履行助长义务而应承担的不利后果或者强制性的义务。[1]167《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认为,最常用的道义和法律责任是指人们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一个人本可以采取相应的行动却没有采取,那他就是有责任的,他因此就会受到别人的责备、抑制或者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3]701中外文化对于责任的理解大致是相当的。
(二)社会责任论
在可考的古希腊文献中,亚里士多德没有明确提出责任概念,关于责任的内涵可能隐含在他讨论法律上的公正、不公正与伦理上的公道之关系中。[4]第5卷西塞罗可能是第一位对责任进行细致研究的思想家。他认为,“任何讨论责任的文章都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讨论至善论,另一部分是讨论可以全方位地制约日常生活的那些实际规则。”[5]93西塞罗将他的儿子送入雅典跟随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老师学习哲学,他也自称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信徒。根据西塞罗的记载,雅典的亚里士多德学派和斯多葛学派都讨论了责任问题。亚里士多德学派讨论的是责任的至善论部分,也就是责任的应然部分;斯多葛学派讨论的是责任的规范化问题,也就是责任的实然部分。但他认为,责任观念主要来源于斯多葛学派。[5]89-93在西塞罗看来,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责任论和斯多葛学派的责任论都存在局限性,有将其结合起来讨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认为:“如果他们留给了我们任何对于事物的选择权,以便有可能找到一种发现什么是责任的方法,那么,我们还是有权讨论责任的。所以,这一次我在这一研究上主要是遵从斯多葛学派的教诲,但我并不是作为一个翻译,而是按照我的习惯,根据我自己的选择和判断,以某种适合于我的目的的尺度和方式,从这些原始资料中汲取有用的东西。”[5]92在责任问题的哲学贡献上,西塞罗应该是将道德责任论与规范责任论结合起来的第一位哲学家。
近代自然法学派的创立者格劳秀斯,则继承了西塞罗关于责任的社会性维度。他认为:“人类天生就倾向于过一种社会性的生活,而社会是不可能自发存在并延续的,除非其他所有成员都为相互克制和友善所保护。”[6]29正是在社会性维度上,格劳秀斯认为,“自然法是正当理性的命令,它指示任何与合乎本性的理性相一致的行为就是道义上的公正的行为,反之就是道义上罪恶的行为。”[6]32如果说格劳秀斯关于自然法的定义具有某种神学或者是道义色彩的话,那么,格劳秀斯关于自然法的证明则更一步揭示了他关于自然法的社会性的主张。[6]36近代自然法实际上是对启蒙时期主要立场的法学表达。
近代自然法学派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家普芬道夫,则干脆建立了一个人和公民的自然法义务体系。他认为:“社会性(sociality,socialitias)法律——教导一个人如何使自己成为人类社会一个有用成员的法律——就是自然法。所以很明显,最基本的自然法是:每一个人都应尽其所能地培养和保存社会性。想要达到目的,就必须要重视达到目的所必不可少的手段。因此,所有必然和通常会有助于社会性的事项都是自然法所允许的,所有破坏和违反社会性的事项都是自然法所禁止的。其余的法令都归入这一基本法则。它们是不证自明的,这一点为人所固有的天赋悟性(natural light)所揭示。”[7]61普芬道夫明确提出了天赋义务说,它是文艺复兴后期霍布斯和洛克提出的自然权利学说的反论。
(三)社会责任论的颠转
西方责任传统的遮蔽始于霍布斯提出的自然权利学说,但成就自然权利学说则要归功于洛克,他的学说是对近代自然法学说天赋义务论的逻辑倒置。自然权利由霍布斯率先提出,被洛克所继承和改造。霍布斯建立了近代规范主义的权力政治学,而洛克建立了现代规范主义的自然权利学说。洛克宪政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自然权利学说、自然法学说、有限政府和分权制衡学说几个部分。但是,自然权利学说是其他所有理论的基础。洛克是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法治理论中最早从规范主义的本体论角度对自然权利进行系统论证的思想家。[8]第2章自然法学派最重要的成就是自然权利学说。彼得·斯坦和约翰·香德认为,“在自然权利理论中求助于人类本性,这样做之所以十分重要,是因为它具有消极的和积极的两方面特点。‘为反抗权威而求助于人类本性,使权威失去了神秘色彩,为反抗制度而求助于人类本性,却使制度的寿命更加长久’。另一方面,‘对自然权利的宣称,不仅意味着对习惯或制度的权威的反抗,而且意味着将这些权威置于每一个个人本身的判断之下的呼吁。’”[9]21自然权利学说的诞生满足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双重需要。正如阿尔都塞所言:“从17世纪开始,资产阶级整合出了一套令人敬畏的政治哲学,自然法哲学……建立这套哲学的基础,是那些源于法律意识形态,源于个人作为主体的权利概念。这套哲学试图从法律意识形态赋予人类主体的那些属性(自由、平等、所有权)出发,在理论上推论出实在法和政治状态的存在。”[10]112从此,权利话语遮蔽了责任话语,法学以权利话语为基础开启了现代法治文明的元叙事,责任话语成为权利话语体系的修辞学。
(四)社会责任论的回归
对西方法治文明权利话语的元叙事产生焦虑,不是始于社群主义。早在1943年薇依就认为,“义务的概念优先于权利的概念,后者从属于它也相关于它。一项权利并不因其自身而有效,而是因它所对应的义务;一项权利的有效实现并不缘于某人对它的拥有,而是出于其他的一些人,他们承认在某些事情上对此人有义务。当义务被确认时,义务就有效。”[11]1在薇依看来,权利哲学宰制的西方现代文明导致人类全面的拔根状态,人的灵魂的需要被彻底抽空,必须在人类中重新注入责任才能招魂。她认为,“首创性和责任,成为有用乃至不可或缺之人的感觉,是人类灵魂必不可少的需要。”[11]11从薇依的责任宣言所论及的立场、观点、内容和论证方法来看,它应是当代社群主义者的先声。
二、社群主义的责任论
社群主义的核心话语是提升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和社会责任。[12]6它反对权利本位论克减人的责任,重申义务的必要性;反对间接民主对公民参与的排挤,主张公民参与的必要性;反对建立在多数人民主基础上的量的国家,主张建立在共同善基础上的质的国家。
责任的论证逻辑有道义责任论、社会责任论、规范责任论。[1]169社群主义责任论的论证逻辑主要是以社会责任论为基础展开的,它对康德式的道义责任论总体上持积极的批判态度,对规范责任论持极为持谨慎的态度。
社群主义动用了一切反对和抵制自由主义的学术资源对自由主义进行了全面围剿。桑德尔自己宣称:“我们可以在多种名目下描述我们的自我理解的这些构成性特征的一种普遍解释:一种人格理论,一种自我观念,一种道德知识论,一种人性论,一种道德主体理论,一种哲学人类学。”[13]62社群主义对责任的论证如同他们对社群的定义一样错综复杂、飘忽不定,每一个社群主义者都有众多面孔。
莱斯诺夫认为,许多人认为麦金太尔“是当代鼓吹社群主义政治哲学的一个领军人物。麦金太尔确实是个特例,他是个在一生中表现出许多极端相反的立场变化的理论家——从天主教到马克思主义,到亚里士多德主义,再到托马斯主义(就我所知,还有许多我没有提到的阶段),因此对他很难严肃对待,也很难对他的思想做出首尾一贯的说明。在所有这些朝秦暮楚的表现中确实存在着一条主线,即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仇恨。”[14]7泰勒的思想主要采用了哲学人类学的方法。但是,他并未完全否认康德人性尊严的意义,只是凸显了人性尊严的道德维度,同时,他与公民共和主义具有很密切的亲和性。当然,他也在公民共和主义的交往理性中植入了道德基础。泰勒在对自由主义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对自由主义的基本观念进行了充分吸收,并将其理解的道德根基植入其中。[15]第1章沃尔泽被德沃金认为是与自由主义能够沟通的唯一的社群主义者。沃尔泽并不追求对复合平等的历史和道德追问,也不进行抽象的哲学论证。他所维护的是多元主义的立场和平等观念。从多元性的维护角度出发,他赞同“宪政、有限政府、一个致力于捍卫所有社会物品的自治并能够捍卫所有社会物品的自治的——而并没有对其中的任何一种做出充分论证——有能力的参与性的公民整体。”[16]3-4在捍卫多元性方面,沃尔泽分享了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只是自由主义的消极个人在政治领域被置换成了合格的、负特定社群责任的、积极参与的公民。在平等问题上,沃尔泽自称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他认为:“复合平等也必须从所有领域内部来捍卫:通过工会抵制资本的暴政;通过教师坚持他们学校的独立性,拒绝服务于狭义的政治(或宗教)目的;通过医疗保健专业人士寻找帮助他们最脆弱的病人的途径;通过福利制度避免使人们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或者免除被市场原则左右的命运。尽管如此,国家仍然是所有这些情况中人们最后诉诸的机构,无论何时,只要各领域内部的努力失败了,国家就介入其中,而且经常如此。处于这个原因,尽管我更喜欢一个高度多元化和非中央集权的政治,即《正义诸领域》所要求的,我也仍然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对强权国家和对民主公民资格的强烈理解有着坚定的立场。”[16]中文版序言4沃尔泽甚至将这种对国家型构秩序的重要性推广到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服务机构之中。沃尔泽的论证体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他的理想层次,他接受了自由主义关于最小国家和个人、社群自治的观念。他认为,这些价值是捍卫他所坚持的复合平等所必需的。二是他的现实主义立场。他认为,秩序对于捍卫复合平等观念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承认国家在供给秩序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
社群主义除了对自由主义持或弱或强的批判态度外,在他们关于责任的建构中,他们是否共享一些基本命题呢?
塞尔兹尼克认为,社群主义的责任主题化依赖对社会依附性的承认和由此所确认的社会连带关系。[12]17-20社会依附性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它来源于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是政治的动物”这一论断,这一论断经阿奎那的传播成为“人是社会的动物”这一命题。(1)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自此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元问题。
在自然权利学说主导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以后,对这一意识形态提出严峻挑战的是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和迪尔凯姆的社会连带主义。在规范领域,狄骥是连带主义法学的创立者。狄骥认为,“社会连带性”这个词与“社会相互关联性”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人们相互有连带关系,即他们有共同的需要,只能共同地加以满足,他们有不同的才能和需要,只有通过相互服务才能使自己得到满足。因此,如果人们想要生存,就必须遵循连带关系的社会法则。许多赞成社会连带主义的思想家都认为,社会连带关系是一个道德概念而不是一个事实概念,但狄骥认为社会连带关系是一个事实。他认为,连带关系不是一个行为规则,它是一个事实,一切人类的基本事实。[17]224-226他拒绝接受社会连带关系是一个道德概念。他认为,“人在社会中生存,他永远并只能和其他同类一起在社会中生存;人类是一个原始的自然实体,绝不是人类意愿的产物,因而所有人无论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人类群体的一部分……随着时代不同,人总是或多或少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即人对人类群体的依赖与人的社会性。这并不是一个先验的断言,而是一个毋庸置疑的观察结果。”[18]7狄骥坚持社会连带关系的实在论立场。
社群主义者对社会连带关系的承认是共同的。桑德尔赞成社会学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也赞同社会学给自由主义贴上的道义论标签。[13]14-16社群主义者在共同承认社会连带关系基本命题的过程中对其利用存在很大差异。
总之,社群主义在共享社会连带关系和支持其社会责任论过程中侧重于三种论证方式:第一种是有关社群对历史的依附性的方法,如麦金太尔和泰勒;第二种是有关社群对社会结构的依附性的方法,如桑德尔;第三种是有关社群内部的依赖关系的方法,如沃尔泽。
三、责任的实现路径
(一)美德的实现路径
社群主义者认为,仅有法律责任是不够的,必须凸显美德意义才能从根本上矫治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所导致的现代性危机。
社群主义突出忠诚、友谊、公道等美德的价值,倡导现代社会做一个负责任的社群成员和负责任的积极公民。但是,令人不解的是,除了沃尔泽以外,社群主义者几乎都没有专门讨论美德与教育的关系问题。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麦金太尔致力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提炼出他所自称之为的美德谱系。在他的视域中,如果承认他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他所担当的角色的确是一个导师的角色——他试图按照自己的理解教育所有其他成员符合他的美德要求。实际上,他充当了一个导师的角色。这种角色类似于我国儒家圣人的地位、基督教教父的角色。他在政治哲学中必然是精英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只承担美德供应商的职责,既不批发美德,也不零售美德。
泰勒致力于从哲学人类学中找到个人与社会相互承认过程中自我教育结果所形成的形象,这类似于杜威所说的“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他似乎没考虑道德养成中的慎独与专门教育之间的功能派分问题。在他的视域中,道德只是在相互交往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泰勒更多地是从学生角度考察自我的根源来源于社会认同这一论点的。所以,他特别强调日常生活的意义。在道德领域,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出他的杜威来源。泰勒之所以以学生的身份出现重述自我的根源——就像一个学生向老师汇报一样仔细讲述自己的道德成长经历,乃是由于他对道德主义背后潜藏的危险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泰勒对美德的伦理学保持敏感的警觉,这也拉开了他与麦金太尔之间的距离。他认为,“最高的精神理想和渴望,也有给人类加上最沉重负担的危险。人类历史的伟大精神视野也是有毒的圣环,是无数悲惨甚至暴行的原因。”[15]815他不仅对美德的伦理学保持高度的警觉,而且对于“价值无涉”命题也极其敏感。他认为,“无价值的危机意识也可能导致罪恶向外喷射;……在政治风景线的极端,这变得尤其刻毒,……由于无意义经常伴随着罪恶感,有时他们就呼应强势的极端化意识形态,根据这种意识形态,靠跻身于与黑暗势力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的行列,人们发现着纯洁感和方向感。对对立面越是不妥协,甚至暴力地对待之,两极化就表现得越绝对,远离罪恶的纯洁感就越大。……这种方式向外指向无法再生的世界,产生着毁灭和专制主义。”[15]812泰勒坚守着道德主义者应有的中庸、谨慎和理性。他认为,“我们所需要的是清醒的、科学的、世俗的人道主义……持续的谨慎教导我们,要降低我们的希望,限制我们的眼界。”[15]816-817正因为如此,泰勒不愿开设一所道德学校并像麦金太尔一样兜售全套教材。
沃尔泽是唯一将教育纳入专门考察范围的社群主义作家。他认为,“每个人类社会都教育它的儿童,它未来的新成员。教育表达的可能是我们最深切的希望:在时间中继续、延续、持续下去。它是一个为社会生存而制定的计划。因此,它总是与它所设计的社会相联系。”[16]261按照沃尔泽的逻辑,既然认为教育对于人类社会如此重要,那么就应该为学校提供一整套教材。实际上,正是在这一关键点上,沃尔泽睿智地保持了与麦金太尔的亚里士多德传统的距离。他认为他有论证教育重要性的职责,但没有为学校提供整套教材的权力。他认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教育的目的是在每一代中繁育一种‘情操’(type of character)以维护政体;建立并维护特定的政体需要特定的情操。但这里也有困难:社会的成员是不可能在亚里士多德的广泛意义上对这个政体实际上是什么、或将是什么、或它应是什么达成一致意见的。他们也不可能统一何种情操能够最好地维护它或哪种情操将如何最好地创造出来。实际上,政体可能要求不止一种情操;学校将不仅必须训练它们的学生,而且还得把他们挑选出来;而那肯定是一种引起争论的事情。”[16]261沃尔泽之所以花很大篇幅讨论教育问题,乃在于他认为教育最能表达他对于“最深沉的共识”的理解和希望。丹尼尔·贝尔一直没有弄清楚沃尔泽“最深沉的共识”这一范畴的确切含义。[19]227-239也许我们能够在沃尔泽关于教育的论证中找到某些线索。沃尔泽认为,教育系统应该是一个相对自治的“特殊的社会”,那里“倾向于繁育更直接的民间记忆、传统和‘技能’传承。”[16]264在沃尔泽看来,多元主义的社群对于复合平等原则的捍卫经常失败,这种失败不得不经常性地邀请国家的介入,而国家在介入后面临退出难的难题。所以,他寄希望于教育培育具有捍卫社群复合平等能力的合格成员,减少复合平等原则失败后向国家发出邀请的机会。只有这样的结果,才是沃尔泽所追求的。与麦金太尔开设亚里士多德式的学校不同,也与泰勒不开学校的模式不同,沃尔泽既倡导开设学校,又禁止兜售教材。他唯一兜售的是多元主义价值和平等原则。他的学校是一个开放、包容、多元、自治而又满足简单平等和复合平等要求的特殊社会。也许在沃尔泽的内心,学校承载了他所追求的“最深沉的共识”和多元主义及其平等的希望。
(二)责任伦理的实现路径
在美德与法律所确认的责任之外是否还有增进个人和社会责任的第三条路径的问题,社群主义者并没有进行仔细甄别。但塞尔兹尼克认为,在社群主义中引进韦伯的责任伦理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韦伯在讨论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时将伦理取向的行为分为“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两种类型。[20]107塞尔兹尼克将韦伯的责任伦理概念引入到社群主义的责任分析框架之中,他讨论了法律责任在提升个人和社会责任时的不充分性,讨论了责任的内在化对于提升个人和社会责任的极端重要性,讨论了私德与公德的责任伦理维度,讨论了私德与公德在责任伦理约束下可能取得富有成效的结果。[12]28-37但从文献的查证来看,他忽视了将责任伦理引入政治哲学领域并作出精细分析的托马斯·内格尔(Tomas Nagel)的重要贡献。
托马斯·内格尔用分析哲学的方法研究了私人道德与公共道德、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之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以及如何克服它们之间的非连续性问题。私人道德与公共道德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界分。自由主义者一般主张应该将私人道德与公共道德区分开来,以便确定不同领域的规范。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是韦伯针对政治家提出的一种分类方式。韦伯认为,政治领域中的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都是指导政治行为的公共道德准则。信念伦理是一种关注目的的实践伦理类型,而责任伦理是一种关注后果的实践伦理类型。他希望提醒人们警惕政治浪漫主义和政治理想主义暗藏的陷阱。[20]105-107他的这一分类方式来源于他对行为合法性的两种类型的认识,即目的合乎理性与价值合乎理性的分类。[21]56-57内格尔对公共政治实践领域的道德问题进行了精细的分析,他试图在公共政治的实践领域中将私人道德与公共道德、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之间的非连续性连接起来,借以克服理论与实践、规范与功能之间的非连续性。
内格尔认为,在政治功能性领域,不能仅寄希望于行动者的美德与智慧,还必须对行动者施加双重规范限制:一种是由规范主义所确定的理念与原则的限制,它源于公共道德的要求;一种是私人道德的限制。对政治功能领域施加双重限制的正当性在于:因为行动者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他们必须受到规范的限制。但是,由于政治功能领域的规范限制只能是理念的和原则的。因此,这种限制只是一种初级规范化方案,很难产生实践上的有效性。为增加限制的有效性,必须嵌入私人道德以补强规范方案的有效性。但是,这种私人道德不是一种纯粹私人领域中的道德,而是置于规范性背景和政治职业情境中被评价了的私人道德。将私人道德作为评价功能性政治行为的正当性与有效性的一种制度化工具,则成为内格尔内在化进路的关键问题。
内格尔认为,这种进路的正当性来源于公务论和公众人物准则。由于行动者执行的是未终极规范化的特许政治行为,因此对它们在进行初级规范化后必须通过私人道德补强。内格尔所界定的公务说与法国的公务说之间存在差异。法国的公务说,主要是为了证明行政权力的正当性,是一种权力论的主张。实际上,它证明行动者的行为只要被证明是基于公务的,则行动者本人并不受追究。[22]25-28而内格尔认为,正是由于你是公务的执行者,你就有特别注意的义务和公共责任。所以,内格尔的公务说是要课以行动者以公共责任。内格尔认为,功能领域的政治行动者应负私人道德责任的另一个正当性理由,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公众人物准则在道德领域中的应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自萨利文案以来形成了严格监督公众人物的注意义务的标准。[23]272-290内格尔认为,由于你执行的是公务,因此你的行为必须符合初级规范化的公共道德的约束;但是,正是由于你是公务的执行者,你就有更多义务使你的行为与政治职业的情景性道德要求相符合。内格尔认为,行动者所执行的公务和执行公务的行动者都应该承担道德义务,公务的执行和公务的执行者应该受到公共道德的规范,这一点也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人们对于公务的执行者是否在负公共道德义务之外还应该负私人道德义务则存在争论。内格尔认为,公务的执行者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应该比普通人清楚自己的执行行为是个体化的,并清楚自己的执行行为将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这是政治行动者应负私人道德义务的认知要素和意志要素。冷酷无情的命令不能解脱你应负的道德责任。对国家的义务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来自义务的道德背景。实际上,内格尔涉及到了拉德布鲁赫所提出的“非法”与“非法律”的解决方案。[24]227-236另一方面,政治行动者在行使政治权力时实际上满足了个体自我最个人化的欲望和需要,这乃是人的最原始的感情之一,是政治行动者应负私人道德义务的动力要素。
在解决了对政治行动者课以私人道德的正当性以后,内格尔所要解决的就是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的连续性问题,也就是私人道德对公共道德的有效性补强问题。内格尔认为,我们无法推断公共道德是不是由私人道德推演出来的,也不能推断特权领域中的私人道德是不是由公共道德推演出来的,更不能证明他们之间彼此独立。他认为,公共道德和私人道德可能同享一个道德源泉,它是公共道德和私人道德的终极来源,也是公共道德和私人道德的连续性成为可能的共同背景。由于内格尔是一位分析主义的哲学家,他所说的这个公共道德和私人道德的共同来源可能是指哈特所指的次级规则或拉兹所指的社会规则,或是一般称之为公共利益的功利主义概念,而且很可能不是指洛克所说的自然权利或自然法学派所指的道德。内格尔认为,由于政治行动者执行的是只具有纲要式规范的功能性行为,因此行动者就有特别的道德义务。非个人性的公共行为只适合于对结果的高度重视和对公正性的严格要求,而功能性政治领域不符合这两种条件,功能性领域的行动本身具有试验性,它所关注的是行为本身而不是行为的结果。私人领域的道德约束允许偏好的存在,但是公共领域排除自我放纵和个人偏好。政治权力在功能领域中的设计必须将注重结果和注重行为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合理性的。由于现代政治权力机构庞大且复杂,它对于结果并非总是敏感,因此增加行动者的个体化道德义务能够改善机构敏感性降低的消极后果。内格尔认为,在政治功能性领域植入的私人道德并不是纯粹的私人道德,而是置于公共道德背景评价过的私人道德,这种个体性规范是以公共性规范为镜像的,是公共性规范在政治功能领域行动中的一个微型版本,在这种条件下,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建立了一种连续性。[25]83-99他同时认为,必须在初级规范化的政治功能领域补充私人道德的约束,对行动者本人课以特别义务,这种个体化的道德义务是可以转化为法律责任的。但是,我们认为,如将其转化为一种法律责任则必需设置可接受性的前提和条件,首要的条件就是从事公务的人接受与公务有关的承诺。
(三)法律责任的实践路径
一般观点认为,社群主义的泛道德主义主张会削弱法治的价值。实际的情形是,所有社群主义者并不希望借助于共同善排挤法治。
关于法律责任的定义,“在中国法学界乃至世界法学界尚没有一个能被所有人接受并能适用一切场合的法律责任概念。”[1]167法学一般倾向于将责任界定为义务的消极后果。法律责任是一个很难分析的概念,即使是分析法学派的重要法学家霍菲尔德给我们提供的仍然是一个有关法律责任的极其模糊镜像。他认为,法律责任与权力有关,与豁免(或免除)相反,有时它能产生义务,而不仅仅是法律义务的消极后果,法律责任在公法领域常常是“职责”的代名词。决定法律责任的是选择权。[26]52-70尽管霍菲尔德列举了很多有关法律责任的判例与观点,但他没有给法律责任任何确切的定义。我国通说将法律责任定义为:“有特定法律事实所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补偿、强制履行或者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亦即由于违反第一义务而引起的第二义务。”[1]167我们认为,这一定义对于私法责任可能是有效的,但用于讨论公法责任则存在诸多欠缺。公法责任中的很多法律责任是一种约束选择权的责任伦理,它不一定必然引起损害补偿、强制履行或接受法律惩罚的特殊义务。
规范法学一般是从具体责任主体角度考察法律责任本身的,社群主义对责任的考察则主要关注四个方面:一是在具体制度设计中要求增加更多的责任内容和分量;二是法律责任必须考察责任者与他人的关系、法律责任的公共性,而不是仅仅考虑主体自己的负责任性;三是如何理解法律制度中责任设置的总量与提升个体和社会的负责任性之间的关系;四是法律责任的增量如何维护社群传统文化根基的重要性。
首先,在设计具体法律制度时,必须克服权利本位论,保证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平衡。
社群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在设计具体法律制度时倾向承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弱化或者遮蔽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他们在考察这一问题时,主要批判的是自由主义的权利本位论。塞尔兹尼克认为,社群主义赞成权利与义务的结合。但是,必须区分适度的权利观和无限的权利本位论。权利本位论的精神漠视合作,而合作调和利益并寻求对理性的与目的的共同义务。在公共生活中,权利本位论造成了社会分裂、僵局和扭曲的优先权。从义务的角度行使权利或从关怀他人的角度行使权利,与利用权利保护狭义的利益之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差异。当我们考虑后果尤其是社会和谐与合作的后果时,我们可靠地断言权利。[12]67-69因此,塞尔兹尼克主张在具体制度设计过程中必须实现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其次,每一个法律责任主体在履行自己的责任时,必须认识到自己是社会责任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严格恪守自己的责任就是为社群的和谐与共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凯恩正是从这一角度考察法律责任问题的。他认为,法律责任可以被理解成一套服务于许多社会功能的社会实践;法律责任具有人际性,它不仅涉及行为引发责任的个人的境况,而且涉及该行为对其他个体以及社会的影响。相反,关于责任的更哲学化的分析则专注于行为人,其代价就是忽视了被害人和整个社会。[27]8塞尔兹尼克认为,法治是法律与标准的结合。“法律服从调整法律如何制定、使用和遵守的规则和原则及其来自‘法律背后的法律’的批评,这些标准使法律保持在限度内。它们限制那些以法律名义滥用权力的人。法治的主要功能是限制国王、总统和其他行政官员,它宣称法治政府而不是人治政府:任何官员,无论权力大小,都没有超越法律的权力。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法治限制法官和立法者,也限制行政官员和机构。成文宪法或不成文宪法为审查官员的行动提供标准,实现法律背后的法律。[12]106因此,从广泛意义上理解,法治是政治制度的一种总体上的设计,必须从宏观上考察法治的功能。从个人角度考察,责任不仅意味着行为者的责任,行为者在行为前更应理解其行为的负责任性与所承担责任的政治和社会意义。以行为为中心对责任的理解是自由主义道义责任论的狭隘的理解,只有站在对社会或者对政治设计的层面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法律责任的意义。
再次,法治必须维护社群和共同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根基和共善标准。
塞尔兹尼克认为,法治最重要的意义就是通过法律维持一种合法性文化的根基。[12]106即使是美德传统最坚定的捍卫者麦金太尔,也不否定法治在维护社群文化根基中的不可替代的功能。他认为:“法律的统治——就其在现代国家中是可能的而言——必须得到维护,非正义与不正当的伤害必须得到认真对待,宽大慷慨必须得到践行,自由必须得到捍卫,所有这一切有时惟有通过政府制度机构的运作才有可能。然而,每一项特殊的使命,每一项特殊的责任都必须靠其自身的功过来得到评价。现代系统的政治观,无论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无论激进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从一种真正忠于美德传统的观点来看,都必须被拒斥,因为现代政治本身以其制度性的形式表达了对于这一传统的系统拒斥。”[28]324-325麦金太尔是如何得出这种结论的呢?
麦金太尔并不一般地反对法治,他所反对的是建立在自然权利基础上的自由主义法治及其制度安排。他认为,作为自然权利既不诉诸于神性法律,也不诉诸于成文法。自然权利说的本质是,无人对我拥有权利,除非他能举出某项契约,证明我签定了它,他履行了该契约载明的他的义务;说我在某方面有权利,只不过说无人能合法地干预我,除非他能证明他在这方面对我拥有权利。由于自然权利的本质是经济上的交易观念崁入到法律之中,因此,人与人相遇于竞技场,自由市场经济的现金交易关系和日益集中的国家权力二者合力摧毁了赖以确立传统合法性的社会纽带。[29]210-213不仅如此,他认为自然权利确认的个人主义与新教的结合彻底摧毁了传统生活方式。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脱胎于新教的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兴起,瓦解了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这使社会生活的现实远离那些蕴含在传统词汇中的准则,使得职责和幸福之间的所有联系都逐渐地断裂了。结果是对道德词汇的重新解说。幸福不再是那支配着生活方式的准则所理解的满足,而是依据于个人心理学来界定。”[29]225在麦金太尔看来,自然权利赋予个人无限权利,道德和法律不是个人欲望满足的尺度;相反,法律和道德必须以个人欲望的满足为尺度。
麦金太尔在对自由主义法治观念的批判过程中分享了保守主义的法治观,欧克肖特的法治观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他认为,“‘法治’这个词确切地理解,指一种承认已知的、非工具性的规则(即法律)的权威的道德联合模式,它将在做自我选择时同意限定条件的义务强加给所有在它们权限内的人。”[30]170-171欧克肖特认为,法治的关键在于通过相互义务的制度设置维护一种已知的道德联合,这正是社群主义者所要表达的法治观念。
社群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的启发和鼓励。[31]193-100贝尔认为,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在西方发展的结果必然会以与集体目标之间的矛盾而告终,这一矛盾是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发展的必然逻辑。摆脱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重构公共社区(他称之为公共家庭)。[32]185-186贝尔所确认的对自由主义批判的基本立场、逻辑、框架和发展方向几乎全部被社群主义所接受。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几乎都是贝尔逻辑的展开。贝尔认为,“法律和道德的分离在经济王国才有着最大影响。法律应该很规范,很程序化,并不是附属之物,它和道德的分离意味着国家不会干预谈判双方拟定的经济契约。这是19世纪后半叶,最高法院在大法官斯蒂芬·J·菲尔德授意下制定的一系列法律所依据的原则。”[32]297在批判自由主义法治观问题上,桑德尔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1996年,他在一系列讲座的基础上逐步提炼出美国的程序主义新传统和共和主义的悠久传统之间的互竞问题。[33]4-7
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悬搁法律责任的指责在哪些方面被自由主义者所认同呢?自由主义的重要辩护者威尔·金里卡认为,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强的批判是没有根据的,而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弱的批判与自由主义的主张之间并不冲突。但是,他仍然认为自由主义的逻辑并没有在新自由主义中得到很好阐述,尤其是在对少数群体文化权利的维护方面。他认为,“我对自由主义以一种冷漠的或者充满敌意的方式对少数群体文化的集体权利做出的回应感到不安。在所有情况下,核心的争辩都已经由于缺乏对社群和文化的自由主义说明的一系列讨论而受到损害。”[34]1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悬搁法律责任的指责并非无中生有。
那么,社群主义者如何在法治中提升法律责任呢?对此问题,社群主义者主要围绕最高法院的宪政功能来讨论。贝尔和桑德尔坚持最高法院应尊重共和主义传统。麦金太尔认为,现代社会不可能在道德问题上达成真正的共识。但是,他仍然认为“最高法院的功能之一,必须是通过展示一种体现在其判决的不偏不倚之中的公正性,而在信奉互竞的、互不相容的正义原则之互竞的社群之间媾和。”[28]322社群主义者承认最高法院应该积极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提升法律责任,以维护社群赖以生存的文化根基的合法性。
注释:
(1)阿伦特认为是阿奎那在翻译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将“人是政治的动物”翻译成了“人是社会的动物”。([美]汉娜·阿伦特著:《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 2 章。)但是 ,唐特雷佛(A.P.D’Entrves)的研究表明:将“人是政治的动物”翻译成“人是社会动物”的是摩尔贝克的威廉(Willian of Moerbecke)。圣托马斯在《政治学诠释》一文中采用这一译法,但是在其他所有的著作中则一直使用“政治的和社会的动物”。[罗马]阿奎那著:《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英译本编者序言第15页。
[1]张文显.法理学[M].第3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
[3][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古罗马]西塞罗.论老年·论友谊·论责任[M].徐奕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6][荷]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M].[美]A.C.坎贝尔,英译;何勤华,等汉译.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7][德]塞缪尔·普芬道夫.人和公民的自然法义务[M].鞠成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8]程关松.行政法治二元模式的法哲学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09.
[9][英]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M].王献平,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10][法]路易·阿尔都塞.马基雅维利的孤独[G]//[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现代君主论.陈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1][法]西蒙娜·薇依.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M].徐卫翔,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12][美]菲利浦·塞尔兹尼克.社群主义的说服力[M].马洪,李清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3][美]迈克尔·J.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M].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14][英]迈克尔·H.莱斯诺斯.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M].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5][加拿大]查尔斯·泰勒.自我的认同·现代认同的形成[M].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16][美]迈克尔·沃尔泽.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M].褚松燕,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17]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8][法]狄骥.宪法学教程[M].王文利 ,等 ,译.沈阳 :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
[19][加]丹尼尔·贝尔,[美]丹尼尔·贝尔.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M].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
[20][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21][德]马克斯 ·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2]王名扬.法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
[23]任东来,陈伟,白雪峰,等.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24][德]拉德布鲁赫.法哲学[M].王朴,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25][美]托马斯·内格尔.人的问题[M].万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6][美]霍菲尔德.基本法律概念[M].张书友,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27][澳]皮特·凯恩.法律与道德中的责任[M].罗李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8][美]A.美金太尔.追寻美德·伦理理论研究[M].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29][美]A·麦金太尔.伦理学简史[M].龚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0][英]迈克尔·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M].张汝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31]徐大同.当代西方政治思潮·70年代以来[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32][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严蓓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33][美]迈克尔·桑德尔.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M].曾纪茂,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34][加拿大]威尔·金里卡.自由主义、社群与文化[M].应奇,葛水林,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Suspended from Duty,Push to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Apparition:Narrative of Western Legal Responsibility
CHENG Guan-song,ZHANG Zhi-gan
(Jiangx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Nanchang 330077,China)
Before the Renaissance,based on persons in one’s social o r community,construction in the West of 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entral control system.However,the development of the bourgeoisie and the sp read of Protestantism,natural rights construct the theory has the right to center fo r law system,and become the legitimacy of the western social life foundation.When western encounter in the crisisof modernity,Communitarianism reflect individualism right system exp ressed ascending individua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strong appeal.Closely examines the histo rical circum stances which the Western responsibility idea evolves and identify the Western responsibility view the connotation and the realization way has the vital significance.
responsibility;evolution;accountability
D251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672-0539(2011)04-049-09
2010-11-11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07AFX007);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政府选择性社会管理创新权的行政法学研究(11BFX09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程关松(1965-),男,湖北黄冈市人,副研究员,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法哲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刘玉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