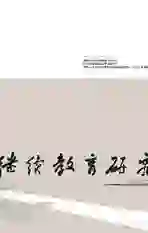教师-人工智能:互利共生的选择
2025-01-24邓丽群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赋予教师发展挑战与机遇,教师个体何以生存、明确其角色定位亟待研究。从概念出发,基于生物共生关系的类型学隐喻,提出人机共生是教师与人工智能的应然选择。从共生的理论基础分析,人工智能运用于教育后给教师带来的“利”与“害”。在此基础上,提出需从理解角色间的相互关系出发,探索教师生存、转向和共生之路。在“乘风破浪”的人工智能时代,希冀教师得以保有其角色的生命力,构建与人工智能相得益彰的新格局。
关键词:人工智能;教师角色;共生理论;GhatGPT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25)01-0030-0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指出,教师需要主动适应新技术变革,从而有效地进行教育教学工作[1]。随着ChatGPT的出现,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在即,教师正面临巨大的角色转型挑战,这同时也为其自身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2022年4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要求“进一步挖掘和发挥教师在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中的作用”[2]。对于智能时代教师角色转型的具体指向以及时代诉求,学界对此的共识表现为引导者、学习者、设计者、组织者、研究者、心灵塑造者和评估者等七大角色,其中,引导者、学习者、设计者这三类角色是占比最高的教师角色[3]。当前,教师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找准角色定位,并正确处理人机关系,已成为摆在广大教师面前的重要任务。何以扮演好引导者、学习者、设计者角色,让教师满腹疑团。以共生理论为基础,分析教师角色所面临的“利”与“害”,并从生存之本、转向之姿和共生之态等三个维度对教师角色进行澄明。溯本求源指向教师生存的意蕴和价值,希冀教师能够在智能时代的激烈竞争中保持角色的充盈和生命力,争做智慧教育时代的弄潮儿。
一、选择:人机共生
(一)教师角色与定位
角色(role),最初用于描述舞台上或者电影中演员所扮演的人物。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米德将其引介到社会心理学范畴,将角色定义为个体基于所处特定社会而产生的行为模式[4]。它包括以下三种结构:一是角色表现为一连串的社会行为;二是角色取决于人的身份、社会地位;三是角色与社会期待相吻合。角色是个体置于特定社会地位,所产生普遍适应的身份或行为模式,总体表现于个体的内在思想与价值观之中,如教师、学生角色等。
在教育社会学的视域下,教师在教育这个舞台上饰演一种独一无二的社会角色。叶澜教授认为,“教师”是指“对受教育者的心灵施加特定影响为其职责的人”[5]。解读这个角色,实际上就是探究教师群体在社会关系构架中的行为方式。这个位置由社会、学校、学生以及教师本人共同塑造而成。一个人所处的社会角色不仅定义了他们活动的范围,也同时规定了与之相匹配的权利、义务和行为标准[6]。由此,“教师角色”这一概念是指在教育结构中与教师社会身份、地位相符的预期行为模式。社会对教师的期望以角色和期望角色的形式呈现。教师的行为受到其社会地位和身份的遏制,表现为实际角色和期望角色两个方面[7]。教师是一种具有多种角色的独立行动者,其所展现出来的行为即为教师的角色行为[8]。在时代进步的推动下,“教师角色”也会随之改变。
(二)人工智能的嬗变
人工智能的嬗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萌芽(1950—1981年)、沉淀积累(1981—2011年)、快速发展(2011年至今)[9]。2022年11月30日,OpenAI推出了ChatGPT(聊天机器人),其凭借不间断问答、文稿自动生成摘要、翻译、分类以及编写代码等功能迅速风靡全球。构成ChatGPT的核心架构归总为两类:第一种是GPT语言模型;第二种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简称AIGC)模型。GPT与AIGC结合,达到不同场景相互应用、补充的效果,从而使用者得以享受愈发高效、智能和定制化的内容服务。比如,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表现如下特点:一是依靠强大的算法支撑,教育资源达到万物互联的状态,提升了学生实践的创造力;二是基于人工智能训练数据库和模型结构的自动生成,拓宽了人机交互的通道,有助于增强学生认识的能动性;三是在基础模型的迭代升级中,人工智能持续关注用户的特征,可以更好地适应用户的行为偏好,个性化定制强化了学生选择的自主性;四是大数据促进减负增效,在教学层面,人工智能助力部分传统业务实现自动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教师日常的工作压力,有助于促进教师专业发展[10]。
(三)人机共生的选择
“共生”(symbiosis)一词肇始于生物学范畴,最先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在1879年刊布。他给共生体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不同名的生物体在一起生活。”他着重指出,各种有机体间的密切关联。共生观念的发展和演化反映出生物体间相对利益的动态变化。按照生物间的利益导向的不同,共生又可分为六种,即偏利共生、偏害共生、无关共生、寄生、互利共生、竞争共生[11]。作为一种有隐喻的生物学现象,“共生”的探索研究已经扩大到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并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共生理论。
1960年,最先建言“人机共生”(Man-Computer symbiosis)这一概念的是约瑟夫·利克莱德,他将互利共生关系隐喻为人机关系,认为人类与机器之间密切耦合[12]。在智能时代背景下,得益于新兴科技,机器的工具性能愈发增强,与人建立了协作关系。由于人工智能系统认知和行动力增强,因此机器拥有更多自主权和决策权[13]。人机关系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并非简单地朝着互利状态发展,这里“利”与“害”的主要区别是促成了还是损害了“人”发展个性化和社会化的有机统一。由于教师、人工智能属于不同领域,因此二者间利益评估存在标准差异。对前者而言,“利” “害”是指是否有助于或损害了教师进行教育和教学;对后者而言,“利” “害”不仅涉及机器物理上的生存问题,更关注其在学习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升降。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人工智能作为半自主决策者出现,展示出与教师相似的特质,致使机器与教师之间界限愈发模糊。在人工智能时代,复杂性化身为共生关系的特质,呈现为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样态。
在此基础上,从生物共生理论中的类型学隐喻出发,展现教师和人工智能在不同交互情境下的合作与竞争关系。为了能够展现不同的人机交互场景,尝试将教师同人工智能共生与共生理论中的偏利共生、偏害共生和互利共生等三种典型类型遥相呼应。
二、解析:智能时代教师的“利”与“害”
在智能时代下,随着ChatGPT4.0以及各种智能工具争相涌入市场,智能机器的功能得以强化和提升,致使人机关系呈现多样化。在教育领域中,教师与智能机器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态势。
(一)偏利共生
在智能时代,技术的迅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机器自动化和适应性的提升。作为更加高效的工具存在,机器与教师形成了一种被称为“工具型”的共生关系。这种模式强调了教师和机器的协作关系,即教师使用智能机器以完成特定任务并获取反馈,从而体现了教师的主观能动性。从技术角度看,机器与教师建立起一种相对松散的“工具型”合作关系,形成了一种积极的共生关系。在偏利共生中,“利”展现为教师与机器之间互相合作致使二者中的一方得到发展。重点讨论偏利共生中对教师而言的“偏利”,主要表现为机器能够为教师处理日常大量的重复性且耗时的工作,减轻教师的部分工作负担。
1.智能机器助力教师学习评价者角色。教师运用人工智能的自动化评估和反馈技术,可以大大节省其批改作业时间,使其专注于更复杂的评估任务和提供个性化指导。教师可以利用ChatGPT的功能开展智能评测,比如,自动生成文本、语音和视频等方式,增强学生学习评估方式的客观性和科学性[14]。
2.智能机器助力教师教学引导者角色。人工智能可以为教师提供各种辅助工具,帮助教师简化教学过程。例如,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技术可以帮助教师自动转录和生成课堂讲义、笔记和课程录音;智能图像识别技术可以辅助教师识别和分类学生的作品和实验结果;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以帮助教师分析学生的写作和表达能力等。教师不再需要独自承担传统的教学环节,如课堂讲解、问题解答和任务批改等。这些工作可以由虚拟助手来完成或者由学习伴侣及其系统提供支持。智能教育机器人或者辅助系统可以接管部分教师的职责,从而使他们从日常的重复性且耗时的工作中得到释放[15]。此外,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分析大量的教育数据,为教师提供决策和干预的依据。它可以帮助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趋势、弱点和潜在问题,提前预测学生的学习成绩和需求,从而采取相应的教学策略和措施。
3.智能机器助力教师研究者角色。ChatGPT能有效地提升教师进行科研活动的效率。在过去,教师需要通过阅读文献或交流与同行来激发灵感和明确思路;现如今,他们可以先与ChatGPT进行初步讨论以获得启示。总的来说,人工智能可以在教师工作中提供更高效、个性化和智能化的支持,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
(二)偏害共生
在偏害共生模式中,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不断赋能教育领域,机器可能超越教师的潜力,使智能机器对教师精神世界产生一种价值挤压的异化,形成了一种“竞争性”的共生关系。这表现为人工智能对教师的接替,从模仿教师的内在能力开始,不断打击教师的存在价值。借助于深度学习和情境感知等技术,日益智能化的机器在共生关系中得到能力提升,实现自我优化并获得价值回报,而教师则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智能机器持续打破教师思维劳动的限制,开始介入和替代一些知识性工作,而这些工作以前只有教师可以完成,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教师对人工智能的焦虑[16]。随着人工智能不断渗透于教育教学中,教师同时面临教学环境、内容更新、教师角色转变等全新角逐。
1.人工智能正冲击着教师知识权威者的角色。从智能时代教育发展的现实样态看,“从师”不再是“求道”“解惑”的唯一路径。有学者认为,ChatGPT是“无所不知、知无不尽、全年无休且人人可得的‘超级教师’”[17]。人工智能建构的泛在学习场景,使广大求知者可以通过智能手机、电脑等工具,进行资料查找、信息交流、线上课程学习等。与此同时,“不知疲倦”的人工智能不仅能够改变知识传输的单向性,还能够探索学生潜在的思维过程,替代教师并为他们提供精准的规划和个性化的指导。
2.人工智能正冲击着教师设计者角色。在教育领域,ChatGPT可以替代教师制订课程计划,收集教育资源并撰写教学评论。例如,在设计课程方案时,ChatGPT能够创建一个基础的课堂计划,包括学习目标、授课内容、授课步骤和评估等方面。部分教师对智能工具过分依赖、滥用,致使自身思想“锈化”,不利于教师发展更高层次思维和素养。此外,部分教师在借助于人工智能进行教学活动时,往往更注重单一的“智育”功能,忽略教育的其他面向,使教学可能异化为单向度的知识传授。比如,在制作教案时,ChatGPT提供的同质化教案使教学过程存在固化的风险。教师个人劳动表征为服从机器指令,其专业化程度恐被削弱。
(三)利害演化
对偏利共生、偏害共生的演化特性进行深入剖析和反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工智能时代机器与教师的共生关系,从而动态且有进化性地理解机器与教师之间的共生联系。
1.人工智能对教师的“利”与“害”共同存在。无论是偏利共生,还是偏害共生,二者不可孤立看待。前者,教师利用人工智能的工具特质,与之建立了一种在提高工作效率和优化内容上相对协调的搭档关系,即“偏利共生”;后者,机器的智能特性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角色产生了挑战,形成了一种相对有冲突的角逐关系,即 “偏害共生”。
2.人工智能对教师的“利”与“害”互为表里。人机共生关系是一个与日俱新的过程,不论是“利”,还是“害”,往往是形影相依的。它们都基于彼此的存在,有“利”皆有“害”,反之亦复如是。在偏利共生模式中,尽管教师表现出正面的价值利益,但同时也隐藏着负面影响。同理,在偏害共生模式中所体现出来对教师的损害倾向,实际上也浮现着正面的效益元素。两种模式均存在于一种互通、交错状态中,因此在人机共生模式中,对教师并没有绝对的好与坏,这种双向的好坏导向实际上是同时存在且无法分离的。作为一个不可拆分的整体,“利”与“害”相互依赖,形成了一种对立统一。
3.人工智能对教师的“利”与“害”的相生相成。在人机协同关系中,“利”与“害”不仅是彼此依赖的,也有可能实现互相促进与转化。随着人机共生关系的动态发展及变化,对教师的优劣因素在维持彼此依赖的同时,也在进步和改良,在特定情境下显现出互为转换的趋势。对于教师来说,“利”有可能变成“害”;反之,“害”同样有潜力转变为“利”。
现如今,教师和人工智能的关系日益复杂,二者间呈现出祸福相依的倾向。审视目前的人机共生关系,各个时势下的得失是对立发展的,利害得失,祸福倚伏。在这种变易的环境下,只有对人机关系实时动态调整,才能在恰当时间将“害”转为“利”。在智能时代,教师与智能机器相辅相成、共同演进的双赢共生轨道——互利共生,为人机关系健康发展打开了新窗口。
三、互利共生:教师角色的澄明
“互利共生”是指人类和机器在合作中均获得了好处。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相得益彰,其结合比各自独立时所展现的效果更上一层楼, “搭档型”的共生关系形成。在互利共生模式下,解决问题的方式由教师与人工智能对等的智能感知及交互决策完成。二者的结合不仅展示了教师的主动性,也突显了机器的独立性,最终演变为密不可分的“合作式”关系。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二者互补,相辅相成,共同创造价值。在教育领域,利克莱德所描绘的“人机共生”的憧憬得以回归,即教师与人工智能相互补充,实现了“教师+人工智能>教师”或“教师+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效果。
(一)定位:教师角色的生存之本
作为生命启明星的教师潜移默化地指引着学生成长,其角色包罗生命灵性,角色生存之本在于递升生命的价值。正如叶澜教授所言,教育是一项直面人生命、提高人生价值的事业[18]。教师的生命意蕴在于明确其角色关系中的存在坐标。
在教师与人工智能的互动中,教师应满怀“无可替代”的信心,明确人类教师的专属特质与意义。如德雷福斯所言,智力、社会和文化的积淀,培养了人类的理性和智能,人工智能所呈现和程序化的都远远达不到这种“人”专属的特质[19]。尽管ChatGPT能够替代教师在教育工作中的一部分工作任务,但是换一个角度思考,教师的创造性劳动,比如教育机智等是其所独有的。教师更应该知晓作为人——生命个体所充盈的价值无与伦比。这份价值是专属于人且区别于ChatGPT以外的任何人工智能所独有的。教育的原点是育人,教师的教学不单是“授业、解惑”,更多地指向“育人”,如叶澜教授强调要把学生培养成为“主动、健康发展的人”,引导学生形成生命自觉。就像海德格尔对诗意栖居的向往一样,诗意即创造,以自我存在的状态来展示世界,无论技术如何迅速发展,人类教师都应自持一种教育初衷的胆识,“宁静居于人世,远离喧嚣纷扰”,坚守教育本质,在诗意的生态中与人工智能互利共生。在物质组成和存在方式上都有根本差异的教师与人工智能,分别是有生命的有机体和无生命的非有机体。意识到二者存在的异质性,教师与人工智能共生之路便不再遥远。
(二)转化:教师角色的转向之姿
在人工智能技术演进与教育革新的氛围中,教师角色面临种种挑战,亟须转向以适应当今时代需求。就像叶澜教授所倡导的,教育的转型变革必须为教师所理解和接受,否则将一事无成。需要从社会角度重新定义教师的角色,以真正改变教师的本质,明确教师角色的转型方向。
1.从“知识权威者”转向为“个性化教学者”是教师角色转向的首要之义,从注重知识权威转向关注个体个性发展。个性化的实现,需要教师转变知识观,注重知识的智慧化。借助于人工智能可以承担起传递知识的职责,教师可以从重复性的劳动中解脱出来,转向提升自我智慧。首先,以学生为本,教师需要关注他们成长的需求。从浩如烟海的信息中挑选出有意义的知识,辅助学生完善知识体系。授之以渔,使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其次,教师应精通各种人工智能技术和教育智能工具,并创新性地设计个性化教学以适应不同特质的学生。最后,教师应进行终身学习和反思。在教育过程中,面向人工智能,教师需要跳脱技术束缚之环,以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来审视每一个教学步骤使用的智能设备是否合理、有效且公平。在科技与社会发展演变过程中,教师必须持续提高自己以发展新型教学方式,从而更深入地开发学生潜力。
2.强化技术整合能力,赋能教师设计者角色。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育的背景下,高科技产品进入教育教学已习以为常。这不仅是因为人工智能技术拥有超出人类范围的信息处理、传递和展示能力,更是由于它有人无法比拟的信息联通性及不断更新、共享信息的特点[20]。这启示教师需要建立更广阔的合作观念。从小到大,从市区到省份再到全国甚至全球,所有教师都应联动起来,形成一个教育社区,并创建一个能够整合知识资源以及朝气蓬勃、兼容并包的学习环境。久而久之,每位教师的个人发展愿景在新兴人工智能联通技术的赋能下得以实现。把握好教师自身相对于人工智能而言的专长,将宝贵的时间投入智能机器无法取代的任务中,比如创新性教学和社会化育人等。教师需要擅长发掘和转变与机器间对话的价值,尽管ChatGPT可以自动创建文本,然而对于复杂的需求,其自动生成的文本几乎存在同质化甚至出现错误。教师需要将复杂需求分解并简化为一系列小任务,提供必要的人工干预。加强自身专业知识,深入自身专业素养,“去粗存真、去伪存真”,把设计者角色做好做强。
3.彰显角色育人性,凸显教师引导者角色价值。教师现存的“学富五车”已经不足以跟上迅速发展的智能机器拥有的巨额存储。在应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教育的变革时,教师需要调整教学观念和思维方式,将教学实践主动权归还学生,并与其在知识创造、探索和应用上同心协力,以激发学生的智慧和灵感,在发挥引导者能动性的同时,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此外,教师要把握好人特有的机能,比如想象力、表达交流、好奇心、共情、关怀等软能力。积极发挥自身情感的优势,在面对自我控制力差、过度暴躁的学生时,利用自身的情感满足其需求。
教师与机器共生,既不过度排斥,也不过度依赖;既不过度自卑,也不过度骄傲。把握好与人工智能联袂的“度”,主动探寻人机和谐共生共赢之道。正如叶澜教授所言,只有适度,技术才能在教育中成为“人自由发展”的重要工具[21]。
(三)存在:教师角色的共生之态
教师的功能可以分为本体性功能和工具性功能:前者对于人工智能来说是教师的不可替代功能,主要表现在情感、价值观、创造力等方面;后者是可以为人工智能所代替的功能。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的功能表现为教师的工具性功能和本体性功能此消彼长、不分畛域。为了让教师寻求角色的生存和发展,教师与人工智能共同体亟待建构。这既可以在知识层面支持教师,也能助力教师专业发展。教师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来替代教师的工具性功能,即利用人工智能完成繁杂的程序性任务,圆梦教师智能化改造教育教学活动。教师需要有效应用人工智能,接纳人工智能技术。接纳是指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应用智能技术和设备,但更重要的是,教师能够将人工智能理念和技术融入自身的教育观念和方式中,并以创新性的方式对科技加以利用引导,探索出教育科技的潜力。教师能够如同“导演”一般联结教育与人工智能,共同推动教育教学活动创新发展。借助于人工智能科技对课程形式、内容等方面进行新颖探索,并在此过程中保持警惕,避免陷入被科技束缚的困境中[22]。
推进“教师-人工智能”互利共生,要诀为:以本体性教育为基础,活用人工智能的工具性,将智能工具的应用范围限制在“亲人、利人、为人”的发展畛域内。在人工智能时代,借力智能机器,扩大教师感知、思维、表达和行动能力,二者便可渐行渐远,从而教师的生存、适应与发展力也可与日俱进。总之,教师需要成为“人机协同者”,积极拥抱人工智能技术,与其协调合作,共同创造新型教育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造力。为了应对人工智能时代跨界融合的挑战,教师也需要成为“资源整合者”,提升整合和设计各类资源的素养,实现资源的跨界融合和共享。
走向“教师-人工智能”互利共生是增强教育机器智能、扩展人类教育智慧的必然之路。教师用其所长,将自身的教育机智迁移其中,机器智能则运用自身的数据、计算、模拟等优势拓展催生出功能更强大的学习模式、资源以及教育场景。二者的互利共生使教育教学效果远远超越传统教学。“教师-人工智能”共生的一般形态是“‘人机’双主体的协同,即人和机器共同计算得到的知识生成与获取”[23]。最初,拥有千万神经元的智能人类创造了机器,赋予机器人特有的智能——人工智能;如今,技术日益高超的人工智能,反向赋能教师,促使教育可持续发展。教师与人工智能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更高层次的共生,二者将一起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升级。在智能时代,教师与人工智能将由追求各自的美好转向实现共生,最终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EB/OL].(2018-01-31)[2023-05-18].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8/content_5266234.htm.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印发《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的通知[EB/OL].(2022-04-11)[2023-10-30].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4/14/content_5685205.htm.
[3]李鑫,易凯谕,钟志贤.国内教师角色转型研究的共识分析[J].中小学数字化教学,2023(1):32-37.
[4]奚从清.角色论:个人与社会的互动[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130.
[5]叶澜.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32.
[6]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20.
[7]顾明远.教育大词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843.
[8]王伟杰.课堂教学中的教师角色行为分析[J].外国中小学教育,2003(9):35-38.
[9]荆林波,杨征宇.聊天机器人(ChatGPT)的溯源及展望[J].财经智库,2023(1):5-36+135-136.
[10]冯雨奂.ChatGPT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价值、潜在伦理风险与治理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2023(4):26-32.
[11]袁纯清.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34.
[12]LICKLIDER J C R. Man-Computer Symbiosis[J].IRE Transactions on Human Factors in Electronics,1960(1):4-11.
[13]LIST C. Group Agenc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J].Philosophy amp; Technology,2021(34):1213-1242.
[14]杨小微,王珏.ChatGPT应用于基础教育的机遇、挑战与应对——“刷题式”教育、学生学习、“超级教师”及教育公平[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125-136.
[15]余胜泉.“互联网+”时代的未来教育[J].人民教育,2018(1):34-39.
[16]赵磊磊,张黎,章璐,等.中小学教师的人工智能焦虑:现状分析与消解路向[J].现代教育技术,2022(3):81-91.
[17]顾小清.ChatGPT对教育生态的影响[J].探索与争鸣,2023(3):30-32.
[18]王枬.成己成人:叶澜教师观解读[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2:4.
[19]李世瑾,胡艺龄,顾小清.如何走出人工智能教育风险的困局:现象、成因及应对[J].电化教育研究,2021(7):19-25.
[20]尤瓦尔·赫拉利.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19.
[21]叶澜.“生命·实践”教育的信条[N].光明日报,2017-02-21(13).
[22]陆石彦.论人工智能时代的教师角色再造[J].江苏高教,2020(6):97-102.
[23]方海光,孔新梅,李海芸,等.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协同教育理论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2022(7):5-13.
Teacher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Symbiotic Choice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brough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o teachers, and it is urgent to study how individual teachers can survive and clarify their roles. Based on the typological metaphor of biological symbiosi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human-computer symbiosis is the natural choice for teacher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nalyzes the “benefits” and “harms” brought by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teachers in education from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symbiosis. On this basis,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paths for teachers’ foundation of survival, the posture of turning and the state of symbiosis,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u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ole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achers can maintain the vitality of their roles and build a new pattern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ey wor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acher roles; Symbiosis theory; GhatG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