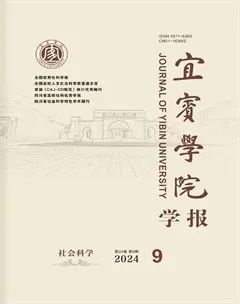从物的情动到符号的规训:《一双长丝袜》的主体性问题再探讨
2024-12-31吴卓颖
摘要:学界既有的对《一双长丝袜》的解读主要形成了女性主义与消费主义两种不同的逻辑,得出了主体觉醒与主体消解两种不可调和的对立性观点。这些解读简化了萨默斯太太与物的多重关系及过程,忽略了萨默斯太太消费活动的起始点,也就是与丝袜的关系的复杂性:萨默斯太太触模到丝袜时以身体直感的悸动为基础的情动,指向行动的、生成主体的可能性。但是在后续的审美消费和信息消费中,具体的物从与个体的占有式联系中脱身,情动被纳入表征,重构为商品世界中的审美的、感性的符号化经验,在气氛营造和具有区隔感的信息中指向消费的体验性快感,主体也在这种消费逻辑中被规训。
关键词:一双长丝袜;情动;主体性;物
中图分类号:I01
DOI:10.19504/j.Cnki.issn1671-5365.2024.09.04
《一双长丝袜》(A Pair of Silk Stockings)是凯特·肖邦(Kate Chopin)的代表作之一。这一短篇小说最初在1897年发表于Vogue,这本杂志至今仍是全球时尚界的标杆性存在,过百年的时尚前沿记录,使它承载了女性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大众意义及变迁。而《一双长丝袜》的小说内容也与女性/时尚消费息息相关。小说讲述了家庭主妇萨默斯太太意外获得十五美元后的消费旅程,她本打算用这笔钱为子女添置衣物,却在购买了一双长丝袜后,分别在商场、高档餐厅和戏院把钱全部花光,短暂欢愉后不得不回到惨淡现实中。自然而然,女性主义批评和消费文化批评成为观照这部小说的重要范式,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解读。有的学者认为由这双丝袜引发的反常消费折射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1];有的学者从消费文化出发,认为萨默斯太太“反抗她受累的生活现状是盲目冲动,完全绝望地屈从于消费伦理驱使的指令”[2]357-358,这种视角通常把萨默斯太太的消费行为放在更大的政治-经济背景中观照,结合美国在19世纪晚期的消费文化转型,提出这种“炫耀式消费”只为萨默斯太太提供的暂时的、虚幻的满足感[2]357-358。而申丹则试图超越中对立性解读,以叙事的隐性进程来观照文本,认为“女主人公既不代表受男权社会压迫的女性,也不代表受消费文化影响的购物者,而是代表受环境变化左右的个体”[3]。
在这几种解读中,最不兼容的一点是萨默斯太太的主体性问题,而这个问题又是理解文本的关窍所在,不同的回答指向几乎完全不同的批评方向。萨默斯太太的放纵消费行为在女性主义批评视角眼中,是“把自我作为一个主体来对待”的过程[1],这个消费过程使她从母亲、妻子的角色身份中逃离,重新框定自己的主体性;恰恰相反,在消费文化视角中这是一个丧失自我的过程,看似成为“独立的个体”,实则只是在“炫耀式消费”中成为“消费文化的牺牲品和被动承受者”[4];从自然主义的视角观照,萨默斯太太同样“缺乏自我意识”[3],她只是在环境决定论的主宰下让自己的消费行为短暂地趋同于婚前的富有阶层。引发争议的主体性生成问题和文本本身的复杂性相关,萨默斯太太确实在消费过程中完全依凭个人的意愿支配金钱,并短暂地悬置了作为妻子、母亲的沉重责任,这种逃离本身潜藏着重新认识自己、审视自己的一种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意味着德勒兹意义上指向行动的潜能的“可视的伦理力量”[5]51。但这种潜能并不体现为她所有的消费行为中,而仅仅表现为她最初的接触丝袜本身时那种身体化的唤醒过程中,但是在小说中,这种可能性又很快地被消费逻辑裹挟着从多种可能性垮塌为现实一种。萨默斯太太的消费链条是丝袜-鞋-手套-杂志-高级餐厅-戏院,消费对象所具有的“物”的特性逐渐削弱。到戏院时萨默斯太太已经完全为信息、审美体验而付费,在这一过程中对物的占有转变为对信息和审美的体验和享受。体验和享受并不干预和改变现实,它给予萨默斯太太的只有被包装为主体自主性的消费者自由。消费活动中的挑选动作使人告别了与行动相联系的自由,它不打断现存的事物和已有的社会认知,也不将新的、全然的他物放置到世界当中[6]17。这是区别于行动自由的挑选自由,它抹杀了主体行动之潜能,而这恰恰“证明自身是一种幻象”[6]17。以往的解读之所以所形成了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式冲突,就在于简化了萨默斯太太与物的多重关系及过程,对这一问题或不以截然分明的有或无进行表述,需要回到文本逐步升级的、曲折发展的消费过程中。
一、触觉、情动与生命力的唤醒
小说开篇,萨默斯太太意外得到十五美元后的消费计划与理智紧密相扣,她在作出决定前经过审慎的思虑:“她左思右想,有一两天都是恍恍惚惚的,一直在心里拿捏盘算。”直到为这笔钱“找到最合适、最明智的用途。”[7]258在这个阶段她最关心物的实用价值,附加于物之上的符号价值几乎没有被纳入思考的范畴,为贾妮买鞋要多花些钱是因为“贵的鞋子能多穿很久”[7]258,为孩子们多买几双长筒袜是为了让自己少做些针线活儿。她想到孩子们穿上崭新的衣物,便“满怀期待,躺在床上兴奋地翻来覆去,难以成眠”[7]258。叙述者指出萨默斯太太这桩具有阶级落差的婚姻造成其生活质量的断崖式下跌,而这种落差本身指向生活环境的改变。自然主义视角认为这种环境上的改变对萨默斯太太自我意识有决定性力量,但这似乎不足以解释她在后续消费中对符号价值与审美体验的主动追求;而这一阶段的消费计划在女性主义视角中是“丧失个体独立意识”的表现[1],萨默斯太太则是典型的为家庭压抑自我的美国平民妇女形象,因为妇德规范下的萨默斯太太已经完全把家庭的需求放置于个体之上,两相对比下,后续的放纵消费形成了被压抑的个体欲望的宣泄,这正言明萨默斯太太度过的是如此奢侈的一天,也成为真正为自己活的一天[8]。
何为主体性?在对萨默斯太太的已有分析中,“个体意识”和“自我意识”可被辨识为被压抑的欲望或对己身需求的满足,但主体话语本身拥有更复杂的话语谱系。20世纪的主体话语从静态的、自律的主体论转向主体与世界的联结、谋和与交融。19世纪末的现代理性主体观以笛卡尔的“我思”为核心,形成自律的、自足的先验个体理性。对于这种封闭的、静态的唯我论,海德格尔抛弃“主体”的概念,提出“此在”(Dasein)。“此在”呈现出“在-世界中-存在”的结构,人(存在者)总是在互相牵引之中打开(有意蕴的)生存空间或存在的可能,自身的构成与世间不可分[9]141。而梅洛庞蒂在现象学的基础上谈身体,他认为身体是“‘在世’的根本式样”[10]2,而机体与环境的关系并不是单向决定而是环形互动的,身体并非一件工具而是“我”与世界的某种中介,它动态改变着处境中的物体特性,并与物发生某种融合关系[11]。而这种“融合”的行动表明“在盲目的机制和理智的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经典的机械论和理智论都没有说明的定向活动”[10]2。
萨默斯太太购物前的目标导向十分清晰。不仅购买什么种类、性质的商品经过了审慎的考量,而且在购物方式上也是直奔主题,可以为打折商品“一连排好几个小时的队”,“只要能得到它,等多久都不在乎”[7]258。这是一种理性算计之后的目标明确、坚定不移的意志的力量,然而这种理性的表象与其后续的放纵消费之间具有一道明显的裂缝,计划与实施的南辕北辙或须回到萨默斯太太对现有处境的描述中寻找缘由,也就是梅洛庞蒂所说的“理智的行为”与“盲目的机制”之间的暧昧地带。萨默斯太太在邻人提起出嫁前的“好日子”时没有为此生发情绪上的涨落,因为“生活耗尽了她所有的精力。有时,她会觉得未来就像一只怪兽,暗淡、憔悴、面目可憎,万幸的是,她没有未来”[7]258。过去的好日子无暇顾及,未来也没有可期待之处,因为现下的生活已经将萨默斯太太生理和心理上的所有能量榨取一空,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消费活动发生之前。但是这次消费前的身体状态显得尤其虚弱,萨默斯太太为了照顾儿女和收拾家务,竟连午饭都忘了吃,到达商场时已经“有点头晕,又有点疲乏”[7]258。这时她的身体机能已经处于极虚弱的状态,购物当日因儿女众多而家务缠身的情况如同生活的缩影,连基本的进食都不能得到完全的保证。长期的匮乏感和当下的疲倦互相交织,萨默斯太太作为一个有机体的生命力与精神都已经处于极度衰竭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萨默斯太太脱下手套,触摸到了丝袜:
激动的人群把卖衬衫和印花细麻布的柜台围了个水泄不通,她找到一个相对冷清的柜台,坐到转椅上,深吸一口气(trying to gather strength andcourage),准备杀出重围。但她突然泄了气,整个人瘫软下来,随意(aimlessly)把手往柜台一搁。她没戴手套,忽然感觉(aware)碰到了什么手感绝佳的东西,摸着舒服极了。她低下头,看见自己的手正搁在一叠长丝袜上,旁边的标签显示丝袜正在打折:原价两块五,现价一块九毛八。柜台里那位年轻的女售货员问她想不想看看这些丝袜。她笑了,感觉那女孩就像在问自己付款前要不要再仔细瞧瞧这顶钻石王冠。她继续用两只手抚摸那些柔软光亮的高级织物(luxurious things),捧起它们,仔细端详上面细密的闪光,任它们像蛇一样滑过她的指尖。
萨默斯太太苍白的脸颊泛起红晕,她抬头望着那女孩。
“有八号半的吗?”[7]258
这一段落是小说中关键的转折点,也是萨默斯太太消费活动的起始点。女性主义批评和消费主义批评都注意到“蛇”这一意象的丰富意蕴,“蛇”作为一种修辞可引申出文学与宗教的种种故事,其中最重要的是亚当和夏娃在撒旦的诱惑下偷吃禁果,在消费主义视角看来“蛇”的意象指向难以抵御的商品的诱惑[3];在女性主义视角看来则是以原型来暗示女性意识对父权制传统的反叛[1]。这些说法都有其合理性,然而在意象的发散性指涉之外,段落中还存在对有机体生理状态转变的叙述。触摸到丝袜这一偶发事件让萨默斯太太从疲乏、泄气的状态转变到“苍白的脸颊泛起红晕”。不同于先前的理智计划和目标导向,首先,先于目的性、理性化的视觉,这里是手的触觉与物发生的关系;其次,摸到丝袜完全是“aim⁃lessly”的行动,是随机的、偶然的、无目标的。在自然主义视角看来,这一来自感官的偶发事件“引发的内在冲动左右了人物的行动”[3],但这“偶然”当中或许有更丰富的意蕴。摸到丝袜时,萨默斯太太的生理状况已经极度疲乏到需要“gatherstrength and courage”,也就是说萨默斯太太的消费行为需要积攒体力与勇气才能继续下去,对自身强调意志力的必要性已经说明身体状态处于强弩之末。在这种情况下萨默斯太太摘下了手套,生理感受在这刻被放大到极致,摸到丝袜时的“手感”和“舒服”来自意志与理智以外的肉身悸动。这种变化与德勒兹所理解的“情动”相契合,也就是存在之力(force of existing)或行动之能力(puis⁃sance)的连续流变[12]6,这种流变将身与心统摄到情感行为当中,强调的是人与人(物)、身体与身体(物)的平行感触[13]。萨默斯太太对丝袜的触觉是“肉身”受到物的不连续刺激下孕育出的感觉“团块”,知觉从混沌的、不确定的肉体中被框定而出。这种流动性的力量是“ 非表象”(nonrepresentation)的,即暂时没有进入“话语”的类似意愿或意志的效果和力量[14]。对丝袜的触觉是非形式的,非表征的,是前符号性的,是肉身(物)与丝袜面料(作为质料的物)发生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传递给她无形之形的单纯快感,实质是感知物发生中的“共振”,肉身和本不直接勾连的物并置,形成交错和碰撞,情动从而产生。萨默斯太太对丝袜的触碰以肉身参与将世界的可感性变成能感性,这种直感性经验将“丝袜”本身具有的符号属性和文化意义悉数剥离,将“丝袜”还原到一种“柔软光亮”的面料,像“蛇”一样具有光滑的、冰凉的触觉特质。触觉使混沌作为宇宙之力或强度重新返回到身体中,人与物的关联浮现出具有力的强度的情动,构成萨莫斯太太行为转变的关键机缘。萨默斯太太对丝袜的购买欲望源于对丝袜(物)的“占有”渴望而非对信息的短暂享用,这种占有具有私密性和内在性从而根本区别与信息的透明和共享。也就是说,“丝袜”此时不仅仅是可掌控的消费客体,而且作为“物”本身具有与人建立深刻关系的可能性,即本雅明所说的占有是“人们与物之间所能拥有的、最深沉的关系”[6]25。情动本身具有指向行动的潜能,作为一种伦理“使不可见的力可见”[5]51,期待超越当下的逻辑并在各种复杂因素之间建立联系[14]。萨默斯太太摸到丝袜时的悸动是未被社会文化规训定型的身体直感,指向行动的、朝向未来的可能性,即一种重新发现自己、作出行动的契机。对于这种流动性的力量我们尚且不能用合适的表象语言加以表象,这种非表象的表象化正是我们理解当下和朝向未来的过程[14]。而在小说中,触摸丝袜仿佛魔法般让处于“瘫软”状态的萨默斯太太一下子像通了电一样重新获得了饱满的生命能量。这是一种生命力的唤醒,就像她的另一篇小说著名的小说《一小时的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在得知丈夫意外死亡之后,她经历了一种身体的乏力,精神的困顿,然后意志力消解了,在她呆望着天空的时候,一种不自知的力量“从天而降,化作空气中的声音、气味和色彩向她涌来”,她突然意识到“自由”,“她的脉搏剧烈地跳动,血液在他体内流淌,给每一寸肌肤带去温暖和愉悦”[7]215。这种生命力的突然的非理性的唤醒也是个体从既定生活逻辑中逸出而意识到自身主体性的时刻。这也是当萨默斯太太作出第一个消费决定,解除了既有的与物的目的手段关系,而是一种更自由的与物本身的关系——即买下丝袜后的选择仍悬而未决,这意味着仍有无数可能性潜藏其中,而这种可能性正是建立主体之可能所在。
二、目光逻辑的介入与符号性消费的快感
从萨默斯太太意图为子女购买的“衬衫”“鞋子”“便帽”和“水手帽”到真正购买的丝袜都是具有商品属性的“物”。这些物本身具有共同点,即作为主体的占有物时,它们具有自身的命运,须承载时间赋予它历史的物质印记。在人的手、身体对这些贴身物的不断触碰中,它们会产生磨损、空缺、污迹,这些印记只可能在“物”之上铭刻而不能在一段信息上留下痕迹。但是这几件商品(物品)之间又具有细微的差别,萨默斯太太计划消费时对衬衫、鞋具等物品的考量更倾向于物本身的“效用和目的性”[15]。购买丝袜这一物品时则起始于肉身的悸动,丝袜在她看来像“钻石王冠”一样美丽,闪着“细密的闪光”,“钻石王冠”不仅仅意味着一种绝对的美,而且也意味着一种绝对的权力。丝袜这一廉价之物被提升到了一种绝对的美与力量的高度——它是不可比较的,它因为本身而具有一种绝对的价值,而萨默斯太太是因为这种丝袜本身的绝对的美而不假思索地想要拥有它。但与此同时,“钻石王冠”作为绝对权力的对象又潜在地是人人可以欲求的,它包含着一种欲望化的视觉幻象,中介了一种他者性的欲望。所以,一方面萨默斯与丝袜的关系是自由的,另一方面似乎又潜在地滑向了“对他者欲望的欲望”的消费逻辑之中。这种视觉价值“由它们的吸引力、灵气和气氛构成,它们服务于装扮和对生活的提升”[15],这种考量关注到物品中所蕴含的符号性的审美价值。萨默斯太太的后续消费逐渐从对物本身的自由的情动性的关系转向对物的符号性体验与想象性的身份认同。先来看看萨默斯太太消费丝袜后:
她躲在角落脱下棉袜,换上新买的丝袜,根本没过脑子,也没经过什么尖锐的思想斗争,更没刻意去想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她其实什么也没想。当时,她大概是给自己的脑袋放了假,放弃了艰巨而沉重的思考,彻底把自己交给本能的冲动,让它主导自己的行为,解除自己的责任。
天然的丝绸紧贴着皮肤,那感觉是多么美妙!她真想靠在带衬垫的椅背上尽情享受这片刻的奢侈。她靠了一小会儿,然后穿上鞋,卷起棉袜塞进包里,直奔女鞋部,坐下来试鞋。[7]260
萨默斯太太购买丝袜后径直走到一个小角落脱下棉袜,换上的新的丝袜。这一动作只为渴求再度感受“天然的丝绸紧贴着皮肤”的触觉。萨默斯太太对丝袜的感知形成重复性的动作,这时候她仍然“没过脑子”,“也没经过什么尖锐的思想斗争”,这种未经深思熟虑的知觉原动力体现了某种流动生成的、难以规定的潜能,这种力量被德勒兹称之为欲望。而对物的直觉性依恋与丝袜的品牌美学和符号价值无涉,但与其最本原的质感、面料有关。这种触觉凸显了通过身体和空间的混杂(Promiscuité)而形成的梅洛-庞蒂意义上的身体图式。梅洛庞蒂指出身体图式“并不是以经验主义者的方式表明身体图式是‘延伸的感觉’的拼凑物。它是一个向世界开放的,与世界有关联的体系”[16]190。这种将自身建构为身体的能力将感知到的丝袜质料(物)在身体空间中重新融合。身体图式的融合与变形在另一层面上是身体内部与外部系统之间的能量互换和动态变化,其中融注欲望本身的流变。萨默斯太太因其具有感知能力的身体而成为欲望主体,其欲望基于肉体性。肉身对物的感知也将感知物变成双重的,向外的内部探索和向内的外部探索同存于触觉当中[11]。当身体与物碰撞而成为欲望,也就形成萨默斯太太初次与丝袜接触的身体直感呈现出来的肉身悸动、脸庞红晕;萨默斯太太第二次对丝袜产生的欲望使其再次敞开感官,成为接合外部世界的努力。这种欲望在萨默斯太太对丝袜的两次感知中唤醒了萨默斯太太作为一个有机体的活力和能量,直观地表现为她在后续消费活动中的神采奕奕。欲望被德勒兹视作主体形成的内在动力,而人就是一架欲望机器。父系权力、婚姻契约和约定俗成的道德体系等作用力将个体收编为“贤妻良母”,而身体上的触觉指向主体的流动、偶然生成性存在状态,对父系社会下萨默斯太太所扮演的“贤妻良母”的身份认同进行了解码,产生了多种可能性。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萨默斯选择一个僻静的角落去享受丝袜接触身体的快感,而不需要他者的目光来获得这种快感,“占有的特征是私密性与内在性”[6]25,她通过占有实现与物的这种“私密性与内在性”。
然而这种私人性的享受只能成为“片刻的奢侈”,因为对感性身体的利用也是审美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焦点,丝袜这一物之上附加了天然的时尚性和审美要素,而当萨默斯太太一步步打造自己审美身体时,不能忽视她对自我形象的观看和审视。
观看之道在于自我观看与他者目光中建构起的自我形象,萨默斯太太的消费心理与这种目光伦理密不可分,她时刻在自我观看和虚拟或现实的的他者目光中建构起消费欲望。当她买鞋时:“她提着裙子,盯着脚上那双锃亮的尖头靴子,头摆来摆去,脚尖变化着方向。她的脚背和脚踝好看极了,好看得不像她自己的。”[7]260买手套时也写到萨默斯太太和女售货员“目不转睛地欣赏手套里那只匀称的小手,看得如痴如醉”[7]261;女性主义解读侧重于萨默斯太太对自身身体的欣赏和购买的物品特有的女性之美[1];自然主义的解读则关注到在这一消费过程中萨默斯太太身处的婚前常去的高档购物环境中,心态也因此回归到富家女的心态,“只关注商品是否中意,注意搭配、质量和时尚”[3]。这些解读都有其合理性,但具有一定的片面性,金钱和时尚衣物所代表的消费文化与女性文化如此紧密相连,如同发布这部作品的刊物《vogue》杂志本身以消费文化与女性文化交织而成一种暧昧语境,这种紧相连属使二者无法截然区分,而萨默斯太太为何能被“高档购物环境”和“时尚”轻易驱使也是一个有待思考的问题。
萨默斯太太“盯着”和“目不转睛地欣赏”的对象是穿上靴子和手套的身体。问题在于,当感觉“脚背和脚踝好看极了,好看得不像自己”时,观看的对象和自身产生割裂,这时是谁在观看?她在镜中发现和观看着另一个自我,这个自我是具有时尚美感的,与生活中那个饥饿的、受挫的、贫困的“我”相区别。在时尚或者说资本的逻辑中,尖头靴子、手套等商品形成一个镜像的装置,以便消费者获得一种理想自我的主体感。而这种观察的目光从根本上来说是将自己的身体客体化,肉身不再以感受的形式与世界产生联结,而是在视觉化的构造中以他者的目光将自己异化。也正因如此,触摸到丝袜时唤起的协调性的、完整的“我”也随之分裂。
目光的引入,也就意味着丝袜、手套、靴子甚至手里拿着的杂志不完全以物性吸引萨默斯太太的购买,关键在于这些商品内蕴着的与视觉紧密相连的符号性的审美内容和审美价值。细细考量,萨默斯太太所购买的商品从来不以单独的形式出现。实际购买的长丝袜与计划中为女儿购买的棉袜相对,新手套和以前偶尔买的“打折货”相对,新靴子和计划中为贾妮买的实用性强的鞋子相对,这些物品并不在初等功能中起作用,而是在一个二次度功能上起作用,那就是“个性化”的物品[17]155。构成时尚的也正是这种二次度功能,时尚定义了何为“光鲜亮丽的女人”。审美的决定权归结于社会上享有特权的极少数人,他们实验各种时尚风格,裁决合适的方法、款式和材质,定夺审美与时尚的流行方向,这种流行元素又通过Vogue 或萨默斯太太手里拿着的杂志影响个体的消费心理。萨默斯太太选择棉袜或丝袜、靴子或其他鞋子、羔羊皮长手套或打折手套,不论是出于母亲身份的考量还是为自己消费的意愿,都在这种似是而非的选择自由中进入到一整个文化体系当中,区别只在于她的选择到底指向贤妻良母抑或是时尚女性,而这两种属性都指向显化或隐藏的对生育价值的认肯。而且无论选择何种商品都会使萨默斯太太进入到整个经济体制当中,也就是说,在这种个性化的消费行为中,正是因为主体有一个成为主体的要求,她便把自己形成经济所要求的客体[17]167。这是从经济层面到文化层面形成的彻底的个人客体化。
萨默斯太太的消费计划被经济体制所定义的“光鲜亮丽”所拆解和过滤,她以为的审美选择其实早已僵化,只余下个体性的幻象。这一异化过程有其吊诡之处:“活的选择体现在死的差异中,而就是在异化的欢愉中,计划自我否定且感到绝望。”[17]168萨默斯太太看似自由的选择恰恰让她产生自我异化,同时丧失真正的行动能力。在异化的欢愉中她体验到为情绪消费的快感,这种稍纵即逝的快感为她带来建立主体性的幻觉,但这一过程恰恰是萨默斯太太丧失建构主体性之可能的过程。萨默斯太太触摸到丝袜时的情动是“身体的感触,这些感触使身体活动的力量增进或减退,顺畅或阻碍”[18]98,德勒兹在此基础上指出:“重要的是一个身体能做什么?”[19]13身体的感触与行动能力相勾连,身体感触不区分道德上的好坏,唯有适宜的际遇与有害的际遇,而这两者指向行动能力的增强或减弱[19]15。感性身体被消费意识形态所宰制,也就是说触摸到丝袜时的具有可能性的直感经验在满目缭乱的商品世界中被重新规定并塑造[20],指向行动之力的身体直感在审美消费中被暗中置换成可供消费的情绪和体验。商品带给人的快感在某种程度上将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和运行逻辑内化于人的感觉和爱,正如伊格尔顿所说:“能有什么纽带比由感觉、‘自然的’同情和本能联合结成的纽带更牢固、更无懈可击呢?”[21]94具体的物从与个体的占有式联系中脱身,指向消费的体验性快感。体验指向场景化和表演,其短促与不可留存意味着它无法与人建立更深层的联系,无法活化为真切长久的陪伴同时不会产生磨蚀与老化,而这种体验的可能性正强化了消费主义意义上的自由,即意味随机性和即刻消散的消费者自由。
三、消费的表演化中被规训的身体
萨默斯太太在实用性消费到审美消费的过程中,总以具体的“物”作承托。无论是“丝袜”或“棉袜”、便宜女鞋或“尖头靴子”、打折手套或“羔羊皮手套”,这些消费对象存在使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统一。直到萨默斯太太在高级餐厅进行消费,食物反倒是成为次要,审美和气氛被推到前台。而最后一个消费活动“ 剧院表演”中,其消费对象——戏剧表演完全剥离“物”的外壳,纯粹以信息和体验为待售商品。这个过程像是对物的舍离仪式,而萨默斯太太触碰到丝袜时的情动被商品逻辑重构为感性经验,通过气氛营造、场景化等手段为萨默斯太太提供短暂而虚幻的身份体验。
在萨默斯太太对物的消费中,已经隐隐期待着体验的快感。她在购买丝袜后直奔女鞋部,试鞋子时:“她眼光很高,售货员猜不透她的喜好,找来的鞋总不配她的丝袜。而且她也很难伺候。”在试完鞋子后萨默斯太太“告诉那位男售货员,她想买一双合脚又漂亮的鞋子,只要她满意,贵一两块也无所谓”[7]260。占据依附于物之上的符号时,萨默斯太太表现出与符号体系相称的富裕习性。也因此,只有购买了一身相衬的鞋袜手套后她才感觉“整个人仿佛有了底气,好像自己也是那种光鲜靓丽的女人”,餐厅侍者对她鞠躬道谢的姿态“仿佛她是位出身高贵的公主”。自然主义视角下,“出身高贵的公主”等词暗示了人物出身和贫富差距对人物行为的极大影响,进而深入阐释了萨默斯太太这系列的消费是特定环境下的特定心态和行为的自然回归[3];消费主义的解读在某种程度上与之相反,认为萨默斯太太这一系列在着装上的炫耀式消费并非完全由环境论主宰,而是有意地向路人表明自己属于有闲阶级的一员[4];近年有研究进一步从审美资本的角度指出萨默斯太太通过消费行为确认自我身份,指出这是社会结构造成的阶级区隔通过差异化的消费行为和审美趣味得以正当化[22]。
当萨默斯太太需要以衣饰这类象形符号来包装自己,才得以形似“有闲阶级”或“确认自我身份”,那么“好像”“仿佛”这些拟词正是在审美与信息构成的场域中,将萨默斯太太与“光鲜亮丽的女人”或“高贵公主”之间标识出隐含的裂纹与偏离。进一步说,尖头靴子、精致手套等商品具有表征时尚的符号功能,其中蕴含的美学内容和展示价值成为储存在物中的信息。信息与情动无涉,情动的基础是身体的感触,而信息指向符号的交换与情绪体验,于此人与物的碰撞及其所带来的可能性让位于体验的经济学。究其实质,时尚与否看似只与个体的品味相关,品味又归属于私人情感领域,但隐秘的事实是时尚/品味与审美资本的运作息息相关。布尔迪厄将品味视作一种铭刻于个人身体之内的区分性制度,他指出“‘眼光’是由教育再生产出的一种历史产物。今天被规定为合法的艺术认识方式,即审美配置,也是历史的产物。”[23]4具体来说同一阶级内的教育机制塑造出的阶级成员,一般来说具有相似的文化品味和审美选择。阶级区隔不仅体现在经济资本和社会地位,更存在于文化和审美领域。这意味着商品制造的带来区隔感的信息让身为消费者的萨默斯太太获得了高于贫家妇女的身份体验,换句话说,她获得了一次饰演有闲阶级的体验。她购买的不完全是物,而是情绪与信息。萨默斯太太通过嵌在物中的信息感知这些物,也通过消费这些物来将自己放置到场景中,并将自己场景化。
这种场景化和表演不仅在他者的目光中起效或得到肯定,而且导向了某种悖论性的目光。一方面,必须引入他者的目光后表演才得以生效。萨默斯太太在一系列消费后经过每个十字路口“都会把裙子高高提起”[7]261,好让新靴子、手套和丝袜同时展露。人来人往的马路成为萨默斯太太展示的舞台,这一具有表演性质的动作暗示了她希望这身新装得到他者目光注视,也就是通过物本身向他者传递出具有区隔感的信息,甚至连同自身成为他者眼中的某种场景化的美学景观,以具身化的形态将自身构筑为一种社会符号。值得注意的是,早于萨默斯太太制定消费计划时已有他者的目光参与建构欲望。在盘算了具体详细的实用物消费后,萨默斯太太想到打扮一新的孩子们时激动莫名。这一段英语原文中的表述是“thevision of her little brood looking fresh and dainty andnew for once”,“vision”和“looking”等词暗示了萨默斯太太的愿景与视觉化的感知相勾连,指向由欲望想象出来的画面。画面中,核心是主体与他者的欲望关系——她希望孩子们穿得崭新漂亮,在这个场景中的重点不完全是她所“希望”的内容,即孩子们得到的物质享受;更是这种“希望”的形式本身,即其中内蕴着的萨默斯太太渴望从中获得的身份认同——一个能把孩子们照顾得很好的、无须为金钱发愁的母亲与妻子。这是萨默斯太太在他者的欲望质询中占据的位置与作出的回应,也就是齐泽克说的“主体的欲望就是他者的欲望”[24]230。令萨默斯太太感到兴奋的朦胧希冀指向齐泽克意义上的围绕虚无(缺失)而形成的换喻游戏,欲望建构的逻辑隐秘地驱使其心理-行动。提起裙摆的小动作泄露同一种逻辑主宰的秘密。萨默斯太太的主体性建构与目光伦理紧密结合,只有在主体间性的社会符号网络中占据一个位置,才能获得一种大他者的凝视。理智主宰的消费计划与真正的消费活动相对比,区别只在于她所占据的位置发生了改变,其身份认同从“萨默斯太太”转变到“光鲜亮丽的女人”。而这两者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客体化,也难以将与自由相联系的行动去改变自身所处的困境。
吊诡在于,萨默斯太太需要他者目光的同时“惧怕”他者的目光。步入高级餐厅时“起初还怕引人侧目,但她走进餐厅却没有引起任何震动”,等餐时仍点明“所有人都在安静地用餐,根本没人盯着她看”[7]261。从十字街道到高级餐厅,这种对目光的渴慕和规避并存的感知指向了某种隐形的区隔结构,也就是以更高的消费门槛制造的隐形的社会区隔的媒介。
在这一异质场所中,只有排除餐厅顾客的打量目光才得以说明她自然地成为有闲阶层的一员,但这种自然本身又已经过了萨默斯太太在他者目光中对自己的微调和安排。高级餐厅不仅仅为解决饱腹的生理需求而生,更由“完美无瑕的花缎餐巾、晶莹剔透的水晶杯盏,还有侍者迈着轻盈的脚步为上流人士服务”、“柔美动听的音乐”和“窗外吹来的微风”[7]261构成某种叠合着复合型欲望的场所。审美、资本逻辑和消费在此间形成复杂的勾连,灯光布设、器具摆置、侍者的贴心服务无不表明精致气氛的人工营造性,而这也表明高级餐厅不完全是吃饭、休息的场所,也是资本进行审美操控的场所。居于此间的萨默斯太太敞开自身而形成处境性的身体际遇,身为贫家妇女却可通过消费而获得短暂而虚幻的体验。然而在体验的强度中,萨默斯太太真实的生理需求被非强制性地、看似自愿自然地隐没,即使她一天都没有进食,也只点了些精致的吃食如“半打蓝点牡蛎,一份猪扒配水芹”、“外加一杯莱茵红酒,餐后再来一小杯黑咖啡”[7]261,并感到由衷满足。其自身在表演中从情动的存在转变为“景观所指向的展示型目标和异化性需要”[25]。
萨默斯太太从餐厅出来后,驱使她为剧院表演而付费的直接原因是:“她的钱还没有花完。接下来,她被一张剧院海报所吸引,想好了下一个去处。”[7]262去剧院的动机并非出于自己真实的诉求,而是因为手头还有金钱。还有金钱就意味着她仍可以短暂享受操纵自我的虚幻性快感,而被海报所吸引去消费则是商品世界所带来的完全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氛围中,昂贵衣饰、身体和物品作为一种符号不再指向某种确定的意义,因此可以自由地、无限地替换,从而在纯粹的交替中引出某种差异游戏。这种无目的的目的性迫使我们接受“各种形式的参照理性的断裂”[26]。至此,萨默斯太太在消费中不断获得的眩晕式快感已经完全消融了理智的盘算、计划,在金钱主导的结构性差异中短暂地居于高位成为最重要的身份体验。
在这种体验中,商品的场景性功能尤为关键。在高级餐厅消费时,萨默斯太太尚且点了一些食物,但是在“剧院表演”这一消费活动中甚至没有提到具体的戏目。文化变成了商品,变成了一段体验,但这体验却与其所奠定的共同体价值和文化源泉无关。重要的是在剧院表演中萨默斯太太得以彻底地沉浸入气氛和场景:“萨默斯太太那么在意周围的环境。她把剧院里的一切——舞台、演员还有观众——统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细细品味。”[7]261台上之戏已经无法调动她的情感,情感也不再是德勒兹意义上的人类存在方式,而成为一种表演的形式。萨默斯太太跟着身旁的时髦妇人或哭或笑,但真正打动她的是时髦妇人递给她的“ 一方香气四溢的蕾丝薄手帕”和“ 一些糖果”[7]。在剧院中,不仅台上需要舞台设计,台下甚至整个场所带给消费者特定的“第一性的整体性空间情调的情调感受”[27],这种气氛需要与主要消费者——为“显摆显摆自己华贵的服饰”的“打扮入时的妇人”[7]261相契合,只有如此才能为有闲阶级的显现创造条件。波默指出“场景化涉及的是某种普遍化的商品美学精神———商品美学的目的在于制造气氛———,因而涉及的是一种情感基调之精神———我们在这种情感基调中接纳世界、各种场景及其中的个别之物,特别是接纳商品。”[20]在剧院中,情感、气氛和商品巧妙地融合为不可拆分的一体,情调和氛围成为萨默斯太太的主要消费品,而其身体与情感也在愈来愈强烈的消费体验中被改写与重新形塑。然而这种体验带来的身份认同也是短促的、难以为继的,小说末尾“戏剧落幕,音乐停止,观众纷纷离场,仿佛做完了一场美梦”[7]261,剧院中的戏剧表演结束,随着金钱耗光萨默斯太太也须从消费场域退出,搭电车回到以往的生活中。电车上有个男人饶有兴致地观察她,萨默斯太太自己的或是他人的目光始终隐现于文本中以至于成为某种结构性的重复,在目光中人们微调自身的形象与欲望,交换时尚符号及附加于之上的区隔性信息。但直到最后这个难言的目光,也始终读不懂萨默斯太太的神情或心理,它不刺穿任何意义,只成为一个漂浮的、空洞的眼神。
结语
萨默斯太太生活中客观存在着女性困境。她无名无姓,仅以丈夫之姓作为自己的称呼,其家庭生活更是困窘难堪。而在消费中“贤妻良母”的身份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被松动或者说被解码了,这也是女性主义解读的侧重点;但很快资本主义商品逻辑将其再编码或说“辖域化”为一个嵌入时尚符号秩序的、追求体验的消费者,消费主义解读的焦点则在于此。
其实在编码和再编码之间存在一种流动、生成的状态,即萨默斯太太触摸到丝袜时形成的情动。以身体直感为基础的情动唤醒了她的生命力和能量,这种产生于身体的情感感触具有力的强度,期待更多的可能性甚至隐隐指向一种具有独立人格的、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生活。然而逃逸线之不可能性在于人与物碰撞而成的身体直感很快被消费主义所俘虏,被重构为商品世界中的审美的、感性的经验,非表象的、未被话语框定的情动也在被收纳入表征世界时弥散。具体的物在消费过程中逐渐退出,而审美消费和信息消息使萨默斯太太愈加深入地卷入符号的法则与游戏。这种虚幻的身份体验并不挑战阶级秩序,而只是通过场景化和表演的形式,以美学方式进行自我满足和自我层叠,短暂地体验一个富裕的、光鲜亮丽的人生切面,然而这种消费体验带来的是更分裂的、不协调的主体性。在今日,审美和数据化被推到更加瞩目位置,信息更进一步地穿透物。人与物、人与世界如何在消费社会中建立更为自由的联系,仍是绕不开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 尹静媛,艾险峰.一双丝袜折射出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凯特·肖邦《一双丝袜》之女性主义解读[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S1):101-103.
[2] STEIN A. Kate Chopin’s“ A Pair of Silk Stockings”: The Marital Burden and the Lure of Consumerism[J]. The Mississippi Quarterly, 2004, 357-368 (3).
[3] 申丹.女性主义和消费主义背后的自然主义:肖邦《一双丝袜》中的隐性叙事进程[J].外国文学评论,2015(1):71-86.
[4] 曾桂娥.消费的牢笼:论凯特·肖班《一双丝袜》中的炫耀式消费[J].名作欣赏,2010(5):83-85.
[5] 弗朗索瓦·祖拉比什维利.论“感—动”(Percept)的六则笔记:批评与诊断的关系[M]//汪民安,郭晓彦.生产(第11辑):德勒兹与情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6] 韩炳哲.非物:生活世界的变革[M].谢晓川,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3.
[7] 凯特·肖邦.觉醒[M].齐彦婧,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20.
[8] 刘辉.十五美元带来的意识觉醒:从“一双丝袜”看妇女的家庭责任与个人追求[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S1):155-156.
[9] 张祥龙.海德格尔传[M].北京:商务印书局,2017.
[10] 莫里斯·梅洛-庞蒂.行为的结构[M].杨大春,张尧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1] 李钰辉.梅洛-庞蒂与拓扑学[J].哲学研究,2023 (4):91-101.
[12] 吉尔·德勒兹.德勒兹在万塞讷的斯宾诺莎课程(1978-1981)记录[M]//汪民安,郭晓彦.生产(第11辑):德勒兹与情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13] 汪民安.何谓“情动”?[J].外国文学,2017(2):113-121.
[14] 张锦“. 情动”与“新主体”:德勒兹与福柯:一种朝向未来的方法论[J].东南学术,2020(5):206-214.
[15] BÖHME G. The Aesthetics of Atmospheres[M]. translated by Jean-Paul Thibaud. London: Routledge, 2017.
[16] 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局,2001.
[17] 让·鲍德里亚.物体系[M].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18] 斯宾诺莎.伦理学[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19] 吉尔·德勒兹.德勒兹在万塞讷的斯宾诺莎课程(1978—1981)记录:1978年1月24日情动与观念[M]//汪民安,郭晓彦.生产(第11辑):德勒兹与情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20] 刘毅青,吴昊.气氛美学:作为感性学的美学重构及其批判性[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57-67.
[21] 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M].王杰,傅德根,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2] 董雪飞.习性、趣味与象征资本《: 一双丝袜》的阶级区隔[J].外语研究,2020,37(2):97-100,111.
[23] 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M].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局,2015.
[24] 斯拉沃热·齐泽克.快感大转移[M].胡大平,余宁平,蒋桂琴,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25] 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文本解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6] 让·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27] 贾红雨.感性学:美学传统的当代形态:格诺特·波默“气氛美学”研究[J].文艺研究,2018(1):17-25.
【责任编辑:王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