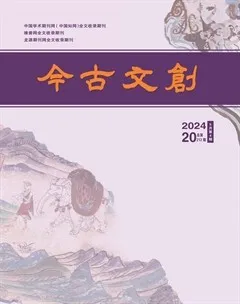荒原的咆哮
2024-06-28金子涵
金子涵
【摘要】1847年,天才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出版了第一部作品《呼啸山庄》。100年后,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深入人的潜意识,提出关于欲望的理论。回看《呼啸山庄》,欲望叙事是贯彻其中的隐含叙事路线。本文从拉康的理论出发,重审主人公被压抑的、被构建的、虚无的欲望,进而为解读书中人物心理、文化隐喻与种族征服提供了理论视角。
【关键词】雅克·拉康;欲望叙事;种族征服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0-0032-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0.010
一、返回的被压抑者——永不满足的欲望
在19世纪中叶,正值英国工业革命的狂飙期,大英帝国版图不断地扩张,征服地域和种族被看作光荣使命。[1]与此同时,在文学作品上,成功文学风气盛行,膨胀的时代充斥着膨胀的欲望。艾米莉始终冷冷地注视着外面喧嚣的世界,求助于狂风呼啸的荒野,试图寻找生命的力量。出于这样的背景,《呼啸山庄》的欲望叙事开始了。
拉康关于欲望的理论核心是“缺失”或“剥夺”的概念。也就是说,当遭受“缺失”或者“被剥夺”时,人的欲望便开始膨胀。得知原本与自己心意相通的凯瑟琳在画眉山庄居住几日后答应林淳的求婚,缺失感几乎要把希刺克厉夫压垮。压抑并不意味着被压抑者的消失,而恰恰意味着被压抑者的返回——夺去林墩的至亲,诱骗其妹伊莎贝拉,奴役辛德雷之子。希刺克厉夫采取“以牙还牙”式复仇,试图以高经济地位的主导姿态抹灭林墩带来的社会性压迫感。[2]
“我倒不懂,这一头头发没叫他害头疼。就像小马的马鬃那样披在他的眼睛上!”[3]通过林墩的描述,再加上小说中一再被称呼的“吉普赛人”,暗示了希刺克厉夫的边缘民族身份。而辛德雷和埃德加则作为欧洲传统白人男性的两类代表:或残酷野蛮,或温柔优秀,他们象征着传统优势父权文化。而作为边缘民族人,显然希刺克厉夫拥有自然的生命力,不同于英国传统白人男性的他被排挤在主流文化之外。与其说他的复仇是丧失理智的疯癫,不如说是在强烈欲望驱动下对制暴者的抵抗和颠覆。维多利亚时代,传统英国白人父权地位大都是通过武力夺取方式实现,希刺克厉夫这一边缘者以相似的方式成为制暴者,进入了权力中心。“现在我嫁给希克厉,那可辱没了自己。”[4]这是凯瑟琳对接受林墩求婚的解释,也是社会对异族文化的他者的标签。
作为“缺失”的边缘者在情欲与权欲推动下,以返回的复仇者身份确立了新的家族父权秩序——掌握经济大权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暴力王国。
当他成为了权利话语者,看似自己欲望得到满足。但真的会满足吗?
凯瑟琳的爱与尊重是希刺克厉夫匮乏的原始欲望,在这一欲望对象匮乏状态下不断通过压迫、夺取的方式转移欲望。拉康认为,这种欠缺,不是缺这个或那个,它不是任何一个实存性的客体能够使其满足和完整的欠缺,而是一种本质性欠缺,拉康称其为“存在性欠缺”。经过这种处理,欲力在拉康那里成了以“欠缺”或说“匮乏”的形式起着动力源泉的核心装置。[5]
故而,无论希刺克厉夫怎么努力转移欲望,原始欲望永远匮乏、永远无法满足。
女主公凯瑟琳,虽然只存活在叙述者口中,但她的独特在场具有很强的解读性。同希刺克厉夫相似,她也是返回的压抑者。选择嫁给经济富足的林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改变希刺克厉夫的处境。没有对自己以及对社会有着清醒认知的凯瑟琳选择压制住内心对男主人公的爱,压抑住本质上的野性、自然之气,真正走进象征社会文明的画眉山庄。但当希刺克厉夫再度出现时,她变成了压抑的返回者。“她呢,一直盯着他看,好像生怕她把眼光一移开,他就会消失似的。”凯瑟琳的欲望再也无法满足,哪怕她努力告诉自己:我是林墩的妻子,哪怕她不断转移欲望,但匮乏的原始欲望仍然不断折磨着她。
二、幽灵的在场——他者的欲望
凯瑟琳为什么内心深处爱着希刺克厉夫却选择嫁给林墩,嫁给林墩后依旧放不下希刺克厉夫?这一问题是小说情节的重点探究点,也是凯瑟琳欲望的表层体现。“人的欲望就是他者的欲望,因为人总是欲望他者所欲望的,人总是欲望成为他者欲望的对象,人总是在他者的场域中欲望。”[6]这是拉康对人的欲望的一个拓扑学定义,其核心是人的欲望是被建构的。在无意识中,欲望是转喻,症状是隐喻。
凯瑟琳的欲望是成为富太太与和希刺克厉夫在一起的矛盾欲望。维多利亚时期,社会强调家庭是不可侵犯的,妻子应该是温柔体贴的,优雅端庄的。欧洲传统父权文化被塑造成优雅理性的,通过宗教、道德教化等方式向整个社会传送父权文化的讯息,女性常常被教化成恪守父权道德规范的贤妻良母。与此同时,传统父权的巩固通过牢牢掌控经济主导权来实现。这种意义上,嫁给富太太的表层欲望是由男权至上、金钱至上的社会构建的。但从小到大身边所有人都对她说:要乖一点,一位优秀的女性应该是什么样时,她的表层欲望就此被构建。然而,凯瑟琳身上有着反传统的自然气息。
“在她听到人家把希克厉叫做一个‘下贱的小流氓”,和“比畜生都不如”的地方,她留神着别做出像他那样的举动来。可是回到家里,她才不高兴讲究什么礼貌呢;因为讲礼貌只落得旁人的讥笑;她也不肯收敛自己的不受管教的本性了,因为那样做并不会给她带来什么称赞和声誉。[7]”
凯瑟琳幼时并不是别人家的乖孩子,相反她的身上有着难以去除的野性。面对父亲这一强大的家族男性权威,她常常挑衅的姿态应对。她的父亲曾无奈说:“我不能爱你,你比你哥哥还要坏。”[8]而面对家族继承人——传统英国男性代表辛德雷时,她在日记中表述自己和希刺克厉夫要反抗。某种角度上,与希刺克厉夫相爱相守的欲望固然包含两性吸引的因素,但其背后亦是一种文化上合谋的构建。并不甘心被传统男权体系驯服的凯瑟琳看到了与她相似的异族人希刺克厉夫,本质上她们是一类人,都是传统男权话语体系下的被压迫者。作者艾米莉本人就是非传统的作家、非传统的女性,不愿合群,不擅交际,迷恋自然野性的生命力,她同样是位不愿被社会框架束缚的女性。因此可以相信,凯瑟琳与希刺克厉夫的爱有着文化隐喻的深层意味。与希刺克厉夫相守的欲望一定程度上是女性反叛意识构建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
同样,作为文章核心人物的希刺克厉夫的欲望亦是“他者的欲望”。在阐释他的欲望是如何被构建前,了解希刺克厉夫人物身份的隐喻性以及故事所内藏的民族情结尤其重要。艾米莉·勃朗特是爱尔兰裔作家。爱尔兰——英国最早的殖民地,希尔承认:“爱尔兰是保证大不列颠取得世界霸权的那个体制的最大受害者。”[9]“几百年来英国已经剥光了他们的本土文化,以一种人所共知的现代主义方式使他们的民族身份陷入巨大危机。”[10]在殖民者的强势文化强烈冲撞着被殖民地文化时,勃朗特姐妹不自觉地关注着爱尔兰与英国文化冲突问题,尤其关注爱尔兰裔生存问题。在《呼啸山庄》中,到处可见爱尔兰大饥荒的隐射。希刺克厉夫被老庄主带到呼啸山庄时,他肮脏不堪,同时他在利物浦被捡——这是背井离乡的爱尔兰人所到达的第一站。对大饥荒惨状的暗示并不是巧合,这是艾米莉作为爱尔兰散居裔作家对英国殖民的控诉。当然,也可以揣测出主人公希刺克厉夫实则是爱尔兰人:故事中希刺克厉夫渴望读书,渴望通过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渴望配得上凯瑟琳,但作为话语中心的辛德雷剥夺了他从牧师受教诲的机会,这一情节不正是历史上爱尔兰天主教徒被禁止入学的写照吗?
在这一意义上,希刺克厉夫渴望颠覆与重构话语体系的欲望实则是被构建的欲望,是有着深层民族叙事意味的欲望。艾米莉通过该希刺克厉夫的模拟反抗戏拟了英国实行殖民统治的手段。希刺克厉夫颠覆英国主流话语权的欲望实则隐喻着爱尔兰人争取反抗与平等地位的欲望,艾米莉用隐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和为解决英爱矛盾提出的设想模式。[11]
如果是希刺克厉夫的欲望是他者即爱尔兰裔(甚至于作家本人)的欲望,那么作品中两位英国白人文化的代表者:辛德雷与林墩的欲望则是维多利亚时代下英国帝国主义的欲望。辛德雷将自己视作家庭话语、社会话语的中心,对自己的妹妹凯瑟琳以强硬手段压制着,更不用说对外来者希刺克厉夫的辱骂了。他迫切地想要铲除在呼啸山庄里一切阻碍他统治话语权的事物。由于妹妹凯瑟琳总是顶撞他,父亲又疼爱异族希刺克厉夫,所以这两个“反叛者”就成了他对付的对象,而他本人将这样的“对付”看作是拯救妹妹和希刺克厉夫的荣耀使命。这一点上正是英国在殖民扩张的写照,英国帝国主通过海外殖民途径实现阶级跃迁。
有趣的是,尽管电影《呼啸山庄》历经无数次改编,但几乎每一次都暗含了原著中极具哥特小说特征的“幽灵”。无论是故事中的主人公还是艾米莉·勃朗特,甚至是无数读者,似乎都在这般幽灵的窥视下。故事中的“幽灵”正是始终存在的欲望。他者的欲望始终如同幽灵跟随着故事里的每一个人,在这一层面上,所有人的欲望是在社会大环境下被构建的欲望,或巩固秩序,或颠覆秩序。而千百年来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本身也成为了“历史的幽灵”,以难以驯服的反抗性、反殖民压迫情节不断打破符号秩序,向主流文化权威发出挑战。
三、欲望的虚无与不可妥协——补偿叙事
“死亡”是《呼啸山庄》自出版以来被热议叙事艺术。《呼啸山庄》的阅读过程如同静卧荒野之上,狂风在耳边呼啸而过。大量人物似乎在一个阴暗之日死亡。自凯瑟琳病故后,书中的许多人物都相继离世,像是中了魔咒一般。凯瑟琳面对本我欲望与外在束缚的冲突下陷入混沌矛盾之中,最终死亡结束了她的苦痛;希刺克厉夫即使成功占有了呼啸山庄和画眉山庄,即使看似复仇成功,但仍然陷入欲望迷网。不难发现,“死亡”对于凯瑟琳和希刺克列夫而言是解脱,是无法满足的、被构建的欲望最终得以虚无的终了。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中提到:我们的生活仅仅是通向死亡的条条迂回曲折的漫长道路。[12]凯瑟琳的死亡是文本叙事意义暂时终结,她的死似乎意味着此前一切欲望的幻灭。艾米莉赋予凯瑟琳不甘被主流父权秩序束缚的野性,但从社会语境来看,处于维多利亚时期父权意识形态中的女性,她无力挣脱父权话语。因此,当她妄想通过嫁给林墩改变希刺克厉夫的经济处境后,她发现一切都是徒劳,被构建的表层欲望——贤妻良母再也无法困住内心深层欲望——颠覆父权话语,自由享受人生,于是她崩溃之下唯有选择死亡让这些缠绕的欲望、不可妥协的欲望“覆灭”。
同样,当复仇计划实现后,希刺克厉夫陷入了与凯瑟琳相似的痛苦处境。他发现内心对凯瑟琳的爱的欲望以及真正获得美好生活的欲望困扰着他,他避无可避地感受到一种虚无感。作为想颠覆传统父权话语的异族人,成为新的父权中心并不是他的初心,只有死亡才能结束他个人意义上所有不可得的、又无法妥协的欲望。两位主人公的死亡隐约透露出作家意识形态与内心情感的焦虑。
布努艾尔导演《呼啸山庄》,又名《情欲深渊》,正如片名所隐射的,欲望与毁灭、虚无相耦合,精神分析上的“返回的被压抑者”和叙事上“施暴的回归者”、电影中“空间破坏者”合二为一。[13]欲望以毁灭者的表象出场,作为被毁灭的对象落幕。在法国导演里维特的改编电影最后,希刺克厉夫躺在凯瑟琳当年卧室中,窗外树枝摇曳、窗户破碎,死去的挚爱凯瑟琳的手伸了进来,希斯克利夫努力去握。此刻,镜头切到了窗外,只有一条孤独的伸向虚空的手臂——似乎在为欲望的招魂。
欲望最后沦为虚无,这似乎在经典文学的定律,也是人生的映射。《金锁记》中曹七巧将子女长白、长安看作“金钱同质”欲望对象的替代品。由于丈夫残缺的身体,她在初始欲望对象匮乏状态下不断寻找替代物,在《金锁记》最后,“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从受害者到加害者,她们似乎永远找不到自我。欲望最后沦为“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虚无。
但艾米莉没有沉溺于短暂的虚无感中,取而代之的,故事最后小凯瑟和哈里顿的故事体现了艾米莉探索可能性的诗学艺术。她并没有仅仅在小说中为爱尔兰民族遭受的不平等对待表达“对宗主国的愤怒和爱尔兰散居族裔崛起的期望”[11],更深层次体现了她对和平途径的思考,她在小说中试图打造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人物自然地相爱,尽情表达生而为人的欲望,而非在社会话语体系中被构建的欲望;在这个世界中,没有种族、阶级之差别,不再有仇恨。她想告诉读者:或许复仇并不是真正反抗殖民的途径,跳出狭隘的民族观,用爱与理解,才能真正获得一致的尊重。这也恰恰是艾米莉的伟大之处。
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小凯茜和哈里顿爱情产生地为呼啸山庄,脱离了象征现代文明体系的画眉山庄,两人身上的自然人性才得以书写。由此,可以说所谓大团圆结局并不是艾米莉的妥协,而是一种补偿。缠绕强烈欲望,被压抑者永不满足的欲望,作为幽灵始终在场的他者欲望,以死亡终了的虚无欲望,都指向不可妥协的欲望。不可妥协的叙事背后是艾米莉隐藏在爱情线下的种族政治与民族叙事。如何正视欲望,又如何合理处置欲望?艾米莉为大家提供了现代性答案。《呼啸山庄》作为世界文学史研究经典,对它的研究呈现出开放性的姿态。作为维多利亚时期的天才爱尔兰裔女性作家,身份的多样性使她的小说也呈现多样性的风采。传统父权话语下弱势群体的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下边缘民族的呐喊……这些都融入到欲望叙事中。她坚守、独立、自强、永不妥协,她绝对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反而对自然人性抱有乐观态度。
参考文献:
[1]于承琳.《呼啸山庄》中的社会流动与帝国逻辑[J].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3,(04):21-33.
[2]姜吉林,赵莉萍.对父权文化的抵抗和颠覆——论《呼啸山庄》的叙事政治[J].妇女研究论丛,2010,(03):67-72.
[3]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M].方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10.
[4]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M].方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280,138.
[5]胡成恩.精神分析的神话学:拉康欲力理论研究[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199.
[6]胡成恩.精神分析的神话学:拉康欲力理论研究[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401.
[7]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M].方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246:157.
[8]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M].方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89,101.
[9]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58.
[10]伊戈尔顿.历史中的政治、经济、爱欲[M].马海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1]刘涛,邓云华.《简·爱》和《呼啸山庄》里隐藏的“爱尔兰情结”[J].湖南社会科学,2018,(05):171-177.
[12]SigmundFreud,JenseitsdesLastprinzips,ed.cit.,248-249,Beyondthepleasureprinciple,ed.cit.,71-74.
[13]刘岩.幽灵的重返与重构——《呼啸山庄》电影改编研究[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3,(06):3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