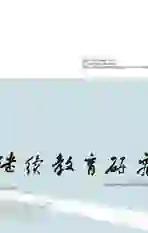中国终身教育体系建构的时代理路
2024-06-14王星炎
摘要:在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复兴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终身教育的文化选择、实践主体及基本动力将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也显现出前所未有的新趋势,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实态化。以时代理路的尺度,去廓清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内在逻辑,审视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现实焦点,谨慎地提出以“文化创新”为体系构建的纲领、以“实态推进”为体系构建的抓手、以“全员参与”为体系构建的基点等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中国;终身教育;体系建构;路径
中图分类号:G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24)06-0023-06
终身教育是为人类新文明时代准备的教育体系,而不是原有教育与新型教育的嫁接体[1]。在终身教育国际化与中国化的新时代,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也显现出前所未有的新趋势。这种新趋势既是对以往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批判与审视,也蕴含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新局面与新未来,因此,有必要从时代理路的视域,阐明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内在逻辑,廓清体系构建的现实焦点,思考体系构建的可能路径,为中国终身教育的科学发展注入些许新思维。
一、中国终身教育体系建构的逻辑思辨
终身教育作为一个思想引领和发展方向,已经深深融入我国教育改革发展中,并成为现代化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2]。进入新时代以来,各类终身教育的理念层出不穷,学术界对于终身教育的理念也进行了更深层次的辨析与思考,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思维与见解,使得对于中国终身教育概念体系构建的认识也更为清晰与系统起来。
(一)中国终身教育体系建构的概念审视
从本然意义而言,终身教育与其他类教育的概念有着本质差异,至少涉及三个方面:
一是属性的差异。终身教育不仅是一种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更是一种与自然和社会同生共进的原初概念,在整个教育领域内处于主体位置,而其他教育概念均由它衍生,并处于从属地位。在中国教育领域内,终身教育虽无常形,但有着客观性和普遍性,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清晰触摸到它无所不在的衣袂。二是价值的差异。与其他类教育“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或“满足市场需求”的价值目标不同,终身教育直面不断变化与转型的社会发展,总是以不断变革与创新的体系建设去适应社会的变化,并通过及时调整体系构建的走向以及纳新的社会要素,在历史潮头上全面展现自我社会价值。三是范畴的差异。每一个教育类型都有自我特定的边界与范畴,并以此为自我生存与发展主要平台。而终身教育则突破了边界与范畴的制约,以“人类共同体”的气势,不仅将所有的教育形态融为一体,更是面向社会,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文化建设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中极其重要的环节。
在上述意义上,终身教育作为顶层概念,其所诉求的体系构建不仅是一项教育变革活动,更是一项宏大的文化创造行为。近代社会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成人教育的空前发展推动了现代终身教育理念出现,这种变化标志着在“一次性学习时代的终结”的同时,“终身教育”“学习化社会”时代的到来[3]。终身教育不仅强调要通过对成人教育、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远程教育、农村教育、老年教育、扫盲教育、人才教育、弱势群体教育、社区教育、继续教育、回归教育、幼儿教育等的重新整合与广度汇集,构建一种高度开放、深度交互、全面协调的社会教育体系,还要求在传承中国传统终身教育文化的平面上,对诸如孔子关于“学而不已,阖棺而止”的教育思想、荀子关于“学不可以已”的教育理念、朱熹关于“教育阶段论”的论述、近代陶行知关于“我们要求的是整个寿命的教育”的教育观念,进行现代化改造,生成新的文化元素与文化成果。现有史料也佐证,从中国文化史发生的多次重大终身教育事件来看,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总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互为因果,二者之间没有顺序关系,或传统文化发展促进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或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推动传统文化进步,从春秋时代的“公学与私学共存”到“书院教育与启蒙教育同步”再到近代的“实业教育与学历教育偕行”,莫不如此,从更为纵深的视角共同彰显出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文化属性。
(二)中国终身教育体系建构的社会基因
如何与新时代发展相适应,这是中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重点与难点。体系建设作为终身教育发展的首要标识主要取决于两个社会生态的建设。一是文化生态,是指终身教育在国家或地区范围内长期发展中所积淀的社会价值观、人们参与的程度、展开的行为方式及其习惯倾向。文化生态对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具有基础性和持久性影响。在终身教育发展的初期和中期,不同地区终身教育发展的形式大同小异,表现出“同一性”的发展态势,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就是明显的例子。而进入近现代后,不仅不同国家终身教育表现各异,就是一个国家内不同地区的终身教育也有不同,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不同国家或地区文化生态的差异,即文化生态差异性决定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二是资源生态,是指社会资源与终身教育发展和体系构建需求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既包括国家和各级政府所提供的大政方针、法律法规、宣传导向等软质资源,又包括教育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等硬质资源。这些资源生态作为终身教育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其所表现的差异性与特殊性,在生成不同国家或地区终身教育缤纷特色的同时,也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产生差异性影响。
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一个基本国情和突出优势就是:终身教育文化底蕴厚重和教育资源丰富,且在原始社会时期,中国终身教育文化已然萌芽,产生了以“伏羲教民以猎”“神农教民农作”“后稷教民稼穑”“仓颉造字”为代表的原初终身教育文化,之后又历经两千余年的持续发展与不断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终身教育文化传统。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不但加大了终身教育的物质资源投入力度,更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持续为终身教育的发展提供政策制度与法律法规上的支持,使得终身教育有条件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体系建设的基本目标,生成更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终身教育发展生态。
(三)中国终身教育体系建构的理论假设
“后学校化”理念为教育体系要素变革提供了更多必要性与可能性,终身教育理论为教育体系要素变革提供了学理依据,终身学习理论还进一步补充并发展终身教育观念,使“终身学习”成为全球广泛共享的教育目标之一,进而逐渐成为教育政策制定的规范之一[4]。随着终身教育思潮越来越深度地融入社会各个领域,国家和社会对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尤其是如何通过终身教育体系的科学建构与合理布局,充分展现终身教育“处处可学、时时能学、人人愿学”的鲜活特色,必然要求从理论的高度,廓清终身教育体系建构的时空分布与层次形成、政策供给与制度安排、内容架构与实施过程、方式选择与行为推进、社会参与资源整合等诸多要素,剔除构建过程中不必要的变量,围绕事关体系构建的本质特征与关键环节,与时俱进地实现与新时代社会发展大趋势接轨,而不是把若干教育形态简单地叠加在一起。只有这样,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才能在适宜的环境中畅行无阻,最大化地释放自身活力和增强凝聚力。很显然,这种理论假设对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提出了新诉求与新思路,因此,要以更为开放的视野、更加创新的理念、更新的行为方式,推进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特别是在以新的构建思维取代原先有效但现在已逐步过时的构建观念时,更要以一种“大破大立”的理论自信,促进终身教育各个板块内和各个板块之间的重组与协同,保证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
从理论假设着眼,中国终身教育体系应由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老年教育等五大模块有序组成,其中,学前教育模块包含幼儿及辅助教育,基础教育主要是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涉及职业高等教育和学历高等教育,而成人教育则覆盖成人职前教育、成人职后教育、成人学历教育、成人社会教育等,老年教育包括老年休闲教育、老年社区教育、老年艺术教育等。这些教育模块的发展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既相互衔接又相辅相成,但在具体实践中各自的主体与价值取向则大不相同,如学前教育发展的启蒙本位、基础教育发展的增智本位、高等教育发展的成才本位、成人教育发展的人力本位、老年教育发展的养成本位。在这些模块的排序中,学前教育与基础教育是前沿,高等教育与成人教育是中继,老年教育则是收官,共同组成中国终身教育共同体。
二、中国终身教育体系建构的现实观察
终身教育是个体或集团包含一生的、人性的、社会的和职业的过程,包括正规的、非正规的以及不正规的多种学习形式,是一种综合和统一的理念[5]。终身教育体系构建要素的深刻变化,必然导致终身教育体系基本格局的重大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是文化选择、实践主体及基本动力均发生极大变化,需要从新时代的站位,对这些变化进行一个更为纵深的现实观察。
(一)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文化底色
将何种文化作为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底色,是一个学界和业内争议不休的现实问题。一些人认为,终身教育作为专有概念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文化,是由保罗·朗格朗提出的,并在1972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中,建议把终身教育作为各国今后制定教育政策的主导思想。虽然将西方文化作为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底色,是有现实依据的,但从历史辩证的视角,既要关注终身教育的概念起因,也要观照它的思想与实践的源起。终身教育思想内核自古有之。徐莉和肖斌提出,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提出的人生修养“阶段”论便是对终身教育思想的论述,庄子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揭示出教育应贯穿人的一生[6]。何思颖和何光全认为,终身教育经历了“从古老观念的复兴到现代概念的厘定再到理论体系化”的发展过程[7],因此,将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底色是应有之义。虽然不能否认西方文化尤其是现代西方文化对国际终身教育事业所作出的努力与贡献,承认引入和借鉴西方终身教育成果与经验对中国终身教育发展的重要意义,但这些并不能作为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必须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理由。
唯物主义教育史观认为,教育文化具有明显的不可复制、不可交易、不可蹴就的特性,终身教育文化尤甚。任何国家或区域的终身教育都有其独特的发展历史,所有的发展历程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迁,要为各国家或地区不同程度地铭刻下厚重的印记,并转化为特定的文化元素,深刻影响着国家或地区终身教育发展的观念、方式、行为、趋向,进而决定终身教育发展的国家或地区文化特色。这些文化特色又深刻地影响着后继终身教育的发展,使得终身教育与特定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联系更为密切,除了要履行自我应尽的职能与责任,还要承担更为重要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生成一种“以文化发展引领终身教育、以终身教育促进文化发展”的良性循环。在此意义上,如果脱离中国终身教育赖以生存且具有悠久历史传承的本土文化传统,去奢谈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文化底色,就必然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淖。
(二)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实践主体
“谁是体系构建的主体”问题,既事关中国终身体系建设成败,也是社会和学界争议最多的难点问题。从哲学意义上看,任何事物(虚态与实态)的存在,必然有一个主体作为支撑,否则这个事物的存在就是空泛的,也不可能持久,尤其是在一个事物的实态转化过程中,明确谁为主体的问题就显得极为重要和迫切。为此,一些人提出了“共同主体论”,认为在终身教育领域内,所有教育模块都处于平等地位,模块之间没有主从关系,共同为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服务。还有一些人提出了“成人教育主体论”,认为从顶层概念上分析,终身教育还可以分为“未成年人教育”和“成年人教育”。二者之间,无论是教育属性、教育对象、教育特色还是教育范畴,“成年人教育”显然更与终身教育的原则与初衷相契合,已具有作为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主体的资格与要素。当然,这里所讨论的“成年人教育”并不是理论意义上的专业学术概念,而是一种相关教育实体的集合,其中,成人教育(或成人继续教育)居于中枢位置,并有逐步覆盖所有成年人教育模块的趋势。近年来,成人教育进高校、成人教育进职教、成人教育进社区等实践活动的兴起,就是成人教育张扬终身教育主体地位的显证。
从唯物主义实践观视角来看,在终身教育已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终身教育作为一种原则去指导各类教育的发展虽然很重要,但与终身教育在国家战略中所承担的使命与责任还有较远距离,要办好“人民满意的终身教育”仅有某些原则是不够的,也不能充分展现出终身教育“社会性、广泛性、实用性、长期性”的特色,需要有一种相应的教育实体作为终身教育转化的现实基础,即“从顶层设计上打破教育资源融通的制度壁垒,做好搭建终身教育立交桥的衔接工作”[8]。在众多教育模块中,成人教育(或成人继续教育)从本质、目标、范畴、功能、关系等要素相比较,尤其是成人教育“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本质属性、“有教无类”的发展纲领、“诲人不倦”育人精神以及“教育对象的广泛性、教育过程的终身性、教育内容的实用性、教育目的的多样性、教学方法的多元性”等基本特征,与终身教育的理念、原则、特质、要求高度吻合,有着其他教育模块所不具备的鲜明优势。尽管社会和学界关于“成人教育是终身教育的火车头”的争论还在继续,但成人教育(或继续教育)模块作为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实践主体,已是不争的事实。
(三)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主要动源
“以什么为主要动源”,这既是困扰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重要问题,也是社会和学界普遍关注的焦点所在,在业内更是存在诸多不同的声音。一些人提出了“政府动能论”,认为发展终身教育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政府通过出台相关政策方针、建立相关制度体系、供给相关法律法规、投入相关教育资源,推动终身教育发展,可以说政府职能是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主要动源。也有人提出了“市场动能论”,认为市场需求不断增长,既吸引了更多的教育机构参与终身教育实践,也带动了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终身教育领域,直接促进了终身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成为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主要动源。不可否认,上述观点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也是当前中国终身教育发展的事实,但是否二者就是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主要动源,还有很多可商榷的问题。相关调研表明,尽管各级政府对终身教育的发展下了很大气力,市场需求也有明显增长,但事实却不尽如人意,在一些教育领域内,终身教育原则或要求只存在于规划、总结、口号之内,甚至蜕变为一种业绩装饰,并没有落到实处,更谈不上惠及社会全体成员了。
显然,还有更为主要的动源存在。从“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终身教育既是社会发展重要组成,也是历史发展的重要事件,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终身教育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体系构建也是一句空话。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体现了国家教育事业发展与人民群众期待的一致性[9]。相关史实也佐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正是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包括扫盲教育、农民教育、技术教育、职工教育、干部培训教育等具有鲜明终身教育属性的各类成人教育蓬勃发展,才描绘了中国终身教育史的辉煌篇章,创造了世界终身教育史上的奇迹。这也表明,在新时代条件下,终身教育只有政府的职能或市场需求的推介,极易僵化为一种教条,局限于某些教育领域或校园之内,丧失应有的锐气与活力。这也意味着,终身教育只有跨越校门进入社会,始终将发展的重心放在人民群众之中,以特色的理念指导群众,以丰硕的成果感染群众,以普惠性、特色性和大众化的实践项目吸引群众,生成一种“人人自觉参与终身教育”的社会生态,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才会拥有用之不竭的发展动力。
三、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基本路向
我国推进终身教育的整体目标尚未在各参与主体间形成聚合力[10]。衡量和推进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与教育变革,我们需要用终身教育的意蕴来重构教育与社会发展内在关系的理论,进而创造在重构理论指导下的变革实践[11]。终身教育体系构建作为一项重大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指导与预设已然成为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重要手段,必须因时应势,根据国情及终身教育发展的走向,提出应然的预设思考。
(一)以“文化创新”为体系构建的纲领
教育现代化既包括现代性对传统性的改造与改变,也包含对优秀传统的传承与弘扬[12],将文化传承创新作为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纲领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的必然。从中国文化史上看,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终身教育文化源远流长,无论是王朝的变迁或是外族的入侵都未曾中断,历经两千多年而不衰。在剔除诸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糟粕后,所蕴含的终身教育理论与实践,集中反映了终身教育的基础特征,深度阐明了终身教育体系最基本又最普遍的结构与框架,全面廓清了终身教育的边界与范畴,尤其是所倡导和践行的“立志教育、立德教育、立身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更是创造了中国终身教育发展及体系建设的早期辉煌;否则,仅作为一种教育理念或教育形态就不可能流转千年而存在。这也强烈表明:中国终身教育的发展及体系构建不仅需要现代教育思想的指导,更要立足本土文化传统之上;不仅要以传承与创新中国传统终身教育文化,作为衡量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水平与层次的主要尺度,更使之成为从根本上改变以往终身教育体系构建过程中存在的“以西为主”的认识偏失、“视度不清”的方向模糊、“校园化”的资源布局等问题的现实依据。
建立“文化共同体”是终身教育文化传承创新的应然之举,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改造传统文化要素。既要对传统终身教育文化中关于“教育与社会相联合”“教育与人的成长相协和”的文化元素进行全面改造,将现代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教育精神、教育纲要植入其中,转化成现代文化元素,也要对那些难以转化的“教育与政治相契合”的特质文化元素,加速“文化变革”步伐,对那些为封建社会和封建统治服务的文化元素,通过“基因介入”“内涵重组”“结构改良”等方式,使之演化成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的新型文化元素,最大化地实现传统文化为现代终身教育发展服务的战略目标。二是集合业内文化资源。要在全社会范围内突破行业界限,在“兴家风、淳民风、正社风”号角下进入社会方方面面,对社会和业内相关的文化资源进行全方位整合,尤其是要对那些以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为主体的校园文化资源进行深度置换,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原点上,与其他社会文化资源互动,大胆吸纳哲学文化、企业文化、行业文化、政治文化、科技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最新成果和前沿,通过借鉴与创新,生成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所需要的理论文化、职业文化、政治文化等元素,丰富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文化结构。
(二)以“实态推进”为体系构建的抓手
“实态推进”是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本质体现。其初衷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以往终身教育发展中出现的“重理念原则、轻实践行动”的局限,从中国终身教育发展历史上看,这种实态化进程一直没有停止过,进入新时代就显得更为迫切。传统终身教育的实态化进程大致遵循以下两种路线。一是通过理论研究与传播去影响社会。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国终身教育理论初具雏形后,历朝历代的相关学者总是以“一边改造原有的理论要素、一边创造新的理论体系”的形态,使终身教育理论更为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为更多的社会成员所认同,其中,以孔子的“论语”、朱熹集注“四书五经”、王阳明创立“心学”的社会影响最大和持续时间最长,为终身教育的实态推进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二是以教育实体的扩张去覆盖社会。历代先贤总是将教育实体的扩张及改革,作为推进终身教育思想的主要载体,从春秋战国时期的以私学为主的“门派教育”到隋唐之后的书院教育及私塾教育再到近代的乡村教育,无不是以倡导终身教育为己任,以发展终身教育为使命,为中国终身教育持续两千多年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实态推进”过程中,理论研究与传播是动力,教育实体扩张是载体,通过二者之间的相互衔接、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构建传统终身教育体系,使终身教育在全社会范畴内成为不同文化、不同阶层、不同需求的社会成员的共识与自觉。
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终身教育的实态推进,除了要继承以往“理论创造与实体拓展”的两条腿走路的优良传统,还要在终身教育理论成果与实践成果的积累和转化上下大气力。应该看到终身教育目前还处于成果匮乏的状态,虽然随着终身教育的发展,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也不断延伸,发刊的论文与出版的著作在数量上相当可观,但罕见国家层面的重大成果,难觅具有时代意义的倾力之著,极大降低了终身教育的学术价值与社会形象。要进一步完善终身教育成果创造与转化机制,既要加强终身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协调配合,又要增加终身教育理论与实践成果创造的周期要素,根据国家终身教育发展战略要求,动态调整重大成果的立项率与成功率。在此基础上,还要注重新成果的利用与转化,诸如理论成果转化为社会成果、学术成果转化为文化成果等,实现成果总量调控与系统性转化的有机结合,并在终身教育体系构建中设置“内在平衡器”,促进终身教育的实态化推进。
(三)以“全员参与”为体系构建的基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13]。这里强调的“全员参与”,并不是纠结于那些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成员参与人数的多寡,而是诉求以“全员参与”为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基点,深入更为宽广的社会界度,尤其是走进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社会群体的职业生活、劳动生活、家庭生活、文化生活、情感生活、学习生活、闲暇生活等,了解和揭示他们在终身教育发展引发的种种社会变迁的面前,是一种什么样的国家认识与行为方式、什么样的人生目标与职业操守、什么样的人生态度与价值展现、什么样的理想信念与团队精神、什么样的社会理念与文化意识、什么样的岗位需求与组织观念。当上述问题获得切实诠释或深度解码之后,必然促使更多的社会成员认同终身教育和参与终身教育,“全员参与”不再是个目标理想,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存在。这也意味着当下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亟须解决的,并不是表象宏大或是走向僵化的理论推进,而是对终身教育社会主体的深切关怀。
一是促进政府职能与终身教育发展相协同。各级政府相关终身教育职能的发挥,尤其是政策法规与制度建设的供给,在保障终身教育稳定和科学发展、提升终身教育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同时,对终身教育还有指导、组织、实施的作用,因此,要通过对政府职能与终身教育关联性与溢出效应的评估,强化政府职能的宏观杠杆作用,避免出现政府工作滞后于终身教育发展的负面窘况。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是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质量需求的重要途径,仅通过正规教育机构的力量,难以满足时代和群众的需要[14]。二是促进终身教育发展与社会需求相协同。终身教育不再以满足某些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或个体的需求为目标,而是一种惠及全民的“教化社会”行动,在把政教风化、德教感化、身教淳化等有形与无形的要素综合一体的前提下,把满足社会发展趋势与要求作为自我发展的终极目标,并在终身教育与社会发展的碰撞和交汇中,产生新的教育思想,生成新的教育形态和教育模式,使终身教育呈现出时代性亮色。当然,上述协同并非主观臆测,更不是率性而为,而是建立在大量研究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与协作,对当前社会发展和未来的形势进行的合理判断。运用大数据选择终身教育发展的量化指标,形成对终身教育发展的合理预期,并以此作为决策终身教育发展的依据。
参考文献:
[1]徐莉,杨然,辛未.终身教育与教育治理在教育现代化中的逻辑联系——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的思考[J].中国电化教育,2020(1):7-16.
[2]王敬杰.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指标架构、建设成就和优化路径——《教育规划纲要》十年回顾与展望[J].职业技术教育,2021(7):19-24.
[3]李兴洲,耿悦.从生存到可持续发展:终身学习理念嬗变研究——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7(1):94-100.
[4]ASPIN D,CHAPMAN J,HATTON M,et al.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Lifelong Learning[M].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1:405-406.
[5]吴遵民.现代国际终身教育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13.
[6]徐莉,肖斌.新时代终身教育的理性遵循与价值诉求[J].中国电化教育, 2022(6):37-46.
[7]何思颖,何光全.终身教育百年:从终身教育到终身学习[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9(1):66-86.
[8]吴遵民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终身教育的历史回顾与展望[J].复旦教育论坛,2018(6):12-19.
[9]史秋衡,季玟希.新时代教育体系要素变革的理路[J].高等教育研究,2022(7):14-21.
[10]袁雯,刘雅婷,马颂歌.教育即终身教育——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终身教育变革[J].教育研究,2023(6):138-146.
[11]叶澜.当代中国教育变革的主体及其相互关系[J].教育研究,2006(8):3-9.
[12]陈乃林.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与全民终身学习探索[J].当代职业教育,2022(6):4-12.
[13]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N].人民日报,2022-10-26(1).
[14]高巍,何雨丹,李欣雨.我国终身学习政策何以落地?——从制定到实施的路径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23(28):65-71.
The Rationale of the Era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Wang Xingyan
(College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54, China)
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Chinese culture, the cultural choice, practical subject and basic power of lifelong education in China will undergo significant chang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shows an unprecedented new trend, the most prominent manifestation of which is the actualiz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This paper tries to outline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and examine the reality of the focu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by the yardstick of the rationale of the era. It cautiously puts forward the possible path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such as taking “cultural innovation” as the program for system construction, “actual promotion” as the grasp of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full participation” as the base of system construction.
Key words:China;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Pat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