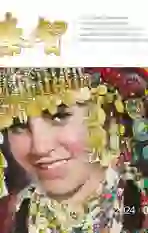袭警罪司法适用问题探析
2024-04-13唐磊
[摘要]袭警罪中的暴力袭击行为应具有对人的攻击性和主动性,但不能有突然性及伤害结果等条件作为限制,因此驾车拖拽行为应属于暴力袭击。对袭警罪法定刑升格条款进行把握时,应当注重手段与结果的关系,在兼顾民警损伤程度的同时,还需结合行为人在行为时主观上的恶性、客观上所处环境、暴力袭警的手段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关键词]暴力袭击;辅警;加重;法定刑升格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20122/j.cnki.2097-0536.2024.03.005
从袭警罪设立后的司法实践来看,从袭警罪设立之初将所有针对公安机关的暴力均认定为袭警,转变为轻微的暴力与反抗,排除在暴力袭击行为之外的审慎认定。司法机关也在不断的反思与完善该罪名构成要件的认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以下三个争议较大的问题:一是为逃避处罚驾车拖拽民警的行为定性;二是辅警是否属于人民警察;三是法定刑升格条款的适用条件。这三个问题,各地法院作出的认定及判罚均不甚一致,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袭警罪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及研究,以期解决上述之争议并为适法统一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一、“暴力袭击”的含义及理解
从袭警罪的法条表述来看,“暴力袭击”是表述的核心。但《刑法》的表述出于简洁性及规范性并未对暴力袭击的方式、程度作相关具体的规定;另外,对于如何来理解暴力袭击,实践中的观点各不相同。因此,为解决拖拽行为是否属于暴力袭击,有必要先行对暴力袭击的这一概念进行解读和分析。
(一)“暴力”的解读
暴力的对象是“人”而非“物”。从“暴力”一词的文义来解读,泛指通过武力侵害他人人身、财产、精神的行为。从刑法的体系来解读,所规定的“暴力”大部分均是对被害人的“身体施以外在有形力的打击或强制”[1]的“硬暴力”。根据暴力的对象,可以从覆盖面的广度将其分为四类,但笔者认为暴力的对象只能是“人”,其理由在于,法条对于袭警罪的描述是“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条文表述的本身就已经明确规定了袭击的对象是警察这一“人”,而非“物”;同时,两高一部《关于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也对袭警罪的“暴力”作出了解释,将“暴力”限缩于对民警人身进行攻击。有观点认为若采纳“狭义暴力说”,在打砸警车中,只有砸破警車伤害到警察时才能认定袭警罪;笔者认为,尽管该暴力行为从形式上看是一种间接暴力,但因物与警察人身紧密结合,打砸警车在本质上还是属于直接攻击警察人身的行为,虽然没有直接对人的身体造成伤害,但也需要被看作是针对“人”的暴力行为,仍属于狭义的暴力层面。
暴力程度具有妨害公务的抽象危险即可。学界对此问题,主要分为抽象危险说和具体危险说两种学说,主要争议在于暴力是否需要足以阻碍警察执行职务。笔者赞同抽象危险说的观点,即无需阻碍,理由在于:首先,从文义角度,法条并未要求暴力足以阻碍执行职务;其次,《指导意见》中亦未对暴力的程度作出规定;最后,若要求暴力必须足以对人民警察执行职务造成阻碍,则必将导致违法成本的降低,变相导致鼓励行为人破坏民警执行职务。
暴力行为应具有攻击性,但不能要求有伤害后果的发生。有学者主张司法实践可以将袭警罪中的“暴力”具体划定为轻微伤以上,但不能包括重伤及以上的程度。[2]但笔者并不认同该观点,如行为人持管制刀具追砍警察,因其过于紧张导致未能砍中,若主张必须暴力行为需要有伤害结果的发生作为限制条件,则该具有高度危险性的持刀挥砍行为将不能被评价为暴力行为,这是十分荒谬的;故在袭警罪中,暴力行为不需要一定存在伤害结果,而需要综合分析行为人的手段、方式等要素。
(二)“袭击”的理解
“袭击”一词,从文义的理解来说就是“乘敌人不意或者不备突然实施攻击的作战行动。是进攻的基本方法之一。目的是打敌措手不及,快速歼敌,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3]据此,部分学者主张袭击行为需要具有突然性和不可预见性。[4]
但从文义理解上的“袭击”一词,明显系战争及军事层面的用词,将其理解贸然作为法律层面上对“袭击”的解释,会不合理的限制袭警行为的范围。例如,行为人与警察对峙后,多次扬言要攻击,然后实施了攻击行为,此时若因行为人的攻击行为不具有突然性、警察已有了预见性,就将其排除在袭警行为之外,明显是不符合常理和认知的。
据此,笔者认为,“袭击”在此应强调的是行为的主动性,即行为人主动、积极实施的行为。例如,在《指导意见》中所列举的“撕咬”“踢打”“投掷”“打砸”均为主动实施,是一个积极的身体动作,而非被动的消极反抗行为。
(三)关于驾车拖拽的行为定性
通过上文对“暴力”及“袭击”要素的分析可以合理得出,暴力袭击行为对象是人,同时该行为应具备攻击性和主动性。行为人为逃避处罚,实施了驾车拖拽警察,从主观上看,明知自己的拖拽行为可能会导致警察被带倒受伤的危害后果,仍放任了这种危害结果发生,系间接故意;从客观上看,驾车拖拽行为系行为人主动实施的,以将车辆作为犯罪工具、通过加快车辆的速度对警察造成伤害,并非消极的、被动的反抗,而是具备攻击性。因此,驾车拖拽行为在主观上有袭警的间接故意,客观上具备攻击性和主动性,应属于暴力袭击行为。
二、人民警察范围之界定
(一)辅警身份问题的由来及争议
上文中已明确,暴力袭击的对象是人,也就是警察;但如何去界定警察范围,一直是司法实践中极具有争议的问题,该争议主要集中在辅警人员的身份上,也就是说暴力袭击辅警的行为是否也能够视为袭击人民警察。辅警在执法活动当中分担了警察职能的一部分,作为辅助民警执法的一线工作人员,随时面临着不法侵害,因此如何正确认定辅警的身份问题对于袭警罪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辅警的身份认定问题,学界目前存在三种意见,即否定说、肯定说及折中说:否定说认为袭警罪的对象只能是人民警察;肯定说认为人民警察不限于身份,需要判断辅警人员是否正处于执行公务的状态中;[5]折中说主张需要同时考虑职务与身份,即辅警在与民警执行职务时是否可以视为执法的共同体。
(二)辅警不能认定为人民警察
对于辅警的身份认定问题,笔者认为辅警在任何情况下均不能被认定为人民警察,其理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就身份而言,辅警并非人民警察。按照我国《人民警察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来看,人民警察的范围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由于该定义采用列举式的规定,辅警从任何角度来看都不属于警察的一种。在《刑法解释》中,对一个问题如果能通过文义解释得出合理结论时,就无需通过其他方法再进行解释,否则就可能涉及不当的扩大、缩小,甚至类推解释。因此,在《人民警察法》已对警察进行了定义,且不存在理解上的争议时,就应采纳该定义,而非另行再进行解释。
2.从袭警罪的立法目的能够看出,设立袭警罪是希望能够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保障在执行公务中的警察的人身安全。有观点提出,袭警罪保护的法益仅能是社会公共秩序。笔者认为,社会公共秩序是通过执法行为来保护的,而执法行为是由警察来具体实施的;对于社会公共秩序的破坏,体现在对警察执法行为的破坏上,同时必然涉及对于执法主体的侵害;因此,暴力袭警行为侵害的是“复合法益,也就是暴力袭警行为同时侵害了执行公务(社会秩序)和警察的人身安全的復合法益”,[6]而辅警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没有执法权利、不具有人民警察身份,当然无法认定为人民警察。
3.从《刑法》的体系上来看,在法条的表述中用到“人民警察”的罪名共有五个,分别是武装叛乱、暴乱罪、投敌叛变罪、袭警罪、招摇撞骗罪以及非法生产、买卖警用装备罪,在这五个罪名中关于“人民警察”的定义及内涵应当是一致,且与其前置法《人民警察法》中的“人民警察”的定义亦当一致。倘若在袭警罪中对“人民警察”的范围进行扩大解释,那么根据《刑法》体系的协调性,在其他的四个罪名中自然也应当一并予以进行扩大解释,但这种扩大解释对于其他四个罪名明显是不当的且与前置法相违背。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在现有的相关法律已对人民警察的概念进行定义的情况下,企图通过进行解释的方法来消除辅警成为袭警罪犯罪对象的争议、将辅警纳入警察之范围的方法恐难行之有效。这种方式看似维护了辅警权益,实则突破了“人民警察”的法定概念,走向了类推解释。因此,笔者建议立法机关应在修订法律时考虑将辅警纳入袭警罪的犯罪对象来解决该争议。
三、袭警罪法定刑升格条款的适用及认定
袭警罪法定刑升格的条件为:“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该条款在司法实践中的争议主要集中于“等手段”和“严重危及”这两个要素上,下文将逐一进行分析。
(一)“等手段”的理解
1.“使用”是“等手段”的判断前提。“使用”一词在法条中作为开篇,承接后续的暴力手段,作为动词强调的是行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故在对于“等手段”的判断上,应当将“使用”与“携带”“持有”等概念进行区分,若行为人没有以使用的方式发挥工具应有作用的行为和故意,那就无需进行后续“等手段”的判断。举例而言,若行为人携带管制刀具,后用拳击方式袭击人民警察,因行为缺乏对于管制刀具的使用,因此不适用袭警罪法定刑升格条款。
2.对“等手段”的理解应坚持同质性解释。袭警罪的法条表述,在立法上采用了“手段列举+兜底”的方式,例如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通过对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四种行为的列举,来明确“其他危险方法”的行为性质。因此,对于“等手段”兜底的外延范围判断时,应与明示罗列的加重与升格手段进行相当性比较,实现法益保护目的的统领和例示条文的限制下进行同质性解释。[7]从法条当中规定的三种方式可以看出,使用枪支、管制刀具和驾驶机动车撞击均有严重暴力性和人身危害性,因此在对“等手段”进行判断时,必须将行为的暴力性和人身危害性与法条列举的三种行为进行比较,只有具有相当的暴力性和人身危害性时才能适用该条款。
(二)“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判断
1.与“等手段”的关系。笔者认为“严重危及人身安全”与手段绝非强调的关系,只有在两者同时符合时才能适用袭警罪的升格条款,也就是说在袭警的过程当中需要通过枪支、管制刀具和驾驶机动车撞击来完成袭击行为,并且所采取的行为对警察的人身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举例说明,甲为逃避检查驾车撞击同向进行拦截的乙驾驶的警车后侧,在该情形下并不会给乙带来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具体危险,因此无须适用法定刑升格条款。
2.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把握。因目前尚未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于“严重危及人身安全”这一要素进行规范的解读,因此对于这一基本取决于人的主观性判断的要素。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该要素的把握,不仅要考虑人民警察所遭受的损害,同时还需要考虑行为人在袭警时的主观恶性、客观上所处环境、暴力袭警的手段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参考文献:
[1]刘艳红.刑法学(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280.
[2]李翔.袭警罪的立法评析与司法适用[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2,37(1):105-118.
[3]夏征农,陈至立.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6):2462.
[4]刘艳红.袭警罪中“暴力”的法教义学分析[J].法商研究,2022,39(1):15-28.
[5]段甜甜.袭警罪的刑法教义学分析[J].山西警察学院学报,2021,29(2):30-36.
[6]简雯琪,赵杨.袭警罪的法教义学再审视———以“暴力”相关问题的解释切入[J].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22,21(2):46-51.
[7]梅传强,刁雪云.刑法中兜底条款的解释规则[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7(3):110-121.
作者简介:唐磊(1993.3-),男,汉族,上海人,法律硕士(法学),研究方向: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