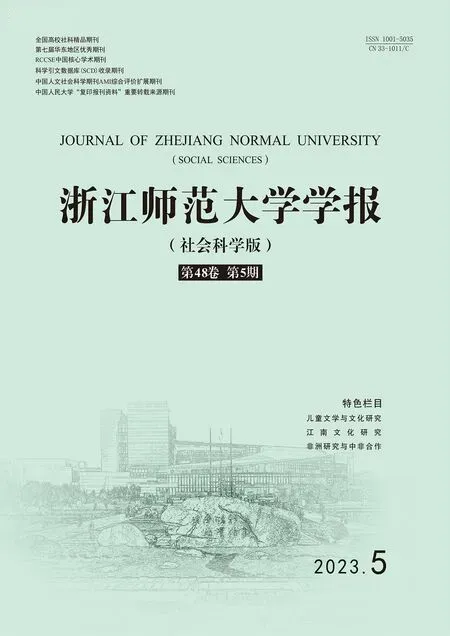以爱代恩与幼者本位:论鲁迅的父子观及其实践
2023-12-29徐仲佳
徐仲佳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433)
父子关系是礼教秩序中重要的一环。作为礼教基础的三纲包含着父子的关系规范,“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者张也”。[1]316父为子纲,即父亲有对儿子的绝对支配权:“父子者何谓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子者,孳也,孳孳无已也。”[1]316父亲是儿子行为规范的制定者,儿子则是宗族的传承者。父亲的绝对权威表现为对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和对儿子人身的处置权。如《礼记》言:“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2]“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3]
儒家文化最初对父子关系的阐述虽有等级之分,但也有双向的义务限制:“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4]父慈子孝的双向性随着儒家文化逐渐成为王权专制的护符而日益被弱化,父子的等级制关系则一步步强化,直至绝对化为父权高于一切。三纲学说的提出是为维护王权专制统治服务的。其中所强调的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等差与王权专制的等级秩序是同构的。例如,“夫臣之事君,犹子之事父”[5]便是将君臣关系与父子关系联系起来。宋代以后,随着儒学的理学化、王权专制日益严密,父子的等级制度越来越偏枯:父亲的权威被强化到空前的高度。罗从彦(1072—1135,字仲素,号豫章先生)提出“天下无不是底父母”。[6]在民间甚至出现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极端说法。因此,父子的等级制可以看作王权专制的基石之一。
“三纲”学说出现之初,有恢复社会统治秩序的历史合理性。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这种建立在严格等级制度基础上的绝对支配关系已经完全不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在传统中国现代转型期,随着个性主义思潮进入中国,它受到了颠覆性的冲击。鲁迅的父子观及其实践是这一颠覆性变化的一个例证。
一、父子关系的创伤性记忆
鲁迅的童年和少年是在礼教制度支配之下度过的。“父为子纲”的家庭伦理曾经给他带来创伤性记忆。《五猖会》(1926)是《朝花夕拾》中的一篇。《朝花夕拾》中的材料来自鲁迅内心深处无法忘怀的记忆。这些记忆之所以难以忘怀是由于它们曾经在鲁迅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笔之于书的这些生命印记中有美好温馨的,如《无常》中对乡间赛会的热闹场景的深情追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为一个荒园增光添彩;更多的还是在鲁迅生命历程中抓铁留痕的创伤性记忆,如《二十四孝图》《五猖会》《父亲的病》《琐记》等。
《五猖会》记述了鲁迅幼年的一次创伤经历。文章述说自己童年时因家居城里无法亲睹东关五猖会的盛貌而遗憾,充满了对迎神赛会的渴盼。好不容易有一次亲赴赛会的机会,父亲却偏偏在出发前要“我”背诵什么“粤有盘古,生于太荒,首出御世,肇开混茫”[7]262直至太阳高升,磨灭了“我”的兴致。它对幼年鲁迅的心理造成巨大的伤害。根据西格蒙·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创伤性记忆很容易进入作家的文学实践,成为文学创作的源头。《五猖会》中记载了幼年鲁迅如下的创伤经验:从初听到要背书时的“忐忑着”、到初读时的“担着心”、再到得知要背诵二三十行书时的无奈——“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有什么法子呢?”[7]262最后是看着时间一点点过去的绝望。下面这个细节尤为细腻:
应用的物件已经搬完,家中由忙乱转成静肃了。朝阳照着西墙,天气很清朗。母亲、工人、长妈妈即阿长,都无法营救,只默默地静候着我读熟,而且背出来。在百静中,我似乎头里要伸出许多铁钳,将什么“生于太荒”之流夹住;也听到自己急急诵读的声音发着抖,仿佛深秋的蟋蟀,在夜中鸣叫似的。[7]263
静肃的气氛、照在西墙上的朝阳、清朗的天气、众人的沉默与“我”极力要夹住那些并不理解的字句的慌乱、急急诵读的发着抖的声音构成了一幅令人绝望的图画。时光过去了接近四十年,这一幅图画仍然能够清晰地被描绘出来,由此可以推想出当年它给幼年鲁迅带来了怎样深巨的伤害。当幼年鲁迅终于完成了背诵任务之后,他原先的兴奋、渴盼都已冰消:“我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7]265前文中所描绘的幼年鲁迅对于赶会的兴奋与临时被父亲要求背诵《鉴略》的不愉快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落差。我想,这样的经历在中国的礼教家庭中是极其平常的。父母常常会以爱的名义忽略甚至故意延宕孩子的欲望满足。在儿童教育方面,周家在当时的环境下还算是开明的。周作人晚年认为,祖父介孚公、父亲伯宜公都有相对宽容的儿童教育法:“介孚公的确喜欢《西游记》,平常主张小孩应该看小说,可以把他的文理弄通,再读别的经书就容易了,而小说中则又以《西游记》为最适宜。”[8]696幼年的鲁迅和周作人十分喜欢漫画。他们曾经用压岁钱买了一本《海仙画谱》,担心被大人骂而偷偷地看。将它“藏在楼梯底下,因了偶然的机会为伯宜公所发见,我们怕他或者要骂,因为照老规矩‘花书’也不是正经书,但是他翻看了一回,似乎也颇有兴趣,不则一声的还了我们了。他的了解的态度,于后来小孩们的买书看的事是大大的有关系的”。[9]626《五猖会》中的父亲应该也是基于对孩子的爱而作出背诵的要求。他的出发点是希望孩子能够读好书。他选择赶会之前,幼年鲁迅特别兴奋的时候提出这一要求,也许是为了选择一个更加合适的时机强调读书的重要性。他要求孩子读的《鉴略》是清代王仕云所著的初级历史读物,由四言韵语写成,读起来相对容易上口。但是,父亲的这种出于爱的做法却忽略了幼儿的感受,在幼儿的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创伤。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礼教父子关系中的爱如何因其严苛的等级制而成为孩子成长的“毒药”。《五猖会》的结尾,鲁迅写道:“直到现在,别的完全忘却,不留一点痕迹了,只有背诵《鉴略》这一段,却还分明如昨日事。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7]266这种历经四十年而清晰如昨的记忆证明当时的伤害是巨大的。“诧异”是中年鲁迅对造成这一创伤的父亲怀着同情之谅解,并非赞同父亲当年的做法。鲁迅真正的意图是从亲情的伤害中反思造成这种伤害的缘由。
另一方面,鲁迅也难以忘怀他曾经打扰临终的父亲的平静。这种愧疚在他心里延续了几十年,因此也算是一种心理创伤。鲁迅的父亲伯宜公去世于1896年。这件事在鲁迅的生命历程中影响巨大。父亲早逝(虚岁37岁),作为长子的鲁迅就成为这个家庭的顶梁柱,承担起支撑家庭的责任。这使得成年后鲁迅对父亲的感情比较隐匿,打扰父亲临终时的平静的内疚是为数不多的例外。鲁迅有两篇专文记述这一创伤性记忆。1919年鲁迅在《自言自语(六)》中记载了父亲临终时,自己听从乳母的说法,大叫“爹爹”,打扰父亲“徐徐入死”,是“大过失”。[10]95同样的愧疚之情在1926年的《父亲的病》中又一次出现。这一次,乳母换成了衍太太(诚房的叔母)。但愧疚之情丝毫没有改变:“‘父亲!!’我还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气。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11]288-289《父亲的病》用了大量的笔墨记载父亲生病、治疗的过程。除了揭露中医近巫的欺骗性之外,《父亲的病》里比较清晰地刻画了自己父亲的形象:一个理性清明的读书人。庸医束手无策之际,提出了一些荒唐的办法(灵丹点舌头,解冤愆),都被他拒绝。[11]288-289在周作人的回忆中,伯宜公也是类似的形象。在甲午(1894)秋冬之际,他在和友人的谈话中提出要送自己两个儿子分赴西洋和东洋留学。“那时读书人只知道重科名,变法的空气还一点没有,他的这种意见总是很难得的了。”[12]635-636《父亲的病》把《自言自语(六)》中的愧疚之感进一步扩展,更为清晰地将鲁迅内心无法抚平的创伤宣泄出来。鲁迅为什么要把这一念念不忘的“最大的错处”笔之于书?也许文学创作可以舒缓这一创伤的痛苦吧。鲁迅对父亲的愧疚及创伤的疏解是他接触到现代思想之后才有的体验。它显示出,在礼教父子关系中,那些被礼教所塑造的子对父的爱与情感也是“毒药”。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新父子观
五四新文化运动试图以来自西方的科学、民主、自由、个性主义等思想改造礼教中国。家族制度及其伦理成为首当其冲的靶子。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认为“忠孝者,宗法社会封建时代之道德,半开化东洋民族一贯之精神也”,明确地将家族宗法制视为“东洋民族社会中种种卑劣不法残酷衰微”的罪魁祸首。他提出,“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13]在“立人”这一新文化运动的核心目标中,妇女与儿童是解放的重要目标。现代儿童教育观念逐渐为中国思想界先驱们所接受。当年影响中国思想界儿童教育观念的外来思想资源有多种。瑞典女权主义者爱伦·凯(Ellen Key, 1849—1926)的自由主义儿童教育观、社会主义者与新村运动的儿童公育观、进化论的儿童观等都曾经在中国接受者那里得到极其热烈的回应。鲁迅也是这些新思想的积极回应者之一。他借助上述思想资源猛烈抨击礼教的“父为子纲”观念,要求建立幼者本位的儿童教育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不过,这种希望是建立在对“吃人”普遍性的绝望的基础之上,带有鲁迅所特有的悲观色彩。当狂人发现吃人者不仅仅是家庭外面的人,还包括自己的哥哥,甚至他自己也是一个吃人的人。他几乎绝望了,唯一的希望就是孩子,虽然这一希望的前景同样是渺茫的,但是,舍此还有其他的希望吗?
《狂人日记》的这种悲观性预测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中有了肯定性的回应。《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是鲁迅新的父子观的集中体现。鲁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因此“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14]鲁迅的意见可以约略归为以下几个部分。
首先,颠覆“父为子纲”的等级观念。礼教的父子观把父子的等级制比附于父子的血缘关系。父子之间的等级关系被转换为生育的“恩”。父亲是施恩者,儿子必须报恩。这样就把人为的等级制度自然化了。鲁迅则从进化论出发,认为“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14]进化论背后的基础是科学理性,而科学精神是“五四”那个时代的超级信仰。鲁迅借此推翻了礼教制度中“父为子纲”观念的基础——恩——的合法性。他把父子关系视为生命自然传承的链条,“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14]撤去了父子间的“恩”,撕去了“父为子纲”中血脉关系的脉脉温情,将父子关系还原为进化链条上的自然选择,也就从根本上否认了礼教伦常的合法性。
其次,改“父为子纲”的长者本位为幼者本位。“父为子纲”的长者本位是借助“恩”的自然化程序来维护父权的绝对权威。幼者本位的观点则借助进化论来颠覆这一自然化程序。在进化论中,儿童代表了人类进化的方向:“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14]鲁迅认为,明白了人类进化过程的人便应该放弃礼教秩序中的长者本位和利己思想,觉悟到幼者本位“便是最合于这生物学的真理的办法”“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再纯洁明白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领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领,将来还要交付子女,像他们的父母一般。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个过付的经手人罢了”。[14]礼教秩序中父子间施恩与报恩蕴涵着等级关系,这种等级关系被自然化之后就成为不可怀疑的所谓“天道”。鲁迅以进化论先来与后起的线性发展顺序取代了施恩与报恩的等级制,幼者本位取代了长者本位。
最后,以“爱”来代替恩。作为礼教秩序基础的“恩”也有爱的成分,但建立在“恩”的基础上的爱,因为尊卑上下的等级被纳入王权专制的文化传统而遭到异化:父权的绝对权威带来了爱的偏枯。如《父亲的病》《五猖会》所显示的,自然的伦理化戕害了人的天性,爱变成了父子间的“毒药”。鲁迅认为进化论中的父子之爱是基于天性(生命本能)的,“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纲’。倘如旧说,抹煞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乖剌的种子”。[14]鲁迅强调应以从天性出发无功利的爱代替“恩”的爱。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伦理的自然化,即恢复人作为生物的天性之爱,去除非自然的礼教束缚。
在鲁迅那里,这种代替“恩”的爱又不同于纯粹的动物本能,而是人性化的、上升为人的类本质的爱。它包括三个方面:理解、指导与解放。所谓理解是指父亲应该理解孩子独有的、不同于成人的世界,“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所谓指导是指祛除了礼教父权的权威的平等协商,“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所谓解放是要父亲们明白:“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14]由此可知,上述三者的理论基础是平等、自由、个性等现代观念。
从上述引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鲁迅那里,从“恩”到爱的转换,其实质是以现代的个性主义、自由、平等观点重塑父子关系。在这一传统向现代转换中,父亲应该是一个自我牺牲者:“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14]进化论是这种自我牺牲精神背后的理论和道德支撑。其中当然有一些乌托邦的色彩。这一父辈应自我牺牲于子辈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来自日本白桦派作家有岛武郎。与《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同一期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鲁迅的另一篇文章《随感录六十三“与幼者”》,摘录了有岛武郎的《与幼者》中父辈需自我牺牲、激励子辈超越父辈“向着高的远的地方进去”等相关文字。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将有岛武郎称为“一个觉醒的”人,称赞他对于“一切幼者的爱”。[15]1922年,鲁迅全文翻译了有岛武郎的《与幼者》(改译为《与幼小者》),由此可见鲁迅对这篇文章的推崇。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随感录六十三“与幼者”》中的父子观,可以看作鲁迅颠覆三纲学说、重塑伦常的重要基石。《父亲的病》《五猖会》对童年创伤性记忆的书写,也是这种新的父子观的产物。当然,鲁迅那时候还没有做父亲,他把自己的父爱倾注于侄子女们身上,这种倾注在羽太信子那里被拿来作为发泄不满的工具。如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落魄时受到房东老太婆的鄙视一样,这对于鲁迅恐怕也是一种创伤吧?
三、“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的为父实践
鲁迅与许广平结合后,最初采取避孕措施,不希望有孩子。后来避孕失败,遂有海婴。从此,鲁迅有了为父的实践。做父亲,虽然给鲁迅带来了许多日常的烦恼,不过更多的是乐趣,也使得他有机会实践他早年的儿童教育理念和新的父子观。
鲁迅对海婴的到来无限欢喜。许广平回忆:“海婴生下来了,每个朋友来到,他总抱给他们看,有时小孩子在楼上睡熟了,也会叫人抱他下来的。他平常对海婴的欢喜爱惜,总会不期然地和朋友谈到他的一切。”[16]62当年有朋友嘲戏鲁迅对海婴的溺爱。鲁迅自我解嘲道:“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17]在这首诗里,鲁迅一方面承认自己对海婴深深的爱,甚至称得上是溺爱;一方面又为这种爱辩护:这种爱是无可厚非的呀,你看,连作为动物之王的老虎都时时反顾自己的幼崽。那些以无儿女之情来显示自己的豪杰气、丈夫气的说法没有道理。这里的“朋友”,指的是郁达夫。[17]鲁迅在给母亲、朋友的信件中并不掩饰自己对海婴的喜爱。鲁迅的母亲那时在北京,虽然未曾见面,却对海婴特别牵挂。鲁迅的家书中几乎每信必提及海婴。海婴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常常成为鲁迅家书的内容:海婴感冒了,拉痢疾了,病情好转了,说了什么好玩的话,做了什么有趣的事,淘气了,挨打了,爱吃什么,等等,举凡鲁老太太感兴趣的,鲁迅都不厌其烦地告诉母亲。例如鲁迅1932年3月20日致母亲家书中提到海婴:
海婴疹子见点之前一天,尚在街上吹了半天风,但次日却发得很好,移至旅馆,又值下雪而大冷,亦并无妨碍,至十八夜,热已退净,遂一同回寓。现在胃口很好,人亦活泼,而更加顽皮,因无别个孩子同玩,所以只在大人身边吵嚷,令男不能安静。所说之话亦更多,大抵为绍兴话,且喜吃咸,如霉豆腐,盐菜之类。现已大抵吃饭及粥,牛乳只吃两回矣。[18]
此信是“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后,鲁迅一家外出避难回家之后不久写的。其间,海婴出疹子。旧时小孩子出疹子为一大关,多有过不去而夭折的。出疹子要避风。海婴安然度过此关。鲁迅在家信中体贴着母亲的心意,详细报告海婴的行状,连及海婴说绍兴话、喜欢家乡口味等。这些想是鲁老太太最愿意听到的吧,其中也饱含着作为父亲的鲁迅对海婴真挚的爱。
鲁迅对海婴的喜爱,并非将他当作一个玩物,而是亲力亲为地参与育儿,这是传统父亲所做不到的。许广平曾经回忆海婴初生时,鲁迅积极地参与抚育,甚至闹出了很多笑话。比如,他们自己给小海婴洗澡,却因为没有经验而导致海婴不断感冒;严格按照婴儿定时哺乳法哺乳而使得海婴饥饱无常。鲁迅和许广平初为人父母,和许多年轻的父母一样,没有多少育儿经验而狼狈不堪。鲁迅还为海婴唱自编的儿歌,哄其入眠。[16]64-67即使在最开化的1930年代的上海,像鲁迅这样亲力亲为参与孩子养育的父亲还是并不多见。
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谈到应以父亲的自我牺牲的理性之爱来代替礼教秩序中的恩情观念。其核心是将孩子视为成长着的一个独立个体。在鲁迅的为父实践中,他实践着这种理念。他对海婴的爱便是以科学、理性为基础。在许广平的《鲁迅先生与海婴》(1939)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这样的例证,对当下的我们仍然有启发意义。比如,面对海婴询问“我从哪里来”这一涉及生命的终极追问,鲁迅耐心地一直给他讲到单细胞的发生。海婴再往下追问,鲁迅只好说:“等你大一点读书了,先生会告诉你。”[16]64-67他并不因为孩子无休止的追问而恼怒,也不肯因为孩子问到终极之处,自己无法回答而离开科学常识,随意乱说。这可以看出鲁迅对孩子的尊重,对孩子好奇心的保护,也有顺其自然、努力释放其天性的考量。
鲁迅对海婴的理性之爱还包括科学的性教育。科学的性教育在中国礼教社会中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中国的儒家文化虽然是生殖崇拜的文化,但性的污秽观念却根深蒂固。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猛烈地抨击过礼教社会的性污秽观念:“性交是常事,却以为不净;……人人对于婚姻,大抵先夹带着不净的思想。亲戚朋友有许多戏谑,自己也有许多羞涩,直到生了孩子,还是躲躲闪闪,怕敢声明。”[14]因此,他认为:“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再纯洁明白一些。”[14]鲁迅对海婴的性教育是本着科学的、开放的性净观,即把性视为人的一种普通常识,以正常的态度传授科学的性知识。在平时的家庭场合,他和许广平以坦白的态度向孩子传授性的知识:
对于孩子的性教育,他是极平凡的,就是绝对没有神秘性。赤裸的身体,在洗浴的时候,是并不禁止海婴的走出走进的。实体的观察,实物的研究,遇有疑问,随时解答,见惯了双亲,也就对于一切人体都了解,没有什么惊奇了。他时常谈到中国留学生跑到日本的男女共浴场所,往往不敢跑出水面,给日本女人见笑的故事,作为没有习惯训练所致的资料。这也正足以针对中国一些士大夫阶级的绅士们,满口道学而偶尔见到异性极普通的用物,也会涉遐想的讽刺,这种变态心理的亟须矫正,必须从孩子时代开始。[16]75
许广平的回忆提示我们:首先,鲁迅夫妇对海婴的性教育是自觉的。其次,他们对海婴的性教育是建立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之上的。自觉的科学的性教育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五四时期,现代的性科学知识被广泛地介绍到中国。周作人和周建人是推动这一浪潮的骨干,[19]鲁迅自然也是科学的性教育的坚定支持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在抨击礼教父子观的基础——恩——时便是以科学的性净观来立论。因此,鲁迅在海婴的教育中施以有意识的性教育是渊源有自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鲁迅作为父亲基本上实践着他所提出的“以爱代恩”、幼者本位等观念。这种实践虽然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父子观的羁绊,但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代它的确体现着时代的标高。
结 语
父子关系是礼教秩序的三大柱石之一。在礼教为王权专制服务的过程中,父子这种人类的自然关系被注入了大量维护王权专制所需要的内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推动着现代价值体系对这些内容形成颠覆性的冲击。鲁迅对“父为子纲”中等级性、压迫性的内容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种批判的目的不是为了取消父子之间的天性之爱,而是要去除其中的等级制。按照进化论的逻辑,鲁迅主张改长者本位为幼者本位。幼者本位需要父亲能够自觉承担作为生命进程中的“过付的经手人”角色,自我牺牲。同时,鲁迅主张以现代人文思想和科学的理性来糅合父子间的天性之爱,以这种现代的父子之爱来代替“父为子纲”的情感逻辑——恩,这样就完成了父子关系的由礼教向现代的转换。
在做父亲的实践中,虽然现实生活的琐碎与不同生命的碰撞并不能完全进入观念推演的理想状态,但是,鲁迅尽其可能地践行着他之前所倡导的观念。其中当然也会有一些罅隙,但那是历史条件限定的结果,非个体能力所能完全弥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