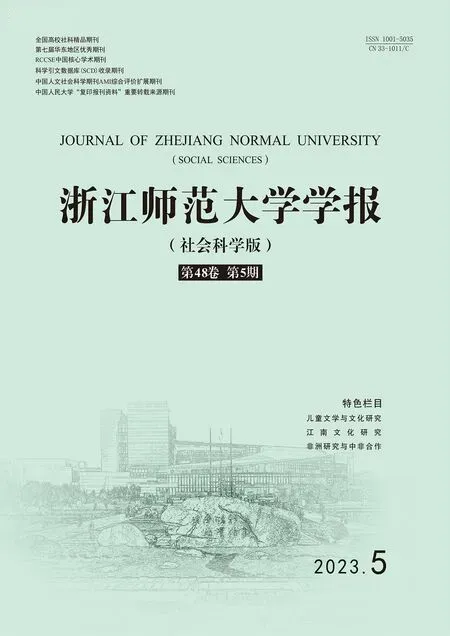当代大众媒介建构下的鲁迅改编
——以互联网创作为例
2023-12-29徐君
徐 君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大众媒介的更新与发展,为当代文学、艺术的传播建构了新的模式。那些曾被奉为经典的、严肃的、精英的文学、艺术作品或形象被改造成了流行的、大众的文化符号,从而在当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生发出新的价值和意义。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作品和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经过历史的重重洗礼,“鲁迅”已然成为中国当代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符号,并在不同领域内或语境下被不断地重塑或改造,由此形成了丰富多样的“鲁迅”文化景观。在大众媒介的建构之下,鲁迅作品中的经典文本、人物形象、精神信念甚至鲁迅自身的形象和风格与当代大众文化、流行文化、青年文化实现了一种巧妙的接合。因而,从大众媒介的视域出发,人们在解构传统的“鲁迅”,建构新的“鲁迅”、当代的“鲁迅”的过程中,共同塑造了当代社会文化中的一个不一样的“鲁迅”。本文将聚焦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当代大众媒介对鲁迅及其作品的重构,借助媒介文化研究者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①的大众媒介文化理论,分别从大众媒介对鲁迅及其作品的挪用与重构,媒介文化建构的内在逻辑,大众媒介和流行文化、青年文化之关系出发,以此把握“鲁迅”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与意义。
一、互联网创作中的鲁迅改编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中,鲁迅及其作品一直是与精英的、严肃的、批评性的文学或文化相联系的。然而,随着社会文化和技术的发展、大众媒介的普及,鲁迅及其作品逐渐走出精英文化的藩篱,而变得越来越“大众化”。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文本,它频繁地出现在当代大众媒介中,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日渐交织在一起,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在电视、电影中,其作品被反复地改编,如《伤逝》《药》《阿Q正传》《祥林嫂》等。而除去对其作品的改编,以鲁迅个人生活、事迹为主要内容的纪录片或传记片同样是影视作品中的常客,如《鲁迅传》(1981年)、《鲁迅之路》(1991年)、《先生鲁迅》(2011年)、《鲁迅的大家庭梦想》(2013年)等。这些改编或创作因其与鲁迅直接的、亲密的联系,不仅受到大量观众的注意和喜爱,同样引起了学界的重视,至今,已有许多相关的讨论和研究。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专题化、主题化的改编和创作之外,还存在大量的与鲁迅相关的视频、音乐和互联网创作。其中,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扩张,互联网作为新兴的大众媒介为人们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更大限度的独立和自由。不同于传统大众媒介中固定的角色职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大众媒介打破了以往的规则,使得人们能够在创作、欣赏和批判之间灵活地转换,以此极大地丰富了文艺创作的内容与形式。在哔哩哔哩(国内年轻人聚集的网络文化社会和视频网站)上,创作者们通过对鲁迅经典作品和文本的挪用与改造,进一步实现了鲁迅与当代大众文化、流行文化、青年文化的接合。其中,视频作品《〈野草〉:我把16篇鲁迅写成了歌》《〈闰土〉:我把鲁迅的书写成歌》《〈孤勇者〉鲁迅版填词 献给先生的歌》,分别达到了1 182.8万、224.2万和782.0万的播放量。在这些作品中,人们解构了鲁迅经典作品的神圣性、权威性和完整性,通过碎片化的剪辑和拼贴,建构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鲁迅”,一个具有当代生命力的“鲁迅”。
其一,《〈野草〉:我把16篇鲁迅写成了歌》融合了说唱音乐、图文视频,对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进行了综合性的重构。创作者分别选取了原著中的16篇散文诗,包括:《好的故事》《影的告别》《秋夜》《过客》《求乞者》《我的失恋》《复仇》《复仇(其二)》《希望》《雪》《死火》《这样的战士》《墓碣文》《腊叶》《死后》《一觉》,通过对其重新编写,叙述了一个属于当代的故事。
《好的故事》被改写为:
昏沉的夜/灯火温吞地灭/我昏沉的梦里/故事拉开画卷
鲜花和云朵/在水影里/升腾摇曳/我坐在小船/岸边是/村人和月
好的故事/都融化在水里了/昏沉的夜里/我猛然睡醒了。
《秋夜》《过客》被改写为:
我在野地里/赶路/疮痍满目/奇怪而高的天上/星/洒下寒露
枣树刺向天空/利/穿破惨雾/引恶鸟发声/但飞蛾扑火/亦义无反顾
得继续走/前面是坟/和野百合/走完了坟地/和百合后/是什么呢
我不能留/所以/踉跄地返回夜色/要继续走/只有/拿水补我的血了。[1]
与此同时,创作者还在作品中附上了由裘沙、王伟君和裘大力等人为《野草》创作的插画。于是,文学、音乐、绘画在此巧妙地融合成了一体,给人们带来丰富生动且直观的艺术体验。
其二,《〈闰土〉:我把鲁迅的书写成歌》也是创作者基于说唱音乐,对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进行的重新书写。然而,不同于《〈野草〉:我把16篇鲁迅写成了歌》对原著文字的浓缩,创作者则是以鲁迅作品中的经典人物形象——闰土为符号,将其与当代城市青年,特别是从农村到城市谋生的年轻人联系在一起,从而创生了“闰土”的当代意义。
一张乌漆麻黑的脸和我累断的筋
我不听/我甚至不知道瓜田为何会腐烂
我没有文化/老爷/不知该怎么表达苦难
我才不是什么老爷/什么也不是
……
一位闰土在权力面前点头哈腰/一位闰土在迫不得已两肋插刀
一位闰土在上班路上还没睡醒/一位闰土在屈辱面前不敢发飙
你活在这个世上你又何尝不是闰土/闰土们卑颜屈膝却又何尝不想愤怒
谁小时候不曾把金钱视为粪土/困苦的日子来了/每个人都是闰土。[2]
从《故乡》的“闰土”到当代社会的“闰土”,创作者通过对“闰土”形象的挪用和重塑,跨越了时间的枷锁,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找到了一种契合,表达了对当代现实社会问题的反思与批判。
其三,《〈孤勇者〉鲁迅版填词 献给先生的歌》则是将鲁迅作品中的经典文本与当代流行音乐、影视剧相结合,以此塑造了一个与当代大众文化相呼应的鲁迅形象。创作者以歌曲《孤勇者》为曲,以鲁迅作品中的经典文段为词,并剪辑了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片段,通过对三者的重构,形成了一个新的供大众观看、欣赏的视频文本。鲁迅作品中那些已成为经典符号的文字,如:“麻木”“脊梁”“馒头”“铁屋”“呐喊”“炬火”等,在此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于其作品的感知和体验。[3]于是,伴随着视觉和听觉的冲击,人们在观看作品时,将鲁迅及其作品与自身的境况相联系,从而建构起鲁迅与当代社会的深刻联系。
如果说以电影、电视为代表的鲁迅改编是一种单向度的媒介传播,那么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鲁迅改编则是一种多向度的传播过程。观众的反应与评论同样是鲁迅改编作品中的重要部分,是作品真正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上述作品的留言区或弹幕区,无论是对作品本身的评判,还是有感而发的自我抒情,人们与作品、与鲁迅都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反应。用户名为“起名困难户被占用了”的网友在《〈野草〉:我把16篇鲁迅写成了歌》下评论:“每次在做和鲁迅先生有关的课文的时候都在想,先生的深奥确实成年人也难读懂,那我们这些‘二传手’(不仅限于编辑,还有教师)为什么一定要用讳莫如深的态度,让他变得更加难以被接受呢?”[1]用户名为“旅行者—尤利娅”的网友在《〈闰土〉:我把鲁迅的书写成歌》下留言:“我现在大抵是清醒的,但却不知道何时会变成闰土;我对自己的情况是清楚的,但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被染缸染上闰土般的颜色。”[2]用户名为“银妆锦官工作室”的网友在《〈孤勇者〉鲁迅版填词 献给先生的歌》下感叹:“如今已经比先生所处的时代光明得太多,或许不该再有一个鲁迅。但雄起的高楼大厦之间,有些黑暗反是藏得更深了,我们应寻着光芒,刺破这最后的见不得人的黑暗。”[3]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与鲁迅作品的距离或远或近,而当他们在此相遇时,个人的人生经验在鲁迅的作品中,却找到了新的共鸣。可以说,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大众媒介的建构中,人们既是在与作品对话,也是在与鲁迅对话,是在与作者对话,也是在与其他观众对话,更是在与自我对话。于是,传统的艺术接受理论不再适用,创作者、观众在一次又一次的对话中不断地赋予作品新的内容和意义。相较于对传统媒介文本的接受,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大众媒介为人们自由地表达个人私密的情感体验提供了空间。
可以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大众媒介为人们建构鲁迅及其作品在当代社会中的意义和价值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上述三部作品,分别从具体作品的改编、经典人物的再建和不同文本的拼贴出发,实现了鲁迅与当代社会的接合,激活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且,通过对这些作品的接受和批判,人们体验到了一种积极的情感共鸣。人们不再被动地接受鲁迅,而是与自身的境况相结合,由此真正地理解鲁迅和理解自我。可见,大众媒介并不是一种僵硬的、机械的传播介质、工具,而是一种积极的、能动的、具有建构意义的对象。
二、接合:大众媒介建构的内在逻辑
在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看来,“媒介是经济、历史和社会权利关系的一部分,同时是人们生活体验、意义和身份认同的外在形态,它们相辅相成”。[4]14大众媒介的建构是置于特定的语境之下的,它联系着社会经济、历史、权利等多重因素,影响着人们的情感生活和精神世界。分析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当代大众媒介所建构的“鲁迅”文化景观,必须置于具体的语境之中,把握各个不同关系之间的接合。因为,“接合(articulation)关注的是创造、拆解和重塑关系,以及语境的变化性实践。在这种实践中,新的关系从事物之间的旧关系或无关系中建立,描绘出事物之间的关系”。[5]20因而,只有在接合的关系中,才能真正地理解当代大众媒介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解构与重构,理解差异性、破碎性、异质性如何被重新统一成新的整体。就互联网创作而言,作为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符号的“鲁迅”,其在大众媒介中的传播,实际上正是与当代的社会、历史、经济、权利、文化、技术重新接合的过程,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
其一,鲁迅改编与当代数字技术的接合。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的”媒介逐渐取代了“旧的”媒介(如广播、电视、电影等)的地位,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为人们建构起了新的生活模式。首先,数字技术为大众媒介解构、重构鲁迅及其作品在当代的表现形式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在多媒体、互联网出现之前,“鲁迅”的改编往往依附于某一主要的艺术形式,或电视、或电影、或戏剧。这些改编往往受制于技术的单一形式,因而需要依附其独特的艺术形式进行改编,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固化了媒介的传播模式。而以鲁迅为资源的互联网创作恰恰解构了作品的统一性,它选取不同艺术形式中的“鲁迅”碎片,在拼贴、并置中,创作出新的文本。人们能够利用数字技术,对文字、图片、视频等艺术形式进行多样化的处理,以此超越传统艺术对创作的桎梏,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其独特的创作目的,如对社会真相的揭示、对艺术形式的新探索,或仅是表现个体化的情感等。其次,区别于“旧的”媒介(如:广播、电视、电影等)的单一性、单向性和权威性,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放、多元、自由、平等的沟通空间。其中,尤尔根·格尔查兹(Jürgen Gerhards)和迈克·谢弗(Mike S.Schafer)在讨论互联网与公共空间领域问题时曾指出:“正如尤尔根·哈贝马斯,一直对‘旧的’大众媒体持批评态度,认为它们无法促进自由和多元的社会传播。相比之下,互联网的出现让人们产生了希望,希望它能让以前被边缘化的行为者和争论更容易被更广泛的公众看到。”[6]一方面,互联网扩大了人们的自由度,让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习惯、喜好来选择具体的作品,并使得人们的参与和互动成为作品建构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互联网更加开放,它能够使得更多的声音被听见。可见,正是在与当代技术的接合过程中,鲁迅改编获得了新的形式,同时在新的形式中建构起了新的价值与意义。
其二,鲁迅改编与当代流行文化的接合。从互联网创作来看,在当代大众媒介中,鲁迅改编是与流行文化密切联系的。《〈野草〉:我把16篇鲁迅写成了歌》和《〈闰土〉:我把鲁迅的书写成歌》都使用了当下的流行音乐形式——“说唱(rap)”。而在当代大众文化、青年文化中,说唱音乐已经超过朋克、摇滚的影响力,在当代青年中具有更大的号召力。在早期的说唱音乐研究中,特蕾莎·马汀内斯(Theresa A.Martinez)就认识到“说唱与主流文化、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主义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并指出说唱是“反抗主流社会秩序的一种存在形式”。[7]通过与说唱音乐的接合,当代青年与鲁迅的作品成功地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合作。而作品《〈孤勇者〉鲁迅版填词 献给先生的歌》则是直接延续了流行歌曲《孤勇者》的歌名和曲调。《孤勇者》发行于2021年11月,最先是为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所作的中文主题曲。在其原有的受众(《英雄联盟》是全球玩家数量最多的电脑游戏)基础上,因其“孤独的勇士”“平凡的英雄”的立意,迅速火遍全网。在哔哩哔哩上以“鲁迅”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以播放量排序,这三部作品分别排在第2、第71和第7位(包括以“鲁迅”为关键词的非艺术创作),而传统意义上的鲁迅改编,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都难以进入前100名。实际上,鲁迅改编与流行文化的接合并非偶然。当代青年被当代学者亲切地称为“互联网土著(Internet-natives)”。[8]出身于千禧年前后的当代青年,是与互联网技术共同成长起来的。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大众媒介与青年、流行文化相亲近,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此,在当代大众媒介中,鲁迅改编势必与青年、流行文化相接合。并且,正是这样的接合使得鲁迅及其作品在当代文化中获得了新的阐释与传播。
其三,鲁迅改编与当代消费主义的接合。一方面,文化产业的兴起与繁荣,使得文化作为一种商品流通于市场之上,成为人们消费的对象。鲁迅及其作品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遗产,是文化产业开发的重点对象。不同于传统文学、艺术创作的无功利性,在消费主义影响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大众媒介中的鲁迅改编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野草〉:我把16篇鲁迅写成了歌》《〈闰土〉:我把鲁迅的书写成歌》《〈孤勇者〉鲁迅版填词 献给先生的歌》这样的作品,可以通过点击量、播放量、评论数来获取经济利益。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潜在传播力(拥有的粉丝数、流量),又能为创作者带来额外的利益。因而,从创作者的角度而言,对鲁迅及其作品的改编行为本身就带有一种社会性的消费意味。另一方面,联系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消费社会》中所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身体(corps)作为一种消费品的存在,“使得个体把自己当成物品,当成最美的物品,当成最珍贵的交换材料,以便使一种效益经济程式得以在与被解构了的身体,被解构了的性欲相适应的基础上建立起来”。[9]127-128由此出发,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审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当代大众媒介中所潜藏的消费主义陷阱。因为在媒介的建构过程中,个体的身体、精神是被当作商品来看待的。对于互联网而言,最大的经济利益来源就是“流量”,任何成功的作品都必须有巨大的流量支撑。而流量的背后意味着人们的注意力,当观众的身体或精神需求被作品激发时,人们便会做出进一步的消费行为,即常见的点赞、关注、投币或打赏等行为。因而,从经济的视角出发,当代大众媒介中的鲁迅改编是与消费主义相接合的。就此而言,对于经济效益的追求,推动了当代鲁迅改编的多样化,促进了其在大众文化中的传播与发展。
从上述讨论中,可以发现,经济、技术、文化在当代大众媒介对鲁迅改编的建构中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它们在不同的接合关系中,不断地解构“旧的”鲁迅,又不断地建构新的“鲁迅”。在文化研究中,格罗斯伯格将“关系、接合”看作“是历史转变的物质过程,是文化本身的场所”。[10]“接合”作为大众媒介的建构逻辑使得鲁迅改编在适应当代社会的现实前提下,焕发出了新的光彩。因而,从不同的接合关系出发,能够更好地认识和理解鲁迅及其作品在当代社会中的传播现状及价值意义。
三、媒介建构:鲁迅改编的当代意义
媒介的解构和建构带有浓厚的现实色彩。尤其是当媒介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媒介的建构意义更加得以凸显。在格罗斯伯格看来,媒介“在建构自身的同时也在建构着其他东西”,它包括“挣钱、型塑日常生活、建构意义和身体认同、创建真实、建构行为、建构历史”[4]7等。可知,在不同时代和社会环境中,不同媒介中的鲁迅改编具有不同的价值和意义。而在当代大众媒介建构中,鲁迅改编既建构了自身在当代社会文化中的形态,又在不同关系的接合中建构起了新的社会价值和意义。从媒介的建构逻辑出发,以互联网创作为代表的大众媒介建构中的鲁迅改编,其价值意义主要来源于其与当代消费文化、大众文化、流行文化、青年文化的接合。这些接合关系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对鲁迅及其作品的重新阐释,并使得人们在新的阐释中,获得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同时,找到了一种共同的关于青年、非主流的身份和文化认同。
其一,当代大众媒介中的鲁迅改编在建构自身的同时,也建构了其所期待的受众。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就互联网创作中的鲁迅改编而言,其所期待的受众是由市场的受众和文化的受众所构成的,即“把受众建构为市场”和一种“文化身份”。首先,将受众建构为市场是基于“现代人口统计学”“品味文化(taste culture)分析”和“族群生活方式分析”而实现的。[4]234-244人口统计学能够精准地图绘出当代社会人口的类型、数量,如年龄、性别、职业、受教育水平等;品味文化分析能够把握受众人口对于某一文化类型的喜爱程度,如音乐中的摇滚、朋克、说唱等;族群生活方式分析则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对某一特定群体的消费特征、文化喜好所做的综合性分析。从互联网创作中的鲁迅改编来看,它正是在建构媒介产品(具体的鲁迅改编作品)的同时,建构起了其市场的受众——能够使用互联网、喜欢流行文化、能够为数字产品付费等。其次,将受众建构为一种文化身份是通过对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念的解构而实现的。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念认为存在一种固定的身份,由基因所决定,如白人、黑人、黄种人。而文化身份是与社会、经济、政治、心理、文化等相联系,它无法由单一的标准来定义。从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文化观来看,“反本质主义文化身份观认为文化身份同质性基础并不是天生的、自然的、原始的整体,而是由话语通过符号建构的”。[11]于是,媒介作为一种话语的建构,就具备了重新建构文化身份的功能。在互联网创作中的鲁迅改编,隐含着对于受众文化身份的建构,尤其是针对当代青年——这一文化身份的建构。它通过对鲁迅及其作品中的“反抗”“觉醒”“麻木”“压迫”等境况的重构,将其与当代青年相联系,从而为当代青年建构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身份。这也是鲁迅改编能够在当代青年中掀起热潮的重要原因。青年文化的核心观念是斗争与抵抗。为了反抗主流文化的桎梏,青年往往采取独特的生活或行为方式(如嬉皮士、飞车党),以此建立自身的文化身份。因而,鲁迅改编的热潮体现了人们对重新确立青年文化身份的努力。
其二,在大众媒介中作为被建构的受众,并非消极、被动的,而是积极、能动、具有创造力的。20世纪以来,大众媒介是与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相联系的。而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受众则常常被视为非理性的、盲目的、沉迷的、易被操纵的、屈服于欲望的。然而,格罗斯伯格却认为在流行文化中存在两种不同的受众:“更大的一部分仍然被认为是被动消费大众文化文本的文化笨蛋。但还有另一部分人,规模小得多,也分散得多,他们积极地挪用特定流行文化的文本,并赋予它们新的、原创的意义。”[12]通过对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和使用满足理论(uses-and-gratification perspective)的批判,格罗斯伯格将情感、情绪、愉悦引入受众行为的分析范畴。(1)积极的受众通过主动地使用媒介或消费媒介来理解自己的情感生活或建构特定的情感状态。于是,当青年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压迫、剥削、不平等的待遇时,他们会主动地寻找与之相关的作品,来表达或宣泄自身的情感。当代“闰土”的悲酸、“野草”青年的反叛、“孤勇者”的坚韧使得人们主动拥抱鲁迅。人们有意或无意地通过点赞、投币、收藏等行为表现其对作品的肯定与喜爱。(2)大众媒介通过情绪的散播和共享,以此促进社会中人们共同的、积极的行动。当代青年正是在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鲁迅改编作品中,获得了一种独特的情感共鸣,个体在感受作品所传递的情感和精神时,可以即时地分享,通过转发或评论,将自己的想法和情绪展现在公众平台之上,或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在共同的建构和阐释中,使得鲁迅及其作品的改编超越原有的意义,从而获得新的生命力。(3)受众从流行文化中获得愉悦是对主流文化的一种反抗行为。正如,有学者曾指出:“鲁迅在中学里的传播基本是失败的。学生和老师多难以愉快地面对这个历史人物。”[13]而在大众媒介建构下的鲁迅却意外地受到欢迎。从审美的角度而言,人们在此所获得的愉悦不能仅被理解为一种单纯的正面的情绪,它同样意味着心灵的共鸣与压抑的释放。在上述所列举的互联网创作中,人们不再是被动地阅读作品,强制性地解读所谓的“奴性”“国民性”“阿Q精神”,而是从自身境况出发,在真切的情感中理解鲁迅的思想与精神。人们不仅不厌其烦地反复播放视频,还自愿打赏创作者,甚至购买与之相关的文化产品。这些行为,不仅是人们对改编作品的肯定,同样也是人们基于自身境况对鲁迅及其精神的深刻认识。在大众媒介的建构下,人们终于脱离对解读作品终极意义的盲目追求,而是将作品与个人的生活困境与隐秘情感相联系,从而实现艺术创作的现实意义。可见,由当代大众媒介所建构的鲁迅改编的受众,正是在积极、能动的接受与阐释中,与当代流行文化、青年文化共同激活了鲁迅的当代意义。
由此可知,在媒介建构中的鲁迅改编,其意义既来源于鲁迅及其作品本身的价值,也来源于现实的社会境况。比如,网络媒体对“孔乙己脱下长衫”的讨论不仅仅是对鲁迅作品中经典人物形象的再解读,更是人们对自身社会境况的一种表达。人们通过讨论孔乙己,来展示当代社会中的个人困境。在当代大众媒介建构中,鲁迅改编使得人们,尤其是青年群体,在表达和宣泄情感中,在愉悦的反叛中,获得了一种文化和身份的认同。正是在这种独特的认同中,处在困境中的人们不仅理解了鲁迅的作品,还深刻认识到了现实的真相。也正是在这种认同中,鲁迅的作品被一次又一次地重新书写,并在不同的时代社会中给人们带来力量。
结 语
随着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当代大众媒介对鲁迅及其作品的挪用与重构现象越来越普遍。技术的创新为鲁迅改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人们能够通过更多的方式认识、理解和阐释鲁迅。鲁迅改编与当代社会的接合,既建构起了鲁迅及其作品在当代社会中的现实价值和意义,也建构起了当代流行文化、青年文化的身份认同。虽然互联网创作中大量涌现的鲁迅改编,其质量参差不齐,但不难发现,只有那些真正理解鲁迅,也真正清醒地认识现实的创作者,才能在大众媒介的建构中,获得受众的肯定与喜爱。因而,人们或许不必太过悲观地看待当代大众媒介建构下的鲁迅改编。大众媒介并未削弱鲁迅改编的深刻性,反而使其更贴近人们的生活,在型塑人们日常行为的过程中,使其价值得以实现。正是在与新的社会语境的重新接合过程中,鲁迅及其作品的精神和思想才能走出传统的阐释模式,与大众产生真正的共鸣。当代流行文化、大众文化中的鲁迅改编以另类的方式推动了人们对鲁迅作品的理解。在教科书式的解读之外,人们重新认识了鲁迅的作品及其思想精神,并使之成为自身情感的一种表达方式。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鲁迅改编,使得人们的自由表达成为可能,使每一个平等的个体都能够以自身独特的方式理解和解读文学、艺术。这正是当代大众媒介建构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注释:
①美国文化、大众文化、传媒研究者,曾主编国际学术刊物《文化研究》(CultureStudies)、《大众文化》(PublicCulture),在文化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