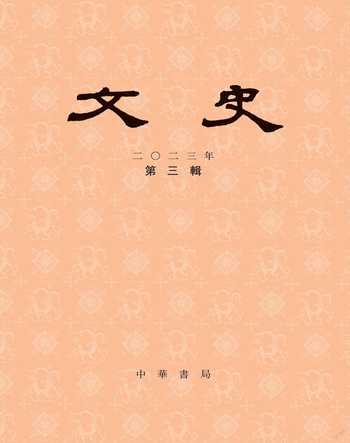四怯薛與各愛馬:元代怯薛的二元組織架構
2023-12-25陳新元
陳新元
提要:元代文獻中“愛馬”一詞,一般理解爲諸王、貴族投下,其實也時常指代怯薛的一種下屬單位。怯薛各愛馬以諸執役分支爲基幹構建而成,這些執役分支完成愛馬化進程的時間遠比學界過去推想的要早,至遲在世祖中後期,各主要執役分支就已實現由執事團體向愛馬集團的轉變。愛馬在怯薛管理體制當中主要負責處理日常行政事務,其職能大致分爲掌管財政收支和操辦人事選舉兩大塊。四怯薛與各愛馬在組織上相互平行、互不隸屬,怯薛内部之所以形成這種二元組織架構,歸根到底是由於它需要同時承擔宿衞宫禁和打理皇室家政兩項職能。
關鍵詞:元代 怯薛 愛馬 組織架構
怯薛(keig)是元朝特有的一種政治、軍事機構,其名號來自突厥語詞kzig,原意是“輪流值班”,後被蒙古人借來稱呼輪班值守的宿衞軍。元人根據怯薛分爲四個班組來番值的特點,習稱其“四怯薛”。蒙元怯薛職能非一,不僅負責拱衞皇帝(大汗)的人身安全,還承擔着服侍皇帝衣食起居、出行享樂的任務,“近侍帷幄,湛露龍光”,在高層政治生活中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
怯薛是元廷中與皇權聯繫最爲密切的機構,其組織架構問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最早梳理怯薛内部設署分職情況的是箭内亘,他僅依照《元朝秘史》,將全體怯薛成員簡單分成宿衞(kebtel)、箭筒士(qori)和侍衞(turqaud,即《秘史》所稱之“散班”)三大職業群組,各自編入四怯薛的框架之中;接下來,蕭啓慶亦考察過怯薛的組織體系,指出怯薛内部的職業分工複雜,除宿衞、箭筒士和散班之外,還設有其他多種爲皇帝打理家務的執事部門,這些部門統一歸屬於四個怯薛長領導;此後,姚大力同樣討論了怯薛的内部結構,設想怯薛之中存在着一種金字塔式的領導體制,其層級自上而下分别爲:怯薛之長(四怯薛首領)、怯薛官(“怯薛執事當中各色帶班的首長”)和一般怯薛歹。以上三位學者對怯薛組織結構的認識,本質上大同小異,都認爲怯薛内部實行的是一種四怯薛框架下的一元管理體制,所有執役分支皆由四個怯薛長垂直指揮和統領。
片山共夫的看法與上述諸人有所不同,他廣泛利用正史、文集及金石材料,深入考察怯薛中專門掌管鷹獵事務的執役分支—昔寶赤(ibaui),指出整個昔寶赤部門所轄不僅涵蓋少數在宫廷中活動的近侍昔寶赤,而且包括數量衆多、散居在全國各處的地方昔寶赤,其組織體系早已溢出僅在宫墻内執役的四怯薛之外。片山氏的見解極具啓發性,儘管他並未明確否定四怯薛首領對昔寶赤的管轄權,但却點出了有大量該分支成員並不屬於四怯薛編制序列的事實,使人思考怯薛内部是否另有一套獨立於四怯薛的管理體制。
總的來看,前賢圍繞怯薛的組織架構問題雖多有討論,但仍有若干不足:從史料方面來説,對《通制條格》《元典章》《至正條格》及《元史》諸志的挖掘和運用尚有欠缺,而這些典志文獻恰好是探索怯薛内部結構時最值得重視的基本史料;就研究方法而言,在處理從蒙古文翻譯過來的漢文材料時,未能充分運用多語種史料互證的手段,解讀出原文中被漢文語境所遮蓋的重要信息,導致立論大多建立在翻譯者的表述之上,根基不牢。
本文擬在前人討論基礎上,全面考察元代怯薛的組織結構,主要聚焦於各執役分支而非四怯薛,力圖解決兩個問題:一,各執役分支作爲怯薛内部的下屬機構,在元代理應有一個官方稱謂,該名稱究竟爲何?二,四怯薛與各執役分支之間,是否如前賢所認爲的那樣,是一種簡單的上下級關係?倘若不然,實際情況又到底如何?
一、元代怯薛中的愛馬、各枝兒
“愛馬”(或作“愛麻”)一詞,是元人對蒙古語詞ayimaq的漢語音譯,該詞在13—14世紀的蒙古語中指代一種社會組織,弗拉基米爾佐夫認爲中世紀蒙古人所稱之ayimaq指:“互有親族關係的家族,從古代氏族(斡孛客)的分裂中産生出來的不同分支的聯盟或結合體。”《元朝秘史》第156節的旁譯部分直接將其釋爲“部落”。
源自蒙古語的外來詞愛馬,在元代漢文史籍中頻繁出現。一種頗具代表性的觀點認爲,元代的愛馬基本可與“投下”對應,其具體義項在不同場合下略有差別,但主要有兩種:一,指千户軍事遊牧集團;二,指王公貴族的封地封民。至於“各枝兒”,則是ayimaq複數形式的漢語白話意譯,簡言之就是各愛馬,學者解釋稱:“各枝兒,元代俗語。通常指各投下,即諸王貴族的封地或私屬人口。”
投下分封制度是蒙元史研究的熱門話題,因此作爲諸王、貴族投下之代名詞的愛馬早已爲衆所悉,然甚少有人注意,“愛馬”“各枝兒”在元代文獻中時常同怯薛相聯繫。李治安孤明先發,最早揭櫫二者之間的關聯,意義重大。李先生已抉出《至正條格》中的幾則關鍵性史料,因其亦爲本文立論根基,爲便分析,仍不憚贅録如下。
先看《條格·倉庫·支請怯薛襖子》:
元統二年二月初七日,中書省奏:“户部官俺根底與文書:‘比年以來,各衙門俸官、閑良官員,畸零索要怯薛襖子的多有。車駕行幸上都,直至臨期,才動事頭,虚實難以稽考,一概支請段匹有。今後委係見行應當怯薛人員,須要各愛馬、怯薛官總押事頭,年終到監,比及三月終,給散了畢。若有過期擬不支付,將孛可孫依例治罪的,説有。依他每定擬來的,各處徧行文書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
再看《條格·厩牧·宿衞馬疋草料》:
天曆二年正月,吏部議得:“度支監關:今後各衙門除授怯薛人員,隨令供報端的是何人氏,自幾年月日,於是何怯薛、某愛馬内千户、百户、牌子某人下應當何等名役,每年某官署押事頭,與若干人一同支請衣糧、馬疋草料,至今已幾年,備細供報明白。拘該委用衙門,先行勘會是實,方許除授。吏部憑准,行移宣徽院、太府監照勘衣糧,户部照勘年例鈔定,度支監照勘馬疋草料。如是檢照得名字稍有差訛,或音同字異,許令供報。其所指怯薛、愛馬争差不同,不許再行補答。有初任已經照勘草料,次任除授不須再照。”都省議得:“上項事理,度支監委令文資正官、首領官專一提調,置簿銷附,設法關防,餘准所擬。”
以及《斷例》部分的《厩庫·用斛支糧》:
至元三年十一月初九日,中書省奏:“去年奏了:‘怯薛丹各支兒根底,合與的米糧、馬料并俸米,教斛裏起與者。麽道,説來。如今各怯薛官并衆怯薛丹人等,俺根底説有,‘怯薛丹的支糧、馬料,斛裏不與,用斗支與的上頭,好生少了。麽道,説有。俺商量來:他每既是用斛收受。又除了鼠耗,似這般斗裏支呵,怎中有?今後怯薛丹各支兒内外倉分裏合支的米糧、馬料及俸米,教斛裏支與。少了呵,初犯,倉官決貳拾柒下,斗子參拾七下,親臨提調運司官柒下。再犯呵,依等第加等斷罪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
三件公文都涉及向怯薛成員分發財物的問題,對怯薛内部管理體制多有呈現。《支請怯薛襖子》條規定,怯薛歹在支請襖子(參加内廷大宴時所穿之只孫服)時,須在每年年終之前向掌管收支只孫段匹的太府監提供有“各愛馬、怯薛官總押事頭”的證明材料,表明自身確係“見行應當怯薛人員”,方可在次年三月皇帝巡幸上都之前領取衣物;《宿衞馬疋草料》條規範了怯薛人員出職除官時的審查程式,怯薛歹在出職時需向吏部提交每年“支請衣糧、馬疋草料”的完整記録,不僅須説明其人爲四怯薛當中哪一怯薛的成員,還要釐清自己到底是在“某愛馬内千户、百户、牌子某人下應當何等名役”,供報明白之後,各衙門才能爲其授官;《用斛支糧》條處理怯薛口糧發放過程中出現的舞弊問題,重申了後至元二年(1336)的一通命令,向“怯薛丹各支(枝)兒”提供食糧時必須用斛支散,不得换成斗來克扣斤兩。
從怯薛制度研究者的角度來看,這三份公牘裏最引人矚目的是“各愛馬”“某愛馬”“各支兒”等字眼。由於上述公牘的大意都比較簡單明了,全文談論的僅限於御位下怯薛内部事務,不及其他,因此能够肯定,所謂“各愛馬”“各支兒”應與一般所稱之諸王、貴族投下無關,而“怯薛丹各支兒”的提法則表明,它們是怯薛的一種下屬機構。
這些“愛馬”“各支兒”具體指代什麽?李治安認爲是指怯薛的各執役分支,他援引《元典章》爲據:“至大四年四月初九日,特奉聖旨:‘昔寶赤愛馬裏,休教漢兒人行者……麽道,聖旨了也。欽此。”這條材料相當有力,證明元人確實把昔寶赤之類的怯薛執役分支叫做愛馬。此外,還可補充其他兩則史料。
其一見於元末文人高徵《重修顯靈王廟之記》碑:
至正癸巳(1353)孟夏日,扎安赤愛馬譯史教化的□乎言曰:“昌平東一舍許,有墅粤芹城,泉甘土肥,風俗淳樸,舊有關王廟存焉,經值年深,不蔽風雨。時則有若御位下管領扎安赤愛馬達魯花赤火者,慨然有志,協謀僚友達魯花赤六十、耆宿馬資、馬欽,重爲修理,僉曰:唯唯……”
文中扎安赤(aani),詞根來自蒙古語的aan(象),意爲“馴象人”,御位下扎安赤則是怯薛裏專門負責馴養大象的執役分支。據此碑,怯薛中被稱之爲愛馬的執役分支顯然不只有昔寶赤。
其二見於《高麗史·兵志一》:
(恭讓王元年)十二月,憲司上疏:“……自事元以來,昇平日久,文恬武嬉,禁衞無人。乃於近侍、忠勇,皆設護軍以下等官,以代禁衞之任而禄之,於是祖宗八衞之制,皆爲虚設,徒費天禄。而其迃達赤、速古赤、别保等各愛馬,寒暑夙夜,勤勞甚矣,而不得食斗升之禄……”
王氏高麗政權向元朝稱藩後,曾模仿蒙古人在宫廷中設置過一整套怯薛機構,迃達赤
(eteni,司閽者)和速古赤(kri,掌服御者)都是元朝御位下怯薛中固有的執役分支,高麗人以愛馬呼之,所遵循的自是元人稱法。
結合上述三條記載,可確認愛馬是元朝官方對怯薛執役分支的正式稱謂,《至正條格》等典志文獻提到的與怯薛有關的各愛馬、各枝兒,指的都是怯薛下屬的各執役分支。
二、怯薛各愛馬的成立時間
元代除了貴族投下之外,怯薛内部的執役分支亦被官方稱作愛馬,然而各類史籍中全然不見大蒙古國時期使用這種稱法的踪迹,不僅如此,通過《元朝秘史》第224—232節可知,成吉思汗時代的怯薛組織架構之中,並無執役分支愛馬。那麽,那些内部下設千户、百户和牌子(十户),組織規模膨脹到足以與四怯薛並稱的各愛馬,形成於何時?
李治安認爲,“愛馬”“各枝兒”延伸進入怯薛内部用以指稱昔寶赤等怯薛分支,是ayimaq的詞義在元代後期所發生的一次較大變化,經過這次變化,ayimaq在“具有血緣關係的親屬群體”“貴族那顔所屬軍民集團”等基本含義的基礎上,又發展出了“部”“集團”“支系”等衍生義。换言之,怯薛各愛馬形成於元代後期。李先生主要據《至正條格》立論,該書中明確提及怯薛“愛馬”“各枝兒”的公文基本都發布於文宗、順帝年間,以順帝朝居多。但如將視綫擴展到元代其他典志文獻,就會察覺實情並非如此。
《通制條格》和《元典章》收録的元中期公文中,將怯薛執役分支稱之爲“愛馬”“各枝兒”的例子頗多。最爲典型的莫過於前揭《元典章》中使用了“昔寶赤愛馬”提法的公文,其主體便是仁宗在至大四年(1311)剛上臺時發布的一道聖旨,出自愛育黎拔力八達本人之口的“昔寶赤愛馬”字眼足以表明,至遲在仁宗初年,怯薛中的昔寶赤愛馬就已成立。
《通制條格·雜令·冒支官物》進一步證實了愛馬在仁宗初年的御位下怯薛中的廣泛存在:
至大四年五月初七日,中書省奏:“‘支散聚會襖子的上頭,重冒休索者。麼道,各愛馬裏省會了來,支散的官人每,幾枝兒重冒要的拏住有。帖木迭兒丞相等俺商量來,既奉皇帝聖旨省會了,做無體例的,將他每的分揀的孛可温每,要了罪過,重冒支了襖子的人每,只于萬億庫前面教號令了,將他要了的襖子納了,要了罪過,怯薛裏教出去呵,怎生?”麽道,奏呵,“那般者”,麽道,聖旨了也。欽此。
元制,新帝即位要在忽里台大會期間舉辦盛大的只孫宴招待來賓,與會的宗室、外戚、貴族和怯薛近侍須身穿特賜的只孫服。至大四年三月仁宗即位前後,政府曾頒賜大批“聚會襖子”,然在分發過程中出現許多舞弊冒領的現象,這份文書記録的正是對弊案的處理結果。
由負責追查此事的中書省奏請處罰怯薛中司職發放衣糧的孛可温(bkel)和要求將冒支者逐出怯薛來看,此次“支散聚會襖子”的發放對象僅限於四怯薛成員,與其他宗室、外戚無關,“各愛馬裏省會了來”一句所稱之各愛馬,是指怯薛的各執役分支,而非諸王、貴族投下。
除了“愛馬”以外,“各枝兒”一詞在仁宗朝官文書中也時常同怯薛聯繫起來。如《通制條格·户令·怯薛元役》:
延祐元年十月二十二日,中書省奏:“郎忙古歹小名的人,根脚裏係運糧船户,在後寶兒赤裏行呵,完澤篤皇帝時分,寶兒赤官人每奏了,將他根脚裏當的差役教除豁了來,漕運司官人每又教當役有。‘教除豁了他元當的差役,只教寶兒赤裏行者。麽道,驢驢、三閭等奏了,俺根底與了文書來。似這般,各枝兒裏行的多有,將他元當的差役除豁了呵,怎中?不教除豁他元當的差役,教寶兒赤裏行呵,怎生?”奏呵,“依體例教當役者”。麽道,聖旨了也。欽此。
該公文的主角郎忙古歹(疑爲南人)元係運糧船户,後來夤緣投入怯薛當了寶兒赤(bauri,
司膳),他原本應承擔的船户差役遂由寶兒赤官人奏請成宗而免除,但漕運司不滿此裁決,圍繞郎氏的差役問題與寶兒赤方面一直纏訟到仁宗上臺之後。中書省認爲,像郎忙古歹這樣的情形,在整個怯薛中很常見,“各枝兒裏行的多有”,如果將除豁的口子一打開,就會影響差役制度的正常運作,因而駁回了讓郎忙古歹免除元役的聖旨,重新安排此人去應役。這裏的“各枝兒”仍舊是指包括寶兒赤在内的怯薛各執役分支。
上面分别列舉了怯薛“愛馬”及“各枝兒”在仁宗朝公文中用例。還有用“本枝兒”一詞來指代怯薛執役分支者,《通制條格·禄令·馬疋草料》云:
至大四年九月,中書省奏:“官人每一處行的,支請馬疋草料的多有,怯薛裏真實宿睡的,本枝兒相合着要也者。官人每一處行的人每根底,不與呵,怎生?”奏呵,“休與者”。麽道,聖旨了也。欽此。
“本枝兒”,點校者釋爲“皇族宗親”,恐非,因爲該文書主要談的是有官職的怯薛成員(即原文所稱之“官人每一處行的人每”)是否應支請馬疋草料的問題,這些在政府部門做官的怯薛歹無論如何也不會跑去各投下領取草料。而“怯薛裏真實宿睡的,本枝兒相合着要也者。官人每一處行的人每根底,不與呵”意謂,全職在宫中輪班值宿的怯薛歹,其應享有的馬疋草料由所屬執役分支集中發放,如在外朝做了官,却不參加輪值的,就無此待遇。儘管“本枝兒”對應的蒙古語原文究竟爲何還有待研探,但“枝兒”即怯薛愛馬,這一點毫無疑義。
總之,爬梳仁宗朝官文書,以“愛馬”“各枝兒”“本枝兒”等詞來稱呼怯薛執役分支的做法在元代中期已相當普遍,不待後期才出現。上述四件公文的年代,其中三件記録至大四年仁宗即位之初的情況,這似乎表明,怯薛執役分支的愛馬化在時間上仍有上探之可能。的確如此,武宗時官文書中同樣有“各枝兒”與“怯薛”連用之例:
大德十一年九月,江浙行省:
照得近爲住支雜職官禄米,移准中書省咨該:“〔來咨:〕‘本省所轄蒙古教授、醫學教授、平准行用等庫,俱係遷轉人員,合得禄米依例支給。准此……送户部議得:‘各處平准行用庫、直隸行省懷致庫、廣濟庫,如無職田,不曾于各枝兒應當怯薛,别名色支請口糧,自承准月日爲始,驗俸支付相應。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該咨文主要解決應向哪些雜職官支付俸米的問題,據户部意見,應當怯薛者即使擔任了倉庫官,也要被排除在領取俸米的範圍之外,因爲他們已享有歲賜,不宜再向官方支取薪給。引文中“各枝兒”,有學者將其解讀爲諸王、宗戚投下,而實際上指怯薛内部的各愛馬,原因是:一,元代諸王宿衞士到政府部門中出任雜職官的現象比較罕見,當局似無專門針對這批人出臺政策之必要;二,以愛馬爲單位向怯薛關支口糧是元朝慣例,聖旨當中便有把發放給全體怯薛歹的糧食稱之爲“各枝兒怯薛丹口糧”的説法,相較於諸王投下,將怯薛成員“别名色支請口糧”的對象—“各枝兒”解釋成其所屬執役分支更合情理。同類例子還見於《元典章·聖政》至大改元詔書:
大德十一年十二月,至大改元詔書内一款:
近爲漢人南人軍、站、民、匠等户,多有投充怯薛歹、鷹房子等名色,影占差徭,濫請錢糧,靠損其他人户。已自元貞元年爲始分揀,今後除正當怯薛歹蒙古、色目人外,毋得似前亂行投屬。其怯薛歹各枝兒官員,亦不得妄自收係。違者並皆治罪,監察御史、廉訪司嚴加體察。
這裏的“怯薛歹各枝兒”,點校者斷作“怯薛歹、各枝兒”,將“各枝兒”當成了一般意義上的貴族投下來對待,這種理解不符合詔書原意。首先,這款聖旨條畫僅針對漢、南人依靠“投充怯薛歹、鷹房子(昔寶赤)”來影占差徭的問題,無一處涉及諸王、宗戚投下;其次,《至大改元詔》的另一款條畫明確提及貴族投下,稱“諸王駙馬各投下”,與“怯薛歹各枝兒”判然有別。所以,武宗改元詔書所稱之“怯薛歹各枝兒”,仍是指愛馬化之後的怯薛各執役分支。
以上確認了“各枝兒”亦存在於武宗朝怯薛之中的事實,但這並不等同於説怯薛執役分支的愛馬化就是從武宗時代開始的。據現存元代公文判斷,“各枝兒”在怯薛内部的出現,至少可追溯到成宗期間,其中一條關鍵證據見《通制條格·雜令·分間怯薛》:
大德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中書省奏:“四怯薛裏怯薛歹人數明白有。近年以來,内外城子裏的百姓内,回回、畏兀兒、漢兒、蠻子人等,投充昔寶赤、阿察赤、怯憐口各枝兒裏,并諸王、駙馬、公主、妃子位下投入去了的多有,‘做了怯薛歹也,麽道,支請錢糧、馬疋草料,此上多費耗了係官錢糧有。更似這般,壹、二年不敷支持。在先曾有聖旨來:‘到(大)〔上〕都呵,木八剌沙平章根底不商量了,休教入去者,到大都呵,省官每根底不商量了,休交入去者。有聖旨來。那言語不曾行。可憐見上位有嚴切聖旨呵,省、院、臺裏,各枝兒裏,摘委着不覷面皮的人好生分間呵,多省減錢糧也者。商量來。”奏呵,奉聖旨:“您説的是。那般行者。街市漢兒人每也‘投入去行。麽道,説有,委好人嚴切分間者。”欽此。
大德七年(1303)二月,元廷清理御位下怯薛,將一批無“根脚”的漢人、南人逐出怯薛,該條正是記録此次沙汰行動的決策經過。文中兩次提及的“各枝兒”,黄時鑒、方齡貴均理解作諸王、宗戚投下,遂把第一處的“各枝兒裏”與“投充昔寶赤、阿察赤、怯憐口”之間點斷,將其同下文“并諸王、駙馬、公主、妃子位下投入去了的多有”連讀。然“各枝兒裏”中的“裏”字實是蒙古語向位格助詞“dur/dr、tur/tr”的漢譯,含義爲“向……”,在語法上起着爲動詞“投充”指示對象的作用,如把“投充昔寶赤、阿察赤、怯憐口”與“各枝兒裏”斷開,這句話就失去了幫動詞指示對象的格助詞,按蒙古語語法不能成句,故此處“各枝兒裏”無疑應與前文連讀,而“各枝兒”則是在句中充當“昔寶赤、阿察赤、怯憐口”的同位語,指代怯薛中的各愛馬。另外,中書省要求從“各枝兒裏,摘委着不覷面皮的人好生分間(怯薛)呵”,亦爲判明“各枝兒”所指提供了依據。《至正條格·斷例·衞禁·分揀怯薛歹》與上引文性質極近:
至順元年閏七月初十日,中書省奏,節該:“各怯薛、各枝兒裏,將無體例的漢人、蠻子并〔高麗〕人的奴婢等夾帶着行呵,將各怯薛官、各枝兒頭目每,打伍拾柒下……將不應的人,看覷面情,不分揀教出去,却將合行的分揀擾害呵,將各怯薛官、各枝兒頭目每,并孛可温、亦里哈温,只依這例,要罪過……不應行的漢人、蠻子、高麗人每的奴婢,并冒名數目等有呵,怯薛官、各枝兒頭目盡數分揀出去。其有體例合行的每根底,依舊與衣糧,不依體例行的,教監察御史每好生用心體察者。各怯薛、各枝兒裏曉諭呵,怎生?”奏呵,奉聖旨:“是有。與的每根底,依恁商量來的,與者。”
《分揀怯薛歹》條比《分間怯薛》條晚發布數十年,但依舊重申了由“各枝兒”派員參與清理怯薛,足見這是元代傳統做法。《分揀怯薛歹》條所稱之“各枝兒”清楚指代怯薛各愛馬,援此可推定同類文書《分間怯薛》條中“各枝兒”也指怯薛各執役分支,而非前人以爲的諸王、駙馬投下。
以上不厭其煩地徵引元歷朝公文,是想建立一條時間綫索完整的證據鏈,來説明“愛馬”“各枝兒”開始用來指稱怯薛内部分支的年代要比學界此前設想的早得多。不過,元代官文書存世數量有限,查尋硬譯體公牘中的關鍵字,只能將愛馬在怯薛中的出現溯及至成宗朝,世祖以上則無從稽考。
怯薛各執役分支的愛馬化是否濫觴於成宗朝?恐非如此。成宗“以簡重守成功”,其施政以恪遵乃祖成憲而聞名,不大可能對怯薛這種宫廷核心機構作大幅組織改造,且從中書省安排“各枝兒”同省、院、臺一道參加大德七年的沙汰行動來看,作爲管理單位的各愛馬似已在怯薛内部運作了很長一段時間,全然不像是成宗年間才成立的樣子。
事實上,大多數怯薛執役分支至遲在世祖中後期就已完成了愛馬化的進程,表明這些愛馬業已成立的標誌性事件是至元二十一年(1284)對怯薛的江南戶鈔分封。四怯薛及各執役分支在此次分封中的受賜情況,詳《元史·食貨志三》:
昔寶赤:江南户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衡州路安仁縣四千户,計鈔一百六十錠。
八剌哈赤:江南户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台州路天台縣四千户,計鈔一百六十錠。
阿塔赤:江南户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常德路沅江縣四千户,計鈔一百六十錠。
必闍赤:江南户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袁州路萬載縣三千户,計鈔一百二十錠。
貴赤:江南户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和州歷陽縣四千户,計鈔一百六十錠。
厥列赤:江南户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婺州永康縣五(十)〔百〕户,計鈔二十錠。
八兒赤、不魯古赤:江南户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衡州路酃縣六百户,計鈔二十
四錠。
阿速拔都:江南户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廬州等處三千四百九户,計鈔一百三十
六錠。
也可怯薛:江南户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武岡路武〔岡〕縣五千户,計鈔二百錠。
忽都答兒怯薛:江南户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武岡路新寧縣五千户,計鈔二
百錠。
怗古迭兒怯薛:江南户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常德路龍陽縣五千户,計鈔二
百錠。
月赤察兒怯薛:江南户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武岡路綏寧縣五千户,計鈔二
百錠。
該名單中有兩處需略加説明:首先,這並不是一份完整的受封名單。寶兒赤、速古兒赤、火兒赤(qori,箭筒士)、云都赤(ldi,佩刀守禦者)等執役分支的受賜情況在這份名單中無一字提及,以情理揆之,在八兒赤(barsi)這種邊緣部門都已獲得分封的情況下,寶兒赤、速古兒赤等腹心分支没有理由被忽必烈排除在外,《元史·食貨志》的失載,應是由於《經世大典》或《元史》的編纂者遺落所致;其次,榜單中提到的阿速拔都,在名稱上與以“赤”結尾的其他執役分支有較大差異,前人認爲是指阿速衞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司的前身—至元九年創設的阿速拔都達魯花赤,其實它仍屬於御位下怯薛的一個内部分支,依據是:一,從這份榜單的條目編排體例來看(應承襲自《經世大典·賦典》),纂修者把“阿速拔都”置於諸赤之後、也可怯薛之前,顯然是將其視爲怯薛的一個組成部分;二,有確鑿的證據表明,忽必烈時代曾有成建制的阿速人在怯薛中服役,《元史·兵志二》云“右阿速衞:至元九年,初立阿速拔都達魯花赤,後招集阿速正軍三千餘名,復選阿速揭只揭了温怯薛丹軍七百人,扈從車駕,掌宿衞城禁……”,清楚指出執役於怯薛的阿速人是阿速拔都達魯花赤的兩大來源之一,而這批人的數量至少有七百名之衆,稱得上是怯薛内一個規模較大的下屬單位;三,將阿速與其他怯薛執役分支並舉的提法,除《元史·食貨志三》之外,在《元史·世祖紀》中亦出現過一次,至元二十二年二月壬戌“賜合剌失都兒新附民五千户,合剌赤、阿速、阿塔赤、昔寶赤、貴由赤等嘗從征者,亦皆賜之。以民八十户賜皇太子宿衞臣嘗從征者”。這次分封主要面向的是宿衞士“嘗從征者”,受賜人員被元廷按照其所屬執事部門作了分類,從阿速與合剌赤(qarai,司湩乳者)、阿塔赤(aqtai,司騸馬者)、昔寶赤、貴由赤(gyki,疾足快行者,即貴赤)赫然並列來看,主事者顯然把阿速當成了與後四者地位平等或相近的單位。綜上,可斷言《元史·食貨志三》提到的阿速拔都並未涵蓋阿速拔都達魯花赤的全體成員,而是僅包括執役汗廷的阿速宿衞士,這批人在御位下怯薛内部組成了一個獨立的下屬單位。
該名單篇幅不長,但信息豐富。值得詳加闡明的有三點:第一,至元二十一年的怯薛江南户鈔分封,是以團體而非個人爲受賜對象,易言之,元廷向四班怯薛及各執役分支(含阿速拔都)所頒賜的江南民户,歸該怯薛或執役分支的全體部衆共有,其所有權之性質與怯薛歹以個人名義受封者截然不同。二者的差異,在《元史·食貨志三》的編纂體例中已有所體現,凡以個人身份獲賜民戶的怯薛歹,修撰者爲其編列條目時都注明了姓名、怯薛職使和食邑類型,如:
哈剌赤秃秃哈:江南户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饒州路四千户,計鈔一百六十錠。
阿剌博兒赤:五户絲,壬子年(1252),元查真定五十五户。
前揭諸赤條目則僅登載了各執役分支的名稱,未提到任何怯薛歹的姓字,足證其受賜主體是整個執役分支,與個人無關。
第二,作爲一種以集體名義享有的食邑,各怯薛及各執役分支在至元二十一年所獲得的户數之衆寡,與該集團的組織規模呈現出一種正向關聯性,即:組織規模越大,受賜户口就越多。從理論上來説,四班怯薛是當時怯薛内成員數目最多的下屬單位,故每班怯薛均獲賜五千户,在分封名單中排名榜首。與之反差强烈的是,衆執役分支中的厥列赤只獲得了五百户,八兒赤和不魯古赤相加亦只有六百户,此三者正是小執役分支的代表。怯薛分支集團的組織規模與受賜户數之間的正向相關性,爲根據各執役分支與每班怯薛的受賜户數之比大致估算前者的成員編制提供了可能,拿八兒赤和不魯古赤來説,它們所獲得的户數只有每班怯薛的二十五分之三,那麽按比例推斷,其下轄成員合計應只有300人左右,由於八兒赤、不魯古赤這兩個冷門分支的規模很小,所以300人的數目比較合理。再來看昔寶赤,若按相同比例來計算的話,受封四千户意味着該執役分支擁有約2000名部衆,這當然並非昔寶赤集團的實際成員數目,而是表示元廷爲昔寶赤分支設立了兩個千户的編制,著籍於此二千户的昔寶赤可享受怯薛正式成員的待遇。簡言之,通過比例换算,可大概推估出《元史·食貨志三》中所開列的每一執役分支的成員編制。從换算的結果來看,凡食邑超過三千户的執役分支都達到了設置千户的標準,這一時期的史料也直接證實了千户組織在執事部門内部的存在,如《元史·阿沙不花傳》云:“乃顔叛……帝乃議親征,命徵兵遼陽,(阿沙不花)以千户帥昔寶赤之衆從行。”許有壬撰《鎮海神道碑》稱:“世祖立極,又以公(鎮海)舊部及降虜千人爲貴赤,命公之孫莊家爲千户,曾孫也里卜花爲百户。”考慮到怯薛各執役分支的成員規模在至元中後期均都有不同程度的擴張,有理由相信昔寶赤、貴赤之外的各大執役分支内部應也出現了千户、百户、牌子的建制,在組織架構上已具備愛馬集團的雛形。
第三,至元二十一年面向怯薛的江南户鈔分封,創造了一種以怯薛下屬單位爲領主的特殊食邑投下,確立了各執役分支與元廷頒賜民户之間的領屬關係。怯薛下屬單位所領有的江南户鈔食邑可否稱之爲投下,元代文獻中無直接記載,但《元典章新集》提供了一條間接證據:
延祐六年三月□日,袁州路奉江西行省劄付:
來申:“分宜縣怯憐口四千户長官司、萬載縣三千户計勾當,元撥户設置,止是催辦本投下差役。今恃倚别無親管上司鈐束,又與本路不相統攝,往往違例受理刑名詞訟,擅便斷決,妄招户計,影避差徭……
這裏點到的分宜縣怯憐口四千户,植松正指出歸世祖第二斡耳朵所有。《元史·食貨志三》云:“第二斡耳朵:歲賜,銀五十錠,又七錠,段一百五十匹。江南户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袁州路分宜縣四千户,計鈔一百六十錠。”可見分宜縣的怯憐口四千户同樣屬於以集體而非個人名義領有的江南户鈔食邑,且根據分封時間推測,十有八九係與怯薛各執役分支同時獲賜,既然世祖第二斡耳朵名下的四千户已被元朝地方政府視爲投下,那麽怯薛各執役分支占有的江南民户自然也應被納入食邑投下的範疇。
以上考證釐清了兩個事實:一,至元中後期,比較大的執役分支内部普遍分設千户、百户,在組織上已經具有了愛馬集團的雛形;二,至元二十一年的江南户鈔分封使得各執役分支擁有了屬於自己的食邑投下和大批投下民户。李治安强調,在理解投下、愛馬的本義和引申義時,有兩個因素應特别注意:投下的外在形式—部、集團和投下的内在聯繫—貴族“頭目”與投下民之間的領屬關係,任何一個組織只有兼備這兩重要素,才能被稱之爲投下(愛馬)。而怯薛的各主要執役分支至元二十一年之後無疑同時滿足了成立愛馬的内、外要件,因此可以肯定,它們在元世祖中後期已完成了愛馬化的進程。
最後談一談小執役分支的愛馬化問題。元代怯薛内部的職業體系龐雜,除寶兒赤、昔寶赤等大執事部門之外,還設有一些諸如八兒赤、厥列赤之類的冷門執役分支,此類分支的成員人數一般不多,或有學者懷疑其組織規模能否達到成立愛馬的門檻。實際上,它們最終都演變成了怯薛下屬的愛馬集團。
證據主要有二,其一爲前節所引《重修顯靈王廟之記》,該碑提到的札安赤,是一個在元代史料中極爲罕見的冷門執役分支,成員至多不過數百人左右,儘管如此,該執役分支仍發展成了下設達魯花赤、譯史等官職,擁有完備組織體系的御位下札安赤愛馬,它的存在適足以反映出整個小執役分支群體的愛馬化趨勢。
其二是《元史·順帝紀》云至正十二年(1352)正月“癸亥,刑部添設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各一員,五愛馬添設忽剌罕赤二百名”。此處所稱之“五愛馬”,過去咸以爲是指札剌兒、兀魯兀、忙兀等五投下,但從蒙古語的角度考慮,五投下所對應的是專有名詞tabun-ong,五愛馬則當作tabun ayimaq,二者不能簡單劃等號。更何況《順帝紀》至正十三年十月壬戌云“賜皇太子五愛馬怯薛丹二百五十人鈔各一百一十錠”,足證五愛馬與五投下並無關聯,而是指設置在御位下及皇太子怯薛當中、由五個特定怯薛執役分支所組成的愛馬集團。至於到底爲哪五個分支,現存的元代文獻已不足徵,據明人鄭曉透露的訊息判斷,它們似非人們熟知的大執役分支:“應劭不營十,曰阿速,曰哈剌嗔,曰舍奴郎,曰孛來,曰當剌兒罕,曰失保嗔,曰叭兒厫,曰荒花旦,曰奴木嗔,曰塔不乃麻。”明之應紹不起源於元代的皇室家政機構雲需府,其分部之中,哈剌嗔(Qarain)、失保嗔(ibauin)、奴木嗔(Numu?in,弓匠)都沿襲了元代怯薛執役分支的名稱,而同出怯薛的五愛馬應即塔不乃麻(tabun ayimaq)部前身。相比能够單獨衍生出一支部落的哈剌赤、昔寶赤來説,構成五愛馬的另外五個執役分支在組織規模上顯然要小得多,即使到了明代,也不過才演化成了某個大部落下面的一個小分部而已,然而既然《元史·順帝紀》將其統稱爲五愛馬,那麽它們作爲愛馬集團存在的資格是毋庸置疑的。
總之,怯薛的各個執役分支不管規模如何,無一例外地都經歷了從執事團體擴張爲愛馬集團的過程,八兒赤、札安赤之類的小執役分支開始演化的時間可能略晚於昔寶赤等大執役分支,但伴隨着整個怯薛組織的不斷膨脹,它們最終都完成了愛馬化的進程。
三、四怯薛與各愛馬之間的組織關係
各愛馬與四怯薛的組織關係問題,簡言之就是要弄清前者是否隸屬於後者,受後者管轄。李治安認爲四怯薛與各愛馬之間應是統屬與被統屬的關係,怯薛內部的管理層級則依次爲“何怯薛—某愛馬—千户—百户—牌子”。這五層結構清晰明了、上下有序,不過,把愛馬置於輪班怯薛之下的安排,仍有疑問。
如上節所述,怯薛愛馬的本質是執役分支集團,而執役分支又是由從事相同職業的怯薛歹所組成,因此,每個愛馬都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整體。如果堅持將愛馬視爲四怯薛的下屬組織,那麽當各愛馬被各自分配給四怯薛之後,每班怯薛就只下轄隸屬於自己的愛馬,無法湊全執事部門,這違背學界常識。而假如贊同每個執役分支一分爲四之後,由四分之一成員所構成的群體仍可被稱之爲愛馬的話,那麽怯薛内部又會出現大小愛馬並存、大愛馬之中又包含着四個小愛馬的情況,這也是聞所未聞之事。可見,認定各愛馬從屬於四怯薛的看法在邏輯上尚有無法自洽之處。
更何況,許多反映執役分支内部情況的材料不支持將愛馬歸入輪班怯薛之下的觀點。如《元史·文宗紀》至順元年(1330)八月壬申云:“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言:‘臣等比奉旨裁省衞士……鷹坊萬四千二十四人,當減者四千人……”按此説法,即便經過裁省之後,昔寶赤愛馬的成員仍有上萬名之巨,相反,四怯薛的組織規模則受限於祖制,每班至多不過三四千人,其内部怎麽會包含一個比自身還要龐大的單位?而昔寶赤愛馬的情況在怯薛中並非特例,據《元史·兵志》,御位下哈剌赤僅在折連怯呆兒一處便設有十九個千户,整個愛馬的成員數量與昔寶赤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類似的大執役分支還有貴由赤、阿塔赤,這些愛馬都下轄數千乃至上萬名部衆,絶非只有三四千人的輪班怯薛所能吸納。所以,各愛馬不可能是四怯薛的下屬機構,兩者在組織上到底是何關係,須回歸史料重加檢視。
《至正條格·條格·厩牧》天曆二年(1329)條例是研究該問題不可或缺的材料,爲便討論,再迻録相關部分如下:
天曆二年正月,吏部議得:“度支監關:今後各衙門除授怯薛人員,隨令供報端的是何人氏,自幾年月日,於是何怯薛、某愛馬内千户、百户、牌子某人下應當何等名役……”
如何來看待“何怯薛”與“某愛馬”之間的關係,是判斷各愛馬是否隸屬於四怯薛的關鍵。對此有兩派意見,一派認爲既然該公文把“某愛馬”一詞置於“何怯薛”的後面,就代表兩者之間存在着表示領屬的修飾關係,“某愛馬”統領於“何怯薛”之下;另一派則認爲這兩個詞在句子中充當的是並列成分,它們之間不存在修飾關係。
持前一種觀點者未注意到,在《至正條格》中還可找到不少將四怯薛與各愛馬放在一起相提並論之例。如同樣列於《宿衞馬疋草料》條之下的另一件公文:
延祐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中書省奏,節該:“‘吃俸錢的人每的馬疋草料,依先例與那,麽道,奏呵,奉聖旨有。怯薛的正身人每根底,各怯薛、各枝兒官人每與文書呵,□(與)□(者)。又衙門行的宣使、怯里馬赤、譯史,無數目的、無怯薛的,那般人每根底,休與者。”
又如前引《分揀怯薛歹》條,以及《至正條格·斷例·衞禁·巡綽食踐田禾》:
泰定三年七月二十一日,中書省奏:“每年上位大都、上都往來經行時分,扎撒孫内差撥,教爲頭領着壹伯名怯薛丹巡綽。但有將百姓田禾食踐的,禁約有來……俺如今徧行省諭,若有撒放馬、駝、牛隻,食踐田禾的每根底,壹箇頭疋,令人陪償壹拾兩鈔,斷壹十七下。各怯薛、各枝兒裏徧行省諭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
以上三道公文在描述整個怯薛組織時,全部使用的是“各怯薛、各枝兒”的並列提法,這無疑表明,完整意義上的御位下怯薛是由四怯薛和各愛馬共同構成的,二者之間相互平行、獨立,在組織上並無隸屬關係。如果各愛馬是四怯薛下屬單位,那麽只要用“各怯薛”便可涵蓋整個怯薛,何必畫蛇添足加上“各枝兒”?
四怯薛與各愛馬在組織上的平行地位,主要表現在:作爲怯薛最基本的構成單元,每位怯薛歹同時具有怯薛和愛馬兩種組織關係,在職期間受到其所屬輪值班組和執役分支的雙重管轄。對怯薛成員的二重隸屬,學界過去認識不足,在元人傳記中見到“從某某備宿衞”的記載時,都徑把“某某”當作輪值班組長官來理解,現在看來,此類説法大多表達的是在某位愛馬長官的統領之下執役之義,與傳主的輪值班次所屬毫不相干。下面略舉幾例。
先看《元史·阿魯渾薩理附岳柱傳》:“岳柱(阿魯渾薩理長子)字止所,一字兼山……年十八,從丞相答失蠻備宿衞,出入禁中,如老成人。”丞相答失蠻,據岳柱的年齡推斷,應指貴顯於世祖、成宗兩朝的克烈人答失蠻。答失蠻之生平事迹畢載於姚燧《高昌忠惠王神道碑》和《元史·也先不花傳》。據這兩篇傳記,答失蠻雖在怯薛中地位很高,却並未擔任過掌管輪值的怯薛官(keig-n noyan),其身份僅是世襲的必闍赤長。“從丞相答失蠻備宿衞”的真實含義是説,岳柱入職怯薛時所加入的是必闍赤愛馬,其直屬長官爲克烈人答失蠻。
再看《元史·鐵哥傳》:
鐵哥,姓伽乃氏,迦葉彌兒人……父斡脱赤與叔父那摩俱學浮屠氏……斡脱赤之殁,鐵哥甫四歲,性穎悟,不爲嬉戲……世祖即位,幸香山永安寺,見書畏吾字於壁,問誰所書,僧對曰:“國師兄子鐵哥書也。”帝召見,愛其容儀秀麗,語音清亮,命隸丞相孛羅備宿衞。
鐵哥所隸之孛羅丞相,就是後來遠赴伊利汗國的朵兒邊氏孛羅,余大鈞在勾稽此人生平時,曾據上引材料斷定他作過怯薛長,然而無論在漢地或伊朗的文獻當中,都找不到任何佐證。《史集》所載孛羅早年事迹多半出自其本人之口,若他果真出任過怯薛長這樣顯赫的職務,與孛羅過從甚密的拉施特怎麽會隻字不提?只要將涉及孛、鐵二人怯薛職使的記載略加對照,即可領悟“隸丞相孛羅備宿衞”這句話的真正意涵。《元史·鐵哥傳》云:“鐵哥年十七……(世祖)命掌饔膳湯藥,日益親密。”《史集·部族志·朵兒邊傳》稱:
孛羅—阿合在合罕處擔任丞相和司膳[寶兒赤],並曾任使者來到我國[即伊朗]。他是個顯貴的大異密。他的父親名叫余兒乞,是成吉思汗的廚子,屬於長後孛兒帖旭真的斡耳朵,並曾統率[成吉思汗]直屬千户的一個百户。
孛羅和鐵哥同屬於怯薛中的寶兒赤執役分支,前者還是世襲的寶兒赤長,所謂“隸丞相孛羅備宿衞”,乃是指在孛羅的手下充當司膳。
除鐵哥之外,漢人鄭制宜也曾作過孛羅在寶兒赤中的部屬。鄭制宜字扶威,蒙古語名納懷(noqai,“狗”),他出身於漢軍世家陽城鄭氏,父親鄭鼎是忽必烈的親信,其本人則爲孛羅丞相的女婿,父子兩代都與蒙古上層頗具淵源。關於制宜與孛羅之女的蒙漢聯姻,鄭氏家族的碑傳資料中多有述及,如《鄭鼎神道碑》云:“(鼎)子男曰制宜,賢俊明敏,早有時譽。孛羅丞相愛其才,擢爲子壻,今以平陽、太原兩路管軍萬户鎮守鄂州。”《鄭制宜行狀》亦稱:“(制宜)配可烈真氏,丞相孛羅公之女。”學者已注意到孛羅與鄭制宜之間的翁婿關係,但對兩家如何結下姻緣的内情却不甚了然。其實,孛羅之所以會對鄭制宜青眼有加,與後者的怯薛職使有很大關聯,《鄭制宜行狀》云:
公,忠毅公(鄭鼎)之嫡子也。方勝衣時,忠毅攜見於世祖皇帝,特視偉之,命從大臣習給事儀……詔侍膳殿中……公幼熟内府,營繕工巧供給祠祭之屬,能通達緩急,終歲事集,無曠敗。至大宴席,刀匕樽斝,必命公董領,以重其事。
侍膳內廷、遇大宴席時董領刀匕樽斝,均爲寶兒赤之職責。有理由相信,鄭制宜在寶兒赤愛馬中執役時,頂頭上司正是孛羅,所以孛羅才會有機會注意這位下屬的才幹,進而“擢爲子壻”。
最後來看朱德潤《資善大夫中政院使買公世德之碑銘》:
皇元混一區宇,際天所覆,罔不臣服。于闐尤先效順,時則有若不花剌氏,以佃巧手藝入附,徙置和林,又遷於西京。朝廷設局院,官曹以領之。今資善大夫、中政院使買述丁之曾祖洪城公寔在焉……資善公以李叔固丞相奏,從大都丞相入宿衞。至大中,授尚服院長史……
回回人買述丁早年“以李叔固丞相(即宦官李邦寧)奏,從大都丞相入宿衞”,此大都丞相爲何許人也?據《瓦薩夫史》第4卷“海山合罕登臨汗位”章,大都丞相(Dd Jinksnk)出自木速蠻(Musalmn),是武宗期的顯貴。至於他的怯薛職掌,《秘書監志》收録的一則怯薛輪值史料云:
至大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只(見)〔兒〕哈郎怯薛第三日,玉德殿西耳房内有時分,昔寶赤大都丞相、玉龍帖木兒丞相,寶兒赤朵烈秃,火者太順司徒,速古兒赤抹乞等有來,太尉脱脱丞相、太保三寶奴丞相、伯顔平章、忙哥帖木兒左丞(相)等奏……
大都既列名於只兒哈郎怯薛之下,必非該班的怯薛長無疑,不過,根據他有資格列席御前奏聞來推斷,其人應是武宗身旁地位較高的昔寶赤長之一,“從大都丞相入宿衞”,自然是指在他掌管的昔寶赤愛馬中蒞職。
上舉數例可見元代怯薛歹自入職伊始便處於雙重隸屬的狀態,他們既是四怯薛之中某一輪值班次的成員,也受所屬愛馬(執役分支)管轄。正由於愛馬長官直接領導和管理部屬,部屬的傳記中才會時常提到執役分支首領的名字。
怯薛歹對於四怯薛與各愛馬的雙重隸屬,是這兩大組織系統之間的平行地位在個人層面的體現。而就機構層面而言,這種平等性主要反映在二個組織系統相互包含、滲透上,一言以蔽之:每班怯薛下轄的執事部門涵蓋所有愛馬,同時各愛馬的成員亦遍布於四班怯薛。
上述兩點之中,每班怯薛網羅有全部執役分支,是出於向皇帝提供完整服務的需要,較易理解;至於第二點,稍作考證和解釋。怯薛各愛馬成員在整個怯薛組織内的分布情況,元代典志文獻中記載無多,然而從一些執役分支首領的傳記來看,他們管轄的部屬顯然遍及四班怯薛。如《史集·成吉思汗紀》在述成吉思汗御前千户中的各百户時提到“塔塔兒人也孫—秃阿百户,也孫—秃阿是四怯薛的牧馬長(Amr-i akhtj-yi chahr kizk),隸屬於孛兒帖旭真斡耳朵”,明確指出塔塔兒人也孫秃阿在擔任御前百户的同時還兼任阿塔赤官人(波斯語的amr相當於蒙古語之noyan),四怯薛的全體阿塔赤都由此人統領。又如《元史·鐵哥朮傳》:
鐵哥朮,高昌人。世居五城……曾祖父達釋……達釋之子野里朮……(成吉思汗)甚器重之。丙午,太祖西征,野里朮别從親王按只台與敵戰有功,甚見親遇。王方以絳蓋障日而坐,及聞野里朮議事,喜見顔色,稱善久之,既退,撒其蓋送之十里。遂得兼長四環衞之必闍赤。
畏吾兒人野里朮原在成吉思汗麾下效力,第一次蒙古西征期間一度轉隸宗王按只台(合赤温之子,成吉思汗親侄),當他憑藉戰功升任爲御位下必闍赤長之後,所管轄的正是“四環衞之必闍赤”。
如果説也孫秃阿、野里朮的活動年代偏早,不能反映怯薛執役分支愛馬化之後的情形的話,那麽不妨再關注幾個元代案例。先看八剌哈赤愛馬,元代的八剌哈赤官人之中,聲名最顯赫者莫過於哈剌魯氏柏鐵木爾一家,據《柏鐵木爾家傳》,其家執掌八剌哈赤始於世祖時代:“(伯鐵木爾)祖諱質理華台,備宿衞于太祖第二斡耳朵忽蘭皇后位下。世祖皇帝建都城,立宫闕,以勳臣子孫俾掌門衞,克稱其職。”此後該家族子孫一直世襲八剌哈赤之長,即便貴盛如柏鐵木爾者,在歷任顯宦的同時仍兼領該職,《家傳》云:
某年正旦會朝,上(仁宗)命盡以内外進獻之物賜,王(柏鐵木爾)辭曰:“臣以微才,叨居政府,大懼無以稱塞。兹又加以重賚,何以克堪?願以所賜之物,悉與四怯薛番直司門者,以旌其勞。”上嘉其廉,而衆懷其惠。
由伯鐵木爾請求“以所賜之物,悉與四怯薛番直司門者”之舉可知,全怯薛的八剌哈赤無疑都處於這位愛馬長官的掌領之下。
再看一個必闍赤方面的例子。《元史·斡羅思傳》云:“斡羅思,康里氏……父明里帖木兒,世祖時爲必闍赤,後爲太府少監。斡羅思,至元十九年爲内府必闍赤。二十一年,拜監察御史。”該家族父子兩代蟬聯必闍赤,應是以此執事爲世職。然南士貢師泰對斡羅思之子慶童的怯薛職使却另有表述:“公蚤以勳臣世家之胄遇知仁廟,給事内廷。後長宿衞……”按通常認知,“長宿衞”當作出任怯薛長來理解,但檢仁宗一朝的怯薛輪值記録,怯薛長中實無康里慶童,那麽貢師泰爲何稱其“長宿衞”?泰定元年(1324)的《皇帝登寶位祀北嶽記》碑揭曉了答案:“泰定元年歲次甲子春□月丁巳朔,越七日癸亥,皇帝嗣登大寶,光啓聖□誕修祀事,命速古兒赤領四怯薛必闍赤慶童……奉祀於祠下。”慶童在怯薛中擔任的仍是其家世襲的必闍赤,所謂“長宿衞”,與輪值班次的統屬無關,而是擔任必闍赤長的意思。《皇帝登寶位祀北嶽記》具有官方性質,碑文所載之官職都是元廷的正式頭銜,其中將必闍赤長表述爲“領四怯薛必闍赤”,足以表明整個必闍赤愛馬的成員同樣散布在四個輪值班組之中。
最後舉一個寶兒赤方面的例子。元明善《太師淇陽忠武王碑》云:“月赤察兒……世祖雅聞其賢,且閔其父之死,年十六召見。帝見其容止端重,奏對詳明,喜而謂曰:‘失烈門有子矣。即命領四怯薛太官。至元十七年,長一怯薛。”元氏所稱之“四怯薛太官”,姚大力謂指“總領四怯薛長的最高職務”,多爲學者采信,實際不然。關於“太官”,《漢書》顔師古注釋甚明:“太官主膳食,湯官主餅餌,導官主擇米。”此外,《元史·玉昔帖木兒傳》亦云:“玉昔帖木兒……世祖聞其賢,驛召赴闕,見其風骨龐厚,解御服銀貂賜之。時重太官内膳之選,特命領其事。”足證元代“太官”仍指掌管皇帝膳食的機構,至於“領四怯薛太官”,無疑是寶兒赤官人在漢文語境中的别稱。月赤察兒的寶兒赤官人身份,過去甚少有人留意,據《淇陽忠武王碑》的後文,即使在至元十七年升任怯薛長以後,他仍保留了這一職務:“二十七年,桑葛既立尚書省,簧鼓上聽,殺異己者,箝天下口……尚書平章政事也速答兒,王(月赤察兒)之太官屬也,潛以其事告王。王奮然奏劾,桑葛伏誅。”也速答兒原名帖木兒(避成宗諱改名),兀里養哈氏,名將阿朮之從弟,他所屬的輪值班次在《廟學典禮》中有明確記載:“至元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也可怯薛第二日,昔博赤八剌哈孫内裏有時分,舍兒别赤帖哥、帖木兒平章,必闍赤剌真、脱脱大卿等……”也速答兒在四怯薛當中隸屬於也可怯薛(第一怯薛),並非月赤察兒怯薛(第四怯薛)的成員,所謂“太官屬”,只能是指寶兒赤執役分支的下級。這種在不同輪值班次的寶兒赤之間所保持的上下級關係充分表明,愛馬化之後的寶兒赤執役分支仍是一個由四怯薛寶兒赤共同組成的整體。
限於篇幅和史料,以上僅考察了阿塔赤、必闍赤、八剌哈赤、寶兒赤四個執役分支,但不難想見,其他執役分支的情況應大同小異。從已列舉的案例可見,執役分支首領對部屬的統領和管轄全然不受輪值班組劃分的制約,始終及於四怯薛内的全部本愛馬成員,各愛馬的人事關係並不局限在某一怯薛之内,而是横跨四班怯薛,形成了與四怯薛平行的另一個組織系統。
綜上,各愛馬、四怯薛是兩個各自平行、互不隸屬的行政體系,元代御位下怯薛内部采用的是四怯薛與各愛馬並立的二元組織架構。
四、各愛馬的管理職能
怯薛的二元組織架構決定了其管理體制必然同樣具有二元性,質言之,四怯薛與各愛馬各自都會承擔一部分管理職能。箭内亘已大致梳理過四怯薛的職掌,下面只談各愛馬的部分。
總的來看,各愛馬與四怯薛職掌各有側重,但也非毫無重疊,拿怯薛的核心職能—守衞宫禁來説,固然是由四怯薛所主導,但各愛馬亦有一些機會介入,它們參與宿衞事務的方式,《至正條格·斷例》略有提及:
延祐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書省奏,節該:“……御史臺官奏奉聖旨:‘俺内苑裏的勾當,入怯薛的怯薛官人并怯薛丹扎撒孫、各愛馬的頭目每、留守司官人每、八剌哈赤每等,是他每合管的勾當有。俺衆人商量了,寫定奏目聽讀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麽道,有聖旨來。四怯薛的怯薛官、中書省官、樞密院官人商量來:‘入怯薛的怯薛官、次着的官,各掃鄰裏坐地着,教入怯薛的扎撒孫各門頭守把着,不教空歇了,禁治閑人休入去者。正門上,在先各愛馬裏也教人坐地有來。如今依先例,各愛馬裏教差撥人一同守把……怎生?商量來。”聽讀了奏目文書呵,奉聖旨:“那般者。教伯荅沙明日聚着各怯薛官、扎撒孫每省會了,依這文書體例,好生整治者。”
各愛馬的衞禁職能主要有二:一,各愛馬長官須同其他宫廷官員一起參與内苑(宫城内部)事務的管理,遇事時要參加集體協商;二,按慣例,各愛馬應派員與扎撒孫一道守把宫門,禁治閑人出入。不難看出,在宿衞事務方面,各愛馬僅承擔輔助性工作,部署宫禁守備顯非它們的要務。
處理怯薛的日常行政事務才是各愛馬的主職,具體内容大致可分財政和選舉兩大塊。
首先談財政部分,愛馬這一層級在整個怯薛的財務管理體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因爲怯薛歹所享受的經濟待遇大多是以愛馬爲單位來向下發放,爲此,各愛馬内部專門設置了負責關支衣糧、草料的職務—孛可温(孛可孫)。孛可孫在怯薛中並未形成一個單獨的執役分支,而是多附設於各愛馬之下,舉兩人爲例。
第一位妥桓見於《元統元年進士録》:“(右榜三甲第三十名)燕質傑:貫陵州,怯列歹氏……曾祖也列虔,昔寶赤。祖妥桓,本愛馬裏缽可孫。父執禮化台。”據燕質傑的鄉貫及其曾祖父的職業,該家族應是落籍漢地的昔寶赤,所謂“本愛馬裏缽可孫”,自是指隸屬於昔寶赤愛馬的孛可孫。妥桓生卒年不詳,大致可推定爲世祖朝人,他的仕宦履歷説明,早在忽必烈時代,昔寶赤愛馬中就已設立了孛可孫。另一位是出自康里部的艾貌,他擔任孛可孫的經歷見《元史》本傳:“艾貌拔都,康里氏……又從四太子(拖雷)南伐,命充怯憐口阿答赤孛可孫。”艾貌充當的是怯憐口阿答赤的孛可孫。
妥桓和艾貌之例,足證昔寶赤及阿塔赤愛馬都擁有從屬於本集團的孛可孫,其他執役分支的情形又如何?前引《冒支官物》條或可解答。上文已述,該公文記載元廷對仁宗朝冒支只孫服案的處理結果,負責清查該案的中書省建議,不但要開除有冒領行爲的怯薛歹,還要追究孛可孫們審核不嚴的責任。中書省官員在談到“分揀的孛可溫”時,又冠以定語“他每的”來加以限定,表示這些“孛可温每”從屬於“他每”之下,“他每”究竟指誰?結合上下文,省官所稱之“他每”,只能是指前一句中“皇帝聖旨省會”的對象—怯薛各愛馬。
既然各愛馬内部早就建立了掌管廩餉關支的職官體系,那麽哪些財物是通過愛馬來向怯薛歹發放的?綜合各方面記載,怯薛中米糧、草料、衣物及鈔錠的散給皆與各愛馬相關。
關於怯薛歹米糧的發放方式,前引《至正條格·斷例·厩庫·用斛支糧》中規定整個怯薛關支米糧時,以“各支兒”爲單位向“内外倉分”領取,足見負責發放糧食的正是各個愛馬。至於草料,前引《通制條格·禄令·馬疋草料》所云“本枝兒相合着要也者”,即表達本愛馬集中發放的意思。可見,怯薛成員享有的馬疋草料同樣經過愛馬來供給。
不過,也需注意《元史·百官志》:“度支監,秩正三品。掌給馬駝芻粟……國初,置孛可孫。至元八年,以重臣領之。十三年,省孛可孫,以宣徽兼其任。至大二年,改立度支院。四年,改爲監。”據此,元廷還專門設立了度支監來作爲“掌給馬駝芻粟”的機構,度支監與怯薛各愛馬在供給草料方面,如何劃定各自權責?現存史料並無明文,只能據《至正條格·條格·厩牧》略作懸揣:
延祐元年八月,中書省奏准事理:
一件。去年,“昔寶赤每,教十月裏入大都來者”。麽道,聖旨有呵,預先將鷹入來,教外頭栓的。又將入來了的,也多有來。今年,“教十月先將鷹入來”。麽道,聖旨有來。如今昔寶赤每根底差人去,大都的入來的,十月初一日合裏頭栓的鷹,教將入來者。外頭栓的鷹,教外頭栓者。那裏栓呵,教昔寶赤官人每,度支監官每根底説將來,憑度支監文字,教各州城準備草料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
向昔寶赤發放駐冬草料的程式大致分三步:一,愛馬首領(昔寶赤官人)向度支監提出申請;二,度支監給予准許發放的文書;三,昔寶赤們憑度支監文書向各州城的草場領取。其他執役分支領取草料的手續也應與此相差無幾。通過這種程式性規定可了解到,愛馬同度支監一樣,對怯薛歹支請草料擁有審批之權,執役分支成員未經本愛馬首領的許可,就不可能領取到草料。
前引《冒支官物》條説明,怯薛襖子(只孫服)的分發是以愛馬爲單位。又據前引《支請怯薛襖子》條,支請段匹同樣需要各愛馬的簽字背書,若無愛馬長官批准,衣料的領取自然也會遇到障礙。
最後略談一下鈔錠的發放。元代普通怯薛歹所能領取到的錢鈔通常分三種名目:賑濟、歲賜和朝會賞賚。朝會賞賚爲皇帝登基或大朝會時頒發的恩賜,這部分金錢以何種渠道向怯薛歹散給,史料有闕,暫難説清。至於賑濟和歲賜,則都有據可查。元廷向各愛馬頒發賑濟,屢見於《元史》本紀,如《成宗紀》元貞元年(1295)十月丁卯“以博而赤、答剌赤等貧乏,賜鈔二萬九千餘錠”,又如《仁宗紀》延祐六年(1319)七月辛巳“賜左右鷹坊及合剌赤等貧乏者鈔一十四萬錠”,以及《順帝紀》後至元元年四月丙寅“詔以鈔五十萬錠,命徽政院散給達達兀魯思怯薛丹各愛馬”。這些足以説明,在怯薛歹拿到手的鈔錠當中,有相當一部是以賑濟的名義經由各愛馬轉發下來的。有關各愛馬支散歲賜鈔錠的情況,前已圍繞《元史·食貨志三》詳論,兹不贅述。
接着來談愛馬在人事方面的職掌。由於元代的典志文獻極少從制度層面介紹怯薛内部的人事選舉概況,故只能從愛馬首領這一“人”的角度切入,就愛馬的人事選舉職能稍作探討。
各愛馬首領所握有的人事權,亦可分成兩大塊:其一是招募、批准外部人員加入怯薛的權力;其二則是舉薦部屬出職做官的權力。
元代常見通過走愛馬首領的門路來加入怯薛的現象,由此甚至引發了嚴重的冒入問題。至順元年,元朝政府曾大規模清理過一次冗濫已極的御位下怯薛。據前引《分揀怯薛歹》條,主導這次沙汰行動的中書省,把徇私枉法的“各枝兒頭目”視爲導致怯薛規模惡性膨脹的罪魁之一,並試圖限制他們的權力,可見愛馬長官在收攬部屬時顯然擁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權。
至於愛馬首領薦舉部屬入仕的權力,《元史·選舉志》中雖無明文,但某些顯貴的傳記透露了端倪。如前揭《元史·鐵哥傳》云:
鐵哥年十七……命掌饔膳湯藥,日益親密……(至元)十七年,進正議大夫、尚膳監。帝(忽必烈)嘗諭之曰:“朕聞父飲藥,子先嘗之,君飲藥,臣先嘗之。今卿典朕膳,凡飲食湯藥,宜先嘗之。”又曰:“朕以宿衞士隸卿,其可任使者,疏其才能,朕將用之。”
鐵哥入職怯薛之後頗受世祖寵信,很快當上典領御膳的寶兒赤官人,忽必烈讓他保舉麾下有才幹的寶兒赤。鐵哥的寶兒赤同僚賈秃堅不花的傳記中也有類似記載。虞集《賈忠隱公神道碑》稱:
公諱秃堅里不花,姓賈氏,世爲大興人……幼以世臣子,奉其祖父之職,勤敏著聞,授奉訓大夫,尚食、尚藥局提點……(世祖)間嘗命公察乎宿衞之有才能可用者論薦之,公列其名上聞,因以得官庀職者,亡慮數十,皆稱其用,而賞賚亦稱事有差,時論翕然歸之。
大興賈氏是元代有名的内饔世家,該家族成員世襲寶兒赤官人的職位,儘管作爲漢人,賈秃堅不花在内廷中的地位無法與色目貴族鐵哥相比肩,但通過他的推介而獲得官職的怯薛歹(應以寶兒赤愛馬成員爲主)仍達數十人之多。
薦用部屬並非寶兒赤官人獨享的特權,虞集《靖州路總管捏古台公墓誌銘》還提到過一個必闍赤方面的例子:
至大四年,公(蒙古人卜里牙秃思)年二十有八矣,得見阿難答納辛丞相于京師。時仁宗皇帝居東宫,丞相以其名聞,得備宿衞,主文史,給衣服芻粟以從。仁宗即位,翰林學士承旨闊闊出,則治國家文史於内廷之世臣也。薦公可用,宣授江西行省蒙古字提舉,官承直郎。
闊闊出承旨生平不詳,虞氏稱其爲“治國家文史於内廷之世臣”,應爲世襲的必闍赤長。卜里牙秃思經由闊闊出保舉而獲得官職的經歷,可視爲愛馬長官的薦用之權在必闍赤分支中的具體表現。
劉敏中《裴國佐神道碑》介紹了一個昔寶赤執役分支中的事例:
公諱國佐,字良卿,姓裴氏……里中徐君仲賢喜甄别人物,獨見公奇之。後徐君掾中書……因徐君補鷹坊掾,時至元九年也。十二年,領鷹坊納里忽益貴幸,多所薦引,既熟公才,會御史臺薦章亦上,乃奏公可用……有旨教利用監行者。俄就將仕佐郎、利用監知事。
領鷹坊納里忽,應即《史集·忽必烈合罕紀》中提到的忽失赤(Qu??i,昔寶赤的突厥語形式)之長naliqu,從其人貴幸之後“多所薦引”來看,長官拔擢下屬出職到外朝去做官的作法在昔寶赤愛馬裏顯然也相當盛行。
以上列舉的是寶兒赤、必闍赤及昔寶赤分支的情況,推而廣之,愛馬首領保舉部衆入官的現象在其他執役分支當中應普遍存在。各愛馬長官之所以能獲得薦用部屬的權力,主要因爲他們直接負責本愛馬的日常管理,能對部屬們的個性和才幹有較爲深入的認識。總之,無論是各愛馬首領吸納外人入職或是推薦部屬出職,本質上都反映出各愛馬在怯薛的人事管理體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尾 論
以上討論顛覆了蒙元史學界對元代怯薛組織架構問題的既有認識,推翻了御位下怯薛內部實行的是四怯薛框架下的一元管理體制的看法,點明了各愛馬與四怯薛兩大組織系統在怯薛中二元並立的事實。最後簡單梳理一下這種特殊組織架構的形成過程,並解釋導致其成立的原因。
四怯薛與各愛馬並存,並非出自統治者精心設計,而是數十年間制度自然演化的結果。起初在成吉思汗時代,怯薛尚屬草創,其内部所采用的是一元組織架構。宿衞、箭筒士及散班三大執役分支均被收納在四怯薛之下,而附設於怯薛中的汗室家政機關規模很小,整個部門裏並未出現明顯的職業群組分化。
格局的改變始於窩闊台時代。這一時期,隨着對外征服所帶來的巨額財富被源源不斷地裒集到漠北,蒙古汗室的生活日益鋪張奢靡。在此背景的影響下,怯薛中出現了兩種趨勢:一邊是火兒赤、昔寶赤等舊有執事部門不斷從遊牧民中徵募新成員,在成吉思汗時代的基礎上大幅擴張組織規模;另一邊則是必闍赤、舍兒别赤、八兒赤等一批蒙古人此前並不熟悉的職業被引入汗廷,接連作爲新的執事部門在怯薛裏設立,衆多來自定居社會的外來者亦隨之加入怯薛。時間愈往後推移,這兩種趨勢便表露得愈明顯,大蒙古國後期,許多執役分支已經擁有固定成員編制和獨立組織體系,隱然産生了要從依附於四怯薛的地位中擺脱出來的傾向。
入元之後,各執役分支的組織規模仍持續膨脹,它們除了招募額定的正式成員之外,還把大量散居地方的依附人口及其家屬也一併收入麾下,在此過程中,許多執役分支逐漸演變成了成員數量龐大、内部層級分明的愛馬集團,從四怯薛框架之下脱離的趨勢已難以逆轉。到世祖中後期,元廷正式承認了各愛馬的獨立地位,不但比照四怯薛爲它們頒賜了江南户鈔投下,在其他財政及人事待遇方面,亦盡量將其視爲與四怯薛平等的單位,至此,御位下怯薛的二元組織架構在官方層面得以確立。
怯薛内部分化出四怯薛和各愛馬兩大組織系統的原因,可參考制度史研究總結的一條基本規律—一個國家機構采用何種組織形式,與其需要承擔的職能密切相關。大體上,機構職能越少,其組織架構就越簡單;反之,它肩負的功能越多,組織架構就越複雜。
成吉思汗創設怯薛機構的初衷,除了打算整備武力保衞身家性命之外,便是爲了建立一支由大汗親自掌握的常備軍,由於宿衞和作戰都屬於軍事職能,因此怯薛内部自然是按照軍隊的標準采用了垂直化領導的一元組織架構。成吉思汗之後,歷任大汗親自出征的次數越來越少,怯薛的軍事職能遂漸次退化,到世祖朝已基本不再外出作戰,而是僅承擔宿衞任務。與此同時,家政事務之於怯薛的重要性却在不斷提高。隨着享樂取代征伐,成爲汗廷生活的主軸,怯薛的主要職使亦從一項增加爲兩項,料理家政被抬升到與守衞宫禁同等的地位,這一變動從根源上決定了其組織架構的演進方向。
爲滿足皇室日漸奢靡的衣食住行及享樂需求,許多執役分支不得不大幅增加人手,其成員數量遠超四怯薛的管控能力,必須自行成立一套組織體系來治理内部事務。同時,某些執役分支因工作性質的緣故,需要安排大量部屬散居地方,從事勞作(如馴養動物的昔寶赤、八兒赤、扎安赤、製造飲品的哈剌赤、舍兒别赤等),這導致了它們的組織系統必然溢出宫墻之外。所以,當打理皇室家政上升爲怯薛的主要職能之後,各執役分支脱離四怯薛衍生出各愛馬便成爲順理成章的結果。
此外,北方遊牧民族慣於將從事同一職業的人群集中編組管轄的習俗,也是促成各愛馬在怯薛中成立的重要因素。元廷在治理漢地民政時采取的主要舉措之一,是推行了一套按照職業來劃定户籍的諸色户計制度,顯示出草原社會的傳統思維對元朝行政管理模式的巨大影響。蒙古人在統治人數高達幾千萬、從事行業不啻數百種的漢地百姓時,尚且試圖將他們劃分爲不同的職業群體來行使管轄;那麽面對成員至多不過數萬、内部職業壁壘分明的怯薛組織時,選擇將其編成數十個愛馬來分而治之,更不足爲怪。
要之,元代怯薛内部之所以形成四怯薛與各愛馬並存的二元組織架構,既由於該機構需履行雙重職能,又受到了草原政治文化傳統的影響,前者是主要決定因素。
(本文作者爲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講師)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多語種方志文獻中的元代北方少數民族傳記資料整理與研究”(21CMZ047)階段性成果;修改過程中,劉曉、肖超宇先生多所啓沃,謹致銘感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