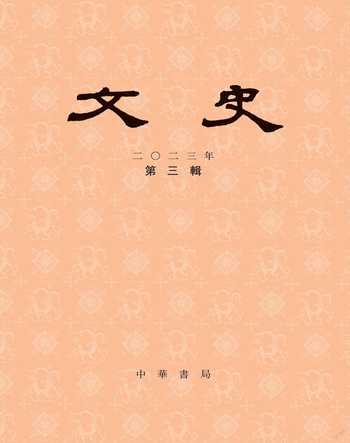談“用”的一種用法
2023-12-25謝明文
謝明文
提要:“用”是一個常用字,但有一類用法的“用”字,研究者關注不够。通過聯繫金文等相關資料,可知“用”有遵循、效法、法則一類意思,引申爲“可供效法、可供法則的東西”即名詞“法”,此即《清華簡(玖)·廼命二》“(憲)用”之“用”以及古書中訓爲“法”的“庸”“甬”。“偶人”之“俑”與“屨賤踊貴”之“踊”可能是得義於此類用法的“用”,即效法、仿效、模擬於真人的人像製品稱之爲“俑”,效法、仿效、模擬於人足的製品稱之爲“踊”。“俑”之於“甬/用”,猶如“像”之於“象”。
關鍵詞:金文 用 效法 詞源
金文中,“用”是一個常用字,但有一類用法的“用”字,研究者關注不够。下面將相關諸例揭示如下(盡量用寬釋):
(1)汝毋敢惰在乃服,恪夙夕敬念王威不易,汝毋弗帥用先王作明井(型),欲汝弗以乃辟陷于艱。(毛公鼎,《集成》02841,《銘圖》02518,西周晚期)
(2)曰:皇祖、考司威儀,用辟先王,不敢弗帥用夙夕。王對懋,錫佩。作祖、考簋,其敦祀大神,大神綏多福,萬年寶。(簋,《集成》04170—04177,《銘圖》05189—05196,西周中期後段)
(3)丼人人曰:淑文祖、皇考克慎厥德,純用魯,永終于吉。不敢弗帥用文祖、皇考穆穆秉德,憲憲聖爽,疐處宗室,肆作龢父大林鐘。(鐘,《集成》00109—00112,《銘圖》15320—15323,西周晚期)
(4)逑曰:丕顯朕皇考,克明厥心,帥用厥先祖、考政德,享辟先王。逑御于厥辟,不敢惰,虔夙夕敬厥尸事。天子經朕先祖服,多錫逑休。(逑鐘,《銘圖》15634—15636、《銘續》1028,西周晚期)
從文義看,例(2)“帥用”的施事省略,實是,賓語亦省略(參下文)。此例“帥用”與其他幾例“帥用”用法相同。上述四例“帥用”之“帥”可訓“循”“效法”一類意思,古書中或作“率”。其中的“用”,合而觀之,似不能理解爲“用”的常用義“使用”“采用”“施行”這一類意思,因爲這種解釋在例(1)(4)雖勉强可通(即“帥用先王作明井(型)”“帥用厥先祖、考政德”分别理解爲“效法並施行先王所創作的明型”“效法並施行其先祖、考的政德”),但在例(2)中基本行不通。因爲例(2)“不敢弗帥用夙夕”的賓語承前而省,單從簋銘看,可能是指“皇祖、考司威儀,用辟先王”。“皇祖、考司威儀,用辟先王,不敢弗帥用夙夕”大意是“偉大的皇祖、考管理威儀(即禮容),臣事先王,我()不敢不每日像皇祖、考那樣管理威儀,臣事先王”。若聯繫與簋同人所作的鐘(《集成》00247—00250,《銘圖》15593—15596,西周中期後段)“曰:丕顯高祖、亞祖、文考,克明厥心,胥尹叙厥威儀,用辟先王。不敢弗帥祖、考秉明德,恪夙夕佐尹氏。皇王對身懋,錫佩”來看,簋銘相關部分似可看作鐘銘相關部分的節録,彼此可以對讀。據鐘銘,例(2)“不敢弗帥用夙夕”中“帥用”的賓語應該是“祖、考秉明德、佐尹氏”,該句大意應是“不敢不每日像祖、考那樣執持明德,輔佐尹氏(掌管威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簋銘的“帥用”,四件鐘銘相應處僅作“帥”,這反映了“帥用”應該是近義連用的並列結構,因此又可省作“帥”。
在例(3)中按“用”的常用義理解也不太合理。晉公盆(《集成》10342,《銘圖》06274,春秋中期)銘文多處押陽部韻,其銘“余唯今小子,敢帥井(型)先王,秉德秩秩”,舊一般在“王”後面斷讀,可從。“秉”應是動詞,“秩秩”可看作“秉德”的補語或後置狀語。它與秦公簋(《集成》04315,《銘圖》05370,春秋中期)“余唯小子,穆穆帥秉明德”之“秉”的施事應該就是“余”(指器主)。據此可知梁其鐘(《集成》00189,《銘圖》15524,西周晚期)“梁其肈帥井(型)皇祖、考秉明德”之“秉”的施事應是器主梁其,例(3)“不敢弗帥用文祖、皇考穆穆秉德”之“秉”的施事是器主。其中“帥文祖、皇考穆穆秉德”即“效法文祖、皇考穆穆地執持德”,可看作聯動句或主謂結構“文祖、皇考穆穆秉德”作“帥”的賓語。例(3)“用”如理解爲“采用”“施行”一類意思,則“用文祖、皇考穆穆秉德”要理解爲“用文祖、皇考穆穆所秉之德”,“文祖、皇考穆穆秉”是主謂結構作“德”的定語,“文祖、皇考穆穆秉德”實是定中結構。也就是説,同一個“文祖、皇考穆穆秉德”在同一句中與“帥”“用”搭配時卻是不同的結構,這是不合理的。又“帥型”的一些文例與例(3)“帥用”完全相同(參下文)。這些也説明了上述銘文中的“用”不宜用其常用義來解釋,當另尋他解。如例(1)毛公鼎之帥用,張之綱認爲:“用,由也,率用猶率由。言王威不易,宜率由也。此五字(引按:指“女母弗帥用”,即上面釋文中的“汝毋弗帥用”),諸家皆屬下先王明井俗。竊謂五字當自爲句,不屬下讀,于文義似較長。”高鴻縉認爲:“用,近人讀爲由。是也。帥由,即《詩》‘率由舊章之意。”《商周青銅器銘文選》認爲:“帥用,讀作率由,義爲遵循。《漢書·五行志上》‘帥由舊章,顔師古《注》:‘帥,循也;由,從也,用也。”陳夢家據牧簋銘文(簋銘詳下)認爲毛公鼎“用先王乍明刑”即“先王乍明井用”。石帥帥認爲上述説法可並存,並提供另一種讀法,即“用”可讀爲“以”,將它看作虛詞。“用”,讀作“由”或“以”,與韻不合,不可信。但認爲“用”訓釋作率由之“由”,從文義看,則比較合理。下面再略舉一些詞例相關的銘文:
(5)太師小子師朢曰:丕顯皇考宄公,穆穆克明厥心,慎厥德,用辟于先王,純無愍。朢肈帥井(型)皇考,虔夙夜出内王命,不敢不不。(師望鼎,《集成》02812,《銘圖》02477,西周中期)
(6)丕顯皇祖、考,穆穆克慎厥德,嚴在上,廣啓厥孫子于下,(加)于大服。番生不敢弗帥井(型)皇祖、考丕元德,用申固大命,屏王位,虔夙夜溥求不朁德,用敕四方,柔遠能邇。(番生簋蓋,《集成》04326,《銘圖》05383,西周中期)
(7)單伯旲生曰:丕顯皇祖、烈考,逑匹先王,庸勤大命。余小子肈帥井(型)朕皇祖、考懿德,永寶奠……(單伯旲生鐘,《集成》00082,《銘圖》15265,西周中期)
(8)叔向父禹曰:余小子嗣朕皇考,肈帥井(型)先文祖共明德、秉威儀,用申固奠保我邦、我家,作朕皇祖幽大叔尊簋。(叔向父禹簋,《集成》04242,《銘圖》05273,西周晚期)
金文中,“帥型”一語還見於录伯簋蓋(《集成》04302,《銘圖》05365,西周中期後段)、師虎簋(《集成》04316,《銘圖》05371,西周中期後段)、梁其鐘(《集成》00187,《銘圖》15522,西周晚期)、虢叔旅鐘(《集成》00238—00242,《銘圖》15584—15588,西周晚期)、選鐘(《銘圖》15250,西周晚期)、晉公盆(《集成》10342,《銘圖》06274,春秋中期)等,偶作“型帥”,見於史牆盤(《集成》10175,《銘圖》14541,西周中期前段),“帥”“型”係近義連用。
比較上述“帥用”與“帥型”的文例,如例(3)“帥用文祖、皇考穆穆秉德”與例(8)“帥井(型)先文祖共明德、秉威儀”,例(4)“帥用厥先祖、考政德”與例(7)“帥井(型)朕皇祖、考懿德”,可知它們詞例幾乎一致。因此,“帥用”之“用”也應是動詞,與“帥”“型”意義相近,表示遵循、效法、法則一類意思。《尚書·召誥》“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型)用于天下,越王顯”,舊或在“刑”後斷讀,今按“小民乃惟刑(型)用于天下”可作一句讀,“刑(型)用”與“帥用”可合觀,前者的“用”也當統一看待。從金文中表示遵循、效法、法則一類意思的“帥”“型”“用”的使用情況來看,它們常近義連用,“帥”“型”有少數單用的例子,而“用”没有單用之例,這可能與“用”如單用易被誤解作其常見的動詞用法有關。它們連用時,一般是“帥型”“帥用”兩種,“帥”在“型”或“用”之前,“型”在“帥”前僅見於史牆盤,而“用”在“帥”前未見於金文,這可能與“用”如在“帥”前很容易會被誤解作連詞有關。
西周中期的牧簋(《集成》04343,《銘圖》05403)銘文中有如下一段話:
(9)王若曰:牧,昔先王既命汝作司士,今余唯或改,命汝辟百寮,有冋事包(?)廼多亂,不用先王作井(型),亦多虐庶民。厥訊庶有訟,不井(型)不中,廼侯之耤(作)怨,今司匐厥辠厥辜。王曰:牧,汝毋敢□□先王作明井(型)用,越乃訊庶有訟,毋敢不明不中不井(型),乃敷政事,毋敢不不中不井(型),今余唯申就乃命,錫汝秬鬯一卣、金車……
簋銘前部分的“不用先王作型”之“用”,舊或理解爲施行一類意思。如此解釋,則“先王作”是主謂結構作定語,“先王作型”表示“先王所作之型”。“不用先王作型”即“不采用先王所作之型”。僅看這一句,該解釋似可通,但聯繫上下文以及相關資料看,此“用”字也可能存在其他解釋(詳下)。
牧簋銘文是摹本,字形多有誤摹之處,如“夗”訛作“”,“”訛作“”,“尃”訛作“”,“”訛作“”等。摹本亦有多處奪字,如“四匹”前有一字的空間,應奪“馬”字。“取”和“寽”之間存兩字空間,應奪“”與一數目字。“汝毋敢”後面留有容納兩字的空間,據銘文文例,“敢”後應奪一否定詞,如“不”“弗”一類。金文中“敢”後接“弗”時,“敢”前一般用“不”字,構成“不敢弗”的句式(西周金文多作“不敢弗”,東周金文中偶作“弗敢不”,意義一樣,如叔夷鐘,《集成》00273,《銘圖》15553,春秋晚期),且見於施事或隱含施事爲器主的陳述句中。若“敢”前用“毋”時,其後都是用否定詞“不”而不用“弗”“勿”,構成“毋敢不”句式,且出現在上級對下級的祈使句中,此類祈使句式中若“毋”搭配“弗”時,則不要“敢”字,構成“毋弗”的句式,見於例(1)以及蔡簋(《集成》04340,《銘圖》05398,西周中期)。據此,牧簋“汝毋敢”後面當擬補“不”字,《商周青銅器銘文選》擬補作“勿”,《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擬補作“弗”,《殷周金文集成引得》、《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銘圖》等徑釋作“弗”,都是不妥的。“汝毋敢〔不〕”後所缺一字應是“帥”“型”一類。
牧簋“不用先王作井(型),亦多虐庶民。厥訊庶有訟,不井(型)不中,廼侯之耤(作)怨”講了兩層意思,第一層是如果“不用先王作井(型)”,就會出現“多虐庶民”的後果。第二層是訴訟過程中如果“不井(型)不中”即不能秉公辦理的話,就會出現“作怨”即激起民怨的後果。後文的“汝毋敢〔不〕□先王作明井(型)用,越乃訊庶有訟,毋敢不明不中不井(型)”顯然和上述兩層意思相照應,即“汝毋敢〔不〕□先王作明井(型)用”對應“不用先王作井(型),亦多虐庶民”一句,“越乃訊庶有訟,毋敢不明不中不井(型)”對應“厥訊庶有訟,不井(型)不中,廼侯之作怨”一句。即周王用雙重否定表肯定的強烈語氣告誡器主牧要“□先王作明井(型)用”、對待訴訟要既型又中即秉公處理,言下之意,這樣就能避免出現“多虐庶民”“作怨”的後果。“汝毋敢〔不〕□先王作明井(型)用”的“用”顯然應該是對應“不用先王作井(型),亦多虐庶民”的“用”。又結合牧簋銘文摹本多誤來看(參上文),前者“先王作明井(型)”後面的“用”應是摹寫者摹錯了位置或所據原銘鑄造有誤,它本應位於“先王作明井(型)”的前面。綜上,例(9)牧簋“汝毋敢□□先王作明井(型)用”本應作“汝毋敢〔不〕用先王作明井(型)”或“汝毋敢〔不帥〕用先王作明井(型)”。這樣牧簋上下文的“不用先王作井(型)”“汝毋敢〔不〕用先王作明井(型)/汝毋敢〔不帥〕用先王作明井(型)”跟例(1)“汝毋弗帥用先王作明井(型)”詞例基本一致,其中的“用”顯然也應統一看待。因此牧簋這兩例“用”也是與“帥”“型”意義相近,表示遵循、效法、法則一類意思。
《清華簡(玖)·廼命二》簡11—12有文作:
(10)母(毋)或聖(聽)告(臚)言,乍(作)(美)亞(惡)取爲(憲)用,以加悳(德)於外。
整理報告將“”讀爲‘憲,訓爲法,在“(憲)”字後斷句,“用”屬下讀,作“用以加悳(德)於外”。王凱博根據《廼命二》以及與《廼命二》爲同一書手書寫,内容也相互關聯的《廼命一》的相關文例,指出“用”應與“憲”相連屬上讀,並對其用法作了探討,認爲:
現在知道“(憲)”“用”相連作賓語,頗疑“用”字表義或當與“(憲)”相類。筆者認爲“用”或當讀作“庸”或“甬”。《爾雅·釋詁上》:“庸,常也。”(《廣雅·釋詁一》:“甬,常也。”“庸”“甬”實係一詞。)檢其文獻用例如下:
《淮南子·泰族》“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爲庸;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爲常”,許慎注:“庸,常也。”
楊雄《太玄·中》:“龍出于中,首尾信,可以爲庸”,范望注:“庸,法也。”
《後漢書·左雄傳》:“輿服有庸”,李賢注:“庸,常也。”
又,古人名、字關聯,《金史·盧庸傳》載“盧庸,字子憲”,亦可佐證。可見簡文“(憲)用(庸/甬)”是個近義並列複詞。
王説可從。今按《廼命二》“(憲)用”之“用”、古書訓爲“法”的“庸”“甬”與前引金文中“帥用”之“用”表示的可能是同一個詞。金文中與“帥”“型”近義的“用”作動詞,是效法、法則一類意思,引申爲“可供效法、可供法則的東西”即名詞“法”,這也就是“(憲)用”之“用”、訓爲“法”的“庸”“甬”。意義引申可與之類比的有“型”“法”“則”“憲”等字,如“型”在金文中常用作動詞,表示效法、法則一類意思(參上文),“法”“則”亦有同類用法,如司馬楙編鎛(《銘圖》15768、15769,戰國早期)“朕文考懿叔亦帥型法則先公正德,俾作司馬于滕”。它們亦皆可引申爲“可供效法、可供法則的東西”即名詞“法”(金文中都是用“井”來表示訓爲“法”的“型”,古書中常假借“刑”來表示訓爲“法”的“型”)。“憲”可作動詞,表示效法、法則一類意思,如《清華簡(伍)·厚父》簡7—8“惟時余經念乃高祖克憲皇天之政功”。它作名詞,訓法,在古書中習見,上引《清華簡(玖)·廼命二》“憲”即屬此類用法。這些皆可反證將“帥用”之“用”與《廼命二》“(憲)用”之“用”、古書訓爲“法”的“庸”“甬”等相聯繫是合理的。
上文揭示了“用”有“法”義,且有名動兩種情形。下面討論可能與之相關的“偶人”之“俑”以及“屨賤踴貴”之“踊”。
《説文》:“俑,痛也。从人、甬聲。”《説文解字注》:“此與心部恫音義同。《禮記》《孟子》之俑,偶人也。俑即偶之假借字,如喁亦禺聲而讀魚容切也,假借之義行而本義廢矣!《廣韻》引《埤蒼》説:‘木人送葬,設關而能跳踊,故名之俑,乃不知音理者强爲之説耳!”《説文》:“偶,同(小徐本作“桐”)人也。从人、禺聲。”《説文解字注》:“偶者,寓也,寓於木之人也,字亦作寓,亦作禺,同音假借耳。按木偶之偶與二枱並耕之耦義迥别。凡言人耦、射耦、嘉耦、怨耦皆取耦耕之意而無取桐人之意也,今皆作偶,則失古意矣。又俗言偶然者,當是俄字之聲誤。”
馬叙倫認爲“俑爲偶之東侯對轉轉注字”。《古辭辨》對“偶”“俑”作了詳細討論:
雕刻人像,漢代以前可能多用梧桐,所以許慎用“桐人”來解釋“偶”。其實只要是模擬人像的雕塑品都可以叫“偶”,是不限於桐人的。《戰國策·齊策》“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即用桃木雕的人像,“土偶人”即用土塑的人像。總之,凡是模擬人像或神像(其實也是人像)都可以叫“偶”或“偶人”……
古代雕塑偶人多半用來代替活人的殉葬品,《淮南子·謬稱》“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不過殉葬用的偶人另有一個專名,就是“俑”(yǒng)。《孟子·梁惠王上》“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注“俑,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謂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惡其始造,故曰:此人其無後嗣乎”……
從詞源上看,以“禺”標音的多有兩兩相合、成雙配對的意思,木偶稱“偶人”,即取與活人相合,用以代替活人的意思。“偶”的偶數、配偶諸義,也是從成雙成對義來的,這個意義的“偶”,古代多寫作“耦”。“偶”的偶然義也是從兩者適逢其會、趕巧碰到一起的意思來的,如:《吕氏春秋·勸學》“凡偶,合也,偶不可必”;王維《終南别業》“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俑”的得名大概是從甬道來的。古代墓葬,納棺的隧道也稱“甬道”,隨葬的偶人多置於甬道,所以殉葬的偶人也稱爲“俑”了,而且成爲殉葬偶人的專名。
《説文解字注》認爲木偶之偶得義於寓,並將它與耦耕之耦相區别,又認爲偶然之偶是俄字之聲誤,而《古辭辨》將它們統一看待,後者顯然是合理的。關於偶人之“俑”,《説文解字注》認爲是“偶”的假借,馬叙倫認爲是“偶”的轉注字,《古辭辨》則認爲“俑”的得名大概是從甬道而來。“甬”本從“用”聲,兩者關係密切,古文字中習見兩者相通。據古文字看,“甬”應該就是“用”的分化字。又據前文所論,“用”有效法、法則一類意思,《廣雅·釋詁一》:“甬,常也。”因此偶人之“俑”可能是得義於這一類用法的“用”字,即效法、仿效、模擬於真人的人像製品稱之爲“俑”。古書中“象”常有效法、模仿一類意思,如《左傳》襄公三十一年:“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它亦可引申爲“可供效法、可供模仿的東西”即名詞“法”。《説文》:“像,象也。从人、象,象亦聲。”效法、仿效、模擬於真人或真物做成的物品可稱之爲“像”,如雕像、肖像、畫像、圖像一類。“像”顯然是得義於效法、模仿一類用法的“象”字。“俑”的情形與“像”恰可合觀。“俑”之於“甬/用”,猶如“像”之於“象”。“俑”可分析爲從人、從甬(用)會意,甬(用)亦聲,如套用《説文》關於“像”字的分析,則是“俑,甬(用)也。從人、甬(用),甬(用)亦聲”,它是“偶人”之“俑”的專字,與《説文》訓“痛”之“俑”是同形字關係。訓“偶人”之“俑”與“偶人”之“偶”是音義皆近的兩個詞,但彼此得名之由不同。
《左傳·昭公三年》:“屨賤踊貴。”杜預注:“踊,刖足者屨。”馬宗霍認爲:“俑,象人而用之;踊,象足而用之;皆有象似之義焉。”蔣禮鴻認爲:“此説甚是。或著人旁,或著足旁,分别之;與踊躍義則異。”馬、蔣兩位將“踊”“俑”相聯繫很有道理,按照本文關於“俑”的意見,則此“踊”亦是得義於效法、法則一類用法的“用”字,即效法、仿效、模擬於人足的製品稱之爲“踊”。
(本文作者爲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臺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