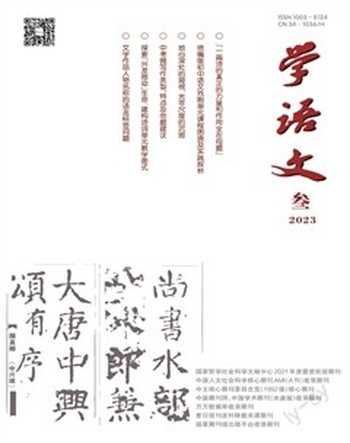历史情境下的抗战文艺叙事选择
2023-07-14潘晓嫣
摘要:孙犁的抗战小说多以平和舒缓的笔调叙事,作品的抒情性与诗意美为人称道,开“荷花淀”派一脉先河。其战争书写对血腥与死亡的匿避,不仅同作家的审美偏好与人道取向相关,也是有意的叙事选择。教学中可立足于课堂教学实践,以学生质疑为契机,深入文本内部逻辑,关照革命历史背景,探索孙犁抗战文艺创作与革命需要之间的紧密关联。
关键词:抗战文艺;叙事选择;革命需要;《荷花淀》
*本文系安徽省马鞍山市教育科学研究专项课题“文史学科融合视域下的高中读写教学策略研究”(课题编号:MJG220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为革命文学的经典篇目,小说《荷花淀》收录于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选择性必修中册,隶属“中国革命传统作品研习”任务群。在《荷花淀》的品读课上,鉴赏新鲜活泼的人物群像者有之,品味清新洗练的语言艺术者有之,感受诗情画意的唯美格调者有之,但多聚焦于非战争因素。《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新课标”)学习任务群教学提示指出:教师应利用多种形式,针对学生思想实际,敏锐发现热门话题,开展研讨活动,增强学生的论辩能力[1]16。在“新课标”指导下,教师立足学情实际与文本特质来确定教学内容,即缘“疑”定“教”。课前学生分小组交流,细读文本并提出疑问。学生可对不理解处质疑,也可对不寻常处质疑。在将所有问题分类汇总时,一个有趣的疑问引起笔者的注意:荷花淀战斗结束后,作家为什么要写水生打捞“一盒精致纸盒包装着的饼干”?课堂实践时,教师将这一疑问作为完成学习目标的“话题点”,引导学生质疑、析疑、释疑,让文本阅读由浅表走向深层。
一盒饼干:回到历史的现场
学生的困惑首先指向文本细节的真实性,农业化的水乡阵地出现工业化的食品,尤其还是“精致纸盒装着的饼干”,让人有点“出戏”。革命传统文学作品因其距离青少年的生活时代较远,学生容易产生常识性理解方面的偏差。教师适时引导,要分析“餅干”出现的合理性,就要将文本置于历史情境中考量,“弄清作品的时代背景,把握作品的内涵”[1]15。据此,教师提供杨成武将军在1937年平型关大捷后的一段回忆记录,请学生阅读,展开探讨:
继日军坂垣师团主力在平型关被歼后,它的第二运输大队也在此覆没,只几个骑兵漏网。我们共毙伤日本侵略军一百多名,缴获摩托车三辆,大车一百二十多辆,骡马八百多匹,步骑枪七十多支,各种短枪十多支,炮弹二十多箱,子弹四十多箱,罐头、饼干、汽水等食品多达二千二百多箱,还有一大批呢大衣、军毯。
满身泥土、硝尘的战士们,把缴获的物资重新装上大车,运往上庄子地区。在路上,大家打开一包包饼干吃起来,那饼干配有红红绿绿的小糖豆,嚼在嘴里嘎嘣嘎嘣响,味道可真香甜。[2]287
将文本与史料对照阅读,学生有了两个发现。第一个发现是,阻击运输队往往能够缴获军需,罐头、饼干、汽水都在内。据此可知,《荷花淀》中的“饼干”并非一般的生活用品,而是与前文中的“枪支”“子弹带”“面粉和大米”等同属于敌人的军用物资,在战场出现很合理。再者,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开启“以战养战”的计划,荷花淀所在地区有着特殊的战略地位。在当时,白洋淀是连通河北与天津的水上要道,日军的船只需要通过这条水道,把大量军火和军用物资从天津往西运至保定。水生所在的游击小队能在战斗后缴获大量军需用品,恰恰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细节。第二个发现是,饼干在抗战时期有用作战后临时补给的先例,水生嫂及其同伴拼尽全力摇船进淀,无意中将日军引入了包围圈,也算是立了功。
小说虽是虚构的艺术,但也要遵守历史的事实。正如孙犁所说:“《荷花淀》所写的,就是这一时代,我的家乡,家家户户的平常故事。它不是传奇故事,我是按照生活的顺序写下来的。”[3]78作家在虚构小说时,需要从现实的经验出发,让故事具有颠扑不破的合理性,才能取信于读者,收获艺术的共鸣。
一条纽带:深入文本的逻辑
与“饼干”相关的情节有其合理性,但是否有必要性呢?这是学生的第二个困惑。读懂小说,首先要读懂作家对情节的布局安排。在文本细读的过程中,对可质疑处不断追问,才能发掘细节背后的深层意蕴。这是学生理清小说叙事逻辑的必要步骤,也是走向阅读深水区的必经路径。面对这一困惑,教师设计“增减删换”的文本变形活动来引导探究:
能不能将文中的“饼干”替换成“米面”?这一设想很快被否定。就常理而言,水生无法将“一袋子一袋子叫水浸透了的面粉和大米”“顺手”丢给女人,这一动作决定了所丢的物件是轻巧的。更重要的是,“米面”作为缴获的重要军需,应当收归组织统筹安排。将“米面”私赠家属是违犯纪律,必然会对战士的形象主体造成损害,违背了作家塑造人物的本意。“饼干”与“米面”虽然同属军需,但“饼干”有着相对灵活的处置方式。正如杨成武将军在回忆录中所记述的,抗日战争期间,部队在作战之后会将收缴的军粮饼干分发给战士,用以补充消耗,恢复体力。水生给女人的那一盒饼干,正是游击小队获得胜利之后分得的补给用品。如此看来,将“饼干”丢给家属的情节设定,既合乎战斗纪律,又贴合人物身份。
不能替换,那能不能将“饼干”部分从小说中删去?经过探讨,学生分析得出了不可删除的结论。从情节发展的逻辑来看,水生打捞纸盒丢给女人,顺理成章地引出双方的对话,故事情节也由“战斗模式”切换回“日常模式”。从对人物的塑造来看,“饼干”部分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小说塑造了两个群体的形象,无论是以水生嫂为代表的别夫、念夫、寻夫的女人们,还是以水生为代表的赴战、设伏、歼敌的男人们,他们都有着一致的认识——大敌当前,保卫祖国才能护住小家。正因为如此,水生夫妻话别才那般含蓄克制,其他战士甚至没回村里,这都是民族危难之际私情让位于公义的选择。但孙犁笔下的人物是血肉丰满的,大义与人情并不矛盾。正因如此,夫妻话别时才有了“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这句最重要的话,也才有了“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的郑重承诺;探夫歼敌时才有了“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而水生将饼干“顺手丢在女人们的船上”又何尝不是一种默契的回应呢?
“饼干”部分既是勾连情节的纽带,也是人情连结的纽带。通过梳理文本逻辑,学生还认识到广大民众为什么而战斗。庞大的国由无数个小家构成,正因家园美好、亲眷情深,人们才要拼尽一切去守护保卫一方土地,亲人伦理和家国情怀推动个人成为民族抗战的斗士,这种信念有着朴素而强大的力量。
一个视角:展现新生的力量
课堂研讨继续进行,学生再度追加疑问:作家为什么要详写“战后”而略写“战斗”呢?这是个好问题,实际上,这也是一段时期内《荷花淀》引发争议的焦点。时任“冀中军区司令员”的吕正操将军曾对1942年日本发起的“五一大扫荡”作如下记述:
这个阶段,是冀中部队作战最紧张、最激烈、最频繁的时期,损失也最大,但也使敌人真正领略到了冀中军民英勇顽强、宁死不屈的精神。
从五月一日到六月底,在两个月的反“扫荡”中,我军共作战二百七十二次,击毙日伪军三千八百九十一名,击伤日伪军七千五百二十一名。我伤亡指战员四千六百七十一名,区县游击队损失五千三百余人,被杀害、抓走的群众达五六万人,使冀中平原“无村不戴孝,到处闻哭声”。[4]231-234
自1938年吕正操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冀中平原地区多次遭受敌人的“扫荡”“清剿”,损失严重。小说《荷花淀》发表于1944年,正值抗战白热化的阶段,而孙犁笔下的战斗却显得轻捷而迅速,战争的苦难是否被弱化消解了?
针对这一问题,学生先从自身的阅读经验出发,谈及小说主题叙事具有多样性。都德《最后一课》以普法战争为背景,从孩子的视角去展现沦陷区的屈辱、对故土的思念。海明威《桥边的老人》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通过写被战争无情摧毁生活的老人,表达对生命的悲悯与珍视。茹志鹃的《百合花》以淮海战役为背景,饶有诗意地展现了战时美好的军民关系,而将小通讯员牺牲的情景借他人之口说出,揭示出解放战争胜利的力量源泉。战争题材的叙事选择并不是单一维度的,这与作家对文学写作的审美追求有关,略写或不写战争场面,同样能深刻反映战争的苦难。
教师继而引导学生回归文本,探寻叙事选择背后的创作意图。《荷花淀》以女人们的视角展开叙述,她们原本在后方照顾老幼、维持生产、识字进步,理解丈夫离家的决定但依然感到不舍。然后,作家安排她们水上遭遇日军,写她们镇定下来摇船入淀,写她们做好以死明志的准备,写她们亲眼见证丈夫杀敌。一步一步,女人们从“后方”逐步走上“前线”,从设伏的局外人、战斗的旁观者变成伏击的助力者、战斗的参与者,而这一过程中她们所展现出的抗压力、应变力和不屈之心,预示着女人们将成为抗日前线的新力量。
之所以略写“战斗”而详写“战后”,是因为作家的创作目的不在于描摹“男人们的战斗”,而在于展现“女人们的成长”。如果对战争过程大加描写,会造成叙述重心的游移,也会对文本一贯的诗意风格造成破坏。
一种精神:体认理智的欢快
课堂探究推进至此,学生还需了解抗战文艺赖以生发的特定背景,将小说纳入上世纪40年代“全民抗战总动员”的日常政治环境中,才能理解孙犁有意的叙事选择。为此,教师自孙犁1939年创作的长篇叙事诗《白洋淀之曲》中摘取片段,请学生进行比较:
一束干草,/放在棺的上面;/送葬人走在棺的前头,/一个人散放着纸钱。//跟在后面,/菱姑紧紧抓住木棺,/把头在棺蓋上碰撞,/用湿透的白巾盖住脸。//她简直是被棺拖走,/两条腿再没有了力气,/眼泪从她眼里流干,/她叫着水生哭泣!//太阳还没有升出,/大地蒙住一层雾;/在一个苇塘的边沿,/掘好水生的坟墓。//当棺木送进坟坑,/铜笛开始了尖声的吹呜;/人们先围绕着墓穴用手撒土,/然后用铁锹堆起坟墓。//八个抬棺人,/这时站在坟前;/他们都穿着黑色短衣,/铁青着脸。//八个人,/都是二十上下的青年;/八个人,/都生长在白洋淀。[5]36-37
《白洋淀之曲》与《荷花淀》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两部作品的主要人物都是“水生夫妇”,故事同样发生在抗战背景下的白洋淀,同样有伉俪情深难舍的描写,同样有妻子走上抗日道路的情节。某种程度上,《荷花淀》可以视作《白洋淀之曲》的“衍生本”。对两个文本略加比较,学生发现两部作品的叙事角度、情感基调、审美风格迥然不同。可以想见,孙犁就如何叙述战争的苦难经过了长时间的摸索,他积极地调整自己感受、认知、记录民众抗争的方式,不再着力正面表现人们在战争中的无力与悲哀,而是侧重于发掘他们心底追求新生的欲望与冲动,展现人们不屈服的勇气与乐观精神。关于《荷花淀》的创作背景,孙犁曾谈及:
冀中平原的抗战,以其所处的形势,所起的作用,所经受的考验,早已为全国人民所瞩目。但是,这里的人民的觉醒,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共产党和八路军及时领导了这一带广大农民的抗日运动。这是风起云涌的民族革命战争,每一个人都在这场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这是全民战争。
那时的动员口号是: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4]76
作家的自述给了学生新的启发。孙犁避开对战争残酷景象的直接描写,并非仅出于个人审美的偏好,而是自觉抗战文艺工作者的政治身份,洞察革命新人“辗转在战斗里,生活在理智的欢快里”[6]223,捕捉并记录战区民众呈现的崭新思想与精神风貌,以期“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7]22-23使自我创作适配于抗日动员的需要。
革命传统教育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值得细究文本微处,体悟作者匠心。孙犁叙写水生投递“饼干”绝不是闲笔,“饼干”具有“战利品”的属性,接过“战利品”的女人们得到了初次战斗的“勋章”,从此与“抗战”更紧密地连接了起来。《荷花淀》所在单元的人文主题是“苦难与新生”,小说展现的正是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广大妇女思想解放的进程,她们于苦难中奋起,从本能到自发地站到抗日民族斗争这一光荣队列里,释放出全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
[2]杨成武.杨成武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20.
[3]孙犁.晚华集[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4]吕正操.吕正操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
[5]孙犁.白洋淀之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64.
[6]孙犁.孙犁全集?卷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7]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延安:解放社,1950.
(作者:潘晓嫣,安徽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教师)
[责编:芮瑞;校对:夏家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