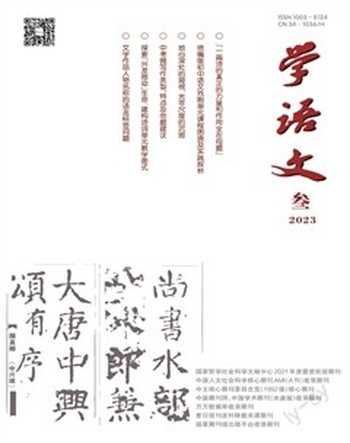文学作品人物名称的语言标签问题
2023-07-14宗守云王仪韵
宗守云 王仪韵
摘要: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其不同的外在形式会在人头脑中形成不同的想象,这是语言符号的标签性质。在文学作品中,人物名称往往能够体现语言的标签性质,从人物名称数量看,有单一性名称和多样性名称,因而语言标签也相应地分为“单一性标签”和“多样性标签”。文学作品人物名称作为语言标签,具有求实效应、联想效应和风格效应。
关键词:名实关系;语言标签;效应
一、语言的标签性质
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语音是语言的外在形式,语义是语言的所指内容,语音和语义结合在一起形成符号,用来指称特定的认知对象。对同一指称对象而言,用不同的语音形式表现,往往会产生不同意象。例如:
(1)吕旷说,我发现日本人还挺会起名的。欧阳阳问,怎么呢?吕旷说,猪肉不叫猪肉,叫豚肉,鸡翅不叫鸡翅,叫手羽先,河泡子不叫河泡子,叫川,名起得洋气,听着一下就上档次了。(郑执《森中有林》,《芒种》2020年10期)
(2)老百姓对那些高大上的电子研究所、高新技术看不懂,他们更关心那些时兴且实用的新玩意,所以网上、报上是硅谷,在普通群众口中,还是叫电子一条街。(刘汀《水落石出》,《十月》2022年第5期)
例(1)在所指对象相同的情况下,“猪肉、鸡翅、河泡子”是一般性名称,“豚肉、手羽先、川”听起来洋气,上档次;例(2)“硅谷”是高科技名称,“电子一条街”则是俗称。例(1)(2)不同的语音形式就像是不同的标签,尽管所标示的内容是相同的,但在人们头脑中产生的联想是不同的,这种现象可以称为语言的标签性质。
在文学作品中,人物名称经常可以表现出语言的标签性质,从而形成特定的语言标签效应。例如:
(3)他愿意根据名字,想象出主人的长相,抑或性情。比如憨厚的“蔡毛根”、愚钝的“刘卫忠”,或者精明的“张林娣”、世俗的“王丽花”,他就没有想去认识他们的欲望。……只有林若梅,令他在见到名字时,就陡然地生出了些许仰慕。他当然不认识林若梅,他仰慕的,只是那个名字。他觉得,叫林若梅的女人,应该是文静、优雅的,也许,身上还有着他人无法懂得的美。(薛舒《相遇》,《人民文学》2018年第2期)
例(3)作品主人公根据人物名称想象人物的性情、品质,其中林若梅这个名字深深地打动了他,这就是人物名称的语言标签效应。再比如:
(4)说是“老”娄,其实他也不过四十岁出头吧。我们老娄老娄地叫,把他都叫老了。当然,老娄老成持重,也是当得起这个“老”字的。老娄的老,不仅仅代表着年龄,还代表着资历、影响、身份、江湖地位。老娄是专业领域内的大牛、领军人物,咖位高,分量重。这都是圈子内公认的。(付秀莹《纸船》,《湘江文艺》2022年第1期)
例(4)“老娄”这个名字有一系列语言标签效应,包括性情、年龄、资历、影响、身份、地位等等。
文学作品人物名称往往有明显的语言标签性质,可以产生特定的想象,正因为如此,作家在创作作品的时候都非常注重作品人物的命名,有时还在作品中把人物名称的标签性质及其效应显明出来,从而突显作品人物形象,推进作品叙事进程。
二、作品人物的语言标签类别
在文学作品中,同一人物,有的只有一个名称,这是“单一性命名”;有的有若干个名称,这是“多样性命名”。无论是单一性命名还是多样性命名,都可以体现语言的标签性质,因此可以分别叫“单一性标签”和“多样性标签”。
(一)单一性标签
对一个特定的个体而言,只有一个名称的情况并不多见,一个人除了学名,往往还有乳名、绰号甚至字、号等名称。但在文学作品中,作家可以只赋予特定人物一个特定的名称,这样在情节展开的过程中容易做到清晰准确,有利于读者理解。有些单一性命名语言标签效应非常突出明显。例如:
(5)有一天老远悄悄告诉我,自己在校园西角大松树下发现了一位晨读英语的女生,长得double beautiful。第二天早上跑步时我拐一下路,果然见到松树下那位挺养眼的女生。我们不知道她的出处,就依着歌曲暂时把她命名为“小芳”。此后我们每天清晨跑步都会绕道经过大松树,近距离让眼睛愉快一回。某一个晚上,老远突然告诉我,自己可能爱上那位小芳了。(钟求是《除了远方》,《钟山》2020年第6期)
(6)盘子应该还记得隔壁班班花,以前我们去网吧看《我的野蛮女友》,一致觉得她和全智贤特别像,主要是瘦高个和长头发,背面看一模一样,正面转过来,班花的皮肤要黑很多。我说,当然是全智贤更好看。盘子说,你不懂,黑里俏,全智贤要有她这么黑,还不如她一半好看呢。但盘子肯定想不起深圳全智贤了,谁,有这个人吗?(王占黑《韦驮天》,《上海文学》2021年第6期)
例(5)(6)分别用“小芳”“全智贤”命名,这样的语言标签,自然让人联想到淳朴漂亮的农村姑娘小芳和韩国著名演员全智贤。
(二)多样性标签
一个特定的个体往往有多个名称。多样性名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对塑造刻画人物有很大作用,是修辞同一手段实现的方式之一。多样性名称也具有语言标签性质,可以反映人物的性情、特征。
多样性名称有时是说话人赋予他人的,反映说话人对特定主体的评价和态度。例如:
(7)在我的感觉中,奶奶嘴里的爷爷像是一道影子,或者别的什么——反正,是一种稀薄的、抓不住也摸不到的“飘泊之物”,一种似乎不那么真实的存在。在奶奶的只言片语中,爷爷有太多的名字,譬如“你爷爷”;譬如,“他”;譬如,“不着家的”“睡窝棚的”;譬如,“死鬼”“痨病鬼”“胜儿他爹”“瘦兔子”“疯子”。(李浩《像是影子,像是其他》,《江南》2022年第2期)
例(7)爷爷的多样性标签都是奶奶赋予的,是奶奶对爷爷多种特征的描述,包含著特定的评价和态度。
多样性名称有时是特定主体自我命名的,这些名称都有特定的含义或韵味,有明显的语言标签功能。例如:
(8)女孩把手放下来说,我叫马久久,原名叫马晓童,公司让我改个名,说马晓童太像九十年代的艺人。我说就叫马久久吧,九九归一,长长久久,还骑着马。……其实我原来也不叫马晓童,马晓童是我上表演夜校的时候改的,我身份证上的名字是马小千。(双雪涛《刺客爱人》,《收获》2021年第1期)
例(8)同一个人拥有不同的名字,每个名字都有特定的来源和意味,都反映了特定主体的性情或愿望,语言标签功能非常明显。
三、作品人物的语言标签效应
文学作品人物名称的语言标签效应包括求实效应、联想效应以及风格效应。
(一)求实效应
文学作品人物的名称往往能够使人想到人物的实际品性,这就造成了作品人物语言标签的求实效应。
名实关系是语言学、哲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问题,早在人类轴心时代就有了关于名实关系的深刻论述,像古希腊的“自然派”和“规约派”,像先秦墨子的“以名举实”和荀子的“约定俗成”,等等。名实关系最基本的情形有两种,一是名实一致,一是名实不符。对文学作品人物名称而言,名实一致和名实不符的情况都是比较多见的。
先说名实一致的情况。在文学作品中,名如其人,是作家塑造人物的常用手段,作家通过给作品人物命名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例如:
(9)丁军芳长得很像丁军芳这个名字,周若愚第一眼看见她,就觉出这应该是一个简单、质朴,抑或有些大大咧咧的姑娘。(薛舒《相遇》,《人民文學》2018年第2期)
(10)跟着蓝芬姐采菜的有两三个或四个孩子,都是我的小伙伴。野草不好找,野菜更难找,所以要跑更深更远的地方。我们兜了好大一个圈子,刚钻进玉米地,就被护青的二驴盯上了。人起这样的名字,脾气会好吗?(尹学芸《蓝芬姐》,《北京文学》2022年第1期)
例(9)“丁军芳”和例(10)“二驴”都是名实一致的情形。
根据言语行为理论,话语和客观世界的适从方向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从话语到客观世界(word-toworld),一种是从客观世界到话语(world-to-word)。就作品人物而言,如果人物名称是绰号,其适从方向都是从客观世界到话语,例如:
(11)鸭蛋不叫鸭蛋,因为脑袋长出了鸭蛋形,老乔两口子又卖鸡蛋灌饼,大家就叫他鸭蛋。叫多了,老乔两口子也跟着叫鸭蛋,本来的名字大家就给忘了。(徐则臣《兄弟》,《大家》2018年第3期)
语言往往有建构功能,在名实不符的情况下,特定主体可以根据名称能动地改变自身现状,以达到名实一致的目的,这是从话语到客观世界的适从方向。例如:
(12)她生完多多,何秀竹体重达到一百四十斤。马勋倒是没有嫌弃她胖了,但是她自己接受不了这件事。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她天天感慨,马勋就说,咱们再买新的呗。她说,我叫啥名?马勋愣一下说,胖又不影响脑子,自己啥名还能忘了,何秀竹啊。她就说,那你说,有我这么粗的秀竹吗?就算为了配得上这个名字,我也得把这身肉减下去。(刘汀《何秀竹的生活战斗》,《十月》2020年第4期)
再说名实不符的情况。在文学作品中,人物名实不符表现出一种张力,往往用于贬义性语境。例如:
(13)她不知道秦瞎子早就把她的底摸得门儿清,秦瞎子只是叫瞎子而已,人家不瞎,脑子够使、鬼精,那家伙整天斯斯文文坐在路边大梧桐树下,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就是专为着骗人来的。(肖勤《隐秘的船》,《人民文学》2022年第7期)
(14)这个买下龟兹女人的男人十分懊恼,说话的语气里都是懊恼,他感觉很吃亏,他是人财两空,儿子带着财物被女奴拐跑了。这个龟兹女奴叫光明,名字起得挺好的啊,可干的都是很黑的事情,一点也不光明,她还把他家里另外一个侍女也拐跑了。(邱华栋《流沙坠简》,《绿洲》2023年第1期)
名实一致反映了语言标签的正向性,而名实不符反映了语言标签的负向性,但两者都是为刻画人物设置的,具有同等的修辞功能。
(二)联想效应
文学作品人物的名称能够引起同音联想,这是语言标签的联想效应。例如:
(15)他接过报到单看到写着“同意该生报到,请组织科给予分配”。领导栏签名是“傅责”。您名叫傅责?他认为这名字真好,谐音负责。傅责轻轻将钢笔杆插进钢笔帽说,当年我进华北联合大学读书,自己改名傅责的。(肖克凡《洁本工厂情史》,《四川文学》2020年第8期)
(16)宋可行,绰号鸡公,大学时代与方圆睡上下铺。另一位,刘备,当时同学们都乐了,你敢叫皇帝的名字?刘备扶扶眼镜:“老爸起的,他胆大我也没办法。”(矫健《潜伏期》,《青岛文学》2022年第2期)
例(15)人物名字傅责使人联想到同音的常用词“负责”,例(16)人物名字刘备使人联想到同音且同形的古人名字“刘备”,这些都是语言标签导致的联想效应。
同音联想有积极同音联想和消极同音联想两种情形,这在作品人物命名的联想方面都有表现。例如:
(17)我们发现,白志浩的主要问题出在其名字上,因而应当严肃追究其父母。他老爹为什么要姓白?他们是怎么给儿子起名的?“志浩”是什么意思?志向浩荡,或者志向浩大,总之名有大志,但是加上其姓就完蛋了。白志浩就好比白欢喜,弄半天一场空,白有浩荡大志,注定无法实现。且“浩”与“耗”同音,稍加创新联想,白志浩就类同于耗子,有如癌症研究所饲养的实验用小白鼠。(杨少衡《真相大白》,《鸭绿江》2018年第2期)
(18)黄主任你叫什么名字?黄泉,黄泉这样回答。冯有义问:“是黄泉路上无老少那个黄泉吗?”黄泉认为冯有义这玩笑开得有些过了,便解释道:“是黄金的黄,泉水的泉。”冯有义举杯对刘总道:“来,咱俩再喝一杯,别忘了要戴好玉佩,老兄可是天天见黄泉。”(老藤《爆破师》,《芙蓉》2019年第3期)
例(17)“志浩”能够引起积极同音联想,“白志浩”“浩”则引起消极同音联想;例(18)“黄泉”很容易引起消极同音联想。在修辞学中,语音修辞的原则是容许积极的同音联想,避免消极的同音联想。但在文学创作中,作家有意利用人物名称的消极同音联想推动情节的进展,这也是另一层次的修辞创造。
(三)风格效应
文学作品的人物名称还可以唤起不同的表现风格,这是语言标签的风格效应。例如:
(19)父亲粗通文墨,我和哥的名字带了那么一点儿文艺。哥叫马屈,我叫马伸。(胡学文《内吸》,《花城》2020年第5期)
(20)听听,陶陶,欢欢,我们县城里人,生個孩子不是叫二柱就是叫二花,再不然连二柱二花这样的名字都懒得起,直接叫二小子和二闺女。陶陶,欢欢,这得多电视剧的名字呀,何况孟朝阳还教他们说普通话。(苏二花《安格尔大宫女》,《都市》2019年第1期)
例(19)“马屈、马伸”有强烈的文艺风格,例(20)“二柱、二花”风格较俗,“陶陶、欢欢”风格显雅,这都是不同的语言标签导致的风格效应。
语言有时还能表现出文化风格特征,作品人物名称作为语言标签,也可以表现出文化风格特征。在汉文化中,给孩子取贱名,或者男性取女性名字,往往被认为容易养活,这样的文化风格特征也会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成为语言标签。例如:
(21)我蹲在父亲手术室门口,想的却不是他了,而是小芹。小芹怀孕这些日子,每次看见她日渐鼓胀的肚子,我都会想起那些母羊。隔着肚皮,我跟她肚子里的孩子说:小羔子,你快出来吧。小芹说,你咋管孩子叫羔子,正经起个名。我就说,大名你起,你是初中毕业生,我都没毕业。小名就叫羔子,又皮实又亲切。(刘汀《一岁一枯荣》,《芙蓉》2022年第4期)
(22)还不是怪家里,我五个姐姐,我老幺,给我取个名叫樊小花,好养活。分配专业的老师估计一看这名字就默认性别女了。全班二十七个女同学,就我一个男的。(郭爽《挪威槭》,《收获》2021年第2期)
例(21)作品主人公给孩子取名“羔子”,例(22)作品主人公是男性,父亲为他取女性名字“樊小花”,都是为了容易养活,有鲜明的文化风格特征,这是语言标签导致的风格效应。
参考文献:
[1]宗守云.拾荒,培根,车厘子[J].咬文嚼字,2021(4).
[2]俞东明.什么是语用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
[3]宗守云.修辞学的多视角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作者:宗守云,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仪韵,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责编:胡承佼;校对:芮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