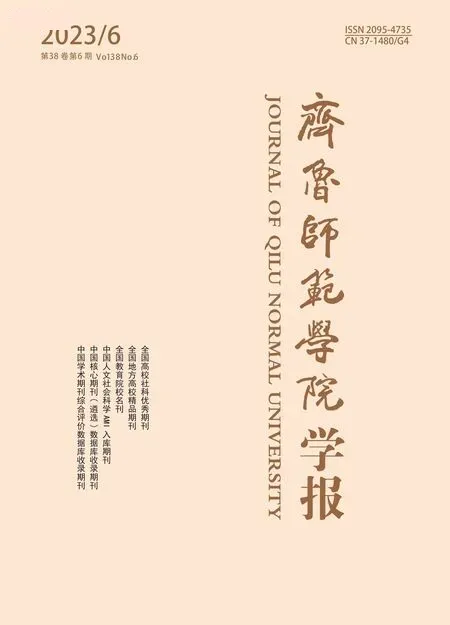韩湘入仙故事早期流变再考
2023-04-25李梦翰
刘 磊 李梦翰
(济南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众所周知,“八仙”之一的韩湘子,真实原型是唐代大文豪韩愈的侄孙韩湘。其入仙故事流变过程,20 世纪30 年代以来经学者不断研究①,主要脉络已基本清楚:晚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五代杜光庭《仙传拾遗》和北宋刘斧《青琐高议》中的相关记载,是三大重要节点,随着时间推进,故事不断丰富化、神异化、定型化,成为后世韩湘入仙故事的共同来源。但某些具体问题还有进一步考辨的必要。本文拟对这些文本从文本演变生成、雅俗文学互动等角度再作细致考辨,以期对韩湘入仙故事在晚唐至北宋的早期流变过程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一、韩湘故事的历史基础
韩湘入仙故事,源于韩愈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以下简称《左迁》)一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1]1097②
蓝关即蓝田关,又称青泥关,“在(蓝田)县东南九十里,即峣关也”(《元和郡县图志》卷一),自古就是关中平原通往南阳盆地乃至楚、吴、岭南等南方地区的交通要道。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正月,韩愈因谏迎佛骨触怒宪宗,被贬潮州,仓促上路,至蓝关时逢天大雪,意外遇到从长安追赶而来的侄孙韩湘,遂作《左迁》一诗,抒发悲慨之情。
韩湘(794-?)小名爽,字北渚,韩愈侄韩老成之子,韩愈侄孙。幼读书宣城,韩老成卒后,韩愈接韩湘至两京任所读书,数次应试不第。韩愈获罪贬潮时,韩湘冒雪追至蓝关,之后一路随行护侍至潮州。一年后韩愈量移袁州,不久后返京,韩湘皆伴随左右。长庆三年(823)韩湘30岁时进士及第,同年冬,授校书郎,被江南西道宣州刺史崔群辟为从事,官终大理丞,其后事迹不详[2]387-398。从现存记载看,韩湘一生经历比较平常,虽有屡试不第之经历,但30 岁进士及第,在当时犹可谓年少得志。姚合赠韩湘诗云:“年少登科客,从军诏命新”(《送韩湘赴江西从事》)[3]76,“昨闻过春关,名系吏部籍。三十登高科,前途浩难测。”(《答韩湘》)[3]591虽有恭维成分,但大致属实。
韩湘性格可能有点孤僻、不合群(详后文),但品行很好,谦恭孝顺,深得亲友认可。韩湘赴官时,韩愈作《示爽》诗送之:“念汝欲别我,解装具盘筵。日昏不能散,起坐相引牵。冬夜岂不长,达旦灯烛然。座中悉亲故,谁肯舍汝眠。”[1]1275可见送行亲友们对韩湘都很有感情。沈亚之也有《送韩北渚赴江西序》:“北渚,公之诸孙也。左右杖屦,奉应对,言忠情劳。”对韩湘在韩愈身边孝顺侍奉的表现赞赏有加。
要说韩湘有何不同常人之处,大概都来自其叔祖韩愈的影响。韩愈自幼父母双亡,靠兄嫂抚养,与韩湘之父韩老成一起长大,“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韩愈《祭十二郎文》),感情极深。韩老成去世后,韩愈将韩湘、韩滂兄弟从宣城接到身边抚养、教育,视同己出。韩愈年长韩湘26 岁,二人虽属叔祖孙,但从年龄差距、依存关系、情感深度等方面来看,更近于父子或叔侄,这也是后世传说将韩湘误传为韩愈“子侄”或“外甥”的原因。
韩湘无诗文传世,《全唐诗》录其2 首诗皆后人附会,不可信。写与韩湘的交游作品,主要来自韩愈及其门人,有诗文数篇。比较集中的是长庆三年(823)韩湘离长安赴江西任职时,韩愈与贾岛、姚合、朱庆馀、无可、马戴、沈亚之等人饯行所作诗文,大概是通过某种小集的载录,基本都保存下来了。除此之外,关于韩湘的真实材料就很少了。在原始记载中,未见韩湘有信奉道教的迹象。他是怎样逐步被演化为仙人形象的呢?
从背景角度看,随着韩愈贬潮、返京,韩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应该有所提升,为其传奇故事产生提供了基础和可能性。根据是:
(一)《左迁》一诗的传播。今知韩愈最早流传的小集——潮州人赵德所编《文录》(成书于长庆年间,原书已佚),收录诗文75 篇,其中以文居多,今人刘真伦《昌黎文录辑校》共辑出64 篇作品,仅8 篇诗歌,其中就包括《左迁》诗。韦庄于唐昭宗光化三年(900)编成的诗歌选本《又玄集》,选韩愈诗仅2 首,亦有此诗。可见此诗的传播影响。此诗题含“示侄孙湘”,故而韩湘其人其名也会随着诗歌的传播而广为人知。
(二)韩愈声望的影响。韩愈本来名声就很大,贬潮返京后,作为文坛领袖,又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要职,位高权重,加上谏迎佛骨、遽遭远贬一事的强烈戏剧性,使韩愈在朝野各界的声望更高、影响更大。韩愈的家人、交游等信息,必然更受人关注。韩湘十岁起便寄居韩愈家中,潮州之贬中又有突出表现③,知名度必然会提高。在这种状况下,自然容易被小说家们敷演出许多传奇故事。
(三)韩湘及第,韩愈及众多韩门文人饯行,作诗文赠别,声势颇大,参加者皆著名人物,交游广泛,这件事也会扩大韩湘的影响。
二、初步传奇化:《酉阳杂俎》“疏从子侄”故事文本来源辨析
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九《广动植之四·草篇》“牡丹”条中引述韩愈“疏从子侄”的一段文字,一向被视为韩湘入仙故事的萌芽:
韩愈侍郎有疏从子侄,自江淮来,年甚少,韩令学院中伴子弟,子弟悉为凌辱。韩知之,遂为街西假僧院,令读书。经旬,寺主纲复诉其狂率,韩遽令归,且责曰:“市肆贱类营衣食,尚有一事长处,汝所为如此,竟作何物?”侄拜谢,徐曰:“某有一艺,恨叔不知。”因指阶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黄、赤,唯命也。”韩大奇之,遂给所须试之。乃竖箔曲,尽遮牡丹丛,不令人窥。掘窠四面,深及其根,宽容人座。唯赍紫矿、轻粉、朱红,旦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填坑,白其叔曰:“恨校迟一月。”时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发色白红历绿。每朵有一联诗,字色紫分明,乃是韩公出官时诗,一韵曰“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十四字。韩大惊异。侄且辞归江淮,竟不愿仕。[4]1383-1384
这则文字虽未提及韩湘之名,但其故事框架与韩湘经历很类似:韩湘当初从江南宣城被韩愈接到京城读书,年方十岁,以子弟身份入官学就读,屡试不第,登第后又回宣城幕府做从事,这与故事中“疏从子侄”“自江淮来,年甚少,韩令学院中伴子弟”后来又“归江淮”的情节吻合。当然,现实中韩湘是去江南赴官而非“不愿仕”,这样改动大概是编故事者为了寄托仕途难料、世事无常的感慨,作了艺术加工。故事引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的“云横”两句诗,自然也会引发有关韩湘的联想。与韩湘真实事迹对比,故事主人公的“狂率”个性、巧妙的牡丹变色显字术,是值得注意的两个情节要素。
段成式(803?-863),段文昌之子,工诗,才学富赡、颇具文名。《酉阳杂俎》成书至迟在大中末(859),其时距韩愈去世未远;段成式仅比韩湘小9 岁,算同代人;两家又有某些关系④,因此段成式对韩愈、韩湘的情况应当有所了解。但《酉阳杂俎》一书并非纪实性质,该书在知识性叙述的表面下,收录了许多当时流传的传奇小说文字,鲁迅称其书“或录秘书,或叙异事,仙佛人鬼以至动植,弥不毕载。”[5]93具体到“广动植”部类,段氏在其序中说:“因拾前儒所著,有草木禽鱼,未列经史,或经史已载,事未悉者,或接诸耳目,简编所无者,作《广动植》,冀掊土培丘陵之学也。”[4]1095明确交代了这一部分内容的文本来源、写作目的。“牡丹”条中的“疏从子侄”这段文字,对比前后文,内容情节格外细致、生动,其文本来源大概就属于“接诸耳目,简编所无”一类。“牡丹”整条内容的写作目的,是记述唐代牡丹栽培历史、变色培育技术,中间引入“疏从子侄”一段,也是从园艺角度着眼。实际上,使花朵变色的园艺栽培技术,在当时并不稀罕,其他笔记小说中也有记载,如《龙城录》记述宋单父“能种艺术,凡牡丹变易千种,红白斗色,人亦不能知其术。上皇召至骊山,植花万本,色样各不同。”[6]151不过,通过花色改变的方式显示诗句文字,并夹杂着对韩愈遭贬命运的感慨,有些离奇,显然具有一定的虚构成分。虚构者未必是段成式,或另有其人。
许多研究者认为,此则《酉阳杂俎》文字,源自韩愈《赠族侄》一诗:
我年十八九,壮气起胸中。作书献云阙,辞家逐秋蓬。岁时易迁次,身命多厄穷。一名虽云就,片禄不足充。今者复何事?卑栖寄徐戎。萧条资用尽,濩落门巷空。朝眠未能起,远怀方郁悰。击门者谁子?问言乃吾宗。自云有奇术,探妙知天工。既往怅何及,将来喜还通。期我语非佞,当为佐时雍。[1]98
该诗描写韩愈在徐州遇到一位偶然来访的不速之客,自称族侄,“自云有奇术,探妙知天工”。诗歌内容与《酉阳杂俎》文字确实有一定关联,如“族侄”的身份、“探妙知天工”的“奇术”、徐州离江淮较近等。但也有可疑之处:
(一)《赠族侄》诗不见于唐人所编韩愈文集和各种早期选本,而是南宋人整理注释韩集时,“得于洪庆善《辨证》”,遂收入“遗集”。庆善即洪兴祖(1090-1155),有《韩集辨证》。因此这首诗的可靠性成疑,甚至不能排除是伪作。清代方世举就说:“此诗更与蓝关之事无涉。‘探妙知天工’者,不过如星士之言,故云‘既往怅何及,将来喜还通’也。词浅意陋,或非公作。”[7]51
(二)两种文本在时间、地点、情节方面都有明显差别。《赠族侄》贞元十五年(799)作于徐州,“疏从子侄”文写的是元和十五年(820)年底韩愈贬潮返京后的事情,时间相差20 多年。诗中写此“族侄”冒然前来,韩愈事前并不认识他,问了之后才说是同宗,连“疏从子侄”也算不上,更像是一位投机行骗的江湖术士。后来此人是否被韩愈收留,也没有下文,更谈不上“令学院中伴子弟”“读书”之事了。“族侄”自诩的“奇术”,并非园艺,而是预言术。
据此,我们可以推测,《赠族侄》仅是《酉阳杂俎》“疏从子侄”故事的可能来源之一;完整准确地说,此故事是以韩湘经历和《左迁》一诗背景为雏形,拼接了不同来源的情节、片段,综合加工而成。其中两个重要情节要素——“狂率”个性、变色园艺术,与韩愈及其门人的一些诗文作品可能有一定关系。
一是韩门文人沈亚之《送韩北渚赴江西序》中对韩湘个性的反映:
或曰:近世有府之侯,邀士拜宾,不由己之所尚,而使群居不类。故有谀言顺容积微之谗,以基所毁。四邻之地,更效递笑,飞流短长,天下闻之矣,而其侯尚且不寤。夫言谀足以瞽明,薄毁足以害忠。若是虽欲明其桡直,而明莫之遂也;虽乐闻己之所阙,而阙莫之闻也。彼思勤过畏者,一牵于谀谗即尔,而况己之所尚,又使群居不类乎?是以慎行者之所畏也。昔者余尝得诸吏部昌黎公,凡游门下十有馀年。北渚,公之诸孙也。左右杖屦,奉应对,言忠情劳。其馀则工为魏晋之诗,尽造其度。今年春,进士得第。冬则宾仕於江西府。且有行日,其友追诗以为别。乃相与讯其将处者而谁与?曰:有弘农生倞耳。夫弘农慎行其道不欺者也,北渚之往,吾无虞其类之患,勉矣惟耳,不衰于道而已。[8]170-171
沈亚之,生卒年不详,约生于代宗末、德宗初,卒于大和五年(831)后不久。沈氏游韩门十余年,与韩湘接触较多。擅写传奇小说,有《李绅传》等,风格奇婉,受韩愈较大影响。这篇序作于长庆三年(823),韩湘及第后赴江西任职,沈亚之为之送行时。此序通过对幕府中“群居不类”“薄毁害忠”这一问题的阐述,表达对韩湘前途、处境的关心,是了解韩湘性格的宝贵材料。“弘农生倞”,即杨倞,杨汝士之子,弘农人,曾注《荀子》,官至大理评事,他与韩湘入幕为同事,后来又都做了大理寺官员,可见他们仕途的起点、终点都有类似处。在沈亚之看来,韩湘、杨倞都属于“言忠情劳”“慎行其道不欺”这一类人,所以容易相处;但这种性格也有真率刚直、不合流俗、容易得罪人的一面,所以沈亚之一开始担心韩湘到任后恐有“群居不类”之患,招致流言谗毁。这种性格,很像《酉阳杂俎》中那位“狂率”、不合群的“疏从子侄”。
二是韩愈有关牡丹、园艺的一些诗文。韩愈有《戏题牡丹》诗:“幸自同开俱隐约,何须相倚斗轻盈。陵晨并作新妆面,对客偏含不语情。双燕无机还拂掠,游蜂多思正经营。长年是事皆抛尽,今日栏边暂眼明。”[1]943-944表达了对牡丹的喜爱之情。韩愈还常在诗文中以园艺之法来比喻为学作文之道,如:“少知诚难得,纯粹古已亡。譬彼植园木,有根易为长”(《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1]84,“浚其源,导其所归,溉其根,将食其实”(《重答张籍书》)[9]134,“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答李翊书》)[9]169等。这些观点及其比喻方式,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如沈亚之《送韩静略序》就借韩愈之喻,“闻之韩祭酒之言曰:善艺树者,必壅以美壤,以时沃濯。其柯萌之锋,由是而锐也。夫经史百家之学,于心灌沃而已”[8]172,并进一步引申发挥,说明文章写作之理。这些作品与《酉阳杂俎》“疏从子侄”故事未必有情节上的直接渊源,但至少为故事中园艺术的理解提供了知识背景。
唐人常在相聚宴饮时“宵话征异,各尽所闻”(李公佐《庐江冯媪传》),或在结伴旅行时“昼宴夜话,各征其异说”(沈既济《任氏传》),据此创作了很多传奇小说。由于韩愈韩湘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其真实经历和相关诗文作品中的一些片段、材料,在这样浓厚的小说创作氛围中,不断被传奇化演绎,《酉阳杂俎》“疏从子侄”故事大概就是这样逐步形成的。
三、道教劝诫和俗文学主导下的韩湘仙化过程
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述“疏从子侄”故事,纯属偶然;但五六十年后,另一种经道士加工过的韩湘入仙故事新版本的出现,则是有意为之。杜光庭(850-933)《仙传拾遗》(成书约为前蜀时期,即907-925 年)中的一篇《韩愈外甥》,使韩湘入仙故事真正迈出了神异化的一步。文中的主人公身份是“韩愈外甥”,虽然仍未标明是韩湘,而商山冒雪相送、韩愈作《左迁》赠诗等情节,更明确地指向了韩湘其人。该故事与《酉阳杂俎》“疏从子侄”故事,有明显继承关系,但多出了许多道教仙化情节:主人公信奉道教,其师为“洪崖先生”,曾“慕云水不归,仅二十年,杳绝音信”“行入林谷,其速如飞”“玄机清话,该博真理,神仙中事,无不详究”,而且有未卜先知的能力——早在韩愈贬潮作诗之前,他就将诗句暗置于牡丹花上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的韩愈,也出现了羡慕、向往道术的思想倾向,甚至也秘密加入了修道行列:“吏部加敬曰:‘神仙可致乎?至道可求乎?’”“其后吏部复见之,亦得其月华度世之道,而迹未显尔。”[10]331-332杜光庭身为道门领袖,《仙传拾遗》所记皆为道教神仙异事,出自道士之手,因此,这个“外甥”故事的宗教背景是很明显的,富于劝诫意味,超越了《酉阳杂俎》一般传奇小说的范畴。
五代至宋初,《仙传拾遗》“韩愈外甥”故事可能通过杂传文字传抄、道教讲唱等方式在民间广为流传,并不断演变。北宋中叶,刘斧《青琐高议》中的《韩湘子(湘子作诗谶文公)》,在《仙传拾遗》故事的基础上,将韩湘入仙故事进一步完整化、定型化。该故事的特点:一是正式将故事主人公定位于韩湘,并以道教方式尊称为“韩湘子”。二是借韩湘、韩愈的对话,批判韩愈排斥佛老的思想:“公排二家之学,何也?道与释,遗教久矣,公不信则已,何锐然横身独排也?焉能俾之不炽乎?故有今日之祸。”韩愈闻之,也表态:“今因汝又知其(笔者按:指道、释二教)不诬也。”[11]1076-1078这俨然是站在佛老立场上讨伐韩愈,并逼得韩愈认输,较之《仙传拾遗》对韩愈的嘲弄,显然更加严厉。
对《仙传拾遗》《青琐高议》中这两个故事的情节和文字演变,学者们大多停留在文本表面上,从文本自身的渊源流变角度去认识。如宋人严有翼《艺苑雌黄》就认为“段成式当时盖有所受之,刘斧特互窜其说而已”[12]69,许多当代学者也没摆脱这种认识角度。刘斧只是“互窜其说”、做了些情节和文字加工而形成的《韩湘子(湘子作诗谶文公)》故事吗?实际上,故事和文本流变的背后,是一股隐藏的道教影响下的民间文艺、俗文学的庞大潜流,只因它们未能留下文献材料,才不为人知。文人传奇文字的记述,可能会保存下一些痕迹,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痕迹,间接进行考察。《青琐高议》“韩湘子”故事中,我们也能发现一些道教民间俗文学的痕迹:
(一)道教歌谣的化用、增补。《青琐高议》“韩湘子”中有一首托名韩湘的诗:“青山云水窟,此地是吾家。后夜流琼液,凌晨散绛霞。琴弹碧玉调,炉养白朱沙。宝鼎存金虎,丹田养白鸦。一壶藏世界,三尺斩妖邪。解造逡巡酒,能开顷刻花。有人能学我,同共看仙葩。” 此诗源出《续仙传》:“殷七七,名天祥,又名道筌,尝自称‘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也。游行天下,人言久见之,不测其年寿。……每日醉歌曰:‘弹琴碧玉调,药炼白朱砂。解醖顷刻酒,能开非时花。’”[10]320-321殷天祥是传说中的道士,这首诗词句浅俗,也不一定是他所作,可能是当时道士们为了宣传炼丹造物之类道术,经常口头传唱的歌谣。某人在改编韩湘子故事时,也把此诗化用进来,并在原有四句的基础上,增补为十四句。
(二)《青琐高议》“韩湘子”一篇的七字副标题“湘子作诗谶文公”,俗文学色彩很浓厚,正如《四库全书总目》之《青琐高议》提要所云:“其为里巷俗书可知也。所纪皆宋时怪异事迹,及诸杂传记,多乖雅驯。每条下各为七字标目……尤近于传奇。”[13]1228从形式上看,此文篇幅较《酉阳杂俎》《仙传拾遗》两文更长,情节更曲折生动,对话丰富,并穿插数篇诗歌,虚构、敷演的程度更高。刘斧作为秀才,身份低微,有机会广泛接触社会底层,《青琐高议》中许多文字,收集自社会上流传的杂传传奇,富于民间气息。也正因如此,文士们常贬讥此书“鄙浅”“诞妄”“鄙俚”。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由《酉阳杂俎》《仙传拾遗》到《青琐高议》,韩湘入仙故事的仙化程度不断增强、道教思想成分不断增多,融入了浓厚的宗教劝诫意味,最后“韩湘子”成为正式仙人形象。韩湘故事宗教化的原因,与韩愈有密切关联。前文曾说过,真实的韩湘一生平常,其容易制造故事的“不同寻常之处”,皆来自其叔祖韩愈。其实唐宋时期关于韩愈本人的传奇轶事也不少。韩愈、韩湘故事之所以产生、被宗教化并流行,有韩愈本人思想性格和社会文化方面的深层背景:
(一)韩愈崇儒、排斥佛老立场鲜明,是儒、道双方都重点关注的旗帜性人物。皇甫湜《送简师序》:“刑部侍郎昌黎韩愈既贬潮州,浮图之士,欢快以抃。”(《皇甫持正文集》卷二)韩愈遭贬潮州、九死一生,佛教徒们闻讯却欢快鼓掌,可见他们对韩愈的憎恨。僧徒道士们在憎恨韩愈之余,便编排许多故事,丑化其形象,著名的韩愈结交僧人大颠的公案故事,即属此类。在韩湘入仙故事中,道教徒后来有意加入的韩愈羡慕、向往道教甚至秘密修道的情节,对韩愈和其他反道教人士来说,颇有调侃、嘲弄的戏剧性效果。晚唐至北宋,随着儒学复兴的进程,儒家与佛道思想从交锋到融合,韩愈被尊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地位声望达到高峰,但在知识精英和民间俗众的不同视野里,韩愈形象仍然是有差别的。
(二)韩愈个性好奇尚异,喜作传奇文字,曾作《毛颖传》《石鼎联句序》等;他思想里也有浓厚的宿命论色彩。这使他容易成为“话题人物”,被演绎出传奇故事。韩愈在《三星行》《祭郑夫人文》《乳母墓铭》等文中多次表达自己生命不辰的观点;在写给韩湘的《示爽》诗中,韩愈也明确表达了厌世、归隐的想法:“吾老世味薄,因循致留连。强颜班行内,何实非罪愆。才短难自力,惧终莫洗湔。临分不汝诳,有路即归田。”[1]1275这些都容易给人想象空间。
北宋中叶后,无论是知识精英还是民间百姓,对韩湘入仙的系列故事,都已比较熟悉,在诗文中常加化用。如:苏轼《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之四:“使君欲见蓝关咏,更倩韩郎为染根。”葛立方《题卧屏花·姚黄》:“抗旌汾浦根移白,竖箔蓝关花染红。”(《宋百家诗存》卷十九)等。南宋以后更多,尤其是以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魏庆之《诗人玉屑》为代表的诗话总集的转载、评论,让此故事更加普及。金代、南宋到元代,北方全真教由创立到盛行,韩湘仙化故事得到更大规模传播。全真教虽然更推崇钟离权、吕洞宾,但韩湘也位列仙班,成为早期“八仙”演变中比较靠前、稳定的成员。其后,韩湘子故事在小说、戏曲、道情、宝卷、弹词等俗文学中越来越多、广为流行,尤其是托名韩若云的小说《韩仙传》的出现,形成了后世韩湘子故事的主要框架。这些后话,并非本文讨论话题。
四、结语
综而言之,韩湘入仙故事早期流变的主要脉络和重要节点的背后,包含着许多有价值的细节问题。韩愈贬潮返京的传奇经历和《左迁》一诗的传播,使韩愈、韩湘的知名度、影响力得以提升,为韩湘入仙故事的创作提供了历史事实基础。晚唐五代浓厚的传奇小说创作氛围之下,韩湘真实经历和韩愈等人相关诗文作品中的一些片段、材料,经过拼接、综合、传奇化演绎,形成了晚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的“疏从子侄”故事。五代至北宋,由于韩愈崇儒、排斥佛老的鲜明立场和好奇尚异的个性喜好,在道教俗文学的潜在巨大影响下,五代杜光庭《仙传拾遗》、北宋刘斧《青琐高议》韩湘入仙故事的仙化程度不断增强、道教思想成分不断增多,宗教劝诫意味更加浓厚,韩湘成为了仙人“韩湘子”形象,在雅俗各阶层影响不断扩大,为其后来位列“八仙”奠定了基础。
注:
① 重要者有浦江清《八仙考》(《清华学报》第11 卷第一期,1936 年)、党芳莉《韩湘子仙事演变考》(《人文杂志》2000 年第一期)、陈尚君《韩湘子成仙始末》(《古典文学知识》2012 年第一期)等。
② 晚唐韦庄编《又玄集》选入此诗,题为“贬官潮州出关作”(傅璇琮等编:《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中华书局2014 年版,第826 页),应是传抄过程中产生的异文。
③ 与韩愈之子韩昶作一对比,更能见出韩湘才学品行的可贵:韩昶小韩湘5 岁,自韩湘被接来后,一起在韩愈身边成长。但韩昶资质愚钝,远不及韩湘、韩滂兄弟聪慧。贬潮时,韩湘一路伴随韩愈、历尽艰辛;韩昶后来才随家人被迫迁到岭南,但并没去条件艰苦的潮州,而是暂居韶关,后来韩愈量移袁州时才全家会合北上。
④ 段成式之父段文昌,曾奉旨重撰原为韩愈撰文的《平淮西碑》,影响很大。另,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五载:“(张)惟素后却索(卫协《毛诗北风图》),将货与韩侍郎愈之子昶,借与故相国邹平段公家,以模本归于昶。”(许逸民:《历代名画记校笺》,中华书局2021 年版,上册,第33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