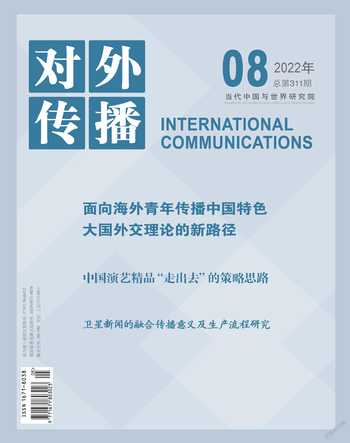国际传播中的共情层次:从理论建构到实践路径
2022-11-10徐明华李虹
徐明华 李虹
【内容提要】情感研究有助于在国际传播中跨越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的障碍,探究理性研究范式规避的社会过程性问题。情感传播的效果受制于多种因素,传播主体无疑在其中占据着优势地位。它不仅是传播内容的把关者,也是传播策略的决定者。传播主体本身的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传播效果。因此,立足于传播主体的差异,对国际传播中共情策略的运用区分国家叙事、媒体叙事和民间叙事,对应“不对称共情”、“弱共情”和“同感共情”三个层次,实施凝聚共识、广泛融情和精准共情的演进机制或可成为提升国际传播效果的有效策略。
【关键词】国际传播 传播主体 传播效果 共情层次
数字媒介时代,国际传播呈现出去中心化、多元赋权的新特征。无远弗届的互联网为多元传播主体的跨时空情感表达和差异化价值诉求构建了通路。技術赋能下的平台媒体和数字终端放大了公众的情绪和情感,舆论常常被情感裹挟,理性主义知识体系的禁锢被突破,国际传播理论研究和实践中的情感转向愈发明显。在这种时代变迁下,对和平与民主的呼唤、对霸权主义的抵制,对人类美好未来的期许,以及对现实歇斯底里的批判等,都折射出“情感共同体”的开拓性价值。①②因此,共情传播以及其赋能国际传播的作用机制将成为未来研究趋势中重要的增长点。
一、共情传播的理论溯源
(一)共情传播的内涵
共情的概念早已有之,但将其移植到新闻传播领域的相关研究还只是刚刚起步。对共情传播的概念界定,也未达到统一。吴飞对共情的心理基础、情感基础及实践路径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并将共情文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联系,以解决“对空言说”的传播困境。③李玲在《民族互嵌与共情传播——一个文化社会心理学的视角》一文中则提出从民族互嵌视角理解“共情传播”,强调个体与群体,以及群体之间的认同整合和文化混搭,以凝聚新的情感共同体。④这一表述打破了心理学视角注重个体之间关系研究的理论范式,扩展到个体与群体、以及群体之间的传播模式,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
刘海明和宋婷将“共情传播”界定为个体在面对群体的情绪情景时参与信息接收、感染和表达以及传递分享的行为过程。⑤赵建国在吸收前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共情传播”是共同或相似情绪、情感的形成过程和传递、扩散过程。⑥二者皆强调了情感的动态性,具有明显的传播学视角倾向。而李成家、彭祝斌对“跨文化共情传播”的界定中增加了共情的可培养性,并将共情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指向自我的情感共鸣阶段;二是指向“他者”的行动反馈阶段。⑦这一划分借鉴了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另有部分学者结合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对共情的种类以及动力机制进行了传播学视角下的理论阐释。
总体而言,共情传播的理论研究还处在探索阶段。到目前为止,相关研究大都停留在对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移植和嫁接层面,根植于传播学土壤的理论创新尚有待开发,共情对传播效果的影响机制也亟需更为深刻的理论阐释。
(二)共情传播的策略研究
关于共情传播策略的研究,近几年在学界逐渐勃兴,不仅形成了一定的成果积累,也为传播学在传播生态及媒介形态发生深刻变革的当下进行理论推进和视域开拓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而共情在国际传播中的应用也愈发受到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领域学者的关注。在诸多研究之中,基于个案分析的共情策略研究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内容涉及带货直播、纪录片、电影、电视剧、综艺节目以及主流媒体的报道等多种类型,其研究重点在于具体实践和微观领域中个体或群体的情感互动策略的应用。
在理论研究层面,以功能主义为主的研究范式居多。近几年来,不少学者关注如何利用共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国家形象以及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构建,如唐润华等指出尊重文化差异,唤醒受众共情能够提升出版业“讲好中国故事”的效果;⑧钟新等认为,诉诸情感共鸣的跨文化传播可成为国家形象建设的破局之道;⑨李克等则提出,利用共情修辞能够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⑩相关研究在切入点上较为集中,因而也留下了一定的研究空白。其形成的理论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聚焦内容文本探索以共情叙事打通传者和受者之间情感通路的途径;二是注重媒介对共情效果的渲染,以视觉强化和VR技术加持的沉浸式体验为主;三是强调区分受众地域,实施分域化共情策略。
综合来看,有关共情策略对传播效果的作用维度,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和传播客体三个方面,忽视了传播主体本身的属性对共情效果的重要影响,并缺乏对勾连传播主体和共情效果的中间作用层的相关研究。基于此,本文立足于传播主体,突出共情在其中的作用机制,通过共情层次的引入,建构从传播主体到传播效果的理论解释框架,并提出对应的策略演进路径。
二、从传播主体到传播效果的理论建构:共情层次的引入
作为传播五要素之首的传播主体在整个传播链条中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不仅决定着传播策略和媒介的择选,也掌握着传播内容的取舍。尽管如此,传播主体本身的属性依然通过影响受众对信源可信度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传播效果。毋庸讳言,相同的内容由不同的主体以相同的方式进行传播,结果可能会大相径庭。可见,从传播主体到传播效果之间引发终极质变的中介因素并非传播内容和媒介,情感及共情因素或在其中发挥重要引导作用成为合理想象。鉴于此,本部分旨在通过建构传播主体和传播效果之间的情感作用机制来探索传播主体之差异如何影响共情效果并导致传播效果发生异化。
(一)国家叙事与“不对称共情”
自进入“后真相时代”以来,国际舆论环境在计算宣传的肆虐之下充斥着情感的宣泄和基于意识形态对立的谩骂,中国面临着持续恶化的国际舆论环境。部分西方政客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威胁,通过抹黑中国和妖魔化中国、构建“中国不负责任论”“中国威胁论”等手段对中国展开话语攻讦。西方罔顾中方长久以来宣贯的外交理念以及在国际关系中的现实做法,一味地排挤和诽谤中国,与其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西方二元对立思维的形成,是由西方哲学、宗教和语言的特点所决定的。11西方哲学的二元对立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爱利亚学派的创始人克塞诺芬尼的学生巴门尼德建立了古希腊第一个二元论哲学体系,他划分了“真理”与“意见”两条完全独立的认识途径,并论证了各自的功用。12这一二分法的哲学思路也限定了整个欧洲哲学思想发展的基本走向。中世纪时期,哲学思想中的主客二分是在其基础上的演进,并进一步形成了系统的认知方法。近代西方哲学最典型的代表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即“思维/存在”何为本源的问题。他以遵循严苛形式逻辑的几何学为哲学范本,非此即彼的思路就发源于此,13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二元对立的产生,如主体/客体,理性/感性,肉体/灵魂,心/物等。在宗教学和语言学领域,也延续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至于西方近代以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本上浸润于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之中。14
基于这种长期以来的二元对立思维造成的敌我观念,部分西方国家不断地区分“自我”与“他者”,并丧失了客观评价“他者”的能力,“以己度人”地视中国的崛起是世界的威胁。究其背后深层次的价值逻辑,其实质是冷战思维和种族主义。在这种背景下,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传播,其共情的传播通路已然受阻。
国外学者的研究指出,通常情况下,客体会基于本能对主体的情感产生共鸣,形成相同或相似的情感反应。但当主体与客体存在竞争关系,或者客体认为双方存在竞争关系,以及主客双方分属于不同群体时,反而会催生与主体不一致的情绪反应。这种不一致的反应称为“不对称共情”。15这一观点随后也得到了更多学者的研究证实。由此可见,在二元对立思想的统筹下,国家叙事透视着意识形态的对立,容易引发海外受众的不对称共情效应,进而形成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鸿沟。
(二)民间叙事与“同感共情”
“民间”一词能够作为“官方”的对立概念在传播学领域出现,得益于网络和智能媒介终端的发展。这也昭示着巨大的民间话语空间已经形成,多元赋权的传播格局正在改变着国际传播实践。
民间叙事与国家叙事最大的不同在于,“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关系弱化。虽然在国际传播中,国家、种族、文化等层面的差异依然存在,传播主体与传播客体依然分属于不同的群体。但除此之外,主客双方拥有超越社会意义的人类天然共通的情感。人类的爱与同理心是超越种族、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我们既能够感同身受相同文化的他者遭遇,也能够对异质文化的他者产生共情。相较于国家叙事,民间叙事更容易跳脱“中国/西方”的二元格局,在更广泛的共享意义空间寻求“同感共情”。
民间叙事更具微观性,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以现实的烟火景观折射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而大量的民间叙事集结成中国故事的群像,能够给受众带来更加强烈的感官刺激和情绪感染,从而基于个体内部的生理驱动带来对传播内容的同向解码,情感的同频共振得以形成。
民间叙事更具真实性。这是民间叙事相比于国家叙事更能激发共情的底层逻辑。传播主体的差异对传播效果的影响,从根本上来看,是对信源可信度的認知差异。共情的过程并非是与理性的彻底割裂,受众在接受情感信息的同时,如果内在理性判定信源不真实或存在虚假成分,共情的传播过程也会阻断。从这个角度来讲,民间叙事更具有说服力,更能以真实的情感打动异质文化的受众。
民间叙事可以弥补国际传播的话语权落差。自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以来,部分西方媒体通过污名化中国来转移国内舆论压力,并对中国的外宣媒体实施系统打压和机构化壁垒,中国的官方机构和外宣媒体难以在国际上发声。而民间叙事拥有相对广阔的话语空间,社交平台上聚集的大批内容生产者,可通过本土化议题的介入讲海外受众想听的中国故事,以此拉近距离,构建共同情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落差。
(三)媒体叙事与“弱共情”
媒体这一特殊叙事主体,既不像国家主体般让受众产生强烈的政治立场对抗情绪,又难以像民间主体那样让受众毫不设防,它是介于国家叙事和民间叙事之间的存在。在不对称共情到共情的尺度之间,媒体叙事对应的是“弱共情”。
国外学者德沙第(Decety)提出,共情的过程包括指向自身的情绪感染(即自动产生和他人相同或相似的情绪)和指向他者的情绪关注(包括安慰、同情、担心等)。16前者是情感在人内被唤起和调动的过程,后者是情感在人际间的反馈与分享,意即共情的生理驱动性和社会构建性。17生理驱动性常常是自发的,而社会构建性则具有较强的主观能动性。在媒体叙事的国际传播过程中,受众依然会基于本能对传播主体产生相同或相似的情绪感染,但后续的社会建构性行为却有极大概率被抑制。原因不外乎社会角色和身份感在其中的参与,使其对传播主体的信源可信度和传播目的判断发生了异化。因此,媒体叙事在国际传播中会引发弱共情,弱化的环节主要在于指向他者的社会构建过程中。
具体到传播实践视角来看,媒体叙事通常有特定的服务对象。它或是国家叙事和对外发声的工具,或是民族精神和大众风貌的窗口。显然,它在作为国家发声工具时,对海外受众而言更倾向于不对称共情。这一情绪也会造成首因效应,使它在发挥其他职能时,容易激发海外受众的反感甚至抵抗情绪。这就从另一视角进一步证实了媒体叙事的弱共情效应。
综上所述,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国家叙事、媒体叙事和民间叙事依次对应“不对称共情”、“弱共情”和“同感共情”三个层次。这一对应关系的形成是基于对共情效果的整体感知,而非微观实践领域的绝对性分野。
三、国际传播中的共情分层演进策略
讲故事是人类最原始又行之有效的话语实践,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叙事是认知建构,能够承载意义并传递信息。故事本身虽不具备支配性,但却可以通过情节的搭建和人物形象的构建内隐地支配受众的内心秩序。要讲好故事,需要建立正确而清晰的叙事观。在国际传播中,叙事要遵循“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道化人”的逻辑,构建情感视野下的立体传播体系。共情效果的强弱与传播主体对应的共情层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在传播的过程中应针对不同的叙事主体,采用差异化的共情策略,来赋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大战略。
(一)国家叙事:凝聚共识
在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传播中,意识形态贯穿于信息流动的全过程,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受众的情感倾向,导致不对称共情效应,收到事与愿违的传播效果。基于此,如何在国际传播中减少意识形态的排斥性,是目前国家叙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凝聚共识,是国际传播中减少对抗,避免冲突的基础。凝聚共识有着不同的面向,现阶段国家叙事所要凝聚的共识是人类共同价值和利益基础上的共识,是作为世界公民平等性的共识。因此,以人类整体诉求作为关注焦点,保持价值中立,寻找全球背景下的文化共识,迎合人类认知共性,不仅可以营造友好互通的跨文化传播环境,也能够提高国际传播的效能。
在社会媒介化趋势之下,国际传播与国内传播的边界逐渐消弭。“人人都有麦克风”使得各类社交媒体上众声喧嚣。这是由于全球政治、文化的多样性所带来的认知差异在社交平台上被放大所致。另外,国家事务在圈层内被频繁讨论,有碍于圈层的知识体系和认知水平,也可能会带来深度的缺失。虚拟网络的意见表达必然是依托于现实世界的,因此,在现实世界中凝聚共识是情感共同体得以形成的前提。有学者提出,跨文化共情传播的驱动机制包括情感本能驱动,理性引导驱动和社交需求驱动。18情感本能驱动是人类的天性,是与生俱来的能力。而凝聚共识则是刺激理性引导驱动的内在动力,是社交需求驱动的必要铺垫。当理解受阻,共情无望,以共识寻求对话的可能或可成就预期的“同感共情”。
共情能力不仅包括自我与他者形成共情的能力,也包括唤醒他者潜在共情的能力。19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凝聚全球共识,唤醒他者潜在共情的最佳理念,它没有明显的价值导向,而且超越了早期中国提出的诸如“互不干涉”等外交理念,是基于人类共同价值和美好未来的共赢理念,也是相对容易被国际社会认同的理念。它能够写进联合国协议,也说明了这一点。
(二)媒体叙事:广泛融情
媒体叙事要避免过度共情,过度共情会导致传播效果负增长。如前所述,国际传播中媒体叙事倾向于引发弱共情效应。在这种情形下,若不顾及受众的情感反应,过度进行情感输出,则可能发酵成共情极化,致使负向情感在社交媒体上聚集,并不断滋长。加之网络的虚拟性和匿名性,网民在社交媒体上情感和意见表达更加“肆无忌惮”,负面的评价有可能进一步演化为污蔑和诋毁,并呈几何增长态势,最终演变为对国家形象的损害。再者,共情过度会导致国家形象陷入泛娱乐化语境。多元赋权下数字媒介挑战了传统媒体的权威,过去严肃、刻板、理性的国家形象传播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温情、无序和感性的传播方式。过度感性化不仅会侵蚀理性价值,无法形成持久的价值判断,也容易陷入娱乐化的桎梏。
因此,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媒体应回归传播本位,树立平台化思维、话语权思维和柔性传播思维,培育新媒体理念,调整战略布局,不断拓宽外宣渠道。同时,尽快搭建自主可控的外宣平台,淡化官方底色,以平台化思维开展定制化传播,将专业媒体角色打造成社交媒體中的关键意见领袖型传播主体。另外,提前布局元宇宙,在新赛道上赋能国际话语权提升,在虚拟时空的数字传播中抢占先机。
不仅如此,主流媒体也要协同关键意见领袖(KOL)做好议程设置,主动介入本土化热门话题,以争取更广泛的国际话语权。媒体建设上也要注重多元化背景的吸纳,多采用在地记者和本土主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广泛融情之声势和力量,进行话语权的强化。
总而言之,借助全媒体网络和平台媒体的优势,推动民间传播、在地化传播和精准传播,通过与国家叙事和民间叙事的“和声共振”,广泛融情,实现从独白式到复调式的传播格局转换,是媒体叙事在国际传播中应发挥的价值。
(三)民间叙事:精准共情
民间叙事是三类主体中最容易激发共情的传播主体。利用这一优势,民间叙事应竭力做到以受众为中心的精准共情。数字空间的国际传播,已具备精准共情的外部条件。首先,传媒业已由过去奉行“内容为王”的理念转变为“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这意味着既往“人找信息”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信息找人”成为智能传播时代的新逻辑。其次,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跨国间的精准传播具有技术可行性。最后,平权化社会的到来使得大众的意见和情绪可表达、可传递。20多元主体在表达自我和接收信息的过程中表现出更多对感性的渴求。
要做到“精准共情”,找准契合点是关键。共情传播,“共”是前提。这一前提有助于民间叙事在国际传播中跨越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的障碍,激发情感的共鸣、共振。在跨文化的传播中,共同的价值观往往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关注不同国家作为世界公民的相似性。以真实动人的故事构建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勾连,以此向国际社会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在实际操作维度,可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整理用户画像,并对受众的情感倾向实施动态监测,以掌握准确的目标受众。同时,聚合社交化的中国故事讲述者,基于一定的算法逻辑进行匹配,实现中国故事的精准传播。从确定目标受众到传播内容的分发,并不是一次精准传播的终结。受众的后续反应,如转发、评论情况,相关话题参与度,预期情感反馈与真实情感反馈的差异等,仍是需要持续关注的焦点。这将成为评价“精准传播”是否成功的重要依据,并能够为之后的精准共情决策提供参考。
四、结语
情感研究有助于在文化差异中跨越意识形态障碍,解读理性研究范式回避的社会过程性问题。理性主义的分析框架致力于因果关系的探究,而模糊了鲜活且具体的感觉领域。但社会科学研究不能仅寻求因果的关联,而是重在其中若干理论通路的构建。基于此,本文针对传播主体与传播效果之间情感质变的内在逻辑构建了基于共情层次的理论想象,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选择。同时,把传播主体在国际传播中的隐性影响重新带回公众视野,以寻求更多具有实践指导力的应对策略。
徐明华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虹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徐明华:《情感传播:理论溯源与中国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33页。
②史安斌:《尊重传播规律,开掘“情感市场”》,《河北教育》(德育版)2021年第59卷第3期,第2页。
③吴飞:《共情传播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探索》,《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5期,第59-76页。
④李玲:《民族互嵌与共情传播——一个文化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文化与传播》2019年6月第3期,第30-35页。
⑤刘海明、宋婷:《共情传播的量度: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的共振与纠偏》,《新闻界》2020年第10期,第11-20页。
⑥赵建国:《论共情传播》,《现代传播》2021年第6期,第47-52页。
⑦李成家、彭祝斌:《论跨文化共情传播——基于国际互助抗疫的探索》,《现代传播》2021年第5期,第65-69页。
⑧唐润华、郑敏:《文化间性视域下出版业“讲好中国故事”的效果提升路径》,《新闻愛好者》2021年第3期,第50-52页。
⑨钟新、蒋贤成、王雅墨:《国家形象的跨文化共情传播:北京冬奥会国际传播策略及效果分析》,《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5期,第25-34页。
⑩李克、朱虹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共情修辞路径》,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88-96页。
11袁晓燕、尹净净:《论西方的二元对立模式》,《时代文学》2007年第1期,第118-119页。
12武贝玫:《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二元论哲学体系——巴门尼德哲学新探》,《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第89-94页。
13袁晓燕、尹净净:《论西方的二元对立模式》,《时代文学》2007年第1期,第118-119页。
14朱立元:《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关于新世纪文艺学、美学研究突破之途的思考》,《文艺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第2-9页。
15Aderman, D., Unterberger, G. L., “Contrast empathy and observer modeling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77(45): 267- 280.
16Decety, J,“Human empathy”,Japanese Journal of Neuropsychology, 2006(22):11-33.
17马龙、李虹:《论共情在“转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机制》,《现代传播》2022年第2期,第77-83页。
18李成家、彭祝斌:《论跨文化共情传播——基于国际互助抗疫的探索》,《现代传播》2021年第5期,第65-69页。
19唐润华:《用共情传播促进民心相通》,《新闻与写作》2019年第7期,第1页。
20喻国明、陈雪娇:《理性逻辑与感性逻辑的交互与协同:媒介内容生产的新范式》,《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2期,第119-125页。
责编:谭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