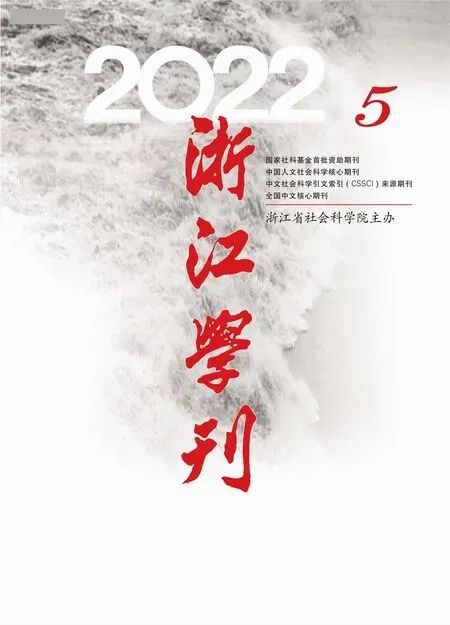今世前身:诗人的自我实现与心理暗示
2022-09-05庄国瑞
庄国瑞
提要:中国古代诗人谈论“前身”,从其身份与文学言说的角度看似乎凭空虚构,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实则是一种“心理暗示”现象。它与个人在生存环境中所进行的自我建构直接相关。清末民初诗人易顺鼎对“前身”的追溯在诗人群体中颇具代表性:他自言有七世前身,但所关注的核心人物是明代才子张灵。易顺鼎因对前身之说确信不疑,由此产生强烈的心理暗示,行为及创作上受到张灵名士狂诞之气、脱俗之深情两方面的影响较大。从长时段角度整体观察中国古代诗人世界,将各种追溯“前身”的言论汇集考察,可以发现诗人追溯“前身”的观念与神话、传说、佛教文化影响均有关系,且受佛教观念影响更为显著,唐宋以后较为普遍地表现于诗人的创作中,可以说是诗人世界中一种特殊的文化行为。
中国古代诗人群体很长时间以来流行一种话语,即关于“前身”的创作表现与言论。谈论“前身”通常被视为文学化的虚构,但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提法并不虚妄,它是一种典型的心理暗示,是自我探究、自我构建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心理现象。人类普遍都会受到心理暗示的影响,“受暗示性是人的心理特性,它是人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无意识的自我保护能力和学习能力。这种与生俱来的能力是人们保护和塑造自己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1)埃米尔·库埃:《心理暗示力》,方舟编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第6页。“前身”一旦确定,便会对具体个体产生一定影响,随着相关内容不断积累深化,个体会通过向外部表达、与外部交流、在外部寻找证据等,来确认输入内容。追寻“前身”对于“自我实现”的意义,在于它会强化某个个体身上具有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本来可能只是不甚显眼的存在,但由于“前身”的确定,激发了强烈的“心理暗示”,使得这些特征得到不断地加强与巩固,最终成为显著的个人标志性风格,从而达致自己努力追求的目标,完成“自我实现”。关于诗人追溯“前身”对自己产生的影响以及追溯“前身”现象本身的产生及发展过程,目前来看鲜有论及。由确定“前身”而对诗人个体反过来产生重要影响,这一点在清末民初诗人易顺鼎身上表现特别突出。其实,这也是存在于中国古代诗人世界中相当普遍的一种文化现象。
一、易顺鼎前身之思的形成
易顺鼎(1858-1920年)字实甫,(2)又字硕甫、实父、石甫、中实、仲硕,少年时自号忏绮斋、眉伽,中年后号哭盦(哭庵),亦号哭厂、一厂等。湖南龙阳(今汉寿)人,出身上流社会,(3)其父易佩绅(1826-1906年),字笏山,曾在贵州、山西、四川等多地任职,官至布政使,尝与郭嵩焘、王闿运游,诗学随园,与陈宝箴、罗亨奎交好,当时被称为“三君子”。幼有“神童”之誉,少年时代便刻印诗词集,十八岁科举高中。虽然中年以后仕途不顺,又经历清末战乱与社会更迭的剧烈变动,有颓唐放纵之态,但他对自己的才情一向自负,交游者对其才华也极为赞赏。他为自己独特的个性才情找到一种解释,便是具有夙慧根基——“前身”,并且终身信之不疑。
易顺鼎有明确前身之思的想法是因一次扶乩活动而起。光绪九年(1883)易顺鼎二十六岁,其父易佩绅在山西布政使任上,七月其长姊易莹殁于太原藩署中,易顺鼎九月闻讣信后,离京赶赴太原。易佩绅素信扶乩,又悲伤女儿去世,于是设坛请仙,降乩者为“李仙(李铁拐)”,并招易莹降灵,谓已成仙,仙号“真一子”,易氏父子与之唱和。在这次扶乩活动中,李仙作语示意顺鼎,有云 :“吹箫王子,乞食张郎”,(4)《〈题张梦晋画折枝长卷寄宗室伯羲祭酒绝句八首〉序》,易顺鼎著,王飙校点:《琴志楼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90页。易顺鼎自言当时在旁者皆不知“张郎”为谁,只有他曾见清初黄周星所撰《张灵崔莹合传》(5)黄周星撰,谢孝明校点:《黄周星集》,岳麓书社,2013年,第108-114页。中有张灵乞食之事,且张灵系母梦周灵王太子晋而生,故名梦晋,契合“王子”“张郎”之提法,自此易顺鼎便自命为东周太子晋、明代苏州才子张梦晋后身,《十二月二十四日雪中独游邓尉元墓宿圣恩寺还元阁》其十八云:“重听元墓寺前钟,山径昏黄鬼气浓。指点前生埋骨处,依然寒雪满林松”,是直以梦晋后身自况。后他亦至张灵墓,《过苏州吊曾季硕女士因访前生张灵墓兼省亡儿墓作》云:“辽鹤归来叹冢累,风花满目更凄其。前生地主今生客,新鬼天人故鬼儿。海内枯禅惟剩我,江南痛哭欲同谁。回车不为穷途恨,阮籍生平易酒悲。”(6)易顺鼎著,王飙校点:《琴志楼诗集》,第332、511页。
如以才子论,易顺鼎的名声比张灵只恐过之而无不及。易顺鼎五岁时便有出奇经历,由于其父迁知府诏防守陕南,家人亦随之入陕,易顺鼎随母居汉中府,太平军包围汉中,其母欲自尽,命差役带着易莹、易顺鼎逃往其父军营,路上易顺鼎不幸与姐姐走散,被太平军获得,后知其为易佩绅子,知会允许赎回,但易佩绅因汉中失守被议革职,已撤营。易顺鼎遂留太平军中半年多,后自述:“五岁陷贼中,贼自陕蜀趋郧襄,以黄衣绣褓缚之马背,驰数千里。”之后因遇僧格林沁大军而获救,“遇蒙古藩王大军,为骑将所获,献俘于王。哭庵操南音,王不能辨,乃自以右手第二指濡口沫书王掌”,僧格林沁大喜,呼曰:“奇儿”,(7)易顺鼎著,王飙校点:《琴志楼诗集》,第1440页。令人送归其家,“归之日,空城往观,神童之名满天下”。(8)奭良:《易实甫传》,易顺鼎著,王飙校点:《琴志楼诗集》附录一,第1445页。相交密切者如王闿运,在书信及日记中频呼其为“仙童”。而易顺鼎也不辜负众人的赞誉,十五岁为诸生即有名,十七岁举于乡,所为诗歌文词广为传播,皆赞其为“才子”。与易顺鼎交往者往往震动于其才华,户部侍郎周寿昌赠诗曰:“此才岂止空当代,老眼犹欣见异人。”刑部尚书潘祖荫初见即曰:“曾读《行卷》(按:指《丁戊之间行卷》),惊才绝艳,倾倒久矣!”又对诸司官曰:“此空前绝后一枝笔也。”(9)王飙:《易顺鼎年谱简编》,易顺鼎著,王飙校点:《琴志楼诗集》附录四,第1562页。又尝与坐客论天下名士,及于易佩绅父子,笑言:“其父人才,其子乃天才也。”(10)王森然:《近代名家评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41页。易顺鼎师事张之洞,尝共联句,辄惊老成。张之洞为显其才,一日设宴署中,邀请诸名士,易顺鼎年少,陪于末座。席上众人联句助兴,以“贺新郎”为题,限九佳韵,“至二十余律,皆不能续。顺鼎独成三十二韵,词句新颖,竟致缠绵,合座惊奇焉。”(11)李法章:《易顺鼎传》,易顺鼎著,王飙校点:《琴志楼诗集》附录一,第1449页。张之洞曾对一门生言:“实甫,旷世天才也。尝以行卷求益,若词章固犹不足传耶?度若才,何学术不可跻,而顾画是耶?”到开封任职时,巡抚倪文蔚以国士见待。其他评价如:“吾友易君实父,才情天妙,文誉早兴。”“实甫少负奇禀,识与不识,莫不推为神仙中人。”“绝奇之才,莹锋如干将莫邪。”(12)王秉恩:《摩围阁诗序》,宋育仁:《易实父诗录序》,王以敏:《魂北集序》,王铁珊:《魂东集序》,易顺鼎著,王飙校点:《琴志楼诗集》附录二,第1491-1496页。以上不过列举典型评价,其他赞赏之词尚多。虽然师友评价不无溢美,但众口一致叹其才华也非易事,今阅其诗作,知非虚誉。

易顺鼎对自己有前世夙缘的说法持之终身。传记作者写道:“哭庵晚年书札中常钤一朱文大印,文曰:‘五岁神童,六生慧业,四魂诗集,十顶游踪’”(16)王森然:《近代名家评传》,第97页。这里提到六世前身,是因为张灵言前身为王子晋、王昙首(394-430年),而张船山(张问陶,1764-1814年)、张春水(张澹,生卒年不详)之所以被列于其中,是因为易顺鼎得到友人薛次申、端仲纲所赠二张的画册,其中均有“张灵后身”小印,所以也被认定为前身,第五位陈纯甫则为其母舅。(17)王揖唐著,张金耀校点:《今传是楼诗话》,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34页。“六生之说”广泛为众所知,王先谦《实甫自言前世为张梦晋其友藏张船山书画册中有张灵后身小印以归实甫携之至台湾索题》云:“祇因宿世俱词客,合作三生石上魂。”周检斋《梦得“竟成忠孝夺才名”句因续成之奉赠仲实观察即希削政》云:“漫从元墓伤遗迹,(自注:君感梦晋事尝哭吊元墓)已悟张家再托生。(自注:梦晋有“何日张家再托生”之句,又张船山画册有张灵后身章,君复得之,知已三托生矣。)”其后实甫之友郑叔问,又说王仲瞿(王昙,1760-1817年)也是实甫前身,遂有“七生之说”,易顺鼎尝有句:“九州我早历其全,三生我尚多其四。(自注:余有七生图记。)”(18)《和屈翁山五十四岁自寿韵》,易顺鼎著,王飙校点:《琴志楼诗集》,第1168页。不论“六生”还是“七生”,其核心人物所指为“张灵”,对易顺鼎影响最大,各种言说也主要围绕张灵的性情及经历展开。
为什么一定要追寻前世,且落实在张灵身上。首先,幼年“神童”、“仙童”之评价,让易顺鼎始终相信自己来历不凡且极欲追寻“真相”。三十七岁所撰《哭庵传》于家世一笔带过,紧接“哭庵幼奇慧”,讲五岁陷落乱军中又得脱之事。这件事被放在传记开头,因为发生早且特别受重视,影响持续终生,后来拜见慈禧时陪同官员仍然提及此事。可以说这种“夙慧”不仅震惊到别人,也震惊到自己,就易顺鼎本人来说他追问此生来历的心理,比一般默默无闻的普通人要强烈得多。易顺鼎曾多次参加扶乩活动,虽受其父影响,但他对扶乩活动中所谓神示之语表现出异常的兴趣,实际上说明了内心寻求答案的渴望。其次,易顺鼎在张灵身上找到了极大的相似性。他的前世都是才子式的人物,其中还有清代三大性灵诗人之一的张问陶,但为何更关注张灵,是因为“乞食”之事明确只发生在张灵身上,而且从气质行为之潇洒不羁来说与张灵更合而与张问陶不合,所以“六生慧业”的说法,最后实际落在张灵一人身上。再次,出于诗人自我标榜、追求新异的心理。诗文创作杰出者绝大多数都是心思活跃、频有异想之人,世俗普通的解释、生活形态都不能满足他们求新的想法,尤其像易顺鼎这样的才子,不可能对自己的突出特点默不作声。果然这一标榜对其自身来说是心理情结的验证与解释,对周围人来说则新奇有趣,在其交游圈内形成了一个可以共同言说的话题,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普通人即便也求证出自己的前世,多半难如易顺鼎这般产生广泛影响。
二、张灵对易顺鼎的影响
张灵虽诗画兼善,但诗作多随手散佚,存世仅数首,并非直接在创作上对易顺鼎产生影响,张灵对易顺鼎的影响,主要在精神气质、个性风度上,可以说在接受扶乩结果之后,便逐渐潜移默化浸润其心,再加之主动追寻与反复验证,“心理暗示”不断得到强化,进而体现于行事风格与文学创作中:一方面是名士狂诞之气,另一方面是脱俗之深情。
张灵《明史》无传,但多种明人史传、笔记、诗话作品中有其短篇传记或零星记载,“吴县人,家故贫窭,作业闾阎,至灵始读书。……灵能人物画,人皆推之。”(19)⑥ 过庭训纂集:《明朝分省人物考》,广陵书社,2015年,第444-445、444页。“张灵本窭人子,力作自给,而灵生乃有爽气。”(20)蒋一葵撰,吕景琳点校:《尧山堂外纪》,中华书局,2019年,第1417页。“才调无双,工诗善画,性风流豪放,不可一世。”(21)黄周星撰,谢孝明校点:《黄周星集》,第108页。“吴中又有张灵梦晋善小竹石、花鸟。”“张梦晋石湖秋渠、风流名士,……所谓‘意足不求颜色似’者,题字亦多佳致。”(22)王世贞:《弇州四部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百五十五、 卷一百三十八。由以上数条可知,张灵并非世家子弟,家贫的条件下能有如此才具,无需深考,可知其人天资聪颖,与易顺鼎一样同属早慧之人。
张灵才子形象固然鲜明,但在世人眼里,“狂生”“狂士”的形象更为突出。其人好酒,“好交游,为侠客,至不过具器,而必欲极其欢,灵醉则使酒作狂,每叹曰:‘日休小竖子耳,尚能称醉士,我独不能醉耶?’”⑥祝允明爱其才,令受业门下。与唐寅最相善。故不少事情皆与祝、唐有关联,“(祝枝山)日偕唐子畏、张梦晋等放浪山水,效晋人风。”“(唐寅)又尝与祝希哲、张梦晋雨雪中被乞儿服,鼓节沿门,得钱沽酒野寺中,痛饮而别,曰:‘此乐恨不令太白知之。’”(23)査继佐:《罪惟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286、2311页。“(唐寅)补府学生,与张梦晋为友,赤立泮池中,以手激水相斗,谓之水战,不可以苏狂赵邪比也。”(24)黄鲁曾:《吴中故实纪》,唐寅著,周道振等辑校:《唐寅集》附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51页。乞食之事,是与唐寅游虎丘,“会数贾饮于可中亭,且咏诗。因更衣为丐者,上贾与食啖之,灵请续和。……贾始骇令赓,灵即挥毫不已,凡百绝。抵舟,命童子易维萝阴下令绝迹。贾使人察之,不见也。皆以为神仙。贾去,复上亭,朱衣金目,作胡人舞形状,殊绝。”(25)蒋一葵撰,吕景琳点校:《尧山堂外纪》,第1418页。此事亦见载于王世贞:《增补艺苑卮言》卷五、冯时化:《酒史》卷上、过庭训:《明朝分省人物考》卷二十二、文震孟:《姑苏名贤小纪》卷下、钱谦益:《列朝诗集》丙集卷九、査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八、尤侗:《明史拟稿》卷四等,大体一致,言辞及细节有一些差别。黄周星《张灵崔莹合传》对此事有较多演绎,与如上诸书所载区别较大。王世贞评价张灵与唐寅:“张才大不及唐,而放诞过之。”(26)王世贞著,陆洁栋、周明初批注:《艺苑卮言》,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93页。
易顺鼎受到张灵狂诞之气的影响还是很深刻的。《哭庵传》概括自己人生云:“初为神童,为才子;继为酒人,为游侠;少年为名士,为经生,为学人,为贵官,为隐士。忽东忽西,忽出忽处,其师与友谑之为‘神龙’。其操行无定,若儒若墨,若夷若惠,莫能以一节称之。……要其轻天下、齐万物、非尧舜、薄汤武之心,则未尝一日易也。”(27)易顺鼎著,陈松青校点:《易顺鼎诗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289-1290页。致陈三立信云:“平生择术,不好孔孟,而好杨墨;平生操行,不喜仁义,而喜煦孑。冥顽不灵、放达不羁。其自视也,若轻而若重;其自命也,忽高而忽卑。不屑为理学,不肯治其私。以为有害于人,有害于心,则不可为。”(28)《与陈伯严书》,易顺鼎著,陈松青校点:《易顺鼎诗文集》,第1290页。另“煦孑”原文为“煦丫”,校点者认为当做“煦孑”,语本韩愈《原道》:“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从其说。前者为其自传,后者为写给挚友之信,言辞虽然带有一贯的修饰夸张,但对自己人生特点、行为风格地概括还是准确的。易顺鼎好山水,晚年钤印有“十顶游踪”之语,即因曾游泰山、峨眉、青城、庐山、衡山、沩山、终南、罗浮、天童、普陀诸山。其登览胜景有与人不同之狂放处,“多于云雾雪月中登宿绝顶,……十顶皆名岳大山,其余若湘之岳麓、汾之晋祠、蜀之中岩、润之焦山、燕之西山、吴之元墓、包山,以及行役所经黔蜀晋秦,亦屡宿万山之顶”,(29)《〈宿顶诗十首〉小序》, 易顺鼎著,王飙校点:《琴志楼诗集》,第1083页。尚奇纵意之态非常明显。
易顺鼎的名士狂气,有时能获上司赏识,有时则招致龃龉。其早年曾在河南作河道属官,尝赴郑州河堤,督修河工,工竣乞假,时任河道总督吴大澂留之不得,笑曰:“诗人固不耐官也。”顺鼎闻之曰:“吾以一官博诗名,足矣。”(30)奭良:《易实甫传》,易顺鼎著,王飙校点:《琴志楼诗集》附录一,第1445页。但后来出任广西太平思顺道道员,才三个月便因争执是否裁撤绿营等事与两广总督岑春煊抵牾,被以“名士画饼”“不谙治理”劾罢,一般官员遇到问题多迂回委婉不与上司冲突,易顺鼎言辞与行事上狂傲之气难掩可谓丢官的直接原因,后于文中自嘲“‘名士画饼’为余一生最著之典。”(31)《诗钟说梦》,易顺鼎著,陈松青校点:《易顺鼎诗文集》,第1896页。
张灵最有名之事莫过于“乞食”,仅此一事即可看出其人自任才气,难掩炫耀之意。易顺鼎在创作上也可谓具有十足的狂气。陈衍论其创作:“学谢,学杜,学韩,学元、白,无所不学,无所不似,而以学晚唐者最佳。……古体务为恣肆,无不可说之事,无不可用之典。近体尤惟以裁对鲜新工整为主,则好奇之过,古人所谓‘君患多才’也。”(32)陈衍:《石遗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2-13页。晚年古体尤狂荡,“我下笔时早视千秋万岁如尘埃……他人下笔皆欲人赞好,我下笔时早拼人嘲人骂、不畏天变兼人言……又谓我诗拉杂复鄙俚,我诗拉杂诚有之,果何句俚何句鄙?我诗虽恶人难学,似我者病学我死,强学我者必至鄙俚而后已。”(33)《读樊山〈后数斗血〉作后歌》,易顺鼎著,王飙校点:《琴志楼诗集》,第1286页。实际上晚年个别诗作令人瞠目,成败且不论,可以说是各种创作路径都尝试殆遍之后继续变化求新的一种尝试。易顺鼎作诗还有特点是极快而佳,“余以己卯(1879年)冬公车北上,取道江南。骑一驴,冒大雪入金陵城,遍访六朝及胜国遗迹,一日中成《金陵杂感》七律二十首。”(34)《琴志楼摘句诗话》,易顺鼎著,王飙校点:《琴志楼诗集》附录三,第1515页。其中佳句多为人传诵,如“地下女郎多艳鬼,江南天子半才人”“桃花士女桃花扇,燕子儿孙燕子笺”“衰柳绿连三妹水,冷枫红替六朝花”“如此江山奈何帝,误人家国宁馨儿”等。易顺鼎交游圈广泛,一般应酬之外,热衷于参加各种诗艺比拼,如联句、诗钟会、叠韵唱和等活动,比如“叠韵”经常连绵不穷,最多一次至十九叠,(35)《十九叠醇字韵赠陶见心敦复》,易顺鼎著,王飙校点:《琴志楼诗集》,第1053页。这些作品除承担交际功能外,创作者对自己诗才自负自炫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易顺鼎诗作数量十分惊人,陈衍《石遗室诗话》说不下万首,他自己说有数千首,现存近三千首。尝云:“一岁得诗三百篇”,(36)《除夕旅店祭诗》,易顺鼎著,王飙校点:《琴志楼诗集》,第202页。可谓无日不有诗,如此作诗成癖,不能不说是一种狂态,何况其尝自言:“佛力如山定,诗心比海狂。”(37)《普陀渡海登洛伽舟中作四首》,易顺鼎著,王飙校点:《琴志楼诗集》,第1079页。
另一方面是脱俗之深情。除了才子狂气之外,张灵身上脱略形骸之真性情,易顺鼎也颇有惺惺相惜之意。张灵存世诗为人称道者,如《对酒》:“隐隐江城玉漏催,劝君须尽掌中杯。高楼明月清歌夜,知是人生第几回。” 于极欢处突然转思人生无常,非深于情者岂能为此、岂堪为此?《春暮送友》:“三月正当三十日,一壶一榼一孤身,马蹄乱踏杨花去。半送行人半送春。”(38)以上两首见朱彝尊辑录:《明诗综》,中华书局,2007年,第1851页。痴立春风怅望远方,孤独送行者之愁绪与深情自然显现。临终前三日作诗:“一枚蝉蜕榻当中,命也难辞付大空。垂死尚思玄墓麓,满山寒雪一林松。”(39)前文所引易顺鼎《十二月二十四日雪中独游邓尉元墓宿圣恩寺还元阁》诗中句子即化用此诗末句,标题中“元墓”即“玄墓”,指玄墓山。后一日又作诗云:“彷佛飞魂乱哭声,多情于此转多情。欲将众泪浇心火,何日张家再托生。”(40)以上两首见蒋一葵撰,吕景琳点校:《尧山堂外纪》,第1419页。生死之际既有通脱潇洒、又有对亲人的眷恋与不舍,表面是旷达狂生,内心却充满牵挂。还有《张灵崔莹合传》里所写一见崔莹而倾心,因机缘乖舛琴瑟未谐,抱憾而逝。虽然有研究者指出黄周星所写未必属实,(41)《唐寅集》附录三,辑校者按语:“徐祯卿《新倩籍·张灵传》云:‘内无僮仆,躬操力作,饔飨不继。父母妻子,愁思无聊。’祯卿撰此约在弘治九年,监察御史方志尚未督学至苏,张灵未为斥罢之前,时唐寅年廿七岁,张灵已有妻子。又崔莹事,祝、唐、文、徐诸诗文集皆未见涉及。黄周星撰传失实。”唐寅著,周道振等辑校:《唐寅集》,第587-588页。但易顺鼎因读此传而知张灵之事,则并不一定不以为真!
易顺鼎生性多情,十五岁时刻诗词集《眉心室悔存稿》,自署号“忏绮斋”,又自号“眉伽”。其中七言乐府如:“冰蟾走入谁家楼,唤起楼中无限愁”“貂裘公子气如虹,十万金钱掷秋雨”“红泪流成无定河,香肩倚倦长生殿”,七言律句如:“眼界大千皆泪海,头衔第一是花王”“生来莲子心原哭,死傍桃花骨亦香”“秋月一丸神女魄,春云三摺美人腰”等,既见才华,又见性情。认张灵为其前身后,这种情感状态在更深层次上被确认并加强,由此去看《哭庵传》:“哭庵平时谓天下无不可哭,然未尝哭。虽其妻与子死不哭。及母殁而父在,不得遽殉,则以为天下皆无可哭,而独不见其母可哭。于是无一日不哭,誓以哭终其身,死而后已,因自号曰哭庵。”(42)易顺鼎著,王飙校点:《琴志楼诗集》,第1441页。周围师友有劝诫者,如王闿运诒书曰:“有一语奉劝:必不可称哭庵。上事君相,下对吏民,行住坐卧,何以为名?臣子披昌,不当至此。……若遂隐而死,朝夕哭可矣。且事非一哭可了,况又不哭而冒充哭乎?闿运言不见重,亦自恨无整齐风纪之权,坐睹当代贤豪流于西晋,五胡之祸将在目前。因君一发之,无以王夷甫识石勒为异也。”(43)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二),岳麓书社,2008年,第89-90页。从士大夫立身行事角度来说,王闿运所劝有理,但就易顺鼎内在心理倾向来说也实属自然。其晚年追逐梨园名角,“实甫尝以贾宝玉自命,而以一班女伶,作大观园诸姊妹观”,(44)王森然:《近代名家评传》,第137页。有不少“捧角诗”,其诗作中涉及当时名角如王客琴、刘喜奎、鲜灵芝、金玉兰、小菊芬、花元春、冯凤喜、贾碧云、梅兰芳、朱幼芬等等,其行为与诗作皆为人诟病,认为是晚年仕途失意后纵情声色。但其《寄玉俞女弟》云:“我生哀乐两无节,性天坐受情波汨。年来徇乐久忘哀,自问宜为天所绝。昔年哭母哀有余,旁人谓我同皋鱼。免丧侵寻八九载,泣血誓死皆成虚。回思往事肝肠断,却取哀情付冥悍。枯稿重开绚烂花,旷达翻成游戏观。或言末路魏信陵,或言结习明张灵。不堪马鬣伤存殁,欲借蛾眉了死生。人生大欲原难遂,强求一遂终为累。徇乐而今又两年,苦甘尝尽人间味。……”(45)易顺鼎著,王飙校点:《琴志楼诗集》,第913页。以此诗所流露之意看,晚年纵情之行为,并非全出于登徒子好色之举,其内里更多是寥落寄情、放旷自遣之意,只不过大多数人早闻其才名、早知其多情,又被他过多“非常”之举震惊,只此便是谈资,哪里还会去深究其内心动机。
易顺鼎对张灵为其前身确信不疑,甚至言“我有墓在邓尉中”。(46)《雪后徐园探梅作》,易顺鼎著,王飙校点:《琴志楼诗集》,第1202页。按:张灵葬于玄墓山麓,邓尉、玄墓紧邻,此处盖泛指。但两人可以说同而不同,最相接近者性情,具体才干,张灵偏于绘画,易顺鼎钟情诗歌,不过,他对自己不善画颇觉遗憾,“我愧前生能画今生转不能”,(47)《寒云主人梦中梦游佳山水且画之本不能画及觉忽能画且能忆梦中所画之稿属鸥客作图索余题》,易顺鼎著,王飙校点:《琴志楼诗集》,第1351页。这既有趣,又让人觉得其痴迷“前身”的状态绝非一般随便比况者可相提并论。这充分表明“暗示”虽具有局限性,并非无所不能,但“主导人的是心理暗示和自我暗示,而并非意志”,(48)埃米尔·库埃:《心理暗示力》,方舟编译,第5页。因此“前身”之思对易顺鼎所产生的心理暗示影响远比他人持久而深刻。
三、诗人追溯前身之结习
在诗文中表达追寻、设想前世前身想法并非易顺鼎独有,在诗人群体中很早便产生了这样的观念,而且这种观念的产生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更为深刻。中国原生神话传说中也有部分人物、动物死后化为他人他物的内容,如《山海经》、诸子等著作中有动物、人物变化的故事;汉晋时代的仙话集如《列仙传》《神仙传》中有变化、火化、服药登仙等事,(49)参见袁珂:《中国神话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第25-50、72-82、124-128页。但一般重在强调神奇变化,而不强调转世。追溯前身观念的产生与佛教的传入关系密切,东汉至唐宋佛经翻译渐多,唐代译经尤其繁盛,自宋以后,佛经翻译逐渐减少,但由于印刷技术的发展,佛经的传播速度得以加快。佛经的这种传播状态,对大众产生显著影响,依靠目前的数据检索条件,可以发现一种明显的趋势,涉及表达前世前身之思的说法,唐以后才较为普遍的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50)以爱如生平台“中国基本古籍库V7.0”版为例,在总库中检索关键词“前世”,共计11248条,“前身”7340条;在文学类中检索,“前世”4073条,“前身”5424条。“前世”“前身”两个关键词比较,前者含义、范围均大于后者,并不单纯表达个体人生的情况,有时是针对整个社会、时代而言;后者则更具体,专就个体人生而言,故本文重点考察后者。关于“前身”在“文学类”中的检索结果显示唐以前仅有5条记录。诗人对前身的追寻方式,大致可分为两类。
第一种类型显著受佛教转世轮回思想的影响,(51)《法华经·方便品》曰:“以诸欲因缘,坠堕三恶道,轮回六趣中,备受诸苦毒。”《心地观经》(三)曰:“有情轮回生六道,犹如车轮无始终。”《观佛三昧经》(六)曰:“三界众生,轮回六趣,如旋火轮。”《身观经》曰:“循环三界内,犹如汲井轮。”《观念法门》曰:“生死凡夫罪障深重,轮回六道。”参见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中国书店,2011年,第2638页。在以上谈及“轮回”概念的佛经中,《法华经》译出最早,先后汉译过六次,现存三个译本:西晋竺法护译《正法华经》、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隋阇那崛多译《添品妙法莲华经》,前两个译本影响至大,同《般若经》《大般泥洹经》鼎足三立,构成了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思想的经典支柱。《法华经》后又为天台宗基本经典,影响广泛而深远。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19页;严耀中:《论隋以前〈法华经〉的流传》,《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具体表现为因异事、因梦境、因占卜扶乩等活动而有所确认。如《明皇杂录》卷上载邢和璞伴房琯游览僧寺,掘地得娄师德与永公书,而知前身为智永禅师。《扪虱新话》上集卷一载张方平游琅琊山寺,得经卷读偈语而知前身事。《春渚纪闻》卷一载张商英因修缮李长者古坟,得大盘石上有“天觉”二字,以为长者为其前身;同卷“坡谷前身”条记载名叫“清老”之占卜者指出苏轼前身为五祖戒和尚(师戒禅师);卷六“寺认法属黑子如星”条载苏轼游寿星寺遂悟前身为山中僧。(52)何薳撰,张明华点校:《春渚纪闻》,中华书局,1997年,第5、93页。《冷斋夜话》“梦迎五祖戒禅师”(53)惠洪著,李保民校点:《冷斋夜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3页。条又载苏辙被贬江西高安(古称“筠州”)时,与交游的云庵和尚和聪禅师做了同一个梦:出城迎接五祖戒禅师。结果东坡书来将至高安,三人出城相迎,东坡又自言八九岁时尝梦其身是僧。惠洪甚至把苏东坡的文学天才也归功于其前身:“东坡盖五祖戒禅师之后身,以其理通,故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而成文。盖非语言文字也,皆理故也。自非从般若中来,其何以臻此?”(54)惠洪著,周裕锴校注:《石门文字禅》,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4033页。后人对此说也颇感兴趣,如李纲云:“东坡夙世乃戒老”,胡维霖云:“前身五祖来筠州”。(55)《东坡谪英州以书语所善衲子曰戒和尚又疏脱矣读之有感》,李纲:《梁溪先生文集》,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215页。《归舟次九江追忆子瞻在黄逸事感赋》,胡维霖:《胡维霖集·檗山吟》,中国基本古籍库,明崇祯刻本,卷一。陈亮自言少时名“汝能”,因其祖父梦状元童汝能转世其家,(56)《告祖考文》,陈亮著,邓广铭点校:《陈亮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7年,第405页。陈亮后虽改名,但状元转世的心理暗示作用十分明显,其一生历经坎坷,但始终未放弃科举,终于在五十一岁时高中状元。《贵耳集》卷中载李弥逊前身为逊道人。《困学斋杂录》载杨奂少年时自悟前身为紫阳宫道士。《坚瓠集》卷三载王守仁游僧寺,遇入定僧人而知为前身。《坚瓠集》中还有一些关于普通文人前身事的记载,《坚瓠集·七集》卷二载周尧佐因夜梦知前身为友鹤山人;《坚瓠集·广集》卷一载金雪洲因扶乩者言知前身为李煜,卷二载王铎前身为蔡襄。《蕉轩随録》卷七载朱珪自以为前身为文昌宫之盘陀石等。
以上仅从与易顺鼎类似的得到某种启示后自己有所觉悟的角度,列举数条关于诗人探究前身的记载,实际关于转世之说更大量的是母亲怀孕或孩子降生时做异梦、神灵转世、动植物转化等类型,各种记载在史书、笔记、小说中无虑成千上万条。谢肇淛云:“前身之说多矣,事既渺茫,语多附会,但取俶奇可喜,不必论其有无。如平子后身为中郞,徐陵后身为知威,武侯后身为韦皋,五戒后身为子瞻,邓禹后身为淳夫,李德裕后身为赵鼎,才名功业颇足相当。至于许玄度之为萧詧,永师之为房琯,谢灵运之为边镐,马北平之为马仁裕,颜延之之为潘佑,牛僧孺之为刘沆,武夷君之为杨亿,玉京之为王素,已自堕落一层。刘公干为昏愚小吏,泽公为浣衣妇人子,羊祜出于邻家,阿练本于沙门,又何轮回之悬绝,至是也明。徐国公鹏举为岳武穆托身,冯宗伯琦为韩忠献托身,然皆功业不迨远甚。王文成前身为僧,差不失故步耳,要之士贵自竖立耳,前生后生可寘勿论,屠纬真苦谭此说,亦通人之蔽也。”(57)谢肇淛:《文海披沙》,中国基本古籍库,明万历三十七年沈儆炌刻本,卷六。虽说追寻前身事实属渺茫,但奈何世俗偏好此道,屠隆这样学问通达者不能免俗,何况他人。诗人自身追寻或者世俗一般人谈论名人前世的现象,反映了人们对个体存在真相的探寻欲望——“秖我前身是阿谁”,(58)《读诸家诗》,杜荀鹤:《杜荀鹤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88页。以及对佛教“轮回”观念广泛而深刻的接受。“轮回”观念被较为普遍地接受还可以从一个形象的运用看出来,即“金粟如来”,(59)维摩居士之前身为金粟如来,见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中国书店,2011年第1342页。维摩居士具有超越寻常的智慧辩才和无限灵活的善权方便,在中国士大夫中接受度很高,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04-407页。尤其元明清以来诗人大量采用这一形象表达对前身的追寻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想法。如元顾瑛自号金粟道人,其所建玉山佳处(玉山草堂)其中一景名“金粟影”,并修造生圹“金粟冢”,其友人有诗云:“自缘金粟悟前身,要接曹溪一线水。”(60)《河南陆仁良贵和韵》,顾瑛辑,杨镰等编校:《玉山名胜集》,中华书局,2008年,第345页。后人亦有诗云:“可怜金粟托前身,隐君之意不在酒。”(61)《金粟道人像歌》,法式善著,刘青山点校《法式善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328页。其他诗人涉此形象的诗句极多,如董其昌:“金粟前身语非妄,膏泽已遍阎浮提。”陈函辉:“前身金粟后青莲,给与寒山一片石。”顾起元:“多病逢君深自省,了知金粟是前身。”王世贞:“莫笑净名居士病,前身金粟老如来。”吴国伦:“前身金粟知非偶,辛苦良当了世缘。” 戴敦元:“青山枯骨犹余恋,金粟前身若等闲。”樊增祥:“佛家金粟前身是,汉殿天香入骨清。”黄图珌:“玉堂当代诚无敌,金粟前身自不同”(62)以上八条见:《问政山歌为太傅许老师寿》,董其昌著,邵海清点校:《容台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第11页。《华顶放歌》,陈函辉:《小寒山子集》,中国基本古籍库,明崇祯刻本,不分卷。《诸葛山人》,顾起元:《遁园漫稿》,中国基本古籍库,明刻本,戊午卷。《元驭学士于新观种花挑野菜前后戏呈得十二首》其三,王世贞:《弇州四部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续稿卷二十三。《羽王自永寿寺移居永兴寺道中有作邀予和之》,吴国伦:《甔甀洞稿》,中国基本古籍库,明万历刻本,卷二十六。《太白楼》,戴敦元:《戴简恪公遗集》,中国基本古籍库,清同治六年戴寿祺钞本,卷三。《次韵监临院桂中秋作》,樊增祥著,涂晓马等校点:《樊樊山诗集》,第275页。《赠熊太史澹冈》,黄图珌:《看山阁集》,中国基本古籍库,清乾隆刻本,卷五。等。
第二种类型总体来说是出于追慕前人。或直接表达倾慕之意,或从才性出发追寻前世,或标榜某一方面的突出特点等,既有写自己的,也有夸赞别人的。
直接表达倾慕之意,如黄滔:“定应云雨内,陶谢是前身。”苏轼:“白发苍颜自照盆,董生端合是前身。”“前身陶彭泽,后身韦苏州。”黄庭坚:“前身寒山子,后身黄鲁直。”秦观:“翩翩曾公子,子猷定前身。”惠洪:“前身定是赤头璨,风帽自欹麻苎衣。”杨万里:“今日犹迟傅岩雨,前身端是谢宣城。”周紫芝:“试为支郎吐幽句,了知长吉是前身。”胡祗遹:“醉墨淋漓风雨笔,只应张翰是前身”等。(63)以上九条见:《贻李山人》,黄滔:《黄御史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次韵子由三首·东楼》,张志烈等校注:《苏轼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909页。《次韵黄鲁直书伯时画王摩诘》,张志烈等校注:《苏轼全集校注》,第3327页。《戏题戎州作予真》,黄庭坚著,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63页。《次韵曾存之啸竹轩》,秦观著,周义敢等笺注:《秦观集编年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155页。《至海昏三首》(其一),惠洪著,周裕锴校注:《石门文字禅》,第2535页。《谢傅宣州安道郎中送宣城笔》,杨万里著,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中华书局,2007年,第392页。《次韵子雍同达书记游安林》,周紫芝:《太仓稊米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六。《武元直风雨回舟图》,胡祗遹:《胡祗遹集》卷七,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177页。类似的表达在唐以前的作品中并不多见,唐以后则数量极多,所倾慕者包括历史上实有人物、泛指身份的某一类人、神话传说人物、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等。除去前边例子中所提及者,其他历史人物如:弈秋、范蠡、黄石公、贾谊、张骞、卫青、东方朔、赵飞燕、苏武、王充、祢衡、王粲、刘桢、虞翻、石崇、阮籍、支道林、孙绰、王献之、陶弘景、智永、李靖、李淳风、李白、杜甫、白居易、陆羽、韩愈、卢仝、杜牧、李商隐、陆龟蒙、苏轼、陆游等。并称者如:唐许、屈贾、许郑、羊陆、元白、贾孟等。泛指身份者如:小乘僧、大乘僧、尘外人、老阇梨、道人、大比丘、出家儿、云水僧、老僧、野僧、毳衲僧、庵中僧、荒山僧、写经僧、比丘尼、阿罗汉、优婆塞、瞿昙、武陵樵、武陵渔、渔父、沧海客、江南客等。神话传说中人物如:姑射、赤松子、广成子、丁令威、散花仙、彭篯、玄都眷、蓬莱使、麻姑、阿环、萼绿华、杜兰香、宓妃等。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如:木兰、柳毅、步非烟、红拂等。
也有从才性出发而追寻前世者,如王维:“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64)《题辋川图》,《王摩诘文集》卷十。王维著,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第477页。这一提法影响极大,历代诗人、艺术家均极感兴趣,从唐代到清代以来,不下60种著作提及或直接用、化用此句,已成为一种具有共识性的话题,如王世贞:“吴兴王孙妙自知,不讳前身为画师。”吴宽:“良工待诏金门里,高生前身应画师。”徐熥:“自堪意气称吾党,不但前身是画师”(65)《赵松雪重江迭嶂图歌》,王世贞:《弇州四部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十一。《高克明溪山雪意图》,吴宽:《家藏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四。《赠胡外史》,徐熥:《幔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三。等。与王维这一思路相同者,也有人在诗歌里提及前身为卫夫人、顾恺之、曹霸、韩干、萧悦、张旭、范宽、郭熙、李公麟、米芾等。与王维这一提法几可比肩的是陈与义的“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66)《和张规臣水墨梅五绝》其四,陈与义著,吴书荫等校点:《陈与义集》,中华书局,2007年,第57页。从画家才性能把握对象之实质而非表象的角度表示赞赏,这一提法自产生之后至清末,有不下40种著作收录、应用、化用此句。
还有一类以“前身”之说追慕前人实际上是一种自我风格、风度的标榜,如白居易:“世说三生如不谬,共疑巢许是前身。”王禹偁:“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黄庭坚:“见我好吟爱画胜他人,直谓子美当前身。”“自疑是南岳懒瓒师,人言是前身黄叔度。”李纲:“泽畔行吟觉憔悴,前身疑是楚三闾。”陆游:“水品茶经常在手,前身疑是竟陵翁。”陈普:“前身曾作孔子孟子为人憎,也曾为禹为稷为人爱。”汪莘:“欧苏寻后辈,郊岛是前身”等,(67)以上八条见:《赠张处士山人》,白居易撰,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1512页。《前赋春居杂兴诗二首间半岁不复省视因长男嘉祐读杜工部集见语意颇有相类者咨于予且意予窃之也予喜而作诗以自贺》,王禹偁:《小畜集》,吉林出版集团,2005年,第85页。《观崇德墨竹歌》,任渊等注,黄宝华点校:《山谷诗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174页。《张子谦写予真请自赞》,黄庭坚著,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第1013页。《得报以谪降官不许同处一州自鄂渚移居澧阳有感》,《梁溪集》卷二十二,李纲:《梁溪先生文集》,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184-185页。《戏书燕几》,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949页。《醉吟(次拙轩和诚斋之作)》,陈普:《石堂先生遗集》,中国基本古籍库,明万历三年薛孔洵刻本,卷十五。《方壶自咏》,汪莘:《方壸存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均以标举某些人物来写出自己的特点与状态,是诗人喜用的一种表达手法。
结 语
诗人世界中的各种现象,从单个的、分离的、短时期的角度去观察,往往无甚特殊之处,至多不过觉得是某一人物一时的突发奇想、灵感闪现,但是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中获取大量样本前后联系观察,便可获得不一样的认识。对于诗人持有“前身”观念的考察便明显体现了这种区别,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到,诗人讲论“前身”在中国有漫长的历史,也有鲜明的特点:一、追溯“前身”的观念受佛教文化影响显著多于本土文化,唐宋以后记载数量增多,且明显地表现于诗人的创作中。二、著名诗人谈论或追溯“前身”的诗作、轶事,更易成为前后传承不衰的经典话题。如王维、苏轼、陈与义等人的例子。三、追溯前身可以说是诗人世界中一种特殊的文化行为。文化心理学者总结“文化行为”具有:“人为形成”“偶然产生”“有历史性和延续性”“带有随意性”“具有稳定性”“是形式化了的”(68)参见J.R.坎托:《文化心理学》,王亚南、刘薇琳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9-199页。等主要特征,这虽然是针对人类社会普遍的文化行为而言,但具体到中国古代诗人津津乐道“前身”这个行为上,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追溯前身”这个现象显然属于人为形成,而且确属偶然产生,在谈论的人多了之后便自然传承并延续,其中大量的表达具有相似性,故而又具有大致稳定而形式化的表现,诗人在谈论和运用时也的确具有随意性,其中不少人极为确信,产生强烈的心理暗示,并由此而对自己的文学创作、立身操守、行事风格等产生明显影响;多数人则将之当作雅趣话题或特殊的表达方式来看待。像易顺鼎这样在生命的早期就确立“前身”观念且通过各种方式加以追寻印证并受到强烈影响,在中国古代诗人群体中是非常突出的,可谓诗人世界中这一文化行为的一个典型例证。